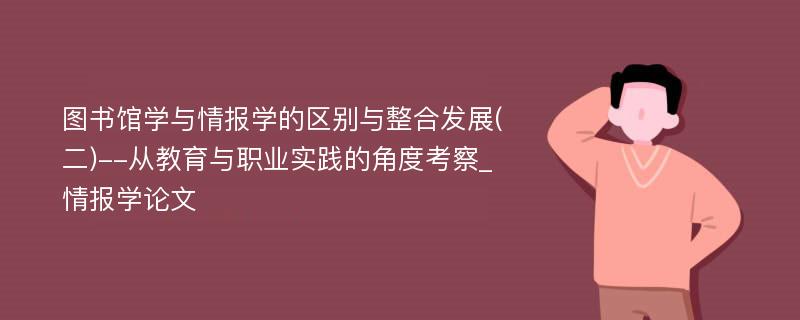
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分野与融合发展(下)——从教育和职业实践方面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学论文,分野论文,图书馆学论文,职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我们在《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分野与融合(上)——对相关理论探讨的考察》(见本刊2007年第5期)一文中对各国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之间的冲突和融合过程在理论上的争论和发展进行了详细论述。但是,在实际发展中,理论研究是与教育实践变革和职业实践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三者是无法分割的。伴随着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理论上的融合发展,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开始出现在同一教育机构之中,而这种教育的合流进一步促进了理论探讨中的争论和主流观点的统一,无论是理论探讨中的冲突和融合,还是图书馆情报学(LIS)教育合流与范式转变都受到图书情报职业实践的深刻影响。为此,本文将对图书馆学和情报学融合发展中教育和职业实践的发展及影响进行分析,以进一步理解二者的分野与融合发展过程。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美国在LIS教育上基本上一直处于引领地位,而其范式的转变也尤为明显,本文中的事例主要取自美国,对其他国家仅稍微涉及。
2 图书馆学情报学的教育合流和范式转变
如果说在图书馆学情报学融合发展上理论探讨争论比较大,各国发展道路也存在较大差异,发展脉络较为混乱。但是,在图书馆学和情报学教育领域,在世界范围内二者的合流都是主流现象,其发展脉络也比较清晰。特别是在美国,从图书馆学院到图书馆情报学院,再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信息管理或信息研究院系直至目前的I-Schools潮流(表1直观反映了这种变化),从中可以看到似乎有一个从图书馆向信息范式的转变。伴随着这一范式转移的则是图书馆相关课程的减少及学者们对图书馆教育危机等问题的争论。
2.1 从图书馆学院到图书馆情报学院(LS-LIS)
情报学诞生之前,美国单一的图书馆学教育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的发展:“图书馆业务进修和现场训练时期(1887年左右)、规划图书馆学院时期(1887-1919)、图书馆学院的认定和发展时期(1919-1939)、课程和学位发生变化时期(1940-1960)”,[3]教学内容主要是围绕图书馆工作和不同类型图书馆服务进行,教育理念逐渐成熟。
1960年代情报学诞生后,情报学教育被纳入图书馆学院与图书馆学教育一体化发展,图书馆学教育的改造和变革成为世界图书情报教育的主流。20世纪60-70年代,尽管图书馆相关内容仍然是教育的核心,但情报学内容已开始渗透进课程体系。1958年西蒙斯大学图书馆学院增加了“情报学导论”和“档案管理”课程,到1967年,美国图书馆协会教育委员会认可的44所学校中,设一门或一门以上情报科学或计算机科学方面课程的有25所,1968年增加到35所。[4]一些先行院校开始更改图书馆学院(系)或专业名称,1964年美国匹兹堡大学图书馆学院改称图书馆情报学院,并分设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专业。1968年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改图书馆学专业为“图书馆情报学专业”。[5]
表1 美国图书馆学与情报学教育从LS-LIS-I-Schools的发展表列
时间
院(系)名称课程设置 学位授予
1887
哥伦比亚图书图书馆经营、书籍的保管、书目、分类法、 培训性质
馆管理学校 目录著录、参考咨询等
图书馆学概论(或原理)、编目与分类、图
1920年代图芝加哥大学
书或资料的选择、参考资料、图书史和图图书馆学硕士和
书馆学院
图书馆学院 书馆史、图书馆行政管理、公共图书馆、学 博士学位
院和大学图书馆、青少年读者服务、专业
图书馆研究、医院图书馆研究和社区服务
图书馆学核心课程外增加情报学课程,如
1950-1960 部分改名情报学基础、知识组织理论、计算理论、计
年代
LIS学院 算机模拟、数据处理、图书馆自动化、图书 图书馆学硕士和
馆管理、系统评价、行为科学、统计学、数 博士
学[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订的LIS教育大纲:
社会通信、用户调研、情报源、情报/数据
贮存与检索组织、专题研究或学位论文、
1970-1980 图书馆情报 选修(图书馆与情报业务的历史研究、国LIS硕士和博
年代
学院际性比较图书馆学、历史性书目、印刷及士;情报学硕士
图书、出版业及书籍业、档案管理与记录和博士
文献管理、图书馆教育、电子计算机程序
设计等)等七大板块[2]
去“L”化、 I-Schools课程围绕人、技术、管理和政策 双学位、合作学
1990年代以“information” 设立,如:计算、网络、信息系统、系统分 位;图书馆学硕
来 前移以凸显 析、信息机构、数据库管理系统、信息分
士;LIS硕士;信
信息析、电信和信息政策;安全、项目管理、人 息学硕士;情报
21世纪 机交互、电子商务技术、网页设计、团队工 学和交叉领域博
I-Schools潮 作、灵活学习等。此外,大多I-Schools保 士
流 留图书馆学模块
资料来源:自己整理,参考了I-School的相关论述
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日本等国普遍出现了以“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并列命名的教育机构或专业,如1973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将图书馆服务学院改为LIS研究生院,其博士研究计划包括了三大领域:信息资料的选择、采集、鉴别和保存;信息存储、检索、解释、传播和利用;图书馆和信息中心的管理;1979年日本创办“图书馆情报大学”。截止 1990年,美国60所被正式认可的图书馆院系中有53所院系名称中融入了“信息”或“信息研究”字样。[6]伴随着学院名称的改变,则出现了更实质性的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学位授予的调整。1970年代中后期,学者研究指出应把情报学科目与传统内容统合,并提出彻底重筑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学院也要成为培养情报专家的场所。[7]在此背景下,大多数图书馆学院拓宽培育目标,从培养图书馆员和档案馆员转向了注重培养能满足商业和政府机构信息管理需求的人才。课程结构随之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截止1982年,62所图书馆学校大幅度增加了情报学的科目和计算机有关科目,尤以情报检索和编程科目最多。[8]1985年美国图书馆情报学教育协会强烈提议,将来的图书馆学教育要在本科课程里学完情报学科目,并把这个作为攻读硕士课程的必要条件。同时,情报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以及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硕士和博士合二为一的学位开始确立。
情报学方面课程比重和学位增加,改变了图书馆员的知识结构,增强了图书馆学院系毕业生适应未来技术变化的能力以及就业适应面。此外,情报学在与图书馆学融合的同时还向其他学科领域拓展,出现了若干新兴分支学科,如信息经济学、信息社会学等。[9]但是,情报学等课程的引入是伴随着图书馆学核心课程的萎缩和改造的,这其实为后来学者所称的“图书馆教育危机”埋下了伏笔。同时,由于社会信息环境的不断变化,LIS教育没有扭转传统图书馆学院走向弱势,从1978年美国俄勒冈图书馆学研究生院关闭开始,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图书馆学院关门风潮。截止1992年,全美有将近20所图书馆学院关闭,很多院系被迫与其他系或项目组(如信息技术或计算机系、传播系等)合并。[10]对此,美国UIUC图书情报学院前院长Jeffrey Katzer说:LIS专业受到了挑战,因为发生了一个基本转变,从一种以图书馆为中心的“托勒密”信息宇宙转变为一种动态的以信息为中心的“哥白尼”信息宇宙……所有组织对信息管理的需求迅速增加;图书馆仅仅是信息产业的一部分,对社会上许多行业来说,图书馆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图书馆员在信息工作者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信息管理所要求的知识和技能正在从边缘部分转向我们领域的核心部分,而不仅仅是交叉学科的问题。[11]
2.2 从图书馆情报学院到信息学院(LIS-I-Schools)
面对上述变化和挑战,图书馆情报学院出现了新一轮的变革,院系名称也再次发生更改,出现了去“图书馆”或“信息”前移,以突出“信息”,LIS学院开始突破机构取向模式,转向“信息”为中心的模式。1993年伯克利加州大学图书情报学院首先开始改革,1995年改名信息管理和系统系,强调以高深的学术内容吸引一流教师和有能力的学生,他们毕业后成为有关领域或行业的领导者。截止2000年,合计有15所图书馆情报学院更名,约占总数的1/3。
伴随院系更名的则是LIS院系课程体系的进一步修改或与其他院系联合办学或机构重组。首先,在课程结构上,北美图情教育协会统计表明,课程越来越多学科化或交叉学科化,加入社会、经济等方面内容,去掉和图书馆相关的目录、图书馆学、编目等,转向对信息研究,如人—机交互、知识管理、信息构建、信息经济学、知识经济学等。[12]其次,学位授予越来越不集中。例如长岛大学帕尔玛图书情报学院自60年代起一直提供图书馆学和情报学两种硕士学位,1992-1993年设立了合二为一的“图书馆与情报学理硕士学位”,1996年始又引入了“信息传递理学士”和“信息研究哲学博士”,本科和博士计划的知识范畴都比图书馆学甚至情报学宽泛。[13]到1999年美国ALA认可的硕士学位中,授予LIS或图书馆与信息研究硕士或单独的情报学硕士的学院有23个,而授予的博士学位大都属于情报学及交叉学科领域或图书馆情报学、通讯信息与图书馆研究。[14]此外,图书情报学院与计算机信息管理、经济信息管理等专业合作办学趋势明显。美国Kellogg董事会直接资助德雷克塞尔、密西根等4所大学图书情报学院教育改革,其重要举措之一即加强与计算机科学、工程学等学科专业合作。德雷克塞尔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提出“重新定义21世纪信息专业人员的含义”,新的教育计划设立了LIS理学硕士、信息系统理学硕士、软件工程理学硕士,商业管理学院也加强了与LIS学院合作,共同举办合作学位或双学位。正如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研究委员会所说的,“可以包含在信息研究课表内的许多课程已由校园内其他院系开设,图书馆与信息研究学院成功的关键在于能把这些课程与图情课程积聚为一股力量,借以提供一个完整的一体化的项目”。[15]这种合作与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信息教育的整合趋势,而这或许也是之后I-Schools兴起的重要原因。
在90年代后期变革的基础上,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一些著名LIS学院又掀起了I-Schools运动。伊利诺斯大学、华盛顿大学、密歇根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北卡罗莱那大学等知名大学的LIS学院宣称自己为I-Schools,2005年通过章程成立了I-Schools联盟(The I-Schools Group),目前共有20所大学成员,多数为ALA鉴定合格的LIS学院,也有几所偏重计算机科学和技术的学院。[16]目前,在欧美一些国家I-Schools运动都在发展,有学者认为可能继续为LIS学院带来“身份危机”,[17]有学者认为“这个 I是信息技术、信息科学而非情报学教育”,[18]图书馆界有识之士则发出了“图书馆教育危机”(Library Education Crisis)的呼声,并得到了图书馆学院教师和博士研究生的认同。信息学院则认为不存在危机,“我们的专业正在兴旺,目前LIS教育的学生比以往更多”。那么,如何认识I-Schools,其将引领LIS教育走向何处?其与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研究和教育整合的关系?如何认识图书馆教育危机?
2.3 对I-School发展趋向和图书馆教育危机的分析
2.3.1 对I-School的分析
目前美国的I-Schools运动仍处于探索之中,从其颁布的章程、一些I-Schools领导者的访谈录以及这些学院的课程、教学人员、教学项目等进行分析,可以形成如下认识。
首先,在I-Schools的身份识别方面依然很困难,多样化的信息教育(如涉及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软件工程、电信和图书馆学等领域)很难归类,目前基本达成的共识是强调信息、技术和人三大因素,以此为纽带将信息领域教育整合在一起。雪城大学I-School院长反复强调,无论如何称呼这些学院“信息、信息研究或信息科学学院”,其中“信息”都是最重要的,I-School中“I”是信息而不是技术,通过信息扩展人们的能力,增加服务的价值,I-School的倾向是人、技术、服务、管理,通过它们来整合information science这一领域。[19]从这一点来看,I-School似乎并不像国内某些学者认识的“I是信息技术,是走向技术的教育”,而是一种基于信息、技术和人的information science教育的整合。但是,I-School对技术的重视也是有目共睹的。这从这些学院开设的教学项目和课程、授予的学位以及研究人员的背景及研究方向上都可以反映出来。
其次,在突出信息范式下,目前大多数I-Schools对图书馆教育依然十分重视。除了伯克利、Georgia Tech和UC-Irvine以及Penn State外其他I-Schools都授予LIS硕士或博士学位。其中伊利诺斯大学和北卡罗来那教堂山分校的图书馆学教育十分优秀。[20]伊利诺斯大学在平衡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上做得比较成功,早在1998年美国图书馆与情报学教育协会年会上,其院长Leigh Estabrook教授在介绍教学改革经验时就提到,一直努力不把图书馆学和information science分开划分课程(学校图书馆领域除外),同时尝试把对基本技术和技能的学习作为应具备的基本素质置于课程教学内容之外。[21]目前其硕士课程从7个方面反映LIS的不同内容:历史、经济和政策;信息组织与知识表达;信息系统;管理与评价;资源、利用与信息用户(包括馆藏发展等);社会、集团与组织信息;青年文献与服务。
再次,I-Schools强调学术研究,重视确立其在学术界和知识界的地位。“I-Schools成员都是在研究或博士生教育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学院,强调高层次研究”,“致力于培养未来的研究者(通常为研究型的博士点)来引领信息职业领域的发展”。[22]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如果从历史视角来看,I-Schools的出现可以说是不同领域的information science教育趋向整合,信息范式走向主导的必然。从上文可知,information science项目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当时主要是由传统学科领域吸收和附加的。Saracivic曾指出,“在美国information science教育存在两种模式,一种为谢拉模式,即将information science项目教育附加于图书馆学院;一种为索尔顿模式,将information science主要是信息检索教育附加于计算机科学系,前一种倾向于以人文和用户为中心,后者倾向于以系统、计算和算法为中心,两者各自独立没有整合。”[23]Debons对比了1970年代和如今I-School的两次I-conference,指出“在当时information science不得不包容进这些不同的传统领域存活下来,这带来的影响即学术界趋向于通过传统学科来看待information science,并争论information science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性工程领域或仅仅是图书馆学和文献学的延伸,而不是依据其创新性和独特性。但是,I-Schools的兴起,已使其成为为其他不同学科团体提供基础的家,已经从1960-1970年代将information science安置到哪个学术领域转变到今天I-Schools决定应包括哪些学科?哪些与I-Schools的框架相吻合,旧的学科在新的不断变化的学科之中扮演什么角色?对其定义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从来源概念看待。”[24]如果从以往LIS被迫与其他学院合并、联合似乎是从大学内争取教学资源以维持自己的生存角度看,目前I-School的成立似乎表明information science在学术界和知识界的地位在提高,但是其身份识别问题依然存在,与信息领域其他学科的合作和竞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继续模糊它们的界限,从而使自己识别性更差。
2.3.2 对图书馆教育危机的分析
在以上叙述中我们已经提到70-80年代图书馆学院关闭、重组、课程和教学项目的改革已经隐藏着图书馆教育的危机,2003年Michael Gorman明确提出了“各国特别是在美国图书馆教育存在危机”。他指出,美国各种类型的图书馆达117000余个,很多图书馆员将在5-10年内退休,需要一批热情且有学养的年轻馆员替补,但是目前LIS学院中许多教师对传统的使命、制度及图书馆价值失去信心,对图书馆之外的领域更有兴趣,或者训练他们的学生在图书馆以外的领域就业,原来的图书馆学院已经变成了信息科学和信息研究学院;图书馆学院的教学内容与大多数图书馆实践脱节,如图书馆长认为是图书馆教育中心内容的编目、参考咨询、馆藏发展等课程已不再是目前LIS课程的中心;美国几个有声望的研究性大学已放弃LIS教育,这导致对图书馆课题研究质量的下降。[25]
国外学者对于“危机论”仍存在异议,在对国外图书情报学院的课程调研后可发现,尽管出现了这种去L化,增I或I迁移的举措,但是即使在I-Schools中大都仍保留着图书馆模块(library program),这是衡量图书馆学实质存在的依据。不过,图书馆课程及教育信息化倾向却不容质疑,如果我们可以用危机描述 Gorman先生所述现象,应该说,这是图书馆教育范式转向“信息范式”的必然结果,其实质或许如我国学者叶继元指出的教育定位问题,[26]即为什么培养人才——为信息产业还是为图书馆培养人才。这是因为,在西方图书情报学教育界一直存在着信息范式和图书馆服务范式之争,信息范式支持者认为,图书馆职业只是信息职业的一个“子集”,传统图书情报学硕士教育是不适宜的,他们要求图书馆重视“信息管理职业”的要求,目前这种旨在为图书馆培养学生的专业教育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因为多数课程没有对“信息”管理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此思想指导下,一些院系将以图书馆为方向的课程改造为“信息管理”课程,有的开设了独立的信息研究计划,(如雪城大学),另一派认为把“图书情报学”改造为“信息管理”忽视了这一事实——即图书馆职业包容许多信息科学或信息技术无法触及的领域,如文化知识培训,成人教育,文献保管保护,版本鉴定,文本选择及书目教育。尽管这些领域都可利用计算机技术,但并不仅仅依赖计算机技术。[27]那么,从70-80年代图书馆学院关闭原因可以看到仅仅针对图书馆培养人才、封闭式的教育、不重视高质量研究,图书馆学院无法进一步获得发展,70年代之后的改革后融入information science并向技术转变确实带来了招生和就业的繁荣。转向信息范式后 library program与其他information program如何协调发展,这确实是个两难的问题,值得继续探索。
图书馆教育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已引起美国图书馆学界人士的积极关注,ALA新任主席Leslie Burger认为当前世界上图书馆教育与信息领域其他事物一样处于快速变动中,目前ALA打算创建新的认证标准来影响这些变化。例如,定义图书馆教育的核心要素以及社会所期待的LIS研究生院的学生应具备的能力;现实地思考21世纪图书馆所需人才的教育水平及继续教育类型,确保新培养的人才具有最新的、熟练的工作技能;通过图书馆教育灌输给学生职业核心价值,使学生理解图书馆服务的基础,传授学生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以促使下一代图书馆的转变。[28]
3 职业实践对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与教育的分野与融合的影响
从上文的叙述可以看到国外图书馆学发展经历了从图书馆学到图书馆情报学及如今信息范式凸显,而教育上也经历了从图书馆学院到图书情报学院再到I-Schools的发展,其中information science的地位不断突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演变过程?如果想更深刻地认识这一问题,我们还必须回到图书馆职业实践,或许正是LIS研究和教育与图书馆实践的密切关系,以及图书馆职业实践一直在发生的各种变化才使得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分野和融合及范式转变有了根基。
3.1 图书馆服务范式和信息范式之对立对图书馆学情报学融合的影响
根据美国学者雷蒙德(Boris Raymond)的研究,图书馆界长期存在两种颇为对立的职业范式和争论,即“图书馆服务范式(library service paradigm)”VS“信息范式”(information paradigm)。[29]图书馆服务范式是19世纪中后期随着现代图书馆职业出现而出现的。20世纪后期,在信息社会迅速发展下,图书馆服务范式开始受到来自图书馆界内外的很多批评,批评者认为,首先,这种范式的视角局限于图书馆这一社会机构,忽略了更广泛的社会需求,这些未满足的社会需求为其他信息职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导致一些“图书馆地盘”的沦丧,图书馆职业在缩小了的地盘上很难避免走向萎缩;其次,图书馆服务范式中的图书馆员过于保守,这种‘职业性格’导致他们地位低下、报酬羞涩,对职业队伍缺乏足够的吸引力;此外,信息技术从根本上说是信息处理技术,对新技术的应用必然要求图书馆职业更加关注信息及其管理,拒绝这种变化会导致图书馆职业落伍于新技术发展,从而导致其社会地位进一步边缘化。因而,传统的图书馆服务范式已不能适应新的社会背景和技术条件,已不利于图书馆职业的发展,必须改造而采用信息范式。信息范式是指体现在各类型专业图书馆和信息中心工作中的范式,特征即注重情报交流过程,注重新技术的应用及从职业外部吸收新理论。其起源可追溯到19世纪末出现的专业图书馆(special libraries),它们服务着少数专业化的工程技术人员、商业人员和政府官员,视自己的使命为向具体用户提供具体准确的情报,如事实性数据和书目数据。20世纪初,在这些专业图书馆活动和科研机构文献活动基础上产生了以科技文献的加工、整理、检索为主要内容的“文献运动”(documentation movement),到20世纪中期,随着“文献运动”的专业协会在英美更名为情报学会,信息范式渐趋成熟。此后,随着信息被视为社会的重要资源和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信息处理,越来越多的出身于专业图书馆和文献运动的人员把自己视同“信息管理人员”而非图书馆员。[30]
如果将图书馆界这两种职业范式对应于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分野和融合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这两种范式的对立冲突很大程度上带来了情报学的诞生以及之后LIS研究和教育的信息范式转变,其中主要表现如图书馆学研究的非机构化倾向和教学的信息化改造。情报学诞生后,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图书馆学研究“淡化机构身份”的倾向表现得相当强烈,如前边提到的交流学派将图书馆学定义为“研究图书馆中情报交流过程的学科”,美国图书馆协会将图书馆学定义为“为满足用户群的信息需要和需求,对记录信息进行选择、获取、组织和利用的知识与技能”。[31]20世纪80-90年代,图书馆学领域的未来学派和技术学派多次预言实体图书馆的消亡、图书馆职业的“非机构化”,如兰卡斯特认为,以非机构化(deinstitutionalized)、无纸的、信息管理范式将取代以机构和纸质文献为基础的、传统图书馆服务范式。[32]在教育领域,对信息范式的推崇则导致了LIS学院产生以及90年代以来一些院系将以图书馆为方向的课程改造为“信息管理”课程或开设独立的信息研究计划 (如雪城大学)乃至今天的I-Schools运动、图书馆教育危机的出现。
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两种范式的未来发展也将决定着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研究和教育融合发展趋向。尽管目前在实践、研究和教育领域向信息范式的转变是有目共睹的,如LIS研究和教育中突出信息,有的国家如英国情报科学家协会和图书馆协会合并等,但是图书馆职业毕竟具有信息范式所不能涵盖的内容,如职业精神、概念体系、用户需求(如文化氛围、学习空间、娱乐需求)和功能构成(教育、道德、美学)、核心价值等,[33]也没有迹象表明实体图书馆会消亡,图书馆有识之士也在积极应对图书馆教育中出现问题,因而,未来图书馆学情报学融合发展和范式转变之路还取决于多种力量的博弈和塑造。
3.2 专业教育领域学科与实践的联系对图书馆学情报学融合发展的影响
除了图书馆职业内部“图书馆服务范式”和“信息范式”的冲突之外,LIS教育作为一种专业教育与职业实践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作为大学中的一门学科,为在大学中赢得一席之地,提高其在学术界和知识界的地位,从而加强理论和学术研究,对于LIS向信息范式的转变以及与实践隔离、图书馆教育危机的出现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按照科学学科的发展理论,在与职业实践密切相关的领域,学科不一定从研究领域或学术兴趣小组发展而来,而是从职业实践建立的培训学校或职业本身而来,图书馆情报学、管理学或医学、护理等就是例子。作为图书馆工作专业化过程的一部分,图书馆学在诞生之初更多关注图书馆工作技艺。之后,卡内基公司资助成立了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研究院来提高其理论水平,但是对理论的过度重视又带来了对图书馆技术革新的忽视,最终导致了文献工作和情报学在图书馆学之外诞生。尽管情报学为图书馆学发展带来了重视技术和理论的视角,20世纪70年代-90年代许多图书馆学院依然面临着关闭的命运,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即其在大学中的学术性受到置疑,[34]这使LIS教育者意识到要重新界定和扩展这个领域,突出信息研究和I-Schools的出现即其表现。I-Schools重视高水平学术研究,以信息为导向有利于突出LIS在大学中的学术地位,但这也将带来与实践的更大隔离。正如Gorman所说,对实体图书馆的需要缺乏全神贯注的研究,这既是倾向于信息科学的教师与图书馆实践分离所造成的,也是LIS学院趋向于作为大型研究性综合大学奖励理论研究超过应用研究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图书馆教育危机不可避免。如何既确立自己在学术界的地位同时又不脱离实践,这对于专业教育来说确实是个两难的问题。
总之,图书馆职业中“图书馆服务范式”和“信息范式”的长期冲突,专业化职业所带来的研究、教育与职业实践的两难冲突,以及图书情报档案工作一体化的发展,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推动着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分野与融合、范式转变以及图书馆教育问题的产生。
4 结论和启示
20世纪初到60年代,时代环境的变化,图书馆学研究对技术的轻视,以及图书馆活动无法满足社会上信息爆炸和信息需求状况,这些原因使得情报学作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而形成。情报学的发展对图书馆学带来了极大冲击和影响,图书馆学逐渐向图书情报学(LIS)方向发展,二者在研究内容和范围上的融合一直没有间断。但是,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融合发展在各个国家不尽相同。尽管学科的发展有其内部的基本规律支配,但是由于社会科学研究受到研究者主观认识、导向和价值体系的影响,各国基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和研究状况采取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在美国,情报学诞生后有关图书馆学和情报学分离或整合发展的争论十分激烈,甚至延续之今,尽管如此,情报学科主要被吸纳入图书馆学形成图书馆情报学(LIS)发展的。最近10余年中,情报学地位凸显,LIS向信息范式的转变十分明显,I-Schools的出现即其佐证。在日本,尽管也曾有争论,但研究共同体很快统一了研究方向,从而使其图书馆学情报学一体化发展没有出现过多的分歧,并逐渐向信息范式转移。而在中国,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发展同时受到欧美和苏联的影响,从发展之初就形成了两门学科并列发展的传统,而研究共同体在二者融合发展探索中选择的基本是条寻求上位学科和学科群发展之路,其今后如何发展需要在借鉴国际经验同时考虑其历史发展脉络及现实实践。当前,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发展中分野因素和融合因素依然并存,但是在学科名称、研究内容上,图书馆学信息化发展为图书情报学似乎已经成定势。
在图书馆学和情报学教育的融合发展上,从总体上看,各国基本上走过了从图书馆学院到图书情报学院再到信息管理院系的过程,但是内在差异依然存在。当前I-Schools发展势头在美国最为强劲,其他国家尽管也有苗头,不是十分明显。国内从20世纪90年代就改名为信息管理系,但是与美国I-Schools的发展道路还是存在差异的,似乎呈现一种压缩饼干式或跳跃式的发展,同时大多数院系似乎尚没有力量实现对其他更强势学科如计算机科学等相关领域信息教育的整合,而在本科层次上的整合更多的是一种行政力量主导的专业调整,带来的相关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关于Gorman提出的图书馆教育危机论,在美国也存在争议,如果从对比角度来看,其图书馆教育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依然十分强大,但是图书馆教育主导地位让位于信息范式趋向是明显的。这种导向将为 LIS教育带来什么?在我国也出现了“图书馆学教育低潮”及“图书馆学教育殖民化”的提法,这些该如何理解,仍需要进一步思索和探讨。
在国外,图书馆学将情报学纳入自己的版图,今天又出现信息教育更加凸显的态势及其他问题是受到图书馆职业和信息职业实践深刻影响的。作为一种专业教育,图书馆学研究和教育与实践密切联系在一切。但是,在国内,图书馆作为一种专业教育的观念似乎并不那么强烈,关于专业教育、学科(academic discipline)及研究领域(research field)的关系在研究者心目中似乎不那么清晰。而这似乎也造成了国内外在探讨这一问题时的一些理解差异。
收稿日期:2007-05-25
标签:情报学论文; 图书馆论文; 图书情报硕士论文;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论文; 信息管理学院论文; 美国教育论文; 大学课程论文; 范式论文; 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