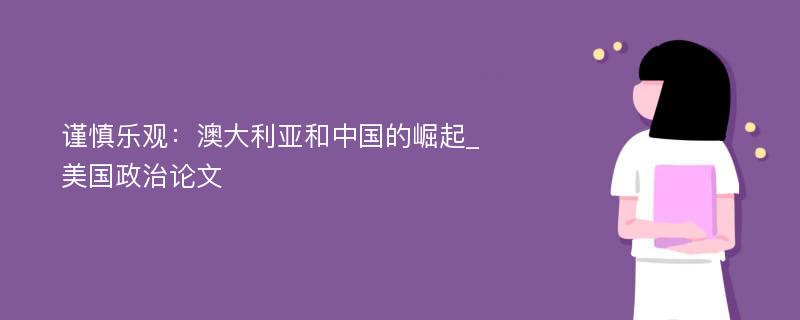
谨慎乐观: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崛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大利亚论文,中国论文,谨慎论文,乐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澳大利亚来说,中国经济近几年的发展给它带来许多益处。未来25年,中国经济极有可能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果真如此,中国将改变澳大利亚的经济面貌,取代日本成为带动澳繁荣的主要动力。中国也将改变亚洲地区,中国不断增长的巨大引力作用已将东亚各国经济吸入越来越统一的地区经济体,并为更加紧密的政治一体化打下了基础。对澳大利亚而言,这种前景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格外诱人。中国处于中心地位的新亚洲观已占据澳大利亚的外交界。
澳大利亚政府对此一直非常乐观。新一届政府上台不久,便决定其首要工作是与中国建立密切的贸易关系,并为这种关系提供必要的政治基础。北京提出,任何国家想要从中国独特的经济机遇中受益就必须承认其不断增长的政治影响力。澳接受了这一要求,并认真权衡了中国的政治和战略利益。在澳外交政策中,中国被赋予了新的重要地位。2003年10月布什总统和胡锦涛主席同时访问澳大利亚,并都受邀在国会发表演讲即是证明。胡锦涛是除美国总统之外获此殊荣的第一人。这两个访问的同时发生,以及澳对两位访客同等规格的礼遇,表明在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中,澳美关系和澳中关系同等重要。此后,约翰·霍华德总理在一系列演讲中强调了这两对关系的不同基础和动力,并明确表示在美中两国出现分歧时,澳不会支持任何一方。澳大利亚拒绝与美日共同对欧盟施压促其继续对中国进行武器禁运,也没有参与美国对中国军事建设的批评,而且对美中两国一旦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冲突时澳是否愿意支持美国不置可否。
澳大利亚政府的言行引起了美澳部分人士的担忧。他们想知道堪培拉将如何在它与北京日益增强的经济、政治甚至战略联盟和与美国的同盟之间保持平衡。对此,澳政府一直持坚定的乐观态度——至少目前仍是如此。霍华德总理和唐纳外长都曾表示,澳大利亚不会被迫在美中之间做出选择,因为两国不断升级的战略竞争并非不可避免。① 我们可以理解政府的观点。澳大利亚认定它能够在与中国保持生机勃勃、日益密切关系的同时,也与美国保持越来越亲密的同盟关系。只有鲁莽的政客才会怀疑它的可信性。但这种乐观主义合理吗?如果它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将会存在怎样的风险呢?最重要的是,如何才能促使其成为现实呢?
这些问题对澳大利亚的外交和战略至关重要,远远超越了如何处理澳中和澳美这两对存在潜在矛盾的双边关系这一狭隘问题。在有关亚洲未来这一重要问题中,它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如果中国继续保持增长,亚洲战略环境将被其越来越强大的实力所改变。在未来几十年,如何应对这一变化将是亚洲、甚至是全世界最棘手、最重要的安全问题。对澳大利亚而言,真正的问题并非如何平衡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而是如何在这种战略变化中保护自己的利益。澳大利亚的利益非常明确,即希望亚洲继续保持强劲增长,而它能融入其中;希望美国保持对亚洲的接触政策,阻止中国获得主导权,但不强迫澳在美中之间进行选择,或抑制亚洲经济增长。
最佳结果
澳大利亚政府对中国崛起所持的乐观态度似乎主要建立在这样一种希望之上:中国未来的权力能够被纳入美国领导的单极世界秩序中。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这既是最好也是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的确,对澳大利亚来讲,这可能是最佳结果:可以同时从美国的强大中获得战略收益、从中国的繁荣中获得经济收益,而又不必在它们之间进行艰难的选择。对中国而言,如果接受美国的领导地位,就可以实现经济增长而不必承受与美战略竞争的压力并可以避免打破地区均势,引发其他国家对其未来霸权的担忧。
在乐观主义者看来,这似乎是后冷战时期国际事务中三个主要现象自然发展的结果。这三个现象分别是美国超强的主导地位,经济上不断加深的互相依赖关系,以及全球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向美国市场民主模式看齐。这些全球趋势预示,中国如果想要保持增长,除遵守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外别无选择。因为,与美国这个拥有巨大实力的国家进行战略竞争,只能徒耗资源;并会因失去美国的市场和投资而导致经济停滞。此外,随着中国的发展,其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必然与美国越来越相似,竞争的动机也终将消失。
然而,出现上述情况的前提是,当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时,它必须自愿融入由美国领导和塑造的地区及全球秩序中。但就本质而言,这似乎不太可能。中国可能在经济上已经太庞大,在政治上太有影响力,野心太强,并且太过看重其独立性,因此无法使自己平静地接受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观。
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部分,其惊人的经济增长和更加惊人的开放性正在改变着全球经济,成为保持世界经济稳定和繁荣的不可或缺的力量。② 它的廉价出口产品满足了消费者需求,并抑制了全球通货膨胀,它的储蓄对于弥补美国预算赤字至关重要。因此,中国对世界经济,特别对美国经济的重要性,已经与后两者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趋于等同。劳伦斯·萨默斯曾将这种结果描述为美中之间的金融恐怖平衡,在这种平衡关系中,任何一方都无法承受破坏对方经济的行动后果。③ 从战略上看,这对北京有利:现在中国对美国的繁荣太重要了,因此华盛顿不能将经济作为战略的工具。
就更广泛意义而言,如今美国的主导地位与以前甚至是几年前相比,已不再“超强”,在亚洲地区尤其如此。导致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美国对中东地区的全神贯注,以及在伊拉克政策上的反复。但是,太平洋两岸的战略家都开始认识到,军事上,中国日益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虽远落后于美国,但仍能增加美对华采取军事行动的代价和风险。政治上,在亚洲与中国的影响力竞争中,华盛顿已丧失了大片阵地。中国非常成功地将经济机遇转化成地区政治影响力,而且近几年,中国一直非常明确而灵活地利用它来改善自己与几乎所有邻国的关系。中国的定调适中而合理,例如,它不再尖锐批评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同盟关系,并且巧妙地利用了它的巨大软实力资产。
目前,中国的多数邻国都能更加轻松地面对它日益增长的实力,并因此感觉自己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美国。这使美国丧失了一项重要的政策资产。多年来,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一直期望对中国实力的恐惧会对中国的地区影响力产生限制。他们认为,中国越强大,其邻国就越感畏惧,也就越欢迎美国采取行动限制中国的影响。但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现在大多数亚洲人接受并欢迎中国上升为亚洲领导角色,而且,只要中国继续保持近几年的适度政策和有说服力的外交,它们将继续如此。
澳大利亚能寄希望于中国国内政治提供另一个限制其挑战美国权力的自我调节机制吗?随着中国的不断强大,其政治制度会演变得与美国更加相似,因而它更加乐意接受美国的领导地位吗?许多人这么认为,但笔者不敢苟同。中国集权体制取得的经济增长超过了许多观察家的预测。它可能还未达到其政治制度的经济极限。但同样可能的是,与美国和其他地区普遍流行的观点相反,21世纪将出现一个与美国截然不同的新的国家成功模式。今天,在中国看到的可能就是这种新模式的诞生,并且它可能挑战西方模式。
所有这些意味着,中国意愿对亚洲未来走势至关重要。目前,有一点似乎非常明显:中国的目标比单纯地适应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更具野心。随着实力和自信心的提升,中国与美国的竞争将更加公开,而且会更不甘心在美国领导的地区和国际秩序中扮演配角。如果中国公众更广泛地参与政治,这一趋势会进一步加强,因为一种非常激进的民族主义正形成于中国新兴阶层。其原因是,中国今天的自我定位源于一种强有力的混合情感:对历史上长期强盛的自豪,对近期蒙羞受辱的愤恨,以及对辉煌未来的巨大信心。从长期看,中国的首要目标很可能是:在亚洲,取代美国成为亚洲的头号强国;在全球,最大限度地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中国已强大到足以承受住压力,不必理会华盛顿制定的原则、价值观和优先事务。而且,中国依据自己不断上升的实力,认为现在没有理由把领导权无条件地拱手让给可能处于、也可能不再处于全盛期的美国。因此,最佳结果出现的可能性似乎很小。
次佳结果
如果无法迫使或劝说中国将其不断增长的权力从属于美国的主导地位,那么美中在亚洲地区达成一项分权协议(包括在美中之间以及在美中和其他国家之间进行权力分配),将最有利于维护澳大利亚的利益。这虽不能为澳提供像在美国主导下的那种简单而安全的战略环境,但仍能提供一种长久的地区秩序。这一秩序将保留美国的重要作用,限制中国的权力,保护该地区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利益。初看起来,这种地区秩序模式似乎显而易见,简单明了。但这是假象。笔者认为,所能预见的未来世界和地区秩序并不会出现一个由美国的主导地位、全球化和不断扩张的民主制度所塑造的新时代,更不会出现国家间权力政治的老一套做法在新时代被取代。相反,多极体系将会进一步演化,几个巨型国家将按照传统的欧洲外交方式争夺影响力;世界又回归到梅特涅、皮特和塔列朗时代。
科拉尔·贝尔向我们说明这个新世界是如何出现的。她已然看到美国单极时刻的没落。她认为,当今时代的大趋势是几个非常强大的国家——不仅仅是中国和印度,也包括欧洲和日本——和主要大国第二梯队的崛起。这种权力结构与1914年前几个世纪的现代欧洲权力结构颇为相似。在此情况下和平处理国际关系的最佳(可能是唯一)方式是拿破仑战争后出现于欧洲的那种大国协调。与“欧洲协调”相同,它的重要前提是多数大国在以下两个原则上达成谅解:互相承认对方政府享有平等的合法性;为维护和平愿意在各国利益问题上进行妥协和协调。④
贝尔有关多极世界的看法符合亚洲情况,她所说的强国大多聚集于此。亚洲需要一个足够强大的大国协调来调整大国关系、抑制竞争、维护和平。其中,美中关系将是重中之重。如果中国不接受美国的主导地位,那么解决过度竞争和冲突的唯一办法就是建立一种互相容忍和尊敬的关系——它是大国协调的基础。美中能建立起这种关系吗?这并非绝无可能。美中拥有对双方而言都极为重要的经济关系,而且近几年一些可喜的迹象表明两国甚至能够在一些敏感的战略性问题上进行合作。如两国在朝鲜等双方利益暂时重合的问题上进行了较好的合作。但是,在特定问题上的有限的策略性合作与广泛而持久的战略性协调存在着天壤之别。尽管在经济上相互依存,今天的美国和中国绝对是战略竞争者,它们均以零和方式看待彼此关系。
从竞争走向谨慎而礼貌的合作并非易事。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缺乏在这种国际秩序中运作的丰富经验。它们都已习惯于主导各自的国际环境。对中国而言,可能容易一些。在过去几十年中,由于处于相对弱势,它接受了美国(以及苏联)霸权的现实,因此它更能够妥协。中国非常清楚美国的实力,以及全面对抗的经济和战略风险;知道要谨慎地应对美国,至少今后几十年必须如此。
对美国而言,适应老一套的欧式权力外交将会更加困难。美国最深厚的外交传统——可追溯到乔治·华盛顿的《告别演说》——是反对妥协外交,近期历史进一步强化了这些原则。美国人记得,冷战的胜利不是因为国际关系的缓和,而是以武力为后盾的对美国利益和价值观不屈不挠的坚持。15年来,他们一直怀着建立新的“美国世纪”目标,即坚持对美国权力和价值观的不妥协以创造更美好的世界。
当然,美国也拥有令人尊敬的现实主义传统,它试图理解欧洲权力政治的传统并将其运用在美全球影响力上。这一传统的支持者包括乔治·凯南、亨利·基辛格等。他们认识到亚洲的持久和平需要双方在关键问题上进行妥协和让步以顾全对方利益。但是,现实主义者在美国的政策辩论中常常是局外人,在现任政府中尤其如此。在美国断裂而相互竞争的政策程序里,如果没有总统的明确领导,在美中和解政策上形成长久一致的意见非常困难,因为这与其国家传统和经验完全背道而驰。
即便是现实主义者也会发现,他们很难主张与日益强大的中国进行真正妥协。在美国舆论界,没有任何强有力的集团——甚至是那些主张与中国建立合作关系的人——愿意承认,今天的中国在亚洲拥有合法领导权。多数人认为,中国不愿接受美国的主导地位证明它决心称霸亚洲,因此对中国妥协等同于绥靖。而中国的军事建设进一步证实了这种看法,并直接挑战美国的权力、利益和价值观,美国必须应战。几乎没有人承认,中国拥有发展武装力量以保卫其直接的国家利益不受美国侵犯的合法权利;中国保留最小限度的威慑力量以对抗美国核压力是合法的。总而言之,几乎没有一个美国人承认,中国是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强国,美国必须与它妥协并达成协议;中国崛起意味着单极时刻的结束。只有当他们都接受了上述观点,“亚洲协调”才会出现。
贝尔和平多极世界观面临的另一障碍是其他大国是否参与亚洲协调。目前看来,印度将发挥关键作用。日本似乎是最重要也最麻烦的第三方。近年来,中国崛起深深困扰着日本,这主要是因为中日之间的问题与中美之间的问题截然不同。北京似乎无法接受日本在地区事务中扮演合法角色,也未让日本相信强大的中国会尊重日本利益。日本对中国未来的权力心存恐惧,并担心其成为美中和解的牺牲品。故而日本将是美中和解的主要反对者。美国不能忽视日本的担忧。美日关系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重要战略资产,而且一旦美国与中国形成敌对关系,日本的支持至关重要。
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乐观地认为,亚洲必然会出现一个新的稳定的多极秩序。与经济不同,政治和战略影响力的竞争是零和游戏。在战略问题上,并不存在经济学家所说的那种“看不见的手”,可以默默地保证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行为的相互作用会最终增进社会福利。只有积极、灵活且富有创造性的外交,才能营造那种能够协调亚洲地区主要各方利益和期望的稳定的地区秩序。
但目前并无此迹象。美国人常说,中国掌握着塑造未来美中关系的决定权。但这并非事实。美国需要决定是否承认中国要求的合法性,让中国在地区发挥领导作用,以及是否接受其中隐含的对其在该地区和全球秩序中的角色定位。或者,它将抵制中国不断增长的权力和影响,并为此甘冒不断恶化两国关系的风险,尽管美国同时必须保持对华贸易关系,并继续帮助中国发展。中国也必须做出选择。但是美国的选择会在重要的方面影响和限定中国的选择。所以应该由美国这个更强势的大国走第一步。美国尽早采取明确的行动来勾勒亚洲未来的多极均势格局将最有利于这一格局的出现,并能使美国对结果的控制达到最大化。但目前并无迹象表明美国有此想法。美中之间的冲突绝非不可避免,但通向稳定的地区均势之途似乎充满艰辛。
三种不好的结果
如果美国和中国不同意分权,会出现哪些其他的可能?似乎只有三种可能,但都对澳大利亚不利。第一种可能是中国在地区影响力的角逐中获胜,而且在亚洲成功地建立了极大限制美国权力的有效势力范围。这种可能性不大,但将之完全排除是不明智的。毕竟,近年来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较之美国上升得很快,而美国权力被拙劣的政策所滥用和浪费了。谨慎的悲观主义要求我们至少认识到这些趋势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这对澳大利亚并非利好消息。我们没人知道一个强大而不受约束的中国将作何表现,但它试图在政治、经济甚至军事上主导该地区的做法可能严重冲击澳的利益。在缺乏强大的美国作用的情况下,除中国自制外,防止在亚洲出现中国霸权的唯一保障可能是一种不稳定的均势,它是由日本、印度、俄国和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其他大国之间不断变化的联盟关系所维系的。与19世纪的相对稳定相比,它更类似于欧洲17、18世纪变化莫测的权力政治。这种前景令人不安。
第二种可能是美中之间出现全面的敌对关系——一种中美冷战。这将迫使澳大利亚这类国家支持其中一方。如果无法说服中国将自己从属于美国权力,也无法说服美国与中国分享权力,那么这种结果最有可能发生。一些美国人对待这种可能性的态度是镇静甚至是狂热的。⑤ 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将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以及美国经济造成多么严重的损害。全面的猜疑和敌对将限制所有国家的经济机遇,并提高发生冲突的风险,会使彼此曲解对方的行动,导致敌对情绪的自我膨胀。我们已能看到这种相互刺激的怀疑在不断滋长(它如同一战爆发前的欧洲):中国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加深了美国对中国意图的担忧,而且被用作增强美国军力的借口;反过来,这又进一步刺激了中国的军事建设。
第三种可能也是最糟糕的一种——武装冲突。近来发生的事件可能使美中部分人士认为,两国间的任何冲突都将是短暂且能够被控制的。但笔者认为,它们也可能会变得没完没了、无法解决,即使是双方最终结束了长期的争斗,但已形成了深深的敌对。虽然避免它的发生均有利于双方,华盛顿和北京也不想要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不会发生。问题的关键在于双方能否足够聪明地避免冲突。目前,美中之间的怀疑和不信任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使得任何危机都变得更加难以应对。如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等将轻而易举地引发任何一方都不愿看到的冲突。最近,出现了关于美中爆发战争时澳是否军事支持美国的讨论。实际上,这是次要问题。重要的是,如果美国和中国开战,澳大利亚有关地区和平与繁荣的希望就将破灭。无论选择什么道路,届时澳都将处于一个全然不同的陌生世界中而别无选择。
避免最坏的结果
综上所述,我们的乐观主义不能不被冷静的分析冲淡一些,未来亚洲很容易走入歧途,而且一旦如此,澳大利亚将受到严重影响。它还表明,澳大利亚的首要任务应是设法影响事态发展方向,使其符合自己的利益。当然,澳的利益大大超过了自身的影响力,这是中等强国无法避免的困境。但澳还未虚弱到无需承担塑造自身生存环境的责任。
如果中国崛起是个长期过程,它对澳大利亚战略环境的改变在其短暂的国家历史上将是前所未有的,也将对澳外交产生史无前例的挑战。直到20世纪中叶,澳最大的贸易和战略关系都集中于英国。之后,澳最大贸易伙伴日本一直是其主要盟国美国的战略附庸。但几年后,澳大利亚将面临新的情况:其最大贸易伙伴将是中国,但中国将是自己主要盟国的战略竞争者,甚至可能是敌人。这意味着澳大利亚的利益将不再能简单地被其同盟关系所界定。在此复杂的新环境下,澳大利亚如何围绕国家利益调整其外交和战略,这与过去有着质的区别。从中国对澳美和澳日关系所施加的压力中,已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澳大利亚在这一结果中的利益非常巨大。中国崛起可能最终结束500年前由达·伽马开启的西方对亚太地区的海洋统治时期。而澳大利亚正是这一时代的产物。这一时代的没落以及澳大利亚如何度过过渡期,将成为澳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也将成为澳与其主要盟国(美国)关系中的重要事件。澳大利亚人总是透过亚洲均势的棱镜来审视他们的主要同盟关系,而其同盟关系的力量主要源于这样一条共识:维持西方主导地位的现状对澳美都有利。现在,中国崛起为地区首要大国正在挑战这一共识。自身利益和美国的本能使澳左右为难。这种分歧可能会导致华盛顿和堪培拉之间产生两国历史上的最大裂痕。
澳大利亚该怎么办?笔者认为应该采取四个步骤以明确澳的选择,并使其影响最大化。首先,澳大利亚必须决定未来何种亚洲模式最能保护自身利益。如上所述,对澳大利亚而言,美国继续保持主导地位将是最好的结果,但这只会出现在中国的实力和野心不大之时。因此,澳必须将精力集中在次佳结果上——大国协调在亚洲的演变。现在该将这一理念付诸行动了。
其次,澳大利亚必须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大国协调在亚洲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如何建立这种机制。首先是美国必须承认中国在该地区不断增长的领导作用的合法性。然后是协调地区各大国的利益和影响,它不仅仅指美国和中国的利益和影响,也包括印度、日本和亚洲中等强国的利益和影响。其中,日本的地位问题特别关键,也对中国提出了直接挑战:如果北京希望美国接受中国的地区领导者地位,它也必须接受日本在该地区发挥合法的领导作用。只有这样,日本才会对美中长期和解持默认态度。
第三,澳大利亚必须认识到,在亚洲,稳定的大国协调机制所面临的最主要障碍是美国的态度。澳大利亚别无选择,唯有尝试改变美国的想法。首先澳必须坦率地向美国说明其对中国的看法。澳大利亚政府已开始这么做了,但可能是无意识的。堪培拉对中国热情而积极的外交活动、霍华德精心安排的同等礼遇,以及唐纳偶尔抛出的草率之言都向华盛顿传达了这样一条讯息:澳大利亚对中国以及对自己在亚洲未来作用的看法比美国要积极得多。但是,这种偶然为之的外交活动必须被明确、积极而坦率的行动所取代,以向华盛顿明确表明澳对亚洲未来的想法——澳愿意接受中国不断提高的地区领导地位。
澳大利亚必须向美国说明为何这么想,并坦率指出美国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外交与其更加现实主义的传统之间的差异。澳必须说明,它看到亚洲在接受美国持续而积极的接触政策以及它对日本、印度和地区中等大国利益提供保护的同时,也在逐步协调与中国日益增长的权力关系;澳认为对中国在该地区的作用应该予以哪些限制,以及它应该如何帮助自己设立这些限制。而且,澳大利亚必须找到使美国的国内辩论转化为如何让美在亚洲未来发挥积极而合作作用的方法。就目前而言,没有哪个国家比澳大利亚更适合在此问题上对美国施加影响。但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可能是澳大利亚同盟外交史上最大的考验。
第四,澳大利亚必须仔细思索与中国关系何去何从。中国要求密切的经济联系必须以顺从中国在重要政治和战略问题上的意愿为条件。对此,澳一直是默认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仅仅反映了伴随中国的崛起亚洲出现了新均势的现实。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澳大利亚已仔细思考过应采取怎样的限制措施来制约中国对其政策的影响力。为了换取中国给予的经济机遇,澳做出的让步可能已超过了必要限度,就长期利益而言亦是如此。在1994年的一次采访中,时任总理的保罗·基廷曾反问道,“我们想进入中国的轨道吗?”他毫不含糊地回答,“不,我们当然不想”。⑥
注释:
①Alexander Downer," Biennial Sir Arthur Tange Lecture in Australian Diplomacy," Canberra,August 8,2005,http://www.foreignminister.gov.au/speeches/2005/050808_tange.html.John Howard," The 2005 Lowy Lecture on Australia in the World,"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Sydney,March 31,2005,http://www.pm.gov.au/news/speeches/speech1290.html.
②Mark Thirlwell," Shaking the World? China and the World Economy," Lowy Institute Perspectives,Sydney: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Augest,2005.
③Lawrence Summer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lobal Adjustment Process," Speech at the Third Annual Stavros S.Niarchos Lecture,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Washington,DC,March 23,2004.
④Coral Bell,Living with Giants:Finding Australia' s Place in a More Complex World,Canberra: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2005.
⑤Robert D.Kaplan," How We Would Fight China," Atlantic Monthly,295( 5) ,2005,pp.49-57.
⑥Greg Sheridan,Tigers:Leaders of the New Asia-Pacific,Sydney:Allan and Unwin,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