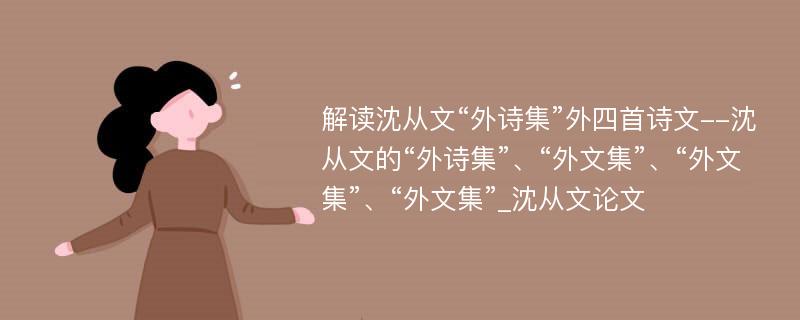
“看虹摘星复论政”——沈从文集外诗文四篇校读札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文论文,札记论文,摘星论文,文集论文,复论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种境界》、《饭桶——见微斋笔谈》、《逛厂甸》、《巴鲁爵士北平通讯(第七号)》这几篇诗文,是我在阅读杂志的时候偶然发现的。因为过去对沈从文略有所知,从它们的作者署名“雍羽”、“上官碧”和“巴鲁爵士”及其行文风格上,初步判断这几篇诗文是沈从文的作品。经查阅《沈从文全集》和沈从文的年谱,发现它们并未收入现在通行的沈从文作品集中,可以大体认定是沈从文的集外佚文。
倘若把沈从文的这几篇散佚诗文与他在抗战及40年代的相关文本联系起来,进行“文本互证”式的对读,则不难发现,《一种境界》颇为扼要地表达了沈从文创作《看虹录》、《摘星录》和《七色魇》等作品时那种在万物和情愫的溶解和变迁中,以“爱欲”为救赎的迷离情致。《饭桶——见微斋笔谈》呈现了作者从细微之处看政治的独特视角,以及对借政治而混吃饭之人的深切反感,笔下有对抗战中某些积极为官之人行为的尖锐讽刺。《逛厂甸》以一种类似于《东京梦华录》般的缅怀笔调,来描绘作者近三十年逛厂甸的感触,有一种历史转折关头对文人士大夫精致文化即将消逝的殷忧,以及对北京小市民文化的抵触。《巴鲁爵士北平通讯(第7号)》,延续前六篇“北平通信”,为沈从文对玄黄未定的时局的判断和展望,有柏拉图《理想国》般的光彩。企图将人性中“迷信”情绪与科学结合,与政治剥离,有一种社会解体、大厦将倾前极力挽救的救世热忱。
一
刊发于1940年6月16日昆明《今日评论》上的诗《一种境界》,是迄今发现的沈从文以笔名“雍羽”刊发的第二首诗,在时间上仅次于《一个人的自述》,先于《莲花》和《看虹》,上述作品,均署名“雍羽”。①《沈从文笔名和曾用名》云:“雍羽,1940年1月26日发表新诗《一个人的自述》时的署名,1940-1941年间多用于发表诗或散文诗作品”。②查阅《沈从文全集》、《沈从文文集》和《沈从文别集》,并未发现它们收录《一种境界》,现存的几种沈从文年谱,也未见记载此诗。因此,判断《一种境界》为沈从文的一首佚诗,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一种境界》虽然未曾收入现存沈从文作品集中,可是却被引入《新摘星录》和《摘星录》中,成为这两篇内容大略相同的小说文本的一部分,构成小说内在情绪的核心,甚至敷衍出部分情节。反过来看,《一种境界》的意义,恰在于它为沈从文的小说集《看虹摘星录》提供了一个情绪上的起点。虽然沈从文在《一个人的自述》中已经提及自己喜爱“一种希奇的旅行”,在“攀援登临”追逐“一夥”星子,“走进天堂”,表达一种对爱欲的抽象沉迷,不过这种对异性身体“转弯抹角,小阜平冈”的旅行兴趣,上承早期诗歌《颂》,③下启后来的小说《看虹录》,成为沈从文笔下一种爱欲事件隐喻化的惯常策略。可是,《一种境界》中却呈现了明确的时间“去年”,和具体的对象“你”,与一种名字古雅的花“剪春罗”,并且雨后“虹霓”和天上“万千颗星”同时并存。宋代翁广元在《剪春罗》中云:“谁把风刀剪薄罗,极知造化著功多。飘零易逐春光老,公子樽前奈若何。”传达的是一种春光易逝,珍惜哀婉的情致;沈从文使用这个意象,同样表达了一种脆弱难久的美好情愫。或许《一种境界》所述的是沈从文一次具体的爱欲体验,它发生于抗战初期的昆明,有一个不同于“主妇”的特定对象“你”,并且引发了作者关于世界正在变动不居,人格和灵魂需要在“爱”中多次溶解的感触。在沈从文的同期诗歌中,与《一种境界》相近,虹和星同时作为主要意象出现的诗,此外仅有1941年底的诗《看虹》,诗中在沉迷于爱欲中时看见“有长虹挂在天上”,即将别离时祈求“摘一颗星子把我”。不过,《一种境界》表达的是对爱欲本身的体味和思索,《看虹》表达的是一场爱欲正在进行和即将结束的感觉。在沈从文的小说《看虹录》和《摘星录》中,沈从文把这次特定的爱欲体验,分别从“我”和“她”的角度,着力进行了抽象集中的或散漫隐晦的叙述。《摘星录》和《新摘星录》写的是一个二十六岁青春将逝的美丽温雅女子,处身于一个老在变化的古怪世界中,在一个“良辰美景奈何天”的时节,在古典爱中的诗与火和现代爱中的具体而庸俗之间,在有地位有身份的老朋友和年青的又穷又无用的大学生之间徘徊瞻顾、游移不定的心态。这个“老朋友”说:“其实生命何尝无用处,一切纯诗即由此产生,反映生命光影神奇与美丽。任何肉体生来虽不可免受自然限制,有新陈代谢,到某一时必完全失去意义,诗中生命却百年长青!”④这段话在沈从文作品中反复出现,可以看出这个“老朋友”身上清晰的留有沈从文自己的印记。下文在叙述这个“老朋友”三个月前离开她时留下了一首有点古怪的小诗,即是这首《一种境界》。不过,在《新摘星录》和《摘星录》中隐去了诗的标题,除了标点符号和划分章节稍有不同外,文字则完全相同。⑤在《一种境界》中,隐含作者“我”和作为爱欲对象的“你”,处于一种对偶关系中,尽管叙述视点聚焦于“我”,言说者是“我”,“你”是被凝视的和被询问的,二者共处于一个碧草连天、夕阳微明有着小窗的房间,一种惆怅欢欣兼有的悒郁沉迷气氛在房间中流淌。在《摘星录》和《新摘星录》中,则是从“她”的视点来叙述对《一种境界》所呈现爱欲氛围的追念和怀想。从即将萎悴的蓝色的抱春花,转向萎悴多日的红色的剪春罗。“小瓶中的剪春罗已萎悴多日。池塘边青草这时节虽未见,却知道它照例是在繁芜中向高处延展,迷目一望绿。小窗口长庚星还未到露面时。……这一切都像完全是别人事情,与她渺不相涉。自己房中仿佛什么都没有,心上也虚廓无边,填满了黄昏前的寂静。”⑥下文“她”阅读不同时期不同情人的编号清晰的情书时,名称尽管情人的身份不同,均留下了这个“老朋友”的影子,甚至可以说,他们都是作者沈从文的不同化身。
刘洪涛在《沈从文与张兆和》⑦一文中认同金介甫的观点,《看虹录》是沈从文与高青子的恋情产物;他在《沈从文与九妹》中认为《摘星录》是九妹爱欲体验的产物。《一种境界》的发现,可以证实《摘星录》同样是沈从文爱欲体验的记录。至于故事中的“她”,究竟是高青子还是其他未知的女性,现在还难以确定。
《新摘星录》写于1940年7月18日,距离《一种境界》的发表时间不到一个月。1943年6月30日,沈从文特别看好的、并且在昆明常与之同住的诗人卞之琳,写了一篇似小说而又似散文的作品《巧笑记:说礼》,记述了爱慕者“神经病”和一位“温柔朋友”在一场轻颦浅笑的谈话中,和对男女交际礼仪不经意的展演中,在昆明的匆匆相遇及转瞬分离。这里的神经病有卞之琳自身的影子,温柔朋友则以张兆和的妹妹张充和为原型。但是表示“神经病”的白日梦的一段话似乎别有用意。“即使做了丈夫也无有丈夫的义务,责任,丈夫把太太的好处享受够了,还可以向外发展,在当今这个开通时代,大家都知道女子的青春比男子的易逝,大家会原谅一个丈夫到一个时候会感到寂寞的苦衷,如果他是一匹种马式的天之骄子。于是他可以虽然偷偷摸摸,也实在堂堂正正的另外找一个年轻的女子。……因为天生是情种啊:也就因为天生是情种,在社会上的责任就是讲恋爱,……整个心机就都可以化在诱引女子。而且太太总该讲礼,爱的表现,认为应该使丈夫快乐,就可以代为勾引。……另一方面自己也可以告诉最善感的生物说,他过去实在没有经验过真正的爱,人家就更不由的同情。不错,既如此,再加以随年龄俱进的老练手腕,准可以打倒一切那怕是漂亮小伙子的敌手。……然而,天,他自己也会有小妹妹的,他自己也会有小女儿的!”⑧“神经病”的身上又似乎投射了卞之琳对某类情场老手的深切怨怼的情绪。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最后温柔朋友坐汽车回昆明乡下朋友家里(指沈从文和张兆和的家里)去了,留下了“神经病”死心塌地长久守望的身影。接着,沈从文在1943年底1944年初发表了《绿黑灰》,⑨该篇后来又衍化为《绿魇》,⑩成为沈从文以魇字开头的第一篇作品。在《绿黑灰》中,涉及到卞之琳的失恋和沈从文的偶然,二者很可能交织于一个善于唱歌吹笛的聪敏女孩子——即张充和身上。“一些人的生命,虽若受一种来自时代的大力所转动,无从自主,然而这个院子中,却又牵来一个寄居者,一个失恋中产生伟大感和伟大自觉的诗人,住在那个善于唱歌吹笛的聪敏女孩子原来所住的小房中,想从窗口间一霎微光,或书本中一点偶然留下的花朵微香,以及一个消失在时间后业已多日的微笑影子,返回过去稳定目前,创造未来。或在绝对孤寂中,用少量精美文字,来排比个人梦的形式与联想的微妙发展。”诗人两年来,完成了一部五十万字的小说(指卞之琳的小说《山山水水》),并希望藉此获取女孩子的爱情。不过叙述者说,这是无关紧要的。“就因为他还完全不明白他所爱慕的女孩子几年来正如何生存在另外一个风雨飘摇事实巨浪中。怨爱交缚之际,生命的新生复消失,人我间情感与负气做成的无奈环境,所受的压力更如何沉重。一切变故都若完全在一种离奇宿命中,对于她加以种种试验。这个试验到最近,且更加离奇,使之对于生命的存在发展,幸或不幸,都若不是个人能有所取舍。为希望从这个梦魇似的人生中逃出,得到稍稍休息,过不久或且居然又回到这个梦魇初起的旧居来。”(11)“梦魇似的人生”看来就是沈从文《七色魇》集的本义,因此这段文字是相当重要的。更何况,这里的“女孩子”,与《新摘星录》中的“她”,有着非常明晰的相似性。在《绿黑灰》和《新摘星录》之间,似乎有着不易觉察的一座桥梁,指向沈从文在《水云》中反复叙说的“偶然”,在三年前,1940年的春夏间。
沈从文的《黑魇》同样隐约其辞地涉及张充和的这次来访及诗人卞之琳和张充和的阴晴不定的情事。“孩子们取水的溪沟边,另外一时,必有个善于弹琴唱歌聪明活泼的女子,带了他到那个松柏成行的长堤上去散步,看滇池上空一带如焚如烧的晚云,如镶嵌于明净天空中梳子形淡泊新月,共同笑乐。这亲戚走后,过不久又来了一个生活孤独性情纯厚的朋友,依然每天带了他到那里去散步。”诗人和孩子把野花和石子放在小船上顺水漂流,将一种痴愿寄托于不可知的远方。对于他们这些事情,隐含作者插话道:“生命愿望凡从星光虹影中取决方向的,正若随同一去不复返的时间,渐去渐远,纵想从星光虹影中寻觅归路,已不可能。在另一方面,过不久,孩子们或许又可以和那个远行归来的姨姨,共同到溪边提水了。玩味这种人事倏忽光景,不由得人不轻轻的叹一口气。”把张充和与沈从文作品中象征爱欲的“星光虹影”连系在一起,颇为难解。是仅仅指卞之琳和张充和二人之间扑朔迷离难有定局的情事么?似乎并非这么简单。《黑魇》随后又涉及到这件事:“虎虎还想有所自见,‘我也做了个怪梦,梦见四姨坐只大船从溪里回来,划船的是个顶熟的人。船比小河大。诗人舅舅在堤上,拍拍手,就走开了。……’”(12)“四姨”张充和和虎虎“顶熟的人”乘船归来,爱慕四姨的诗人舅舅卞之琳为什么要无言离开呢?这个“顶熟的人”究竟是谁呢?这里边似乎暗含着某种外人不易觉察的玄机。
关于沈从文的小说集《看虹摘星录》,似乎始终笼罩着一层神秘氛围。《沈从文全集》的编者将之列为“有待证实的作品”类,认为大约是1945年江西某书店出版的;并在第16卷注明《〈看虹摘星录〉后记》初次发表于1945年12月8日和12月10日天津《大公报·综合》副刊鲀署名从文。不过,早在1944年5月21日, 《大公报·文艺》第29期的重庆版和桂林版就分别刊载了署名“从文”的《看虹摘星录后记》,文字与全集本《〈看虹摘星录〉后记》略有出入。而1945年底《大公报》天津版所刊载的《看虹摘星录后记》,署名是“徇文”不是“从文”。在这篇后记中,作者写道“天气阴沉得很。房中真闷人,我从早上五点起始,就守在这个桌边,不吃不喝,到这时为止,已将近十一点钟,买了一小束剪春罗花,来纪念我这个工作,并纪念这一天。”下面并提到女主人送走客人后独自在庭院中看天上星子的情形,可知这篇后记是紧随着《摘星录》的重写稿而成的。这样,虽然沈从文《看虹摘星录》的内容我们还不大了解,综合《看虹摘星录后记》发表的时间、《看虹录》和《摘星录》的写作时间和修改时间,我们可以知道,在1944年上半年以前,1943年5月以后,《看虹摘星录》已经编辑成书了。
在抗战期间,沈从文在文学上的收获主要是《看虹摘星录》和《七色魇》两个集子。在这两个集子中,沈从文延续“乡村抒情想象”体小说和“都市讽刺写实”体小说中对男女爱欲的关注,并使之获取了一种更加抽象的、更加唯美化的形式。《看虹录》和《摘星录》以精雅的小说体式,沉醉而微带悒郁的抒情笔调,分别从男女两性的角度,叙述一种绅士和仕女的艳而不庄的传奇。《七色魇》则在《水云》、《绿魇》、《黑魇》、《白魇》、《赤魇》、《橙魇》、《青色魇》等七则颇具文体试验性质的篇章中,若断若续地逐一呈现“我”的不同形式的爱欲体验。由于作者将他的在昆明时期的日常生活也作为一种贯穿性的结构编织进这个叙事体式中,《七色魇》呈现出一种真幻交织的特殊色泽。这里的叙述者“我”,被认为是一个居住在乡下的“城里绅士”,可是内心依然有不同于一般城里绅士的对自然和人性的认识。
二
抗战前后沈从文另外写了一些兼有政论性的作品,期望将自己对人性和自然的理解,注入到“社会重造”和“国家重造”的理想中去。抗战初期,沈从文的“反差不多论”,即已判然界画出其深微精雅的创作取向与浅白平实的抗战文艺主流的分歧;他在其后诸多杂文中对文艺宣传功能的抨击,更进一步加重了他与抗战文艺阵营主体的疏离,固然沈从文所执着的文艺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对当时粗疏浮泛的文艺创作不无纠偏补蔽之效。在抗战结束后,沈从文呼应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说,并婉转而果决地提出了“以美育改造政治”的主张。乍然看来,这似乎与他所一贯坚持的文学独立于政治和商业的姿态大不相同,所关注焦点也从文学转向美术,不过,这种变化也是沈从文文艺自尊自重思想在政局动荡情势下的合理发展,和他以文学“社会重造”、“国家重造”、“民族重造”思路实异曲而同工。《饭桶——见微斋笔谈》、《逛厂甸》和《巴鲁爵士北平通讯(第七号)》三篇文章均为表达沈从文这方面思索的重要文献。
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4卷的《见微斋笔谈——小说上吃人肉记载》、《宋人演剧的讽刺性》、《吃大饼》、《应声虫》和《宋人谐趣》五篇文章,编辑者拟定的题目是《见微斋杂文》。此处发现的《饭桶——见微斋笔谈》一文,应属于这一系列的第二篇。这组文章沈从文的自拟题目应是“见微斋笔谈”。沈从文从浩如烟海的中国野史笔记中选取一些与时弊有关联的细节,将其栉次鳞比地编织在一起,使之生气贯注的是沈从文自身对时局的深忧和暗讽。在酣畅淋漓地发掘历史细节中的诙谐可怖感觉时,沈从文的敏锐而节制的笔锋,同时指向抗战阵营中的某种伪道学习气。比如《见微斋笔谈——小说上吃人肉记载》:“庄季裕《鸡肋》,却叙述到靖康山东各种吃人时情形,被吃的且有各种美好切题名称,使千载后人犹感觉恐怖,恐怖中见出悲悯。因时移世乱,历史所常在,这类事也难免不发生于不可想象情形中……脍炙人口的,是张巡许远守睢阳,杀爱妾享士情。因一面为其所私爱,一面为保国土,激励士气,因之虽情形残忍,却仿佛有悲剧的庄严性。”(13)在这里,沈从文对借好名词吃人现象的抨击,既承袭了“五四”时期批判“礼教杀人”的思路,又与周作人沦陷前反抗宋人道学习气的姿态吻合,其意味也是双重的,既反映了沈从文对抗战阵营中某类混乱粗暴现象的无情讥刺和深切担忧,同时也表达出沈从文对于抗战中逐渐抬头的“新理学”思想的疏远和抗拒。《饭桶——见微斋笔谈》所嘲讽的则是抗战文艺阵营中积极为官者的混饭吃习气,同时隐含着沈从文对自己与群体疏离、被群体漠视的读书人自我身份和处境的体认和坚执:“四个故事正代表四种身份,四种人生态度”,“第四种是混饭吃的卑鄙态度,北宋末有这种人,任何时代也不缺少这种人,每一个国家遭遇困难,社会解体,或外患内乱,改朝易代时,具有这种无所谓态度的人,照例就相当多。”“今古相似而不同,弥衡可说是被‘酒瓮饭囊’压死的,因为话语中损害了这种人的尊严。……现在筵席中,已不用鼓吏,……倒不是言论宽容。只像是‘酒瓮饭囊’已无尊严可伤。”(14)与稍后发表的《〈七色魇〉题记》等文对照阅读,可知沈从文当时早已被以老舍为首的抗战文艺主流阵营指认为思想落伍,的确,沈从文那种深具庄子和道家习气的自在超脱姿态,与老舍等抗战文艺主流阵营同人秉承儒家汲汲救世的热诚担当精神,有着根本的不同。沈从文少量的精雅作品固然没有老舍诸人投身抗战通俗文艺创作的切于时用,可是沈从文超然而开阔的视野也使他从动荡混沌的时局中察觉出了已然开始的触目惊心的国家、民族和社会腐烂和分解,即使众人期盼的抗战胜利,也未能使这种腐烂和分解终止。
《逛厂甸》一文是北平文物美术市场三十年的缩影。它传达了北平乃至整个中国文物美术方面精雅文化品的渐渐消失,传统读书人优游闲适地位的逐渐丧失,和中国人雅文化鉴赏趣味的日趋萎缩。虽然这些是社会平民化和文化通俗化的共同伴生物,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潜在结果,不过在沈从文看来,这象征着中国古典文化的全面沦落,结果是相当凄楚的。因此,他要只身拯救。《逛厂甸》一文也正预示着沈从文即将放弃其内外交困的文学事业,转入他始终流连不已的中国文物美术事业。
此外,此时沈从文的思想变化,也是促使他完成从文学向文物美术转变的重要因素。《巴鲁爵士北平通讯(第七号)》与收入《沈从文全集》第14卷的《北平通信》六篇文章属于同一系列,发表时间是1946年9月—1948年10月。在这组文章中,沈从文或拟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或化身为来自西洋、精通中国文化且与中国上层文人交游密切的巴鲁爵士,对陷于国共交战漩涡悬而未决的中国时局、建筑古雅庄严美丽的故都北平的存亡,以及性情纯良、在血与火中辗转死亡的中国人的前途命运,以一个局外人的口吻,发抒着一个目睹了过多杀戮而心怀悲悯的自由主义文人的深切忧虑和超迈理想。沈从文选择颇具迷惑色彩的巴鲁爵士作为笔名,乃深感事态危急,言路崎岖,事有难言,又不能已于言,因此文章风格庄谐融会,文意晦涩,正如沈从文自己在《故都新样》中所言:“作者既于国事有深忧,文章难为有信而不忧之士所懂”。沈从文所犹者何?非仅关城池古物,乃在“人心趋向”,因为“中国上层,分解圮坍,蛆腐溃烂,自心起始。”(15)可见“杞国无事忧天倾”的沈从文,企图在抗战后千疮百孔的政局中,通过“美育重造政治”,为上层统治者进行渺茫的补天工作,其着眼点同样是人的改造。
这组《北平通信》文章,是典型的论政文章,沈从文与此相关的文章还有《政治与文学》、《性与政治》、《一种新希望》、《中国往何处去》等文,发表时期与《北平通信》大略相同,可一并来看。对于国共两党间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生死存亡的最后斗争,沈从文认为似“一种民族集团在歇司迭里亚之痉挛中挣扎,人人作悍恶困顿状,虽痛苦异常,实无意义,少结果,此起彼伏,如连环之无端。”(16)“余意以为在政治中无妥协,在战争中又无结果,均属事实……。”沈从文认为,要突破这种困局,就应该寄希望于音乐和美术。他提出用音乐来溶解战乱中普通人们苦闷情绪与调和以人民国运作赌注的伟人英雄的坚硬神经,可以使社会国家发展,“稍柔和而具弹性”。(17)并且认为美术作为全人类心智与热情的产物,负有丰饶人民情感,加深其生命深度,消除因宗教情感隔阖和现代政治偏见所引起的战争的责任,通过美术应形成一种新世界观,对人类关系重新修正。(18)沈从文对于音乐和美术的这种殷切期望,实乃其来有自。20世纪初蔡元培就已经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说,希望美育负起维系世道人心的重任。在《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中,沈从文已经提到以“美育代宗教并改造政治”(19)在《故都新样》中,沈从文明确提出了以“美育重造政治”的观点。(20)在《试谈艺术与文化——北平通讯之四》中,沈从文自己多年前即已立志作“美育代宗教之真实信徒”,自己二十年前已有“艺术重造政治”的思想,现在有志于进而言“美育重造政治”,作为蔡元培学说的补充。这里沈氏所谓的政治,“实为用‘美育’与‘诗教’重造政治头脑之政治进步理想政治。”言及此,沈从文的目光已投向遥远的未来,由美育培养下一代领袖,下一代标准公民。(21)
在《迎接秋天——北平通信》中,沈从文有感于当时徘徊于国共两派间无所适从的部分学者文人热衷于为孔夫子祝寿,独辟蹊径,回到孔夫子的平常心和人性上来。他提出:“余意以为研究‘人’出发之‘人性科学’,在最近将来必成为一种世界所关心学问,其重要发现引人注意处,必不下于原子弹。”并畅想一种专家积极参加政治的理想政府。面对现实中与自由主义学人日益疏远的青年学生和不断分化的学术界文化界本身,沈从文对于一种崭新的人生哲学寄予厚望,希望藉此使分崩离析的各阶层“移情忘我”,“使此多数得重新分工合作,各就地位,各执乐器,各按曲谱,合奏一新中国进行曲”。(22)他深信中国历史不会完全用战争点缀,因此,阶级斗争的哲学也有被阶级间和谐的哲学所取代的可能。
在《巴鲁爵士北平通讯(第七号)》中,尽管沈从文对政治和迷信结盟的忧虑,似有历史的预感;可是他对“迷信”依然有所期待,期待着融和爱和生命本源的新的宗教情绪扑灭血与火交融的矛盾与战争。沈从文将“迷信”的重新定义为:“试从人性深处发掘,迷信实和生命同在。是一种生命青春期的势能”;将自己的工作的明确定位为:致力于创造一种“人的科学”,“将为生命本质之被有效控制,游离,转移于旧宗教或新政治以外”。
简而言之,沈从文在抗战前是以“文学独立于政治”的姿态,对抗抗战文艺阵营主流对政治的归附;在抗战后则转而以“美术重造政治”的立场,通过对“人性科学”的探求,企图改造在冲突和矛盾的社会环境中产生诸多对立分歧的人性,达到人性的和谐,和国家远景的繁盛。这在当时虽然不可能实现,现在看来,则具有独特的启示意义。至于沈从文个人,在重重殷忧中抛开时贤,忍痛放弃了自己以“诗教”重造政治的企图,只是孤独地守护着自己以“美育重造政治”的信念,以美术作为“人性重造”的支点,度过了三十余年的寂寞长途。
注释:
①《一个人的自述》、《莲花》和《看虹》分别刊载于香港《大公报·文艺》第775期,1940年1月26日;第907期,1940年8月19日;第1219期,1941年11月5日。
②沈虎雏编,见《沈从文全集·附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第234页。
③刊载于1928年11月10日《新月》第1卷9号,署名甲辰。
④见《新摘星录》第4节,第15页,《当代评论》第3卷第3期,1942年11月29日,昆明。
⑤同上。《摘星录》,《新文学》第1卷第2期,1944年1月1日桂林,文末注明重写于1943年5月。
⑥见《新摘星录》第4节,第15页,《当代评论》第3卷第3期,1942年11月29日,昆明。
⑦见刘洪涛:《沈从文与张兆和》,《新文学史料》,2003年第4期。
⑧见《新文学》第1卷第2期第70页,1944年1月1日,桂林。
⑨连载于《当代评论》笫4卷第3~5期,1943年12月21日,1944年1月1日,1944年1月11日,昆明。未标注写作时间。
⑩初发表时标题为《绿魔》,见《当代文艺》第1卷第2期,1944年2月,桂林。文末注明1943年12月10日重写。
(11)见《当代评论》第4卷第4期第19页,1944年1月1日,昆明。
(12)见《黑魇》,《时与潮文艺》第3卷第3期,第67,68页,1944年5月15日,重庆。文末标注的时间是1943年12月末一天云南呈贡。
(13)见《见微斋笔谈——小说上吃人肉记载》,《文学创作》第2卷第2期,第62,84页,1943年6月1日,桂林。
(14)见《饭桶——见微斋笔谈》,《大公报·战线》第991号,1943年9月24日,重庆。
(15)见《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与《试谈艺术与文化——北平通讯之四》,《沈从文全集》第1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372页,第383页。
(16)同上,第377页。
(17)《北平通信——第一》,见《沈从文全集》第1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356,358,360页。
(18)《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见《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372,375~376页。
(19)《苏格拉底谈北平所需》,见《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375页。
(20)《故都新样——北平通信第三》,见《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369页。
(21)《试谈艺术与文化——北平通讯之四》,见《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383,389,384,385页。
(22)《迎接秋天——北平通信》,见《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395,39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