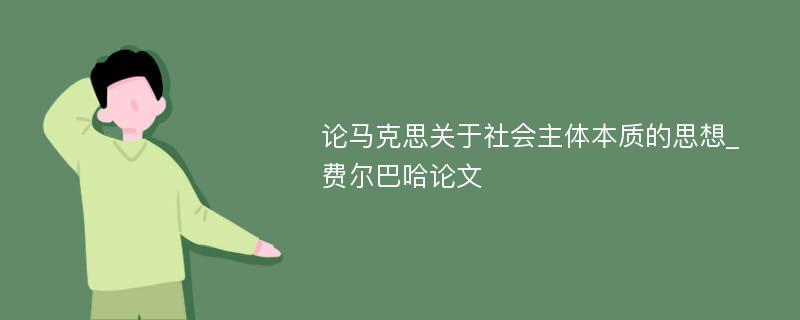
试论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体本质的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试论论文,主体论文,本质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体本质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存在主义者歪曲马克思的学说是见物不见人,漠视人,指责唯物史观中存在着“人学空场”;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阐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以历史客体淹没历史主体,片面强调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忽视人的实践能动作用和主体价值地位,忽视对社会主体的分析研究,从而使丰富、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变成呆板、僵硬的东西,越来越不能适应现实历史的发展。因此,深入研读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挖掘和重现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体本质的完整思想,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2页)那么,作为主体的“人”是什么呢?或者说人的本质是什么呢?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种现实的本质,历史的主体、社会的主体是“现实的人”。根据马克思的论述,我认为,“现实的人”具有如下三个本质规定性。
自然存在物。“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页)这是一个根本前提。同一切唯物主义者一样,马克思认为,作为社会主体的人首先是有血有肉的自然物质实体,首先是现实的自然存在物,他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结果。黑格尔在研究英国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劳动是人的本质的观点,这是黑格尔的一大功绩。但他所说的人,不过是“自我意识”,是绝对精神发展中的一个环节。他将人与精神的关系颠倒了,将人降低为精神的产物,实际上就使“人”失却了主体的性质和地位。马克思指出:“这样用客观的东西偷换主观的东西,用主观的东西偷换客观的东西……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是把某种经验的存在非批判地当做理念的现实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92—293页)费尔巴哈直截了当地批判了黑格尔哲学的全部神秘性,把被黑格尔唯心主义地颠倒了的存在与思维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从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出发指出:“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读》上卷,第115页)费尔巴哈把“人”规定为肉体的人,是感性的存在物。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提供的崭新思想武器,批判黑格尔把劳动归结为“抽象的精神的劳动”,把人归结为绝对精神,认为费尔巴哈把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是可取的,明确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7页)。他的身体和各种器官,他的自然力,生命力乃至整个生命过程都属于自然界并受到自然条件和自然规律的制约和支配。
承认社会主体——人是自然存在物,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都承认人是自然存在物。马克思批评旧唯物主义,并不是反对他们将人看作感性的对象,并不是要否定人的自然本质,而是批评他们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也是从承认人的自然本质出发的。“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页)如果人没有自然本质,不是自然存在物,那么他就只能是一种虚幻的精神性的东西,而这就脱不出唯心主义的怪圈。
实践存在物。人的肉体组织为了生活和在生活中必然产生各种需要,而他所面临的自然界不会自动地满足他的全部需要,因而人必须劳动。费尔巴哈停留在生物学意义的人的规定性上,仅仅把人看作感性的对象,而看不到人同时也是,而且更重要的是感性的活动,人是活动的人、实践的人,自然界和人本身都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尽管费尔巴哈也想认真地研究人,“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所以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一著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规定。”(同上书,第16页)总之一句话,费尔巴哈没有把人“当作实践去理解”(同上)。他不研究人的劳动,更不知道劳动是人的本质,他“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同上书,第50页)。黑格尔天才地猜测到劳动是人的本质,但由于他是客观唯心主义者,“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活动本身的”(同上书,第16页)。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同时吸收其合理的思想并加以唯物主义的改造,揭示出实践首先是生产实践即劳动是社会主体——人的现实本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东西区别于人和动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同上书,第24—25页)可见,生产实践(劳动)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所以,劳动就成了人类生存和一切历史的第一前提和基本条件。这样,马克思就既超越了黑格尔,不是局限于人们的抽象的精神活动来理解人,也超越了费尔巴哈,不是把人仅仅看作自然界的结果和附庸物,而是把人理解为实践的动物,看到了人的实践本质。
人类有劳动,动物有活动,那么是不是说动物也是实践的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人的劳动同动物的活动作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说明人的劳动是在目的的指引下进行的,而且这个目的是自觉的,是“他所知道的”。具有自觉目的性是人的实践活动区别于动物的本能活动的显著标志。(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的自由自在的活动,是对人的本质的肯定,是人的本质的生成。视“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为人的本质,是马克思在研究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过程中扬弃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重要成果。人是从自然中、从动物中发展出来的,但这种发展是分化和超越,通过实践实际地创造一个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的自然界,就是人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并获得主体地位的确证,就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存在物的明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且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劳动使人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的即潜在的力量发挥出来,并在劳动产品上打下这种力量的印记(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因此,劳动活动的对象化也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是实践存在物,他必须通过自身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才能生存,并只有在对象化活动中,才能实现自己的本质。所以,社会主体并不是一般的自然物质实体,一般的自然存在物,而是实践着的能动的物质实体。
社会存在物。人是实践的动物,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是生产实践。“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页)生产“始终是社会的主体”的生产。个人的存在和个人的活动总是以社会整体的存在和发展为背景的,抽象的脱离开社会的孤立个体是不存在的。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人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性的。“个人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是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页)“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同上书,第24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在社会中进行活动的个人当然是出发点,但是这些个人并不是孤立的个人,孤立的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活动是罕见的事。个体的人正是在与他人交往中确认自己,通过他人才反观到自身,人只能是社会的人,所以马克思明白地指出:人“天生是社会动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202页)。
费尔巴哈研究了人与宗教的关系,认为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上帝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他揭露了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但更重要的工作他没有去做。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们分析的现实的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这就是说,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的异化本质的根源在于社会主体的社会关系,他不能对社会主体的社会本质作出科学分析,即不能把人看作社会存在物,而仅仅看作自然存在物,因此,他的哲学只是半截子的唯物主义,他的历史观摆脱不了唯心主义的羁绊。
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人们又必定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实践活动。任何个人不可能脱离和他人的关系,脱离社会而孤立地成为现实的人。所以现实的人不仅具有直接物质性,能动实践性,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具有社会历史性。社会本质是社会主体——人的最高本质。社会与主体是合二为一的统一体,如果将社会看作一个有机体,那么它的产生、构成、变化等全部内容的有机性,仅仅在于主体——人的有机性,在于它是人存在和发展的形式。人创造并构成着社会,个人的存在和发展与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须臾不可分离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39页)马克思还指出,实际上,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而是从属于一个较大的集体。人类自诞生之时就具有了社会性,社会性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上面,我们分别分析了社会主体的三个本质规定。那么,这三个规定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首先,这是社会主体的三个不同层次的本质,三者之间具有层层决定的关系。自然存在物是主体的最基础的本质,没有这一本质,实践本质和社会本质都无从谈起。“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反杜林论》第119页)但是,人怎样开创自己的历史呢?通过实践和在实践中。实践活动是首先人为满足自身需要即对自然进行的占有活动。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2—363页)而这样的活动之所以必然和必须,其内在根据并不在人之外,而在于人自身,人们最初的需要和后来出现的新需要,是社会发展的最深刻的动因。这是从现实历史上看。从理论方法上讲,也只有从经验的人、肉体的人出发,从人的自然本质出发,才能进一步达到对人的更高本质的把握和认识。在这个问题上,从唯物主义出发,就是从人的自然本质出发,把人首先看作自然物质实体。
自然存在物和实践存在物(尤其是后者)又共同决定社会存在物这一本质。“一开始就表明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页)这实际上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在主体本质理论中的特殊表现。生产力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和实践能力的结果,它决定生产关系也就决定人们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这就是说,人们的实践能力决定着自己的社会存在方式。正因为如此,人们的实践能力,从而生产力,从而劳动工具等物质性的东西才可以成为标识社会主体本身发展的精确性的座标;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实现了把对人的研究作为一门科学的伟大创举。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或者在抽象的社会本质内打转,不研究人的实践本质及其发展,或者只研究人的实践本质,不能从中透视人的社会本质,都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深刻底蕴。可以说,正是实践本质使社会本质成为具体的和可衡量的;正是社会本质使实践本质成为现实的和历史的。
其次,实践本质是人的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的中介。由于人的肉体组织的需要,人开始实践活动。通过实践,人们不仅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了自然界,而且同时也改造了人自身。从人的生理构造来看,人类最初的四肢分工、直立行走,头颅形状,大脑形成乃至语言的产生,都是在人们改造自然的实践过程中变化和生成发展的。从人的生物性需要来看,人们在向自然的不断索取中,也就是随着人们实践活动的发展,需要的结构不断地发生变化,不断产生新的需要。马克思指出,人们在不断改造客观条件的同时,也在“炼出新的品质,……造成新的观念和力量。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语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94页)另一方面,由于劳动,主体不仅与自然发生关系,而且同时与他人,与整个社会发生关系。“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页)这就是说,人们的实践本质不仅与人的自然本质相联系,而且更重要的是与人的社会本质相联系,人们的实践活动方式与人们的社会存在方式是一致的,正是前者决定着后者。
不过,人们的社会存在方式并不只是消极受动的,它对人们的实践能力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举例说明人的社会联系使人类具有极大的实践能力。人类正是因为具有社会本质,是社会动物,才由此产生出一种任何非社会性的动物所不可能有的改造自然界的实践能力。
最后,自然存在物、实践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三位一体”,共同构成现实的人——社会主体的综合本质。自然本质是人的物质性的基础本质,实践本质是人的能动性的核心本质,社会本质是人的关系性的最高本质,但它们之间是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我们必须反对离开人来谈实践和离开实践来谈人;必须反对撇开个人谈抽象的社会和撇开社会谈孤立的个人;必须反对脱离实践谈社会和脱离社会谈实践。而应该肯定没有无主体的实践和不实践的主体;应该肯定个人的存在和活动以社会为背景,同时社会也离不开个体的活动;应该肯定没有社会性就没有实践性,没有实践性就没有社会性。自然人、实践人和社会人是统一起来的。从逻辑上讲,人的自然本质、实践本质和社会本质是社会主体的三个不同层次的本质,而在实际上,它们只是三个不同侧面的本质,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刻起,它就同时具有着这三个本质。
相对于人的社会本质来说,自然本质和实践本质具有更大的基础性和稳定性,马克思在考察社会主体的本质时,立足于这两者但并不停留于这两者,而是通过这两者把目光投向人的社会本质,达到对人的社会本质的认识。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表现出来的超越前人的地方正在于他不是在抽象的社会关系中考察人,也不是用对物的关系的考察来代替对人的关系的考察,而是时时处处透过实实在在的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物与物的关系发现人与人的关系,这才是马克思历史哲学的要旨和秘密。所以,无论在《手稿》还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社会主体本质的历史发展的概括都是着眼于人的社会本质,而着手于人的自然本质和实践本质。既以人的社会本质为主线来描绘人的本质的历史发展,但一刻也没有离开人的实践本质,而且正是以人的实践本质、实践能力为精确的尺度来衡量人的社会本质的发展。所以我们在研究社会主体的本质时,绝不能片面地强调某一侧面,而应该坚持统一的社会主体本质论,并将每一本质置于其应有的位置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现既是受动的,又是能动的,既是单个的,又是社会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的现实的社会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