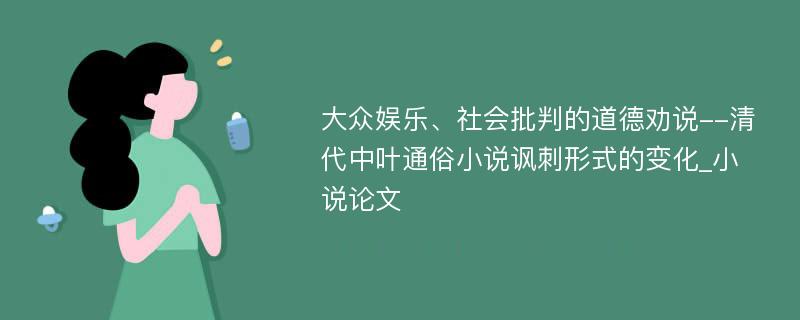
大众娱乐、道德劝戒到社会批判——清中叶通俗小说讽世形态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通俗论文,形态论文,道德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6051(2009)02-0048-06
清代中叶,一大批具有很高文化修养的文人参与通俗小说的创作,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慨,发表自己的社会人生观感,在内在精神上形成一个群体,这些通俗小说被有的学者称为文人小说[1](P461)。文人小说的创作主体、创作观念、叙事手法有了明显的新变,而引起这些新变的则是这些文人小说关注焦点的变化。由于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书坊商业性运作的操纵,文人小说家能够更真切地关注社会,对社会的批判也就更为深刻。与前两个世纪的通俗小说相比,清代中叶的通俗小说将目光投向了真正的社会,而不是虚拟的伦理世界和道德的虚拟空间。清代中叶文人小说的社会批判与文人情怀的抒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文人英雄梦交织在一起,使得清代中叶文人小说的社会政治批判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
一、摇摆于道德劝戒和娱乐之间
如果把隋唐时的讲经、说唱作为通俗小说的开端,那么通俗小说从一开始即在道德劝戒和娱乐大众之间摇摆不定。宋代的话本和文人的话本拟作中,娱乐和劝戒都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市井的说书艺人和书会才人挖空心思搜求、编写曲折生动、充满刺激的故事,因为追求娱乐的市井大众是他们的忠实听众和衣食父母;但另一方面,艺人和才人们以市井中的文化人自居,感到有宣传伦理道义,对世俗大众进行劝戒的责任,因此他们不仅在故事结尾总要归纳出对世俗人生有指导意义的哲理和教训,而且说书人在讲述的过程中不时地出来解释故事片段的生活借鉴价值。
到了明代,通俗小说作家和书坊主更强烈地感觉到娱乐和劝戒的双重压力。一方面,书坊主为了达到赢利的目的,为了以新奇的故事吸引尽量多的读者,在书坊如林的印书业中求得生存,雇佣文人为其编辑、改造和写作故事;而另一方面,通俗小说的大量编辑出版,使文人深感为其正名、争取合法地位的必要,特别是李贽、汤显祖、袁宏道等带有叛逆色彩的文人,怀着挑战传统的心理,宣称通俗小说与正统诗文史传一样可以不朽。但叛逆文人和通俗小说的编写者为通俗小说争取地位的名义显然不同,叛逆文人认为小说与诗文一样可以抒情泄愤,而一般的通俗小说作者则强调通俗小说净化道德的作用。《清平山堂话本》中的一些模棱两可的故事,经明代通俗小说家的改编,被赋予了鲜明的道德色彩。警世、醒世、喻世、醉醒石、石点头、贪欣误等等,仅仅这些话本集的命名,就表现出强烈的劝戒倾向,而劝戒的内容,涉及儒家伦理道德的各个方面以及人生的种种误区和陷阱。章回小说也不例外。历史演义要向大众传授历史知识,总结历史教训,同时也可以劝化风俗,如张尚德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中所说,通俗演义用俗近语,使听众入耳、通事、悟义、兴感,裨益风教。[2]神怪小说如《韩湘子全传》、《南游记》、《三教开迷演义》、《天妃济世出身传》等,则用荒诞离奇的故事宣传宗教教义。至于世情小说《金瓶梅》,据欣欣子所说,作者的写作是为了“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此书“关系世道风化,惩戒善恶,涤虑洗心,无不小补。”[3]《金瓶梅》对淫欲之害的强调,让人想到明代中后期的纵欲风气和艳情小说的泛滥。在这些艳情小说中,对淫欲的露骨描写之后常常附上要节制淫欲的劝戒。明代中后期通俗小说中鲜明的道德训诫色彩,或许与《太上感应篇》等善书和功过格的流行有一定的关系。
并非所有清中叶之前的通俗小说都没有个人情怀的抒写,如秦淮墨客就指出《杨家府通俗演义》表达了一种人生态度[4],邓志谟也称自己的一系列神魔小说表达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追求。即使在话本小说中也偶尔可见作者的情感流露,如《警世通言》中被认为是冯梦龙自己创作的《老门生三世报恩》中就蕴涵有失意文人的感慨。到清初,通俗小说中个人情感的表现越来越鲜明,古宋遗民的《水浒后传》隐含着作者的亡国哀痛,被称为泄愤之作[5];《西游补》的作者声称要借小说“入情内,破情根,悟大道”[6],对上下古今的嬉笑怒骂中隐隐可见作者的面容。话本小说《十二楼》中有九篇为作者李渔的创作,表现了李渔的生活情趣和人生态度,其中《闻过楼》篇中的顾呆叟甚至就是作者的自喻。情况相似的还有署名圣水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在这一时期新出现并迅速繁荣的才子佳人小说,借青年男女的风流韵事,抒写文人心中的黄粱事业,小说中的才子是美人富贵兼得,而现实中的小说作者则常常要为最基本的生活而奔波,所以有的小说作者承认,小说中的歌与笑正是现实文人的悲与哭。
但是道德训诫仍是17世纪通俗小说无法忘怀的题旨。17世纪最成功的通俗小说之一《醒世姻缘传》,虽然被有的研究者称为文人小说[7],但“醒世”的标题和道德教育的内容显示了它与劝世话本的血缘关系。更重要的是,《醒世姻缘传》采用了话本小说常用的因果报应来结构情节,在明代以及清初的话本小说中,因果报应是最有力的道德劝戒工具,违背道德伦理规范的人要受到现世报或者在来世受惩罚,《醒世姻缘传》中的晁源和狄希陈,计氏和薛素姐,都是在世后仇报仇、冤报冤,最后靠佛经的力量才将前世的怨隙化解。
17世纪的通俗小说也逐渐将视角转向真正的社会政治批判,如《西游补》在对历史人物的变形描写中,在嬉笑怒骂中,表达了对历史的嘲讽,对现实政治的尖锐批判,不仅有对误国奸臣的仇恨,而且对有至高无上权威的皇帝的昏庸无能也表达了前所未有的嘲讽,这部小说也第一次把科举对士人心灵的腐蚀表现得如此形象和深刻。但社会政治批判明显不是17世纪的通俗小说关注的焦点,有的讽刺批判显然缺少社会政治批判的广度和深度,比如《西游补》、《鸳鸯针》以及文言小说集《聊斋志异》等中的科举批判,更多的是从个人的角度,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牢骚,因而不会有《儒林外史》那样的反思深度。
二、文人情怀抒写中的社会政治批判
不可否认的是,清代中叶的通俗小说并未完全抛弃道德劝戒,历史演义小说的编写者仍然在称扬通俗说部普及历史知识的优势,而英雄传奇小说的编写者和出版者则强调通俗小说表彰忠烈、净化风俗的巨大作用,话本小说如《通天乐》、《雨花香》等则从现实生活中搜集素材,力求以新颖的、易为读者接受的故事达到更好的劝戒目的。但是,这类小说不是清代中叶通俗小说的主流,位于中心位置的是文人创作的小说,而文人小说抛弃了对世俗大众的道德劝戒。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在清代中叶,最适于充当道德教材的话本小说走向衰落,高水平文人的参与也未能挽救其命运。
在清代中叶的文人小说中,仍然涉及道德问题,但却不是以劝戒为目的,道德问题与文人的自我意识联系在一起,获得了新的意义。例如对嫌贫爱富的势利小人的批判,是此前话本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而在清代中叶的文人小说中,深受势利之害的几乎都是文人书生,因此这种道德批判中实际上蕴涵了作者浓重的文人情结。在《金石缘》中,势利的富户林家背弃了与才子金玉的婚约,因为金玉变得一贫如洗,而且染上了一身疯癞之病,但事情的发展出乎林家的预料,金玉以出众的才华高中头名状元,又率领大军平定大炉山贼寇萧化龙和台湾海寇的叛乱,被封为侯,不弃贫贱、尊重才识的石无瑕也因而得享荣华富贵,而林家却受到了最严酷的惩罚。在小说中,林爱珠和她的父亲被描写为道德败坏不堪的人,利图父子则是贪官污吏,与书生金玉形成鲜明的对照。
类似的还有对忠奸斗争的描写。大多数文人小说写到了忠与奸的对立,例如《金石缘》中金玉与奸相卢启封的对立,《野叟曝言》中文素臣与阴谋篡位的景王一党的激烈交锋,《绿野仙踪》中冷于冰与严嵩父子及其党羽的冲突,《希夷梦》中仲卿、韩速与奸臣包赤心、余大忠等的斗争,《飞花艳想》和《梦中缘》中严嵩对才子柳友梅、吴瑞生的陷害,等等。文人小说中的这种忠奸的斗争模式,显然受到前代传奇的影响[8]。从明代的《宝剑记》、《义侠记》一直到清中叶的《鸳鸯镜》、《无瑕璧》、《桂林霜》,忠奸斗争是最主要的描写题材和主题之一。在清代中叶的英雄传奇故事如说唐、说宋系列小说中,忠义之家与祸国奸臣的斗争不仅是故事的起因,并且是推动故事发展的最主要的力量。作为政治斗争的集中体现,忠奸斗争是从远古的传说时代到封建时代的永恒主题。在元明时代,政治批判与道德批判联系到了一起,奸臣一般都是道德上有问题的人,市井文化渗入了文学的政治批判之中。文学作品中鲜明的政治批判,叙事文学对忠奸斗争的关注,可以从文人传统的社会批判意识找到深层的文化根源,以掌握所谓的道自居,认为道高于现实,是衡量现实政治的最高标准,使得文人有了批判的自信,而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主义,也让文人感到现实社会政治批判的责任。晚明的东林党人高标“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批评朝政,与阉党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让人想到东汉时代的党锢之祸。明亡之后,顾炎武总结历史教训说:“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9](卷五《清议》)清代中叶文人小说中的政治批判,正是通俗小说文人化的必然结果,通俗小说由书坊走向书斋,自然地将关注焦点从世俗道德劝戒转向文人视为己任的社会政治批判。
但是清代中叶文人小说中的社会政治批判又有与文人传奇和同时代的英雄传奇故事不同的特点。一方面,文人小说中与奸臣进行斗争的不是朝臣,而是像《野叟曝言》中的文素臣、《绿野仙踪》中的冷于冰这样的在野文人。联系清代中叶包括这些小说作家在内的士人多穷愁不遇的事实,可以体察到这些小说所描写的忠奸斗争中蕴涵的文人情怀。奸臣的阴谋陷害恰恰促成了文人英雄的功业,而铲除权奸是文人事业的组成部分。仕途之外的文人担负起与权奸斗争的重任,本身即是对政治的一种含蓄的批判,虽然这些文人英雄大多被朝廷接纳,但他们往往在平定叛乱,铲除权奸,获得朝廷的承认之后,却又毅然退出政坛,避入深山或者过起田园生活,这种安排虽然可以认为是儒家功成身退理想的表现,但也体现了清代中叶文人的幻灭与感伤,同时也是对科举用人制度的怀疑。确实,这些文人小说家以及与他们同时的学者是那个时代的文化精英,却要为最基本的生活而奔波,脑满肠肥的官僚则是庸碌无能者,国运的昌隆显然不能指望他们。在文人小说中,虽然也有不与权奸同流合污的大臣,但如果没有在野文人的参与,他们几乎无能为力。文人小说中孤独的文人英雄和朝廷官员形成较为鲜明的对照。
在清代中叶的文人小说中,贪官污吏的不法举动已不是简单的道德问题,而是严重的社会政治肿瘤。《儒林外史》中的汤奉一上任就打听地方的出产,范进这样的人之所以对中举有着疯狂的欲望,除了可以获得人人羡慕的荣耀,最主要的还是可以一改贫困的经济状况,一夕之间即获得富贵,而金银财产就是来自对地方的盘剥。《红楼梦》中葫芦庙门子的护官符道出了为官的真谛。一个门子能总结出这样的为官之道,说明官场的腐败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绿野仙踪》中贪得无厌的县官甚至连冷于冰捐献的赈灾善款也不放过,督军平寇只是为赵文华提供了搜求财物的大好机会。在十六、七世纪的通俗小说中虽然也有对卖官鬻爵、科场舞弊的描写,但多是作为异常的行为来描写的,而在清代中叶的通俗小说中已经成为被多数人认可的行为,《红楼梦》中的那个内监以谈生意的口吻说起龙禁尉的买卖,《儒林外史》中用银子不仅可以免除假扮官员的罪罚,而且能够变假成真。在一些文人小说中,不第的士子背着行囊,一边替富家子弟科考以赚取生活费用,一边寻找适当的时机追求自己的功名,而在前一个世纪中,这种科场舞弊还是令文人极度痛心的。
如果说文人对权奸的斗争带有较多的虚拟色彩,是文人小说家为了表现自己的济世抱负而进行的艺术虚构,那么对腐败官场的描写,对堕落世风的批判则有更多的写实成分。虽然雍正帝制定出种种措施来对付官僚的腐化,但严厉镇压的恐惧终究抵抗不住财富的巨大诱惑,养廉银的设置无论如何也满足不了那些贪得无厌的饕餮的胃口,所以到乾隆时,就在惩治腐败的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的时候,贪污腐化已渐渐地成为散播在空气中的毒素。连像袁枚这样有正义感的官员也承认,当几年知县就可以赢得下半辈子的生活费用,过起奢侈的生活,而如果仅仅靠薪水,显然是根本不可能的。对财富的贪婪必然伴随着渎职,吏治的败坏于是一发不可收拾。搜刮民脂民膏以至于赈灾款,侵吞治河的经费而不顾千万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危,在案件的审理中为了贿赂而颠倒黑白,如此等等,文人小说中都有深刻的揭露。
值得注意的还有对战乱的描写。几乎所有的文人小说都写到了叛乱或山贼草寇,如《驻春园小史》中被诬陷的才子黄玉史在充军的途中,被先已投大义山入伙的侠士王慕荆劫上大义山,而本来黄玉史被强加的罪名就是通联盗匪;《五凤吟》中广东南雄知府郑飞英被贼寇围困,祝琪生率领军队才大破盗寇;《幻中真》中强盗在二妖狐的帮助下起兵反叛,是文武双全的吉梦龙平定了叛乱;《金石缘》中则有大盗萧化龙在大炉山占山为王,担负起平叛重任的是小说的主人公才子金玉。这些对叛乱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中叶的情况,虽然国内安定,没有大的动乱,但小的骚乱一直不断,特别是对边疆的大规模用兵,几乎绵延了整整一个世纪,无疑为这些文人小说提供了素材。但这些描写中着意虚构的成分显然更多,因为叛乱的发生,为文武双全的文人主人公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也使得文人小说家才能无所施展的郁闷稍为舒展。
所以,清代中叶文人小说的社会政治批判带有鲜明的个人表现色彩,道德问题被提高到了社会批判的高度,而社会批判是在个人胸怀的抒写中实现,或者说社会政治批判是他们表现自我的方式之一。我们可以以《儒林外史》、《何典》、《钟馗平鬼传》为例看看清代中叶文人小说讽世的几种形态。
三、清代中叶文人小说的讽世形态
成书于康熙年间的《儒林外史》,被称为中国最伟大的讽刺小说。对小说主旨的理解,虽然没有明显的分歧,仍然有许多讨论文章试图对这部已被公认为批判科举制度的通俗小说作新的解读。按照传统的理解,这部儒林小说是对士林的讽刺,或者是在讽刺中寓有对毒害士人的封建科举制度的批判。小说确实以很大的篇幅讽刺了一些士人的行为,特别是前半部分,有些讽刺是非常尖锐的。周进在贡院前的号哭,范进听到中举消息后的发疯,让我们想到《西游补》中的类似描写,范进和那双象牙筷子,严监生和两根灯草,都是对士人的缺陷的嘲讽。侥幸进入仕途的文人,首先想到、也只能想到的就是攫取富贵,王惠、汤奉等成为贪婪成性、敲骨吸髓搜刮民脂民膏的贪官猾吏,严致中、张敬斋等则依仗功名在乡里横行霸道。匡超人、牛浦郎一步步地走向堕落,冒充名士,包揽词讼,忘恩负义,诋毁师友。但是,如果把《儒林外史》仅仅视作儒林群丑现形记,即使不能说是错误的,也是片面的。它显然不是对儒林故事的简单汇编,它超过前代儒林小说的,不仅是描写的集中和形象,更在于深度和广度的开拓。《醒世姻缘传》、《世无匹》、《终须梦》、《女开科传》等小说中的片段描写,无法与《儒林外史》相比自不待言,即是文言小说《聊斋志异》和话本小说《鸳鸯针》等,也只是本着个人感愤的个别批判,其针对的也多是文人的道德品质问题,而《儒林外史》则将这种批判提高到了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高度。
有的研究者从《儒林外史》中找到了时间发展脉络,认为这部小说采用了史书纪传体的结构,是一部士林没落史。实际上,相对于时间,《儒林外史》中的空间更应该受到重视。所谓的片段聚合式结构,因为缺少贯穿始终的明晰的线索,在早期被认为是《儒林外史》的白璧微瑕,但近来这种散漫的形式被称为独到的结构艺术。实际上,作者的如此安排,是为了在纵的时间线上实现空间的拓展,小说叙述的焦点人物频频变换,小说人物不断地游走,使描写的笔触涉及士人的各个层次,涉及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从为了每年十二两馆金在肮脏的破庙中忍受屈辱的不第穷儒,获得点滴功名在乡间扬威的无德贡生,不用为衣食发愁而有闲暇假扮名士的富贵公子,到有机会接近皇帝的大儒名贤,从山东的一个偏僻落后的小镇,广东的险恶的城关,到繁华热闹的杭州西湖,明代开国都城文化中心南京以及威严的京城,小说所揭示的已经不是个别的偶然现象,已经不是士人的个人道德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浓雾弥漫悲凉,从这一角度,才能理解贤人们的三山门话别,才能理解泰伯祠倒塌的意义。
所以也就不能将《儒林外史》简单视为对士人、儒林或八股、科举制度的批判。《儒林外史》是以文人的独特视角,从儒林的角度切入的社会批判和文化反思。在多数情况下,小说对文人同情多于讽刺。小说中的马二先生沉迷于科举,但他急人之难、不吝钱财、诚笃善良,有许多可爱之处,虽然他也有迂腐、庸俗、无知的一面。实际上,甚至范进、严监生、匡超人等,作者也寄予了同情和理解。周进、范进的贫穷无助,世俗的偏见、势利与白眼,才促使他们为科举而沉迷发疯。靠喂猪、磨豆腐维持最平常的生活都不可得,积极上进的孝子匡超人为了生计不得不一步步走向堕落。在为财势和虚名而举国若狂的时代,天真而热爱知识的贫家孤儿牛浦郎的所作所为是值得同情的。这些贫穷的士子让我们想到清代中叶为了生计而到处奔波、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文人,包括吴敬梓这样的文人小说家。正是本着对文人处境的理解,《儒林外史》对士人表达了最大限度的同情。《儒林外史》真正着力批判的恰恰是让儒林没落的社会,薛家集的愚昧,五河县的势利,都是作者强烈批判的,对假名士的讽刺也恰是对真名士的肯定。尊敬士人的戏子鲍文卿受到表扬,附庸风雅的投机商人受到嘲讽,而以财势破坏世风、贬低士人的商人如方盐商之流更受到尖锐的批判。那两个秀才对胆敢穿士人服装的妓院龟子的咒骂和殴打,表现了士人强烈的自觉和对势利社会的强烈仇恨。所以,也许把《儒林外史》看作一部儒林悲剧和世俗喜剧更为合适。楔子中王冕对儒林的预言即指明了小说应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是文人的厄运,另一方面是文人维持文运、对抗世俗化的努力。
与《儒林外史》的寓戚于谐不同的是玩世不恭的讽世小说,其中的代表作品是《何典》。《何典》与《钟馗平鬼传》、《常言道》、《妆钿铲传》等小说形成了清代中叶通俗小说的一种类型。《何典》通篇写的是鬼的故事,在小说的开头即明确了描写的范围。不同于其他神怪小说的以人间对照神魔,这部小说讲的是纯鬼怪的故事,除了其中的形象以鬼来命名,很少有一般神怪小说神奇的法术变化。在阴山的鬼谷中,野鬼们过着世间普通人的生活,“也有念书的,也有种田的,也有做手艺,做生意的。东一村,西一落,也不计其数。”因此也就不可能给其中的鬼怪设置人间的参照系。《何典》是一部寓言讽刺小说,正如太平客人在序言中所说,《何典》“其言则鬼话也,其人则鬼名也,其事实则不离乎开鬼心……真可称一步一个鬼矣”,但不能不担心“读是编者疑心生鬼”[10](太平客人《何典序》),因为小说实际上是对现实社会的鲜明批判。
虽然小说写到了财主的吝啬,三家村的势利,鬼庙里和尚的好色贪财,脱空祖师庙中师姑的助纣为虐,但小说讽刺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官场。作者在第二回的开篇词中就指出“赃官墨吏尽贪财”。小吏催命鬼依仗当方土地的势力,在地方上无恶不作,到处讹诈钱财,土地饿杀鬼更是又贪又酷,极其好色。布政轻脚鬼搜刮足了民脂民膏后,退官回家享受,而他的儿子依仗其财势无恶不作。在鬼世界中也盛行卖官鬻爵,饿杀鬼向识宝太师行贿,代替白蒙鬼当上了枉死城的城隍。当识宝太师的女儿畔房小姐打死豆腐西施,豆腐羹饭鬼告状时,饿杀鬼听从刘打鬼的建议决定以两个大头鬼顶罪,因此激反了大头鬼,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动乱。而鬼门关的总兵胆小无能,在叛军威胁之时竟然弃城逃跑,致使酆都城面临覆亡的危险。
这部小说与众不同的是在社会政治批判中所采用的语调。小至求子、谢神、婚姻,大到官场政务,都被作者当作可笑的鬼话,甚至最高统治者也成了作者的笑柄。在小说结尾,阎罗王宣众鬼入朝,论功行赏,所谓的青史留名,所谓的君臣际会,夫妇团圆,荒唐的鬼世界还要存在下去,整个鬼世界也不过是个不大不小的笑话。刘半农在为重印《何典》而写的序文中就指出作者的态度:“此书把世间一切事事物物,全都看得米小米小;凭你是天皇老子乌龟虱,作者只一例的看做了什么都不值的鬼东西。”[10](刘复《重印何典序》)从小说的叙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愤世嫉俗的文人小说家。
《何典》每回前都有通俗小说惯用的显示风雅的诗词,但却采用了粗俗的格调,如第一回开首的《如梦令》:“不会谈天说地,不喜咬文嚼字,一味臭喷蛆,且向人前捣鬼。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活死人和臭花娘的姻缘是对才子佳人小说的模仿;活死人的求师学艺、打败叛军、建功立业,是以儿女英雄小说为代表的清代中叶通俗小说中最常见的情节,而在《何典》中被以戏谑的口吻讲述出来。但另一方面,我们仍可以从小说中找到稍微严肃的、有作者个人色彩的东西,那就是对文人的描写部分。通读全书就可以感到,小说写到书生时语调变得温和。秀才形容鬼是小说中受到嘲讽最少的形象,他有一副热心肠,重视亲情,在充满势利的鬼世界中特别突出。形容鬼被白蒙鬼请去当幕僚,热心公务,担当起守卫鬼门关的重任,在强盗犯关时,又出谋划策,并亲自带兵上城防卫,被长舌妇称为吃狗屎忠臣,城池陷落时,只有他以身殉国。另一个读过书的鬼是温柔乡里的臭鬼,他本来思量要入学、中举人、发科甲,但文章却总不入试官的眼,心灰意冷,为了谋生而弃文经商。小说中的活死人没有其他鬼的恶劣品质,他是阳间白面书生下降,因而天生聪明,十几岁时就文才出众,令老先生甘拜下风;学武艺则在很短的时间内超过了他的师兄,武功高强,能够打败黑漆大头鬼带领的叛军,挽救了濒临灭亡的鬼王朝。他还能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救了臭花娘,与臭花娘缔结姻缘。这几个读书人身上有现实社会中文人的影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何典》与《儒林外史》在深层精神上有着相通之处。
有必要提到清代中叶的两部钟馗系列小说,即《钟馗平鬼传》和《精神降鬼传》,虽然这两部小说沿用了以前的钟馗小说的故事模式以及寓言讽刺的形式和手法,但仍然可以发现一些细微变化。在以前的钟馗小说如《斩鬼传》中,有为戏谑而戏谑的倾向,钟馗所斩的鬼是捣大鬼、绵缠鬼、寒碜鬼、酽脸鬼等,只是涉及一些个人道德或性格问题,有的甚至只是一些笑料;而《钟馗平鬼传》、《精神降鬼传》则将讽刺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社会问题,显示了作者的济世之心。
随着社会政治的发展,不断变化的时代政治问题进入文人的批判视野,清代中叶文人小说的社会批判主题也随着发生变化,比如十八世纪末的《蜃楼志》就注意到了海关官吏贪污横行的问题。广州互市的设置是在乾隆二十二年,洋商与盗贼勾结作乱,也是海关贸易发展之后才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蜃楼志》反映的是新的社会问题,与现实非常贴近。小说的作者庾岭劳人在开卷诗中说:“心事一生谁诉?功名半点无缘。……妆点今来古往,驱除利锁名牵。”[11]作者正是以落魄文人的姿态对社会政治进行批判,小说中的文人李匠山若隐若现,却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是黑暗社会政治的旁观者、见证者,又以局外人的姿态参与社会政治,最后又毅然辞官,飘然而去,这个人物的身上无疑有作者的影子,寄托了作者的情志。
总的说来,清代中叶文人小说中的社会政治批判与文人的英雄事业梦以及文人的自我张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表现了现实中文人的济世热情和自我实现的强烈渴望。如果联系清代中叶包括绝大多数文人小说家在内的文人的处境,就会体会到这种强烈的现实批判责任意识中蕴涵着传统儒家的理想主义精神。
标签:小说论文; 儒林外史论文; 文学论文; 醒世姻缘传论文; 道德批判论文; 绿野仙踪论文; 金石缘论文; 西游补论文; 叶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