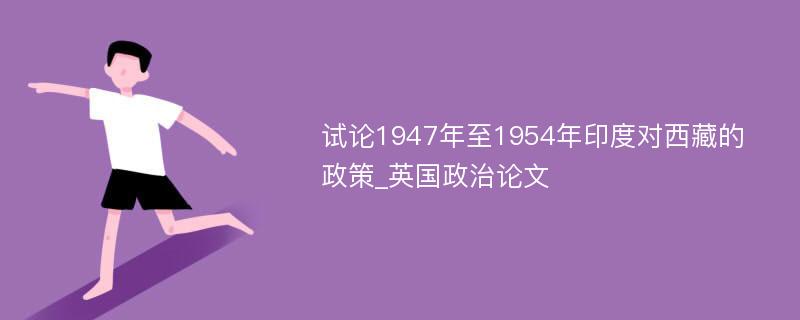
论1947年—1954年印度对藏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印度的西藏政策是从英国继承的。英国的西藏政策形成于19世纪末英俄“大角逐”(the Great Game)扩展到西藏之后,它企图以反对他国控制西藏、制造和保持西藏的缓冲状态来保障印度的安全。本世纪上半叶英国的所有侵藏活动和炮制所谓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 Suzerainty)理论,无不源自该政策(注:李铁铮:《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页1~2。)。印度在独立前夕, 就继承在藏权益与英国达成一致, 为获得西藏的认可, 英印于1947年7月就此分别通知噶厦(西藏地方政府),不管后者是否同意, 英驻藏使团于8月15日印度独立时摇身变为印度使团, 其人员全部留任,“唯一明显的变化是易帜”(注:H.理查森:《西藏及其历史》( H.Richardson,Tibet and ITs History,伦敦,1984年),页173~174。)。这类强加于人的行为使噶厦震惊,遂于10月致函印度总理兼外长尼赫鲁,要求归还被占土地,11月正式拒绝印度的要求。在以放松贸易限制和支持西藏独立的诱骗未成之后,印度驻藏代表、英国老牌侵藏分子理查森(H.Richardson)威胁要断绝印藏间一切交通往来(注: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86年版),页227~229。)。西藏的对外交往和绝大部分贸易均借道印度,噶厦恐慌之余一筹莫展,只得保持沉默。印度的政策也留有余地。1949年初,印度答应满足西藏的部分贸易和外汇需求。虽然尼赫鲁明知不能支持西藏独立,但还是欺骗说西藏可以在印度派驻大使,此前可设商务处,再逐步改为大使馆(注:夏格巴:《藏区政治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下卷,页226~227。)。印度背着中国政府进行了上述活动后,又加之以欺骗。1949年1月, 印度外交秘书梅农(K.P.S.Menon)向中国大使罗家伦表示印度不会与西藏谈及有关中国主权的问题(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蒙藏委员会档案:“西藏商务代表团出国经过及在英、美情形”,全宗号141,卷号3982。); 尽管尼赫鲁于1947年12月告诉罗家伦印度不会继续英国的西藏政策,但他仍表示:印度视西藏为一自治地区,只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蒙藏委员会档案:“西藏商务代表团出国经过及在英、美情形”,全宗号141,卷号3982。)。由此可见, 印度不仅希望继承英国的在藏权益,而且也企图继续英国的对藏政策。
印度领导人对中国政局日益感到不安,他们在1948年就开始丧失对国民党的信心,因此较早地对其西藏政策进行了检讨。面对崛起的中国,如何维持西藏的缓冲状态和保证印度的安全呢?驻华大使潘尼伽( K.M.Panikkar )——与梅农同为尼赫鲁对华政策的主要顾问——向尼赫鲁提交了一份名为《西藏未来及其在印度政策中的作用》的长文件,他认为共产党最终会在中国上台并将全力重建对西藏的统治,但印度仍要支持西藏保持自治。这是因为:1.印度已继承了英国的涉及西藏自治、商业、驻藏使团和麦克马洪线等权益,西藏保持自治本身就是保持其他在藏权益的前提;2.中国一旦占领西藏,就会像1910年那样宣称尼泊尔和不丹是它的属国,这是绝不能答应的;3.“麦克马洪线是印藏谈判达成的,若印度接受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且中国不承认西藏的自治,则中国有相当资格说,与西藏协议而成的边界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的统治到达印度实际的边界将会造成它所有边界的不安,这将成为印度此后的主要困难”。潘尼伽认为印度不仅应该、而且能够保持西藏自治。他估计在中国恢复对西藏的统治前也许有10年时间,此间西藏将会抵抗,印度应提供武器装备并训练其军官,提高藏军的战斗力。而且,印度应在外交上支持西藏,加之地理障碍,就可以阻中国于西藏之外了(注:A.兰姆:《1914 ~1950 年的西藏、 印度和中国——英帝国外交史》( A.Lamb,Tibet,India and China 1914~1950:A History of ImperialDiplomacy,赫福德郡,1989年),页517~519。)。 值得注意的是,潘尼伽排除了印度与中国兵戎相见的可能。尽管潘尼伽正确认识到中国事态的发展方向,仍未能充分估计新中国解决藏事的巨大力量。因此,尼赫鲁接受了上述建议后,又不得不根据事态的发展对其进行不断地调整。
二
印度以秘密武器援助西藏和支持西藏独立的空头支票大大刺激了西藏独立分子的欲望,引发了1949年7月的“驱汉事件”, 理查森则起了导演的作用,他事前密告说:“拉萨有许多共产党,留他们在这里,将会充当内应,引进解放军”(注:夏扎·甘登班觉:《1949年夏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起的‘驱汉事件’的来龙去脉》, 载《西藏党史通讯》1984年第5期。)。该事件是印藏乘中国政权更迭之机, 企图重演1912年驱汉的历史,为达到西藏孤悬于外的目的而制造的。然而他们却未料到中国共产党的愤怒反应。新华社在9月2日发表社论,指出该事件纯为英美及其追随者尼赫鲁政府所为,警告其在西藏止步,否则必须承担全部责任。社论强调要解放西藏在内的所有中国领土(注:《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选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页548~550。)。中国共产党随后又指出印度的目的是企图确立它对西藏的宗主权(注:R.K.贾因编:《中国和南亚关系文献集(1947—1980)》,第1卷(印度)(R.K.Jain,China—South Asian Relations1947—1980,vol.1:India,新德里1981年),页4~6。)。虽然尼赫鲁把上述反应视为革命者难抑的激情,但他不能不正视中国复兴的现实,无论从和平中立的外交原则还是从保持在藏利益的考虑出发,印度都必须与新中国打交道,承认新中国政府已成为保持其在藏利益的先决条件(注:《尼赫鲁演说集,第2卷(1949—1953)》(J.Nehru's Speeches,Vol.2,1949—1953,新德里,1954年),页147。), 也符合以外交手段支持西藏自治的政策。尼赫鲁关于世界格局和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也推动了印度对新中国政府的承认。冷战开始之初,他就决定采取和平中立和与各国友好的外交政策(注:B.R.南达:《尼赫鲁时代的印度外交政策》(B.R.Nanda,India Foreign Policy:The Nehru Years,新德里,1976年),页134~135。),他自信能与中国共产党人对话,展开英国人不能获得的富有成效的谈判(注:J.尼赫鲁:《印度的外交政策》(J.Nehru,India Foreign Policy,新德里,1961年),页309。 )。为此,他力排异见特别是副总理帕特尔(S.V.Patel )关于中国以承认印度在藏利益换取印度的承认,否则就与美英保持一致的建议,同时又坚决抵制美国的引诱和压力。尼赫鲁还力主尽早的特别是赶在英国之前承认新中国,以向中国显示印度并非英国的尾巴。1949年12月30日,印度正式承认新中国。尽管尼赫鲁对中国先谈判后建交的做法深感不满,仍作了让步(注:爱德温·W.马丁:《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胜利的反应》(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页134 。)。1950年4月1日,两国正式建交,潘尼伽出任驻华大使。
尼赫鲁力主和急切地承认新中国并与之建交,是为了保持在藏权益。尼赫鲁后来指出,承认的目的就是了解中国并与之打交道;潘尼伽对此后两国消除误解和建立合作关系表示乐观(注:K.M.潘尼伽:《在两个中国——一位外交官的回忆》(K.M.Panikkar,In Two Chians:Memoirs of a Diplomat,伦敦,1955年),页102;另见S.戈帕尔:《尼赫鲁传(第二卷)》(S.Gopal,Jawaharlal Nehru:A Biography,Vol.2,德里,1979年),页64~65。);理查森对此则有以下阐述:“1950年1月,印度承认中共政权,其原因不只一个,但就西藏而论, 则给印度保持在藏利益以最好的希望,中国从未接受英国、因此也不会接受印度的在藏地位。所以如果印中无官方联系,一旦中国入侵,印度在西藏的存在将很容易被驱除,要么印度为此与中国对抗,但这是不可能的。印度一旦承认中共政权,将能与之进行定期的外交对话。作为承认新政权的第一个非共产主义国家,印度甚至可以期待中国的某些感激,以期缓和中国在西藏的行动”(注:H.查理森:《西藏及其历史》,页179~180。)。
印度与中国建交后,积极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朝鲜战争爆发后,它拒绝追随美国谴责中国。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劳氏(B.N.Rau)在1950年9月指出,印度的行动完全是为了它自己的利益(注:R.K.贾因编:《中国和南亚关系文献集(1947—1980)》,第1卷(印度),页22~23。)。该年8月12日、22日和10月21日、28日, 印度曾几次递交照会或备忘录给中国政府,以撤回它对联合国威胁中国不要采取或停止对西藏的军事行动的支持,这也证明了印度的目的,尽管其考虑不仅仅限于西藏。
如果说印度承认与支持新中国的目的不只限于西藏,那么它拒绝公开援藏和反对美国干涉藏事的主要目标则仅为保持其在藏权益。为了遏制中国,美国虽然没有完全改变其承认西藏为中国主权一部分的政策,但却积极干涉西藏、怂恿印度与中国对抗,企图阻挠西藏的解放并把印度拉入其冷战集团(注:美国的对藏政策及动因,详见拙文《美国西藏政策的演变(1947—1951)》,载《史学月刊》1996年第5期。 )。新中国成立前夕,解放军已迫近藏边,11月初,噶厦慌忙向印英美等国求援。为避免中国更大的愤怒,尽快建立两国政府间的沟通渠道,印度拒绝公开援藏。21日,印度外交部秘书长巴杰帕伊(G.S.Bajpai)拒绝了美国要印度援藏的请求,他说印度不会以军事行动对抗中国对西藏的接管(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49年, 第9卷(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vol.9,华盛顿, 1974年),页1080~1082。)。对12月22日噶厦派团求援的再次请求,印度予以拒绝也反对他国接受,因为援藏物资的运输必须经过印度,这会使它成为中国谴责的目标(注:M.C.戈德斯坦:《1913—1951年西藏现代史——喇嘛国家的衰亡》(M.C.Goldstein,A History of ModernTibet,1913—1951: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伯克利, 1989年),页633。)。 1950 年1 月9 日, 梅农告诉美国代办多诺万( H.Donovan):印度的外交支持仅限于西藏自治的保持,只有中国拒绝,它才会提出西藏政治地位的问题,印度反对西藏外派使团而只求维持现状,无意向中国提出关于西藏的任何问题,任何对西藏的军事冒险均不会为印度所欢迎,它只会把西藏引入歧途,从而激怒中国人(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0年,第6卷,页272~273。)。19日, 梅农又拒绝了美国大使汉德森(L.Henderson )关于美国派代表团访问西藏的请求,“因为尼赫鲁认为那只能加速中共的行动”(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0年,第6卷,页283~286。)。 昌都战役开始后,印度对中国表示不满,美国以为有机可乘。10月26日,汉德森表示美国愿向西藏提供武器,希望允许过境。30日,巴杰帕伊警告说,在印中交涉的关键时刻,该行动一旦曝光,将使印度的外交努力化为乌有,“也会使印度领导人感到美国正致力于利用北京对西藏的干涉在印中之间制造分裂”,所以,“美国什么都不干才是对印度最好的帮助”(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0年,第6卷,页545~547。)。 事已至此,美国不得不暂停干涉西藏的努力,以免恶化与印度的关系。
三
噶厦在向他国求援的同时,向中央政府派出了以孜本夏格巴为首的谈判代表团。1950年5月末, 中央政府复函欢迎他以西藏地方的名义到北京谈判西藏和平解放的问题。印度虽然赞成和平解放西藏,但却不希望谈判在北京举行。6月4日,它在加尔各答强行阻止了夏格巴的旅行。
早在2月下旬代表团从拉萨出发前, 噶厦就请求印度为其赴香港提供方便,印度反对夏格巴赴京,因为它对此时在北京谈判的结果没有信心。如果尼赫鲁认为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9 月宣布解放西藏是一时忿激之言的话,1950年的新年献辞给解放军规定的任务却使之忐忑不安。在中国对西藏前途进而对印度在藏利益作出承诺之前,就不能把夏格巴这张牌交出去,他希望在印度谈判以便保持密切的注意和影响。3月初, 梅农要求英国驻印高级专员奈氏(A.Nye )推迟夏格巴的行程,因为“西藏与中国接触的任何努力均不会有令人满意的结果”(注:M.C.戈德斯坦:《1913—1951年西藏现代史——喇嘛国家的衰亡》,页648。 )。4月7日,奈氏通知夏格巴,要推迟给代表团赴港的签证。印中一建交,尼赫鲁马上决定促使西藏代表在印度与即将到达的中国大使谈判(注:夏格巴:《藏区政治史》,下卷,页233。)。 在被阻止登机后(注:印度一个偶然的错误使夏格巴等代表获得了去香港的签证,详见前引 M.C.戈德斯坦书,页649~651。),夏格巴于6月7 日到新德里再次向梅农和奈氏提出请求,后者则合演了一出双簧戏:梅农说“香港为英国属地未经其批准不得不阻止”;奈氏则帮梅农劝导说,北京显然不会平等对待西藏代表,所以不能去那里谈判,新中国代表即将抵印,加上印中之间的良好关系,新德里已成为更合适的谈判地点(注:M.C.戈德斯坦:《1913—1951年西藏现代史——喇嘛国家的衰亡》,页657。)。 无奈之余,噶厦只好决定在印度谈判。
对西藏代表“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个中原因,中央政府是知道的,看来,不诉诸适当的武力就不足以推进和平解决的进程。6 月下旬,解放军一部开始渡金沙江与藏军接触。8月3日,香港报纸刊载了刘伯承宣布解放西藏日期已定的消息,引起了尼赫鲁的不安(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0年,第6卷,页439~441。)。 为避免中国采取军事行动,潘尼伽于12日、22日和26日3 次与中国政府讨论西藏问题(注:卡·古普塔:《中印边界秘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19~20。)。“如果能在中国主权的框架内对西藏法律上的自治进行合适的调整,将会创造一个特别有利于中国的环境”(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0年,第6卷,页477。10月18日,梅农在致袁大使的一份照会中仍称:“印度政府关于西藏的全部建议就是在中国主权框架内的自治,这种自治应通过和平协商取得。”见熊真:《一对外交官夫妇的足迹》(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页87。),这是印度第一次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企图以此换取中国的让步,为此,印度还把阻拦西藏代表的责任完全推给英国,并称是印度才使英国改变了立场(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0年,第6卷,页477。)。“为使尼赫鲁减少恐惧”和“争取西藏代表来京”,中国答复说:中国不仅希望与印度、也希望与中印之间的尼泊尔和平相处(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页64。);中国和印度一样不希望发生武装冲突,已令大使在抵印后立即与西藏代表展开尝试性谈判,但最后的谈判应在北京举行(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0年,第6卷,页449。)。31日,中国又通知印度,若西藏代表在9月中旬仍不来京, 解放军就向西藏前进(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册(1949.9—1950.12),页475。)。 鉴此,梅农在9月5日要求夏格巴拜会已经抵印的中国代办申健并在大使到达后开始谈判。8日, 尼赫鲁拒绝了夏格巴关于印度在谈判中居间作证的要求,劝其莫再提及西藏独立,“否则事就难办了”。“印度居间作证,那是30年前的事,现在不同了,诸位代表珍惜开始谈判的时机甚为重要”(注:夏格巴:《藏区政治史》,下卷,页234~235。)。然而,由于受外国长期恶意宣传的影响,西藏代表在初步谈判后仍犹豫观望、迟不离印,解放军于10月6日发起攻击,21日解放了藏东重镇昌都。
印度领导人对中国的军事行动甚为不满。以帕特尔为首的干涉派再度活跃,他们反对尼赫鲁的对藏政策,主张对抗。在11月7 日给尼赫鲁的长信中,帕特尔认为中国解放西藏不仅会使印度在藏权益陷于危殆,而且将对印度的外交、边境安全和国内政治都造成严重威胁,他要求彻底检讨既往政策,停止在联合国支持中国,同中国对抗并与美国合作(注:R.K.贾因编:《中国和南亚关系文献集(1947—1980)》,第1 卷(印度),页29~35。)。尼赫鲁决心尽可能以外交手段达到目的。因此,在命令驻藏各机构不得撤出和继续秘密提供武器援助的同时,他向中国发动了一场外交攻势(注:夏格巴:《藏区政治史》, 下卷, 页237~238。)。10月21日和28日,潘尼伽两度照会中国政府,声称“中国入侵西藏”会影响谈判的和平结局,使中国在联合国更加孤立,“印度对此感到悲叹和深深的遗憾”。这与其说是关心,不如说是威胁。中国断然予以拒绝后,印度于11月1日再次提交照会,其立场与8月26日的备忘录相比大为后退,重新提出了所谓中国宗主权之下西藏自治的老调,声称如果不停止军事行动,它就“不再劝告西藏代表赴京”。最后,印度终于提出了它真正的要求并摆出对抗的姿态:“印度政府对西藏并无政治或领土野心,亦不为印度政府或其在西藏的国民谋取任何新的特权地位,同时,印度政府曾指出:某些权力是由于惯例和协定而产生的,它们在具有密切的文化和商业关系的邻居之间是自然的,这些关系表现在:印度政府在拉萨派有代表,在江孜和亚东有商业代表,在到江孜的商路上有邮政和电讯机关。为保护这一商路,四十多年以来,就一向在江孜驻扎了一小队卫兵。印度切望这些机构应继续存在,这些机构对印度和西藏都是有利的,并不在任何方面损害中国的宗主权。因而在拉萨代表团的人员以及在江孜和亚东代表机构的人员已受命留守在他们的岗位上”(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辑(1949—1950),页164~167、页177~181。 )。
关于进军西藏的原因,中国在11月16日复照指出,那完全是因为“西藏代表受外界唆使、制造借口迟不离印”,尽管如此,中国仍未放弃和平解放西藏的愿望。关于印度的在藏权益,中国“欢迎印度政府又一次申明对中国的西藏并无政治或领土野心,亦不谋取新的特权,只要彼此严格遵守相互尊重领土主权及平等互利的原则,我们相信,中印两国的友谊应得到正常的发展,中印在西藏的外交、商业和文化关系,也可以循着正常的外交途径获得适当的互利的解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1辑(1949—1950),页177~178。)。
中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印度在藏利益予以考虑,除其他原因外,还因为中国政府深知印度的态度对和平解放西藏的重要影响,而此时的印度在提交照会的同时,再次阻拦西藏代表、煽动和帮助噶厦向联合国求援,以此向中国施加压力。昌都战役开始后,噶厦命令夏格巴立即动身赴京谈判,10月23日,梅农劝夏格巴暂停,他说:“如何对待条款,拉萨无任何明确答复,却让你们去北京,此话令人吃惊”。31日,梅农为此又派专人递送他给夏格巴的亲笔信。与此同时,理查森煽动噶厦于11月1日命令夏格巴不得启程, 因为他此时赴京将“明显在强制下工作”(注:夏格巴:《藏区政治史》,下卷,页240~241。)。印度鼓动噶厦向联合国求援,为避免承担责任,巴杰帕伊认为“由西藏而非印度把该问题直接提交联合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1950年,第6卷,页440~441。)。理查森帮助起草信件, 其原件于10日被电传到联合国,副本分致驻印度的各国使馆,要求联合国对中国的“侵略”进行干预(注:夏格巴:《藏区政治史》,下卷,页243~246。)。
为配合外交行动,印度决定支持萨尔瓦多在联合国提出的“外国入侵西藏”案,然而,中国16日的复照改变了印度的这一立场。尼赫鲁在18日给帕特尔的回信中指出:中国的答复有缓和的迹象,“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没有特别提及我们在拉萨的使团和我们在亚东等地的商业和军事机构,我们曾在照会中特别提及,虽然中国没有直接回答,但复照最后所指的正是我们的这些机构。我们本来是等着要我们撤走的消息,事实将表明他们这样做有某种意义,而且照会反复强调要加强与我国的友好关系,并答应给西藏自治权”。尼赫鲁接着分析了印中冲突的危害,他认为发展经济使印度无力承担与中国军事对抗的压力,况且已树敌于巴基斯坦,印中一旦对抗,它就会利用这一形势,“我们不能在东西两侧都树敌”。印中有很长的共同边界,要长久地保持印度的安全,两国必须友好,印中可能的交恶会给两国和亚洲带来无穷的灾难,“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急切希望印中交恶,苏联亦如此”(注:R.K.贾因编:《中国和南亚关系文献集(1947—1980)》,第1卷(印度),页41~47。)。印度当时的情报局局长穆立克的回忆印证了上述观点。1950年春,梅农召集穆立克、潘尼伽和陆军总参谋长恰里阿帕将军等人,讨论中国武装“入侵”西藏的可能性以及印度可能的反应,恰里阿帕将军说,即使中国“入侵”,也绝不可能为此抽调哪怕一个营的兵力,他已受到巴基斯坦前线与国内共产党太大的压力,而且,装备、训练水平的差距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印度军队根本不是中国军队的对手。军事冒险不得不因此放弃(注:B.N.穆立克:《与尼赫鲁相处的岁月——中国的背叛》(B.N.Mullik,My Years with Nehru:The Chinese Betrayal,孟买,1971年),页80~81。)。基于以上考虑,印度决定不对萨尔瓦多的提案采取行动。与中国的军事行动一样,尼赫鲁的行动也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他指示劳氏:在与中国交涉的关键时刻,“任何对中国的谴责都不仅无助问题的解决反而有极大的危害”。24日,劳氏要求推迟表决并得到英美的支持,他声明中国已停止进军并转向和谈,“印度政府对此有信心而且相信该解决可以延续几十年以来的自治”(注:M.C.戈德斯坦:《1913—1951年西藏现代史——喇嘛国家的衰亡》,页729、734~735。)。尼赫鲁念念不忘保持西藏现状,在允许西藏代表赴京时, 他既担心他们态度僵硬导致谈判破裂、中国重开战事,又担心他们让步太多影响了印度的权益。他告诫说:“估计中共会提出以下三个条件:一是要西藏回到中国,不承认这一条没法谈判,国际地图早就表明西藏属中国,故必须承认;二是西藏外交要由中国管理,不承认这一条也没法谈;三是解放军进驻西藏。承认了这一条,西藏今后就会有很多困难,我们与西藏毗邻,对我们也很危险,所以不能承认。要用巧妙的办法,力争维护西藏的政治经济权利,但切记不可与中国作战,那是打不赢的”(注:《西藏文史资料选辑(三十周年专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页36。)。
谈判前夕,西藏亲印分子把17岁的达赖喇嘛挟持到亚东,企图重演十三世达赖逃印的历史。1951年3月21日,周恩来召见潘尼伽, 指出印度的态度对西藏自治和两国关系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页141。)。印度别无选择, 潘尼伽告诉尼赫鲁,若允许达赖在印度政治避难,印中的友好关系将会受到损害(注:K.古普塔:《 1948 — 1952的中印关系——潘尼伽的作用》( K.Gupta,Sino-Indian Relations,1948-1952:Role of K.M.Panikkar,加尔各达,1987年),页73。)。印度因此回答说它不鼓励达赖离藏,可劝告其不去印度,如果他坚持,印度只按国际惯例允其避难(注:廖祖桂:《西藏的和平解放》(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版),页50。)。
西藏和平解放后,印度在与它打交道时仍事事沿袭旧制、有意撇开中央政府,甚至把西藏当作国家来对待,以显示它在西藏的的特殊地位(注: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页260。 )。1952年6月14日,周恩来针对印度数次提及的在藏权益, 向潘尼伽提出了处理印度与中国西藏之间关系的原则:印度对英国侵略留下的现状没有责任,英国的在藏特权已不存在,新中国与印度在西藏的关系可通过协调建立起来(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页242。)。印度虽表示同意,但在1954年初的谈判中, 它又极力维护这些特权。中国允许不损害中国主权的传统惯例继续存在,但坚持取消特权,使印度不得不放弃无理要求,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西藏回归祖国后印度还保留一些特权,实在保留不住,才同意撤军(注: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页254。)。除此之外, 尼赫鲁等人对保留这些特权亦并非理直气壮。早在1950年8月14 日会见印英记者时,梅农曾说印度在西藏的地位很奇特,虽然在拉萨有代表,但却无明确的地位,它多多少少还是英国的继任者,而英国人是误入歧途并在那里留下来的(注:K.古普塔:《1948—1952年中印关系——潘尼伽的作用》,页73。)。1951年10月,潘尼伽在回国讨论对藏政策时指出:治外法权在现代两个友好独立国家的关系中没有地位,印度将会由于坚持延续英国勒索的权益而受到损害,中国无论如何是不会同意的,所以,最好的选择是体面地放弃那些在法理上站不住脚的所有特权,坚持那些基本上是自然产生而非建立在条约之上的经济和文化权利(注:K.古普塔:《1948—1952年中印关系——潘尼伽的作用》,页74~75。);尼赫鲁本人私下也承认西姆拉条约对中国没有约束力(注:夏格巴:《藏区政治史》,下卷,页235。)。如此,印中双方找到了共同点。在4月29日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印度承诺取消它在西藏的各种特权并承认西藏是中国主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印度领导人顺应历史潮流,最终完成了从承认宗主权到承认主权的过渡。
四
尼赫鲁的官方传记作家S.戈帕尔在评论印度外交时认为它部分是对英印时期政策的反动,部分是对该政策的继承(注:S.戈帕尔:《尼赫鲁传》,第2卷(S.Gopal,Jawaharlal Nehru:A Biography,vol.2, 德里,1979年),页43。)。印度的西藏政策正是从英国继承的,该政策的目标是:坚持所谓的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保持西藏的自治,使西藏成为印中之间的缓冲地区。1948年潘尼伽给尼赫鲁的备忘录以及后者的许多言论都充分表明了这一点。目标虽始终如一,但是尼赫鲁达到目标的手段却随着世界和地区形势的变化而相应改变:从最初与西藏地方背着中国政府交涉继承英国在藏权益,到在军事上秘密支持西藏地方谋阻中央的进军,再到企图以对华友好与外交谈判的手段达到目的。在分析这些变化的因由时,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在国际层面上,印度独立之际正是全球冷战方兴未艾、世界正逐渐分成两大集团之时,刚从英国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的印度也受到了威胁,印度的国情决定了它中立于两大集团之外,又与两大集团及其以外的国家保持友好(注:R.C.辛格拉尼:《尼赫鲁的外交政策》( R. C.Hingorani,Nehru's Foreign Policy,新德里,1989年),页1~5。)。随着“二战”的结束,亚洲兴起民族解放的浪潮,一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相继获得独立,这些国家有相似的命运和经历。印中两国人民在斗争中相互支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上述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为印度政府出台有利于中国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政策提供了条件。
2.在东亚,随着内战的结束,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国家一跃而成为东方强国,这才是尼赫鲁改变其外交手段的根本原因。S.戈帕尔也认为,中国共产党已在中国建立了稳固的统治并获得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印度政府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已别无选择(注:S.戈帕尔:《尼赫鲁传》,第2卷,页64。)。与其说以不承认、 晚承认或有条件的承认结怨和触怒中国,不如无条件尽快地承认以与之交好,为保存在藏权益创造条件;而且,中国共产党在新政府成立前后对尼赫鲁政府的猛烈批评使之认识到不可能以强硬手段获得中国的退让,尼赫鲁更知道印度没有实力做到这一点,此其一;其二,在南亚,印巴分治后两国因克什米尔的归属而交恶,印度本来就不强大的军队被迫集中于西部,而且,印度军方人士认为印军根本不是中国军队的对手。印度以和平手段保持其在藏权益的政策符合它的外交总方针,但在西藏问题上,更是因为它实在是力不从心、别无选择。穆立克的回忆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3.尼赫鲁论者都认为他热衷并控制了印度的外交事务,《印度对华战争》一书的作者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曾说过:“在尼赫鲁任总理和外长17年的生涯中,在理论、言论和行动上,外交政策向为他的私人专利”(注:N. 马克斯韦尔:《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N. Maxwell,"Jawaharlal Nehru:Of Pride and Priciple"),"Foreign Affairs",vol.52,Apr.1974,页633。)。所以, 尼赫鲁的思想及其对全球和地区局势的认识,无疑决定着他推行其西藏政策的手段。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认为中国无力解决西藏问题,就在压西藏地方承认印度继承英国在藏权益的同时,煽动西藏分裂分子闹独立,在西藏制造麻烦;在中国政权更替期间,印度又阴谋制造“驱汉事件”、向西藏地方提供军援、训练其军官,企图以武力达到目的;新中国建立后,尼赫鲁采取了对华友好的政策,可以说,保持印度的在藏权益是该政策出台的根本原因。尼赫鲁自认为是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他视中国革命为该运动的一部分,因此可以与中国展开建设性的对话;尼赫鲁还认为,与中国交恶会把中国推进苏联的怀抱,使其奉行苏联的好战政策;反之,若待之以友好,中国则会疏远苏联而愿避免冲突并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注:S.戈帕尔:《尼赫鲁传》,第2卷,页65。)。尼赫鲁以影响中国为己任,不遗余力地宣传特别是向美国宣传他的思想。他认为只要对中国主动示好并承认其对西藏的主权,中国就会对他的好意作出报答,承认西藏的自治及作为印中之间一缓冲区的地位,承认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从而使印度国家安全得到保障。他对1954年两国关于西藏的协定的评价最充分地反映了上述观点,他说:“我们仅放弃了事实上我们不能保持或实质上已不可能存在的东西,我们放弃了应在西藏内部实施的某些权力。很明显,我们已不能再保有这些权力。然而,我们却获得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比如:一个友好的边界和一个对该边界的默认”(注:S.戈帕尔:《尼赫鲁传》,第2卷,页105、181。)。
显然,尼赫鲁深知历届中国政府关于麦克马洪线的一贯立场,没有勇气与中方就该问题展开讨论,只是一味地希望中国会在此问题上作出让步,这纯粹是他想象的结果。然而在当时,这不可避免的影响着他的外交决策。
4.中国政府的决策对尼赫鲁产生了重大影响。这表现在:(1 )正确的民族政策产生了巨大威力。新中国建立前夕,临时宪法《共同纲领》规定了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该政策不仅争取了大部分西藏上层人物,也减轻了尼赫鲁的忧虑,因为他的目的之一就是保持西藏的自治状态;(2)印度于1949年底承认新中国后, 中央解决藏事的方式由以军事为主改为以谈判为主军事为辅、以战逼和。为此,在两国的建交谈判中,中方给印度以不同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待遇,两国得以顺利建交,为两国政府展开谈判铺平了道路;(3 )在解决藏事的过程中,中方反复强调和平谈判的方针和诚意,昌都战役开始后,尼赫鲁暗中操纵西藏分裂分子向联合国呼吁干涉,再次阻拦西藏代表赴京谈判。在此关键时刻,中国政府再次重申和平解决的愿望,鉴于印度在藏事解决上的作用,中方也作出某种程度的让步(注: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页254。)。 中国之原则的坚定性和政策的灵活性打击了印度的干涉派,同时也挫败了美国利用印度侵略西藏的图谋。
总之,影响尼赫鲁西藏政策的因素很复杂,它既与不断变化的国际与地区形势相关联,又与中印边界问题、中印关系密不可分。在尼赫鲁心中,他所主张的中印边界对于其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是印度的核心利益。建立和改善对华关系,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都仅是获得该核心利益的手段。这也就决定了尼赫鲁的政策中的另一方面:在主张两国友好之时,仍视中国为其潜在的敌人。这正是对英印时期的政策逻辑的继承,这种政策逻辑便是:一旦中国据有西藏,则将严重威胁印度的安全(注: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历史引言——帝国的界限”,页7~61。), 而且也遵循了印度的“近邻国家是潜在的敌人”的古训。中国革命胜利后不久,尼赫鲁在人民院的一次讲话中明确阐述了这种观点,他说:“自中国革命以来,我们自然不得不思考新中国将以何种面目出现。我们认识到,这次革命在亚洲和全世界以及对我们来说都是一重大事件。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强大的中国一般说来是崇尚对外扩张的,考虑到中国一旦强大就会产生内在的扩张冲动,我们已认识到印度面临的危险,随着岁月的推移,这种危险将日益显露出来。如果有人认为我们在推行政策时没有认识到这种危险,那他就大错特错了”(注:P.S.贾雅拉玛:《印度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P.S.Jayarama,India's 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新德里,1987年),页24。)。
尼赫鲁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新中国建立之前,尼赫鲁政府就行动起来,努力强化对中印边界地区的控制。1949年和1950年,印度强迫尼泊尔、锡金、不丹3国与其订立条约,先行控制了这些国家(注:R.K.贾:《印度外交政策中的喜玛拉雅诸王国》(R.K.Jha,The Himalayan Kingdoms in Indian Foreign Policy,新德里,1986年),页1~25。);为加强对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国领土的控制,印度政府于1949年专门在此设立中央直属的东北边境特区,修筑公路、建立哨所、加强阿萨姆步枪队的巡逻。与此同时,印度政府命令向北推进,以实现对麦克马洪线以南所有中国领土的占领和管理。1951年2月, 在同意西藏代表赴京谈判之后,又出兵占领了战略重地达旺(注:B.桑都:《未解决的冲突——中国和印度》(B.Sandhu,Unresolved Conflict:China and India,新德里,1988年),页93~95;参见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页72~73。)。1950年,他在人民院的一次讲话中,有议员提及中国的地图并不承认麦克马洪线,尼赫鲁马上就激动起来:“我们的地图表明,麦克马洪线是我们的边界,不管地图不地图,这就是我们的边界。这个事实没有变,我们坚守这条边界,我们决不让任何人越过这条边界”(注: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页64。)。
印度无理占据中国的领土并声称为此不惜一战,必要时还要“与一个甚至是帝国主义的国家并肩战斗”(注:P.S.贾雅拉玛:《印度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页13~14。);另一方面,尼赫鲁又虚幻地认为中国会以那块广袤的土地来交换本来就属于中国的对西藏的主权。一旦幻想破灭,两国关系就必然急剧恶化,一场冲突也必不可免,因为按尼赫鲁的逻辑,中国对自己领土的主权要求伤了印度的“威信和尊严”(注: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前言。)。所以说,中印冲突的根源正是尼赫鲁早就制定和执行的西藏政策,由此观之,此后尼赫鲁的种种拒不妥协的态度和走向战争的政策则可以得到合理的解读。
标签:英国政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