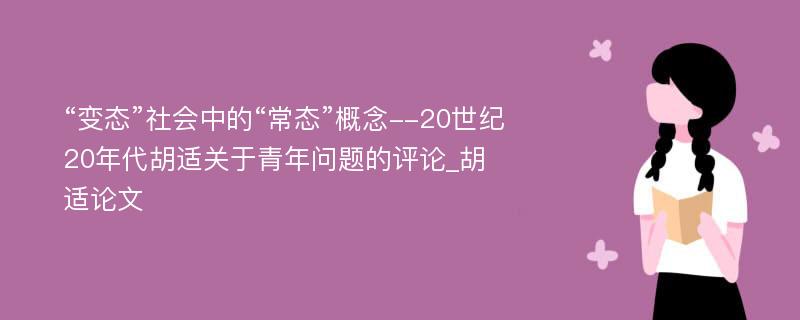
“变态”社会中的“常态”构想——胡适1920年代有关青年问题的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常态论文,言论论文,年代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以《新青年》群体为代表的一代知识精英与青年学生的结合,构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得以展开的一个重要前提,在改造社会与再造文明的诉求下,两代人之间彼此支援,催生出一种新型的文化政治模式。五四之后,在不断激变的社会氛围中,“导师”与“青年”之间的“合作”与“召唤”关系,虽然发生了重重异变,但一批“海内外学者名流”、“负有指导青年重责的前辈”仍不断站出来,针对青年人格、习性、学风、运动等方面问题,高调发表指导性意见。在这个群体之中,胡适自然是一个重要的发言人。由于其“新学钜子”的特定身份,他的言论在青年界有着广泛影响力,①而他自己也喜欢扮演负责任之指导者的角色,每每“忍不住了,不能不说几句良心逼迫的话”。②面对学生运动的“嚣张”,胡适与蔡元培、蒋梦麟、陶孟和等知识界、教育界人士,曾反复强调“救国不忘读书”,“先救出自己”,“造就有用人才”的重要性与优先性;③通过鼓吹“实验主义”、倡导“整理国故”,以及为青年学生开列“最低限度国学书目”等方式,他也一直想引领风气,希望青年走上学术化、专业化的道路。这一路线常被看做是某种维护学术独立、教育独立的非政治化选择,事实上,不仅“非政治”的选择包含了强烈的政治性,某种权威性启蒙结构的内在危机,也显现在他的这些言论之中。
在胡适对青年运动的“指导”中,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即:所谓“变态”社会与“常态”社会的区分。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在与蒋梦麟联名发表的《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一文中,胡适就开出一个所谓“古今一例”、“中外一理”的公式,即:“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纠正的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④依据这一公式,胡适当然认可学生运动的合理性,也重视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责任,因为这是“变态社会里不得已的事”;但同时,他又强调“它又是很不经济的不幸事”,态度的矛盾隐含了他对“常态”社会的期待。1928年,胡适在上海光华大学发表演讲,再次谈论五四运动的意义,并正面表述了他的期待:
如果在常态的社会与国家内,国家政治,非常清明,且有各种代表民意的机关存在着,那末,青年学生,就无需干预政治了,政治的责任,就要落在一般中年人的身上去了。试观英美二国的青年,他们所以发生兴趣,只是足球、篮球、棍球等等,比赛时候,个人兴高采烈,狂呼歌曲;再不然,他们就寻找几个女朋友,往外面去跳舞,去看戏,享尽少年幸福。……他们之所以能够安心读书,安心过少年幸福者,就因为他们的政治,非常清明,他们的政治,有中年的人去负责任之故。⑤
显然,以英美二国为榜样的“常态”社会、“常态”政治,以及“常态”生活方式与文化方式,亦即一整套合理化、现代化的社会建制,构成了胡适心目中的理想范本。这一自由主义理念,本来无需更多讨论,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上面一段话中,胡适还强调维护或者实现“常态”的责任,应落在“一般中年人的身上去”。这里的所谓“中年人”,绝非“一般”,更不简单是一个年龄概念,而对应于他心目中真正的政治主体,即那些具有专业能力,“负有指导之责任”的知识精英们。在胡适看来,中年的“导师”与一般“青年”的合理分工,以及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正是“常态”社会的另一种表现,中国青年走入政治歧途,风潮迭起,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这种关系的失衡:“殊不知少年学生所以干政,正是因为中年的智识阶层缩头袖手不肯干政”。⑥
换言之,曾在诗中鼓吹“炸弹!炸弹!”“干!干!干!”的胡适,并不抽象地反对知识分子干预政治,关键是要由谁来干预政治?由知识分子中的哪个阶层来干预?又是怎么来干预?1922年5月7日,胡适等人创办《努力》杂志,聚集一批教育界“清高事业”人士,开始大张旗鼓地谈政治,而他们理想中的政治形态(“好政府主义”),就是落实在一种依靠“少数中的少数,优秀中的优秀”的精英政治、专家政治之上,以致给人留“太侧重好人而忽略一般的民众”的印象。⑦内含于政治主张之中的精英立场,同样表现在他对青年运动的态度上。1925年9月,胡适发表著名的《爱国运动与求学》一文,希望青年学生“在一个扰攘纷乱的时期里”,不要“跟着人家乱跑乱喊”,而努力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个有用的东西!”这似乎只是老调重弹,但在“五卅”之后的具体情境中,却激起了强烈的反弹,在一位青年读者来函发表评论,提出的意见之一就是:胡适忽视了民众运动的意义,外交的任务只在政府之手,民众表现民气即可。他进而指出:“我相信胡先生把国民革命完全忽略过去,而仍抱着前几年‘好人政府’的主见。”⑧这位读者相当有眼光,一下子指出胡适“指导”青年的要害所在。
出于对民众运动情绪性、盲目性的怀疑,胡适等人的“好人政治”,与国民革命兴起背景下的“动员型”政治,直接构成了某种论辩的关系。有意味的是,不仅“谈政治”的责任,要落到“一般中年人”的身上,与“政治”相区别的文化事业,其担当的主体也需要一定的甄别。1923年10月,当“谈政治”的努力已到“向壁”的地步,最终受挫,胡适在给友人信中谈及《努力》的转向:重新接续《新青年》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那么,这个转向后“大事业”该由谁来完成呢?对此,胡适也有明确的规划:
在这个大事业了,《努力》的一班老朋友自然都要加入;我们还应当邀请那些年老而精神不老的前辈,如蔡孑民先生,一起加入。此外少年的同志,凡愿意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我们都应该尽量欢迎他们加入。⑨
不难发现,胡适的“大事业”构想,虽然欢迎“少年的同志”加入,但也只是有限度的接纳,他所真正倚重的还是一班“老朋友”和“前辈”们,“少年的同志”并没被看作是这场事业的主力。一位台湾学生读到这封信后,就似乎有些不满,向胡适建议《努力》应“在青年身上建基础,再向青年方面建方策”,“须多辟欢迎有志青年们参加的机会”。⑩
或许可以说,胡适拟想的“常态”政治方案、文化方案,潜在地包含了某种责任主体的区分性、排斥性,不仅一般的民众不被信任,五四之后作为新兴势力的青年学生,也并没有被特别看待。他们作为历史主体的可能性,即使没有被完全忽略,但在胡适的眼里,这种可能性尚待完成,仍处在一种需要被推迟、延宕的状态。这不简单归因于“中年”与“少年”在年龄、阅历、社会位置等方面的差异,更是连缀了一种对专业能力、知识的要求。在1922年6月的《我的歧路》中,他回顾自己几年来的言论,坦言目的只在提倡一种实验主义的方法:
古文学的推翻,白话文学的提倡,哲学史的研究,《水浒》、《红楼梦》的考证,一个“了”字或“们”字的历史,都只是这一个目的。我现在谈政治,也希望在政论界提倡这一种“注重事实,尊崇证验”的方法。(11)
文章虽名为“我的歧路”,但在胡适这里,学术与政治并非是两个互为“歧路”的领域,而是相互紧密地关联。如果说对“实验主义”的鼓吹,目的在于引入一整套以科学方法为标志的现代学术体系,那么它同样应该是“常态”社会中政治活动的准则,因为“治国是一件最复杂最繁难又最重要的技术”,“要把这件大事办的好,没有别的法子,只有充分请教专家,充分运用科学”。(12)胡适笔下的“专家的政治”,他又曾称之为“研究院的政治”,而“这一命名所揭示的正是‘进研究院主义’与‘好政府主义’的内在联系”。(13)
在强调“读书”之于“救国”的优先性,区分“中年的智识阶层”与一般“少年”之责任之外,胡适、梁启超等通过为学生开列“最低限度国学书目”等方式,推动的“整理国故”的热潮,则可看作是“导师”指导“青年”实际成果之一。对于这种热潮可能的后果,善于引领风气的胡适,最初似乎也没有充分的估计。
本来,“整理国故”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按照胡适后来的说法,其目的在于“打鬼”——传统的批判,但却引来了众多青年的追捧与参与,以致成为风行一时的热潮:“国内人士上而名人教授,下而中小学生,大家都以整理相号召,甚至有连字句也不能圈断的人,也公然在堂堂皇皇地发表著作”。(14)这种现象在文化界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很多人提出了批评意见:或如吴稚晖一般主张在一个“用机关枪对打”的时代,“整理国故”并非急务;或如沈雁冰等人那样担心对白话文的“信仰”尚不稳固,回头去读古书,在客观上会造成“进一步退两步”的局面。(15)就连与胡适同属一个阵营的陈西滢,也曾讥讽:
国故学者总以为研究国故是“匹夫有责”的;适之先生自己就给我们开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梁任公先生更进一步,说无论什么人没有读他开的书单,就“不能算中国的学人”;国立大学拿“整理国故”做入学试题;副刊杂志看国故文字为最时髦的题目。结果是线装书的价钱,十年以来,涨了二三倍。……青年们本来大都是“学时髦的不长进的少年”。“整理国故”既然这样时髦,也难怪他们随声附和了。(16)
陈西滢的这段话,不仅道出了“整理国故”的社会影响,更为重要的是,也揭示了这股“热潮”背后的社会心理机制:当这项学术活动,在一个由导师、青年、报刊、学院构成的新兴文化“场域”中,不再局限于个体专业的领域,泛滥为一种可以被消费的“时髦”,甚至成为一种标榜文化身份的符号(“中国的学人”),那么“打鬼”的初衷便不免被异化了。所谓学术之“实”也已沦为另一种“空”,同样是“不争气”之青年界浮泛作风的表现。
对于“整理国故”的弊病,胡适后来并非没有察觉,也曾哀叹:“现在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故纸堆里去乱钻,这是最可悲叹的现状。”(17)但或许还有一个问题,他没有意识到:以“整理国故”为代表的“进研究室主义”,虽然可以在青年中泛滥成风,但事实上与“专家政治”、“好人政治”一样,仍具有相当的精英色彩,包含了内在排斥性和特权性。“研究室”虽好,但“门槛”也高,并不是一般“束发小生”能随便踏入。(18)在20年代,青年学生的苦读、苦学,乃至失学、失业,已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一些青年“导师”高高在上的指导,往往也会引起被指导者的不满。1927年1月11日,刘半农在自己主编的《世界日报·副刊》上,刊出《老实说了吧》一文,激烈地指斥一般青年“不用功”、“乱发表”、“随便骂人”等恶习,一场围绕青年习性及“教训”是否合理的讨论,也随之沸沸扬扬地展开。有青年在回应中,就将若干“导师”的指导联系在一起,激烈地表达他们的怨怒,如尚钺所称:
当去年胡适之,陈西滢,徐志摩,张奚若等先生用着诅咒的言语,来讨厌青年的时候,老实不客气,我是极端反感的,正如暑天我嗅着臭毛厕的恶气一样。(19)
另外一些读者则坦言自己就是刘半农所骂“一个不争气”的青年,但这也是处境使然:
刘博士骂我们“不肯用功”,“不能作严重的工作”,这是诚然的。但是用功……到那儿用去呢?闭在手冷脚冻的空屋子里,就能平白地悟出什么伟大的发明吗?醒出不朽的创作吗?……说到“国渣应扔进毛厕去!”我们虽有毛厕,可惜无渣可扔?至于外国文呢,我们连“国渣”都没有,更何论数元以至数十元一本的“外粹”呢?(20)
类似的表述,可能只是一些“言过其实”的抱怨,但也从一个侧面,暗示了新兴的文化、学术“场域”内在的阈限。正如陈西滢所说:“国立大学拿‘整理国故’做入学试题;副刊杂志看国故文字为最时髦的题目”,五四之后新文化运动的扩张,得益于与出版事业、教育制度的结合,也在客观上也形成了一种文化生产与再生产的体制。仅以“国故”为例,配合了五四后的“整理国故”的热潮,20年代各个大学开始纷纷设立“国学院”、“国学门”、“国学系”,而这一过程的完成“基本是在‘五四’后10年间”。(21)在这样一个逐渐生成新文化体制、新学术体制中,如胡适、徐志摩、张奚若、陈西滢等这样的教授、学者、编辑,作为五四之后兴起的一个新知识分子阶层,扮演着“负有指导之责任者”角色,而上述角色之所以能成立,其实都与他们占据的位置、垄断的资源,以及掌握的学术能力、语言能力相关。早在1919年,瞿秋白就在《知识是赃物》一文中,敏锐地道破了新的知识体制中的权力关系。在文中,他检讨了知识私有制的历史,认为现代已渐渐从“形而上学时代脱离到实验哲学的时代”。在实验哲学的时代,知识私有制一方面被破坏,一方面还在建设:
破坏的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实验哲学用归纳的解释法来解释一切,使人家对于各种知识多有一条明瞭的途径可循,的确解放了好些。然而在建设的一方面,又因此用许多科学的律令、科学的定义,把这知识私有制弄得壁垒森严,譬如从手工业制度变成工厂制,使劳动家更苦,就是非经过多年的专攻,不能得到一种知识,不能使他到事实上去。……因为教主和学者认定这些知识是他的,一般人也承认这些知识是他的,有所谓宗教的信条,学派,家法,秘传,所以要说这个人知识多,那个人知识少。(22)
在“实验哲学的时代”,当教授、学者、编辑、名流们,责难“不读书”、“乱发表”,指点“必读”或“最低限度”的书目,劝告青年走上学术、文艺的正途之时,他们无疑希望新兴的文化运动不至自我空洞化、浮泛化,力图使其落实为一种“常态”的现代知识、文化建制,但所谓“知识私有制”背后的权力关系,也在无形中随之被一次次确认、强化。
从学理上看,从“进研究院主义”到“好政府主义”,都有相当的说服力,立足于学术与政治的“常态”关联,但“学理”与“事实”往往相悖,“常态”的构想也很难被“变态”的现实容纳,这构成了胡适等自由主义者的尴尬之处。同时,胡适一系列的“负有责任”的“指导”意见,不仅很难为“束发小生”耐心听取,由于他在一系列政治、文化事件中的表现,在不少青年眼里,“‘胡适之’这三个字上,已沾满灰色的尘点”。(23)1925年8月26日,上海学生联合会就曾致信胡适,痛斥他近年来的行迹:
比年以来,先生浮沉于灰沙窟中,舍指导青年之责而谓无聊卑污之举,拥护复辟余孽,尝试善后会议,诸如[此]类,彰彰晈著。近更倒行逆施,与摧残全国教育,蔑视学生人格之章贼合作,清室复辟函中又隐然有先生之名。呜呼,首倡文学革命之适之先生乎!(24)
无论是卷入“溥仪出宫”事件,出席段祺瑞的“善后会议”,还是反对北大脱离教育部,高谈“读书”才是“救国”之道,胡适似乎每一次都有意站到了激进思潮的对立面。对此,他还不无得意,自言“生平不学时髦,不能跟人家乱谈乱跑,尤不能谄事青年人”;(25)青年对他的非议,乃至围攻,也被他看成是“党派”势力鼓动的结果,预示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26)
从所谓“爱自由争自由”的立场看,胡适的担忧并非没有根据,但有一点他可能没有过多考虑,那就是在五四之后,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边缘群体,如何参与到新兴的文化、政治空间中来,已成为一个不能回避的思想课题。诚如有学者指出的,五四新文化的特殊战略之一,就是召唤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新青年”,作为推动社会、思想变革的主体。通过阅读新潮的书籍、报刊,在一整套新文化观念、符号的激励下,众多位置边缘的青年,纷纷挣脱地方性或传统视野的限制,试图参与到新兴的文化事业中来。新文学的兴盛、新学术的增长,乃至社会运动的高涨,都为他们提供了参与的渠道,以及建立创造性自我认同的可能。胡适1920年初“指导”青年的言论,延续了五四时期自我启蒙的“易卜生主义”思路,表面上看,也彰显了召唤、塑造“新青年”的功能。然而,无论精英式、专家式的政治构想,还是“门槛”颇高的“进研究室主义”,都没有充分注意到这个边缘群体的历史可能性,也忽略了具体处境中他们的主体状态,这造成了立足“常态”的一系列“指导”,缺乏某种切身的感召力和说服力,还在无形中助长了新兴文化体制中的等级性、排斥性,“导师”与“青年”之间权威性启蒙结构的“异化”乃至“恶化”,也就在所难免了。
与胡适的“常态”构想构成直接对立的,无疑是当时逐渐高涨革命动员话语。在国民革命兴起的大背景下,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政治派别,都在青年中积极鼓动,以求吸纳这股更新的社会力量。边缘性社会群体的持续加入,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政治、文化的走向。1926年11月,在上海担任凇沪商埠总办的丁文江致信胡适,曾谈及他对一般青年学生的观感:
至于国民党的那一套,我真正不敢佩服。我所检查到的信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主张,是学生应该“少读书,多做事”!你想这班青年,就是掌握了政权,有多大希望呢?
那时的丁文江已加入孙传芳的阵营,站到了国民革命的对立面,但他对一班“少读书,多做事”的青年的反感,不简单出自个人的政治立场,更多源于“专家的政治”、“研究院的政治”与社会动员型政治之间的深刻分歧。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反感未尝不会被好友胡适分享。
如果说“读书”与“救国”、“专家政治”与革命动员、“常态”与“变态”的二元对峙,构成了1920年代青年走向的结构性张力,那么可以参照的是,1920年代中期逐渐与胡适“分道”的鲁迅,(27)也多次表达对诸多“常态”方案的不满。针对“整理国故”为代表的“进研究室主义”,鲁迅就提出这样的质疑:
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毁了事情颇不少。学者多劝人踱进研究室,文人说最好是搬入艺术之宫,直到现在都还不大出来,不知道他们在那里面情形怎样。这虽然是自己愿意,但一大半也因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计。(28)
与其他论者相比,鲁迅关注的重点,不是“整理国故”在社会、文化层面的影响,而是这种风气对于一般青年主体精神的影响:“进研究室主义”作为“一派思潮”,可能会使青年沉溺于某种封闭的知识生产之中,在专业内部的竞技中消耗热情与智力,从而丧失文明批评及自我觉悟的能力:
“束发小生”变成先生,从研究室里钻出,救国的资格也许有一点了,却不料还是一个精神上种种方面没有充分发达的畸形物,真是可怜。(29)
上述显然指向了胡适有关“读书”与“救国”的言论。在警惕“进研究室主义”式陷阱同时,对于“导师”与“青年”之间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鲁迅也有意多次有意拆解。1925年5月15日,他在《莽原》上发表《导师》一文,专门谈及“导师”与“青年”:
近来很通行说青年;开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有要前进的。
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寻不到倒是运气;自知的谢不敏,自许的过果真识路么?凡自以为识路者,总过了“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态可掬了,圆稳而已,自己却误以为识路。(30)
所谓“青年”不能一概而论,所谓识路的“导师”永不可寻,鲁迅彻底祛除了“导师”与“青年”这一对关系概念抽象的自明性。他不仅质疑那些“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自己更是拒绝扮演这一角色,对于报刊上频频出现的“思想界先驱者”、“负有指导青年重责的前辈”之类名号,他也曾公开声明:“此等名号,乃是他人暗中所加,别有作用,本人事前并不知情,事后亦未尝高兴。”(31)这种立场与鲁迅特有的困惑意识以及对个体精神“歧路”状态的深刻认识相关,同时也源于自“青年必读书”的风波以来,他对所谓“‘新思想’仍中了‘老法子’的计”的觉悟。然而,在态度上拒绝“指导”,但在实际行动中,鲁迅“倒是一向就注意新的青年战士底养成的,曾经弄过好几个文学团体”。(32)在20年代中期,他发起创办《莽原》、编辑未名丛书、乌合丛书,将扶植、召唤青年作者当作一项自觉的使命。《导师》一文,正是发表于《莽原》之上。鲁迅编印这份杂志的目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33)
在青年群体中,鲁迅实际发挥着“导师”的影响力,但又拒绝扮演“导师”这一“挂了金字招牌”的角色,在这种反差中,鲁迅的文化批判意识也得以显露。如果说,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新的知识精英们,希望通过“指导”或“教训”,使青年踱入“正路”,也进一步强化某种“常态”的现代文化体制;那么,鲁迅所拒绝的正是“导师”背后的所谓“正路”、“捷径”,拒绝那些现成的、无需反思的“常态”方案,更是拒绝“导师”所代表的权威性启蒙结构的固化、体制化。在这个意义上,鲁迅不仅重视边缘青年的历史参与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他并没有将这种参与,简单理解为对社会运动、政治运动的加入,他更关注“青年”——这个尚未被知识、权力异化的群体的精神可能,希望能在他们身上唤醒一种批判的、能动的主体性,使“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34)拒绝“指导”的姿态,恰恰又是在有意招募,鲁迅的主体性方案,构成了1920年代“召唤”青年的另一种维度。
注释:
①1922年8月15日,一位《努力》的读者徐望之在致胡适的信中这样写道:“一般青年对于先生,倒好像上海人无论买什么东西,都要先到先施、永安去问一问,这实在是先生的荣誉,亦是先生的责任。”(《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1页。)
②胡适:《刘治熙关于〈爱国运动与求学〉的来信附言》,《现代评论》2卷42期,1925年9月26日。
③参见蔡元培:《自去年五四以来学生罢课的回顾与展望》,胡适、蒋梦麟:《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新教育》2卷5期,1920年5月)陶孟和:《救国与求学》(《现代评论》2卷37期,1925年8月22日)胡适:《爱国运动与求学》(《现代评论》2卷39期,1925年9月5日)。
④胡适、蒋梦麟:《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胡适全集》第21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0-221页。
⑤胡适:《五四运动纪念》,《胡适全集》第21卷,第372页。
⑥胡适:《蔡元培以辞职为抗议》,《胡适全集》第2卷,第586页。
⑦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中梅祖芬的发言,《努力》第4期,1922年5月28日。
⑧刘治熙:《爱国运动与求学》,《现代评论》2卷42期,1925年9月26日。
⑨1923年10月9日胡适致高一涵、陶孟和等,《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17页。
⑩1923年11月17日黄逢霖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220页。
(11)胡适:《我的歧路》,《胡适全集》第2卷,第470页。
(12)胡适:《知难,行亦不易》,《胡适全集》第21卷,第406-407页。
(13)钱理群:《北京大学教授的不同选择——以鲁迅与胡适为中心》,《论北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页。
(14)郭沫若:《整理国故的评价》,《创造周报》36号,1924年1月13日。
(15)有关“国故”思潮引起的讨论,参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第六章《机关枪与线装书:关于“国学书目”的论争》以及第七章《从正名到打鬼:新派学人对整理国故的态度转变》,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
(16)陈西滢为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所写的《西滢跋语》,原载《现代评论》第5卷119期,1927年3月19日。
(17)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全集》第3卷,第143页。
(18)1923年3月,胡适为清华学生开出一份“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声称这份书目“并不为国学有根柢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胡适全集》第2卷,第112页)《清华周刊》记者就来信提出,书目“谈得太深了,不合于‘最低限度’四字”。(《胡适全集》第2卷,第125页)梁启超也觉得胡适的书目名不副实:“依我看,这个书目,为‘国学已略有根柢而知识绝无系统’的人说法,或者还有一部分适用。我想:《清华周刊》诸君所想请教胡君的并不在此,乃是替那些‘除却读商务印书馆教科书之外没有读过一部中国书’的青年们打算。……胡君答案,相隔太远了。”(《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胡适全集》第2卷,第151-152页)
(19)《尚钺先生来信》,《世界日报·副刊》7卷15号,1927年1月18日。
(20)负生:《污了名人的宝刀》,《世界日报·副刊》7卷19号,1927年1月22日。
(21)尚小明:《“五四”以后“国学”热的一个新动向——大学“国学系”的设立及其结局》,牛大勇、欧阳哲生主编:《五四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五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49—561页。
(22)瞿秋白:《知识是赃物》,原载《新社会》第6号,1919年12月21日;引自《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3-45页。
(23)董秋芳:《致胡适之先生的一封信》(1925年1月15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02页。
(24)《胡适来往书信选》,第341页。
(25)胡适致邵飘萍(稿),《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03页。
(26)1925年9月,胡适到湖北讲学,武汉各报登出不少批评文章,他在日记中做了相关摘记:“我这回来,挨了不少的骂。湖北一班共产派的学生出的《武汉评论》除了一个‘欢迎’专号,其实全是谩骂。”(《胡适全集》第30卷,第199页)在1925年12月给陈独秀的信中,他谈到了“不容忍的空气”问题,抱怨“我个人这几年就身受了不少的攻击和污蔑。我这回出京两个多月,一路上饱读你的同党少年丑诋我的言论,真开了不少的眼界”。(《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57页)
(27)依照孙郁的研究,鲁迅对胡适看法的转变,大概在1925年左右。“1924年8月以后,两人的通信便中断了”。(孙郁:《鲁迅与胡适》,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89页)
(28)鲁迅:《通讯》,《鲁迅全集》第3卷,第25页。
(29)鲁迅:《“碎话”》,《鲁迅全集》第3卷,第160-161页。
(30)鲁迅:《导师》,《鲁迅全集》第3卷,第55-56页。
(31)1925年8月5日,韦素园在《京报》上登出《民报·副刊》出版广告:“现本报自八月五日起增加副刊一张,专登载学术思想及文艺等,并特约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钱玄同、周作人、徐旭生、李玄伯诸先生随时为副刊撰著,实学术界大好消息也。”这则广告曾引来高长虹的猛烈攻击,鲁迅则发表《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予以回应。(《鲁迅全集》第3卷,第391页)
(32)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4卷,第236页。
(33)1925年4月28日致许广平信,《鲁迅全集》第11卷,第63页。
(34)鲁迅:《华盖集·题记》,《鲁迅全集》第3卷,第4页。
标签:胡适论文; 胡适全集论文; 1920年论文; 现代评论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政治论文; 鲁迅论文; 努力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国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