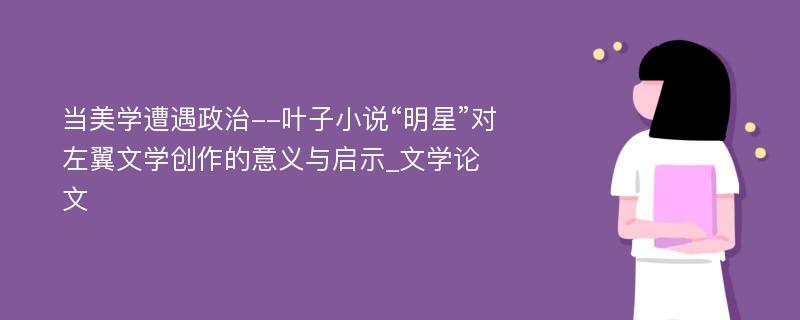
当审美遭遇政治——叶紫小说《星》对左翼文学创作的意义与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翼论文,文学创作论文,启示论文,意义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4)05-0070-04
一、政治理性与审美意识能否和谐共生
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家们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性精神指引下,将文学的发展 方向与政党的政治斗争方向紧密结合起来,选择激进的政治意识作为文学创造的核心理 念,形成了意识形态化的文学观以及文学的党派性等文学的存在方式。这种对文学功能 的激进择取,挤压了文学的审美创造空间,弱化了文学创造的自律意识,使左翼文学创 作在很大程度上沦为政治意识的传声筒。
政治与艺术双重旋律的交织,是公认的中国20世纪30年代文学的一个典型特征。强烈 的政治关怀意识,使知识分子们走出“五四”以个性解放为本位的狭窄天地,将目光和 激情转向广阔而剧烈的社会变动、转向民生疾苦、转向阶级斗争,用文学创作和文学行 为来思考社会和人生。这使文学创作的题材得到空前规模的开拓,表现角度得到深度开 掘,叙事视野、叙事手段、作品结构、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具有了尖端性和前卫性的时 代特点。一大批优秀左翼作家,从各自的现实体验和感受出发,在政治激情的引导下, 特别是在新的文学题材和新的文学品种试验与开拓上,引领文坛之风骚。但政治意识对 文学创作是一面双刃剑,反抗政治、文化专制主义的政治理性要求,使左翼作家们在最 大程度上实践了文学的社会价值和战斗功能,可是急切的政治诉求往往抑制文学自身内 部的美学建构,淡化作品审美意蕴的营造。这使大多数左翼作品至今依然受到诟病。
文学观念不等同于具体的文学作品。作品不是单纯的理念的表达,而是人的直觉、情 感、意志和理性诉求等精神活动的全面艺术化展现;粗俗浅陋的作品不但毫无艺术性可 言,甚至也不足以深入全面地表达政治理念;而有品位的作品不但具有丰富的艺术想象 空间,而且可以借此使政治理念更富于生命力和感染力。詹明信就强调:“我历来主张 从政治、社会、历史的角度阅读艺术作品,但我绝不认为这是着手点。相反,人们应从 审美开始,关注纯粹美学的、形式的问题,然后在这些分析的终点与政治相遇。人们说 在布莱希特的作品里,无论何处,要是你一开始碰到的是政治,那么在结尾你所面对的 一定是审美;而如果你一开始看到的是审美,那么你后面遇到的一定是政治。我想这种 分析的韵律更令人满意。”[1](P7)我们知道,文学与政治本来分属于人类不同的精神 层面,二者没有必然的逻辑从属关系,文学与政治发生关系,主要在于创造主体的自我 意识和自我选择。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文学从属于政治或者文学应当排斥政治,而在 于如何将政治理念与审美意识高度融合在作品中,用作品所创造的艺术想象世界去展现 政治理念。岂止是布莱希特的戏剧作品,古今中外有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具有高 超的艺术审美性,而且还洋溢着浓烈的、充满现实关怀的政治意识,达到艺术与政治的 较为完美的融合。
左翼文学重新受到人们的深切关注,除了文学与政治不解之结之外,还在于它创造了 不少既具有深沉的艺术底蕴又具有浓烈的政治激情的作品。叶紫就是其中的一个佼佼者 。鲁迅曾经评价叶紫说:“作者还是一个青年,但他的经历,却抵得太平天下的顺民的 一世纪的经历,在辗转生活中,要他为‘艺术而艺术’,是办不到的。……但我们却有 作家写得出东西来,作品在摧残中也更加坚实。……这就是作者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 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2](P220)作为一个30年代在上海从事左翼革 命文艺运动的革命作家,叶紫的小说多取材于故乡湖南洞庭湖畔的农村生活,以生动的 笔触和曲折的故事,描绘农民的苦难与抗争,总是回荡着呼唤农民革命的呐喊,具有鲜 明的政治革命意识。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叶紫的小说既非口号式也非概念化,而是以浓 郁悲愤的艺术氛围来展现政治革命的主题,在艺术创造上非但没有被左翼批评的“普洛 克鲁思德斯之床”拉长或锯短,其艺术魅力反而因为深沉的政治革命意识而倍增,政治 理念和革命吁求也借助于艺术的想象空间而变得合情合理,实现了文学的战斗的社会功 能,既展现了左翼文学作家运用文学手段追求政治理想的理性要求,也表明了左翼文学 在艺术创造上具有达到精湛高度的广阔空间。叶紫的中篇小说《星》就是一篇富有包孕 性、政治理性精神与艺术审美意识高度融合的杰作。
二、革命引导下人性觉醒的生理、心理和社会角色的选择
个性解放与人性觉醒是“五四”时代的文学主题。“五四”之后思想启蒙的时代主题 让位于政治救亡的呐喊,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必须看到,“五四” 时代的个性解放和人性觉醒更多是属于知识者内心世界挣脱束缚的精神需要,而中国最 广大的社会实体——农民很少真正走入这个知识者创造的文艺世界。然而在左翼十年间 情况完全不同了。尽管个性解放与人性觉醒成为从属于政治解放主题的次级主题,但是 却不再像“五四”时代那样空泛和轻飘,而是和人间底层人民真实的生存状况、社会地 位以及悲惨的命运连接起来,农民真正成为文学的反映主体,个性觉醒和人性解放获得 了坚实的现实基础和实践路向,启蒙真正落到了实处,虚弱的思想想象化为具体的坚定 的政治实践,个性解放与人性觉醒也获得了血肉丰满的表现对象,和大多数的地之子们 的灵魂与命运休戚相关,共同塑造了更为深沉和广阔的艺术创造空间。
叶紫的中篇小说《星》,就是一篇在政治理性精神和革命原则烛照下,书写个性解放 、人性觉醒的时代新篇章。准确地说,对于《星》的中心人物梅春姐来说,个性解放与 人性觉醒应该是女性的反抗与觉醒。仅就小说建构的艺术空间来看,并没有明显的女权 主义精神迹象,在政治意识的强光辉映下,性别特征并不具有实质意义,反而更近似于 具有普遍特征的个性解放与人性觉醒的内涵和本质。当然,小说对这一主题的表现是借 助于女性命运展开的。描写对象选择弱势群体中的弱势个体,更能激发读者的同情和悲 悯。
小说开篇就充溢着悲剧气息。梅春姐的悲哀和怏怏闺怨不是单纯的少妇思春,而是生 理、心理和社会角色诸多方面压抑下的“地火”。梅春姐是一个漂亮、多情和贤惠的青 春女性,小说以富于诗意和爱怜的笔触描写她的外形和气质,但这样一个美丽的女性, 非但得不到丈夫的呵护,反而只是一个“替他管理家务,陪伴泄欲的器具”,时常遭受 殴打,不但使梅春姐生理和心理受到压抑和摧残,也使她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形象受到损 害,男人们“用各种各色的贪婪的视线和粗俗的调情话去包围,袭击那个年轻的妇人” ,女人们用窥视、讽刺、鄙夷和同情的语言嘲笑她。惟一值得自己骄傲的,是“她用她 自己的眼泪和遍体的伤痕来博得全村老迈人们的赞扬”,“尤其是对于那些浮荡的,不 守家规的妇人的骄傲”。对于梅春姐这样一个有爱有欲、珍视社会形象的青春少妇来说 ,生存境遇所带来的痛苦、悲哀、空虚和孤独,使她难以忍受无涯的黑暗的长夜,常常 幻想奇迹发生。
是地火就要奔突,就要燃烧,梅春姐的生命活力在压抑中忍耐着,等待着命运星火的 点燃。革命成了梅春姐的救世主,尽管她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革命,可当革命第一个事件 “剪头发”降临时,所有女人都痛哭流涕,惟有梅春姐泰然地毫不犹豫地挺身迎接锐利 的剪刀。当人们在紧张、好奇、恐惧和惶惑中关注着革命,连梅春姐那残暴、野蛮的无 赖丈夫也要去参加什么会(因为这个会可以使他发财、打牌、赌钱)时,革命对梅春姐来 说,却是一场从肉体到心灵的脱胎换骨的洗礼。革命带给梅春姐的首先是情欲的解放, “那一个的白白的,微红的,丰润的面庞上,闪动着一双长着长长的,星一般的眼睛! ”搅乱了梅春姐本已绝望的心灵,“在她的脑际里,却盘桓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摇摆不 定的想头”。尽管她觉得“不能让这些无聊的,漆一般的想头把她的洁白的身名涂坏” ,可是欲望、情感和希望的闸门一旦打开一点缝隙,就阻挡不住汹涌澎湃的解放潮水。 当长着一双“长长睫毛的,撩人的,星一般眼睛”的黄副会长向她求欢求爱时,“她犹 疑,焦虑着!她的脚,会茫然地,像着魔般地不由她的主持了!它踏着那茅丛丛的园中的 小路,它把她发疯般地高高低低地载向那林子边前!……”但是偷情被人知晓了,梅春 姐面对的是村人的指指点点,丈夫的暴打,内心的悔恨,以及那不曾熄灭的希望之光。 当黄副会长决定依靠革命的力量解决问题时,梅春姐终于将命运和革命捆绑在一起,情 人黄副会长成了她生命中可以依靠的北斗星:“我初见你时,你那双鬼眼睛……你看: 就像那星一般地照到我的心里。现在,唉!……我假如不同你走……总之,随你吧!横直 我的命交了你的!”
革命让梅春姐饱经摧残的人性得以觉醒、压抑已久的情爱得以释放,更使梅春姐获得 了新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形象。在经历了偷情风波不久,“梅春姐非常幸福地又回到村中 来了:她是奉了命令同黄一道回的。”她手中有了革命者的权威,有了革命者的价值资 源,成了村中的妇女领袖:“她整天都在村子里奔波着:她学着,说着一些时髦的,开 通的话语,她学着,讲着一些新奇的,好听的故事”,“这些话,梅春姐通统能说得非 常的时髦、漂亮和有力量”,尽管从前那班赞誉过她的老头子和老太婆们开始“卑视” 和“痛恨”梅春姐,但是那些年轻的姑娘和妇人们却像疯了一般“全都信了梅春姐的话 ,心里乐起来,活动起来了!”更为重要的是,梅春姐白天高兴地活动着,获得参与和 引导社会事务的满足之后,夜晚还能“名正言顺”地“像一头温柔的,春天的小鸟般的 ,沉醉在被黄煽起来炽热的情火里;无忧愁,无恐惧地饮着她自己青春的幸福!”革命 给了梅春姐新生的机遇,梅春姐也毫不犹豫地将身体和心灵全部交给了其实她了解并不 多的革命。
但是革命失败了,先是反革命的谣言“公妻”和“裸体游乡大会”之类事件动摇了革 命的社会心理基础,而后梅春姐的情人黄被枪杀。怀孕的梅春姐在牢房中生下了她和黄 的爱情结晶。在善良的乡亲们的劝说下,人性未泯的丈夫将她保释出狱。但是革命停滞 了,失败了,一切又都复原了,梅春姐仿佛具有了更深的罪孽,她的丈夫更加残酷地折 磨她。坚强的梅春姐以更大的毅力忍耐着,她怀念着黄,幻想着儿子长大“同他那死去 的爹爹一样”。然而当孩子被残忍的丈夫摔死后,梅春姐不再逆来顺受,“她渐渐地由 悲哀而沉默,由沉默而又想起了她的那六年前的模糊而似乎又是非常清晰的路途来!” 尽管没有了启蒙者、没有了热恋的对象,然而她的信念渐渐明晰、坚定起来。在小说家 叶紫极富象征和预言的诗意笔触下,梅春姐坚定而又自觉地选择了自己的前进方向:“ 北斗星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那两颗最大最大的上面长着一些睫毛。……你向那东方走 吧!……那里明天就有太阳了!”梅春姐义无反顾选择了星光闪烁的前方,她(和黄)在革 命岁月时所感受的幸福的巅峰体验,将会更加灿烂地降临。
这样,通过梅春姐坎坷和悲惨的经历,通过梅春姐痛苦但是坚定的人生选择,通过梅 春姐由爱欲追求到革命精神爆发,一个颇富艺术张力、颇富象征意味的革命故事和革命 预言就诞生了。革命理念在艺术情感和想象世界中,获得了充足的生命力,而且也似乎 预示了革命是惟一的选择和最高原则,不然就是奴役和死亡。
三、革命启蒙的统摄性、包孕性和复杂性的艺术展现
值得珍视的是,《星》所建构的有关革命的艺术想象世界,首先遵循的是文学的自律 性要求,它所创造的想象空间升华了革命理念,而非革命政治理念的机械表达。虽然小 说凸现了革命在社会存在和人生选择方面的终极价值意义,但是小说所展现的革命决非 单纯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而是描述了政治革命背景之下人的全面革命和整体革命, 既包含人的社会地位、社会身份的外部世界的革命,更包括人的生理、心理、情感和理 性的内在精神世界的革命,不但强调了政治理性和革命精神的统摄作用和指导意义,而 且更为细致、敏锐地展现了革命的复杂性和包孕性。
“五四”文学所塑造的人性觉醒与个性解放主题,尤其是女性的人性觉醒与个性解放 ,往往没有现实出路。在汹涌澎湃的个性解放潮流支撑下挣脱枷锁纷纷夺门而出的中国 娜拉们,最终面临的是鲁迅那清醒而深刻地发问:“娜拉走后怎样?”那时的个性解放 和人性觉醒更富于理想化和浪漫色彩,想象固然绚烂、超脱,但缺乏坚实的现实支点。 可是这些到了左翼十年间就完全不同了,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个性解放和人性觉醒有 了明确的现实价值坐标,在“堕落”和“回来”两条路之外,有了选择革命之路的可能 。叶紫的小说《星》就以敏锐的艺术笔触,将“五四”时期云霓般飘浮的个性解放和人 性觉醒,拉回到坚实的大地上,让革命与反革命的角逐来规划地之子们的命运和选择。 尽管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但是就生理、心理和生存状态而言,梅春姐和“五四”时期 中国的娜拉们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一个最底层的娜拉,可是却是一个有了明确现实追求 目标的娜拉,一个革命的娜拉。“五四”时期的娜拉们要么堕落、要么回去,但是梅春 姐却在革命的星光灿烂中寻找到人生的航道,去追求生理、心理和社会地位的解放,“ 革命”成了最高的人生价值律令。
更重要的是,《星》对革命的想象和描绘,完全不同于早期左翼小说的浮躁、浪漫和 激情。早期的左翼小说尤其是革命浪漫蒂克小说,大多侧重于愤懑的革命情绪的宣泄, 侧重于革命政治理念的宣传,急于使政治理想获得传播、获得认可、获得群众,作者的 主观意图没有很好地通过艺术手段进行传达,反而由于宣传革命理念的主观意图过于强 烈,不但使革命理念没有很好地经过艺术转化,反而以意害辞,强烈的主观理念意图严 重妨碍了艺术创造的生长空间。到了叶紫走上文坛的时代,这一切已悄悄发生了变化, 宣传革命的热诚、喧嚣与浮躁开始转换为冷静的思索,左翼作家们在反对者“拿出货色 ”的质疑下,开始深入细致地探索革命和艺术的关系,开始认识到革命与艺术决非简单 的从属与被从属的关系,而是蕴含着复杂的辩证内涵。在尊重艺术规律的前提下来表现 革命和政治的理念,开始得到左翼阵营的理论家、批评家和作家们的重视。
叶紫的小说《星》可视为这一文学思潮语境中的一篇有代表性的杰作,突出表现了左 翼作家在艺术创造上的突破。小说中将梅春姐和革命维系起来的中介,是她的情人黄, 革命的最根本的基础和动机是情欲和爱情受到压抑与摧残,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地位和 社会角色的损害。其小说主题的营造基本上是“革命 + 恋爱”模式。仿佛这个早期左 翼革命浪漫蒂克小说的主题,又复活在叶紫的小说中,但是已脱去了概念化、公式化、 模式化的弊端,使早期左翼小说家们浮躁的浪漫的革命激情经过沉淀,变得更为深沉、 真挚、丰满,更富于艺术感染力,更为有血有肉。尤其通过革命暴力争取社会解放和阶 级解放的宗旨,已具体化于人性觉醒与个性解放之中,从而使作品能发挥更大的社会功 能,在整体上提高了左翼小说的艺术品位,实现了一次高超的艺术超越。
这首先表现在小说所叙述的革命,是整体的、全方位的革命,是从肉体、心灵、情感 到社会角色选择和争取社会地位的全面革命,决非单纯的赤裸裸的政治革命和政治斗争 。这在梅春姐突破封建伦理和礼教文化思想的束缚,首先挣脱了情欲的压抑获得生理和 心理的解放,进而从事革命活动获得崭新的社会角色方面,有着细致和突出的表现。对 小说其他人物,尤其是梅春姐的丈夫和乡亲的描绘上,显示了作者对精神革命的关注。 作者在描述革命作为外力引起他们生存状况变化的同时,似乎更注重他们内在精神世界 的变迁,更注重政治理念和革命思想能否内化为这些人的变革驱动力。作者并没有拔高 和夸大革命的伟力,反而以浓墨重彩来讲述革命的来去匆匆,风过树摇,风止树静,和 鲁迅小说中对革命的疑问和反思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不是作者在强调革命统摄性的前 提下,将焦点移向了革命的包孕性、复杂性乃至脆弱性呢?
在小说中,除了简单提及的看守妇和狱卒之外,没有涉及具体的反革命人物。这意味 着作者并不注重革命和反革命的对抗,而是将革命和反革命的对抗淡化为小说的背景故 事。这意味着“革命如何启蒙群众”就成为小说的思考和表达重心。小说运用了对比的 写作手法。梅春姐自然是革命引导人性觉醒的成功范例,可是同样遭受压抑和剥削的其 他人却似乎与梅春姐形成了鲜明对照。她的野蛮、粗俗、丑陋的丈夫就阶级地位而言, 是属于贫下中农的范畴,然而却没有下层百姓通常所具有的善良品行,反而是一个粗暴 、蛮横的乡间无赖,对待革命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他的革命理想与 目标和阿Q一样。再看那些乡亲们,在革命降临时是那么惊慌失措,仿佛天塌地陷一般 。年轻人怀着好奇心理试探着加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革命作为外力挟裹下的不自 觉的选择,一旦外力失去作用,就会风消云散,缺乏理性主体的革命自觉性,是革命的 盲从者或革命的乌合之众,他们以生存为第一要义,大多数不会为了革命信念而抛头颅 洒热血。老年人面对革命的风起云涌,先是怀疑叹息,继之以抵制、暗骂和反对。对于 作为革命基础的这些大多数群众,作者借梅春姐之口道出了对革命进程和革命手段的疑 惑。通过小说对乡民们的叙述与描写,可以推断,革命理念世界中的无产阶级并非在人 性上具有优越性,他们既有底层人民质朴善良的品性,又有民间社会藏污纳垢的精神和 心理特点,如同别尔嘉耶夫从人格哲学高度进行的反思:“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缺乏经验 的真实,仅是知识分子构想的一项观念神话而已。就经验真实来说,无产者彼此既有差 异,又可以类分,而无产者自身并不具有圆满的人性。”[3](P187)这在反革命谣言的 传播过程中,表现尤为突出,所谓“公妻”、“裸体游乡大会”的传播和津津乐道者, 就是同属社会底层的老黄瓜之类的乡亲们。也同是这些乡亲们,在梅春姐身陷囹圄时, 没有幸灾乐祸,而是劝说她的丈夫,合力将梅春姐营救出来。叶紫的小说《星》以近乎 原生态般的艺术描绘,将中国乡村社会男男女女们沉重而又复杂的生存和精神状态,置 放于革命带来的社会变动中,着重展现他们在突如其来的革命面前的复杂的心理状态和 人生选择。人性觉醒与否成为革命如何由外在力量转化为内在驱动力的关键中间环节, 革命的复杂性、包孕性乃至脆弱性就鲜活地凸现在小说世界中。
小说对革命复杂性、包孕性乃至脆弱性的描绘,还表现在叙事主体的主观态度、叙事 视角上。与早期左翼小说不同的是,小说的叙事主体不再直接充当革命的传声筒,而是 隐藏在故事背后,用小说世界来展现革命的复杂性。作者不再像早期左翼小说家蒋光慈 、洪灵菲、阳翰笙等人那样近乎歇斯底里的革命情绪的宣泄、那样狂热的革命宣传激情 ,而是变得冷静甚至有一丝疑虑和不安。这一方面说明了左翼小说在艺术建构上的成熟 ,也说明了作者对于革命本身认识和体验的深化。比如梅春姐的情人黄,在小说中是革 命启蒙者的化身,然而作者并没有对他寄予多大的期望与热情,反而显得单薄、软弱, 在和梅春姐偷情被发觉后,只知道抱怨乡民的不开通,只知道依赖“上级”;在梅春姐 怀疑革命手段的激进时,嘲笑她心肠的软弱;在反革命势力反扑之时,缺乏冷静的应变 能力,为革命献身的同时似乎也在表达着自身的无能。这个人物尽管着墨不多,但从他 身上似乎寄托了作者对革命者形象的复杂思索。
总体来看,叶紫的小说《星》在政治理念与艺术塑造的结合上,是一个成功的典型文 本。作者将自己对革命的理性思索艺术化地融合在小说世界的创造中,既表明了作者的 政治态度,又成功地发扬了小说的社会功能。这也证明,政治与文学既非相互排斥,又 非从属、被从属关系,关键在于创造主体如何理解二者的关系,并艺术地展现出来。
收稿日期:2004-0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