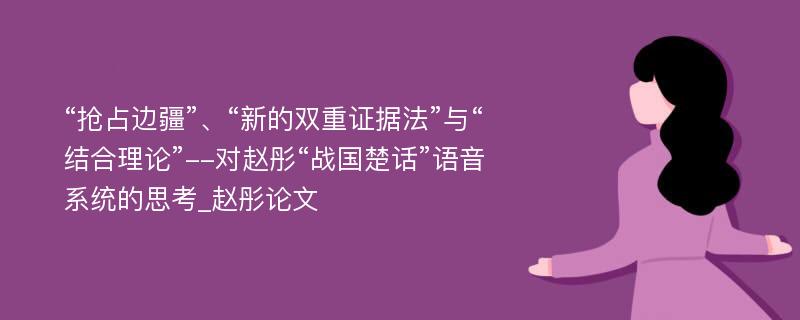
“抢占前沿”和“新二重证据法”、“结合论”——由赵彤《战国楚方言音系》引发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言论文,战国论文,证据法论文,赵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2年8月26日,我在石家庄市举行的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二届学术讨论会暨汉语音韵学第七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辞中曾经讲到,音韵学人应该重视出土简帛的研究,以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为代表的出土简帛文献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且在许多领域内掀起了研究的热潮,“可是音韵学者的反应却显得热情不够”,“自殷商甲骨文发现一百年来,古文字学的发展十分惊人,用这确凿无疑的材料来修正、补充、提升、发展我们的古音学,我大胆推测,这么巨量的而且是陆续不断的出土简帛将是中国好多学科原始性创新的源泉,自然也包括我们的音韵学”。(《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第十二届学术讨论会暨汉语音韵学第七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辞》,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编《音韵学研究通讯》第24期,2004年)
当时我并不知道,一位年轻的博士生正在着手搜集楚简的材料,并且把楚简音韵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的方向。这位博士生就是《战国楚方言音系》的作者赵彤同志。如今赵彤同志在他已经通过答辩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三年来,精益求精,反复磨砺,“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成就了这本专著《战国楚方言音系》。
此书值得赞许之处首先在选题之佳,起点之高。利用新出土的简帛文献以研究古音,这就是抢占学术前沿,意义非同一般。赵彤同志的研究方法的高明之处在于,把出土文献研究和传世文献研究结合起来,以“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互证,符合先贤创建的“二重证据法”的精神;把上古音研究和古文字研究结合起来,这就是“会通”、“交融”。我在2002年9月写成了一篇“义理”论文《论“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议汉语研究中的“犬马一鬼魅法则”》(载《古汉语研究》2003年第1期,又见《鲁国尧语言学论文集》第181-192页)在这篇论文中,我说:“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不可将‘历史比较法’和‘历史文献考证法’对立。”“我们在汉语史的研究中应该将‘历史文献考证法’和‘历史比较法’结合起来,甚至‘融会’,这是新的‘二重证据法’,或是汉语史研究中的‘二重证据法’。”“我们将‘历史文献考证法’和‘历史比较法’都视作前人的宝贵遗产,我们坚定地主张将二者调和、结合、整合,运用于具体课题的研究中,产出精品,甚至传世之作,这是汉语历史语言学的必由之路。”以上这些“结合论”观点是我2002年提出的,不意我却成了预言家,时隔四载,如今在赵彤同志的这本书里应验了。赵彤同志的这本《战国楚方言音系》就是“结合论”结出的果实,至于能否誉为“精品”,还有待学界的评议与时间的认定,但是,我以为,“精心”、“精彩”四字,赵彤此书足以当之。这本新著充分证明了“新二重证据法”是行之有效的,确是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我在此再次指出,“历史文献考证法”和“历史比较法”本来各自都是传统的方法,都是前代的精英、我们的先辈创造出来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各有其优点和缺点,时至今日,我们必须取二者之优,扬二者之长,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形成“新二重证据法”,这方可称为对中外优良传统的继承,方可称为在新形势下、新时代里的创新。我再次大声疾呼,做语言的历时研究的学人,如果想取得令人信服的成就的话,应该运用“新二重证据法”,走“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二者相结合的道路。中国人向来主张“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那么“结合”就是“大”;中国有句古话“取法乎上”,这“结合论”就是“上”!时下竟有人以巧言而背离“结合论”,鼓吹单一论,不知何故“出此下策”?
我还要继续“蠡测”赵彤同志的这本专著。描写、研究现代的方言,在当今中国的语言学界是显学,如今书店里方言学的书琳琅满目,一则因为中国的方言资源特别丰富,二则因为老中青方言研究专家数以百计。而我们汉语的历史很是悠久,可是研究中古、近代方言的学者及其论著则少得多。至于上古,我们一直只知道“上古音”、“上古音韵”、“上古音系”、“先秦音系”、“诗经音系”等术语,约二十年前吧,我们又知道“殷商音系”,这是因为有几位学者发表了关于殷商音系论文的缘故。可是“上古”即秦以前的方言呢?确也有专家利用古代典籍记载的资料对当时的某种或某些方言的特点作了尽可能的研究,出版了专著或发表了论文,这都是应该赞佩的。而描写、构拟上古某个具体方言的声韵调系统的书,却一直没有。现在我要说:如今有了,就是这本《战国楚方言音系》。这在上古音研究史上是不是首次?这是不是具有创新性的意义?毋庸我饶舌了。
赵彤同志奉献给学坛的二千多年前的汉语楚方言音系,是建立在坚实基础之上的,谓予不信,请读此书附录一“‘屈宋庄’及郭店楚简《老子》、《语丛四》韵谱”和附录二“楚简声母谐声关系总表”。收获跟耕耘成正比,所以作者多所发现,比如《楚辞》的用韵,古今研究者不可谓少,或认为与《诗经》无甚差别,或认为有些韵部合用不分,而赵彤同志通过钻研,特别是结合楚简的研究之后,仍然能有新见,比如长入声字变为去声,脂、真两部各有一部分字转入相应的微、文两部,侯、鱼两部应该分立,东、阳两部,真、耕两部亦然,等等,论证既然充分,结论当是可信。作者还通过分析合韵关系的变化拟测了主要元音的演变,这也是有益的探索。
赵彤同志此书以“屈宋庄”加楚简的用韵和楚简文字谐声为两根巨柱,建立了战国楚方言的音类体系,并进而构拟,如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以语音符号显示的战国楚方言音系。构拟是上世纪从西方输入的“历史比较法”的内容之一,或者说是伴生物。构拟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应该充分肯定,因为它以直观的形式体现了作者构建的语音系统。前辈大家如王力先生、李方桂先生都重视构拟,他们多年前的共同看法是,“搞拟测也是搞系统,真正的读音是不是那样子的,还不能说”(《语言学论丛》第十四辑第12页)。我认为,这两位大师的阐述揭示了构拟的实质,可谓得其精义,他们的话才称得上“正”与“确”。已经到了2005年了,居然还有人侈谈、提倡“学术前沿”、“构拟古代音值”,谬之甚矣!如此游谈无根,必然引导青年误入歧途。一个研究语言史的学人,如果在头脑里构建出某个语音系统,或者像高本汉那样以瑞典方言字母(案,并非国际音标)显示,或者像其后的大多数中国学者那样用国际音标显示,皆无不可。我认为,进行语言史研究,如果意欲构拟,当进入构拟阶段时,构拟的准则之一是,力臻自圆其说,避免自相矛盾,亦即必须思虑周密,以求圆融无碍;切忌顾此失彼,而致左支右绌。当然,还需要经得起诸多检验,等等。我知道,赵彤同志为构拟战国楚方言音系尽了很大的努力,我们读赵彤同志的构拟,就是读赵彤的系统。对此道有兴趣、有素养的学人,自可去解读他的构拟,给予应得的评价。
在这本书中,尚有若干值得肯定之处,如不为成说所囿,结合汉语自身特点,提出了“内部比较法”,编制繁复的楚简谐声表、楚简韵谱,等等。当然,“战国楚方言音系”这么一个大课题,这么一个难课题,包含了许许多多需要解决的中小问题直至具体的细节,因此需要讨论的地方肯定是有的。又,作者是音韵学出身,而以楚简文字为主要研究对象,虽然刻苦有加,然而进入一个学术积累也非常深厚、知识含量也很高的相邻学科,短期内要做到游刃有余,那很难的,因此书中的论述必然也会带来商榷,我相信赵彤同志会虚心跟学界朋友切磋的。有学问的,必定谦虚;想做学问的,也必定谦虚。凡自命不凡的,傲视一切的,实际上,都是“嘴尖皮厚腹中空”。
清代古音学的兴盛,促进了训诂、文献等相关学科的发展,相关学科的实践自是对上古音研究结果的一种检验。如今,大量的古文字和出土简帛文献为古音学的深化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古音学研究的新成果也应当反馈、反哺。本书的某些发现已被古文字学家所利用,比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民之父母》第9简“丌才语也”一句,一直无的解,最近陈剑先生受到本书作者对楚简中“其”、“异”通假及以母同见母关系的分析启发,将此句解读为“异哉语也”,便涣然冰释。于此可见,为古文字和出土,文献的专家提供“利器”,是古音学者的分内之事,古音学者不能还是按老办法“关起门来搭自个儿的积木”,应有利他的思想、利他的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放之四海而皆准,古音学说,不是靠花样翻新来赢得市场,必须经得住检验才能“站得住”。
我一贯认为,语言史的研究愈古则愈难,而难知者则愈多,此乃“犬马一鬼魅法则”的效应:“在汉语史中,越近于近代,‘犬马’的成分越高;越是到上古、远古,乃至史前,‘鬼魅’的因素越多。”(《论“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议汉语研究中的“犬马一鬼魅法则”》,出处见前页)春秋之时,语言甚多,强势语言是华夏语(即汉语的前身),其他则以楚语、吴语为著。我曾经在几篇论文(如《“颜之推谜题”及其半解》,见《鲁国尧语言学论文集》)中谈到,寿梦、阖闾、夫差时的吴语是非华夏语,而后在淮河以南至太湖流域,这一片地区的语言转变为汉语的古吴方言。但是怎么转变的,转变的时间,我们 ‘对这个中国语言史上的重大问题知之甚少。与此情况类同,在两千多年前,江湘流域的语言——楚语也本非华夏语,但是后来转变成了华夏语即汉语的一支方言,怎么变的,何时变的,同样是汉语史上的重大课题,值得探究,我特别希望赵彤同志在《战国楚方言音系》出版后,保持锐气,乘胜进取,抢占汉语史上的又一个前沿阵地。
我在少年、青年直至壮年时代喜欢阅读军事题材的文学作品和历史著作,如《星火燎原》若干集、《毁灭》、《日日夜夜》、《朱可夫传》、《第三帝国的兴亡》、《巴顿将军传》等等,知道什么叫“前沿阵地”,什么叫“抢占前沿”。到了中年、老年时代,则在读书与治学中,仰观前代,俯察当今,知道在学术领域里,也存在个“抢占前沿”的问题,捷足者先登,先登者必捷,这是无可置疑的定律。赵彤同志以刚出土的简帛文书与传世文献相结合,以“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相结合,“抢占”了“前沿”,我曾经是他的博士论文的审阅人,如今又为他的专著写序,自然感到欣慰。关于学术前沿的问题,此时我浮想联翩,请先让我摘抄1983年10月21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上古音学术讨论会上三位先生的发言——
朱德熙:我觉得研究上古音,除了汉藏语比较的资料以外,汉语文献资料并没有用完,古文字就是一大宗。我总希望研究上古音的人能注意一下古文字。……我希望上古音研究能够跟古文字研究结合起来。
李方桂:我十分同意这个意见。有些所谓谐声字根本就不是谐声字,这可以从古文字材料中得到证明。看来我们要请教搞古文字的人的地方还很多。
周祖谟:研究古文字的已经向研究古音的挑战了。
李方桂:挑战有挑战的好处,它可以把我们的毛病挑出来,我们好加以改正。
(《语言学论丛》第十四辑第19、20页)
案,朱德熙先生在发言中举裘锡圭先生的研究成果为例。裘锡圭先生也多次论到古文字研究与古音研究结合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并以身作则,屡屡著文。朱德熙先生后来再次指出:
帛书对于历史音韵学的研究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帛书很多地方是押韵的,又有大量假借字,还有许多和现存古书不同的异文,这些都是研究古音的重要资料。
(《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座谈会上的发言》,见《朱德熙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
我在本世纪初看到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公布引发的对简帛文字的研究热潮,可是又眼见“音韵学者的反应却显得热情不够”,因此在中国音韵学2002年夏学术研讨会的开幕辞中提议古音学专家也积极投身其中,以使古音学得到提升、发展。当看到赵彤同志的《战国楚方言音系》的书稿,我在“叹赏”之际,忽然发现,这“学术前沿”的确是被赵彤同志“抢占”了,可是更发现,在不算不热闹的古音学界居然没有什么人去跟赵彤“抢”!赵彤同志占据了前沿后,回首一看,身后竟然没有紧迫者或不紧的追者,当作何感想?
我不胜感慨:朱德熙先生二十多年前的忠告“我希望上古音研究能够跟古文字研究结合起来”,何以响应者寥寥?谈“学术前沿”者竟言不及古文字!
写到这里,不禁悲从中来。
众所周知,朱德熙先生生平很重视理论,对国外语言学特别是美国语言学的动态和研究成果十分关心,密切注意,力求吸取其精华,以充实我国的语言学。他晚年在美国授课、讲演,因此对美国的语言学非常了解,并洞悉其利弊。以他的道德、学问,以他的良知、睿智,他在1991年3月16日明确提出:“美国语言学有重理论轻事实的弊病。”(鲁国尧《重温朱德熙先生的教导——为纪念朱德熙先生逝世十周年而作》,《语文研究》2002年4期)此后不久,朱先生即患癌症,于1992年7月辞世。他的“美国语言学有重理论轻事实的弊病”的命题,可谓“朱子晚年定论”。
朱德熙先生为祖国、为民族、为科学的献身精神,感人至深,他积五十余年摸索、追求之经验,最后得出了“美国语言学有重理论轻事实的弊病”的结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理念,这是朱先生的遗嘱,这是一位语言学大家、智者留给我们后来者的宝贵遗产。
我们应该重视、应该宣传、应该阐述、应该发扬。
然而中国语言学的事实是如此的冷酷,朱德熙先生的“遗嘱”影印件在《语文研究》公开后,已经三年有余,不见中国语言学界对朱德熙先生的“美国语言学有重理论轻事实的弊病”的学说有任何反应,对这么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理念竟然以不理不睬冷处理!
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应者寥寥!
“寂寞身后事”,此乃生前备受尊崇者的通则,朱德熙先生亦何能免?
呜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