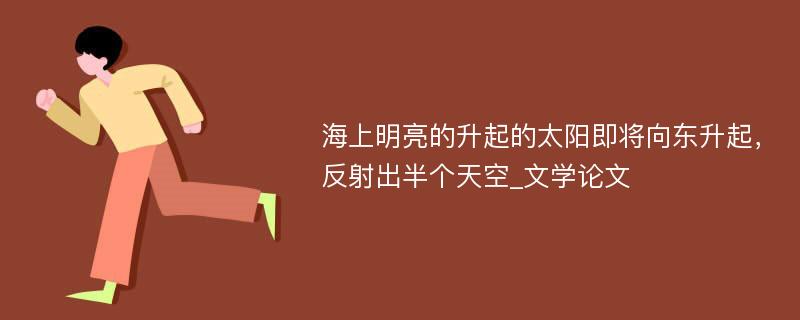
云霞出海曙,辉映半边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云霞论文,半边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是我未曾公开过的小秘密:我对新文学的最初兴趣是由两位女作家激发的——一位是陈衡哲,另一位是谢冰心。
半个世纪之前,我家有一位房客,人称孙老太,江苏人,不知是孀妇,还是老姑娘,总之是一人独居。她自己安装的矿石收音机极为简陋,但可以清晰收听到电台的广播,那时儿童节目正在播放陈衡哲的《小雨点》。孙老太听完之后,就耐心地转述给我听,我当时大约八岁。从这篇融童话、寓言、自然科学于一炉的作品里,我受到了最初的理想教育,知道了世界上除了雨点之外,还有涧水,还有河流,还有大海,而大海小的时候也是一个小雨点。我还为小雨点的爱心而深受感动。为了挽救高山顶上那朵干枯苍白的青莲花,小雨点宁可牺牲回家的机会,心甘情愿地让青莲花将自己吸入它的液管。
而教导我要爱自然、爱人类,特别是要热爱母亲和幼者的,则是冰心女士。大约十岁那年,我从姨妈的书箱中翻出了一本小说《关于女人》。我开始并不知道这本书的内容,但不知怎的,这个书名却使我产生了男孩偷窥邻家女孩隐私似的负疚感,虽然我当时还谈不上“情窦初开”。读着读着,我才知道这并不是一本谈情说爱的书。书中有美艳绝伦、常被男性在心中供养的C女士,有原以“妻死不娶”为男人人格最高标准而后来终于改变观念的L太太,有为追求绝对完美而宁可不嫁的高贵的R小姐,有终日劳作被岁月的流水将青春洗刷得不留一丝痕迹的张嫂……这些纯洁高贵的女性形象在我心中留下了长久的记忆,其中使我终生不忘的还是《我的学生》一文中的S。这位聪颖乐观、生活方式相当西化的女性,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顽强地生活着,最终为输血救人而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些成功的文学形象印证了冰心的一句名言:“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
不过,以我当时的人生阅历,当然无法理解冰心“爱的哲学”中包含的爱国主义内容和曲折反映出的忧患意识,无法充分认清其人性关怀的正面价值。反倒是这种理念局限的一面,使我幼小的灵魂变得更为纤弱,只怀着童稚的幻想遥盼天边的彩虹,而无视人生旅途中随处可见的棘刺。我铭记了冰心的告诫:“人类呵!/相爱罢,/我们都是长行的旅客,/向着同一的归宿。”(《繁星·十二》)后来我才知道,几千年来,人类之间其实没有一天终止过猜忌、倾轧、欺凌、盘剥乃至于厮杀、屠戮。冰心又说:“母亲呵!/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它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繁星·一五》)后来,我“心中的风雨”真的来了,我想躲到母亲的怀里,而我那过于善良而累遭不幸的母亲却早被生活的风暴抛弃到死亡的边缘,自救无门,哪能张开宽厚的羽翼为我遮风挡雨?
我于是又找到了鲁迅,那是读高中的时候。在一篇名为《为了忘却的记念》的课文中,鲁迅记叙他对青年作家柔石“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此时柔石的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然而,鲁迅近乎冷酷的话却不幸而言中。柔石不但曾经被友人出卖,而且终于被捕入狱,作为政治犯而身受酷刑,就义时头与胸部连中十弹……柔石牺牲后,在他1929年10月14日的日记发现了鲁迅的另一番教导:“鲁迅先生说,人应该学一只象。第一,皮要厚,流点血,刺激一下,也不要紧。第二,我们强韧地慢慢地走下去。我很感谢他底话,因为我底神经末梢是太灵动的像一条金鱼了。”我这才领悟到,在真善美与假丑恶并存的社会里,人们既应该从文艺作品中接受“爱”的教育,也应该从文艺作品中接受“憎”的教育,这才是比较全面的人格教育,素质教育。“神圣的爱”与“神圣的憎”本是人的神圣情感中的两极。而在人类的理想社会到来之前,只有灵魂的荒凉和粗糙类似于鲁迅的人,才能够在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的情况,仍然转辗而生活着,坚韧地战斗下去!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生活体验,无意于作为普遍的人生经验加以推广。
就这样,接受了这些作品的熏陶,我在高中毕业之后报考了大学的文学专业,比较系统地学习了中外文学史,知道宇宙万物的生成与运动都是由阴阳二元对立所引起,人类文艺的崇楼广厦也是由男性与女性的两大柱石共同支撑。只不过在绵延着父权制文化结构的社会中,女性文化的支柱出现了长时期的倾斜。由于男性执文化霸权之牛耳,男性话语成为了文化的中心形态,因而女性视角、女性观点、女性声音遭到了不应有的忽略和排斥,整部文学史成为了一部以男权文化为中心、以男权立场和话语描述的历史。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的其它国家,改变上述畸性文化现象都是近百年来的事情。在西方,文艺复兴的狂飙驱散了封建主义的阴霾,显露出人文主义的曙光。随着“人”的发现,“女性”的发现,“儿童”的发现,特别是随着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之后女性自主意识的发展,女性写作终于绽开了绚丽的花朵,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仅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中,女性作家就在瑞典小说家拉格洛夫(Selma Lagerof),意大利小说家黛莱达(Grazia Deledda),挪威小说家温塞特(Sigrid Undset),美国小说家赛珍珠(Pearl S.Buck),智利诗人米斯特拉尔(Gabriela Mistral),瑞典女诗人、剧作家萨克斯(Nelly Leonio Sachs),南非小说家戈迪默(Nadine Gordimer),美国黑人作家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
在中国,女性自觉投身于文学创作并把自己的作品作为社会文化流通一部分的历史更为短暂。虽然在中国历史上曾经陆续出现过卓文君、班婕纾、蔡文姬、李清照一类的才女写作,虽然晚清革命家秋瑾已经在她的作品中渗透了强烈的女性意识,成为了由古代女性写作向现代女性写作过渡的先驱,但女性作家作为一种群体出现还是在狂飙突进的五四时期。在这场被喻中国文艺复兴的新文化运动中,繁星璀璨般地出现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女作家。她们踏着五四时代的鼓声,迎着新世纪的曙光,昂首阔步地走上文坛,其中有“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着文艺气息”(胡适语)的陈衡哲,有以“问题小说”(冰心语)作为“第一部曲”的冰心,有“从《海滨故人》的小屋子门口探头一望就又缩回去了”(茅盾语)的庐隐,有擅以闺秀笔致写“旧家庭中婉顺的女性”(鲁迅语)的凌叔华,有真实表现五四青年“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鲁迅语)的冯沅君,有埋葬于陶然亭“春风青冢”下的蔷薇社女作家石评梅……她们的作品在内容上表现出对妇女人权(特别是婚姻自由权、教育权、职业权)的密切关注,围绕着“娜拉走后怎样”的中心命题对中国妇女的历史命运进行了深沉的探索,对传统的男权中心及其价值观念提出了勇敢的挑战。在艺术形式上,她们的作品也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审美风格,比如陈衡哲的作品善写景物,谈人论事,议论风发,活泼幽默。冰心的作品婉约秀逸,如芙蓉出水,秀韵天成,恰如她笔下的诗神——“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欲语又停留”。庐隐的作品流利自然,纵横挥斥,以激切直露的内心抒发和哀切动人的气氛烘托为特色。作者个人惨痛的婚恋史,又使她的作品在乐观的表层下隐藏着伤感的底色。凌叔华的作品以画笔入文,文字素淡温婉,写凡人小事,如云林山水,落笔简约而意境幽远。其作品结构精巧,能将简单情节铺排得曲折生动,收到了尺水兴波的艺术效果。林徽因则于二十年代崭露才华,于三十年代后半期达到创作高潮。她的诗作自由洒脱,参差斑驳,极具现代意味。这批作家的创作成就自然有高低之分,但她们却共同在中国女性文学的空白之页上谱写了开天辟地的篇章,彻底结束了中国女性在文学史上作为“盲点”而被遮蔽和隐埋的历史。作为五四时期妇女解放的精神代表,她们唤醒了大批女性冲击封建家庭的樊篱,争取作为人和作为女人的正当权利。
中国第二代的女作家群体涌现于三四十年代。在这批作家中,最具承前启后意义的是善写女性并始终坚持女性立场的丁玲。她不拘囿于自我遭遇和个人情感,能透过女性觉醒的表层揭示出她们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因而使其作品最具有近、现代女性的“强己”意识,也最具有面向整个社会和面对全部历史的高度责任感和强烈使命感。这两方面互相渗透,将她的创作一步步推向高峰,使她成为了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年代升起的一颗耀眼的巨星。
三十年代另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女作家是呼兰河的女儿萧红。她通过一种介于小说、散文、诗歌之间的新型的小说样式,表现出“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以及沉滞闭塞的农村生活对民族活力的窒息。她作品中直观、通感的女性话语,率直天真的儿童语言,质朴生动、极具表现力的方言口语,非规范化的遣词造句方式,都表现出女性作者特有的越轨笔致。
在三四十年代的沦陷区女作家中,应该提及的有上海的张爱玲、苏青和东北的梅娘。张爱玲的作品以女性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同情描写转型时代受扭曲、凌辱、压抑和毁灭的女性,并揭示出男性接受传统文化负面影响之后“寡于情,陋于质,趋于利,薄于义”的生命状态。她的作品融合了通俗与先锋、传统与现代的诸多因素,用女性话语、女性文本和女性方式深刻揭示出女性是礼教和家族制度的最大受害者。苏青的作品同样洋溢着强烈的女性意识。她以平实的“写实体”抒写自我,以女性的大胆笔触描写男女情事,用内心独白的方式揭示人物隐蔽而微妙心理。类似于“出土文物”的梅娘在搁笔四十年后又奇迹般地再现于文坛。她当年的所谓“水族系列小说”(中篇《蚌》,短篇《鱼》,中篇《蟹》)善写商宦之家女性的生存状态,也将笔触伸向了沦陷区社会的种种卑微人物和灰色人群。其作品常以第一人称倾诉人物“独白式”的内心世界,文笔明丽婉约,也常有辛辣犀利、雄健强劲之笔。
在中国第二代女作家中,至今留在读者记忆中的还有“文儒女侠一身当”的谢冰莹;有跟凌叔华并称“珞珈山三女杰”的苏雪林、袁昌英——她们集作家、学者、教授于一身;有牺牲时年仅二十四岁的左联五烈士之一——冯铿;有因肩负特殊使命而蒙冤廿七载的左翼女诗人关露——她就是脍炙人口的歌曲《春天里来百花香》的歌词作者;有“喝过鲁迅奶汁”的草明、陈学昭;有巴金关怀、培养过的罗淑、罗洪;有跟老舍共同创作过话剧《桃李春风》的赵清阁;有跟张爱玲、苏青并称为“三大才女”的施济美,有创作、翻译均结硕果并成功自办了出版社的沉樱,有以创作历史小说崭露头角而后来以填写古典诗词赢得盛誉的沈祖棻,有怀着“焦灼的渴意”进行创作的九叶派诗人陈敬容,有沐浴了“一二·九”风暴的小说家韦君宜,有因短篇小说《贵宾》含沙射影“攻击江青”而在文革时期遭到批判的葛琴……跟第一代女作家相比,第二代女作家作品的基本风格更为激越浑厚,体现了女性意识的升华和女性书写的历史进步。
从1949年至1966年的十七年中,中国女作家大多在作品中取中性化或雄性化姿态,表现出女性审美体验的失落。但即使如此,在战争、家庭一类社会性、革命性主题的掩盖下,她们的作品仍或多或少潜隐着对女性命运的关切和思考,渗透出女性情感、心态、价格观念的特殊色彩。在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历史上的一切进步文化基本上都被革除,中国年轻的女性创作当然更没有立锥之地。直到百废俱兴的八九十年代,由于改变了“男女都一样”的生存环境,中国的女性创作才重新复苏,并很快就在题材的丰富性与体裁的多样性诸方面到达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呈现出无比广阔的历史前景。不过,也有些女作家在都市文化意识和商业化倾向的影响下迷失了自我价值,步入了创作误区。有人热衷于“小女人”心态咀嚼身边的小小悲欢,文字矫情、发酸、发嗲。有人过分热衷于与性相关联的“身体书写”,肆无忌惮地暴露女性隐私,挖空心思地设置“男性陷阱”,毫无节制地描写性爱体验,自我抚摸,自我品味,陶醉于自己的性别美,性感美,并以此满足一部分男性读者猎艳窥私、追骚弄荤的低级趣味。这些倾向显然背离了中国女性写作的优良传统,其后果必将由试图“飞翔”而终至“坠落”。
毋庸讳言,跟中国现代文学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世界政治思潮、文艺思潮的影响一样,中国的女性创作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女权主义(或曰女性主义)的影响。其实,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都源于19世纪80年代英文中出现的Feminism一词。这是一种谋求男女平等的意识形态和实践活动,旨在消除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诸方面歧视妇女的现象。由于女权主义的译法容易使人产生女性张扬自身霸权的误读和偏见,目前在港台及其他华人地区比较约定俗成的译法是女性主义或女性性别主义。从强调角度而言,女性主义更为关注性别差异,强调性压迫、性歧视、性的不平等给女性带来的种种压抑。显然,中国现代出现的女作家并不都是女性主义者,她们的作品当然也不能一律划归于女性主义文学范畴。根据我的理解,女性主义文学不仅必须以女性为创作主体,不是男性作者以女性题材写出的作品;而且女性作家必须自觉以女性意识进行创作,并在作品中鲜明体现出性别立场和女性的美学情愫。“女人写”或“写女人”的文学作品并不都是女性主义文学。只有女作家以女性意识对女性的历史状况、现实处境和生活经验进行描绘,并且在艺术方法上对传统男性中心社会文化建构进行颠覆和反叛的作品,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文学。所以,中国五四时期和三四十年代的女作家作品,大多只能称之为女性书写或女性创作,而不能用削足适履的方法统统塞进女性主义文学的靴子。
在这里更需要强调的,是中国近现代妇女运动跟西方女权运动的区别,因为这个问题跟研究中国现代女性创作(或曰女性书写)有着密切关联。自1902年同盟会成员,近代文学家马君武译介赫伯特·斯宾塞的《女权篇》开始,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就跟男性革命家和男性进步学者的倡导密不可分,取一种“常青指路”模式,而没有出现西方文化中那种泾渭分明、截然分立的性别意识,也没有形成独立的思想体系和权威性的代表人物。更由于面临着“三座大山”(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中国社会中的阶级对立和民族对立远远超过了男女性别间的对立。如果中国的妇女运动不汇入挽救国家危亡、推进民主政治的民族民主革命洪流,如果妇女不首先争得基本的生存权,就根本谈不上其他人权和女权。因此,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无法成为一种独立存在的运动。在这种波澜壮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中国的女性创作不但无法跟反映并推动民族独立和社会变革的主流文学脱节,不但无法跟人民大众的主流意识形态脱节,而且不少卓有成就的女作家还自觉淡化性别意识,将自己独特的性别遭遇转换为对民族命运、种族生存的关注,以一种“大女性精神”进行创作。丁玲拒绝为《真善美》杂志的“女作家专号”撰稿,宣布只卖稿子不卖“女”字。谢冰莹要做“女丘八”。冯铿“从不把自己当女人”(《妇女运动概论》)。白薇要做“女子汉”,用文学的武器表现被压迫者的痛苦,暴露压迫者的罪恶。杨刚在北平沦陷的日子里,处于“有男人,不能作男人的女人;有孩子,不能作孩子的母亲”的境地,决心跟蹂躏“中国皇后”的强盗拼死斗争,随时准备牺牲。曾克卸下红妆,以随军记者身份挺进大别山,先后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大西南战役,创作了大量史诗般的战地通讯。菡子更明确表示:“我是一个小兵,埋在我心里最宝贵的东西,是战士生活和回忆,部队是我最早的学校,伟大的革命战争赋予我艺术生命。”只要我们不把女性主义作品跟优秀文艺作品划上等号,只要我们不把女性经历局限于女性隐私、性心理、性经历,只要我们不把女性主义的批评方法视为惟一的文学批评方法,我们就能对中国现代女性创作的成败得失作出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估。
正因为中国现代女性创作为中国文学宝库增添了异彩,好比“云霞出海曙”(唐·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大意是海上日出,云霞绮丽),映红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半边天,深入研究这些女作家的生平史实和心路历程就成为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因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一套《回忆女作家丛书》既是研究中国女性创作的一项基本建设,也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项基本建设。丛书所收诸篇提供的都是作者亲历、亲闻、亲见,更增添了这套丛书的史料价值。多年来,我阅读并研究了不少回忆录作品,也曾比较系统地阐述我对回忆录写作的意见。简而言之,在我看来,对待回忆录应取的态度是八个字:不可不看,不可尽信。“不可不看”,是因为作为史传文学的回忆录能弥补媒体信息储存和文献资料记载的不足,进一步丰富文学史料的仓储。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一门年轻学科,像苏雪林、谢冰莹、凌叔华这样撰写过自传或像庐隐、萧红、王莹这样撰写过自叙性作品的作家并不多,所以作家同时代人提供的回忆和评价就显得更为珍贵。“不可尽信”,是因为任何回忆录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回忆者个人立场、观点、情感和接触范围的局限,带有不同程度的主观色彩,而且从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要求记忆跟事物的本来面貌完全吻合,也是一件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因此,在阅读回忆录的同时必须对所提供的史料进行核实和鉴别。根据我的阅读经验,他人的回忆如果跟作者本人的自述不符,一般应以自述为准。不同回忆者对同一件事说法不一,一般应尊重多数人的说法,但也应该允许少数人保留自己的看法。同一回忆者不同时期的说法如果互相抵触,在正常的情况下,一般说来较早的回忆往往比较迟的回忆更为可靠。回忆如果跟事实不符,则应该无条件面对事实,承认事实。严格的真实性是回忆录赖以存在的基础,而夸张或掩饰的回忆录只会惑乱视听,给读者以误导。在回忆录中,存心作伪的情况也间或出现,这种赝品更值得我们警惕。
标签:文学论文; 女性主义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小说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鲁迅论文; 陈衡哲论文; 凌叔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