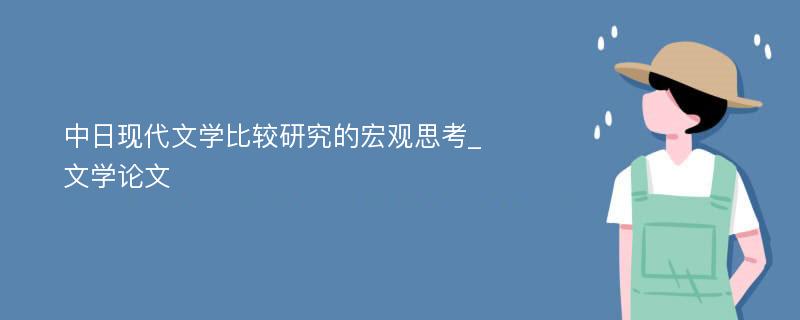
中日现代文学比较研究的宏观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文学论文,中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发展和成长起来的,新文学的“新”的东西大都来自外国文学,因此,离开外国文学谈中国现代“新”文学将是片面的和狭隘的。而在外国文学中,日本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具有特殊密切的关系。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离开日本文学,就无法谈中国现代文学;没有日本文学的影响,没有中国现代作家对日本文学的理解和接受,中国现代文学就不会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早在1928年,郭沫若就在《桌子的跳舞》一文中指出:
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创造社的主要作家都是日本留学生,语丝派的也是一样。
此外有些从欧美回来的彗星和国内奋起的新人,他们的努力和他们的建树,总还没有前两派的势力的浩大,而且多是受了前两派的影响。
就因为这样的缘故,中国的新文艺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礼的。……
尽管现在看来这话并不很严密,但他却正确地指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事实: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重要的骨干人物,都是留学、流亡或长期滞留日本,深受日本文化和文学浸润的。其中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或一定地位的就有百余人。如:黄遵宪、梁启超、章太炎、马君武、陈去病、王国维、秋瑾、苏曼殊、邹容、陈天华、李叔同、陆镜若、徐半梅、任天知、陈独秀、李大钊、吴虞、刘大白、沈尹默、欧阳予倩、鲁迅、周作人、钱玄同、许寿裳、陈大悲、夏丐尊、谢六逸、黎烈文、章克标、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田汉、张资平、陶昌孙、滕固、倪贻德、缪崇群、方光焘、郑伯奇、沈起予、李初梨、冯宪章、森堡(任钧)、徐祖正、汪馥泉、李漱泉、夏衍、王独清、穆木天、杨骚、白薇、林伯修、李一氓、冯乃超、彭康、朱镜我、楼适夷、钟敬文、林林、韩侍桁、胡秋原、刘大杰、丰子恺、刘呐鸥、黄源、孙食工、徐蔚南、张深切、钱歌川、胡风、周扬、林焕平、贾植芳、孙钿、杜宣、孙席珍、雷石榆、梅娘等等。此外,虽未长期留学或滞留日本,却与日本文学有一定关系的,还有茅盾、巴金、冰心、穆时英、萧红、谢冰莹等。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这些作家构成了中国文坛的主力和中坚。和留学欧美的作家们比较起来,他们不仅在数量上较占优势,而且在观念上也更开放。身处近代日本全面开放的社会环境中,他们所了解和接纳的世界最新文艺和社会思潮,甚至比留学欧美的人更多,也更驳杂,更多元化。在当时的欧美,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的保守风气仍未散去,而且在文化和文学界还有相当势力。而能够去欧美留学的人又大都出身富贵,他们身上的中国传统士大夫气很容易和西洋的绅士气融化在一起,从而形成了现代文化贵族的某些倾向和特征,如甲寅派、学衡派的冥顽不灵,胡适的冷静的实证,梁实秋的白璧德式的保守,徐志摩的奢华浪漫,林语堂的儒雅幽默,闻一多对艺术形式探索的迷恋;相反,留日学生大都出身低微,经历坎坷,他们处在东西方文化剧烈冲突和融合的日本社会氛围里,处在因国弱民穷而常常遭受歧视和欺辱的处境中,形成了骚动、震荡、愤懑、激进、忧国忧民的情绪特征,而只有文学是表现他们这种情绪特征的最好途径。因此,留日学生中才有那么多的人,果断放弃原修专业而改行从事文学。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日本近代社会那种特有的社会文化环境熔铸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大批中坚作家。作为留日作家,他们既是接受日本文化、日本文学影响的主体,又是联系中国文坛和日本文坛关系的桥梁。正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的留日作家,日本现代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了持续不断的影响。
一
我们可以把日本现代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作用及其方式归纳为如下两种情况。第一,媒介作用。对于中国现代文坛来说,日本不仅仅是日本本身,也是反映西方的一面镜子。中国许多人是抱着学习西方的目的去日本留学的。他们在日本学习欧美文学,或通过日文译本阅读欧美文学。因此,日本文坛是联系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走廊”、渠道和媒介。严格地说,现代日本的文学观念、文学思潮流派,乃至文体形式,纯属自己的并不多,大都是对欧洲文学的借鉴和仿效。构成日本文学发展演变基本面貌的写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新浪漫主义、新感觉派等现代主义文学、普罗文学等文学思潮运动,最初都是由欧洲引进的。而中国文坛对这些思潮流派的最初的了解,很大程度地依赖日本的媒介。例如,以北村透谷为中心的日本浪漫主义文学对中国的浪漫主义并没有多大影响,但中国浪漫主义的核心团体——创造社的成员,却是在日本阅读和了解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他们对西方浪漫主义的选择和理解是受日本文坛的中介作用制约的。往往有这样的现象:日本文坛推崇哪位西方作家,或哪位作家在日本名声大,中国文坛往往也马上重视和推崇那些作家。如挪威的易卜生在20世纪初的日本备受推崇,随后便在“五四”时期的中国声名大噪。其他如霍普特曼、王尔德、泰戈尔、惠特曼、尼采、歌德、拜伦,左拉,情况也大致相同。换言之,当时中国文坛对一个西方作家的重视程度,主要不是由该作家在西方的地位和影响所决定的,而主要是由该作家在日本的影响和地位决定的。我们现在所认定的西方超一流的作家,如巴尔扎克等,在当时中国的影响都很一般,这也与日本文坛的中介作用很有关系。而且中国文坛对某一国家文学的重视程度,也受到日本文坛的影响。如“五四”时期,我们在欧洲文学中最重视西欧文学,20年代后期我们最重视俄罗斯文学,以至最早一批俄国作品大都是从日文中转译的,这都和日本文坛译介西方文学的侧重点的移动密切相关。第二,日本现代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引发与启示作用。中国的各种文学运动的酝酿和爆发,固然是中国社会文化、中国文学内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但外来因素的引发与催促也至关重要。尤其是来自日本文坛的影响,每每促成了中国历次主要的文学运动的发生。如晚清维新派的文学改良运动及近代白话文运动,启蒙主义思潮与“政治小说”,“五四”时期“人的文学”观念的形成,20年代后期的革命文学运动,30年代前后的新感觉派文学等,最初都是受到日本文坛的引发和启示。尽管类似的文学运动欧洲也有,但由于欧洲有关的文学运动与中国文坛的时间空间距离过大,因而难以造成冲击性的影响。如欧洲在但丁时代就已开始了语言通俗化运动,在文艺复兴时期就有了人本主义文学运动,18世纪有了启蒙主义文学运动。这些隔世的欧洲文学运动,对中国现代文学大都是作为一种知识背景,而不是可及可见的现实榜样。而日本文学现代化与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时差,最多只有30来年,有的文学运动的时差(如革命文学运动)只有几年时间。因此,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尤其是40年代之前的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都是在日本文坛的直接引发、刺激和催促下形成的。
由于上述情况,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也和日本文学的发展进程有着高度的相似性:两国现代文学都孕育于启蒙主义的“政治小说”,而两国现代文学的真正起步,则都始于对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提倡,接踵而来的又都是浪漫主义的文学思潮。浪漫主义在两国存在的时间都很短暂。在日本,许多浪漫主义作家转向了自然主义,在中国,许多浪漫主义作家转向了左翼文学;于是,自然主义和左翼现实主义便分别成为两国现代文学的主潮;在日本,反主潮的文学有白桦派的人道主义、唯美派的艺术至上主义和强调理智地分析现实的新现实主义(新理智主义);在中国,反主潮的文学有新月社的古典主义,京派作家群为代表的自由主义;30年代前后,中日两国同时出现了无产阶级文学和“新感觉派”;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上半期,日本的侵华文学和中国的抗日文学又成为平行对峙的两种文学运动。可见,至少到20世纪40年代,中日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和相似性。我们可以把这种相关与相似简单地表示如下:
日本:政治小说→写实主义·砚友社→浪漫主义·自然主义(主潮)→非自然主义(余裕派、白桦派、唯美派)→普罗文学·新感觉派→侵华文学
中国:政治小说→鸳鸯蝴蝶派·写实主义→浪漫主义→左翼现实主义(主潮)→非左翼文学(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等)→普罗文学·新感觉派→抗战文学
显然,中日两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与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发展进程并不相同。众所周知,欧洲近现代文学的发展演变大体经历了如下的路径:14、15世纪文艺复兴→16、17世纪的古典主义→18世纪的启蒙主义→19世纪前30年的浪漫主义→19世纪中后期的现实主义→20世纪初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平行发展。可见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并不像有人所说的,是欧洲五百年间的文学历程的重演。尽管这些文学思潮大都根源于欧洲,但它们发展演变的“程序”和路径并没有仿效欧洲,而是大体仿效了日本。这种仿效具有双重的必然性:一方面,如上所述,日本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时空差距不大,便于双方的交流影响;另一方面,中日两国共处于东亚文化圈,具有某些基本相同或相似的文化文学背景和相同相似的内外文学环境,因而也就决定了文学现代化发展历程的相同与相似。不过,我们也应看到,在这大致相同的发展进程中,也有一些不尽一致的地方。这首先表现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演进的时速要比日本快,几种规模较大的文学思潮和运动的更叠嬗变所用的时间都比日本短。如日本的启蒙主义文学从明治维新到1895年坪内逍遥《小说神髓》的发表,大约持续了20多年,而中国近代的启蒙主义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不过10来年的时间;和欧洲比较起来,浪漫主义运动在中日两国存在的时间都不长,以北村透谷为中心的《文学界》派和随后的以与谢野宽、与谢野晶子为代表的明星派所支撑的日本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从1893年《文学界》创刊到1908年《明星》终刊,先后也就十几年,而中国的浪漫主义从1921年创造社成立到1925年创造社的转向,持续了不过五六年;自然主义在日本兴盛了十几年,其影响几十年不衰,而它在中国“五四”时期只作为写实主义的补充而提倡了三四年。这些文学运动和思潮在欧洲都存在过几十年、半个世纪,甚至一两个世纪。日本把他们的时值大大压缩了,中国又在日本之后再加压缩,因此,许多东西就显得步履匆匆,甚至一掠而过。尤其在“五四”时代的短短的五六年时间里,各种思潮一齐出现,流派纷呈,欧洲和日本文学中的许多历时性的东西,如写实主义、唯美主义与象征主义(新浪漫主义)等,全都共时性地登台亮相。这就造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既不同于欧洲,也不同于日本的独特现象:由于历时的变成了共时的,而且时值相当短促,许多来自欧洲和日本的思潮流派仅仅限于理论的提倡,并没有拿出创作来。以“五四”时期而论,从理论提倡上看似乎什么都有,但创作上却比较单调。中国现代文学在发展进程中出现的这种理论先行或理论独行的状况,在欧洲几乎没有,日本也不突出。欧洲的文学理论是在创作实践中逐渐总结出来的,中国现代的文学理论则是从欧洲文学和日本文学中比较容易地借鉴来的。理论的相对“繁荣”和创作上的相对贫弱的矛盾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进程中的基本矛盾之一。
二
当我们透过中日现代文学发展进程的相同和相似,进一步探究两国文学现代化的内在动力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日本文学对中国的影响不是绝对的,而是有一定条件、有一定阈限的。诚然,现代社会政治都是中日文学现代化的内部推动力。在日本,现代文学的启动直接得助于明治维新,在中国则直接得助于或者说从属于晚清的维新改良,起点都是社会政治。但是,我们也看到,日本现代文学是在明治维新中一次性孕育而成的,政治为文学铺设了现代化的轨道,并且使劲地将文学向前推动了一把,文学起步了,然后文学和政治两者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了;而在中国,文学现代化受到了社会政治的两次推动:第一次是维新改良,第二次是“五四”运动。而真正把文学推向现代化轨道的,则是“五四”运动。然而,政治对文学给予两次推动之后,并没有离文学而去,而是如影随形。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每一次思潮起伏,每一次创作变化,每一回理论论争,都和政治运动、政治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和日本现代文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文学思潮运动的发展嬗变而论,同样是“政治小说”,日本的“政治小说”主要是政治家消闲时的“余技”,中国的“政治小说”则是维新革命的直接舆论工具;同样是写实主义文学,日本的写实主义明确反对文学的功利性,中国的写实主义则力主文学“为人生”的反封建启蒙的功用;同样是浪漫主义,日本的浪漫主义主要是个人逃避社会的情绪独白,中国的浪漫主义则是对时代变革的热烈呼唤。这此都决定了中日两国在相似的发展路径中形成各自不同的文学主潮——自然主义和左翼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主潮决定了日本现代文学对社会政治的超越,左翼现实主义文学主潮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对社会政治的依附。而且,在日本,反自然主义和非自然主义的文学团体流派,如白桦派的理想主义、唯美派等,并不是反对自然主义的超政治性,而是更强化了文学远离社会政治的纯审美倾向。在中国,反对左翼现实主义阵营的文学团体,如新月派等,虽以自由主义的面目出现,但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中,实质上却不过是以一种政治倾向性反对另一种政治倾向性罢了。在这样的中日现代文学的构成格局中,我们会清晰地发现自由主义文学在各自文学格局中的不同地位。如果我们把力图超越社会政治,个人主义至尊、艺术趣味至上作为自由主义文学或文学家的主要特征的话,那就会看出中日两国现代文坛的自由主义势力的强弱悬殊。日本现代文学的绝大多数作家都属于自由主义的作家,他们以相近的趣味爱好结成同仁社团,而不是以政治倾向性分派立宗。除无产阶级作家之外,其他作家参加党派和政治团体的几乎没有。日本文坛上公认的文坛领袖——森鸥外、夏目漱石,就是自由主义文坛的领袖。森鸥外虽然身为高官,尚能在创作中完全回避政治,标榜文学的非功利的“游戏”性;漱石则把“余裕”和“则天去私”作为自己的创作信条。当个人与社会、艺术与政治处于尖锐冲突的时候,日本作家宁愿以自杀来解决和超脱这种矛盾。如日本最早自杀的浪漫主义文学首领北村透谷、白桦派的主要作家有岛武郎,新理智派的代表作家芥川龙之介等都是这样做的。相反,在中国,现代文坛上的自由主义势力比较单薄且并不那么“自由”。胡适被许多研究者视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首领,但这只是相对而言的。胡适对杜威实用主义的崇拜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排斥,表明他并不是真正的文学自由主义者。30年代的所谓“自由人”也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其中主要人物不过是左翼文坛内部的持不同艺术观点者罢了。“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的许多人和所谓“京派作家”,如梁实秋、徐志摩、沈从文、朱光潜、废名、李健吾等,基本上是文学自由主义者,但他们并没有构成文坛的主流。长期以来中国的各种文学史著作均把他们作为主流文学的对立面来看待和处理的。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学史观的一种必然体现,同时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自由主义作家在文坛上的配角地位。
政治色彩的浓厚和淡薄、自由主义作家阵营的薄弱与强大,使中日两国现代文学发展形成了两种主要的驱动力。从主流上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演进从属于中国现代政治的发展演进:维新改良,“五四”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既是中国革命史的主线,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主线。不管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法采用什么样的体例和体系,这样的事实都是不可抹杀的。而日本的现代文学的发展演进则基本上取决于文学内部的矛盾运动。和中国相反,日本写实主义的产生是对前此“政治小说”的政治化的一种矫正而不是继承;浪漫主义的出现又矫正了写实主义的“客观”性,是对主体和个性的张扬;自然主义的出现则是对浪漫主义主观性泛滥的一种反拨,同时又不自觉地继承了浪漫主义的个人性和感伤色彩;反自然主义的余裕派、白桦派、唯美派则是以“理想主义”对抗自然主义的“没理想”,以人道主义的“善”对抗自然主义的宿命论的“恶”,以审美的“余裕”对抗自然主义的“紧张”,以“唯美”的追求对抗自然主义的“丑”;“新现实主义”则既不赞成自然主义的片面求“真”,也不同意白桦派的刻意求“善”,同时又不赞同唯美派的一螙耽美,而是力图把真、善、美统一起来,理智而又深刻地剖析现实。以后无产阶级文学的勃兴是对整个日本现代文学超政治性的反抗,但很快就有“新感觉派”、“新兴艺术派”登场,指责无产阶级文学“践踏了艺术的花园”。可见,至少在30年代日本法西斯主义肆虐之前的半个多世纪里,日本现代文学是按照自己特有的轨道和路线,按照文学艺术内在矛盾运动的机制发展和运行着的。文学思潮、文学团体流派的相互制约、相互消长,不同作家作品的竞争与互补,是日本现代文学发展的主要的动力。另一方面,在日本文学史上,当政治对文学干预最严重的时候,文学便面临窒息乃至死亡。15年侵略战争时期,是日本政治干预文学最严重的时期,文学也因此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和浩劫。而在中国,政治却是文学的一种外部推动力。正确的、进步的政治影响、甚至政治介入,基本上没有妨害,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文学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的几次高潮都和中国政治的高潮相一致,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杰作,也大都以政治为背景或以政治为主题。众所周知,没有“五四”运动的风雷激荡,就没有《女神》;没有辛亥革命,就不会有《阿Q正传》;没有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讨论,就没有《子夜》;没有时代与政治风云的变幻与召唤,就没有《激流三部曲》和《爱情三部曲》;没有“皖南事变”的刺激,就没有《屈原》;没有土地改革运动,就没有《桑乾河上》和《暴风骤雨》;没有民族屈辱和国破家亡的痛苦经验,就没有《四世同堂》……。
三
这种耐人寻味的差异,是由多种复杂的因素造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两国现代作家的基本立场的不同。我们知道,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日本现代的社会制度、政治结构是由政治家来确立的。正如夏目漱石所说:“在现代的日本,政治就完全是政治,思想就完全是思想。两者处于同一个社会里,却又是各管各而孤立的,相互间没有任何理解和往来的。”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文学家就被推到了一种政治“局外人”的位置上。他们面对由政治家业已设计完成的社会制度结构,只能采取两种立场:一是视而不见的超然,一是站在外围上进行批评。这两种态度虽然不同,但和现实政治都不亲和。这两种态度也就形成了两种文学:一种是超越时代、超越社会的纯个人、纯审美的文学;一种是所谓“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文学。首先是超社会和超时代的文学。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和时代而又要超越它,这在中国作家看来简直是自欺欺人的幻想。鲁迅曾针对这种幻想尖锐地指出,作家企图超越时代,那就像拔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这个地球一样,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日本现代作家有这种企图或做这种努力的却大有人在。除德富芦花、岛崎藤村等作家的个别作品外,日本现代文学作品中有意识地描写和反映时代风云变换的作品很少,一般都局限于封闭的个人生活,且着意地营造超时代的氛围,构筑虚幻的美的世界。在这个问题上,著名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和川端康成的看法颇有代表性。武者小路实笃说:“文艺不可能和人生无关,可是,和社会的关系不一定是必要的。不,根本没有必要。”川端康成也认为,描写时代现实的作品,“其生命保持不了三五十年”,只有超时代的永恒的题材才能有永久的艺术生命力。日本的绝大多数批评家们都以这种价值观念衡量和评价作品。在中国,类似的作品不是没有(如沈从文、废名的有些小说),但是为数不多,况且它们并没有真正的超越社会和时代,这样的作品也没能构成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而更多的是那些紧贴现实、紧追时代的作品。每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社会运动,总是伴随着出现一批直接反映这些事件和运动、或与之相关的作品,即使是历史题材的作品,也都充满着强烈的现实时代色彩,以至后来的历史学家们可以根据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所提供的资料,来研究当时中国的社会思潮、政治党派、战争军事乃至经济状况等等。但历史学家却不能指望从日本现代文学中获得这样的材料。中国现代文学所提供的首先是时代和社会的反映和记录,日本现代文学所提供的主要是超时代、或时代特征暧昧不明的作家的心路历程。
至于日本作家提出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鲁迅也曾借鉴过来并在中国提倡过。但鲁迅所提倡的与日本原有的含义根本不同。鲁迅的“文明批评”是他反封建文学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鲁迅那里,“文明批评”,实质上就是反封建。而日本的“文明批评”所批评的是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社会批评”所批评的是日本业已形成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现象。无论是“文明批评”还是“社会批评”,日本作家不是站在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立场上来批评,而是站在落后的封建主义立足点上来批评的。明治时代的大作家德富芦花不满于明治政府及其社会政治,在小说《黑潮》里,他让一个退隐了的旧幕臣站在幕府时代的封建立场上对欧化的明治政府及政治家大加挞伐;夏目漱石在作品《草枕》中,缅怀陶渊明所虚构的世外桃源,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表现出一种厌恶,甚至对现代文明重要标志的火车极尽挖苦和嘲弄。芥川龙之介在《开化的良人》中对现代的自由恋爱采取否定态度,在《河童》中,则采用寓言手法全面否定了资本主义。从社会学角度看,日本的大多数作家的社会政治态度都是朝后看的、保守的,有时甚至是反动的。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应该“批评”,问题在于用什么价值标准来“批评”。不用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社会价值标准批评,就是用资本主义之前的封建的标准来批评,二者必居其一,日本作家更多地选择了后者。除了明治初年社会上全盘西化的思潮盛行一时外,更多的时候,更多的人却对失去的传统——包括封建的传统——怀有依恋之情,并常常把传统加以理想化来对抗或超越现实。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判定反封建和反资本主义哪一个更“进步”,我们只能说,时代和各自的社会状况给中日两国作家规定了不同的使命和任务。对于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作家来说,首要任务是反封建。至于反资本主义则不是对内而是对外的,它集中地表现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确立,资本主义的弊端已经暴露的日本现代社会中的作家们来说,对资本主义的反省和批评是自然的和必然的。不过,日本作家的“反资本主义”还没有达到从根本上否定、并试图以更先进的社会制度取而代之的高度和深度。所谓“文明批评”,大都止于讽刺嘲骂,发泄不满,常常显得无力而又肤浅。
换一个角度说,中日两国现代作家的立场的不同还表现为个人——社会两种基本立场,或者说两种基本的文学价值观的差异。个人,或者说个性,是日本现代文学的基本内核。这个内核像核裂变一样不断由内到外地产生能量,推动着文学的发展。因此,个性意识、个性解放,甚至个人主义是日本现代文学所探究、所表现的中心课题。日本现代文学的奠基作《浮云》与其说是一部批评社会的作品,不如说是一部以表现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并把个人价值置于社会价值之上的作品,从而为日本现代文学确立了“个人性”的基调。在日本文学中,个人的遭际、个人的体验、个人心理的刻画、个人的喜怒哀乐虽与社会有关,但作家们并不着意把个人放在社会的大视景中去表现,而是尽可能孤立,尽可能纯粹地描写个人,表现个性,以至在小说创作中形成了最典型、最流行的个性化文体——“私小说”,又在“私小说”的基础上形成了所谓“纯文学”,即剔除社会性的文学。在日本文坛看来,文学中加上了社会的政治的东西,就妨碍了文学的“纯粹”,所以,“纯文学”的价值观一直是日本现代文学最核心的文学价值观。在中国,“五四”时期是重个人、重个性的个性解放的时代,而“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又是与社会解放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现代作家很少张扬纯粹的个人或纯粹的“个性”。例如,周作人受日本白桦派人道主义文学的影响而提出的“人的文学”的主张,其宗旨是提倡“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个人与社会相调和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与白桦派作家有岛武郎在《爱不惜抢夺》中宣称的那种恣意对抗社会,按照本能一意孤行的个人主义是不相同的。众所周知,像郁达夫的《沉沦》在格调上受到了日本文学的深刻影响,但作品中个性觉醒的悲哀却与国家民族的悲哀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但透过那个人主义的色彩,就会清楚地看到“五四”文学的反封建的动机。三四十年代民族危机时期,个人主义、个性解放的要求逐渐转换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时代要求。个人的价值、个性解放的要求和冲动对现代文学发展的驱动力更进一步减弱了。
在考察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外国文学中,日本现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最为直接和密切。日本现代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处在一个有趣的矛盾统一体当中。一方面,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是触目显眼的,另一方面这种影响又多是外在的、局部的、而不是深刻的和本质的。日本现代文学的影响多表现在新思潮的发动,新理论的启示,新概念、新名词的引进,新文体、新手法的借鉴,作家与作品的交流与翻译等方面。然而,日本文学中的许多独特的民族性的东西,如作家的超越姿态,近乎神经质的细腻的感觉和感受,弥漫在作品中的无所不在的哀愁,主题的暧昧性,叙事的非逻辑性和结构的零散化,以阴柔的女性化为主格调的审美风格,等等,都没有影响、或很少影响到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影响。毋宁说,在更多的更本质的方面,中国现代文学与欧美文学更为接近一些。直到现在,我们阅读欧美文学作品时,都能直觉地感受到它们与中国文学在思想意蕴、思维方式、谋篇布局、审美趣味等方面的许多一致和契合。而我们面对日本文学作品时却常常产生一种新异感,或是一种不能理解、不可思议或难于共鸣的困惑和阻隔。这种情形,既反映了日本文学的特殊的民族性,也反映了中国人内在的阅读定势、期待视野和欣赏心理。因此,对日本文学的隔膜和对其影响的超越,正好从其反面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学的某些内在的、基本的特征,这些特征又恰与日本现代文学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说,日本现代文学的主流是超政治、超时代的,那么,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则是政治的、时代的;如果说,日本现代文学的主流是反资本主义的,那么,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则是反封建的;如果说日本现代文学的主流是个人的、个性的,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则是社会性的、集体性的;如果说,日本现代文学偏于感受性,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则偏于理性。同样是东方国家,而且又是有着如此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的中日两国,在文学上存在这种深刻差异是耐人寻味的。而这又恰恰给中日现代文学比较研究提出了富于现实意义、学术价值且又饶有趣味的课题。
标签:文学论文; 浪漫主义论文; 自然主义论文; 现代文学论文; 日本作家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艺术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中日文化论文; 日本文学论文; 作家论文; 个性论文; 自由主义论文; 写实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