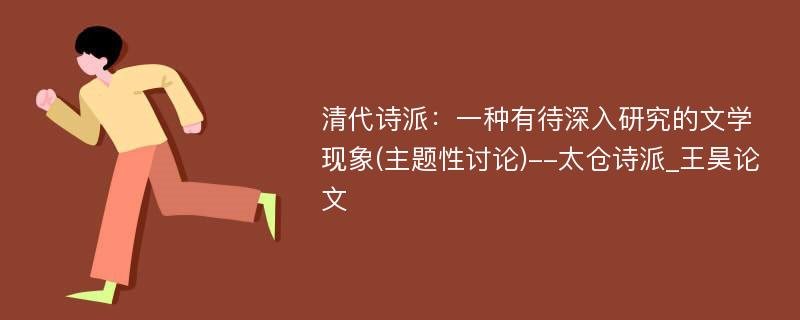
清诗流派: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文学现象(专题讨论)——论“太仓诗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仓论文,专题讨论论文,流派论文,现象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0)03-0094-14
[主持人语]清代二百六十多年间曾经出现了众多风格各异的诗歌流派以及并称群体,其数量之众,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这实在是一个引人注目并且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近十几年来,虽有一些学人着手研究这一文学现象,发表了一批论著,刘世南的《清诗流派史》堪称其中的力作。然而,关于这一文学现象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拓展与创新。为此,我受《河北学刊》主编的委托,特组织了这次“清代诗歌流派”(包括并称群体)专题研究笔谈,我们认为,太仓诗派是清代初年的一个地域性诗派,它的形成既同那一时代诗歌的解放与活跃、文人社团的普遍兴起相关,也同吴梅村有意识的标举与引领相关。清初神韵诗派领袖王士祯所定“长安十子”,其名称多达十二个以上,在这方面堪称典型。对这些名称进行梳理,可以发现不少微妙的问题,有助于学术研究的深化。清代性灵派实际是狭义的江南诗派,其成员的籍贯基本属于苏南与杭嘉湖地区。而性灵派之所以在江南出现,除了乾嘉时期整体的经济文化背景,以及袁枚的个人作用之外,江南特有的自然与人文地域环境也是重要因素。清代最有影响的地域性文学流派——桐城派中的一些作家也从事诗歌创作,就此形成了一个诗歌流派。桐城诗派的主要特点在于将唐宋诗歌的特长加以融合,从而产生出一种令人似曾相识又耳目一新的诗歌类型,它在整合前代传统方面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诗派。希望这组专题讨论文章能够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通过学术争鸣和互相切磋,将这一研究引向深入。
江苏太仓旧称娄东,故“太仓诗派”又称“娄东诗派”。它是兴起于清朝初年的一个纯粹的地域性诗歌流派,其领袖人物为吴梅村,重要成员有周肇、王揆、许旭、黄与坚、王撰、王昊、王抃、王曜升、顾湄、王摅等十人。因这十个人,“生同时,产同地”[1][(程邑《太仓十子诗序》)],故其“(诗歌)风格如出一手”[2][(卷194)],时人号之为“太仓十子”,或“娄东十子”。比他们更年轻一些的毛师柱、沈受宏等人也属于这一诗派。
作为地域性诗歌流派,“太仓诗派”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差不多同时,一批类似的地域性诗派如松江的“云间诗派”、常熟的“虞山诗派”、杭州的“西泠十子”、河北的“河朔诗派”、广东的“粤东诗派”等等如众卉破土一般竞秀争妍,含香吐艳,构成了明末清初诗坛一道绚丽多彩的风景。这实在是一个引人注目并且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
此前的中国历史上亦曾出现过不少地域性诗歌流派,如宋代的“永嘉四灵”、明代初期的“闽中诗派”即为世人所熟知,明代中期的“青溪诗社”、“粤山诗社”也属于此类。但是,以往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明末清初这样一下子涌现出如此之多的地域性诗派。显然,这种文学现象的发生绝非偶然,而是存在着某种必然性,存在着使之发生的某些历史条件和客观因素。
这首先让人联想到那一时期诗歌创作的解放与活跃。明代诗坛,长期被“前后七子”所鼓倡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说捆缚着,变得沉闷不堪。七子末流更是以拟古为复古,一味“模拟剽贼”,剪彩为花,拼凑成诗,制造毫无性情可言的假古董,完全失掉了个性与创造力。从明嘉靖至万历,一批对现状强烈不满的思想新锐在李贽、袁宏道的率领下首先从理论上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和弥漫诗坛的拟古之风大张挞伐,摧陷廓清。他们离经叛道的思想、尖锐泼辣的批判,振聋发聩,让人耳目一新。然而,从创作实绩上看,那种令人窒息的局面直到明末清初才真正起了变化。这一时期,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空前尖锐、社会极度的动荡不宁使得诗人在书斋中浅吟低唱、沉醉于格调声律词语的写作状态和“募缘残溺,盗窃遗屎”[3](《论文》)的作诗方法显得荒唐滑稽。中国诗歌终于开始挣脱清规戒律的束缚,走向广阔的天地。“盛唐”的框框被打破,越来越多的诗人出于反映社会现实和抒写性情的需要不拘一格,多方取法,诗坛变得空前活跃起来,名家、佳作络绎而出,形成自元朝以降古体诗歌发展长链上最为耀眼的一环。众多的风格各异的地域性诗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如果没有诗歌创作的解放与活跃,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
这种文学现象的发生同那一时期文人结社之风的关系就更为直接。自明天启、崇祯起,文人结社成为时尚,大大小小的文社星罗棋布于全国各地。初始的文社都是地域性的,其中声名较著者有松江的几社、杭州的读书社、粤东的西园诗社,等等。影响巨大的复社开始也是局限于一乡一地,后来联合其他文社,才成为几乎覆盖全国的庞大组织。同乡同里的文人有了文社,交流形成制度,来往更为频繁。读经学史、研习时艺文之余,也每喜吟诗作赋。在彼此题赠唱酬和探讨切磋中,不仅促进了写作水平的共同提高,而且很容易形成理论观点和创作取向的一致,容易形成近似的创作风格。倘若成绩不俗,即使他们不自我标榜,也往往被好事者冠以某某诗派之名了。可以说,遍布各地的文社成了地域性诗派产生的培养基与催化剂。
以上说的只是地域性诗派涌现的客观原因,带有共同性、普遍性。至于说到各个诗派,则又各有其形成的特殊因素了。
“太仓诗派”的形成,是与吴梅村的培植、提携和宣传分不开的。他就像一位园丁,滋兰种蕙,悉心垦植出了“太仓诗派”这块园地。
“太仓十子”都和吴梅村有着亲密的关系。其中,年龄最长的周肇比伟业小六岁,是吴梅村的莫逆之交。其余诸人,都比吴梅村小十岁以上,最小的王摅比吴梅村小二十六岁,均为吴梅村晚辈,他们有的父辈与吴梅村交好,本人属吴梅村世侄;有的登堂入室,做过吴梅村弟子。吴梅村对他们以及毛师柱、沈受宏等人始终不遗余力地予以关心、指点、提携和奖掖,例如他曾招周肇、黄与坚来自己的书斋“旧学庵”读书,“相与古学为砥砺”[4](卷23,《姚襄周西墅诗草序》);他曾为王昊延誉,盛赞王昊为“绝才”[4](卷38,《内阁中书舍人王君墓志铭》);他曾写信给王士祯,热情引荐许旭[5](卷3);写信给冒襄,极口称道毛师柱[6](补遗);他曾向沈受宏传授“作诗之要”[7](卷12),等等。至于他召聚他们一起登临赋诗、饮宴联句就更是常事。更为重要的是,他亲手选编了《太仓十子诗选》,并作序加以揄扬。此书刊于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十子”之称和“娄东诗派”从此得以确立,并很快名扬天下,为世人所认可。完全可以说,没有吴梅村,便没有“娄东诗派”。
吴梅村《太仓十子诗序》云:“‘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士君子居其地,读其书,未有不原本前贤以为损益者也。”[1]对于十子等人来说,吴梅村虽然只能说是“时贤”,算不得“前贤”,但他们实际上是把吴梅村当作效法的榜样来看待的,奉他的论诗主张为圭臬,把他的诗当成了诗歌创作“损益”的标准。正如汪学金《娄东诗派·例略》所言:“十子胚胎梅村。”[8]或如沈德潜《清诗别裁集》所说:“娄东诗人虽各自成家,大约宗仰梅村祭酒。”[9](卷23)这一点,从他们现存作品中可清楚地反映出来。
太仓诗人中有专集流传下来者并不多,多数诗人留存至今的仅为见于《太仓十子诗选》中的作品,人各一卷,最多的不过一百零一首诗,少的只有七十几首,而且绝大多数为律绝,很少古体。不过,窥一斑而知全豹,由远非全部创作的这些作品,还是可以看出十子等人的诗风与吴梅村是多么相似。
这种相似首先显示在艺术表现与艺术宗尚上。
从语言上说,十子等人普遍追求的是遣词用语的高华秀雅、妥帖精切。在他们笔下,很少见到俚语俗字,也很少见到冷僻尖新的词汇,他们不以语言的通俗易懂或者奇崛险怪取胜。
从声律上说,十子等人讲究的是和谐圆润、整饬匀称,所作近体诗,无论平仄还是对偶,无不合规中矩,严守绳墨,极少拗句,极少出律现象,几乎每一首都打磨得字调句谐,玉润珠圆。即使是自由度很大的古体诗,也写得流利顺畅,难以找到那种散文化的佶屈聱牙的句式,难以听到那种拗折奇峭的音调。
从抒情手段和整体意境上说,十子等人注重的是意象和风神。他们不喜欢“以议论入诗”,力戒诗旨的浅白直露,避免张狂嚣叫、一泄无余,而是主要靠意象来表情达意,做到唱叹有情,含蓄有味,耐人咀嚼。即使满腔愤怒哀怨,表达起来却尤为注意节制,不违温柔敦厚的诗教。故其诗显然更接近以丰神情韵见长的唐诗。
尽管十子等人与吴梅村在艺术造诣上有高下之别,但由以上诸方面来看,他们在艺术追求上却是一致的,简直没有什么不同。
其次,这种相似还显示在题材内容与意绪情调上。
像吴梅村一样,追怀先朝,抒写遗民之恨,是十子等人反复吟咏的一个主题。“丁卯桥成诗万首,甲申龙去泪三年”(周肇《人日寄许九日》);“瓦砾不堪寻故迹,愁听父老话承平”(王揆《临清阻泊》);“故国垒空云淡淡,夕阳人去草萧萧”(许旭《燕子矶》);“凭君莫问当年事,禾黍同归六代愁”(顾湄《阅江楼》);“白发几人怀故苑,青山何地葬遗民”(毛师柱《追感杜茶村先生》)……类似的诗句在他们笔下不断出现。吴梅村曾经以南京故迹为题写下许多首表达故国之思的诗。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十子等人差不多也都写过以“金陵”为题的诗歌,如周肇有《金陵忆昔》、《南京歌四首》,顾湄有《金陵感兴》,王昊有《金陵》诗,黄与坚有《金陵杂感》,等等。这当非巧合,也恐非相约而作,但受到吴梅村诗作的启示却是极有可能的。金陵既是大明朝“龙兴之地”,又是弘光朝覆亡之都,它成了一代兴亡的见证与象征,因而也就成了抒发兴亡之感最恰当的喷发点。吴梅村抒写于前,十子等人弄笔于后,造成了这种几乎是多诗同题的现象。
像吴梅村一样,反映乱离、揭露新朝虐政也是十子等人诗歌的主要内容之一。王抃的《送友还蜀中》透露出历经战乱之后“城市人民尽非昨”的景况;许旭的《赠余不远》、黄与坚的《沂州客店遇同乡友人》、王昊的《久客》、沈受宏的《衢州书事》等诗写到长期战争、遍地烽火弄得“江郭萧条”、“闾井蓬蒿”、亲友死生不保的现状和人民“厌甲兵”的心情;王昊的《兵船行》反映出清廷强迫修造战船给百姓带来的苦难;王撰的《中秋山塘曲》抨击了清朝“催科大吏”当发生严重水灾、“十家五家相向哭”的时候却连宵开宴、欢赏歌舞的劣行;黄与坚的《过蒙阴》描绘了苛税重赋和官吏的勒索“敲扑”所造成的“死亡填路途”的惨景;王摅的《喜吴弘人闻夏南还》、王昊的《惊闻二首》揭露了清廷对汉族士人的迫害……类似的感时伤世之作,俯拾皆是。
在十子等人的作品中,确实很少有风花雪月之咏、浅斟低唱之篇,即使是题赠唱酬、登临行旅之作也往往浸染上风云之气,即使是自伤自世之作也往往因为个人命运与时代命运的交融而显得内容深厚。可以说,感慨一代兴亡,反映社会现实成为十子等人诗歌题材取向上的共同特征,悲愤怨悒,沉郁苍凉,成为其作品情感意绪的共同基调。这些方面,和吴梅村也是十分接近的。
不过,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十子等人在题材内容与意绪情调上的这些特点除了与吴梅村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实际上也是时代使然,人个命运使然。
我们知道,当清兵下江南、攻灭弘光朝、取得对大半中国统治权的时候,十子中最小的顾湄和王摅也已经十几岁了,其余诸子,多数年龄在二十以上。他们耳闻目睹了清兵屠杀、凌辱江南人民的暴行,亲身感受了清朝官员对百姓残酷的压榨。改朝换代带给他们的印象和痛苦是相当深刻的。并且由于家世的原因,其精神上的痛苦远比一般人来得更强烈。
十子中的六位王姓均有着显赫的家世。其中,王揆、王撰、王抃和王摅的曾祖王锡爵曾为明万历朝大学士,祖父王衡、父亲王时敏也均在明朝做过官,王昊和王曜升的高祖王忬曾为明嘉靖朝右都御史,曾祖王世懋做过万历朝太常寺少卿,他们可算得累世簪缨的望族。许旭的祖父许国荣曾官工科给事中;顾湄的亲父程新曾官惠安县令,养父顾梦麟则为明末名士;周肇、黄与坚均出身富家。随着明朝覆亡,异族入主,他们昔日的特权即刻受到严重削弱,政治上已失去保障,经济上也遭到侵夺。清初的苛税重赋,概不得免,甚至家道越殷实,门第越高贵,越成为贪官污吏敲诈勒索的对象。吴梅村《和王太常(王时敏)西田杂兴》云:“乱后归来桑柘稀,牵船补屋就柴扉。”《芦州行》:“胥吏交关横派征,差官恐喝难供应。”就反映了这种状况。
十子的政治前途也变得黯淡。他们中除了周肇在清康熙十年(1671年)五十七岁时才被授以青浦县教谕这样一个小官之外,没有一个人在康熙十八年(1679年)以前做过官。有的一生落拓不偶,有的还横遭政治迫害。例如,顺治十七、十八年(1660-1661年)“嘉定钱粮案”和“奏销案”中,黄与坚、王昊、王曜升、顾湄均无端受到牵连,被革除功名。王昊甚至锒铛入狱,“械送北上”,受尽凌辱。黄与坚为周肇所作《墓志铭》对其鼎革后的精神状态作了传神的描绘,说他“其后十五年不一遇,肮脏之气,日以纠结,不得已而逃于酒,每饮必欢呼竟夕,或沾醉而后起,大痛哭,坐客不知其为何也。迹其生平,未尝一日得少展,而抑郁以病死”[4](卷38,《新淦县知县周君子俶墓志铭》)。乾隆《镇洋县志》卷十二《王曜升传》写王曜升被“钱粮案”牵连之后“悒悒不自得,东西南北,惟意所之,遇酒辄醉,或歌或哭,用以消其块垒”。周肇和王曜升的精神状态很有代表性,由上述描写便可以探知十子的内心精神世界。
比十子稍微年轻一些的毛师柱、沈受宏等人的身世遭际与精神状态和十子有许多相近之处。
总之,改朝换代给十子等人带来的是家族与身世的不幸,鼎革之变让他们经历了大忧患,感受到大失落,体味到大悲凉。他们无力回天,唯有肝肠寸断,痛苦莫名。因此,在他们的作品里反复吐露亡国之痛,不断发泄对新朝、对现实的不满也就不足为奇了。
姚莹《识小录》对十子等人的诗风作了最为简明扼要的概括,这便是“皆以绵丽为工,悲壮为骨”[10](P132)。“以绵丽为工,悲壮为骨”,岂不正是吴梅村“容娇气壮”风格的翻版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十子“风格如出一手”,并认为这是“宗一先生之故”,是很有道理的。
在吴梅村的指授、带动之下,太仓诗人们的创作一时非常活跃,而且普遍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准。清代的一些重要的诗歌选本都有他们的诗入选,便是证明。环顾一下明清之际诗坛,当时的任何一个地域性诗派都没有显示像“太仓诗派”这样鲜明并且一致的风格特征,都没有拥有像太仓诗派这样多的作手。以吴梅村为领袖和旗帜的“太仓诗派”算得上是当时“宗唐派”中成绩比较突出的一个群体,它在明清之际的诗坛上占据了重要的一席。
但是,宗尚吴梅村一人,也带来弊端,就是使得太仓诗人的创作风格相对单调,限制了创作个性的张扬。吴梅村以外的太仓诗人中,只有王昊、王摅、沈受宏的诗歌稍具个性,其他人的创作个性都被共性冲淡了、淹没了,而个性不鲜明的创作绝不可能超群出众,达到一流水准。这就是说,当十子等人作为一个诗派、作为一个创作群体出现的时候,是引人注目的。而他们分散开来,作为一个个创作个性出现的时候,就大为逊色,容易被一般读者所忽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望吴梅村之项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