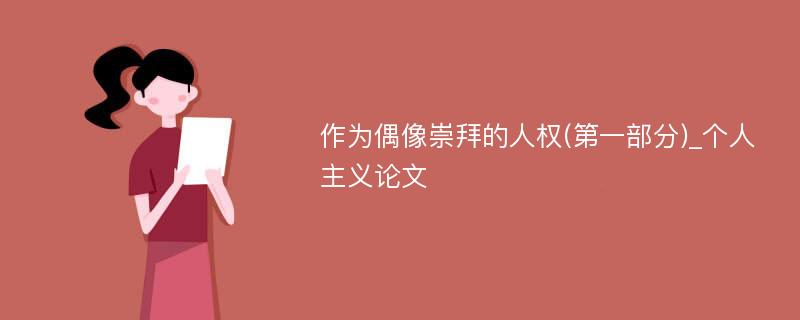
作为偶像崇拜的人权(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权论文,崇拜论文,偶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人权宣言》(以下简称《宣言》)在其被宣布五十年后成了一个神圣文本。埃利·维塞尔(Elie Wiesel)称之为“世界范围的世俗宗教”。(注: Elie Wiesel,“A Tribute to Human Rights,”in Y.Danieli et al.(eds.),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Fifty Years and Beyond, Amityville, N.Y.: Baywood, 1999,p.3.)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称之为“我们衡量人类进步的准绳”。葛迪美(N.L.N.Gordimer)把它描述为“真正总括了指引人类行为的所有其他教义的基本文献、试金石和人文纲领”。(注:Nadine Gordimer,“Reflections by Nobel Laureates,”in Y.Danieli et al.(eds.),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p.vii.)人权成了世俗文化的主要信条,这一文化除人权外恐怕别无信仰。人权成了全球道德思想的通用语,就像英语成了全球经济的通用语一样。
就此类冠冕堂皇的话,我要问的问题是:如果人权是一套信仰,那么,信仰它意味着什么?它是像宗教一样的信仰吗?它是像希望一样的信仰吗?或者,它完全是别的什么?
我将指出,把人权视为一种“世俗宗教”是对人权的一种误解。它不是一个信条,它也不是什么形而上学。使它成为信条或者形而上学就是把它变成一种偶像崇拜:崇拜它自己的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将道德和形而上学的主张提升为人权,可能是想增强其普遍的吸引力。而事实上,它有着相反的后果,它会遭到教徒和非西方群体的质疑,这些人并不需要西方的世俗信条。
把人权理念同如下主张联系起来可能是有诱惑力的:人类有一种天生的或自然的尊严;人类有一种自然的和固有的自尊;他们是神圣的。而这些主张的问题在于,它们并不明晰,而且也存在争议。它们不明晰是因为,它们把“我们希望男人和女人是什么”与“我们在经验上知道他们是什么”弄混淆了。男人和女人有时确实表现得很有尊严。但是,这与我们说全体人类都有一种天生的尊严或者甚至有一种展示它的能力并不是一回事。因为这些关于尊严、价值以及人的神圣性的理念看上去混淆了“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它们是有争议的,由此,它们很可能削弱而不是加强了人们对实现人权所必须承担的实际责任的承诺。它们是有争议的,还因为它们中的每一种理念都必定对人性提出各种在本质上有争议的形而上学的主张。一些人不难想到人是神圣的,因为他们刚好相信,存在着一个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人类的上帝。不信仰上帝的人则必定要么拒绝承认人类是神圣的,要么只基于宗教隐喻的世俗用法而相信人类是神圣的,而信教的人将发现这并不能令人信服。人们通常以讨论和妥协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争论,但这些不同的基本主张以及这些分歧并不能通过这些方式得到解决。我将指出,最好把所有这些各种各样的争论通通抛弃,在“人权实际上为人做了什么”的基础上寻求对人权的支持。
人们也许不能就“我们为什么有人权”这一问题达成一致,但是,人们会一致认为,我们需要人权。人权信仰的基础可能是有争论的,但对人权保护的信仰则可以找到更加可靠的审慎依据。我认为,现代人权所要求的这类依据的基础在于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如果人类缺少基本的自由,那么他们的生命将面临危险;行动自由本身要求通过国际上公认的标准加以保护;这些标准应该授权个人反对和抵制本国不公正的法律和命令;最后,在所有其他补救措施都已用尽后,个人有权利求诸其他的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帮助来捍卫他们的权利。欧洲20世纪的灾难史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些事实,而非欧洲的民族在原则上没有理由不从中得出同样的结论,有关大屠杀以及其他此类犯罪的记忆也没有理由不在以后的岁月里促使后代们支持人权规范的普遍实施。
对人权审慎的和历史的正当性辩护不必诉诸任何特殊的人性理念,也不应在特殊的人性善的理念中寻求其最终的有效性。人权说明什么是对的,而不说明什么是好的。充分享受人权保护的人们仍然可能认为他们缺少良善生活的本质特征。如果这样,共同的人权信仰应该可以与关于什么是良善生活的各种不同态度和谐共处。换言之,一种普遍的保护人权的政治制度应该可以同道德多元主义和谐共处。也就是说,虽然众多不同的文明、文化和宗教在什么才是良好的人类生活这一问题上彼此意见不同,但在它们中间维持保护人权的政治制度应该是可能的。表述这一思想的另外一种方式是,尽管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在什么是善的问题上可能继续争执下去,但他们仍然可以在“什么是不能忍受的、毫无异议的错误”这一问题上达致共识。只有在所包含的普遍主义自觉做到了最低限度时,人权所包含的普遍责任才能与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和谐共处。只有在作为一种关于“什么是对的”的坚定的“稀薄”理论(对一切生活共同的最低条件的根本界定)时,人权才能博得普遍的赞同。
即便如此,它仍有可能因为不够基本而得不到普遍赞同。一种恰当的人权政治意识必须接受:人权是一种战斗性的信条,它的普遍性要求将遭到抵制。人权主张挑战的任何一种权威,都不可能承认这种主张的正当性。人权主张必须偏向于受害者。检验其正当性、因而普遍性的标准应该是我们称之为“受害者的同意”这一标准。如果受害者自主诉诸人权保护,权利语言就适用了。我们也能听到实施压迫的那些人的有关他们是否实施了压迫的事实的辩解,但是,受害者的主张应该比压迫者的主张更加重要。尽管如此,受害者在界定什么构成虐待方面并不能享有无限制的权利。人权侵犯远不只是不方便,寻求人权补救也有别于寻求承认。它是为了保护人们意志力的实质性行使。因而,虽然受害人有关其权利受到侵犯的主张可以启动人权程序,但是受害人仍然有义务证明这种侵犯事实上的确发生了。
人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有助于人们帮助他们自己,保护他们的意志。我所说的意志能动作用是指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 )所说的“消极自由”——每个人不受强迫或阻碍而实现合理意图的能力。我所说的“合理”并不一定是指明智的或值得尊敬的,而只是指那些不会给他人带来明显损害的意图。人权是一种个人授权的语言,对个人授权是可欲的,因为,当个人有能动作用时,他们能够保护自己免受非正义的侵害。同样,当个人有能动作用时,他们能为自己确定他们希望为什么而活、为什么而死。在此意义上,强调能动作用就是授予个人权利,同时也是为人权主张自身设置限制。保护人类能动作用,必定要求我们保护所有个人选择他们认为合适的生活的权利。对此种个人主义通常有一种批评,认为它把一种西方的个人概念强加给了其他文化。我的观点恰恰相反:这种道德个人主义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因为个人主义者的立场必须尊重个人选择去过他们生活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循此思路,人权就是“消极自由”的系统清单、反对压迫的成套工具、个人能动作用——当他们在其所信奉的文化和宗教信仰更加广阔的框架内认为合适时——必须自由行使的成套工具。
为什么我们必须为人权的这种“最低限度”的正当性辩护呢?为什么我们必须找到一条用以协调人权普遍主义与文化、道德多元主义的路径呢?自1945年以来,人权语言已经成为权力和权威的一种来源。权力不可避免地引发挑战。现在,人权教义是如此富有力量,在其普遍性主张上具有如此不可思议的帝国主义性质,以致使自己遭受到严厉的智识攻击。这些挑战带来了一些重要问题:人权是否应该得到它已经获得的那种权威,其普遍性主张是否是正当的,它是否只是西方道德帝国主义所使用的另外一种狡计?
对人权普遍性的文化挑战有三种不同来源。其中两种源于西方之外:一种源于复兴的伊斯兰,另一种源于东亚;第三种源于西方自身内部。这三种来源彼此独立,但是,放在一起考虑,它们对人权的跨文化有效性、因而也对人权规范的正当性提出了实质性问题。
一 伊斯兰的挑战
伊斯兰的挑战从一开始就存在。(注:Katerina Dalacoura, Islam, Liberalism and Human Rights, London: I.B.Tauris, 1998; F. Halliday,“The Politics of Islamic Funda-mentalism”, in A.S.Ahmed and H.Donnan (eds.) Islam, Globalization and Post-Modernity, London: I.B.Tauris, 1994; A.A.An-Na'im (ed.) , Human Rights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1992, chap.I; see also Mehdi Amin Razavi and David Ambuel (eds.), Philosophy, Religion and the Question of Tolerance, New York: SUNY Press, 1997, chap.4.)1947年,当《宣言》正被起草时,沙特阿拉伯代表团就对关于婚姻自由选择的第16条以及关于宗教自由的第18条提出了特别的反对。在婚姻问题上,《宣言》草案的审查委员会的沙特代表提出了一种意见,从那时起,这一意见一直回响在伊斯兰与西方人权的遭遇战中:
在很大程度上,《宣言》的起草人只考虑了为西方文明所承认的标准,而忽视了更加古老的、已经走过试验阶段的文明和经历过许多个世纪被证明为明智的制度,例如婚姻制度。宣布一种文明比所有其他文明更优越,或者为世界上所有国家建立统一的标准,这对委员会来说是不适合的。(注:Glen Johnson and Janusz Symonides,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A History of Its Cre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1948—1998, Paris: UNESCO, 1998, pp.52—53.)
这同时也是对伊斯兰信仰和父权的一种辩护。沙特代表实际上争辩说,对妇女的交换和控制正是传统文化存在的理由,而对女性婚姻选择的限制则是维护父权财产关系的核心。基于对第16条和第18条的这些反对意见,沙特代表团拒绝批准《宣言》。
包括《伊斯兰人权宣言》在内,存在着通过更加强调家庭义务和宗教信仰,以及特别援引伊斯兰的宗教和伦理宽容传统,来协调伊斯兰和西方传统的反复尝试。(注:Paul Gordon Laure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Visions See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8, p.8.)但是,这些企图融合伊斯兰与西方的尝试从来没有完全成功过:各方的一致同意实际上牺牲了每一方的重要东西。最终的协议平淡无奇,也难以令人信服。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伊斯兰对人权的反应变得更加不友好。自从伊朗爆发反对国王专横的现代化的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斯兰重要人物也对这一西方人权规范的普遍性文件提出质疑。他们指出,西方的政教分离、世俗权威与宗教权威的分离,有悖于伊斯兰传统的法理学和政治思想。《宣言》中明文规定的自由在伊斯兰的神权政治理论中毫无意义。结婚和建立家庭的权利以及自主选择伴侣的权利,是对实施配偶的家庭选择、一夫多妻以及深闺制度的伊斯兰权威的直接挑战。在伊斯兰人的眼中,普遍化的权利话语暗含着一个拥有主权和独立的个体,从《古兰经》的视角看,这是对神明的亵渎。
作为对这种挑战的回应,西方错误地假定伊斯兰教与原教旨主义是同义的。伊斯兰用多种声音讲话,有些更加反西方,有些更加强调神权。在说明伊斯兰对西方价值的地区反应时,民族背景可能比宽泛的、作为整体的宗教神学原则更加重要。在努力进行现代化、产生中产阶级、进入全球经济的伊斯兰社会(如埃及和突尼斯),出现了基本人权的支持者。例如,埃及正在通过赋予妇女离婚权的立法,尽管与宗教权威的对话一直都很困难,但妇女的权利将通过新的立法而得到实质性的提高。(注:New York Times, March 3, 2000.)而在阿尔及利亚,世俗的人权文化则处于更大的困境。经过反殖民的流血革命后,登上权力宝座的世俗精英并没有能够使他们的国家现代化。它现在面临着一个由伊斯兰好战分子领导的、反西方和反人权的反对派。在阿富汗,国家本身已经崩溃,外邦军队的输送加速了国家的瓦解,兴起的塔利班运动则公开反对所有的西方人权标准。在所有这些场合,起到主要作用的并不是伊斯兰教本身——一种变化多端、多重特征的宗教——而是西方政策和经济全球化本身的变化过程。
对伊斯兰的挑战,西方也有另外一种同样考虑不周的回应。一种文化相对主义对伊斯兰的挑战作了过多的让步。过去20多年,西方政治主张中有一种颇具影响的思潮,用艾达曼梯亚·玻利斯(Adamantia Pollis )和彼得·施瓦布( Peter Schwab)的话讲,人权是一种“具有有限适用性的西方构造”,是20世纪的虚构,它有赖于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权利传统,因此对那些不分享这一自由的个人主义历史母体的文化并不适用。(注:A.Pollis and P.Schwab (eds.), Human Rights: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Perspectives, New York: Praeger, 1979, pp.1,4; see also Amitai Etzioni, “Cross-Cultural Judgments: The Next Steps”, Journal of Social Philosophy 28, No.3 (Winter 1997).)
这种思想潮流有复杂的知识源起:马克思主义者对人权的批评,对19世纪晚期狂妄自大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人类学批评,以及对欧洲启蒙思想普遍化要求的后现代批评。(注:关于马克思主义者对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人权的批判,见Tony Evans (ed.), Human Rights Fifty Years On: A Reappraisal,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8。)所有这些倾向都一起批评以人权语言表述的西方知识霸权。人权被视为是西方理性狡计的一种运用:西方理性再也不能通过直接的帝王规则统治世界,于是它用中立的、普遍化的人权语言把自己的权力意志掩盖起来,寻求将其狭隘的日程强加于世界上各种事实上并没有分享西方的个性、自我、意志或自由等概念的文化。这种后现代主义者的相对主义最初作为一种知识时髦肇端于西方的大学校园,但现在已逐渐渗入西方的人权实践,使得所有的人权活动家都停下来思考他们曾经想当然的那种普遍性的知识根据。
二 亚洲价值
这种内部的挑战被一种外部的挑战扩大了:在东亚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西方的人权标准受到了一些政治领袖的批评。如果说,伊斯兰对人权的挑战可以通过伊斯兰社会没有从全球经济那里受益这一事实中得到部分解释,那么,东亚的挑战则是地区经济巨大成功的结果。例如,鉴于马来西亚强健的增长率,其领导人很自信地拒绝西方的民主和个人主义权利理念,而支持依靠权威政府和权威家庭结构的东亚发展和繁荣道路。新加坡也是如此,它把政治权威主义和市场资本主义作了一种成功结合。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话说,亚洲人“从不怀疑一个强调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崇尚公有价值的社会,比美国的个人主义更加适合他们”。新加坡人模式的提倡者引用西方日益增长的离婚率和犯罪率来主张,西方的个人主义对为权利本身的享有所必需的秩序具有破坏性。(注:对新加坡人看法的尖锐批评,见Ian Buruma,“The King of Singapore, ”New York Review, June 10 , 1999.Lee Kuan Yew quo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ember 9—10, 1991。)“亚洲模式”把共同体和家庭置于个人权利之上,把秩序置于民主和个人自由之上。当然,现实中并不存在单一的亚洲模式:这些社会中的每一个都已经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政治传统中实现了现代化,它们都拥有不同程度的政治自由和市场自由。不过,声称自己代表了一种向西方模式的霸权提出挑战的文明,这对亚洲的权威主义者来说是很有用处的。(注:W.T.De Bary, Asian Values and Human Rights: A Confucian Communitarian Perspectiv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16.)
让我们同时承认,对人权话语普遍性的这三种分立的挑战——两种来自外部,一种来自西方传统内部——都有一种建设性的后果。它们迫使人权活动家质疑其假定,反思其活动的历史,并且认识到,当所有的文化平等参与进来时,有关权利问题的跨文化对话是何等的复杂。
三 人权与个人主义
说了这么多,我还是认为,西方人权的捍卫者们做出的让步太多了。在人权规范的西方捍卫者们试图寻找到与伊斯兰和东亚立场共同的基础,并肃清后现代主义者所揭露的其话语中的帝国主义残余时,他们损害了其本应捍卫的普遍性。而且,他们还冒着重写其自身历史的风险。
在《宣言》的起草中,许多不同的传统——不只西方传统,而且包括中国人的、中东基督徒的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印度的、拉美的、伊斯兰的传统——都得到了表述,而且,起草委员会的成员明确指出,他们的任务并不是简单地批准西方的信念,而是试图从他们非常不同的宗教、政治、种族和哲学背景中明确一种有限的普遍道德。(注:Johannes Morsink,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Origins, Drafting and Intent,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9.)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文件的序言没有提及上帝:共产主义国家的代表团会否决任何此类提及,各种竞争的宗教传统也不会就如何具体表述“人权源于我们共同作为上帝的创造物而存在”这一思想达成一致。因而,这一文件的世俗基础与其说是欧洲文化统治的象征,毋宁说是一个旨在使各种不同的文化和政治观点可能达成一致的、注重实效的共同标准。
当然,西方的思想以及西方的法律家们在文件的起草中仍然起了支配作用。即便如此,《宣言》起草者们在1947年绝没有必胜者的心态。他们知道,首先,殖民解放的时代即将到来:印度在《宣言》的语言最后敲定时宣告了独立。尽管《宣言》并没有特别认可自决,但它的起草者已经清楚地预见到即将到来的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的潮流。由于它宣告了人民的自治权和宗教、言论自由,它同时也就承认,殖民地人民有用一种扎根于其传统自身的语言解释其普遍道德原则的权利。无论《宣言》的起草者有多少败笔,未经审视的西方必胜信念不在其列。诸如法国的瑞内·卡森(René Cassin)和加拿大的约翰·汉弗莱(John Humphrey )等主要起草者就知道,持续了两个世纪的西方殖民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注:René Cassin,“Historique de la déclaration universelle en 1938”, in La Pensée et l'action, Paris: Editions Lalou, 1972, pp.103—118; J.P.Humphrey, Human Rights and the United Nations: A Great Adventure, Dobbs Ferry, N.Y.: Transnational, 1984,pp.46—47.)
同时,他们也知道,《宣言》与其说是对欧洲文明优越性的宣告,不如说是一种企图把启蒙遗产的残骸从刚刚结束的野蛮世界大战中抢救出来的尝试。《宣言》是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真相已经完全被揭露,而柯利马(Kolyma)劳改营的真相也逐渐为人们所知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对欧洲野蛮行为的觉悟已被嵌入到《宣言》序言的语言之中:“鉴于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
《宣言》仍然是启蒙的产儿,但它是在对启蒙的信仰面临最深刻的信仰危机时被起草的。在此意义上,人权与其说是对欧洲优越性的宣告,不如说是通过欧洲人对世界上其他人的一种警告,警告其不要重蹈欧洲人的覆辙。覆辙的重要方面在于对民族国家的偶像崇拜,这使得个人遗忘了要求他们不遵守非正义命令的更高的法律。起草者们相信,对自然法这种道德遗产的抛弃和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的屈服,导致了纳粹大灾难和斯大林的镇压。如果不把欧洲集体主义这种灾难性的遗产谨记心中,就像《宣言》起草过程中的设计经历那样,其个人主义就会看上去不过是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偏见的承认而已。事实上,它更是一种为了保护个人意志免受专制国家的侵害而重新使用欧洲自然法传统的精心尝试。
因此,《宣言》的核心仍然是道德个人主义,它也因此而备受非西方社会责难。就是这种个人主义使西方人权活动家备感歉疚,认为应该通过更加强调社会义务和对共同体的责任来对其加以调和。有人指出,只有软化其个人主义偏见,更加强调《宣言》的共同体方面,特别是第29条,即“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他的个性才可能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发展”,人权的普遍性诉求才能恢复。这种冲淡个人主义的权利话语的愿望,既受到了使人权更切合较少个人主义的文化这种愿望的驱使,也是对西方共同体主义者有关个人主义价值对西方社会凝聚力具有假想的腐蚀性影响这种焦虑的回应。(注:Michael Sandel, Democracy's Discontent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然而,这种策略在权利实际是什么这一问题上犯了错误,同时,它误解了为什么权利对成千上万生活在非西方传统中的人具有吸引力。权利,只有在它们对个人授权并赋予他们豁免权时才是有意义的;它们也只有在能够针对诸如家庭、国家和教会之类的制度得到强制实施时才是值得拥有的。这即使对集体的或群体的权利来说也是正确的。这些权利中,有些——诸如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践行自己的宗教的权利——是个人权利存在的基本前提。如果一种语言已经灭绝,用一种你所选择的语言讲话的权利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此,为保护个人权利,需要群体权利。不过,群体权利的最终目的和正当根据并不在于保护群体,而在于保护组成群体的个人。例如,群体的语言权利不得被用来阻止个人学习群体语言之外的一种语言。群体践行宗教的权利也不应取消个人自主选择离开一种宗教共同体的权利。(注:Michael Ignatieff, The Rights Revolution, Toronto: Anansi, 2000, chap.3; Will Kymlicka,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权利必然是政治的,因为它们暗含着权利持有人与权利阻碍者(权利持有人能够向其提出正当主张的某种权威)之间的冲突。混淆权利与期望、权利公约与世界价值的融合,就等于是幻想那些界定权利内容的冲突会自行消失。在个人与群体之间将总有冲突存在,权利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语言不能被解析或转变为一种非个人主义的、集体主义的架构。道德个人主义是其假定,在此假定之外,权利语言毫无意义。
而且,正是这种个人主义显现出其对非西方人的魅力,并且给出了为什么人权已经成为一种全球运动的理由。人权是这样一种唯一普遍可利用的道德语言,它使妇女和儿童反对其在父权和部落社会所遭受的压迫的主张得以生效;同时,人权也是这样一种唯一的语言,它使得不自主的人能够认识到他们自己具有道德意志,并且行动起来反对由他们的文化势力和权威所认可的各种实践——包办婚姻、深闺制度、剥夺公民权、残害女性生殖器官、家奴等等。这些行为人之所以想获得人权保护,正是因为人权使他们反抗压迫的抗议得以合法化。
如果的确如此,那么,我们需要反思一下,我们说权利是普遍的,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权利教义引发了强有力的反抗,因为它们对强大的宗教、家庭结构、独裁国家以及部族提出了挑战。试图以权利教义的普遍有效性来说服这些权力持有者是没有希望的,因为,如果这些教义占了上风,他们就必定要削弱和限制其权力的行使。因此,普遍性并不意味着普遍的赞同,在一个权力不平等的世界,有权者和无权者所能达成的唯一方案将是一个完全无力的、只起安慰作用的方案。权利是普遍的,因为它们对无权者的普遍利益作了界定,亦即,对他们行使权力必须采取这样的方式——尊重他们作为意志主体的独立性。在此意义上,人权是一个革命性的信条,因为它对所有人类群体提出了一个激进的要求,即这些群体应为组成它们的个人的利益服务。这由此又暗含着,在可能的范围内,人类群体应该是经各方同意后而形成的,或者,在个人不能忍受群体的约束时,它们至少应该尊重个人退出群体的权利。
群体应该尊重个人退出的权利这种理念并不容易与群体的性质达成妥协。大多数群体(如家庭)都是以继承的血缘关系或种族纽带为基础的血缘群体。人们在其出生上无法选择,也不容易离开它们,因为他们的集体提供了使得个人生活有意义的意义框架。这一点无论对宗教的或传统的社会,还是对现代世俗社会都是如此。群体权利教义的存在是为了保护集体权利(如语言权利),这些权利使得个人意志变得有意义和有价值。不过,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人权的存在就是为了裁定解决这些冲突,确定群体和集体的主张在限制个人生活方面所不能超越的最小值。
尽管如此,接受个人意志的价值并不必定意味着接受西方生活方式。信仰你的不受酷刑或虐待的权利,并不意味着穿西装、讲洋话、或者赞成西方的生活方式。寻求人权保护并不改变你的文明,它只使你能够使用“消极自由”来保护自己。
人权并不——也不应该——剥夺作为整体的传统文化的合法性。为免受塔利班民兵的侵扰而到西方人权机构寻求保护的喀布尔妇女并不是不想再做穆斯林妻子和母亲;她们想把对其传统的尊重与由妇女提供的教育和专职健康护理结合起来。她们希望人权机构能够保护她们不因为主张这类权利而遭受殴打和迫害。(注:See Michael Ignatieff, The Warrior's Honour: Ethnic War and the Modern Conscience, London: Vintage, 1995, pp.55—69.)
这些主张的合法性来自这样一种事实,即,提出这些主张的人并不是外国的人权活动家,而是受害者本人。在巴基斯坦,是当地人权群体而不是国际机构在领导保护贫穷的农村妇女免于“荣誉杀害”(即这些妇女在不服从丈夫时被活活烧死)的战斗;是当地的伊斯兰妇女在批评为此类虐待提供正当根据的、变异扭曲的伊斯兰教育。(注:See Murder in Purdah, BBC Television Correspondent Special, January 23, 1999, directed by Giselle Portenier, produced by Fiona Murch.)通过本土化、通过给无权者以权力、给无声者以声音, 人权已经走向全球。
事实并不像伊斯兰和亚洲批评者所主张的那样,人权把西方的生活方式强加给了他们的社会。尽管人权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的,但它并不要求其信奉者抛弃他们的非西方文化传统。就像杰克·唐纳利(Jack Donnelly)所指出的,人权“假定,由人民自己选择他们认为是良好的生活,这可能是最恰当的做法。无论如何,他们都应该有权做出这样的选择”。(注:Jack Donnelly, “Human Rights and Asian Values: A Defense of Western Universalism,”in Joanne R.Bauer and Daniel A.Bell (eds.), The East Asian Challenge for Human Rights, Cambrid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86.)《宣言》对选择权作了规定, 还特别规定了选择被否定时的离开权。如果这些主张对成千上万的人,特别是对神权、传统或父权社会中的妇女来说没有吸引力的话,那么权利语言的全球扩展就永远不会发生。
对这种人权扩展观点提出批评的人会认为,它太“唯意志”了:它暗含着传统社会中的个人可以自由选择他们参与全球经济的方式,自由选择采纳哪些西方价值、拒绝哪些西方价值。这些批评者争辩说,在现实中人们的选择并不自由。经济全球化摧毁了地方经济,道德全球化——即人权——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的合法化意识形态紧随其后。吉内斯·安德森(Kenneth Anderson)写道:“考虑到推行这一进程的国际主义者阶级的阶级利益,普遍主义就是一种伪装。普遍主义只是全球主义,而且它这种全球主义的核心条款是由资本建立的。”(注:Kenneth Anderson, “Secular Eschatologies and Class Interests”, in Carrie Gustafson and Peter Juviler (eds.) Religion and Human Rights: Conflicting Claims, Armonk, N.Y.: M. E.Sharpe, 1999: p.115.)把人权视为全球资本主义的道德武器的观点忽视了人权运动与全球公司之间关系的对立属性。(注:Richard Falk,“The Quest for Human Rights”, in Predatory Globalization: A Critique, London: Polity, 1999, chap.6.)投身于对像耐克和壳牌这样的巨型全球公司的劳工实践提出挑战的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家,要是发现他们的人权进程一直服务于全球资本的利益,他们会很惊讶。安德森把全球主义和国际主义合并起来,混淆了自由市场国际主义者和人权国际主义者这两个阶级,而这两个阶级的利益和价值是冲突的。
虽然自由市场的确鼓励据称是受个人利益驱使的个人的出现,这些个人诉诸人权是为了保护他们免于市场的无尊严和不体面。而且,这种个人所寻求保护的尊严并不必定源于西方模式。按安德森所写,人权好像总是由那些志在“拯救世界”的国际精英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强加的似的。他忽视了自下而上产生的人权需要的范围。
因此,对人权合法性的检验标准应该来自底层、来自无权者。(人权)活动家无需为西方人权标准的个人主义表示歉意,而是需要注意另外一个问题:怎样为底层的个人自由利用他们所需要的权利创造条件。为了增加人们行使其权利的自由,我们必须从文化角度深入理解经常限制这种选择自由的框架。极富争议的残害女性生殖器官问题说明了这一点。这种做法在西方人眼中可能是残害行为,而对于那些妇女来说,这只是她们成为部族或家庭成员所必须付出的一种代价;如果她们不服从该仪式,她们就会丧失其在世界中的地位。因而,选择行使她们的权利可能带来社会放逐,除了离开她们的部落、走向城市外,她们别无选择。人权倡导者必须知道,对一名妇女来说,抛弃传统惯例真正意味着什么。同时,(人权)活动家也有义务告知妇女这种习俗的医疗费用和后果,并且,作为第一步,努力减少那些希望接受这种仪式的女人们的危险。最后,应该由妇女自己在部落智慧和西方智慧之间做出选择。西方社会中规范病人选择的“使其在获得充分信息的基础上做出是否同意的决定”的标准,在非西方的框架下同样是适用的,而且,人权活动家对意志的独立和尊严负有尊重的义务,这一义务内在于人权话语本身。活动家所应当做的不是替这些妇女做出选择,而是让她们充分意识到其选择将会导致的后果。在传统社会,有害的习俗只有在整个共同体决定抛弃时才能被抛弃。不这样,自行决定的个人就面临着放逐甚至更糟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同意指集体或群体的同意。
对不同文化中限制个人自由的实在约束的敏感性与顺从这些文化并不是一回事。它并不意味着抛弃普遍性。它只是意味着应该勇于面对一种艰难的文化之间的对话,在此对话的每一方都期望被其他各方视为在道德上是与他们平等的。传统社会之所以对身处其间的个人是压制性的,不是因为它没有提供给他们一种西方的生活方式,而是因为它没有给予他们讲话的权利和被倾听的权利。要是传统文化实践仍然得到其成员的赞同的话,西方的(人权)活动家就无权颠覆此类实践。人权不是作为一种文化规定的方言,而是作为一种道德授权的语言才是普遍的。其作用不在于界定文化的内容,而在于努力解放所有的意志以便它们能够自由地决定其内容。
授权和自由并不是价值中立的术语:它们毫无疑问地具有个人主义倾向,传统和专制社会将抵制这些价值,因为它们向维系父权和专制主义的服从习惯投掷标枪。但是,人民怎样使用他们的自由取决于他们自己,而且,没有理由假定,如果他们采用西方的自由价值,他们就会赋予其西方内涵。此外,应该由受害人自己,而不是由外在观察者决定其自由是否受到威胁。那些被西方观察者认为可能处于被压迫和奴役地位的人们,完全可能会努力维护使他们处于这种隶属状态的传统和权威模式。在一些世界宗教中,包括极端保守的犹太教和某些形式的伊斯兰教中,妇女就处于这种隶属地位。一些妇女将越来越憎恶此类地位,而另外一些并不如此,不能假定那些并不如此的妇女受到了某种虚假意识的诓骗,需要人权活动来将她们从这种意识中解放出来。实际上,信徒们相信,参与他们的宗教传统使他们得以享受对他们来说比私人意志的消极自由更有价值的归属感。在人权活动家看来是侵犯人权的做法,在那些被人权活动家认为是受害者的人看来可能并不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在没有生命或者严重的、无法弥补的身体伤害的危险的情况下,受害者的同意应该是对人权干预的明确限制条件。而当危及生命时,那些生命受到威胁的人是不大可能拒绝获得拯救的。
人权话语应该假定:有关良好的人类生活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看法,西方的只是其中之一;倘若意志主体在生活的选择上有一定的自由度,那么,就应该让他们自己赋予该生活与其历史和传统相一致的内涵。
综上所述,西方的人权活动家对文化相对主义者的挑战做出了太多的让步。相对主义是暴政的永恒托辞。我们根本上没有理由为属于人权话语核心内容的道德个人主义而道歉:恰恰是这使得它对于遭受剥削和压迫的依附群体具有吸引力。同样,没有理由把自由视为西方独有的价值,或者相信倡导自由就是把西方的价值不公正地强加给他们,因为试图替其他人决定如何使用自由的做法是与自由本身的意义相抵触的。
应对亚洲、伊斯兰以及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对人权的挑战的最好方法就是承认这种挑战的真实性:权利话语的确是个人主义的。而这恰恰是它为什么是对暴政的一种有效矫正机制、为什么对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具有吸引力的原因所在。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另一个好处在于,它无疑是关于什么是善的一种“稀薄”理论:它只定义和规定了一些“消极的”东西,亦即那些使任何人的生活——无论我们怎样构想这种生活——都成为不可能的压制和不公道;同时,它并没有规定人能过的良善生活的“积极的”范围。(注:消极自由、积极自由、免于……的自由、为……的自由这些划分是由柏林提出的,Isaiah Berlin,“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in 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 ed.Henry Hardy,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97, pp.191—243;关于善的“稀薄”理论,see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人权在道德上是普遍的,因为它宣称所有的人都需要某些特殊的“免于……的自由”;它并不进一步界定哪些“做某些事……的自由”应该存在。在此意义上,它是一种比世界宗教更少规定性的普遍主义:它清楚地表述人类体面的标准,但并不妨碍文化独立的权利。
当然,一如威廉·吉姆里卡(Will Kymlicka)以及许多其他人所指出的, 有一些生活条件——如,讲一种语言的权利——并不能仅靠个人权利而得以保护。一个语言上的少数人群体需要享有用该语言教育其孩子的权利,以使该语言共同体得以生存下去,而这只有在更大的共同体承认它有这样做的集体权利时才能实现。不过,与此同时,所有的集体权利规定必须同个体权利保障达致平衡,以便个人的实质自由不因为群体而被否弃。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就像任何对魁北克语言立法有亲身经历的讲英语的蒙特利尔市民将会告诉你的那样。但这还是可以做到的,条件是个人权利最终能够优先于集体权利,使个人不被迫以一种非自主选择的方式教育他们的孩子。(注:Kymlicka,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pp.2—6.)因此,即使承认群体为了保护共享的遗产而需要集体权利,这些权利本身仍然冒有成为集体暴政的来源的风险,除非个人持有申诉权。正是人权的个人主义使它成为了一种抵制语言或民族群体哪怕出于好意的专制的宝贵壁垒。
在人权规范普遍性上的冲突是一场政治斗争。它导致权力的传统、宗教和权威来源与人权倡导者之间的对立。这些人权倡导者中有一些人就来自其所挑战的文化本身,他们以那些觉得自己遭受排斥和压迫的人的名义对这些权力的来源提出挑战。那些寻求人权保护的人并非其文化的叛逆者,他们不一定认同西方的其他价值。他们所寻求的是在他们自己的文化内部作为个人而享有的权利保护。对这种需要的专制抵制总是采用捍卫其整个文化免受西方文化帝国主义侵入的形式。事实上,此类文化相对主义理由实际上只是捍卫政治权力或家父权力的借口而已。人权干预之所以正当,那是因为依照那些受传统的、父权的或宗教的权威所压迫的人的标准——而不是依照我们的标准——这些权威是原始的、落后的或不文明的。人权干预的正当根据源于他们的需要,而不是我们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