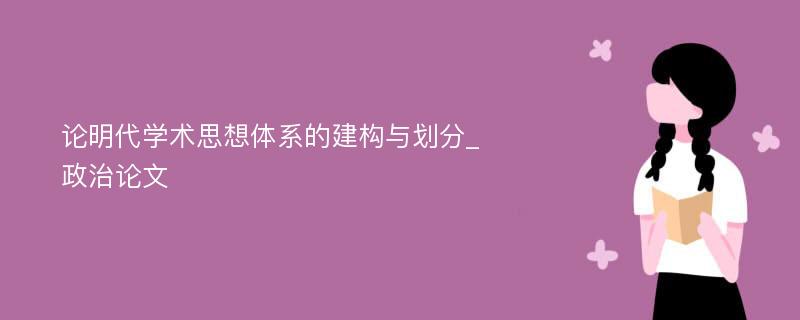
论明代学术思想体系的建构与分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代论文,学术论文,思想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3-0137-11 夏商周三代“学在官府”、“官师合一”,学术一体。春秋战国,天下大乱,《论语·季氏》云:“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学在官府变为“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王官之学变为诸子之学。分裂后的学术各行其道,丧失了整体统一的力量,也就不再具有道的根本和整体特征,只能是道其所道。史华慈指出,中国各家思想存在三点共同预设:“以宇宙论为基础的、普世王权为中心的、普遍的、包含一切的社会政治秩序的观念;秩序至上的观念(无论在宇宙领域还是在人类领域)更普遍地得到了认可;以整体主义的‘内在论’(immanentist)为特色的秩序观成为社会的主流趋向。”[1](P425-426)这种对原初性、根本性和整体性的追求是古代学术思想的一个突出特征,尽管道术分裂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不同时代的各种学说都在努力重建学术完整性,试图以此获得思想的权力。在明代,学术分裂后的三个主要类型是道德、政事、文章,涵括了儒学思想、社会治理、文学表达,三者呈竞争态势,但话语权力与学术处境并不一样,道德是根本,政事是实用,文学止于修辞。气节只是道德信仰下的一种政治行为方式,理想主义和牺牲精神的感召冲击了政治上的退缩保守,也成为建构新学术的一个重要成分。于是,可以看到,各个时期、不同群体都有自己的出发点和目标,既有恢复学术一统的努力,也有意图突破整体化限制的努力。 一、理学统绪建构中的一体化趋向 理学本身包含着一统学术的内在要求,又与现实需求结合在一起,在明初突出地表现在明道论、功业论、教化论之中。 明初谈论比较多的是理学与文学的关系。宋濂提出“诗、文本出一原”,“沿及后世,其道愈降,至有儒者、诗人之分”。[2](P2085)因此他在《元史·儒林传》题序中将儒林、文苑合而为儒学传[3](P4313),这可以视为宋濂以理学思想为中心,试图打破儒林、文苑二分的现实,实现二者融合的努力。宋濂所说的圣贤之学,既是身心之学,又是经世之学,其特征是“心与理涵,行与心一”,指向明道。单纯的文学仅停留在搜文摘句,务求新奇,则“去道益远”[2](P577)。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他提出德立而道明,贯通于身心,施之于事业,这些都是明道观下的产物。宋濂要以理学的“道”、“理”统合文学,从而使文学摆脱文辞修饰的束缚。道学与文章是永恒的矛盾,但道学之弊是流,文学之弊是本,强调道德第一,文章必须在明道明理统领下才有价值。这些都是在理学层面上展开的讨论,由于尚未获得政治上的权力,只能试图在理论上将文学统归到理学门下。 费孝通指出,自孔子以后,就“构成了和政统分离的道统”,出现了“用文字构成理论,对政治发生影响”但已不再“占有政权者”。[4](P25-26)这只是儒学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经过意识形态陶洗的儒学则充分与国家政权合作,从而“占有政权”。明代就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明初朱元璋治天下如王世贞所说是“高皇帝以实求,而天下以实应也”,从定天下起,他所用之人关注的就是实效: 至我高皇帝神武定天下,而一时忠荩硕画之士若徐中山、常开平、李韩公、刘诚意辈,各出其长以就功名之会,所谓云蒸龙变,盖先后无偶焉。[5](卷一百十六,《湖广第四问》) 在这样的背景下,朱元璋所倡言的理学当然要打个折扣,王世贞非常准确地指出他未尝不言理学,特别是通过取士制度将士人纳入正轨之中,但也仅止于“黼黻皇猷、佐理国事”[5](卷一百十六,《湖广第四问》)的实用功效,限制异端思想。明初的思想文化体系围绕着“功业、节义、文章”建立,功业是中心,节义实质上是对王朝的忠诚,文章则仅止于对二者的宣扬。政事论是得位者体制内的建构,宋濂虽任翰林学士,但这更多的是元代政治模式的一种延伸,内阁制度到永乐间才形成。 方孝孺多次强调教化的作用,认为学术、教化、文章三者之关系是“学术视教化为盛衰,文章与学术相表里”,但“天下之人,不能皆生而有闻”,故须“明吾教于天下”。[6](P396)张弼《送松江府同知于公之任序》认为“治教一源”,治教分则不足以达到“治平”。[7](卷一)教化论是传统的思想命题,希望通过普遍的教化来改造社会,从而使社会一归于正。同时,教化论也是政治要求,儒学思想影响下的历代官员都被要求承担这一工作,他们也积极投身其中,成为国家治理的一部分。教化论与政事论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地方官员的具体治理中,是儒家社会责任感和改造社会方式的体现,即所谓“治教一源”。 上述三方面是明初理学思想主导下整体化建构的主要内容,呈现为两个特点:一者属于思想一统的努力,一者属于国家政治的实际需要,这表明统一学术受到理学、政治的双重限定并随之展开。明初文学就受到上述三方面的作用:理学明道观对文学有极大的影响,构成了明初文学的观念背景;明初文学创作充斥着的功臣颂歌及墓志碑铭,即是在功业论的现实要求下的产物;教化论则使文学向着辅赞治理的方向发展。 二、政治话语权力下的整体化要求 元明清三代皇权专制都是通过理学的意识形态化来掌握思想的权力,从而使整个社会都在国家哲学控制下。由此形成了政治文化的概念,“既包含了政治,也涵盖了学术”[8](P7),即道统与政统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永乐初,开始了系统的意识形态建设,编制《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标志着程朱理学的官方地位得到全面确立,并达成道统、政统的合一。 明代政治思想和政治措施的较大变化发生在永乐以来的台阁体制下。台阁文人在思想建构中把道学与政事统一起来,视为一个整体。商辂《草庭诗序》讨论政事与道学之间的关系,认为道是治之本,志于道可以培育仁心,推而极之,即是政道。道德与政事是体用关系,体用一源,对道而言,行道、明道是一样的,只有得位与不得位之别。后世始分为二,依傍道德者鄙功业为庸俗,驰骛功业者斥道德为玄虚,这种相互鄙斥的态度造成了道德与政事的分裂。[9](卷四)作为得位者,台阁官员关注的中心是政事,即“举而措诸天下”,道德在完成了理学意识形态化建构之后则不需要论证,只是作为隐藏的不需言明的思想存在。而且道德是只有“纯乎圣贤之学者”[10](卷二,《与韩知府焘》)才足以当之,道德是高悬在上的准则,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下的实践活动。 台阁文人建立了一套文治方案,从而树立了台阁的思想、政治和文学权威。杨士奇曾论及这种文治思想:“文章、政事本出于一,文章之可施行者即谓之政事,政事之有条理者即谓之文章。”[11](卷四十,《北潭稿序》)杨荣提出“经术之优,推之足以裨世用,文辞之美,达之足以饰政治”[12](卷十二,《送浙江左布政黄敷仲之任序》)。陆深《北潭稿序》将台阁文学的特征概括为:“以明润简洁为体,以通达政务为尚,以纪事辅经为贤。”[11](卷四十,《北潭稿序》)可以看出他们所建立的文治思想是以“通达政务”、“裨世用”为主,又以“柢经据史”为思想根基,使文学足以修饰政治。这是儒学应有之义。杨守阯《送按察佥事林君序》云:“宇宙间事皆己分内事,己分内事用宇宙间事。先儒有是言已,古之圣贤穷理尽性,而尽人物之性,视天下之事礼乐、刑政、钱谷、甲兵之属无一而非吾职之所当为,故讲之有素,处之有术,如有用我,举而措之耳。”[13](卷一“)穷理尽性”的自然延伸便是视宇宙间事为自己分内事,举凡一切实政无不在其把握之中,施之于政,便足以开物成务。这种论述在台阁作家文集中比比皆是,显示出理学对明代政治的巨大影响,已成为士人的普遍认识和信仰。在官僚文化中,政事是第一位的,谢铎《复姜漳州》:“政以道之在圣门,治道为第一义。”[14](卷三十五)天下之理原于心,理涵括一切,是万事万物存在的法则。故理不外于心,不外于物,但理散于万物,并不等于万物皆合于理,这是人性差异所致。所谓“政”就是将存于心的理贯彻到万事万物中去,以“合其异,归其同”,故不论是道学、文学,还是经史、文章都要归结到政事当中。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道学与政事结合在一起,并以文章为附属,形成了台阁文学国家主义的文学观,这种文学观念一直以集体信仰的方式存在。台阁官员提出了一系列主张,以维护这种建立在儒家文治思想基础上的制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言论就是“以文学饰政事”。[15]明初是在重吏治、轻文学的背景下进行讨论的,而台阁大臣则要扭转这一局面,故正式提出并成为台阁官员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则始于永乐。王直《文敏集原序》云: 国朝既定海宇,万邦协和,地平天成,阴阳顺序,纯厚清淑之气钟美而为人,于是英伟豪杰之士相继而出,既以其学赞经纶,兴事功,而致雍熙之治矣。复发为文章,敷阐洪猷,藻饰治具,以鸣太平之盛。自洪武至永乐,盖文明极盛之时也。[12](卷首) 台阁文人的理想是集政事与文章于一身,这是台阁文学的核心思想,因其基于儒家的文治思想,得到了广泛的响应。洪武年间虽然产生了以儒道行治道的主张,但“政事”的概念没有出现,而是只重吏治。这种法吏之治造就了大批循守法律、谨重自奉的官员,文学则没有相应的空间。永乐以来,台阁文学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国家主义文学体系,“以文学饰政事”遂成为主流观念,集政事与文学于一身,支撑起台阁文学的大厦。①尽管台阁文学并不完全否定文学,但却主要强调文学对政治的依附,所谓“敷阐洪猷,藻饰治具”,正是对二者关系的清楚界定。对于较为纯粹意义上的文学,他们甚至是排斥的,杨士奇在与仁宗的一段对话中,提出“诗人无益之词,不足为也”[16](卷二,《圣谕录》中)。这种对纯文学的排斥态度代表了台阁文人的典型心态,那么,文学的地位何在呢?台阁文人发展出三种理论,一是完全在传统诗学理论下强调吟咏性情的合理性,虽视诗歌为末事,但亦不可无,为诗歌的存在提供了一个相对合理的空间。二是实用文学观,先道德而后文艺,道为本,文为用。三是“余事为文”,成为台阁文学的典型论调,盛行一时。 台阁文学最为推崇欧阳修,把他视为政事与文章相结合的典范,杨士奇《王文忠公文集序》提出行为本,文为末,他举出欧、苏作为代表,正是因为二人首先有“立朝之大节”[17](卷十四),其次才是其文。但后来的议论却日益严苛,程敏政《金坡稿序》引用朱熹批驳欧阳修只知政教出于一,不知道德、文章不可为二之言:“夫天下之理一而已矣,蕴之为道德,发而为文章,皆是物也。”[18](卷二十八)丘浚《云庵集序》云:“后世言文者歧而二之,故近世大儒有以人论文、以文论人之说,其意盖谓以人论文若欧、苏之俦,颛颛焉以文名天下。以文论人若司马文正公文名虽不及欧、苏,然心术正,伦纪厚,持守严,践履实,积中发外,词气和平,非徒言之为尚也。”[19](卷九)可见政事论在永乐以来的台阁学术体系中占有核心地位,甚至到了严苛的程度,连作为典范的欧阳修也不符合政事的标准。 三、学术分裂的内在机理 但是,永乐以来的学术一统建立在国家政治权力之下,不能实现真正的儒学思想引领下的整体化,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儒学思想,于是不可避免地产生分裂。丘浚指出这个过程在孔子殁后即开始了,秦汉而下分而为三:文辞、政事、理道。分裂之后的学术存在着诸多弊端:文章之士偏求奇怪艰深之辞,政事流于闳阔娇激之习,道学则弊至于虚矫,求异于世。因此,丘浚提出了“各矫偏而归正,必使风俗同而道德一”的主张,以使学术和整个社会文化回归到古昔“道德一,风俗同”的状态。[19](卷八,《会试策问》其三)张宁《梅溪书屋序》指出学术的分裂是由于“不深于道”,“立异为高,祛陈为新”,背离了六经四书:“尚虚无者,其说诞;言功利者,其说竞;名道术者,其说僣;专艺文者,其说浮;务记诵者,其说冗。”[20](卷十四)陈献章《书漫笔后》说得更明白,如果“大本不立”,不能“心常在内”,使文章、功业、气节皆“自吾涵养中来”,也只是“徒以三者自名,所务者小,所丧者大。虽有闻于世,亦其才之过人耳。其志不足称也”。[21](卷四)他们都极力维护道德即道的权威,以纠正过度强调政事论及其他方面缺失造成的对道德的危害。 顾璘也提出了学分为三的问题,《赠吕泾野先生序》一文从文辞、经义、道学的分裂谈起,指出文辞之弊在务华失实,不能底于大义;经义破裂圣学,徒为口耳之具;道学失实失己,走上立异尚新之途。[22](《息园存稿》卷一)他的论述中没有提到政事,代表明代学术思想发展的一个新动向。从早期对政事的强调,到将政事置于视野之外,显示人们对政事的回避疏离态度,政治不再是学术话语的中心。刘元卿《明贤四书宗解序》:“夫执经程士,匪定于一,斯王制弗信,故其防闲当严。谈经论道者匪极其趣,斯圣真弗著,故其检括贵广。此论治、论学两者途殊,要未始不共贯而互为用也。”[23](卷四)思想的旨趣是要不断适应新的时代需要,故贵广,而政治则是“防闲当严”,二者渐于不能相容,尽管最初的设计本身是“共贯而互为用”,但分离亦是一种趋势。这段文字虽出自晚明,但深刻地道出了政治与思想互不相容的根本原因。在台阁文化体系中,道德与文章是一体的,但这种一体化的设计还是在现实面前崩坏了,破坏的力量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台阁文化的工具论造成的。顾清《道德文章不可出于二论》对学术分裂的现实做出了深刻分析,认为道德是“人之所由共,我之所心得”的“五伦”,完全发自内心,而现实中,道德却被视为“垂世立教”的教化论,成为实行统治的工具。工具化的道德必然丧失存在的本根,陷于虚伪化的境地,昭示了政治一统下完整性的破灭。文学也应是得之口,宣之于心,但在台阁体制下的“华国润身”论也将文学工具化了,“方其为文章也,未尝不言道德矣。顾为文章而及道德,非以道德而发之文章也”,道德与文章离析为二,文章也只是“剪采以为花,形色虽似而精神生意索然矣”。[24](卷二十二)他敏锐地认识到,道德、文学从政治一统的整体化中分离出来,实质上源于道德失去了本质特征而陷于工具化,在儒学本真意义上提示了明代学术分裂的必然性。 理学思想高广但不能“实用”,文人则离道而言文,故而受到礼法之士即政治家的厌薄。顾璘《赠别王道思序》:“学道务虚,学文务奇,其究至于荡人心伤国体,非细事也。”[22](《息园存稿文》卷三)建立在世用论基础上的国家主义文学观念逐渐受到怀疑,作为台阁文学思想基础的理学也遭到虚伪和不切实际的批评,台阁文学的政治模式开始动摇,以道德、政事、文章三者一统的学术系统开始受到怀疑和批判。 随着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的变化,突破思想控制的冲动越来越大,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具体表现在很多方面,如理学内部的变化,陈献章的主静之学;如吴中派从知识体系的边缘寻找对正统的突破,进而形成了以边缘知识体系为中心的思想和行为;最有代表性并具有一定建构意义的是复古派。 四、气节、文章对整体化学术的突破 弘治、正德以来,郎署文学崛起于文坛,以复古号召天下,打破了台阁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但复古文学的意义不仅止于文学,更为突出的是打破台阁道德、文章、政事一统的局面,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反对理学,抨击虚伪化道德;二是以对文学情感的重视和对既有规范的挑战冲决了以政事为中心的文学体系;三是以激昂的政治热情对抗旧有政治格局、政治理念、官僚风习,以气节著称于世。至此,一体化的学术分裂为气节、文章。彭黯《欧阳恭简遗集序》:“弘、治时,主上右文,图理甚盛,是以鸿藻之客、石画之夫,翔起南北,蔚乎龙兴而云蒸也。”[25](卷首)这种“右文”局面无疑激起了士人的人格理想和政治理想,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抱着献身精神,投身现实政治。政治上以风节自砺,显然与台阁文学政治上的宽博、务为优容甚至明哲保身不同;文学上以敦朴道古为标志,也与台阁文学的雅正雍容不同。 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复古派文人投身政治斗争,以激切敢言的精神打破了台阁文人的政治涵养论。李梦阳并非不食“政治烟火”,对此他一直保持着清醒。他在现实政治与人格理想的矛盾之中没有退缩,反而以一种近乎僵化、教条的理想主义精神投身斗争,以一种抗拒世俗、批判世俗的勇气与残酷的官僚政治进行抗争。对他来说,以为官入仕实现自身价值已经不重要了,他将功名富贵置于身后,以超越世俗的精神实现自我价值。正是因为他们有着对精神人格的高尚追求,相信“积久而通,小大必获”,因而能够“不躐其等,不计不必”[26](卷四十二,《钓台亭碑》),在现实面前不甘屈从,敢于抗争。弘治间文人政治的普遍特征是对志节的推崇,所谓政业、文技反倒在其次,后来人们对复古派的推崇也多集中在这一点上。弘治间郎署官员表现出与台阁大臣不同的政治品格,如王九思自称“当世之狂人”②,这不是非理性的冲动,而是充满理想主义精神、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高尚人格的追求和对道义的坚守。不论在儒学思想还是在现实政治中,政事高于文学是自然的,故当文人以文学与政治抗争时其失败便是必然的。但他们又不愿屈身以从,宁愿以志节名世,以文学名世。李梦阳虽然反对理学,但他所反对的仅是理在现实中“性行有不必合”,其思维方式仍是理学的。可见,他所追求的便是性行相合的人格完善。他曾说:“尝自负丈夫在世,必不以富贵死生毁誉动心,而后天下事可济也。于是义所当往,违群不恤;豪势苟加,去就以之。”[26](卷六十三,《答左使王公书》)这成就了李梦阳孤傲不驯的品格和直言敢谏的政治勇气,奋不顾身,备受摧折。其实不仅李梦阳,弘治、正德间的士大夫特别是复古派中人差不多都具有这种特点,可以说,他们内心都横亘着一个绝对的理——特别是建立于其上的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包括精神信仰、人伦关系、政治伦理,因此他们对理学中天理的批判仅止于其现实境遇中的虚伪化,走的仍是外在路径。但不可否认气节在整个学术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晚明赵南星曾说:“余平生喜谈节义事,以为节义生于廉耻,廉耻生于是非,是非生于知觉天下将乱,则人鲜节义,然天地之正气不绝,必有一二矫矫者出焉,笄袆之流时能伏清死节,故邦家有兴亡而宇宙无成毁。”[27](卷八,《终慕录序》)气节是天地正气,欲救天下,必须有“伏清死节”之士起而矫之,不仅有关邦家兴亡,更关乎宇宙之存在。气节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和政治中的作用应作如是观,而不能仅视为士人一时的冲动。 在他们的学术建构中,气节与文章是一体的,陆深多次谈到这个话题,如《送叶白石令邵武序》:“夫以气节根柢乎文章,文章缘饰乎吏事。”[28](卷三)何以“气节根柢乎文章”呢?必须从前七子的养气论入手才能认识清楚。方鹏《静观堂集原序》:“文章类其为人,气之发也有不终类者,学之验也。徒听乎气而无学以养之,则刚者必肆,柔者必靡,其不陷于一偏者几希。”[29](卷首)他很准确地把握了复古派气论的核心,即气指的是气质之气,不是理学家气本论的天地之气。气质之性属于血气之知,易于陷入刚肆桀骜,在精神上完全听从气质的召唤,这就是前七子以理想主义精神奋不顾身地投入政治斗争的原因,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气节根柢乎文章”。陆深《碧溪诗集序》:“夫文章与事功难相兼,而声名与贫贱常相值,大抵安于贫贱以养夫闻望,固君子之心;详于文章,略于政事者,岂君子之得已哉!”[28](卷三)由于坚持气节,他们都是政治的失意者,只能退而以文章名世,故文章与政功难以相兼,却可以与气节同构。台阁建立的“以文章饰政事”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模式也当然面临质疑,并逐渐退出了新的学术系统。 复古诸子建立了一个以“真”、“质”为特征的道论,以文学精神为中心,执着于气质之性的养气论和作为文学发生论的感物论三者一体的文学观念世界[30],对道的破坏十分严重,道德与文学的冲突日益严重,汪道昆《鄣语》: 世之命儒者二,其一道德,其一文辞,当世并訾之,訾其户说长而躬行短也。谭道德者下汉唐而登宋,莫不尸祝程朱;谭词章者左宋而右汉唐,则建元、元封、开元、大历为政,或源或委,一本不殊。迄于末流,且交相訾。……两家难起,分类植群,伐异以徼功,党同以守胜。攻若鸣鼓,守若登陴,由是畔儒者张,归儒者沮矣。[31](卷十六) 道德与文学是一对永恒的矛盾,但在明初以来的设计中并不存在冲突,甚至可以说是一体的,到了弘正之际则陷入矛盾之中。汪道昆对此把握得十分准确,谈道德者“下汉唐而登宋”,谈词章者则“左宋而右汉唐”,两家纠难纷起,甚至党同伐异。同时,复古派反对“尚一”的文学,而这正是盛世文学的特征之一,不追求文学的统一整齐,宁愿在并不和谐的众声同唱中展现自我。这意味着前期文学格局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以台阁文学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文学走向末路,颂盛模式解体,翰林独占文学权力的局面被打破。 新学术话语以气节、文章为中心,打破了理学以理道为中心和台阁以政事为中心建立的学术体系,道德、政事退居其次。这是明代学术思想史上的一次重要变化,冲击了理学的话语权力,突破国家主义下的整体化学术限制,导致整体化学术的分裂。 五、救正气节、文章之失 薛应旂《送王汝中序》梳理了洪武以来学术的变化,指出矜文辞者和高谈性理者都已失去学术号召力,陷于唯言语是从而缺乏躬行实践的局面。[32](卷十)学术的虚浮化导致政事失衡,而新的学术形态如气节、文章又不为人所信服,学术陷于使人无所适从的局面。分裂的学术话语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批判,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倡导实学以纠正政事论及文辞论的不足;第二,对气节进行反思和批判;第三,以学术内涵弥补文学的不足;第四,道德论的提出,以良知为中心对学术进行重新建构。 王廷相《石龙集序》云: 何谓三尚,明道稽政,志在天下是也。明道而不切于政则空寂而无实用,稽政而不本于道则陋劣。……故其见诸文者非道德之发越,必政事之会通矣。夫今人之刻意模古,修辞非不美也,文华而义□,言繁而蔑实,道德、政事寡所涉载,将于世奚益?[33](卷二十二) 这里所说的政事已不同于台阁的政事论,而是以理道为中心参与、改造政治,使政治脱离“陋劣”。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也必须依附于道德、政事。张时彻《潘笠江先生文集序》论仕与学相须:“以为体天地之撰,类万物之情,穷古今之变,则德义之经,藻润政治,鬯达性灵,非此则其道无繇也。”[34](卷二十六)王慎中是嘉靖间讲求实学的代表人物,对官员以文事为高的现象表示不满,《寄道原弟书一》提出“宜立定主意,以明习国家事体为要”[35](卷二十四),而一二文学之徒虽能出于政事之上,但徒陷于“自足”,无实政之能,为人所讥切。更进一步,王廷相将政事的笼统提法改称实学,《送泾野吕先生尚宝考绩序》:“士惟笃行可以振化矣,士惟实学可以经世矣。”[33](卷二十二)实学源于道义之心,身心俱化,凝而为我,故能游心淡泊,甘守贫贱,出则能独断内凝,动中几会。这些主张开启了嘉靖以来的实学思潮,既是复古思潮的深化,也是思想界运动的必然结果。对于复古派单纯讲求文学、气节而言,不啻是一剂清醒药。 前七子多以刚直敢言、气节不屈闻名当代,这在尊崇气节的明代得到了很多赞美之词,徐祯卿《与朱君升之叙别》:“士之贵于世者有三:其上志节,其次政业,最下者文技。”[36](卷末附录)从世用角度将士人承担总结为三个方面,以志节为首,而不是道德。焦竑《原学》将分裂后的学术分为四种类型,有清虚之学、义理之学、名节之学、词章之学。[37](卷四)单列出名节之学,正是对弘、正以来学术新变的总结。名节、气节不仅是一种道德和政治行为,更被上升到学术的高度。但不可否认,这种性格气质不适于政治。弘、正以来,名节之士往往为气所使,不能通时之变,甚至有些浮靡躁进之习。一时刚愤激切,固名于当世,称于后人,然于事无补。士人因此遭遇坎坷,久滞下僚,有终身不得用者,有久而后用者。夏良胜《答李空同书》:“夫天下士之所以自立曰德,惩忿窒欲,德之修也。忿者,恨也,必不平也。若欲岂必是贪欲,有不平则忿忿,心炽则欲上,人忿欲行而德罔滋美哉!”[38](卷四)认为愤怒的情绪必导致德性修养偏乱,这是儒家个体修养论很重要的一面。讲求气节当然有积极的意义,“刚毅”与“俭邪柔媚”根本是两种品格,但不可否认,“刚毅”亦有陷于不平愤恨,“英气害事”之弊。这种分裂学术的形态对旧有秩序形成强烈冲击,对虚伪化道德及政治中的保守态度有一定纠正作用,但却以比较粗陋的激愤形态为主,无法形成学理化学说,只能依附于道德和政治而存在。就道德而言,复古诸子的“道”有陷于日常万物之具体的可能,失去了对道的本质属性的体认,所谓“沉溺气骨,乐随色相”[33](卷首)。唐顺之《寄黄士尚辽东书》:“自儒者不知反身之义,其高者则激昂于文章气节之域,而其下者则遂沉酣濡首于蚁膻鼠腐之间。”[39](卷四)即是针对士人沉溺于文章、气节的批判,文章、气节作为复古文学的两个支撑点,在唐顺之看来居然毫无意义。就政治而言,复古诸子皆被政治抛出,失去了依附。这样一来,气节、文章之学便成为无根之学,无法形成系统的学理化的学术话语。 有鉴于复古文学流于形式和模拟肤浅之弊,后七子开始提倡以学问补文辞之不足。李维桢从经史子集学术分类方式入手分析了集部之学的特点,认为辞林不应单指文辞,“三代而下,经史子故不易作,复不恒作,而辞林一归于集,滥恶日滋甚”,实则“集之名晚出,而其用视经子史为最繁,其体视经子史亦无不有,以其用繁也”,故辞林应涵括四部,即“辞林者,不越经史子集四部矣”。他在《辞林人物考序》中指出: 昔者孔子四科,文学、言语与德行、政事各效其长,令词林四部集与经子史各诣其胜,合固双美,离不两伤。彼一隅之士,分畛域,立门户者爽然自失,孜孜然学如不及,有功于辞林宏矣。[40](卷八)一方面他承认四部“各诣其胜,合固双美,离不两伤”;另一方面,分门立户,各不相及,也是一隅之见,需要以学问入辞林,提升辞林的内涵。胡应麟以博学著称于世,他对“当今之世,士持学术则摈词章,挟词章亦绌学术”[41](卷八十四,《贺张明府子環考绩序》)的风气十分不满,《黄尧衢诗文序》云: 古今人之材果弗相及乎哉?古之世之称材者,词章问学出于一,而今之世之称材者,词章问学出于二。[41](卷八十六) 这段论述没有回到上古学术整体的神话之中,而从近古的诗文入手,指出枚曹李杜、左马扬韩都“未尝废问学”,自李梦阳始取径狭窄,造成词章、问学“判为两途”。问学指向博学,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学术,但对复古文学有很大的修正。由此再进一步,他讨论了诸子的历史和现实。从学术变迁和著述的角度看,“唐宋而下文不在子而在集”,集部之学包含了子部,而这正使文学获得了提升的空间。明代著述不仅包含着“子以文”,也包含着“子以理”,有着深厚的学术内涵。隆庆、万历以来文章盛行纪述,论理者则少闻见,子与文分而为二。[41](卷八十三,《义苍漫语序》)胡应麟为我们审视明代学术提供了两个角度,谈文者纠缠于事实,论理者远离实际,都是学术分裂的产物,这些主张带有强烈的救正意味。 在儒学思想中,立德、立功、立言虽分而为三,但德是中心:“德者,得也,学者得诸心则发于事者,为功其匪躬也。夫衍于声者为言,由其衷也。夫是合一之道也。使无是心则功焉不实,名已耳。言焉不实,华已耳。”[33](卷首)发诸事与衍于声都是德的外现,背离了德,便有不实之弊。王慎中《曾南丰文粹序》也提出了学术一统的主张,不同于台阁文学的政事论,而是要使“学术明于人人,风俗一出乎道德,而文行于其间”,中心是“一出乎道德”。在这个中心命题之下,文的价值和意义在于“通志成务,贤不肖、愚知共有之能,而不为专长一人、独名一家之具”。他一方面对周衰学废之际诸子“各以其所见为学,蔽于其所尚,溺于其所习,不能正反而旁通”,虽有不醇不该之弊,但能够“皆以道其中之所欲言”;另一方面,他极力反对的是“怪奇瑰美”、“道德之意不能入”的文学。[35](卷二十二)徐师曾《临川王氏文粹序》也对“周衰教失,道术不明,士各以其所见为学”的现象表示不满,又承认诸子之文虽多疵驳之言,“故发为文章,类多疵驳之言,然读其文者,仍是“能道其中之所欲言”,反对的是“离本真之实,而掠藻饰之辞,假艰深之言以文浅易之意者”。[42](卷八)他们针对文学的意义缺失之弊设立了两道防线:一道是“能道其中之所欲言”,一道是明于学术,出于道德。前者可使文学表述能达其中之所欲言,后者则能使文学获得道德本体。张位《刻敬所王先生文集序》从理辞关系入手,指出:“谭名理则曼衍天倪,百构一律”,“修辞之子起而振之,率又摹拟太过,浮艳无根,后圣经而先诸子,钩字抉句,饰不必有之事,务以炫奇”,“文人非无一言几道,奈敝帚自享,行不相掩”。[43](卷首)只有将理辞合一,才能超越分裂后各得其一的弊端。提升文学的学术品位,增加文学内涵是改变修辞之士往往流于肤浅模拟之弊的一条途径。 六、融通、破障与新的分裂 罗洪先在《龙场阳明先生祠记》一文中梳理出了王阳明学术思想的三次变化,一变而为文章,再变而为气节,终悟得良知之学,是明代士人思想转变的典型代表。[44](卷五)从自身经历出发,王阳明对学术分裂之弊也有深刻批判,《与顾东桥书》指出自圣学湮没之后,各种学术纷争并起,分裂为训诂之学、记诵之学、词章之学。分裂后的学术“千径万蹊”,使人无所适从,不知圣门归一之学。正是看到学术分裂的严重景象,王阳明欲以心学统之,使归于圣人之道。[45](卷二) 良知之学既是身心性命之学,又是开物成务、经世济民之学。个体只有变化气质,悟得良知,达到不动心、不动气的境界,才能应世。王阳明屡次讲到这个问题,如《与王纯甫》:“变化气质,居常无所见,惟当利害、经变故、遭屈辱,平时愤怒者到此能不愤怒、忧惶失措者到此能不忧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处。”[45](卷一)王畿《读先师再报海日翁吉安起兵书序》引述王阳明之言: 师曰:致知在格物,正是对境应感实用力处。平时执持怠缓无甚查考,及其军旅酬酢,呼吸存亡,宗社安危所系,全体精神只从一念入微处自照自察,一些着不得防检,一毫容不得放纵,勿欺勿忘,触机神应,是乃良知妙用,以顺万物之自然,然而我无与焉。[46](卷十三) 只有超越利害毁誉,不搀杂任何假借之心,顺应万物之自然,才是良知之妙用。而这正是慷慨激昂的文学之士和空言明道的儒学之士所无法达到的境界,就此而言,王阳明确实为明代士人树立了一个超越自我、去除蔽累之心的榜样。陈来说:“只有真正了解阳明正德末年经历的巨大人生困境,和面对的严峻的生存考验,我们才能了解良知学说对阳明自己早已超出了纯粹伦理的意义,而涵有生存意义上的智慧与力量。”[47](P230)变化气质,悟得良知可以使士人超越气节、文章之学的遮蔽,就这个意义而言,王阳明心学不仅是一套完整的思想建构,而且具有应对现实的实用功能,其中所包含的人生智慧与力量确实能够给面对现实的士人提供人生指南。 心学肩负着安顿自我与开物成务的双重使命,变化气质只是开端,更重要的是以悟得良知之心从事经世济民之业。他们提出“政学合一”的主张,主张悟得良知便“道在其中”,便可以“政学合一”。王畿曰: 良知不学不虑,百姓之日用同于圣人之成能,是非之则也。良知致,而好恶公,则刑罚当,学也而政在其中矣。大学之道,自诚意以至于平天下,好恶尽之矣,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意之诚也,好恶无所住,心之正也,无住则无僻矣。身之修也,好恶公于家,则为家齐,公于国与天下,则为国治而天下平,政也而学在其中矣。[46](卷八,《政学合一说》) 他的主张得到了阳明后学的认同,王艮:“夫学外无政,政外无学。”[48](卷下,《再与林子仁》其二)欧阳德:“政学本非二事”,“政与学有二乎?良知酬酢变化而万事出,事者,知之事,知者,事之知,学也者,致其事之知以广业,政也者,致其知于事也”。③“政学合一”是对“以文学饰政事”的超越,不仅超越了国家主义背景下意识形态化的经世论,也超越了文学之士对政治的激情投入和悲愤结局。在更高的层面上,良知之学不仅解决个体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更在用世层面解决了士人如何应世的问题。 在王阳明那里,良知之学以内在理路的方式出现,以此改变人心,使之向善,同时又有外在路径的一面,平辰濠之乱是可以大书特书的伟大事功。同时,他也是一位文学家,将心性与审美结合起来,超越了文人的审美方式。至此,良知之学获得了统一学术的力量,道德、事功、文章、气节均统一于良知之下,既改变个体气质,又以积极入世的面目出现,从而获得了一统学术的号召力。但学术思想的整体化努力依然无法改变学术分裂的现实,心学本身后来就分裂为求圣狂者派、归寂派、求乐自然派、事功进取派[49](P336),并且心学在进入官场并被接受的过程中也被工具化了,成为官员满足自我的手段。内在超越如何转化为外在事功是一个永恒的学术和社会问题,在明代也同样如此,即使有王阳明提出良知之学以重建学术体系,并成为士人的典范,但也仍然无法转化为现实力量,建立一个整体统一的为整个社会所接受的学术思想体系。学术分裂依然在持续着,晚明政治一片混乱,所谓政事、事功离士人理想越来越远,气节也渐陷于党争,相互倾轧,文学则以自我解脱为目的,不再以精神超越为理想追求。聂豹更进一步详尽分析了分裂后的学术各执一偏,一叶障目,不能抵于大道: 或问:“今之学者何如?”曰:“今世之学,其上焉者则有三障,一曰道理障,一曰格式障,一曰知识障。讲求义理,模仿古人行事之迹,多闻见博学,动有所引证,是障虽有三,然道理、格式又俱从知识入,均之为知识障也。”[50](卷十四,《辩诚》) 聂豹深入分析了学术分裂现象,指出胸有所障,故见有不足。在道理障、格式障、知识障中,知识障即李贽《童心说》中所说的“道理闻见”[51](P84)。所谓“义理”一旦成为固定的模式,不能“随事变以适用”,“格式”不能顺应时势,造成义理之学的僵化。至此,有关学术分裂的思考已经进入思想最隐秘之处,指出知识对思想的障碍,摆脱障碍就成了思想保持精进的必由之路,从而引发了晚明思潮中对心性自由和灵明一窍的推崇。在这样的观照背景下,气节、文章固然高于世俗,有过人之处,然“道学不明,士大夫不知用心于内以立其本,而徒以其意气之盛以有为于世者”[50](卷十四)必不能达到超越境界。 晚明文人的精神追求以自得、解脱为中心,但客观上刻意保持、维护血气之知。李贽大胆宣称: 此乐现前,则当下大解脱,大解脱则大自在,大自在则大快活。世出世间,无拘无碍,资深逢源。故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故学至于游艺,至颖,不可以有加矣。[52](P4) 可作为晚明士人精神的自我表白。这样的人生境界完全以个体受用为中心,求得大解脱、大自在、大快活,既有心性无执的畅适,也有享乐的成分。政治斗争充满血气、意气、欲望,经历了明初至嘉靖以来的痛苦,一旦获得了新的思想资源,可以找寻到一个安放自我身心之所,文人便开始抛开令他们痛苦、妨碍他们获得解脱的政治。正如袁宏道所言,中国古代文人心中总是放不下功名,不论是身在政治之中,还是在政治之外,总是抱有幻想,总是希望有明君贤相能够容纳豪杰之士,因此总也说不出如此明白彻底的话。朝政并非是奸臣所坏,即使是智足以知假气魄伪节义的君子只能混干将、楩梓、骐骥、凤凰于庸众之中,不能识别真丈夫。既然如此,英雄豪杰亦不必出而应世,唯一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只有走出刀山剑树,放开性灵,得大解脱,以其灵识透达圆融自足的精神世界超然于世俗之上。[53](P704-705)至此,“以文学饰政事”的论题不再成为士人关注的问题,甚至被完全解构了。明人对李梦阳的斗争精神极为推重,几于赞不绝口,但到了晚明,对气节也有了不同的看法。袁小修《余给谏奏议序》:“古人谓人才当以气节为主。予谓以气节名者,非士君子之得已也。节持于气,气也者,如火热,发而莫已其焰者也。……惟君子者,其气激而不平,名根太重,成心不化,以至龙战玄黄,其害孔亟。”[54](P464)气节只是士君子不得已的行为,由于火气太重,名根太重,实际上有碍于自适自得的人生追求。 从阳明心学中获得启迪,经过一系列转化,晚明文人逐渐摆脱一切束缚,抛开了儒家思想中的现实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形成了以个体生命解脱、自适为中心的生命观念。以此为中心,晚明士人对道德、政事、气节、文章一一加以解构,却无法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体系化的学术,因为这本不是他们所追求的。 考察明代学术思想体系整体建构与分裂的历史可以为我们认识明代思想文化提供一个全面的视角,从而避免单一学科视野的局限。通过简要梳理,我们发现,学术思想的整体建构由于获得了理学思想的支撑而具有深厚精神内涵,明代学术正是由此获得了巨大的生命力。但当理学思想意识形态化之后,这种努力转而成为思想控制的力量,造成思想文化的虚伪化、工具化,限制了思想活力,于是学术分裂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分裂对意识形态化的思想有破坏作用,同时也是重建思想文化的努力,为社会思想文化注入新的血液。但是,这种重建的努力往往被政治和现实的力量消解,无论复古文学还是阳明心学都在现实面前表现出无力之态。由于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的超稳定性,分裂后的学术无力建构一个完整的足以对抗理学的思想体系(心学在总体上也是宋明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的反抗只能是局部的、分散的,只能对旧体系起到解构作用,而不能建构出一个新的体系。 注释: ①陈邦偁《湘皋集序》云:“古谓姚宋不见于文章,刘柳无称于功业,盖慨夫二者之难兼耳,粤稽我朝树开国之勋兼有文传世若青田刘公,后是而名公硕辅若三杨二李、商文毅公辈代不乏贤。”见蒋冕:《湘皋集》卷首,嘉靖三十三年王宗沐等刻本。 ②王九思:《答王德征书》,《渼陂集》卷七,嘉靖刻本崇祯修补本。王九思在与友人的书信中不断重复这个话题,如卷七《与中丞刘养和书》:“夫违俗者骇众,遵道者被谗,固烈夫志士特立独行超世之盛节也。”卷九《春雨亭夜饮离歌序》亦云:“厉志亢节者,君子之高蹈,由众而悲喜者,恒人之情也。有所托而鸣者,风人之意也,击剑悲歌者,烈士之行也。” ③欧阳德:《欧阳南野先生文集》卷二《答方三河》、卷七《缪子入觐赠言》,嘉靖三十七年梁汝魁刻本。相关论述参见吴震《阳明后学研究》第九章“阳明后学与讲学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2~4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