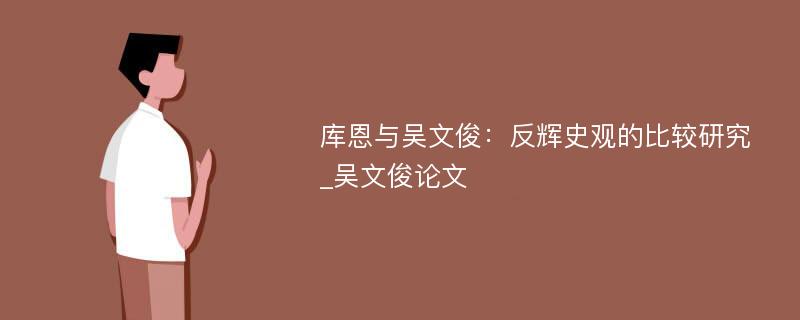
库恩与吴文俊:反辉格史观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库恩论文,吴文俊论文,反辉格史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287(2009)04-0016-05
托马斯·库恩是科学哲学中历史主义学派的代表,他长期从事科学史的研究,在对科学史的考察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科学哲学观点。在科学史研究中,库恩反对辉格史的研究方法,主张用“反辉格史”的原则去展示一门科学的历史整体性。无独有偶,中国当代的数学家吴文俊在处理和研究中国古代数学问题时,也明确反对辉格史的研究方法,提出并示范了“反辉格史”的研究原则和方法,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数学机械化理论的创新。吴文俊对中国数学史研究的方法及其论述同库恩的“反辉格史”的科学史观如出一辙,殊途同归。同时,吴文俊在科学史方法论方面所体现出的观念和方法在某些方面完善甚至超越了库恩的科学史观。因此,在解读库恩的思想时,以吴文俊关于中国数学史研究方法的问题为参照,将会得到许多富有启发的见解。
一、库恩反辉格的科学史观
库恩反辉格的科学史观源于一次偶然的科学史工作。1947年,库恩被要求做一项关于17世纪力学起源问题的研究,这项工作使他必须要将历史追溯到牛顿和伽利略以前的古希腊时代。这种情况下,库恩接触到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物理学》。在解读这一著作的过程中,让库恩大为不解的是,像亚里士多德这样一位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为什么“到运动问题上就一败涂地呢?他怎么会对运动发表那么多明显荒谬的论点呢?而且最重要的,对这种观点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后继者那么长久地认真对待呢?我读得越多,就越感困惑。亚里士多德当时会犯错误,对此我并不怀疑,但是怎么能想象他会错得那么显眼呢?”[1]Ⅲ库恩对此极为不解。但这种困惑在一个夏日消失了,据库恩回忆说,那天他突然领悟到,其实并不是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不合理,而是他自己的阅读方式不合理[2]544。库恩“一下子领悟到,可以采取另一种方式阅读那些我一直苦苦攻读的文本,从而理解有关的入门途径。我第一次对这一事实给予应有的重视:亚里士多德的主题一般是‘性质的变化’……在一个以性质为本的宇宙中,运动必然是一种‘状态的变化’,而不是一种状态”[1]Ⅲ。这使他醒悟到,牛顿物理学和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是不同时代的两种不同语境的物理学,两者关注的主题也不尽相同。因此,不能先入为主地在牛顿物理学的框架内辉格式地去解读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也不能在牛顿用语的范围内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提出问题并给予解答,而应该尽量用亚里士多德时代的科学语境来阅读,“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学会像他们那样考虑问题”[1]Ⅲ,库恩称这是一种“新的阅读方式”。当领会了这种新读法后,库恩发现“牵强附会的隐喻就往往成了自然主义的记录,许多明显的荒谬也不见了”[1]Ⅲ。并且虽然“我仍然知道他的物理学所遇到的困难,但不再那么突出了,而且这些困难几乎都不能恰当地归之为错误了”[1]Ⅲ。
阅读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教训”使库恩彻底醒悟,他于是提出了两条关于历史研究的阅读原则:一、读一个文本有许多方式,拿现代最易于理解的方式用到过去,往往不合适。二、文本的可塑性使各种读法都不一样,因为有一些(人们却总是希望只有一种)比别的更合理、更为前后一贯[1]]Ⅳ。
原则一表明了库恩反辉格史的主张,即反对用现代方法阅读过去的文本。原则二则说明由于文本的可塑性造成不同的阅读方式,人们不应总是用固定的方式,而应使用更合理、更前后一贯的阅读方式。库恩虽然没有提出具体明确的方法,但这种批判式的原则已经使得反辉格史主张非常明显,在阅读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过程中,他已明确表述并示范了反辉格史观点。库恩认为“只有对过时的文本恢复过时的读法”[1]V才能真正理解过去的科学,这种“恢复过时的读法”就是指在文本发生时的语境下,用古人的思维方法及知识背景恢复文本的本来面貌。在做科学史研究时,应当把自己置于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去解读,以古人的视角恢复过去的读法,这种阅读方式比其他方法更加合理,也更加前后一致。
作为对立面,辉格史的观点是科学史家应“根据我们今天拥有的知识来研究过去的科学,以理解其发展,尤其是它怎样导致今天的状况”[3]96。实际上这是一种史学家“凭借后来的介入而‘干预’过去”[3]96的做法。而反辉格史观则认为科学是历史的产物,科学史家应注意到科学本身的历史性质,在面对过时的原始文本时,应了解文本的历史情境。库恩明确反对辉格式地对待古代留下的科学史料,反对用现代科学的眼光去解读过去的科学文本。他在1968年为《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撰写“科学的历史”这一条目时这样写道:“科学史家应该撇开他所知道的科学,他的科学要从他所研究的时期的教科书和刊物中学来……他要熟悉当时的这些教科书和刊物及其显示的固有传统”[4]。换句话说,科学史家的头脑应该如同容器,面对不同时代的文本可以清空并装入不同的内容,以便深刻了解过去的科学。当库恩用这样一种反辉格式的科学史观去阅读另外一些被贴上“错误”标签的著作时,他发现,亚里士多德的动力学、燃素化学或热质说等一些“曾一度流行的自然观,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比今日流行的观点缺乏科学性,也不更是人类偏见的产物”[5]2。因此科学史家“不再追求一门旧科学对我们目前优势地位的永恒贡献,而是尽力展示出那门科学在它盛行时代的历史整体性”[5]3。
正是库恩采用反辉格史的阅读方式完成了他个人的格式塔转换,使他认识到近代物理学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是两种不同的物理学,进而将之扩展到整个科学史,这也为他今后提出范式概念及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提供了思想观念上的准备。可以说,反辉格史的研究方法反映了库恩的科学史观,并使库恩的科学观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开创了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学派,提出了一种大异其趣的科学观,极大地影响了科学哲学的发展。
二、吴文俊研究中国数学史的原则和方法
作为中国现代著名的数学家,吴文俊从拓扑学、数学史研究到中国数学史研究再到数学机械化理论的突破等方面都有重大的贡献,本文所关注的是他的反辉格史的研究方法在中国数学史研究中的应用和作用及在此基础上的创新。
对于中国数学史的研究,长期以来总是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方法论错误,即常常在西方数学的框架内,使用现代方法“以西释中,以今议古,致使面目全非,掩盖甚至歪曲了中国传统数学的真实面目”[6]30,使西方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数学长期存在误解。从20世纪初到现在,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数学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对中国数学的认识及争论焦点,分别经过了中国是否存在数学、中国数学的独立性以及中国数学是否是世界数学发展的主流等问题的争论。当吴文俊介入中国数学史的研究时,西方学术界虽然基本承认中国存在独立发展的数学,但是仍然认为中国式的数学并非世界数学发展的主流[7]。而吴文俊通过对史料的研究和前人资料的分析,认识到学界对中国数学史研究存在的问题,指出“要真正了解中国的传统数学,首先必须撇开西方数学的先入之见,直接依据目前我们所能掌握的我国固有数学原始资料,设法分析和复原我国古时所用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才有可能认识它的真实面目”[6]31。基于这样的认识,吴文俊明确提出了研究中国古代数学史需要严格遵守的两条原则:其一,所有研究结论应该在幸存至今的原著基础上得出。其二,所有结论应该利用古人当时的知识、辅助工具和惯用的推理方法得出[6]83。
就原则一来说,必须依据所能掌握的我国数学原始资料进行研究,而秦汉时代的《九章算术》与魏晋时期的《九章算术注》作为中国最早、最完整的历史纪录,“是研究数学在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的钥匙”[2]197。就原则二来说,由于中国古代数学中没有使用代数符号演算和添加平行线证明几何题的传统,因此,我们应该强调在代数和几何的推理中禁止使用诸如此类的“现代”方法。
依据这样的原则和指导思想,吴文俊对刘徽的《海岛算经》九题做了古证复原。他发现,当时显然没有平行线、角度等这些现代概念,因此在做复原工作时应该避免使用这些现代概念。而与此相反,“出入相补,各从其类”的原理却在很多场合被明显地应用。因此,吴文俊对《海岛算经》九题的复原只是反复使用了出入相补原理推论之一的矩形等积关系,而整个证明简单明了、自然而然,“从最基本的一些关系自然地直接获得刘徽原著所列出的那些形式上颇为复杂的公式”[6]154,示范了更加符合原初意义的“古证”。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提出了古证复原的三项原则:第一,证明应当符合当时本地区数学发展的实际情况,而不能套用现代或其他地区的数学成果与方法。第二,证明应有史实史料上的依据,不能凭空臆造。第三,证明应自然地导致所求证的结果或公式,而不应为了达到预知结果以致出现不合情理的人为雕琢痕迹[6]151。
这3条复原古证的原则可以说是吴文俊反辉格史观在中国古代数学研究中的具体体现和理论总结。可以看出,吴文俊研究中国古代数学的方法与库恩所持的反辉格史科学观思想方法是一致的。此外,作为一个优秀的现代数学家,吴文俊还通过中西数学发展的深入比较与科学分析,指出“我国的传统数学有它自己的体系与形式,有着它自身发展途径与独到的思想体系,不能以西方数学的模式生搬硬套”[6]200。西方欧式体系和中国传统数学是沿着不同的思路经过不同的轨迹发展,从而形成不同的研究传统。西方欧氏体系重抽象概念与逻辑思维及概念与概念间的逻辑关系,以定义、公理、定理、证明所构成的表达方式,是公理化的演绎体系;而中国传统数学从实际问题出发,经过分析提高而提炼出一般的原理、原则与方法,最终解决一大类问题,是机械化的算法体系[6]32。中西两种数学体系“旨趣迥异,途径亦殊”[6]200。中国古代不但存在着与古希腊数学体系完全不同的独立发展的数学,而且中国古代数学的机械化算法是世界数学两大主流之一,为世界数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如果说库恩的反辉格史观使他突破了实证主义的科学观,那么吴文俊的反辉格史观则使他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数学史观,对世界数学史的重建作出了积极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吴文俊并没有就此止步。吴文俊是一位数学史学家,更是一位现代数学家,在他看来,“我们崇拜中国传统数学,绝非泥古迷古,为古而古,复古是没有出路的。我们的目的不仅是要显示中国古算的真实面貌,也不仅是为了破除对西算的盲从,端正对中算的认识,我们主要的也是真正的目的,是在于古为今用”[6]43。所谓“古为今用”就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数学思想通过现代人的继承、发扬和创新,在新的时代发挥新的作用,实现新的价值。吴文俊正是本着这样的想法,在吸收西方数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数学的特点和当代世界潮流做了一番考查,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这两者的契合点。当代世界在“第三次浪潮”的冲击下进入了以计算机为重要载体的信息时代。而我国古代数学的精髓是一种机械化的思想和方法,正好与时代的要求和状况相符合。汉初的《九章算术》就详细说明了开方、立方的机械化过程,《九章算术注》中也记载了几种机械的消去法及其详细的机械化算法过程。至宋代,发展到高次方程求数值解的机械化算法。因此,中国传统数学中大多数的“算法”可以无困难地转化为程序并用计算机来实现。受到这些思想的触发,又结合几十年来在数学研究道路上探索实践的回顾与分析,吴文俊最终形成了数学机械化的思想,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机械化方法,并成功地在计算机上进行了具体实施,对数学机械学这门新兴的学科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导源于我国传统数学的思维方式的数学机械化理论,为中国数学的复兴开辟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是当今中国自主创新的成功范例,成为开拓中华科学自主创新之道的先驱。
三、吴文俊对库恩反辉格史科学观的完善和超越
吴文俊提出的中国古代数学的研究原则与库恩反辉格史的科学史观在思想本质上是一致的,在面对过去的科学时,他们都反对用现代眼光研究过去,主张恢复文本的过去读法。可以说,库恩和吴文俊在处理和研究科学史问题时,殊途同归地反映出了“反辉格史”的科学史观。然而,相比较而言,吴文俊关于中国数学史的研究方法还在某些方面完善甚至超越了库恩反辉格史,进而对解读并反思库恩的科学史观点及其科学哲学思想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和思想价值。
1.从西方科学范式的“时间相继”到地域传统的“空间独立”
库恩反辉格史的科学史观的提出,对科学史研究有很大的启发性。但不可否认,库恩选取的科学史素材和案例没有脱离西方科学史的范围,强调的是在时间的跨度内西方科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不同传统及科学形态的多样性。而吴文俊反辉格史的数学史观则突破了西方框架内的辉格史科学史观的应用,将库恩的反辉格史观向前推进了一步,在对待中国古代数学的问题上,反对以西释中,以今议古,即不仅在时间跨度上反对用现代数学研究古代数学,而且在空间跨度上反对用西方数学研究中国古代数学,因而在更大的两种科学文化传统内自觉地实践其反辉格史科学史观。这可以说是吴文俊对库恩思想的补充和推进,更为我们全面理解库恩的科学史观提供了启示。
由于库恩是在研究西方科学史的过程中提出新的阅读方式,进而形成反辉格史的科学观的,而这为他提出范式概念及科学发展模式做了思想观念上的准备。因此,库恩的范式理论必然无法逃脱西方科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在提到范式时,常常以“新范式”、“旧范式”这样具有明显时间先后推进关系的词语。可以说,库恩的范式理论为我们展现了在历史时间序列中,西方不同科学模式此消彼长相继推进的纵向发展过程。而吴文俊则通过对中国古代数学的反辉格史研究,证明了在古代中国存在着与西方完全不同类型的数学——西方数学是公理化演绎体系,而中国传统数学则是机械化算法体系,而“在数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数学机械化算法体系与数学公理化演绎体系等多次反复互为消长,交替成为数学发展中的主流”[6]53。也就是说,西方欧式体系和中国传统数学是沿着不同的思路、经过不同的轨迹在空间上的相对独立发展,从而形成不同的研究传统。因此,按照库恩的范式理论,吴文俊向我们展示了在中西两种文化传统中形成的两种不同的数学范式,为库恩的范式理论研究提供了更丰富全面的内容。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将库恩的不同范式的“时间相继”扩展为“空间独立”的理解后,我们承认中西两种数学是两种不同的范式。而库恩认为范式具有不可通约性,即不同范式之间不可交流或对话,范式的转换是不能用逻辑合理性来解释的。与库恩这一思想不同的是,吴文俊的数学机械化理论恰恰证明了中西两种数学的“等价性”,并找到了数学的公理化演绎与机械化算法会通与换算的可能与方法。这是因为,中西两种数学范式恰好对应了数学两种脑力劳动的形式——数值计算和定理证明,而数值计算的特点是简单但过程繁琐,刻板而枯燥,其原因是已经机械化,而定理证明则较难但过程简易,灵活而美妙,这之中要靠直觉、洞察、经验及其他模糊不清的原则,其原因还没有机械化[6]359。数学的机器证明的目的就在于把巧而难的证明,化为繁而易的劳动。而吴文俊的数学机械化思想导源于中国古代数学的机械化算法,机械化思想恰恰是用中国古代数学那种繁而易的机械化算法体系来代替西方的巧而难的证明,为公理系统与数量关系之间的沟通作出有益的尝试。因此可以说,吴文俊数学机械化理论的成功找到了中西两种不同数学范式之间交流或对话的可能与方法,这为库恩所讲的范式不可通约性找到了方法论上的可能突破。
2.对库恩反辉格史观的反思和完善
从吴文俊反辉格史观及在此观念下所使用的恢复历史的阅读方法以及受中国古代数学机械化思想而进行的理论创新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一方面吴文俊主张应该“撇开西方数学的先入之见”,设法复原我国古代数学的真实面目;另一方面,吴文俊的数学机械化理论的建立有力地指出复原中算的真正目的不是复古,而是“古为今用”。意即在吴文俊实际所做的历史研究工作中,可以看到存在着两个同时发挥作用的观念,其一是历史观念,在此观念的指导下运用反辉格史的方法对中国古代数学进行研究;其二则是现代观念,意即对古代数学的研究最终是指向当下的。
吴文俊的工作不禁让我们反思,在对科学史做历史研究时,能否真的如库恩所主张的那样完全“撇开他所知道的科学”而再现历史?答案是否定的。由于反辉格史的科学史观要求史学家假装“当下并不存在”[3]98,“理想上要想像自己是处于过去的观察者,而不仅仅是关于过去的观察者。这一虚构的逆时旅行就有了这个结果,即史学家—观察者的所有来自后来时期的记忆都被清空了”[3]97。而这样的假想是存在问题的。首先,科学史家不可能在某种绝对意义上超越当下,完全摆脱他自己的时代的影响从而避免使用当代标准,他总会无法避免地带有某种当下的视角去做历史的回溯。其次,即便真的能完全做到超越当下,那么科学史就会退化成一部与当下毫无关系的“收藏古物的历史”[3]100。然而科学史家不应当仅仅是古物收藏家,他还应该是一个“真理史学家”,也就是说,“他所探寻的真理不是关于历史的真理,而是历史中的真理”[3]100。
因此,尽管反辉格史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历史的客观性,同时也是必不可少的方法论入门和辉格史的矫正剂[3]114,但不得不承认极端的反辉格史观是不可能也不可取的。作为一个科学史家,积极的研究态度应该是,“为了恰当地评价过去,科学史学家必须知道当下;他必须尽全力学习他打算撰写其历史的那门科学……正是在科学史家入门了解科学的现代性的时候,他还能够揭示科学的历史性中更多、更微妙的细微差别。现代性意识和历史性意识在这儿是严格成比例的”[3]99。
通过分析吴文俊中国古代数学反辉格史的研究及其所取得的理论创新的一系列成果,我们发现,科学史学家在实践中并非简单地面临着辉格史视角还是反辉格史视角的抉择。因为“通常两种因素都应当存在,它们的相对权重取决于所探索的特定主题和探索目的”[3]115。在历史性和现代性之间,在传统与创新之间,应该保持一种库恩首倡的“必要的张力”。吴文俊基于中国传统数学的现代创新的成功案例为我们反思和完善库恩的反辉格史观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对于当前科学编史学中的实在论与建构论之争无疑也具有很好的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