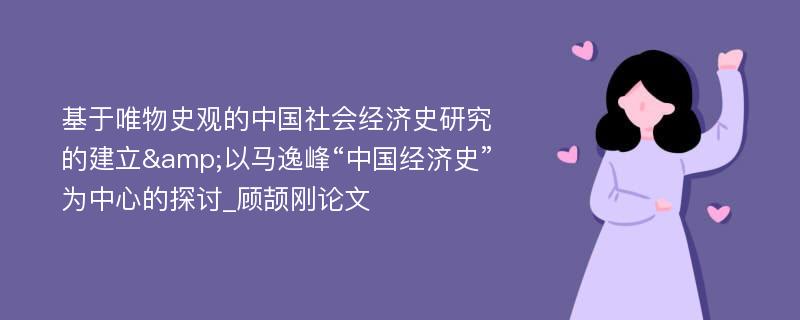
唯物史观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之建立——以马乘风《中国经济史》为中心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唯物史观论文,经济史论文,中国论文,中国社会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20世纪学术史上一个重要门类的社会经济史,其产生和发展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重要媒介的,其体系、内容、特征乃至成败得失皆与唯物史观相关联。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论域几乎是唯物史观派学者的天下。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探索中国社会性质的社会史大论战直接催生了社会经济史。尤其是1933年《读书杂志》停刊后,由论战开启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一发而不可收,焕发出勃勃生机,并呈现如下三方面的特征:其一,开始从政论向学术过渡。社会经济史研究与政治斗争脱节,不再与某一党派的政治路线密切配合,而以求真为本位,偏重学理的探讨,遵循学术的规则。其二,从理论方法的激辩转向史料的搜求整理。如何运用唯物史观把握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确定各阶段社会性质是论战时期各方关注的焦点,论战退潮后由虚入实,各种经济史料的搜集、整理被视为当下急务。其三,专题研究取代了通观泛论。笼统讨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形式缺乏必要的学术基础,难以产生实效,按部就班的常规性断代专题研究遂成为社会经济史领域的主要工作形态。以往学界对193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上述变动有所涉及,但目光多聚集于人多势众的陶希圣“食货”一派,对其他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和作品缺少必要的关切。本文即拟以民国时期著名经济史学者马乘风①为个案,从“食货”派之外的另一视角窥探中国经济史研究由草创到成型的曲折历程。 马乘风以运用唯物史观研治中国经济史而闻名。至于马乘风因何而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结缘,由于缺乏关于马氏早年读书和师承情况的详细材料,目前尚不得而知。但可以推断,马乘风乃是被当时的新思潮所席卷而倾向唯物史观。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实验主义遭到厌弃而马克思主义风靡一时。马乘风当是受到这一风气的熏染。此其一。其二,河南同乡、左派学者嵇文甫大概对马乘风的思想观念有所影响。此时,马乘风信从唯物史观主要出于学理方面的原因,而与党派背景、政治信仰无涉。 马乘风的代表作是《中国经济史》。此书1935年由中国经济研究会出版一册,1937年增订为两册,由商务印书馆再版,经大学教材编审委员会审定,作为大学经济学教材。此书第一册叙述殷商至秦末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第二册则专论两汉经济史。这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撰写的中国经济通史。1972年后再度增订,延伸至唐代,编成四册,达百万字,1980-1984年由台湾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由于本文关注的是中国经济史学的早期发展,下面的讨论以民国时期的版本为主②。 一、关于公式主义的反思 马乘风的《中国经济史》是社会史论战的直接产物,“带着论战时期的战斗气氛”③。其论战色彩集中体现在“诸家批判”一编中,涵括“与李麦麦论春秋时代之阶级斗争”、“与陶希圣论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与叶青李麦麦论墨子所代表的阶级问题”、“顾颉刚古史辨批判”、“与王宜昌论治史方法及中国之用铁时代”五个方面。此外还有对于马札亚尔水利社会说的辩驳等。这些内容都是论战的延伸。④有书评称:马著“在贫弱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今日,总算是一部比较可看的书;单以前三篇而论,大体上没有很大的错误,这一方面由于马君方法论的握紧,同时得力于过去几年间的论战亦复不少。”⑤由此可见马著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密切关联。 以《读书杂志》为主战场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在思想文化领域激起了巨大波澜。然而,横空出世、根基浅薄的社会史论争学术上的流弊很快显现出来。论战参加者大多是理论先行,但在理论方法的运用上又陷入严重误区。马乘风的《中国经济史》上承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余波,对论战进行了学风和方法上的反思。马乘风感慨道:“新近一般研究历史科学的人,对于新兴的历史科学只知道一点皮毛,到运用时连这一点皮毛也保不住;对于旧有的历史资料又舍不得出一番苦力,作一番整理融贯的功夫,所以没有确定的把握,坚决的认识,明白的主张,把史料和理论胡乱一凑敷,便动笔抄呵,写呵,结果,理论被歪曲得不成样子,史料被割裂得不像东西,你问他写的什么,说的什么,一百个回答是有一百个‘莫名其妙’。”⑥这指明了论战参加者在理论方法和材料两方面的失足。 社会史论战的最大弊病在于公式主义。论战参加者提出五阶段论、三阶段论、四阶段论等各种社会发展的公式⑦,简单移植套用于中国历史进程,这五花八门的公式成为论战时期的一道奇观。社会史论战的要角郭沫若日后坦承道:“我初期的研究方法,毫无讳言,是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的,我是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主义的公式,往古代的资料上套。”⑧马乘风反对社会经济史研究中迷信公式的做法,主张“不以多样的社会形态迁就简单的公式才算是最进步的史学家的态度”⑨。他对一些学者墨守五种生产方式学说表示质疑:“‘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构成社会经济发展之相关的诸阶段’。这样的历史划分是否完全正确,到现在成为一个重大的疑问。”⑩在马乘风眼中,信从唯物史观并不必然要遵循其生产方式演进的程式和铁律。 典型的例子是关于奴隶社会问题的认识。由于对社会发展公式的执迷,许多论战参加者将奴隶社会视为中国历史发展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马乘风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奴隶社会问题“决不是随便在马克斯、恩格斯、考茨基、蒲达格诺夫诸人的文献上找出一个划然不同的‘定义’所可解决的,把着一个‘定义’去读历史,往往把历史割裂得支离破碎,把人类的活动舞台变成瓦砾的堆积物了”(11)。马乘风专门对当时奴隶社会论的代表郭沫若提出批评:“统读郭君大著,似对于西周时代为‘奴隶制’抑为‘农奴制’,并未加以仔细的考究,不过在他的心目中以为封建制度之前氏族制度之后少不了奴隶制度这一段落,所以顺水把‘西周’推到‘奴隶制度’的泥坑里,这是根本颠倒的事。我以为先把中国的历史考究确实,至于合不合公式,那倒是小事。”(12)也就是说,史实的探查、确认是梳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前提和基础。 公式主义者强调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和一般性,自然导致了对中国历史自身特殊性的无视和抹杀。“向来许多关于中国社会史或经济史之研究,常常只注意到一般性而忽视了特殊性。”(13)马乘风对此非常不满:“大家都是株守着几段简单的公式,把历史往里边套,实际上,简单的公式是否足以应用于一切人类的历史而完全妥当,中国的历史在世界史的一般进行中除了共同点之外,是否又有其差异点,于此,大家全无活泼的考虑,这一种毒害,最足以妨碍我们的研究业务之前进。”(14)比如,在初期封建社会的佃农问题上,王宜昌“死守着空浮的公式,硬要把中国和希腊罗马一样炮制须先由奴隶制度再经外族的化合然后混合成佣佃耕作制”(15)。 唯物史观被当时的社会史论者视为最先进的科学理论,在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运用上,马乘风持一种相当开放的态度,以马、恩为正统,又不局限于马、恩原典,对后来不同诠释者的各种理论观点予以充分吸收。普列汉诺夫、波格达诺夫、山川均被马乘风认作“历史唯物论的著名学者”(16)。 马乘风称马克思恩格斯为“世界最负声名之历史学家”。他说:“马克思等在历史领域内所给予我们诸多的教训是最值得夸耀的,但是他们的话决不是完全没有再商榷的余地的,他们的话不是完全适用于为他们所不十分了解的社会环境之内,他们的话不是由空想而来,乃是由各种各色的社会生活中之具体的事实归纳而来,因之我们应当从多方面的为他们所未曾研究到的社会环境中,找出丰富的资料,把他们的理论加以补充,发挥或纠正。”(17)他还将恩格斯作为公式主义者的最好教员:“如果遇着了一个机械的公式主义者,最好请恩格斯去纠正他。这一位博学的历史家常常是细心的去分析各地各代的历史,他的讲话极有分寸,他不曾以一个定型化了的框子去削足适履的去修斫历史,他能在各地各代的历史中指出其共同点,但是他又不抹杀其相异点,他是从史实中建立其理论,而不是从理论上修改历史。”(18) 除马、恩外,俄人波格达诺夫对国内唯物史观学者影响甚巨。中国学者称波格达诺夫的《经济科学大纲》为一部经济学名著,并谓:读过此书,我们才能“真正了解社会底经济现象”,才能“真正了解社会底演进过程”。它对中国人尤其有益,“可以根据它来研究中国历史”,也“可以根据它来研究中国现状”。(19)此书几乎成为论战时期一些学者研究中国社会史的蓝本。陶希圣的社会史研究方法、“商业资本主义”说即滥觞于此。马乘风的《中国经济史》多处征引此书。波格达诺夫认为,奴隶制度与农奴制度的根本差异,不在于榨取程度及个人自由程度如何,而在于从属阶级在生产过程中所占的地位。据此,结合国语上的有关记载,马乘风认为西周是农奴制度而非奴隶制度(20)。 德国学者亨利希·库诺的论著也成为马乘风经济史研究的理论来源。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库诺的《经济通史》第一卷。吴觉先在译序中称库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现代有名的经济学者兼人种学者”,其书被誉为“经济史中空前的杰作”,“他撇开旧来的一切虚构,把比较人种学作为处理的对象,根据极丰富的事实材料,从各自然或半开化民族之自然环境及劳动工具出发,阐明各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并进而画出他们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的、法律的形态之本来面貌来,使(足以帮助我们了解文化民族古代生活情形的)现代的落后民族的经济状况,历历如在眼前”(21)。库诺用墨西哥、斐济岛的社会制度和经济组织说明奴隶制并非一个必经的阶段,异民族的征服兼并未必产生奴隶社会(22)。马乘风由此推论商代是氏族社会末期,而非奴隶社会。 俄人库斯聂的《社会形式发展史大纲》为中国学界认识商业资本问题提供了有力依据。此书的任务“就在应用历史唯物论的方法,在资本主义前期的一般社会发展上来研究原始的社会学”,“基本趋向就在研究现代社会形式的发生”。(23)作者舍弃各民族国家的差异而一般性地考察原始社会、氏族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初期的社会发展史。马乘风结合库斯聂关于商业阶级的地位与国家政体的关系的论述断定战国时代绝非商业资本占主导的时代(24)。此外,他还引用商业资本与封建经济可以长期共存的观点来反驳陶希圣的意见(25)。 德国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础》在中国左翼学者中间也流行颇广。中译者自序称:此书“一方面,成功了以唯物论分析一种西方文化起源之企图,他方面,却证明了唯物之观点实为任何历史的唯一可靠的研究方法。”(26)是书第二篇为“罗马帝国时代的社会”。马乘风将关于罗马社会采矿业的描述与中国的战国时代相比较,观察经济性质的变异(27)。他又参照考茨基描述的西班牙银矿中奴隶辛苦劳动的情形来推测战国时代的奴隶的处境(28),还以考茨基提到的希腊罗马通过战争手段获取奴隶的现象,与两汉时奴隶来源相比较,断定当时缺乏出现大规模奴隶劳动的基础(29)。 此外,德国莱姆斯的《社会经济发展史》(李季译,亚东图书馆1929年)、法国拉法格的《财产进化论》(李希贤译,商务印书馆1925年)、日本上田茂树的《世界史纲》(柳岛生译,上海创造社出版部1928年)等马克思主义论著也成为马乘风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依据和参考。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较少从本土传统学术中寻觅资源,而更倾向于从域外同行那里汲取灵感。国际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社会经济史论著成为中国学者进行相关研究的重要凭借。当时中国的唯物史观学界,尚未定于一尊,各种学说争奇斗艳,呈现出相当大的自由度。尽管马克思主义一派内部存在正统和异端之分,这种区分随立说者政治上的荣辱沉浮而变动。但当时国内学者较少受这种政治上正邪之分的羁绊,对各派观点往往博采广收,择善而从。这就造成了唯物史观的多元化局面,打破理论上的封闭状态,使通过唯物史观引入更多的经济学理论成为可能。 二、重视史料真伪和材料扩充 从一味强调理论方法到重视材料是社会史论战高潮过后唯物史观史学的新动向。社会史论战时代,参与者多将理论方法上的讨论作为头等大事,而将文献材料问题视为小节。当时的唯物史观学者多属于冯友兰所谓的“释古”派:“往往谈理论太多”,“是谈哲学,而不是讲历史”;“往往对于史料,毫不审查,见有一种材料与其先入之见解相合者,即无条件采用。至于与此相冲突之材料,则置之不理,并不说明何以置之不理”。(30)时人意识到,撰述一部贯通古今、包罗万象的经济通史尚非其时,当下应“多作史料的考证与专题研究”(31)。当时一般学院派经济史研究尤重史料整理,主张“对历代经济史实,纯为客观的整理叙述,不必急为论断”(32)。陶希圣及食货派的经济史研究也以史料工作为优先。 在此风气之下,以理论为中心的唯物史观学者也作出了适当调整。马乘风力图克服社会史论战时期的弊端,公开承认史料考证的必要性:“汉学家的治史方法,虽然有许多地方,不能令我们同意,但是,他们对于史料的审思明辨的考证,却是最值得领教的一种方法”(33)。 马乘风对经济史研究所用材料的真伪十分留意。在考察西周土地分配时,他首先意识到厘清文献问题为先决条件,没有盲目信从《周礼》,而以《诗经》、《国语》依据(34)。他认为,《周礼》关于井田制度的记载,不过是“在书传上搜集些关于土地的术语,而以按级进位的数字补缀之”(35)。关于周代的井田问题,马乘风主张应以《孟子》朴素的记载为准绳,而不能轻信后世不断发挥引申的井田论:“时经千余年之久,一般笃古守旧之士,对于井田制度,只有迷信,没有批判,只有高筑,没有损毁,于是井田制度愈来愈完全,愈修愈美丽,正因为这样,所以愈加减失其在历史上之素朴的面目”(36)。 马乘风严厉批评王宜昌的治史方法,指出“无批判的引用古书之危险性”。他指责王宜昌迷信古书,对于古人的话无条件的相信,对于古文古字无限制的附会,对于伪书伪事无批判的拿来作证,在治史方法上比汉学家又后退了一步。王宜昌误信《管子》、《越绝书》、《山海经》的记载,不问史料是否可靠,只跟着莫尔干的指点去附会,把莫尔干所指各时代的特征,一一在中国古书中凑付出来。要确立殷代已经用铁的结论,需提供强有力的凭证,不能单靠伪书上的一字半语(37)。他称赞郭沫若在论诗书时代的中国社会时,“先把史料的来源问题弄清楚,郭先生这样的谨慎小心的去剖析史料,较之王先生无批判的附会瞎闹,高明万倍”(38)。 在当时主流学风的影响下,一方面,马乘风注意史料证据的准确性,采取审慎态度;另一方面,他还尽量扩充材料来源,最突出的是利用甲骨文研究上古经济。马乘风说:“对于商代社会经济性质的认识,为两种困难所限制……第一是史料上的困难,文献记载缺乏,甲骨文字的出现会予我们以若干便利”,但研究尚不充分(39)。社会经济史学者对甲骨文的使用自然不拘于文字学。他在书中指出:“自从对于甲骨文的研究发动以后,关于商代之农业情况,有提供了不少的研究资料。在甲骨文中,颇有不少关于农事一类的文字。”(40)他主要利用甲骨文来认识商代的农业耕作工具、耕作技术、劳动组织,着重分析了甲骨文中关于奴隶劳动的记载,否认奴隶劳动在商代农业生产中占有主导地位。在论述商代的渔猎、工艺制作及商业交换、氏族及氏族联盟时,也取用了不少甲骨文材料。 由此,唯物史观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路径发生了重要转变,史料工作成为基础和命脉。对于当时争议最大的奴隶社会问题,马乘风提出一种切实的解决途径:首先把各朝代的奴隶史料搜集充实,再把奴隶劳动与其他的劳动形态加以比较,确定在中国历史上有无以奴隶劳动为基本的生产方式之划然的地位,如果有的话,还须分别出中国奴隶社会导端于何时,正盛于何时,衰没于何时,从多方面加以比量,证据愈多愈好,这“虽是一条笨路,却是可靠得多”(41)。他以“从两汉的奴隶史料中看两汉的奴隶地位”、“从生产过程上论两汉之奴隶地位”、“从剥削形态上论两汉之奴隶地位”、“从人口问题上论两汉之奴隶地位”、“从希腊罗马的基点上论两汉之奴隶地位”几个小节,从史书中出钩沉出大量史料,花费约5万字的笔墨,对两汉奴隶问题进行了爬梳清理。 史料证据的充分与否成为考量相关研究的首要标准。关于汉代是否为奴隶社会的问题,马乘风认为,持肯定意见的郭沫若、王宜昌、陶希圣、叶青等关于奴隶社会的议论,“都是以简短的体裁表露,没有在中国史书上拿出充分的证据给我们看,而且他们又多是匆匆忙忙的在研究了一朝半代的时候,即发表其对于中国整个社会史之意见,这种办法,危险性非常之大”(42)。而持否定态度的《现代史学》杂志上陈啸江的《西汉纯经济过程的解剖》、王兴瑞的《中国社会史细分派的批判》,《食货》半月刊上武伯纶的《西汉奴隶考》“比较着能够举出实际的史料,以讨论中国奴隶社会时代一问题”(43)。马氏本人显然是认同于注重史料的否定派的。 马乘风在经济史材料上的努力劳作获得学界同行的认可和称赞。嵇文甫说:1935年出版的马乘风的《中国经济史》,“一方面带着论战时期的战斗气氛,而另一方面在搜集材料上也很下些功夫”(44)。顾颉刚署名的《当代中国史学》评价马著“材料相当丰富、见解相当正确,为不可多得之佳著”(45)。 马乘风固然重视史料工作,但并未倒向史料主义,对理论方法也毫不轻视,时时不忘理论探讨,与当时的主流学派存在明显的分野。他对论战的反省正是在建立在对史料考据之风进行批判的基础上的。《中国经济史》初版专设一章检讨顾颉刚及其“古史辨”派的工作。书中对在学术界获得盛名的“古史辨”派表示不满:“顾先生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毫无进步的见解,还是死守着清代以前的学者传统的方法,不过是受了胡适的宁可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这一错误见解的哄动,多作了几篇翻案文章罢了。”(46)“顾颉刚及其同盟者,拿着汉学家粗陋的木棒石锥,打着有名无实的‘科学’招牌,目空一切的在中国学术界上乱吹,使我愤怒,成千成万的大学生在顾颉刚《古史辨》的体系的影响之下,无批判地接受一切陈朽的观念及其破片,使我寒心。”(47) 同时,顾颉刚等的治史眼光和问题旨趣也令马乘风颇难认同。马乘风主张,研究历史“要把眼光投放在整个的社会生活上,从多方的试探,求得一个‘大致如此’的轮廓,然后再作细密的工作,求其更加真确。”(48)而《古史辨》提出的问题,都是些小问题、枝节的问题、头发梢似的问题,即使解决了也不能明了古代社会的问题;而“我们所要知道的,是古代社会生活的全部,是古代社会的大轮廓,是古代社会的整个问题。”(49)“当我们分析历史的时候,就不能不从大处着眼,我们必须取出历史长流中的若干大的段落来看,从各主要的事象上,加以仔细的比较,以求出前一段与后一段之不同的征点何在。如果我们单盯住一个极短的时间来看,我们将永远难以求出此一短时期之历史的特征何在。”(50)马乘风等唯物史观派学者力图把握历史变动的大关节、大脉络、大方向,而顾颉刚及古史辨派却一心钻求古书造伪的蛛丝马迹。 马乘风将“古史辨”派治史路线视为歧途:“顾颉刚将古书、古史材料、古史混为一谈”,对科学方法、历史方法完全无知,“只是走着旧史学家的老道,在古书上咬来嚼去,一训二诂,作那种无花果的徒劳”。(51)“对于古代社会之完全的盲目,对于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之孤陋无知,徒欲于字里行间,挑一字之伪,而呶呶然妄辨古史,那就无异于破坏中国古史,火烧中国古史,刀斩中国古史,不但新的成绩拿不出来,而且连原有的几微稀疎之古史轮廓,亦岌岌不可终日矣”。因此,“我们非站在新的唯物论的见地上,对于顾颉刚路线加以无情的排除不可。”(52)顾颉刚及其“古史辨”派缺乏新史学的视野,不考察社会经济的变动,而专注于从古书中吹毛求疵。其与唯物史观派学者是疑古与释古、考据与社会史两种路数的根本对立。更可贵的是,马乘风对古史辨派和社会史论战派进行了双向反思,对整个史学界的风气痛下针砭,力求寻找一条合理路径。 三、从社会形态史到社会经济史的转变 社会史论战后期,社会性质和社会形态史逐渐落地生根为社会经济史。学者已认识到:“为欲瞭解中国社会的本质,而从中国经济史着手,实为正确的方法。”(53)时在中山大学的陈啸江坦言:“近来我国学人,过分重视社会发展形式论,研究者每以公式为前提,而以事实嵌入其中,其结果则成为公式之例证史而非真是之社会经济史。”(54)另有论者称:“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之研究,为一般人认为所迫切需要的一门学科,数年来,曾有不少的学者,企图以新的史学方法整理中国历史,但空论多而实际的探讨少,零文多而系统的叙著少。”(55)1931年陶希圣编著出版一部《西汉经济史》,内容简略,篇幅短小,仅3万言。1934年12月《食货》半月刊创刊和稍后成立的食货学会,催动了社会经济史的专题研究,关于各时代、各方面的论文纷纷涌现,但贯通性、综合性的论著尚付诸阙如。而1935年马乘风《中国经济史》一书的问世,弥补了这一空白。 论战时期,一般所谓社会史基本是社会形态发展史,社会形态问题是讨论的中心,也是出发点和归宿。社会史的主要任务是考察社会形态的演进,进行定性分析,而非描述普通的经济现象和经济活动。研究者的注意力几乎完全围绕社会性质和社会形态的确定而展开的,各种理论、模式争长竞短。论战高潮过后,社会史出现转向,经济史成为社会史的基础,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全面系统的考察开始出现。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的出版标志着唯物史观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体系初步确立。马著既包括对农业、工业、商业等经济部门的考察,又涉及生产、交换、分配等各环节,同时兼顾到阶级关系、政治结构、战争军事等制约经济发展的要素。这种结构和内容的布置安排,奠定了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格局。除了作为主体的农业、工业、商业外,物价、货币、人口等与社会阶段划分关系不大的内容进入社会经济史的视野。与论战时期鲜明的问题导向不同,这些都属于社会经济史的常规研究。 例如,马乘风关于两汉时期物价问题的发掘探究。作者指出:“这一个题目关系于国计民生者至巨,但是,当时没有系统的记载,所以我们无从窥知其详细的全貌,只有从各种典籍的零星断片中,掘拣敲证,以冀归纳出其几微的轮廓而已。”(56)书中依次论述了两汉时期的粮价、地价、金钱兑换价、工价、牲畜价、酒肉价、盐铁价、缣纨价、奴隶价、饭价、珠宝价、旅馆价等。再如,作者对货币制度和货币使用的考察,以“金属货币之普遍”一小节讨论战国时代的货币使用情形(57),专设一章论述两汉的货币制度。(58)此外,马乘风还考察了汉代人口政策及人口消长、人口分布状况(59)。生活史也进入了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范围,书中专门叙述了春秋时代的衣着、食用、住居、行具、武器、玉用、杂具、娱乐等(60)。 除追求内容上的周全、系统外,马乘风的经济史更以细密具体的考求取代此前粗枝大叶的论述。他论及西周时代农业时,罗列当时各种农产物,如黍稷、稻、麦、豆、谷粟、麻等;谈到农庄副业时,又举出园圃作物。在涉及战国以后农业生产方法的进步时,又对耕具、灌溉方法、肥料、土性、时节、劳动力一一进行分析。关于汉代农业生产问题,依次论述了生产工具、生产动力、劳动编制、耕种方法、灌溉事业、生产量等。可谓不厌其详,细致入微。 李大钊曾指出:马克思将私有制社会“经济的构造都建立在阶级对立之上”,“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内”。(61)因此,在唯物史观的经济史著述中,阶级对立和阶级关系成为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除纯经济过程的细致考察外,马乘风此书对各时代由经济关系而产生的阶级关系进行了重点分析。作者指出:除原始共产社会的时代外,人类历史从很早以至今日,都常因社会分化发生冲突,易、书、诗三经中充满了阶级悬殊的记载,苦乐不均的叫喊(62)。他考察了西周时代的“阶级分化与剥削关系”,贵族集团与农奴集团的生存境况。在论及春秋时代时,又对贵族与农民的生活处境作了揭示,认为这反映了“当时阶级营垒之显明的对立”(63)。他描绘了战国以来阶级斗争新局面的展开,包括新兴地主与贵族势力的斗争、商人对贵族及新兴地主的斗争、雇佣劳动佃耕与自由农民之出现、强制奴隶和买卖奴隶的出现、智识生活者的出现、流氓无产者之出现。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马乘风对古代社会阶级关系的研究采取了历史主义的立场,并未一味拔高被压迫阶级,尤其对当时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的起因和作用有着清醒认识(64)。 在唯物史观的影响下,学者多认同经济史“不仅以检讨人类物质生活各过程之经济现象为满足,在社会进化之过程中,阐明社会基础经济制度之沿革,经济要素与其他社会要素政治法律宗教之关系,亦为其重要任务”(65)。马乘风的经济史研究即体现出这样的总体史意识。他以经济问题为主干,将与之相关的政治结构、社会意识等因素都纳入讨论的范围。马乘风认识到:“在纵的关系上来说,经济是政治社会组构的基础条件,在横的关系上来说,政治社会组构,又是经济活动的主观条件,这两者之间,存有密切难离的统一关系,不应当机械的把某一部分轻视。”(66)“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基础是一个客观的物质条件,而政治活动却是一个主观的‘人’的创造条件,人类的历史是单靠客观条件不能成事的,它必须把人的活动参加进去,才能把历史推动起来。”他还批评道:“如果机械的来把经济基础死板板的置在政治行动的头上,忽视了两者间之有机联系,好像以为政治行动如同树叶一般飘来飘去对于树干毫无关系似的,那简直是最不长进的人,最蹩脚的学者。”(67)第一册第二编第七章考察了西周时期的国家结构,叙述了国家机构在经济上的任务(68)。他尤其重视政治良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正反作用。在清明的政治下,政府能奖导生产、轻敛薄赋,社会生产就会徐徐前进;反之,在恶劣的政治下,政府专以搜刮民众为能事,社会的经济财力尽被腐蚀以去,民众日趋穷途,无余力于生产改造。所以政治的恶劣,即是经济的灾害;政治的不良,也足以大大地打击经济的进步(69)。此书重点评述了战国秦末恶劣政治对经济的破坏、王莽时期政治混乱对经济的破坏。 战争是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马乘风非常重视战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马乘风所论述的战争包括内外两方面。内部战争主要是农民暴动,对外战争则是与边远民族的军事冲突。马乘风论述西周时期“战争之经济上的任务”,认为战争是“防守已得的财富并创造将来的财富的一种经济手段”(70)。但战争的破坏性是主要方面,他分别介绍了楚汉之争时期的农民暴动、西汉末年的农民暴动(包括农民军与王莽军、农民军与地主军、地主军与地主军之间的斗争)对社会经济的严重摧残,分析了汉代对匈奴和西南民族的战争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以及对社会经济的拖累(71)。 马乘风还将社会意识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变量。当时部分唯物史观学者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有着重大误解,认识流于片面。马乘风则拒绝将社会意识当作次要的历史因素,反对将重视社会意识贬之为“观念论”。他强调:“不要忘记了人类的‘行动’是先要通过于‘意识’的。”(72)“精神生于物质”,“精神的力量”有时即是“物质的力量”,“精神的武器”即是“物质的武器”。为纠正流行的错误认识,马乘风的经济史研究对社会意识因素予以格外的重视。在谈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发展时,他特别指出当时当时各国之间弥漫着一种竞争意识:为加强战争实力,各交战团体间充满了一种互相竞争的活泼精神,大家都是各自整军经武、秣马厉兵,奖励生产,重视农工,这样的交互观摩,如磋如琢,其对于经济之推动亦非浅鲜(73)。在“拜金主义之人间世”一节中,他专门描述了对周至秦末的社会氛围: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拜金主义泛滥于世间,昔日的三纲五常、礼义廉耻被弃之如敝屣,金钱名利成为世人追逐的目标(74)。 经济史研究的一般方法也得到更广泛的应用。统计是经济学的基本方法(75)。马乘风制作使用了大量的统计图表。他用“前汉郡国户口表”,“后汉郡国户口表”(76)说明两汉时期的人口分布情况。论及汉代黄金货币时,则引用马非百的“西汉赐金一览表”和“西汉馈金一览表”,并加以补正(77)。他又用“后汉赐金一览表”、“后汉馈金一览表”(78)、“东汉赏赐物品一览表”、“东汉赏赐钱货一览表”、“东汉馈送物品一览表”(79),与西汉对比黄金货币的使用情况。马乘风还依据两汉时期户数与口数的统计,推断此时为小农社会(80)。这些统计显然是通过对大量经济史料进行搜集整理而完成的。此外,马乘风还对武伯纶关于西汉奴隶数量的计算提出质疑(81)。与此同时,马乘风初步运用区域分析的方法,不仅注意经济发展的时代差异,还留心到空间差异,尝试分区域讨论经济史。书中考察了战国时期各经济区域之不平衡的发展,各地自然环境和物产的不同,齐、楚、秦、周鲁、燕赵地区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情况和所占比重(82)。这种种方法工具的运用,也使经济史研究化虚为实,走上正轨,学术含量大幅提升。 总之,马乘风的《中国经济史》一书,塑造了唯物史观的中国经济史的特色和风格。与一般经济学者的作品不同,它注重总体观念,以经济问题为中心,涵盖与之相关的政治结构、社会意识和自然条件等因素。再者,《中国经济史》既是社会史论战结出的果实,又是对论战进行深刻反思的产物。此后唯物史观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风气和面目发生了显著变动,即使是通论性作品,也不再凌空蹈虚,以驰骋议论为能事,而是立足于扎实细密的研究基础之上。 这里需要补充一点,以往学界通常将郭沫若、吕振羽等的相关研究作为唯物史观派经济史的代表(83)。但是,郭、吕诸人始终坚持理论先行,遵从政治经济学范式,社会形态和社会经济性质一直是核心和焦点,社会经济的具体问题居于从属地位,因而,其论著与其说是社会经济史学,不如说是社会经济史论(84)。简言之,郭、吕等正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经济史研究基本仍停留在社会史论战阶段,已不足以反映论战消歇、学风调整之后唯物史观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的新面貌了。 1930年代中国社会发展史向社会经济史的调整转向,意义重大,最显著的是推动经济史学融入民国学术主流,为一般学院派所接纳。当社会史论战硝烟弥漫之际,主流学界和多数学院派学者基本持一种不以为然、冷眼旁观姿态,“无论是传统的记诵派,还是新起的科学考证派、疑古派,都不太理会这些争论”(85)。论战之后社会经济史则渗入主流学术界,表现有二:一是经济史研究成果不断在主流学术刊物发表。除1931年创刊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更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外,《史语所集刊》、《燕京学报》等时或刊载经济史的专题研究,二是一些学院派学者开始涉足社会史研究且取得了可观的成绩,较突出者如史语所的劳干、全汉升、燕京大学的齐思和、周一良、连士升等。社会经济史不再是一般知识阶层(包括革命理论家)可以天马行空纵横驰骋的论域,而变为职业学者的专门之学(86)。社会经济史研究已经接受通行的学术纪律和规范的约束和驯化,特别是受到科学理念和实证法则的洗礼。陶希圣及“食货派”即是因克服单一社会科学化路线、接受实证方法影响而风行于史坛的。这表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已逐渐步入学术化的运行轨道。 民国年间中国经济史学的产生发展是体现学术与政治的互动关系的一个典型。经济史研究由解答政治议题发端,而后驶入学术化之途,最终上升为现代史学的核心门类。政治变局、意识形态角逐为经济史的发生提供了初始的驱动力。社会经济史论与政论纠结缠绕在一起,由某种政治理念引申而出,为特定的政治主张作注脚,肩负指导革命的使命(87)。此时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主力是参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革命者、左派知识分子。这种政学不分的形态为社会经济研究制造出空前的声势,使这一新兴门类脱颖而出。但同时,强烈的政治诉求又使得社会经济史探索为一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导向所左右,偏离科学求真的轨道,最突出的弊病是公式主义泛滥。这种公式主义的根源不是学术思想,而是政治信仰。受政治牵引的社会经济研究陷入严重的困境。穷则思变,在一部分眼光敏锐的学者引领下,社会经济史研究脱离政争党争走上学术化、专门化的道路,终于附庸蔚为大国。近代中国经济史的发展历程充分昭示出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的复杂性,政治可以为学术提供动力,也能制造阻力,学术有时可以借力于政治,有时又遭遇政治权力的压制。总之,学术与政治完全绝缘是一种空想,巧妙化解二者之间的张力,趋利避害,互补共生,方为正途。 注释: ①马乘风(1906-1992),原名马鸿昌,又名马持盈,河南宜阳人。1923年考入开封河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随即被派往北伐军张发奎部作政治工作。1927年在冯玉祥开办的青年党政训练班中任教官,不久又任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宣传部指导科长。1933年到北平后,先后在北平中国大学、民国大学任教授,并兼任北平商业高专校长。后出任河南烟草专卖局局长。1949年赴台。 ②与1935年初版相比,1937年版第一册书前增加冯友兰序,并增补殷商时代一编、附录从西周到隋初之经济简史;删去原第四编诸家批判、第二编第五章春秋时代之社会生活及其他,章节标题略有变动,余皆相同。 ③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一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嵇序”,第4页。以下该版本只标年份。 ④马乘风:《中国经济史》,上海:中国经济研究会,1935年,第453页。以下此版本只标年份。此编在1937年商务版中删除,据说是由于顾及到顾颉刚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委员的关系。见马持盈:《中国经济史》第一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0年,“序”,第5页。 ⑤基夫:《书报评介:中国经济史(马乘风著)》,《清华周刊》第43卷第5期,1935年6月。 ⑥马乘风:《中国经济史》,1935年,第453页。 ⑦叶桂生、刘茂林:《中国社会史论战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1期。 ⑧郭沫若:《海涛》,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第118页。 ⑨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二册,1937年,第231页。 ⑩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二册,1937年,第229页。 (11)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一册,1937年,第56页。 (12)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一册,1937年,第57页。以作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续篇自期的郭沫若被马乘风视为公式主义者的典型代表。马乘风还批评说:郭沫若关于周初用铁的论证,“颇有为公式而曲解历史之嫌,其根据亦涉于勉强”,乃“作茧自缚之治学方法”。见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一册,1937年,第31页。 (13)石决明:《中国经济史研究上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国经济》第2卷第9期,1934年9月。 (14)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一册,1937年,第1-2页。 (15)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二册,1937年,第289页。 (16)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二册,1937年,第231页。 (17)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二册,1937年,第308-309页。 (18)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二册,1937年,第303页。 (19)[俄]波格达诺夫:《经济科学大纲》,施存统译,上海:大江书铺,1929年,“译者序言”,第3页。 (20)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一册,1937年,第58页。 (21)[德]库诺:《经济通史》卷一,吴觉先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译者序”,第1页。 (22)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一册,1937年,第12-16页。 (23)[俄]库斯聂:《社会形式发展史大纲》第4版,高素明译,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年,“序言”,第5-6页。 (24)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一册,1937年,第241页。 (25)马乘风:《中国经济史》,1935年,第407页。 (26)[德]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汤治、叶启芳译,上海:神州国光社,1932年,第1页。 (27)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一册,1937年,第212-213页。 (28)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一册,1937年,第214-215页。 (29)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二册,1937年,第319页。 (30)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一册冯序,1937年,第1页。 (31)傅筑夫:《研究中国经济史的意义和方法》,《中国经济》第2卷第9期,1934年9月。 (32)梁园东:《中国经济史研究方法之诸问题》,《食货》第2卷第2期,1935年6月。 (33)马乘风:《中国经济史》,1935年,第542页。 (34)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一册,1937年,第72-76页。 (35)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一册,1937年,第82-83页。 (36)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一册,1937年,第78页。 (37)马乘风:《中国经济史》,1935年,第543、545、548、555、550页。 (38)马乘风:《中国经济史》,1935年,第550-551页。 (39)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一册,1937年,第1页。 (40)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一册,1937年,第4-7页。 (41)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二册,1937年,第233页。 (42)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二册,1937年,第233页。 (43)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二册,1937年,第236页。 (44)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一册,1937年,“嵇序”,第4页。 (45)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93页。 (46)马乘风:《中国经济史》,1935年,第485页。 (47)马乘风:《中国经济史》,1935年,第495页。 (48)马乘风:《中国经济史》,1935年,第499、500页。 (49)马乘风:《中国经济史》,1935年,第506、500页。 (50)马乘风:《从西周到隋初之一千七百余年的经济转移》,《食货》第2卷第9期,1935年4月。 (51)马乘风:《中国经济史》,1935年,第495、498页。 (52)马乘风:《中国经济史》,1935年,第522、499页。 (53)基夫:《书报评介:中国经济史(马乘风著)》,《清华周刊》第43卷第5期,1935年6月。 (54)陈啸江:《中山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室计画书》,《现代史学》第3卷第2期,1937年。 (55)见《中国经济史》广告,《食货》第2卷第6期,1935年8月。 (56)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二册,1937年,第430页。 (57)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一册,1937年,第242-244页。 (58)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二册,1937年,第399-429页。 (59)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二册,1937年,第333-351页。 (60)马乘风:《中国经济史》,1935年,第192-209页。 (61)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史学论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页。 (62)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一册,1937年,第53页。 (63)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一册,1937年,第170页。 (64)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一册,1937年,第171、132页。 (65)秦璋:《经济史概论》,《中国经济》第1卷第3期,1933年6月。 (66)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一册,1937年,第313页。 (67)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一册,1937年,第277页。 (68)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一册,1937年,第92页。 (69)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一册,1937年,第276页。 (70)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一册,1937年,第64页。 (71)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二册,1937年,第14-38、190-196页。 (72)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一册,1937年,第293页。 (73)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一册,1937年,第222页。 (74)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一册,1937年,第253页。 (75)[俄]波格达诺夫:《经济科学大纲》,第10-11页。 (76)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二册,1937年,第338-344、345-351页。 (77)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二册,1937年,第412-419页。 (78)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二册,1937年,第420-420页。 (79)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二册,1937年,第421-428页。 (80)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二册,1937年,第297-298页。 (81)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二册,1937年,第245页。 (82)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一册,1937年,第224-240页。陶希圣在《西汉经济史》一书中较早指出,古代尤其是战国时期经济发达的地区不平均(参见陶希圣:《西汉经济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1-5、17-18页)。 (83)李根蟠:《唯物史观与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河北学刊》2002年第3期。 (84)参见吕振羽的若干文章,如《秦代经济研究》,《文史》第1卷第3期,1934年8月;《周秦诸子的经济思想》,《劳动季报》第1卷第2期,1934年7月;《隋唐五代经济概论》,《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4期,1935年10月。 (85)何怀宏:《世袭社会及其解体》,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44页。 (86)陈啸江指出:“近来谈社会史者,多是一般研究历史学以外的社会科学的人们”。见陈啸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总成绩及其待决问题》,《社会科学论丛季刊》第3卷第1期,1937年1月。 (87)陶希圣即断言,共产主义者社会史研究的意图在于制造无产阶级以实行社会革命。见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上海:新生命书局,1930年,第19页。标签:顾颉刚论文; 中国经济史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陶希圣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