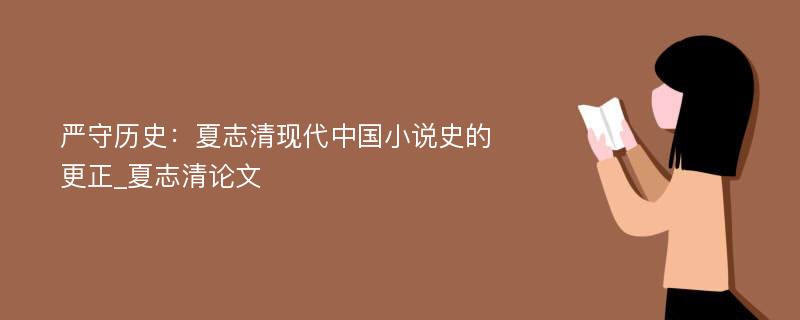
为史需严谨: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勘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严谨论文,现代小说论文,夏志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早读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以下均简称《小说史》),是20世纪80年代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虽然只是走马观花地浏览了一遍,但有两个印象却十分深刻:一是《小说史》所涉猎的研究范围,要比国内同类题材的现代文学史宽广许多,对于我们这些刚入门的青年学子来说,无疑是极大地开拓了眼界;二是《小说史》的立论颇为大胆,像被国内学界所推崇的文学大师鲁迅、巴金等人他都不以为然或不屑一顾,但对沈从文和张爱玲这些为国内学界陌生的作家却大加赞赏,很有一种颠覆历史者“舍我其谁也”的英雄气概。应该说,那个时代的青年学者,对于夏志清还是比较敬仰的。 然而,近来我因要为博士研究生开设一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的专业课程,而夏志清也早已被许多人捧为西方汉学界的神话人物,那么他的《小说史》就不能不去再次重读。由于经历了30多年的学术磨炼,毕竟具有了一定的知识储备,看问题也相对地深刻了一些。此次用的是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的简体字版,未曾想读罢之后大吃一惊,这部《小说史》中的史料错误随处可见,实在是太多了。虽说夏志清是在美国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史,但他毕竟在出国之前曾系统化地接受过传统的国学教育,出国之后又追随新批评大师接受过现代的西学训练,于情于理他都应该懂得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为学者的基本信条,就是学风严谨言必有据。因为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推崇“格物致知”的治学态度,而孔子也一再告诫中国学人,对待历史应“毋意、毋必、毋固、毋我”,①必须实事求是,绝不能凭空杜撰。想必夏志清本人,对此是有所了解的,否则他也不会对台湾编写的中国现代《文艺史》,在史料方面的一些错误给予严肃的批评。②批评谬误以正学风,这一点的确值得肯定;但为什么《小说史》本身,也犯有同样的低级错误呢?复旦版《小说史》是由国内著名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专家陈子善引进的,出版时陈子善根据我国国情做了一定的删减,“个别明显的史实错讹也作了订正。”陈先生非常谦虚地说,这个版本“如果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责任自然在我,欢迎读者批评指教。”③我绝不怀疑陈子善的为学水准和治学态度,故赶忙从网上“淘”得一本1961年耶鲁大学英文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1),并借助汉英词典仔细地将中英文版《小说史》对照了一遍,发现错不在陈子善的复旦本,英文版的耶鲁本就已经存在了。可想而知,假如陈子善没有为其校勘“错讹”,耶鲁本的《小说史》到底会有多少“错讹”?恐怕我们就不得而知了。由于夏志清是西方的汉学“权威”,他又是用英文去向西方介绍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所以英文版《小说史》的知识性“错讹”已经在西方流传,其所造成的不良学术影响也难以挽回。现在,我把《小说史》中的其他“错讹”也罗列出来加以勘误,只是想维护学术的严肃性而已。 1.鲁迅部分的史实错误 夏志清知道,鲁迅是他撰写《小说史》所无法绕过去的一道坎,必须对鲁迅及其文学创作做出一个评价,但他又不接受国内学界对于鲁迅的正面见解,所以《小说史》的第二章“鲁迅(1881-1936)”,开篇便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鲁迅是中国最早用西式新体写小说的人,也被公认为最伟大的现代中国作家。在他一生最后的六年中,他是左翼报刊读者群心目中的文化界偶像。自从他于1936年逝世以后,他的声誉更越来越神话化了。(第23页) 这段评语隐含着两个潜台词:(1)鲁迅“被公认为最伟大的现代中国作家”,其实无非是“靠几个短篇小说就建立起来”的(第43页),他本人似乎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因为在他看来,包括《阿Q正传》在内的鲁迅作品“显然是受到过誉”(第28页),是国内学界“神话”鲁迅的历史产物。(2)夏志清暗示鲁迅后六年的杂文,都是发表在“左翼报刊”上,那么它们的阅读对象,自然也都是些“左翼”读者。这种轻率而随意的主观论断,完全有违于历史事实。从1930年算起,鲁迅创作的杂文集,总共有《二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等八本,收录的文章也有400多篇。我仔细统计了一下,真正发表在“左翼报刊”(当然是指“左联”办的报刊)上的,只占百分之十五也就是60篇左右,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发表在当时与“左翼”无关的报刊杂志上。鲁迅自己在《南腔北调集·题记》中就曾清清楚楚地写道:收入该集里的文章,曾分别在“《十字街头》、《文学月报》、《北斗》、《现代》、《涛声》、《申报月刊》、《文学》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过。④《十字街头》、《文学月报》、《北斗》固然是“左翼报刊”,但其他却根本不是。《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这三本集子里所收录的文章,基本上都是发表在《申报·自由谈》,鲁迅自己说“我的投稿,平均每月八九篇”,后来由于当局封杀,“从六月起的投稿,我就用种种的笔名了。”⑤我们总不能把《申报》,也说成是“左翼报刊”吧?至于几部《且介亭杂文》里所收录的文章,发表的刊物更是五花八门,绝大多数都与“左翼”无关,读者群体也是当时社会的普通民众。夏志清一概用“左翼报刊”加以冠之,不管其主观用意如何,但对历史事实的全然无知,的确有损他西方汉学的“权威”身份。另外,《小说史》中还写道:鲁迅“1927年1月离开厦门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第36页)夏志清的资料明显有误,因为鲁迅本人在日记中有记载:“被任为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开第一次教务会议。”⑥这些资料都非常好找,只要稍下点工夫,就不会出现差错,不知《小说史》的作者为何没有去认真地核实。 2.郁达夫部分的版本错误 《小说史》对郁达夫的评价非常差,虽然专门用了一节加以论述,但把他的作品都归结为是“性”书,除了“性欲”几乎没有任何艺术价值:“郁达夫和其他创造社的人一样,伤感气味太浓,文章写得马虎,结果每篇小说都有缺陷,也很可惜。不重视艺术也破坏了他自我探讨的功夫。我们有时候觉得,尽管他坦白,他也有些装腔作势,从心理学的书里偷些东西,补他才力的不足。时而观淫,时而睹物兴起淫念,时而同性恋,时而以被虐满足性欲,时而有偷物狂,他的自传体主人公花样太多了。”(第79页)夏志清把郁达夫贬得一塌糊涂,我不想浪费口舌与其论辩,权当是见仁见智一家之言罢了;但既然你那么了解郁达夫,并且通读了他所有小说作品,为什么还会出现版本错误呢?在《小说史》所列出的“参考书目”中,关于郁达夫的作品是这样记载的: 《达夫文集》(The Collected Works of Yu Ta-fu).7 vols.1928-1931.This edition was published by Pei Hsin Book Co.and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titles: 《寒灰集》(Cold Ashes).Mainly fiction,some prose. 《鸡肋集》(Chicken Ribs).Fiction,including "Sinking." 《过去集》(The Past).Fiction and prose. 《奇零集》(Fugitive Pieces).Prose. 《敝帚集》(Battered Brooms).Prose. 《蕨薇集》(Ferns).Fiction. 《断残集》(Miscellaneous Pieces).Prose and translations. 夏志清说他看过的《达夫全集》,是由北新书局1928年至1931年出版的七卷本。可是根据我个人的印象,他的说法有误。于是我赶紧把《达夫全集》找来核对一下,立刻印证了我的判断。众所周知,郁达夫是第一个人还在世便出全集的新文学作家,他的所谓“全集”实际上就是作品集,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当年的七卷本《达夫全集》,具体出版时间是这样:第一卷《寒灰集》,1927年6月由上海创作社出版部初版;第二卷《鸡肋集》,1927年10月由上海创作社出版部初版;第三卷《过去集》,1927年11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第四卷《奇零集》,1928年3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第五卷《敝帚集》,1928年4月由上海现代书局初版;第六卷《薇蕨集》(《小说史》将其写成了《蕨薇集》),1930年12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初版;第七卷《断残集》,1933年8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初版。通过查对我们可以发现,前三卷都是出版于1927年,且前五卷也都不是由北新书局出的,难道在此之外还有一部北新版的《达夫全集》不成?于是我又多方求证无果,后来终于从《唐弢文集》里找到了一条可靠信息:《达夫全集》当时就是那么七卷,并没有什么额外的“北新版”。⑦这我就有些糊涂了,夏志清所说的北新版《达夫文集》,到底是从哪里搞到的绝世孤本呢? 3.巴金部分的史实错误 《小说史》对巴金的评价也不高:“巴金是这十年间(指1928-1937年,笔者注)最流行又最多产的作家之一,但是却不是最重要的一位。尽管佳评如潮,受到群众的爱戴,我们却无法从他这一期的作品内,发现任何追求完美的企图。”(第168页)“好评如潮”与“群众爱戴”,都无法使巴金显得“重要”,我真不知道《小说史》的评价尺度,到底是依据什么样的审美标准。《小说史》在巴金部分里,既存在有史实错误,又存在有史料错误,更存在有版本错误。 史实错误有:巴金这个笔名,是两位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名字拆拼起来的。(第169页)这完全是夏志清本人毫无根据的主观猜想。巴金在《谈自己》一文中,就已经说得很清楚:“金”的确是来自于克鲁泡特金,但“巴”却是对一个同学的纪念。巴金在法国留学时,有一个北方的同学叫“巴恩波”,他们相处了一个月,“第二年听说他在项热投水自杀。我和他不熟,但是他自杀的消息使我痛苦。我的笔名中的‘巴’字就是因他而联想起来的。”⑧ 史料错误有: 1927年正月,当他23岁的时候,巴金到了法国,大部分时间待在巴黎研读法文。同时开始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一书,完成了一部名叫《灭亡》的小说。《灭亡》分期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到了1929年,当巴金从法国返回中国时,他有点惊异地发现,自己已是颇负时誉的作家了。(第171页) 这更是一种夏氏杜撰的无稽之谈。据巴金本人讲,1928年《灭亡》写完以后,把原稿寄给了上海开明书店的一个朋友,准备自费出版。“直到这年12月我回到上海,那个朋友才告诉我他把我的小说介绍给了《小说月报》的编辑叶圣陶、郑振铎两位前辈,他们决定在《小说月报》上发表。”⑨据查,《灭亡》从1929年1月至4月在《小说月报》上连载,此时巴金早已回国。换言之,巴金回国之后,《灭亡》还未开始连载,何来“他有点惊异地发现,自己已是颇负时誉的作家了”之说? 版本错误有: 《新生》(New Life).1932.…… 《砂丁》(The Antimony Miners).1932.(第466—467页) 我仔细查证了一下,《新生》写于1931年,1933年9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而《砂丁》则是写于1932年,1933年1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我真想知道,夏志清的注释依据,究竟是来自何处? 4.老舍部分的史料错误 《小说史》对于老舍的评价十分有趣,夏志清认为老舍是北平的个人主义作家,他“后悔错过了1920年后半期国内发生的种种令人振奋的事。但是如果他那时真的留在中国,他多半会淹没在革命的潮流里面,接受那些激进分子全部的政治和经济信条。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是否能创造出他个人主义的一派小说,就很难说了。”(第116页)所以,“在抗战时期的紧张气氛里,老舍为了反日救国,重新倡导英雄式的行动——但只是在宣传上这样做,并且缺少他先前对中国的需要和缺陷的深思卓识。”(第132页)故写出像《四世同堂》这样的“失败之作”,也就在所难免了。(第240页)我真不知道夏志清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仅以《骆驼祥子》为例,他认为虽然这是一部最佳的“现代小说”,但却又为老舍“脱离早先个人主义的立场”而惋惜。(第130页)既然老舍脱离了“个人主义”立场,仍能写出最佳的“现代小说”,那么不正说明老舍的创作转型,是一种非常正确的思想选择吗?还是回到史料方面吧,《小说史》在参考书目上注明:《骆驼祥子》(Camel Hsiang—tzu).1938.(第462页)。 这等于是夏志清在告诉我们,《骆驼祥子》初版于1938年,可事实并非如此。《骆驼祥子》写完以后,首先于1936年9月至1937年11月,在《宇宙风》杂志连载了24期(老舍本人称其为“二十四段”)。到了1939年3月,才初次出版发行。现在有两种说法:一是孔令云认为,《骆驼祥子》1939年3月由上海中国科学公司初版;⑩二是郝长海认为,《骆驼祥子》1939年3月由人间书屋初版。(11)我认真地核对了一下,郝长海是正确的。但不管是“孔说”还是“郝说”,《骆驼祥子》都是于1939年初版,而不是夏志清所说的1938年初版。此外,《小说史》还这样写道: 《惶惑》和《偷生》分别在1946年7月和11月出版(该年4月,老舍和剧作家曹禺,同时接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访问一年);《饥荒》则迟至1950年9月,才开始在《小说月刊》上连载。(第240页) 仅在这段简短的表述里,就有三处史料错误:(1)老舍与曹禺是1946年1月接到的邀请,1946年3月4日乘坐美国运兵船“史各脱将军号”赴美的,而不是1946年4月接到的赴美邀请。对于这一点,当时各大报刊均有报道,曹禺本人也曾有过说明。(12)(2)《惶惑》1944年连载于《扫荡报》,1946年1月而不是7月,由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初版。初版时用的名称是《四世同堂》,直到1946年11月再版时,才用了《惶惑》这一篇名,而“四世同堂”则成了总称。(13)(3)核实史料,《饥荒》写于1947-1949年,前20段连载于1950年5月至1951年1月,上海《小说》月刊第4卷第1期至第4卷第6期。(《小说》杂志虽说是月刊,但不知是何缘故,1950年5月出版了第4卷第1期,6月出版了第2期,到了10月才出版了第3期,11月出版了第4期,12月出版了第5期,1951年1月出版了第6期)也就是说,《饥荒》是1950年5月开始连载的,而不是9月开始连载的,夏志清的资料明显不实。 5.蒋光慈部分的史料错误 《小说史》对于蒋光慈的评价极低,说他“从来没有被认为是现代中国的一个伟大作家”,只不过“是最早一个卖文为生的共产党作家”而已。(第184页)在夏志清本人看来,《少年漂泊者》“似乎极幼稚”。(第186页)《冲出云围的月亮》更是“浅薄之作,根本就不需要批评”。(第187页)夏志清不喜欢蒋光慈的小说创作,应该是在情理之中,因为人们不可能指望对“左翼”存有偏见的他,能够认真仔细地去阅读蒋光慈的全部作品。我之所以这样定论,自然是有客观依据的,比如夏志清在《小说史》的参考书目中,有三部蒋光慈作品的出版时间,就存在着明显的错误: 《哭诉》(Lament).1929.…… 《少年漂泊者》(The Youthful Tramp).1925.…… 《菊芬》(Chü-feng).1927.(第468页) 我仔细核实了一下历史资料和作品版本,发现夏志清简直是错得令人不可思议。《哭诉》是蒋光慈1927年所写的长篇抒情诗,后改名为《写给母亲》,1928年3月由上海春野书店初版,被列为“太阳小丛书”第四种,1933年上海新文艺书局再版。《少年漂泊者》1926年1月由亚东图书馆初版,1927年至1933年间,总共印刷过15次。《菊芬》1928年4月由上海现代书局初版,到1930年底已经被印刷了四次。也就是说,这三部作品的初版时间,一部被夏志清推后了一年,两部被《小说史》提前了一年。众所周知,蒋光慈是20世纪20年代末与30年代初最受欢迎的中国现代作家之一,由于他的读者群体非常之大,作品的发行量也一直是名列前茅,故出版社给他的版税也极高。据蒋光慈夫人吴似鸿自己说,蒋光慈曾告诉她“鲁迅作品是抽百分之二十的,我也和鲁迅一样。因为销路大,书店赚得多,给我们也多些。”(14)吴似鸿的话我们还可以从唐弢先生那里得到印证,唐弢先生在《翻版书》与《再谈翻版书》两篇文章里,就曾告诉我们鲁迅和蒋光慈是当时中国文坛两大畅销书作家,正是由于他们的书太畅销了,所以社会上出现了许多盗版本。(15)有学者曾做过考证,蒋光慈作品被盗版的情况十分严重,“仅次于‘新文学泰斗’郭沫若和‘三角恋爱小说家’张资平,这个数字可以说明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他的受欢迎程度。”(16)蒋光慈作品的畅销与被盗版,最起码可以揭示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以上海大都市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读者群体,其实并不如夏志清所想象的那样没有审美水准。我倒担心起一个问题来,《小说史》评价蒋光慈的理论依据,用的不会是盗版本吧?那可是事关学风的大问题啊!但愿这只是一个充满善意的黑色幽默。 6.丁玲部分的史料错误 《小说史》对于丁玲的评价是:“丁玲在1930年的声誉,主要是基于她早期的小说。由于这些小说的性问题比较开放,它们遂被认为比谢冰心和凌叔华的较为含蓄的小说优越了。可是自1931年开始创作无产阶级小说后,这一点微带虚无主义色彩的坦诚也丧失了,剩下来的,只是宣传上的滥调。”(第190—191页)将丁玲的小说视为是带有性开放特征的艳情之作,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种提法。我们固然可以从《莎菲女士的日记》里看到青春期女性的“性苦闷”,但是若把青春期女性的爱情幻觉理解为“艳情”那就大错特错了。夏志清对丁玲小说评价的随意性,与他运用史料的随意性几乎是一致的。比如他在书中这样写道:“1931年丁玲加入共产党,决心要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作家。”(第187页) 这是一个毫无事实依据且根本没有去做认真考证的主观臆说。丁玲自己说,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那时我还没有参加共产党呢!”“一九三二年二三月我入了党”。(17)《丁玲评传》的考证也支持这一说法:1932年2月,丁玲向阳翰笙提出了入党申请,3月被批准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仪式在上海南京路大三元饭店秘密举行。文委负责人潘汉年主持,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宣传部与会,同时宣誓入党的有田汉、叶以群和刘凤斯等3人。”(18)如果说夏志清因客观原因拿不到第一手历史资料,那么他完全可以对于时间问题模糊处理,比如用“30年代初”一笔带过,别人也不会产生什么异议。既然敢使用时间的具体指定性,那就必须给出史料的出处或来源,但《小说史》却并没有这样做,给人的感觉是治学态度很不严谨。《小说史》对《我在霞村的时候》的初版时间,也做了错误的注释:“《我在霞村的时候》(When I Was at Hsia Village).1st Peiping ed.1946.”(第469页) 丁玲的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创作于1940年,最初刊载于1941年6月20日《中国文化》第2卷第1期;1944年3月,由桂林远方书店初版,以《我在霞村的时候》冠名,内收7篇短篇小说;1946年被收入周扬编的《解放区短篇小说选》(东北书店),1947年又被冯雪峰收入《丁玲文集》(开明书店)。夏志清说《我在霞村的时候》1946年在北平初版,明显与史实有很大的出入,我本人也没有查到有什么1946年本。况且一篇仅一万多字的短篇小说,也是不可能出单行本的。 7.沈从文部分的史料错误 《小说史》对沈从文的评价极高,夏志清认为沈从文的小说作品,“显露着一种坚强的信念,那就是,除非我们保持着一些对人生的虔诚态度和信念,否则中国人——或推而广之,全人类都会逐渐地变得野蛮起来。因此,沈从文的田园气息,在道德意识来讲,其对现代人处境的关注之情,是与华兹华斯、叶芝和福克纳等西方作家一样迫切的。”(第134页)“他对人类精神价值的确定,固然切中时害——但造成他今天这个重要地位的,却是他丰富的想像(象)力和对艺术的挚诚。”(第146页)夏志清之所以会如此看重沈从文,除了沈从文小说自身的艺术魅力外,还因为他特别看重沈从文为了自觉地抵御“当时激进的革命气氛”始终坚守的自由主义创作立场:“胡适后来致力于历史研究和政治活动,徐志摩于1931年撞机身亡,而陈源退隐文坛——只剩下沈从文一人,卓然而立,代表着艺术良心和知识分子不能淫不能屈的人格。”(第137页)对于这种人为将沈从文划入到以胡适为代表的“英美派”或“新月派”的轻率做法,沈从文研究专家凌宇先生早已有过驳斥,(19)我们没有必要再去浪费笔墨。既然沈从文是夏志清最喜爱的作家之一,那么对于史料的掌握和运用,总该会严谨些了吧,未曾想错误同样存在:“1930年他在国立武汉大学教了一个学期,次年即到青岛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一直到1934年为止。”(第140页) 沈从文到青岛大学任教是1931年8月至1933年7月,1933年8月初他已回到北平,并忙于筹备他与张兆和的结婚事宜,而不是“到1934年为止”。其次,沈从文在青岛大学是任讲师而非教授,同时被聘为讲师的还有游国恩、杨筠如等人。众所周知,中国大学很讲求资历,虽然沈从文当时已经小有名气,但是他的小学文化程度,是不可能被直接聘为教授的,后来他到西南联大,也只是被聘为副教授而已。此乃错一。 《小说史》写道:“抗战时,沈从文在西南联大中文系任教……最重要的一本《黑风集》(1934年出版),包括了《静》以及另外一篇同样精致的《白日》。”(第233页)据查,《黑风集》是1943年由桂林开明书店初版的,而不是什么1934年出版。此乃错二。 《小说史》又写道:“1934年冬,在暌隔了18年后,他重游湘西,之后写了《边城》、《湘行散记》”。(第233页)沈从文是1923年离开湘西去北京的,真不明白夏志清是计算错误还是记忆错误。另外,沈从文因母亲病危,是于1934年1月7日离开北平的,1月22日到达湘西凤凰;1月27日离开凤凰到沅陵,在他大哥家里小住数日,于2月9日回到了北平。回到北平后不久,便写完了小说《边城》。同年10月,傅东华将《边城》编为“创作文库”之九,由上海生活书店初版。(20)如果说沈从文是1934年冬回的湘西,那岂不是《边城》出版以后他才回家的吗?怎么又会是“他重游湘西”之后“写了《边城》”呢?实在是太乱了。此乃错三。 《小说史》还写道:“1937年冬,沈从文继续逗留在湘西,有4个多月。”(第234页)沈从文第二次回湘西是1938年1月初,而不是1937年冬。他先由武汉到长沙,在长沙呆到了1月中旬,然后才去沅陵他大哥家。4月13日离开沅陵,经贵州去昆明,4月30日抵达昆明。(21)满打满算也就3个月,何来“4个多月”之说呢?此乃错四。 我原以为沈从文部分的错误能够少一些,殊不知一点也不少,可见夏志清对沈从文还是不太恭敬的。 8.张天翼部分的史实错误 张天翼是《小说史》唯一被正面评价的“左翼”作家,也许夏志清意识到自己把“左翼文学”贬得有点过分,所以为了维护他没有任何政治偏见的学术立场,才不得已把张天翼拉出来以充当点缀。《小说史》称“张天翼在中国现代小说中是首屈一指的”(第150页),“如果我们剔除掉他小说三分之一的公式化的习作,其余的三分之二,不但代表着张天翼的丰饶多产,而且说明了他高水平的成就。他同期的作家内,只有沈从文,质或者量方面来说,差堪比拟。”(第151页)张天翼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早有公论,我总觉得夏志清“抬张”的目的并不是那么得纯洁,因为在张天翼“首屈一指”的定论之下,巴金、老舍等人的大师地位自然也都被《小说史》人为地消解了。夏志清喜欢张天翼的小说无可非议,既然喜欢就应该对作者的创作有所了解;可是《小说史》在张天翼一章中的史实错误,却立刻令这位汉学权威的颜面全无: 张天翼是这十年当中最富有才华的短篇小说家。1929年,张的作品初见各刊物,即使要找他毛病的批评者,也不能否认这位新进作家异于常人的“耳”聪“目”明,以及喜趣横生。(第150页)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张天翼从1929年开始,才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文学作品,完全是一派胡言乱语。张天翼从1922年(16岁)起,就已经开始以“张无诤”或“无诤”署名,在“鸳鸯蝴蝶派”出版的刊物《礼拜六》、《星期》以及《半月》等杂志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了。具体篇目为:《新诗》(短篇小说,1922年《礼拜六》第156期)、《怪癖》(短篇小说,1922年《礼拜六》第158期)、《流星》(短篇小说,1922年《礼拜六》第169期)、《少年书记》(短篇小说,《半月》1922年第1卷第22期)、《人耶鬼耶》(短篇小说,1922年《星期》周刊第23期)、《空室》(短篇小说,1922年《星期》周刊第32期)、《遗嘱》(短篇小说,1922年《星期》周刊第34期)、《苦衷》(短篇小说,1922年《星期》周刊第38期)、《玉壶》(短篇小说,1922年《星期》周刊第39期)、《恶梦》(短篇小说,1922年《半月》第2卷第7期)、《铁锚印》(短篇小说,1923年《半月》第2卷第19期)、《月下》(短篇小说,1923年《半月》第2卷第22期)、《斧》(短篇小说,1923年《侦探世界》第13号)、《X》(短篇小说,1923年《半月》第3卷第6期),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杂文和小品。如果说张天翼这些早期作品还不算是“新文学”,那么1926年以后他发表的散文小说,则完全与新文学接轨了,比如散文《黑的颤动》(载1926年12月《晨报,副刊》第1497号,从这篇散文开始,他以后的作品都署名为张天翼)、小说《走向新的路》(载1927年9月《晨报·副刊》第2062—2064号)、小说《黑的微笑》(载1928年《贡献》旬刊第3卷第8期)。(22)夏志清说张天翼的作品1929年才始见于各种刊物,不是无知又是什么呢? 另外,《小说史》还写道:“张天翼的第一篇故事《三天半的梦》,是在1928年的一份名叫《奔流》的杂志上刊出的,是年他21岁。”(第151页)首先,夏志清犯了一个自相矛盾的低级错误:既然张天翼是1929年才开始发表作品的,又说他1928年发表了《三天半的梦》,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么?据查,张天翼《三天半的梦》发表在《奔流》杂志1929年4月第1卷第10号,而不是1928年。其次,即使是1928年,出生于1906年的张天翼(《小说史》上有注明),也应该是22岁才对啊,怎么得出的21岁呢? 9.萧军部分的史实错误 《小说史》对于萧军的评价比较平面,主要是分析《八月的乡村》这部作品的思想内容,夏志清一方面说“《八月的乡村》是第一部以反日斗争为主题的成功的共产主义小说”,另一方面又认为该小说根本就没有摆脱“革命+恋爱”的俗套模式。(第195页)我个人实在有些无法理解,“成功”的肯定与“俗套”的否定,究竟哪一个词汇才是夏志清的真实评语,因为两者完全是一种矛盾对立关系。然而,《小说史》在谈及萧军的文学创作时,其史实与史料方面的错误,却是清清楚楚地写在那里。比如他说: 萧军虽然是一个热诚的共产党员,但他并没有完全依照共产国际当时的统一阵线路线来写他的小说。《八月的乡村》宣传阶级斗争,强调农工兵贫苦大众与军阀、官吏、土豪、劣绅的对立。此外,枪毙地主王三东家这一重要的情节也预示了以后土改时期小说的模式。(第196页) 众所周知,《八月的乡村》创作于1933年,那时萧军既不是左联成员更不是什么共产党员,只不过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文艺青年。萧军不仅在上海期间没有加入共产党,抗战期间他在延安时也没有加入共产党。1945年,萧军离开延安去东北前,毛泽东曾经问他,“听彭真说,你要入党,我们欢迎,只要你自己什么时候下决心。”(23)从萧军这段回忆中我们可以得知,一直到1945年他还没有加入共产党。萧军真正的入党时间是1948年,那年7月25日他向凯丰正式提交的入党申请书:“我个人感到现在已是我走人共产党内的时期了——因此我郑重提出,请求加入共产党,请你转达东北局,如何考虑给予回答。”(24)8月份东北局便批准了萧军的入党申请。夏志清说萧军左联时期就已经是共产党员了,可是又不提供他所掌握的历史资料,这种以想象历史去评说历史的治学方法,无论如何人们都难以认同。 又如,《小说史》的参考书目中还写道:“《八月的乡村》(Village in August).1936.……《羊》(Sheep).1935.”(第470页)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由鲁迅作序,1935年被纳入“奴隶丛书”,自费由上海容光书店初版,1947年由哈尔滨鲁迅文化出版社再版,根本就没有1936年版本。《羊》是一部短篇小说集,1936年1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而不是1935年。《小说史》总共提到了萧军四部作品,其中两部就出现了史料错误,其错误的概率之大,不能不令人咋舌。 10.其他部分的史料错误 除了上述9位作家之外,《小说史》中还有其他方面的许多错讹,在此也一并纠正。 A.关于《现代》杂志停刊原因的勘误。《现代》杂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刊物,它不仅开启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历史先河,同时更是成为了先锋派小说和诗歌的试验基地。《小说史》对此并不否认,它的具体评价如下:《现代》杂志对促进政治独立的严肃文学,有很大的贡献。可是后来在革命作家不断攻击下,迫得在1934年停刊。(第95页) 《小说史》的这段评语,有两个明显错误:一是《现代》杂志的停刊,与“革命作家不断攻击”无关,而是“现代书局资方分裂,张静庐退出书局,另外去创办上海杂志公司。洪雪帆病故。”于是施蛰存与杜衡便自动辞职,“徐朗西请汪馥泉接手主编《现代》,只出版了二期,因现代书局歇业而停刊了。”(25)所以,《小说史》将《现代》杂志停刊的原因强加给“左翼”革命作家,大有一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讨伐味道。二是《现代》杂志的停刊不是1934年,而是1935年5月。查证《现代》杂志,施蛰存与杜衡1934年11月辞职以后,汪馥泉接手还编了三期(施蛰存先生的记忆有误)。《小说史》的立论,不知是何依据。 B.关于《倪焕之》初版时间的勘误。《小说史》对叶圣陶的《倪焕之》评价颇高,认为在当时“《倪焕之》算是很不错的一本小说了”(第48页),但正是这部被夏志清所赞赏的长篇小说,初版的时间却被他本人给搞错了。参考书目里是这样写的:“《倪焕之》(Ni Huan—chih).1930.”(第457页) 查阅史料,《倪焕之》1928年1月初动手写作,1月中旬便开始在《教育杂志》上连载,一直连载到该年的12月份,共计连载了12期。1929年8月由开明书店初版,书前收有夏丏尊的《关于〈倪焕之〉》,书后收有《作者自记》,并节录了茅盾的《读〈倪焕之〉》一文。既然《倪焕之》是1929年初版的,那么1930年说显然不实。(26) C.关于《呼兰河传》初版时间的勘误。《小说史》对于女作家萧红谈得不多,几乎是一笔带过并不展开讨论。但是就是那么不多的文字交代,也出现了十分明显的史料错误: 萧红的回忆之作《呼兰河传》(1942),所详细描写的呼兰县(在黑龙江省),有如鲁迅小说中的绍兴那样萧条和落后,而那儿的人民比起绍兴村庄的居民来,更为懦弱、残忍与愚蠢。(第383页) 萧红的《呼兰河传》从1937年开始写作,到1940年最终完成,用了长达3年多的时间。这部作品从1940年9月1日到12月17日,在《星岛日报》副刊《星座》上连载了5个多月。1941年5月,由桂林上海杂志公司初版。萧红临终前为了感谢骆宾基对她的照顾,决定将《呼兰河传》初版的版税赠给骆宾基。可是后来,骆宾基却无法从上海杂志公司那里讨到版税。于是1943年6月,他又将《呼兰河传》进行了修订,并以“松竹文丛社”之名,交由桂林河山出版社出版。1947年6月,上海寰星书店又再次修订,出版了第三版《呼兰河传》。(27)也就是说,1942年版的《呼兰河传》,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D.关于《法律外航线》初版时间的勘误。《小说史》对于沙丁,只是做了初步的介绍;未曾想即便是几百字的介绍文字,也存在有史料错误:艾芜的好朋友沙丁,早在1936年,已因他的一本短篇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而崭露头角,不过只有到了抗战时期,他的小说才显露出熟练的讽刺技巧。(第220页) 《小说史》意指沙丁是因1936年出版了《法律外的航线》,才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崭露头角”的,这无疑是大错特错了。早在1932年8月,《法律外的航线》便由辛垦书店出版了,其中收录有《法律外的航线》、《汉奸》、《撤退》、《俄国煤油》等12篇作品。诚如吴福辉先生评价的那样,“在1932年年底的中国文坛上,‘沙丁’这个崭新而略显古怪的名字,便和他的第一部集子、第一篇刊载小说,同时诞生。”(28)然而不知是出于何种缘故,《小说史》却将《法律外的航线》的出版时间,向后推延了4年之久。 E.关于《现代中国文学作家》(上册)初版时间的勘误。《小说史》在介绍“第一阶段的共产主义小说”时,特别提到了钱杏邨的一本小册子,即《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第一卷)。其中作者这样写道: 1929年共产主义文艺批评家钱杏邨出版了他的曾经引起极大争论的《现代中国文学作家》上册。书中收集了四篇早先发表过的评论鲁迅、郁达夫、郭沫若及蒋光慈的文章。(第183页) 我手头正好有一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阿英全集》,找出第二卷稍加校对便发现了错误:《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第一卷即《小说史》所说的“上册”,1928年7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初版,第二卷1930年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初版。故此注时间明显有误。 F.关于师陀获奖时间的勘误。《小说史》对于师陀的评价不是很高,认为他小说的艺术水准“比不上钱钟书和张爱玲”。(第293页)但夏志清在评说师陀时还是出现了史料错误: 虽然他在战前已成为北京作家中的知名分子,并于1936年以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谷》获得众所瞩目的《大公报》文艺金奖(曹禺《日出》、何其芳散文集《画梦录》同届获奖),但他真正值得我们珍视的小说该是1947年出版的长篇《结婚》。(第293页) 我查了一下历史资料,《大公报》1936年9月1日正式刊发“文艺奖”的评审启示,10月又推出了“文艺奖”章程和审查委员会委员名单,内有叶圣陶、朱自清、杨振声、朱光潜、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徽因、沈从文、凌叔华等10人。经过8个月的认真评选,直到1937年5月15日,才正式向社会公布了最终结果。最初小说奖不是给师陀的《谷》,而是给萧军的《羊》,由于萧军本人拒绝接受,才转而颁给了师陀。所以,师陀获《大公报》的“文艺奖”,应是1937年而不是1936年。 此外,《小说史》又说:《马兰》写成于1942年,于1948年初版发行。(第295页)我也查了一下资料,师陀的长篇小说《马兰》,写成于1941年12月,1942年曾在《文汇报·宇宙风》连载,1948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29)《小说史》说“《马兰》写成于1942年”,时间上明显不对。 以上是我对《小说史》中我熟悉的部分,所做的一些史实或史料方面的勘误,我没有时间去对全书进行详细的校对。但仅就我发现的这些错误,如果再加上陈子善先生已经做过的“订正”,这部《小说史》的错讹究竟会有多少?想一想我都觉得可怕。阅读夏志清的《小说史》,我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小说史》的英文版1961年、1971年和1999年,先后在美国出版过三次,而台湾与香港也分别于1979年、1991年和2001年出版过三次,夏志清竟然对《小说史》的错讹始终都未加修正。我想,夏志清对于这部《小说史》,肯定是充满了学术自信的,因此才会觉得他不会犯那种低级错误。中国有句俗话: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果仅仅是几处版本错误,完全可以谅解,一时疏忽的毛病谁都难以避免;可是《小说史》列入章节的15位作家当中,超过半数都出现了“错讹”,这说明还是一个治学态度的大问题。常言道,谎言说三遍就变成了真理。夏志清的《小说史》,中英文版恰好都各出了三版,即便是错误连篇,它也早就变成了夏志清的“真理”了!试问,在错误史料建立起来的错误文学史观,到底有何学术价值值得人们去大肆吹捧呢? 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9页。 ②夏志清在《新文学的传统》的第6—7页,就曾对《文艺史》关于萧红本人的真名和《呼兰河传》的篇名错误,提出过质疑和批评。 ③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04页。(以下引文该著仅标出页码) ④《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13页。 ⑤《鲁迅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190页。 ⑥《鲁迅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643页。 ⑦唐弢先生对于《达夫全集》的论述参见《唐弢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772页。 ⑧《巴金选集》第10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1页。 ⑨《巴金选集》第10卷,第116页。 ⑩孔令云:《〈骆驼祥子〉的版本变迁——从出版与接受的角度考察》,《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11)郝长海、刘慧智:《老舍著译年表》,《文献》1983年第4期。 (12)克莹、侯堉中:《老舍在美国——曹禺访问记》,《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1期。 (13)吴福辉:《〈四世同堂〉:从小说到话剧(答北京话剧观众问)》《汉语言文学研究》2013年第4期。 (14)吴似鸿:《我与蒋光慈》,付建祥整理,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8页。 (15)唐弢:《翻版书》、《再谈翻版书》,两篇文章均收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的《晦庵书话》。 (16)刘震:《蒋光慈作品的畅销与盗版》,《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2期。 (17)《丁玲全集》第10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48—250页。 (18)杨桂欣:《丁玲评传》,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年,第103页。 (19)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第52页。 (20)吴世勇:《沈从文年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9—160页。 (21)吴世勇:《沈从文年谱》,第202—206页。 (22)张天翼早期创作的历史考证,可参见沈承宽:《关于张天翼的“初作”问题》,《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4期。 (23)《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第452页。 (24)萧军入党申请书的全文,可参见方朔:《萧军入党的前前后后》,《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 (25)施蛰存:《〈现代〉杂忆》,《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 (26)关于《倪焕之》的版本考证,可参见金宏宇:《〈倪焕之〉的版本变迁》,《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27)关于《呼兰河传》的版本考证,可参见章海宁:《〈呼兰河传〉校订记》,《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5期。 (28)吴福辉:《沙丁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120页。 (29)关于《马兰》的写作时间问题,可参见刘增杰:《师陀小说漫评》,《河南师大学报》1982年第1期。标签:夏志清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我在霞村的时候论文; 沈从文论文; 小说月报论文; 骆驼祥子论文; 读书论文; 边城论文; 鲁迅论文; 老舍论文; 张天翼论文; 灭亡论文; 丁玲论文; 巴金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