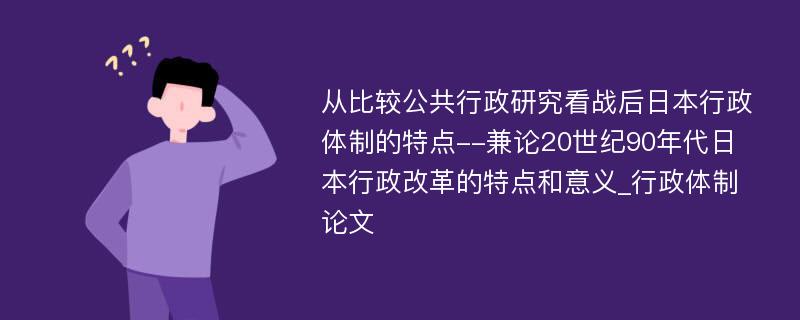
从比较公共行政研究看战后日本行政体制特征——兼论90年代日本行政改革的特质、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行政论文,战后论文,特质论文,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行政体制包含与政府行政相关的制度、组织结构、人事管理及其经常性的运行机制等基本内容,而传统行政学往往出于对组织目标的实现这一现实的效率价值追求,更多地关注行政体制所表现出的政府组织运行的内部管理功能。关于日本战后行政体制的讨论,还需要扩展到组织管理之外的政治功能范畴,分析行政组织及其成员在与国家意志形成相关的政治体制或政治系统中的角色定位、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等政治性特质。
探讨不同政治体制之下的政府行政模式的比较公共行政研究,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向战后脱离宗主国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输出行政管理技术的60年代达到鼎盛,后有所衰退,进入90年代之后又得到发展。比较公共行政研究是将“公共官僚机构”作为分析单位,其代表人物之一费勒尔·海迪重视官僚制分析框架,从行政组织结构、人员管理以及高级官僚群体与政治系统的相关关系三个层面,总结不同国家行政体制特征。
在日本行政学中,官僚制分析框架也得到广泛应用,被证明是一种非常成熟和适合解析日本行政体制的分析工具。同时,对于日本而言,比较公共行政研究尤其需要解决的也是“官僚制的民主控制或官僚制的民主化”这一特殊课题。①而海迪的研究正是将作为中观理论范畴的官僚制作为“比较的手段”,使用“行政官僚机构是特定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系统下的一个次级系统”的研究路径。②这一研究手段和路径以及综观海迪的论著《比较公共行政》所抽象出的以下比较公共行政分析视角,有益于分析日本的相关课题:民主化转型与行政发展;现代化不同发展阶段上的行政发展;“殖民地性”与行政发展;制度、理念与现实之间存在的差距,以及与此相关的行政文化、传统的影响等。③
换言之,这些分析视角是海迪比较公共行政研究探讨各国行政体制的基本方法。运用上述分析视角来说明行政官僚制组织优越和集权型政府体系,以及与此相关的20世纪90年代日本行政改革等则更为适用。因此,本文尝试运用比较公共行政研究的方法,分析日本战后现代行政体制的基本特征,并通过探讨90年代中央政府行政机构以及政府体系的战后变革,深化本文关于行政体制特征的讨论,最后提出行政发展和转型的课题。
一 比较公共行政视角下的战后日本行政体制特征
战后建立和发展的日本现代行政体制,与明治以来的行政体制具有较强的连续性,日本行政学家辻清明关于这一命题做过很多研究。④以战败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及其推动的民主化改革为契机,日本进入了与战前政治体制诀别的新时代。宏观环境的变化以及战后日本的发展,使得战后日本行政体制得以建立、形成。⑤至今,日本行政体制改革仍处于不断摸索和转型的历史阶段。
(一)比较公共行政分析视角的应用
向制度主义回归的以官僚制为基本分析框架的比较公共行政研究,对于研究和总结战后日本行政体制特征具有一定的效用。为了对各国的行政体制进行比较,比较公共行政研究将分析各国政府官僚制的重心置于不同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行政历史传统、行政发展等层面,这更适用于对仍处在变化中的日本行政体制的探讨。我们着重思考比较公共行政研究关注的条件因素对战后日本现代行政体制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与作用。
第一,行政体制容易受到外部环境条件的影响,且作为政治体制的下位系统而直接受到来自政治系统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化改革以及新的宪法制度框架就成为决定战后日本行政体制的最根本因素。同时,战后的选举制度、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政党政治、政党执政时间就成为分析战后日本行政体制特征的关键词。
第二,为便于国别比较,比较公共行政研究用“殖民地性”来观察不同国家间的行政技能转移现象。就日本而言,战后初期美国为贯彻统治政策而实现对日本的有效占领,全力推进了政治、行政层面的制度、技术输出,使日本战后行政体制正如“外力”、“外压”、“模仿”等用词表现的那样,直接或间接、主动或被动地移植了国外的制度和方法并对其加以改造、修正,从而具有了一定的“殖民地性”特征。
第三,对比较公共行政研究而言,官僚制分析视角被作为最为有效的理论框架,包含行政组织(政府体系等)、公务员制度以及官僚制组织及成员与政治等外部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近代以来形成的天皇专制国家体制之下的中央集权模式,以及由此培植和发展出来的官僚制传统和文化,在民主化改革后仍得以延续,行政官僚制具有的从属于政治结构的工具性特征以及自发地与国家一体化的效率性特征也被传承下来。战后日本官僚从属的目标由战前的天皇改换为美国占领当局、自民党、内阁以及国会等。⑥这一官僚制传统或文化、规范及其受到战后影响的嬗变,是观察战后行政体制特征的核心内容。
第四,现代化与行政发展的相互作用。前述的民主化以及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都被日本作为国家发展目标而一贯追求的旨在国力提升的工业化政策,都是现代化命题的主要内容和课题,也是决定战后日本行政活动的重要价值取向。⑦而且,在战后现代国家发展过程中,二者时而相互呼应,时而关系紧张,从而使日本的行政体制总是带有政治性与技术性特征,并被反映到行政改革之中而作为行政发展的课题显现出来。由此,我们可以导出战后日本行政体制具有的政治性、自律性和发展性。
(二)战后日本行政体制的基本特征
以下就战后日本行政体制的基本特征进行具体分析。
第一,战后日本确立了以国民主权为基点的现代行政体制的民主性特征。伴随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民主行政成为战后行政改革的目标以及评价政府行政的标准。这可以归因于战后初期日本在美国主导的制度变革中所确立的国民主权宪法理念。例如:作为行政权最高机构的内阁成为国民的代表机构、最高权力机关——国会的执行机构,战后诞生的公务员制度,使政府人员由天皇的官吏转换为全体国民的服务者;地方自治制度的建立,不仅使政府间关系被赋予民主性内涵,而且地方公众还获得广泛的政治参与权,出现了地方民主治理的崭新局面;除了国会、地方议会对行政体制的政治控制得以实现,战后的言论自由等也使社会舆论对政府行政的民主监督成为可能。
第二,国会制定和健全行政法律,使行政体制的法制性得以增强。在发达国家中,日本行政制度的法律化程度非常高。中国学者对日本行政法律体系的完备程度,给予很高评价。⑧这与战后行政体制的民主性特征具有较强的关联。同时,正因为法律规范化程度较高,因而不仅保证了法律制度对政府行政的有效规范和约束,同时行政活动的自律性和稳定性也得到了保障。因此,在民主政治的国家制度之下,仍能提升行政效率以及现代行政官僚制的成熟度。例如,日本的宪法、内阁法、国家行政组织法、国家公务员法、总定员法、各省厅组织法等,就是如此。
第三,以民主性、效率性为目标的行政体制变革性特征。战后日本行政体制的发展,可以说是一部行政改革史。例如,以追求内阁功能的实现为目标的强化综合协调以及内阁领导力等改革,贯穿战后日本行政改革活动的始终,其中还内含了促进民主行政的改革意义。除此之外,还有追求人员、机构精简等的行政机构改革。20世纪80年代的民营化改革,推进政府功能的作用转换。⑨而且,正由于日本行政组织具有较高的自律性,在区别于行政改革的另一个层面,在政府组织管理中,推动了可与行政改革活动相匹敌的行政体制运行的自我完善,提升了行政效率。为此,行政系统中的综合管理部门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在国家目标设定上,体现出中央政府行政官僚组织的主导性、能动性以及优越性特征。战后日本面对的课题不仅是民主化,战败后的经济复兴以及之后的经济发展也是艰巨的国家课题。众所周知,在战后发展过程中,经济企划厅、通产省等日本经济管理部门积极推进国家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发展,运用产业政策和行政指导等政策手段,为创造“日本奇迹”做出了贡献。这既是行政体制自律性的特征,也是战后自民党长期一党执政的特殊政治结构之下日本行政体制所具有的“官僚中心主义”特征⑩,今天则被作为“官僚政治”的表象而受到诟病,从而使战后日本行政体制内涵承载了发展性课题。
总之,行政结构及其功能和实际运行机制所表现出的现代行政体制,作为政治体制的主要构成要件之一,在日本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战后,日本的国家发展目标逐渐实现了向经济国家政策和福利国家政策转移,作为中央政府的“国家”全面参与社会管理的现代国家特征更为显现,战后行政体制全面融入公众生活的具体层面,发展成为维持和支撑社会运行的基础要件。
二 “超稳定”省厅体制及机构改革的特质
行政体制以及比较公共行政的研究,正如前文所言,通常是以行政官僚制特别是以政府机构和作为政府体系主要内容的政府间关系以及行政人员管理等为切入点而展开的。关于后者,海迪的比较公共行政研究主要围绕日本高级官僚的管理及行为方式进行了探讨,同时笔者在以往研究中就此也做过分析(11),不再赘述。下面主要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政府机构和政府体系的变革这两个决定战后日本行政体制转型的行政改革基本内容的回顾分析,深化行政体制特征的探讨。
(一)“超稳定”省厅体制的形成机制
日本中央政府行政机构基本上由三个层级构成,即省厅、局、课,被规定在行政组织法、各省厅设置法、政令、省会等中。机构编制法制化,特别是法律化机构管理模式,是形成行政机构长期稳定态势的原因之一。1960年以来,包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在内的40多年时间里,日本省厅体制实现了长期稳定不变。这一方面衍生出前文谈到的日本行政官僚制稳定性、自律性特征,而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仍能维持较为稳定的机构编制,确实耐人寻味。这与同处高速发展时期的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则显得非常必要。
战后日本改变了以往调整省厅以下机构编制仅靠内阁、省厅裁量的管理方式,早在1948年就把课的设置定为法律决定事项,将最基层的组织单位——课的编制,完全纳入法律、制度性的政治控制范围之内。而且,根据1969年的总定员法,国家公务员的人员总数上限也成为法律决定事项。由此,中央政府的组织、人员编制实现了法定化。其结果是,虽然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出现了行政需求巨大增幅,但由于有基于法律规范的制度性控制,机构和人员的增加得到了抑制。
在经济低速增长时期,1984年各省厅官房和局以下机构以及派出机构的设置,改为由内阁制定的政令决定。负责机构、人员编制管理的行政管理厅行政管理局以及后来的总务省行政管理局等综合管理部门,与预算编制和法律修订相联动,通过编制审查制度,对机构和人员进行核定和调整,政府官僚制带有较强自律性的自我管理抑制住了行政规模扩张。(12)从结果上看,日本的行政规模在发达国家中是最小的。
由此可见,组织管理与行政管理的效率化,不仅需要法律制度等外部制度性控制,同时组织内部自主、自律的积极管理也具有重要意义。或许这也符合海迪总结的日本官僚制所具有的“弹性和适应性”特征。同时,前者实现的前提是有像日本政府行政那样对统一的法律制度以及规则、秩序的尊重,即如何贯彻官僚制基本原则的问题。因此,仅从比较公共行政研究关于不同国家官僚制成熟度的测定指标来看,日本在行政组织制度和管理层面表现显著,即较彻底地贯彻了现代行政官僚制组织应当具备的基本原则。
(二)官僚制民主化前提下的省厅体制改革
1993年,自民党长期一党执政的历史画上了句号,而这一时期实行的大规模行政改革也昭示着“超稳定”省厅体制的终结。因此,从比较公共行政研究来看,政治系统的变动对行政组织的制度及其运行影响是最直接的,甚至会引发巨大变革。而此次改革同世界规模的旨在“治理转型”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相联动,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关发达国家改革的比较成为比较公共行政研究的热点。
2001年改革之前的日本中央政府机构为1府22省厅,还有内阁中的内阁官房和法制局等,负责政府政策综合协调。当时的省厅组织体制中由政治官员——大臣担任行政首长的政府部门有:总理府本府、金融再生委员会、国家公安委员会、总务厅、北海道开发厅、经济企划厅、防卫厅、科学技术厅、环境厅、国土厅、冲绳开发厅、法务省、外务省、大藏省、文部省、厚生省、农林水产省、通商产业省、运输省、邮政省、劳动省、建设省、自治省。
改革以后的中央省厅最终改为1府12省的基本架构。内阁府内设经济财政咨询会议,以强调对预算等重要政府政策的政治主导,其目的在于减少政治性行政官员参与决策过程的机会,扩大政治控制的范围。由大臣任行政首长的政府部门有:总务省、法务省、外务省、财务省、文部科学省、厚生劳动省、农林水产省、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环境省、防卫省、国家公安委员会等。
以中央政府机构减半为目标的大规模机构重组,是日本时隔40年来的省厅重组改革。对超稳定的省厅组织结构进行改革,是在被称为“失去的十年”的90年代推进的,改革的时期以及规模,耐人寻味。当然,改革成果不仅在于数量上的减半,还包含了确立战后日本行政体制中的政治主导、应对多样化的行政需求、克服条块分割、重视行政活动成效等旨在公共行政变革的改革内容。
改革成果还包括:对准政府部门进行改革,创设了独立行政法人制度,其目的在于将政府中的决策环节与政策实施环节分离;审议各省厅基本政策的审议会的数量,由176个减少到96个,课的数量由1200个减少到1000个,人员也由83万降低到36万。(13)改革政策的目标也包含了如何削弱行政系统的政治决策功能。这一系列的改革,包括下面要探讨的地方分权改革,都是“治理转型”层面的改革。
现代国家的行政改革即便是仅仅改换行政部门的名称,也会触发对行政体制周边的利益进行重新调整,会给一个国家的政治乃至社会经济等带来巨大影响,行政官僚制优越的日本则更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来看,20世纪90年代大规模的省厅改革是如何完成的,对于本文关于战后日本行政体制特征的探讨以及比较公共行政研究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课题。(14)
第一,依法行政改革的推进方式。与很多国家不同,长期以来,日本的行政改革灵活运用法律政策手段,从改革的准备阶段一直到改革成果的保障,往往通过制定众多法律的方式推进行政改革。这不仅适应了战后现代行政体制的特征,保证了改革的推进,也与改革内容实效性的提升紧密关联,更为重要的是适时将国民的意志反映到了行政改革之中。
第二,行政学家、经济界、新闻媒体、社会团体、政府人员等多元主体长期参与改革方针计划的顶层整体设计。这一改革方式,是20世纪60年代学习美国行政经验的结果,一直延续至今。其功效在于政府外部专家等的具体意见不仅能够广泛反映到改革之中,同时还能通过各阶层的参与,即时进行利益协调。这既可以提高行政改革计划的有效性,还可以提高改革计划决定后实施的可行性和实效性。这种制度安排与现代国家行政改革内容的特殊性有着密切联系,同时在行政官僚制优越的日本也是非常必要的。
第三,日本行政机构改革的外延远远超过了机构编制管理的范畴,涉及如何确立政治主导、改革政府外围组织以及转变政府间关系等。行政机构改革涉及决策机制的转变和政治体制改革,是行政体制的结构性变革和转型。这是日本行政机构改革被称为“行政改革”的原因和理由所在,也是战后行政体制和行政改革的特征所在。
总之,从以上探讨可以发现,作为战后日本行政体制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规范条件下的政府组织管理,一方面被置于国会或内阁的政治控制之下,另一方面这种“总量规制”的运行机制又具有较强的自律性内涵,在抑制政府规模上具有积极意义,并保持了官僚制组织结构的长期稳定性。(15)而这一日本行政官僚制组织所具有的强烈的自律性或稳定性特征,就是其优越性的源泉。20世纪90年代省厅体制改革打破了这一超稳定结构,使日本行政体制具有了变革性特征。(16)同时,这一机构变革发生在日本社会的改革运动推动之下,并在行政改革法律的控制管理范围内,最终使其外延拓宽至回归政治代表机构、执政机构优越等适应宪法理念的“政治主导”变革层面,而具有了非常强烈的破除官僚政治的“政治性”特征。
三 宪法理念、集权型政府体系与分权改革的意义
海迪虽然没有就战后行政体制下的以中央与地方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政府体系进行国家比较分析,但从其对日本现代行政体制历史成因的评介来看,也非常重视传统“中央集权封建主义”、“中央集权行政”的影响。同时,他基于比较公共行政研究视角得出的关于日本高级官僚长期在政治权力框架中处于中枢地位,其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发达国家官僚所占据的地位”的结论,直接指向的是中央层面的行政官僚制,而且最终关注的是官僚制的政治控制课题。(17)而日本行政官僚制的优越,应该涵盖它对地方政府的实际决策所保有的巨大影响和作用。这恰恰是日本20世纪90年代提出地方分权改革的最直接动因。
(一)日本行政学中的比较研究与地方自治命题
日本行政学长期以来将日本的政治与行政的关系以及政府间关系作为研究的重点,而且经常以民主制、议会内阁制等为切入点讨论日本行政体制,并通过与国外的比较发现日本地方自治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模式及问题。与传统美国行政学相比,日本的行政学更具有较强的政治学、制度学以及政策学色彩。
这主要是由于民主化改革之后,日本的行政发展同时面对民主与效率价值如何实现的双重课题。辻清明在新版《日本官僚制研究》中就此做了充分探讨,基本研究方法恰恰是通过传统与现代、日本与欧美的比较,然后运用政治学和行政学分析框架抽出特殊日本课题、提出变革方案。这里需要关注的是,近代以来日本建立的中央集权行政体制,正是战后遭遇到了地方自治的创设,因而使新的地方制度承载了这一双重课题。如何整合新制度与旧有的行政传统,如何破解这一双重课题,这对日本行政学来说就成了最贴近学科发展的研究主题。
因此,关于政府体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地方自治等的日本行政学研究是依存于日本特殊的时代条件的。地方自治制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90年代又迎来较大的变革“中央政府集权式管理”(18)的机遇。从这一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日本地方自治制度的发展及变动,如果能与其他实现民主化改革,而且开始由中央集权体制向分权体制转变的国家展开比较,则更有意义。
日本的近代是从建构现代国家开始的,即建设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因此,为了打破明治之前的封建体制、摆脱来自西方列强的威胁,向战时体制转变,日本建立了强固的中央集权统治结构,而地方自治受到轻视和压制。战后在美国占领当局强烈作用之下,民主政治形式的地方自治制度进入日本,政府体系发生了较大变动。而之后的长期制度实施过程中,又经历多次修正、制度调整,集权型中央与地方关系也不断成为政治争论的焦点(19),最终引发了90年代地方分权改革。可以说,日本的地方自治问题同官僚主导、政治主导等政治问题、行政问题一样,是带有浓厚政治特征的行政学课题。
(二)集权型政府体系与回归宪法理念的分权改革
地方自治制度是战后基于新宪法关于地方自治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具体而言,就是地方政府的组织与运行必须要以地方的自治为根本,这也成为今天日本地方分权改革的目标。与传统的地方制度相比,战后自治制度最大的变化是对现代民主政治原则和理念的贯彻。同时,地方政府还被赋予了自治权能,即财产的管理权、事务的处理权、行政权、地方立法权(制定条例)等。
地方民主治理的强化是战后日本地方自治制度的最大亮点。这首先是日本的宪法、地方自治法以及公职选举法所保障的地方选民直接选举地方行政首长、议员的权利。其次是地方居民被赋予了条例制定、修改和废除的请求权以及地方行政和财政事务审计的请求权,解散议会、罢免地方官员的请求权等。由此,基于地方居民政治参与的对地方政府行政施以民主监督的制度得以创设,地方居民的利益表达得到了多项正式制度的保障。因而,地方在制度上成为完全自治单位。
不过,地方自治制度在日本的政府体系中,受到以往中央集权传统的侵蚀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日本政府体系表现为三个层级:作为国家的中央政府、作为相当于中国省级政府的都道府县政府(47个),以及作为基层政权的市町村政府(由过去的3087个,经过合并减少至1788个,另外还有23个特别区)。(20)与很多国家不同,日本“政府”被限定在中央政府层面,“地方政府”一词并非一般用语,仅为部分学者而且还是近年才被使用。作为法律用语,一般使用“地方公共团体”,常用词是地方自治体或自治体。
日本推进的地方分权改革,一直被定位为中央政府“行政改革”的一环或者附带。因此,虽然地方自治制度在宪法等法律层面得到明确规定且为日本宪政的基础,但在实践中其本来的地位和作用并没有充分显现。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到战后日本政府体系中中央政府主导、“国家”主权色彩的强烈。因此,战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制度规定的对等的政府间关系、完全自治单位的地方政府形态并没有充分表现出来。
这里主要的争论点在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的限制以及干预,即日本长期争论的“在其他发达国家极其少见的日本独特的机关委任事务制度”和中央对地方的大量财政转移问题。由此,作为完全自治单位的地方政府要实施大量中央委派的行政事务,同时受其全面干预,而且在财政来源上过度依赖中央财政。(21)因此引发了地方自治质量下降、自治权萎缩、中央权力过度集中等批评。不过,战后政府体系中表现出的中央集权特征,存在传统行政运行方式的连续性因素,同时,战后公共政策的转型以及由此伴生的行政服务扩充而出现的新的中央集权要求也不容忽视。
我们在思考那些正在推进现代化的后发国家行政改革时,以上内容则可以成为非常好的比较因素。而且,这一中央集权的必然性特征,也对我们思考实施福利政策国家的行政改革非常有效,同时对那些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国家进行比较研究也很重要。
日本实现了工业化发展目标之后,行政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公众的公共需求多样化趋势较为显著。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20世纪90年代,日本第一次开始了大规模的地方分权改革运动。其发端于政治改革的动机,即日本的社会思潮越发认识到中央集权体制的逆功能:日本的根本问题在于中央集权体制之下形成的利益结构以及如何去消除;其改革逻辑是通过向地方自治这一宪法理念的回归,以及修正制度与现实的差距,去真正解决日本的问题。
由于当时的财政危机所带来的中央政府能力的弱化,人们意识到有必要确立地方政府的责任意识和主体性,同时出于应对冷战后新的国家课题,需要中央政府从国内活动中部分退出,并通过地方分权来克服一系列的问题。前面谈到的如何应对公共需求的多样化以及公众政治能力、政策能力的提升等,使得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成为必然。更出于公共服务的基本特性,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地方政府的积极作用,推动了90年代“第一次分权改革”的实施。(22)
此次地方分权改革取得的最大成果,首先是全面废除了机关委任事务,将其分割为地方政府的自治事务和法定的中央委托地方的事务。地方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来控制管理,因而提高了地方政府的自治性和自律性,促进地方政府向宪法意义上的完全自治单位回归。其次是通过引入新的行政程序和规则以及司法救济等干预法制主义手段,对中央政府的干预加以严格规制,规范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23)
总之,这些改革措施具有提升地方政府决策和执行的自律性,改变地方政府以往作为中央政府派出机构的角色定位,以及向日本战后宪法所倡导的作为完全自治单位的地方政府回归的积极作用,创造了变革长期以来的中央优越集权体制、统治结构和战后行政体制的基本契机。而比较公共行政研究关于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行政改革的分析中,也认为地方分权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认识到这一变化的重要性在于如何确保对政府官僚制的政治控制。(24)这与日本的改革思想,如出一辙。
四 战后日本行政体制的特征与行政发展的课题
以上探讨了日本战后行政体制的基本特征以及与此相关的20世纪90年代行政改革的特质、意义。在此,我们将二者结合起来展开论述,进而深化战后行政体制的讨论,提出日本行政发展的课题。
本文就战后日本行政体制的基本特征以及政府组织的运行机制和行政改革的特质、意义的概括和分析,主要是基于战后日本进一步凸显的职能国家、福利国家、行政国家等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而导出的,同时它还与二战后民主转型过程中逐渐暴露出的非常现实的日本问题,以及明治时期以来建立的集权国家体制之下中央政府行政优越的传统统治模式紧密相关。日本在战后现代化和民主化过程中,也在克服和超越这些问题和课题,特别是尝试运用组织管理变革以及行政改革的方法解决行政体制发展中显现的效率问题,还进一步努力克服与宪政制度不相适应的统治结构存在的问题。
与此相关联,毛桂荣从“内阁与省厅组织编制”、“政官关系(政治与行政)”、“官民关系(政府与社会)”、“政府间关系(中央与地方)”、“政府规模的控制”等五个基本层面,总结出日本“战后型行政体制”的基本特征,即“割据性、官僚优越、集权、规制等”。在此基础上,指出了构建“21世纪型行政体制”的行政改革课题,即“政治控制、分权、行政的减量与精简、确保行政透明性”。(25)
这些改革课题是基于战后日本行政体制的运行以及行政改革的实践而得出的,也与本文的探讨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而本文基于比较公共行政研究对战后日本行政体制特征的分析和总结,更注重行政体制发展史中传统与现代的阶段性以及行政价值的差异,进而抽象出战后日本行政体制的基本特征。而且,本文提出的相关特征要素,只要是世界上实行行政官僚制的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类似的行政体制特征。恰恰是这样,使我们拓宽比较公共行政的研究成为可能。同时,这些特征随着公共行政环境的变化等,其具体内涵和外延也会发生变化。如果考虑到政策目标、行政制度与行政活动的具体实际之间存在差距等复杂的行政现象,特别是日本2009年出现了一党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向民主党的政权转移,那么行政改革的经常性会进一步加速,今后很有可能发生更为深入的变革。
以上结论,还通过本文探讨凸显“政治主导”的省厅体制改革以及旨在打破传统集权统治结构的地方分权改革而展现出来。时至今日,这些改革仍在继续,还不能看到最后的发展结局。关于前者,在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中民主党政权推动的从“官僚主导型”政治向“政治家主导型”政治转型的改革受到很大挫折。关于后者,虽然在小泉内阁时期推动了旨在向地方下放财权的“三位一体”改革等,但仍然没有完全克服改革课题,民主党政权提出的“地方主权”构想也被束之高阁。(26)
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为未来的改革预留了努力的空间,也成为日本行政发展的课题。在这里还需要关注日本政治学家松下圭一在其论著中就当前日本所处发展阶段作过的总体概括:日本经历了现代国家建设、经济发展等现代化发展的各个时期,但由于没能适时构筑适应新的发展阶段的“先进国家型”自治和分权的市民社会,因此作为现实问题,日本出现了政治不成熟、政府行政劣化、经济老化、财政破产的现象。同时,以20世纪90年代地方分权改革为契机,日本的政治、行政和政策制度由此进入到了向先进国家型自治、分权重构的“转型”时期,行政体制开始出现结构性变动。(27)
正如本文论证的那样,在战后民主政治、经济社会高度发展这一宏观框架下观察日本战后行政体制,今后行政体制的变动也应该总是被置于既定的宪政价值和结构之下,是无法与战后政治和公共行政的基本命题相脱离的。而这恰恰构成了日本当代行政发展的基本内涵和方向。关于这一“长期走势”,在有关发达国家的比较公共行政研究中已经得到证明。(28)
最后,我们可以说这一发展特征使我们比较研究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和其他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行政体制、行政改革成为可能。正如参与过90年代地方分权改革的西尾胜所感慨的那样,要使未来地方分权改革获得更大成功,“不强有力地推进日本政治结构改革是不可能的”(29)。这一阐述指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对于行政体制改革、行政发展所具有的决定作用。这又让我们回到本文关于战后日本行政体制基本特征的最初讨论,即政治系统对作为其下位系统的行政体制的作用等,也让我们更加认识到了比较公共行政的功用。同时,如果需要对海迪的分析框架加以修正的话,本文通过对90年代两项改革政策的总结所得出的回归制度或宪政理念的行政发展分析视角,则可以作为补充而提出。
注释:
①西尾勝·村松岐夫編『行政の発展』、有斐閣、1994年、142頁。
②参见马骏、叶娟丽:《西方公共行政学理论前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78~192页。西尾勝·村松岐夫編『行政の発展』、109~156頁。
③参见费勒尔·海迪:《比较公共行政》,刘俊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④参见辻清明:《日本官僚制的研究》,王仲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
⑤旅日中国学者毛桂荣通过综述不同学者的观点,提出日本“战后型行政体制”的“大部分是在战后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形成的”。参见毛桂荣:《近20年来日本的行政改革》,载宋志勇、王振锁主编:《全球化与东亚政治、行政改革》,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0~171页。
⑥海迪将此称为“日本官僚的弹性和适应性”,认为是“日本官僚制度的一大优点”。但同时指出:“这种弹性和适应性不是建立在官僚对政治制度保持中立态度之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它能顺应瞬息万变的政治气候之基础上的。”参见费勒尔·海迪:《比较公共行政》,第274页。
⑦海迪也认为日本行政官僚制的特征是“与现代化相适应的行政”,而且在现代化转型之初官僚就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参见费勒尔·海迪:《比较公共行政》,第265~266页。
⑧参见蒋立峰主编:《日本政治概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252页。
⑨参见白智立:《日本的行政改革与中日行政学研究》,载北京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编:《日本学》第十六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第267~273页。
⑩海迪观察到日本行政官僚制组织优越产生的原因有民众的顺服、政府的权威性、精英的选拔管理制度、政治任用官员的安排、立法和司法机关等外部控制较弱等。这使高级官僚长期扮演“政治角色”、“全神贯注于政治决策过程”,造成“政治官员和行政官员之间的区别是模糊不清的”结果。参见费勒尔·海迪:《比较公共行政》,第265~278、509页。
(11)参见白智立:《日本中央政府高级公务员的选拔、开发与领导人才任用标准》,载北京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编:《日本学》第十四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白智立:《为什么日本社会不“仇官”、不“仇富”》,《绿叶》2009年第7期。
(12)西尾勝『行政学(新版)』有斐閣、2004年、368~374頁。
(13)西尾勝『行政学(新版)』、123~125頁。
(14)参见白智立:《日本行政体制的结构性转变》,第202~204页。
(15)参见毛桂荣:《近20年来日本的行政改革》,第175~176页。
(16)20世纪90年代的行政改革不同于80年代追求政府职能转变、缩小政府规模等的改革,而是变革政治决策模式的“质变”改革。参见:曽我謙悟「90年代の行政改革と政治·行政システムの変容」、『季刊行政管理研究』2003年第104号、16頁。
(17)参见费勒尔·海迪:《比较公共行政》,第266、278页。
(18)毛桂荣认为日本“战后型行政体制”包含了政府间关系中的“集权·融合”特征,这也是西尾胜比较国外制度得出的。参见毛桂荣:《近20年来日本的行政改革》,第175~176页。
(19)所谓的集权和分权是指“在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中的地方政府决策自律性的程度”,而且在这个意义上,二战前后的日本都具有浓厚的集权色彩。也就是说,战后日本政府体系与之前有着强烈的连续性。参见:佐藤俊一『政治行政学講義(第二版)』、成文堂、2007年、172頁。
(20)行政管理研究センタ一『デ一タ·ブツク日本の行政2009』、ぎようせい、2008年、54頁。
(21)机关委任事务等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中央将大部分的政府行政服务的提供置于中央的事权范围,而具体实施则交给地方执行,同时与此相关的执行方式、标准设计、实施细则等都由中央的政府部门一一规定,因此使地方失去了决策空间,破坏作为完全自治单位的地方政府的自治性。参见:西尾勝『地方分権改革』、東京大学出版会、2007年、9~13頁。
(22)西尾勝『行政学』、2~3頁。
(23)佐藤俊一『政治行政学講義』、177~179頁。
(24)费勒尔·海迪:《比较公共行政》,第485~486页。
(25)毛桂栄「行政システムの再構築とその課题」、川上和久など編『21世紀を読み解く政治学』、日本経済評論社、2000年、32~33頁、46頁。
(26)竹中平藏、船桥洋一编著:《日本“3·11”大地震的启示:复合型灾害与危机管理》,林光江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年,第168~172页。明治学院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編『初めての政治学——ポリテイカル·リテラシ一を育てる』、風行社、2011年、144~148頁。礒崎初仁等:《日本地方自治》,张青松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2~33页。
(27)松下圭一『転型期日本の政治と文化』、岩波書店、2005年。
(28)费勒尔·海迪:《比较公共行政》,第509页。
(29)西尾勝『地方分権改革』、267~277頁。
标签:行政体制论文; 日本战后改革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公共行政论文; 变革管理论文; 日本宪法论文; 宪法的基本原则论文; 政治论文; 中央集权制度论文; 宪法修改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法律论文; 中央机构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