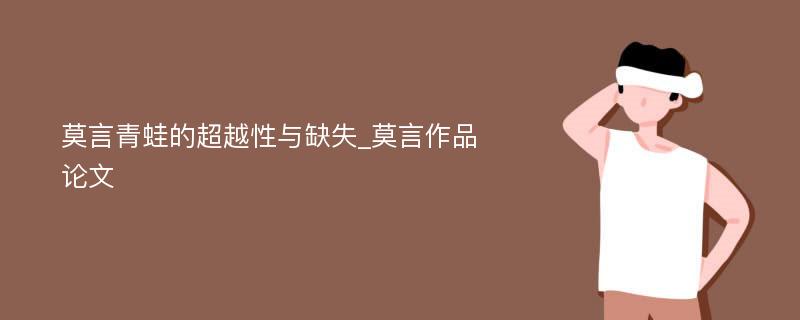
莫言《蛙》的超越与缺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缺失论文,莫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莫言自己好像挺看重《蛙》这部小说的①,得了诺贝尔奖之后,他有好几次都说起过《蛙》。这部小说的题材很引人瞩目,写的是几十年来计划生育“国策”实施过程的真实民间景象,以往很少文学作品敢于正面描写这个敏感尖锐的问题的。这么多年来,西方对我国所谓人权问题的攻击,相当一部分涉及计划生育的强硬实施。我猜想莫言获得诺贝尔奖,跟这部小说亦有关系,某些西方国家政府屡屡批评中国的计划生育违背人权,而不少西方人很想知道中国是怎样搞计划生育的。莫言敢去写,就是一个突破。记得莫言2009年在一次座谈会上也这样说过:“西方老是批评中国作家不自由,不敢触及尖锐复杂问题,《蛙》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回答。”
不过《蛙》这部作品比较复杂。它在艺术上显然有所超越,高出于当代许多作品的艺术水准,是一部杰作,但并不意味着这部小说已达到作家预期的审美境界,它是留下了某些缺失的。
繁复的悖论性的感受空间
莫言是如何处理这个复杂的题材的?阅读全书,感觉莫言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态度有点暧昧。一方面,作者在作品中多有提到,从中国的国情考虑,必须坚决实行计划生育。小说写到王仁美“违法”怀孕第二胎,丈夫“我”(蝌蚪)宁可开除党籍,苦苦哀求姑姑不要把王仁美拉去做流产,让妻子把孩子生下来。姑姑斩钉截铁地说:“计划生育不搞不行,如果放开了生,一年就是三千万,十年就是三个亿,地球都要给中国人压偏啦。所以不惜一切代价把出生率降低,这也是中国人为全人类做贡献!”类似的正面表白,姑姑等人重复多次,这也可以看作是莫言的观点,他借人物之口述说计划生育政策的必要。但小说主要不是写这个“必要”,而是写实施之难,实施之痛,是实施过程中那些让人揪心的事情,那些悲剧。给已经生育的男人结扎,让已经生育的怀孕妇女流产,是小说中心人物“姑姑”的两件大事,许多情节都围绕这些事情展开。村民若违抗,则强迫执行,不惜推倒房屋,甚至逼出人命。当“违法二胎”的家人藏匿孕妇,拒不交出,姑姑就开着拖拉机带领人要拉倒孕妇家的房屋。这时作者又借用姑姑的话说,“我知道这没有道理,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什么是大道理?计划生育,把人口控制住就是大道理。我不怕做恶人,总是要有人做恶人。……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部小说就是写“小道理”与“大道理”的矛盾和悲剧,作者是难免有些暧昧犹疑的。
但这可以理解,也许这种暧昧和犹疑正是小说的好处,甚至使小说产生繁复的甚至是悖论性的感受空间。如果只倾向“大道理”,等于是图解政策;如果一味渲染“小道理”被挤压的悲情,那又“出格”了,可能出版都有困难。莫言在这个尖锐、敏感的“国策”题材上,还是把握得有分寸。很有意思的是,据说当年这部小说获茅盾文学奖时,争议很大,特别是计划生育部门很反感,但报到主管文化部门的官员那里,说这是小说嘛,就网开一面了。看来人们还是能从文学的角度,体谅作者这种暧昧和犹疑的。生活中很多事情很难说绝对是好是坏,对计划生育这样的大事也是这样,看从什么层面去评价。
莫言主要还是从精神层面去写的。小说写近30年北中国农村的生育史,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所引起的巨大的精神变迁历史,里边有现实的无奈,历史选择的困境。那些千方百计违抗政策“超生”的人们,他们是为什么?为传宗接代,延续香火,是要养儿防老。这是非常顽固的观念,也是很实际的需求,你可以说它“落后”,但不能否认它又有合理性。在缺乏完善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制的情况下,这些观念总是生生不息,不可能靠政策实施就根除。《蛙》写出了这种实际,这种两难,特别是写出了那其中容易被遮蔽的民众的无奈与悲凉。对这种困境是难于做道德评判的,你说计划生育不人道?“姑姑”是可恶的坏人?或者完全同情那些为“超生”而挣扎的行为?任何简单的道德评判都会让我们犹疑。好在莫言也没有做非白即黑的评判,他用艺术之笔表现了“政治合理”之下的无奈与悲凉,这也正是小说感人之处。多少年后,读者从莫言的笔下会多少了解到我们民族和国家这段复杂的历史,这就是个贡献。
触及令人困惑的生命及生殖伦理主题
《蛙》的成功,不光是写出历史的部分真实景象,还在于它深入到了人性探究的层面。计划生育政策实施面对巨大的障碍,其中除了传统文化观念与现实需求,还有更深层次的人性的挑战。食色性也。性欲、生育、延续生命,是人性的根本需求,几乎所有民族都曾有过生殖崇拜。即使到了现代社会,这种生殖崇拜的意念仍然或明或暗地存在,特别是在农村民间。在小说的最后一部分的剧本中,作者曾借蝌蚪之口说了这样一段话:“(剧本)暂名青蛙的‘娃’,当然也可以改成娃娃的‘娃’,当然还可以改成女娲的‘娲’。女娲造人,蛙是多子的象征,蛙是咱们高密东北乡的图腾……”其实,那些顽强地反抗计划生育政策的行为背后,都有某种人性的“原动力”,也就是生育和传承生命的“力”,这种力何等强大!所以高密东北乡那些“超生户”,拼死也要生下孩子!姑姑的“事业”就是动员国家力量去控制和压迫这种传承生命的“力”,可以想象何等艰难凶险,又何等无奈。读小说,我们对那些“超生户”都无不寄予极大的同情,尽管理性上也不赞同他们的行为。这就是人性吧,人同此心。
《蛙》中最能体现人性剖析深度的,还是“女性的本能”描写。传宗接代,是婚姻的目的,也是女人的唯一使命,它决定着女人的一生。固然可以说是人性的表现,同时也是传统意识,比如重男轻女,这一思想几乎渗透到所有女人的灵魂深处,是那样根深蒂固。蝌蚪的前妻王仁美已经有了女儿,但非得再生个儿子,甚至不惜让丈夫为“超生”而抛弃前途,结果自己也为此而送命。小狮子本来是计划生育的推行人员,自己不能生育,有些神魂颠倒,也要想办法借腹生子。她们对生儿子的狂热,已超出一个母亲对孩子的爱,骨子里只是希望通过儿子得到一个“正常女人”的名分,获得一种存在感——好像没有生儿子的女人就不是真正的女人一样。整个《蛙》几乎全都是围绕这种普遍的“追求”而展开,其实内里就是一种人性的描写,带有批判及反思的描写。
围绕“生孩子”展开的有些描写可以说惊心动魄,触及到生殖伦理问题,感人至深。比如写王胆当“超生游击队”,避难逃离到船上,姑姑带小狮子等一干人马乘快艇追逐,要让孕妇把胎儿做掉。姑姑的船很快就追上王家的木筏。王胆尖叫求姑姑高抬贵手放条生路。此时姑姑的助手小狮子似乎嗅到产妇“圣洁的血的味道”,心生怜悯,就假装落水,冒着被淹死的危险来故意拖延时间,对河中的神灵祈祷,让王胆快生。家人手持常杆,摆出要和姑姑拼命的架势。陈鼻在筏中揽着王胆,也哭喊着快生!快生!生出来她们就不敢捏死!泪水顺着陈鼻这个大胡子男人的脸滚落下来。与此同时,王胆发出撕裂肝肺的哭叫声。姑姑见此探身要上木筏,陈鼻凶神恶煞摸出刀子:把你的魔爪缩回去!姑姑平静地说:这不是魔爪,是妇产科医生的手!本来是要追逐王胆,让她做引产的,现在却变成要接生。接下来就是侧面烘托描写:大河滚滚,不舍昼夜。重云开裂,日光如电。姑姑双手托着这个早产的赤子。
姑姑是多么强势、甚至有点“冷血”的人物,这也是她作为计划生育干部的无奈;但她对生命有一种特别的看法值得注意:不能让孩子出“锅门”,她可以为怀孕的妇女打胎,但是孩子出了“锅门”,就真正成为一个人,一个个体,必须尊重他的生存权利,要细心地保护。姑姑一方面要保护已出生的孩子,一面又在不断地扼杀未出生的胎儿,这样的矛盾,在莫言《蛙》中反复出现,几乎就成了一个横贯在读者面前、迫使我们要去思索的大问题:即胎儿是否具备生命的意义?人类有没有权利决定胎儿能否出生?我们对生命的尊重,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我们是否能从生命哲学的高度,去解释计划生育的合理性?到底如何解决或者能否解决人类的繁衍本能和社会的发展之间的巨大矛盾?等等。这样,我们就领悟到,这部小说的确有某些超越性的思维,它不满足于表现计划生育这段历史的复杂的民间景象,还想探讨一些令人类困惑的课题,包括面对生命以及生殖伦理的课题。“打胎则生命与希望消失;出生则世界必陷入饥饿。”到底该怎么办呢?这两难处境不是那些简单地指责计划生育“非人性”的西方政治家所能体会的。对此《蛙》没有简单处理,它在矛盾着,而这种文本的僵持纠结使得其在主题内蕴上超越了当代的很多作品。
“姑姑”形象的前后断裂
但我觉得《蛙》有点可惜。它触及到生命的主题,发现人类面临的某些难解的困扰,却浅尝辄止,未能做更深入的表现,甚至遮蔽了所提出的问题。我们分析一下姑姑这个人物,她的“未完成性”,妨碍了小说主题的深入。
“姑姑”原是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形象来塑造的。她出身红色家庭,父亲是八路军著名的军医。年幼时她曾有过和日军司令员“斗智斗勇”的经历。解放后,“姑姑”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从卫校毕业就当了乡村妇科医生,推行新法接生,取代旧时“老娘婆”野蛮落后的接生法,大为减少了产妇和新生儿的死亡。经“姑姑”之手接生的婴儿上万个,遍布高密东北乡,她是乡民心目中的“菩萨转世”,“送子娘娘”。小说用有些神化的笔法写“姑姑”的接生技术之高妙:她的手在病人身上一摸,十分病就去了七分。“姑姑”也曾有过美好的青春,当时高密全县不超过十块手表,“姑姑”已经戴上了一块英纳格;送她手表的未婚夫居然还是令人羡慕的飞行员。不料这个飞行员叛逃到台湾,从此给“姑姑”带来厄运。在“文革”中,“姑姑”少不了受到批斗,但不改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满怀热情投入计划生育工作。她兢兢业业,日夜操劳,努力维护计划生育先进公社的荣誉,不让一人超生。她苦口婆心动员乡民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像指挥打仗那样给已生二胎的放环,三胎的结扎,若计划外怀孕,则强行打胎,甚至不惜推倒房屋以示警戒。这些措施几乎引起民愤,乡民骂这位昔日的“活菩萨”为“婊子、母狗和杀人魔王”。可是“姑姑”“照单全收”,大义凛然,即使挨打受难,也要不折不扣实施“国策”。细读小说,能感觉得到作者是把“姑姑”作为一代有品格、有能力、有事业心的党员干部来写的,特别是小说前半部,“姑姑”无疑是正面形象,作者写到她时甚至不时还用赞美的笔调。
但请留意,到小说后半部,笔调就逐渐变了,对“姑姑”的描写不时伴有讽刺与批评,甚至流露某种厌恶。如写“姑姑”给计划外怀孕的王仁美做引产,产妇大出血,“姑姑”毫不犹疑抽了自己600cc血给产妇。这时在叙述者“我”的眼中,“姑姑”竟是“面相丑陋而恐怖”。而到了小说第4部,陡然大变,“姑姑”仿佛变了个人,从“胆大包天”变得胆小非常,她甚至被一只青蛙吓得口吐白沫,昏厥倒地。
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也许是因为时代在变,也许因为“姑姑”毕竟老了,退休了,心肠软了;但更主要的,是作者开始试图让“姑姑”忏悔了。
某个夜晚“姑姑”醉酒回家,在洼地里迷路了,感觉被一片蛙声所包围,蛙声如万千初生婴儿的啼哭。她又被愤怒的青蛙所缠绕攻击,魂飞魄散,昏死过去。是泥塑师傅老郝搭救了“姑姑”,她便嫁给了老郝。此后“姑姑”几乎人格分裂,总想到自己“手上沾有两种血,一种是芳香的,一种是腥臭的”。她经常精神恍惚地回忆并念叨各种曾被她“扼杀”的婴儿的模样,让老郝捏成泥娃娃,供奉起来,想象着他们再去投胎降生。可以说,后半部的“姑姑”和前面所说带有英雄气息的“姑姑”判若两人,也许作者本意就是要让“姑姑”忏悔,对自己多年实施计划生育的工作进行反思,同时带动读者一起反思。
但仔细分析,会发现小说这样写“姑姑”的忏悔或者反思,是很突兀的。“姑姑”承认了自己的工作是“扼杀”婴儿的罪过,等于完全否定了计划生育以及以往自己工作的合理性。这个在自我谴责与赎罪的“姑姑”,看起来似乎心理很复杂甚至有些变态,实际上是单一和扁平的,几乎就是概念驱使的人物。如果说,前三部所写的“姑姑”,在实施计划生育工作时,虽然风风火火,坚持原则,但毕竟还有内心的矛盾与困惑。所以她才会说自己要“入地狱”,才会说所做的是“大道理”管“小道理”的工作。这时期的“姑姑”形象应当说还比较丰满,但第4部之后的“姑姑”一反常态,成了另外一个人,形象也变得单薄了。问题还在于,为何“姑姑”有如此大的转变?是什么促成“姑姑”要忏悔赎罪?在作品中几乎看不到“过渡”。因为一场醉酒迷路、遭受青蛙攻击,就突然觉悟,要反思赎罪?这未免太过简单。所以,我认为“姑姑”这个人物前半部分写得还不错,这个计划生育干部给人印象颇深,但后半部分的“姑姑”就变得单薄,几乎成了概念化的人物了。
想表现“忏悔”,却显得过于简单
再说说忏悔问题,也许这是作者希望《蛙》要达到的“思想高度”。不久前在山东大学一次研究生的座谈会上,莫言回答学生关于《蛙》的提问时,也讲到在特殊的年代,许多人都做过违心的事情,可能出于某种从众的心理,比如大家都打老师,你不打,就可能会被逐出某个圈子。所以不能只要求他人忏悔,而自己不忏悔。又说,“姑姑”这个人物在革命的知识分子中有代表性,但她是忏悔的。②我理解莫言的意思是,《蛙》是要表现某种忏悔的意识。但是,“姑姑”晚年对自己所从事的计划生育工作完全否定,把自己说成“手上沾满腥臭的血”,这就是“忏悔”?相信因果报应,总幻想着无数小泥娃娃将要去投胎,就是“忏悔”?这种“忏悔”的精神内涵未免过于简单。忏悔不应当只是源于恐惧的逃脱,也不只是道德上的自责和懊悔,而应当是一种担当、再生与希望。而在《蛙》的结尾,我们就几乎看不到担当、再生与希望。这部小说的结束,给人感觉仍然是压抑的。作者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小说中叙事者蝌蚪是以书信形式与日本友人杉谷义人联系的,在第四封信中,蝌蚪开始表示要忏悔当年逼迫王仁美流产的罪,在最后一封信中,蝌蚪则询问杉谷义人:“被罪感纠缠的灵魂,是不是永远也得不到解脱呢?”蝌蚪似乎已经意识到赎罪是不可能的。这也可以理解为是作者的自白,莫言有他的困惑,而他对“忏悔”的“认识水平”并不见到高出于蝌蚪,起码我们读小说时感受不到这点,加上叙事者蝌蚪和超越性叙事者之间的关系不明确,甚至有些混同,读者总是容易把蝌蚪看作是作家本人。因此莫言虽然努力,却未能成功抵达“忏悔”这一主题的彼岸。
也许这又回到前面说的主题的悖论,在《蛙》这部小说中,我们是始终难于找到叙述者或潜在叙述者明确的态度的,这让读者卷进矛盾的涡旋中,甚至有某种晕眩感,而这种悖论的涡旋,也许就是共和国历史本身固有矛盾性的表现吧。莫言显然意识到计划生育这一“国策”带来对生命的管控与扼杀是残酷的,但如果在中国特定时期不实行这一政策,人口膨胀的后果又是另外一种残酷。这就是国家发展的政治和生命个体的矛盾,几乎是“无解”的矛盾,只容许无奈地选择其一。
莫言毕竟只是小说家,他大概并不想提供特别的“思想”或者“历史观”,他对历史的“文学叙述”主要出于感觉,他时常放纵这种感觉,在人性与欲望的旷野里奔走,难免停不下来脚步,去做深入的思索与把握。
无论如何,《蛙》放在当代文学中,或者和莫言自己其他作品相比,都显示出某些鲜明的特异性。这部小说一改过去莫言作品中常见的那种狂欢喧哗的氛围,酣畅的“语言流”,以及“重口味”的风格,③语言回归朴素平淡,书信体的叙述格局④也显得比较舒缓自然,整个作品追求某种超越感,带有哲理韵味,虽然主要人物塑造有些“断裂”,艺术上也不够完整,但我们还是看到了另一个富于创造力的莫言。
注释:
①2011年9月18日,莫言接受新浪文化读书采访,在提到《蛙》时说:这是他的一部比较特殊的小说,“它塑造的人物,小说的结构,所要表达的个人的一些想法,应该在我过去的11部作品里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②2013年4月27日莫言受聘为山东大学讲座教授,他在受聘之后与文学院研究生座谈时,说了以上这番话。
③关于莫言常见的风格之观点论述,可参见拙文《莫言历史叙事的“野史化”与“重口味”》,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4期。
④《蛙》的结构有别于莫言以往的任何一部小说,整部小说就是五封写给日本友人“杉谷义人”的信,而最后一部分竟是一部戏剧。
标签:莫言作品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