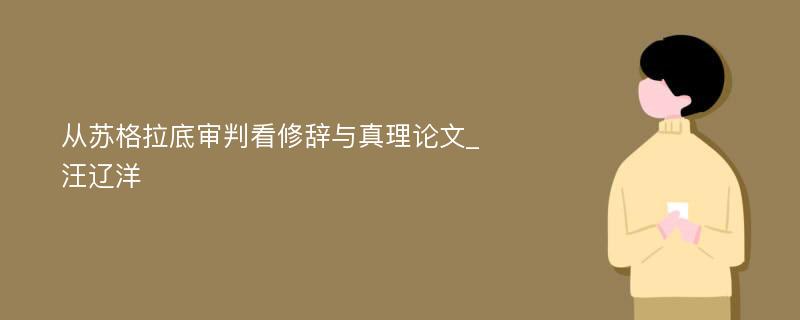
(陕西师范大学,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任何事件的发展,有必然性逻辑,也有拍案惊奇般的偶然性逻辑,这样就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历史。在人类长河中,虽然历史事件也并不仅是有情有意地展示温情脉脉,也会在有意无意之间显示某种极富思考价值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一定源于人类的某种终极价值追求,某种程度上却是源于人的好奇心,正如汤因比所说:“对人类事务进行全面研究的要求出于某些动机。在这些动机中,有些是永久性的,有些是暂时性的,有些系出于公心,有些系出于私心。其中最强烈、最可贵的一种就是好奇,这是人性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关键词:苏格拉底;审判;修辞与真理
苏格拉底审判就是这样的历史事件。后人将苏格拉底置入了西方文明祖先的神殿,所以他的死亡不再只是单纯的有关生命的新陈代谢,相反,它是西方历史上最值得解读的法律与民主事件之一。苏格拉底审判的大致经过是:公元前399年,古希腊时期的公众人物苏格拉底被迈雷托士、赖垦、安医托士(还有人译成米利托斯、吕康和安奴托斯)三人控告到雅典法庭。起诉书内容是:“匹托斯区民迈雷托士的儿子迈雷托士,宣誓陈述如下———我告发爱罗匹格区民素夫罗尼斯库的儿子苏格拉底不尊敬城邦所尊敬的诸神,而且还引进了新的神;他的违法还在于他败坏青年。我们要求将他判处死刑,以整肃城邦之法。”而后,苏格拉底被判有罪。临刑前,朋友和学生都劝苏格拉底逃走,但被苏格拉底严词拒绝,最终引鸩服判。
在苏格拉底审判中,当法庭刚开始进入实质程序阶段,控方做了两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情:一是提醒法官们苏格拉底同智者一样擅长论辩和修辞,以免被苏格拉底滔滔不绝的雄辩所吸引而被蛊惑;二是自己在提起控告时故意露出破绽,让法官们相信原告方是没有使用修辞术以及不屑于使用修辞术。控方的目的很快就达到了。面对将苏格拉底与“智者”等同的行为,苏格拉底本人极其不乐意。为此,苏格拉底在审判过程中明确提出不使用修辞术对辩护词加以雕琢。表面上看,控告方和辩护方都已经远离了修辞。可是,往深处去想想,只要有人存在,只要有话语存在,只要有需要说服的地方存在,修辞又岂会轻易缺场?可以说,苏格拉底审判交织着修辞与反修辞,全方位地展示了法律修辞学的基本要求和方法。
在审判辩护中,苏格拉底通过真理的修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以真理和正义为主旨对控方的控告进行反驳,拔高自身的内涵和品味。比如,苏格拉底在量刑阶段辩护说:“你们或许以为,我被定罪,乃因我的辞令缺乏对你们的说服力,我若肯无所不说、不为,仅求一赦,那也不至于定罪。不,远非因此。我所缺的不是辞令,缺的是厚颜无耻和不肯说你们最爱听的话。”民众甚至喜欢看到苏格拉底哭哭啼啼的求情,法官们也希望苏格拉底通过展现做可怜状以获得法官们的同情。但苏格拉底认为这是不值得的,因为他不愿意卑躬屈膝做奴才状,当然也不愿意苟活于世。在苏格拉底看来,丧失节操的苟活或者不择手段的求活是对真理的亵渎,当然也是德性的丧失。所以,“如果各位要我(苏格拉底)答应这个条件才赦免我,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虽然我对雅典人充满热情,但要我顺从大家,我不如限随神的旨意去死。只要我还在继续呼吸,还有力量,我就要爱惜知识,追求知识”。如果以卑躬屈膝的方式来获得同情,然后免死,苏格拉底觉得这不是他会做、也不是他应该做的。这正如他所说:“人中最高贵者,雅典人,最雄伟、最强大、最以智慧著称之城邦的公民,你们专注于尽量积聚钱财、猎取荣誉,而不在意、不想到智慧、真理,和性灵的最高修养,你们不觉惭愧吗?”第二是更注重逻辑和事实,这里的逻辑并不必然与修辞相对,相反,这是一种有利于修辞能力提升的逻辑,是充斥真理、正义的修辞。比如,他对所谓“败坏青年”的罪名就是从把自己区分于智者开始的:因为他既不收学费,也不传授具体的知识,而是以引导的方法来使之“自悟”,所以不存在蛊惑青年的问题。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而且,那些青年都是自动地追随苏格拉底学习,也不存在所谓的“引诱”的问题。这是逻辑上的推演,而且隐含的是,他自身教授的是真理,行为的是正义。然而遗憾的是,苏格拉底却从没有否认自己“败坏青年”,没有让听众形成对自己与控告截然对立的看法。再如,关于“不尊敬城邦所尊敬的诸神而且还引进了新的神”的辩护,苏格拉底认为,他一直是相信有鬼神存在的。“你说我相信并传授有新或旧之鬼神的踪迹,那么,按你宣誓的讼辞,我相信有鬼神的踪迹;我既相信有鬼神的踪迹,就必然相信有鬼神,不是吗?”苏格拉底的辩护逻辑是建立在让控方同意“相信有鬼神的踪迹=相信鬼神的存在”之规则基础上,所以,他试图以此来证明自己是尊敬鬼神的。但是,这样的逻辑对于听众来说却似乎是太过于隐晦,不仅没有明确的为自己辩护的意思,而且还有引导听众思考其哲 学思想的目的。这种目的让法官们很警惕,以防陷入“苏格拉底陷阱”。更值得指出的是,辩护完毕之后,进入投票表决苏格拉底是否有罪的阶段,结果是281票对220票宣告苏格拉底有罪。就苏格拉底审判而言,修辞使用与否实际上并不重要,因为法官们早就为苏格拉底准备好了“笼子”。而柏拉图显然没有看到这一点。换句话说,即使苏格拉底使用了修辞术,法官们对苏格拉底的恨以及盲从,仍然可能使得苏格拉底身陷囹圄,因此审判的结果是一种与修辞无关的审判,太多的案外因素决定了苏格拉底的命运。
对于苏格拉底之死,人们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如美国人斯东认为,苏格拉底求死心切,一方面家有悍妻,另一方面,身体饱受病痛的折磨,所以苏格拉底放弃了修辞(实际上没有放弃修辞),而处处树敌于法官们。这种猜测或许有其道理,但是,却没有揭示出苏格拉底之死作为悲剧的本质意义。其实,我们进一步推论,如果是以求生为目的的话,苏格拉底的上述策略无疑是失败的。难道明智的苏格拉底真的看不到问题的实质吗?以苏格拉底的聪明才智,他毫无疑问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求生之路在何方,关键问题是他不想走这条让他觉得羞耻的路。所以,我们进一步推论说,苏格拉底是自己在“求死”,特别是在雅典法官们判处他死刑之后,他越发觉得自己的死亡是一种必要了。所以,诠释苏格拉底之死的真实结论应该是,当苏格拉底与雅典公民无法达成共识之后,他感觉到自己的使命已经不再是去求生,而应该是以“死”警醒雅典公民应当培养德性,树立公民意识,追求真理和正义。从警醒雅典公民的表现形式来看,言语意义上的警醒是同自己身边亲近的人所说,行为意义上的警醒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叙说,话语意义上的警醒充满修辞,而生命叙说的警醒又何尝不是一种“死谏”———一种由此及彼、发人深省的修辞?因此,整体来看苏格拉底的自愿服法,实际上就是一种对雅典人、对身边亲人朋友、对后人的行为修辞方法。苏格拉底希望通过自己的献身,说服自己身边的亲人朋友,特别是说服雅典人以奉行法律为荣。只是苏格拉底没有料到的是,因为“死谏”而无意间成了西方历史上的守法楷模而进入荣耀的“长生殿”。
在道德、法律或者政治领域方面,正义本来就是有争议性的,也就是“无论何种正义的观点,都绝不可能在无争的情况下,证明出某一种直观的法则或决策,乃是正义的唯一表现”。真正的正义是建立在合理性基础上的说服正义。所以,苏格拉底所使用的修辞是高傲的真理性追求与城邦正义论统一的修辞。只能说,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形下,苏格拉底选择了自己的理想。
参考文献
[1]〔英〕阿诺德•汤因比. 历史研究. 刘北成,郭小凌,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2]〔美〕斯东. 苏格拉底的审判. 董乐山,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作者简介:汪辽洋(1992-)女,陕西榆林人,硕士,陕西师范大学 710062,研究方向:汉语国际教育。
论文作者:汪辽洋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8年11月中
论文发表时间:2018/10/26
标签:苏格拉底论文; 修辞论文; 雅典论文; 的是论文; 自己的论文; 法官论文; 正义论文; 《知识-力量》2018年11月中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