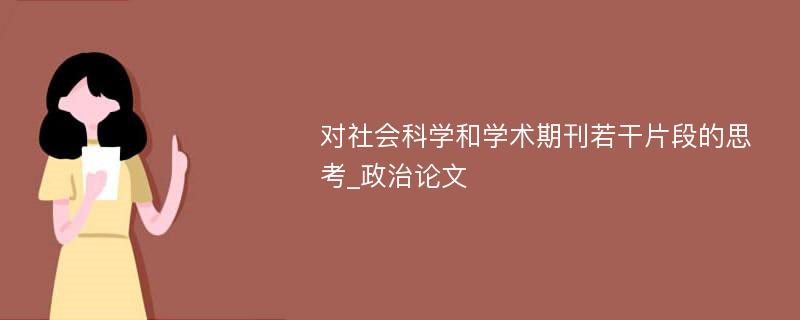
关于社会科学与学术期刊的一些片断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片断论文,社会科学论文,学术期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4)02-0193-06
写下这个标题后,感到涉及的范围过大了一些,好在所谈内容仅限于“片断思考”。虽然我有主编《晋阳学刊》十年的实践,但是历史已跨进了21世纪,办学术期刊的要求已发生了新的变化,自然一些思考随着时过境迁,真不敢保证不是陈词滥调,现不揣浅陋讲出来,旨在求教于大家。主要思考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学术与政治
学术与政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可以说,学术总是无法与政治分开的。离开政治谈学术,当代社会科学也就会失去其生命力。
我在创办《晋阳学刊》之初,曾四处求教,拜访了多位著名的资深学者,其中有北京大学的邓广铭、周一良、宗白华、王力、张岱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杨向奎、贺麟、吴世昌、黎澍、罗尔纲、孙楷第,上海的周煦良、郑逸梅、戴家祥、蔡尚思、吴泽,等等。虽然当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但是他们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禁锢,60年代的浩劫,对于那时的唯政治思维、把学术当婢女的作法,给予了切肤之痛的批评,并提出了诸多建设性的建议,其中尤以贺鳞先生的看法中肯而有的放矢。他在1946年即写过《学术与政治》的文章,对二者关系有深入浅出的阐述。当时,他给我讲了学术与政治的辩证关系;难得的是,其《文化与人生》一书1988年由商务印书馆再版后,他还特意寄赠一册给我,再次强调了处理好学术与政治关系的重要性。
贺麟先生指出:“最易而且最常侵犯学术独立自主的最大力量,当推政治。政治力量一侵犯了学术的独立自主,则政治便陷于专制,反民主。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不单是保持学术的净洁,同时在政治上也就保持了民主。政府之尊重学术,亦不啻尊重民主。”接着他着重阐述道:
所以一谈到学术,我们必须先要承认,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的、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能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它有它的大经大法,它有它神圣的使命,它有它特殊的广大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真正的学术是人类理智和自由精神最高的表现。它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它是独立的,不是依赖的。它的自由独立,是许多有精神修养,忠贞不二的学术界先进,竭力奋斗争取来的基业。学术失掉了独立自由就等于学术丧失了它的本质和它伟大的神圣使命。
在此,贺老从政治与学术的本来含义上说清了二者的科学关系,但二者并非从属关系,贺先生接着强调:“同时在某种意义下,政治也是独立自由的,它也有它特殊的领域,神圣的使命,它有它的规矩准绳,纪纲律例,它也需要忠贞不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英雄豪杰之士来争取保持它的独立自由。政治没有独立自由,便根本不能指导、统治、推动整个社会国家的经济、行政、教育、外交、军事等一切活动。”他认为:“学术有学术的独立自由,政治有政治的独立自由,两者彼此应当互不浸犯,然而学术与政治中间,又有一种密切的联系,失掉了这一种联系,社会两败俱伤。”“由此足见学术和政治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体’与‘用’的关系。学术是‘体’,政治是‘用’。学术不能够推动政治,学术就无‘用’。政治不能够植茎于学术,政治就无‘体’。……政治没有学术作体,就是没有灵魂的躯壳,学术没有政治作用,就是少数人支离空疏的玩物。”
贺麟先生后来与我交往频繁,我长期向他寄赠《晋阳学刊》,每次我进京都要聆听他对学刊的指教。1984年8月,贺老来晋参加傅山学术讨论会,我又专门请他讲授了“学术与政治”的问题,他进一步引申道:因为学术与政治的这种关系,“我们可以说,任何建国运动,最后必然是学术建国运动。离开学术而言建国,则国家无异建筑在沙上。学术是建立国家的钢筋水泥,政治上的所谓真正的健康的‘法治’,或者儒家所提倡的‘礼治’、‘德治’,本质上皆应当是一种‘学治’。‘开明的政治’就是‘学治的政治’。离开学术而讲法治就是急功好利、残民以逞的申韩之术;离开学术而谈德治,就是束缚个性、不近人情、不识时务的迂儒之见;离开学术而谈礼治,就是粉饰太平、虚有其表、抹煞性灵的繁文缛节与典章制度。”[1]
在结束“学术与政治”的有连贯性的谈话时,贺麟先生明确地申明了自己的观点,他所以一再地强调在社会科学研究和办学术期刊过程中要处理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是因为我们在1949年后曾由于长期地推行唯政治思维所带来的严重负面影响,不得不对此给予重新认识。这种唯政治思维曾一度达到了泛滥的地步,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不仅在中国当代的文化重构过程中,使得社会浮夸而不务实际,造成追名逐利、荒废业务、败坏风气的后果;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在文化学术领域,使得本来是学术问题、思想文化问题也往往升格为政治问题,动辄采用急风暴雨式的政治斗争方式去解决。在这种唯政治化思维方式的制约下,那些学有专长、有着中西方文化学术造诣的专家学者,既失去了话语权,也没有了学术探索的条件。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唯政治化思维登峰造极、泛滥成灾的时期。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唯政治化思维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唯政治思维的最为极端、最为典型而又“史无前例”的集中表现。
贺麟先生表示:此种唯政治化思维,显然与我们所讲的“学术与政治”不属于同一个范畴;如果要说是一个范畴的话,也是属于应该抛弃的糟粕或谬误部分。在正常情况下,我们有理由期待社会科学研究及其学术期刊,务必应该清醒地、自觉地反思那段历史,学术研究者和学术期刊主持者务必以学术良心去厘清那些被颠倒与混淆了的是非界限,让我们的学术环境回到更加科学、更加规范和更加宽容的正道上来。
二、学术与成败
凡事皆有成功与失败,学术研究也不例外,问题是如何看待学术的成败与得失?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大有学问的。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功过成败观呢?我以为,既然是科学探索或学术研究,就应该允许有失误,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然而,不知何时我们却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观念,似乎自然科学研究出现失误,是不足为奇的;可是说到社会科学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却是错不得的。这种状况,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从而也使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走向了万马齐喑和濒于枯竭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追求真理的风气何以能形成?科学的结论怎能取得?社会科学又如何能繁荣和发展?虽然以上情况,说得是过去的年代,当今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也不可否认,长期形成的惯性是否就能不存在或彻底绝迹了呢?恐怕不能这么说。这种情况告诉人们,要发展和繁荣社会科学理论,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社会科学及其研究中的成败问题,必须要有一个适合它发展的宽容自由的社会环境,必须允许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失误和对错误的修正。
作为社会科学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它同自然科学研究一样,都是在前人的认识水平和学术成就的基础上进行探索的创造性劳动。所异之处只不过是二者所研究的对象、方法和精确程度不同罢了,前者面对的是社会,后者则是自然,但是不论前者还是后者,却同样是从了解现象到掌握规律的探索过程。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不仅要检验前人的成果,吸取不同学派、不同学说的合理成分,批判继承历史遗产,发展前人已经取得的科研成就;而且要考察历史的、现实的、自然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中国的、外国的一切直接间接的联系。这种社会结构的多层次和复杂性,社会生活的丰富性,社会认识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决定了要获得一个正确的观点和取得一项有价值的成果,需要占有丰富而翔实的资料,经过认真的调研和周密的思考,往往要有多次的失误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恩格斯说到马克思着手研究政治经济学时,这样指出,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已经写出了千百部著作,已经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完整的形态,作为一个不能非难的教义摆在后来者的面前,“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绝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绝不是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作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既然经济学家无非是这些规律的解释者的辩护人,那么,这种阐述同时也就是对全部经济学文献的批判。”[2](P119)这种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的系统的完整的科学探索,“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2](P118)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正是社会科学研究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这种艰巨性和复杂性,决定了社会科学研究和理论探讨中失误的不可避免,决定了要得出科学结论和取得成果的不容易。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探讨上,还有一个值得指出的问题,那就是:不能认为老祖宗没有讲述的,后人就不能讲;或者后人根据发展变化了情况,对老祖宗讲过的话有所修正、有所发展,就是什么“离经叛道”。相反,对于那些在深思熟虑、严密考证、认真研究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新观点、新见解、新理论,更应予以重视。对于那些争议较多的问题,也是不要急于肯定与否定,还是让实践来检验和回答是否为科学。
从上所述,可以看出,社会科学研究本身是有它的特点和规律性的,如何对待社会科学中的成败功过问题,实际上是如何按照社会科学本身的规律对待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问题。
如何对待社会科学研究,不仅有认识规律上的问题,而且有实际过程中的问题。从认识规律的方面讲,需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未知和已知的关系;二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三是长远与现实的关系。
就未知和已知的关系讲,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区分社会科学研究和理论宣传教育两个方面。二者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领域,前者的根本任务是探索未知,即发现尚未被人们认识的社会现象及其本质和发展规律;后者则要求准确地解释党和政府的现行方针政策,它所宣传的是既定的、已知的事物。作为科学研究,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不但是允许的,而且应该大力提倡。对这种研究及其成果的衡量和评价,只能依据科学的实践。作为政治理论宣传教育,它要求统一口径,要求从理论上去论证、解释党和政府的决定和各项方针政策,要求宣传教育的效果。
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讲,科学研究是一种理论研究,但理论研究并不等同于科学研究,这里存在着提高与普及、抽象与应用的问题。作为科学研究,应该着眼于提高,不能满足于现有的认识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与错综复杂的表面现象有着一定的距离,但这并非脱离实际。要知道,“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3](P181)在这里,是不是我不讲社会科学的应用研究功能了呢?不是的。所谓应用社会功能问题,实际上就是社会科学本身的社会价值问题。在此,正确处理好社会科学及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是十分重要的。社会科学的一切科研成果能得到社会承认的根本价值,是它的学术价值。而一项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的表现形式则是它的社会价值,或者叫社会功能、社会需要。如果一部科学著作不具备一定的学术价值,怎么能正确地为社会发展服务呢?在社会价值中,作为社会科学及其成果对实践的作用,在于从理论上去指导实践,它不是实际运动的直观的东西和具体的经验的堆积,而是对社会运动的内在必然性即规律性的揭示和认识。这就是说,我们对于社会运动的研究和服务,不是从一般表面现象去叙述,而应当是通过对社会运动全部事实和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取得对社会运动的理论认识。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要求社会科学及其成果应尽快发挥应用作用,于是我们对社会运动的叙述在不少情况下只停留在感性认识的阶段上,有时还采取具体经验的形式,或者成为具体方针政策的汇集。岂不知这样要求的结果,社会科学及其成果除了成为婢女之外,没有别的作用。
就长远与现实的关系讲,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精神生产,在考虑它为现实服务和满足社会需要时,不但要有一种广阔的、长远的眼光,而且要注重社会科学中各个学科的结构和层次及其特殊规律,千万不可简单化和庸俗化。过去在精神生产方面存在着两种弊病:一个是眼光太浅近,要求太急切,期望为现实服务要“立竿见影”,而且在要求上不加区别,千篇一律;另一个是在社会科学为现实服务上,只许成功不能失败,一旦错了,不论青红皂白都挨批。这样一来,人们只好选择一些离现实远的课题,去回避现实,以免自讨苦吃。由此看来,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并非人们不想为现实服务,而是对过去那种左的作法的一种反抗,是特殊的历史造成的消极影响。
其实,社会科学的应用功能是极其广泛的,其中涵盖着几十个学科,而每个学科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尽管各个学科为现实服务是共同的,然而服务的途径、方式和效果却因自身性质而有区别,它们的应用价值不仅具有功能性,而且具有多层次性,甚至有着多变迁性;既有直接作用,也有间接作用,还有迂回作用;不仅有低层次作用,而且有高层次作用;有的是明显作用,有的则是潜在作用;有的表现为启迪作用,有的则显示出转化作用;除了近期作用外,还有长远作用,等等。面对着这样多的服务作用,如果缺少战略的、总体的、长远的眼光,没有一种多功能、多学科、多层次、多渠道的应用价值观,显然很难达到目的。
三、学术与争鸣
理论、学术问题上不同意见的讨论、批评乃至争鸣,是发展理论、繁荣学术、探究真理的必然途径。人们在理论探讨和学术研究过程中,由于研究条件的不同,掌握资料的不同,探索角度的不同,阅历经验的不同,研究方法的不同,必然会形成不同的认识和不同的结论,这就产生了矛盾,必然要引起理论上、学术上的是非之争。欧洲古代哲学家早就懂得,通过辩论揭露矛盾并克服这些矛盾,是发现真理的最好方法。他们把这种方法称作dialetic,意思就是进行谈话和论战。中国古代思想家也同样知道这个道理,《逸周书》中有“疑意以两,平两以参”之说;《墨子》中有“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之论;王充主张“两刃相割,利锁乃知;两论相订,是非乃见”;班固认为“其言虽殊,譬尤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以上所揭示的都是通过争论可以互相启迪、共同提高的道理,指出了学术争鸣是解决理论分歧的正确途径。
争论之所以必要,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4](P567)理论上、科学上的任何创造和突破,除了需要矢志不渝的攀登、孜孜不倦的探索、良友益友的接助之外,还需要“敌对”意见的帮助。当某个学术观点受到非议和责难时,有些人往往会觉得不愉快,岂不知这种非议和责难正是成功的一种前提。
争论之所以必要,还在于理论、学术研究是一种探索性、创造性的艰巨劳动。凡是要在理论上、学术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都需要人们思想解放,善于独立思考,对前辈、对名人的理论和传统的观念持大胆怀疑、敢于批判的精神。马克思主义主张服从真理,而绝不提倡盲目地服从权威。在认识世界问题上,在科学问题上,在理论、学术研究上,只能以是否符合客观真理为标准,而不能用诸如权力大小、地位高低、影响多大等因素为标准。
争论之所以必要,还因为学问之道,浩如烟海,无论怎样的杰出人物,怎样知识渊博的学者,都不可能穷尽真理,都可能存在着知识结构上的不足,认识能力上的局限。恩格斯指出:“真理和谬误、善与恶、同一和差别、必然和偶然之间的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以前才能被认为合乎真理的。”[5](P40)所以会如此,这是和人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必然具有局限性”和“他们在获得知识时所处的环境对这些知识的制约性”相关联的。
说到争鸣,一些人在原则上赞成,但要真正实行时,却有一种有碍理论、学术发展的风气,就不大愿意进行学术争论,不敢进行学术观点的交锋。究其原因,一则因师承、同窗关系,明知自己的导师和好友在一些观点不正确、不科学,也不愿意与之争长短,担心伤了和气、破坏友谊、疏远感情;二则因某某是名家,是权威,虽然知道他们有些见解是错误和片面的,也不敢公开同他们明辨是非,害怕妨碍名家声誉,得罪权威;三则在理论、学术争论时,既不敢旗帜鲜明,更不敢指名道性,就像京剧《三岔口》,鸣则鸣矣,但不知与谁争论,或羞羞答答,或拐弯抹角,简直在十里雾中。四则把时下学术腐败风气引入学术争论之中,强词夺理者有之,泼妇骂街者有之,剑拔弩张者有之,大动干戈者有之,一些人连起码的学术廉耻都没有,连基本的学术道德、学术规范都不讲了。这种不正常的局面若不能扭转,要想建立一个科学、优良的学风学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四、学术与学派
无论自然科学领域,还是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与出现不同的学派,不仅是学术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而且是学术繁荣发达的内在进步动因及其标志之一。
在学术研究、探讨中产生了争鸣或交锋,进而形成学派,学派的形成又促使争鸣或交锋之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起来。无争鸣或无交锋的学派是没有生命力的;无学派的争鸣或交锋则可能是徒具形式的。可见,学术流派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的学术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产物,也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空间宽松自由的标志。只有当出现了众多的著名学者及其大量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而引起学界竞相追求和仿效的时候,才有可能形成诸多不同成就、不同思想风格的学术流派。
学派是在争鸣或交锋中逐渐形成的。学派大都有其“灵魂”:有自己杰出的代表人物;有独创的建树及其思想体系;有独特的研究方法及其学术风格。一个学派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及其学术影响,得到社会和学术界的认可。一个学派对社会的影响程度,决定于这个学派的理论或思想所能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
任何学派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它是时代的产物,自然有着历史的局限性,还需要在以后的实践中不断发展,逐步趋于完善。任何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只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其原因在于:任何新规律的发现,新定理的证明,对人类历史某些问题的重新认识或“疑古”,都只能是依据科学发展的实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新的科学观念和方法,对各学科领域进行创造性探索的结果。
科学上不同学派之是非,应当通过科学实践去检验,通过学术争鸣或交锋去解决,也就是通过自由讨论去解决。既然科学是一种真理,学派是学术探索中的流派,它就不怕争鸣,不怕交锋,不怕诘难,不怕批评,而是愈辩愈明,愈争愈真。毛泽东曾经指出:“艺术上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6]这不能不说是高明之论。学派定于一尊,正常的学术争鸣或交锋不能展开,学术的生命力也就被窒息了,学派也就无由产生和发展了。历史向我们提供的这方面的教训,可谓不乏其例。
学派建没,应视为是一个国家学术思想发展的一面镜子,一种尺度。我们不仅在国内要形成众多的学术流派,而且在国际上还要形成一个独具特色的中国学派(每一学术领域和每个学科均应如此)。只有这样,才能以特有的风姿步入世界学术之林,才能更好地促进国内学术水平的提高和发展。
那么,如何振兴中国的学说、学派呢?学者们曾经建议:一是真正贯彻“不同理论观点可以展开讨论”的原则;二是新闻出版界要勇于为新学说、新学派鸣锣开道,学术报刊要敢于拔学说之尖、兴学派之利;三是要在全社会兴尊学说、重学派的社会风气。学界要倡标新立异之风,只要不是搞伪科学,只要不是妄自尊大,我们就应予以提携和扶持。
五、学术与期刊
在学术载体中,除了学术专著外,更多的学术成果则是以学术论文的形式进行交流,经过学术期刊这块阵地发表刊布的。学术期刊不仅学术信息最大,而且学术论文的周转率高。作为学术期刊的编辑人员,应当懂得自己刊物在发展理论和繁荣学术方面所肩负的重大责任,应当通过各种努力去促进理论探讨、学术争论的活跃,尽力多刊布一些持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性文章;学术期刊的编辑多数具有以编为主、编研结合的学术水平,在某个学术领域有着自己的学术专长及其学术观点,但是在编发争论文章时却需要有兼容并包的精神,不论哪派的观点都可占有一席之地,不论所刊文章的见解与自己的意见如何相左,只要持之有故、言者有理,能自成一说,就要让其在自己所耕耘的园地中竞放,千万不可以自己的好恶而相排斥;学术期刊的编辑同样需要有胆识,既不可轻视“无名之辈”的小人物,更不必跟在名家权威后边去捧场,在自己责编的学术期刊上该发表什么和不该发表什么,应该有科学的原则,千万不可以名家权威的态度去作出取舍。对于提出新的观点、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发掘新的材料的文章,对于重要学术理论问题的争鸣性文章,务必提供阵地优先刊载。只有这样,学术期刊才能大大有助于理论的发展、学术的繁荣和科学的昌盛。
但也无需讳言,近些年来,一些学术期刊在学术腐败的风气中却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成了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的学术骗子的贩夫走卒,成了欺世盗名、假冒伪劣的学术垃圾的传媒载体。这种学术期刊腐败现象的表现主要是:一是低水平重复;二是粗制滥造;三是学术注水;四是假冒伪劣;五是抄袭剽窃;六是顾问及学术委员挂名之滥;七是评奖之项名不符实;八是“大师”等著名头衔廉价抛售,等等。以上所列举的腐败现象,实际上是整个学术界的表现,但是很多问题正是通过学术期刊暴露出来的。由此可见,学术期刊与学术整体往往是表里关系,就此意义讲,学术期刊的腐败流弊绝不可视为孤立现象。
除了学术期刊腐败的外部因素外,当然也不可小看了学术期刊的内部机制及其自身因素。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学术期刊内部职业道德的滑坡,缺少了全心全意“为人作嫁”的精神,商品原则渗入编辑过程,违背学术原则,以作另类价值取向,“关系稿”、“交易稿”已不再是什么秘密。二是学术期刊内部学术水平下降、业务素质不高,学术研究动态不灵,学术上鉴真辨伪的能力不强,常出现“炒冷饭”、“低水平”的情况。三是学术期刊内部管理上存在着漏洞,或制度不健全,或职责不分明,或奖惩不严格,特别是编辑队伍中的不正之风缺少必要处置。四是对于著名人物的文稿,编辑互相争刊抢发,不仅造成一稿多投,而且致使著名学者陷入尴尬与被动之中,甚至引出官司来。五是当今各种学术期刊都划出了不同级次,这种级次划分可谓喜忧参半,一方面使得刊物发展更趋于有序化;但也给学术发展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弊端,很容易使学界或学术期刊内部形成以论文发表载体为尺度去衡量论文的学术水准。如果采用这种评价标准,而不把注意力集中到论文本身的学术水平及其学术创见方面,很容易形成“文以刊贵”、以刊论文的不良风气。
说到学术期刊如何办?笔者以为,首先就是要爱护学术生态环境,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双百方针”,为学术争鸣提供一方自由呼吸的空间,一片不被污染的思想绿洲,为促进学术繁荣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氛围。
其次就是,学术期刊要有一个基本的精神定位,这个位应定在集中学界智慧保证它的学术独立品格,提供与鼓励学术研究的探索精神和创造精神上,努力发展学术自由,倡导学术无禁区,倡导学术面前人人平等,推动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要尊重学术的多元化、多样化,在发展中形成学派或流派。既然是学术期刊,就应该主张:在提高与普及方面,应立足于提高,坚持学术上的先锋性;在前瞻与现实兼顾方面,应关注前瞻,保持其前瞻性;在阐述与争鸣方面,应既重阐述,又重争鸣,真正体现百家争鸣,具有兼容并包的风范;在追逐潮流与冷热点的选择上,要追根溯源,探求那些存于灵魂最深处、思想最内层的东西,从根本上触及思维之弦。
再次,学术期刊的编辑应该学者化,因为编辑的非学者化,势必带来许多弊病:缺乏学术意识,缺乏学术反馈,缺乏学术兼容。笔者以为,要做好一个合格的学术期刊编辑,他应该既是杂家,又是专家,需要同时兼备编辑与专业研究的能力。显然,学术期刊编辑,如果自身学养高,再加上敬业精神,恐怕那些伪劣产品就难以逃过他们的法眼了,同时也就保证了学术生态的良化。
标签:政治论文; 学术与政治论文; 学术期刊论文; 科学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社会发展规律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晋阳学刊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