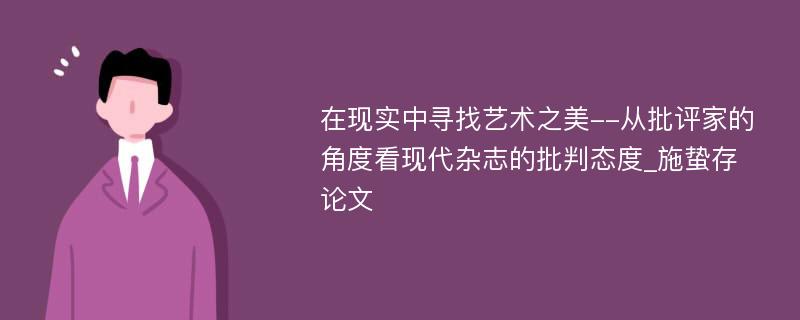
于现实中求艺术之美——从批评家群体看《现代》杂志的批评态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家论文,之美论文,中求论文,群体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的批评家的构成及特点
以“《现代》的批评家”一语来描述或概括出现在《现代》杂志中的批评文字的作者,严格说来并不是那么准确,因为除极个别人外,这些批评家绝大多数均非《现代》所“特聘”,他们也并不只在《现代》上发表文章,实际上,因为不是同人杂志,《现代》也不可能有此举措,而且,这正是《现代》所要尽力避免的现象。但是,若暂时撇开这一点,仅从《现代》杂志自身的角度来看,也的确有一些批评家表现得比较活跃,他们的文字不仅在《现代》的批评中占有较大的份额,所产生的影响也较大,更重要的是,这些文章即使在他们自己的批评生涯中,也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甚至还是他们的代表性作品。
然而这只是“《现代》的批评家”得以成立的客观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代》的编辑方针的主观制约,这也是“《现代》的批评家”形成的重要的原因,因为只有符合《现代》的用稿标准的文章才能发表,这也使《现代》能够将一些文艺观念比较接近的批评家团结在其周围。而这个标准,具体一点讲,就是施蛰存在《现代》的《创刊宣言》里所说的,“只依照编者个人的主观为标准。至于这个标准,当然是属于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方面的。”这里的“文学作品”自然也包括批评在内,而其“本身价值”,则“意味着从文艺观点来审定的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注:施蛰存,《沙上的脚迹》,第28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也就是说,无论批评家是何人,其批评首先必须符合这一条件,才可能被《现代》接受。这就把那些相对较关注文学作品的“本身的价值”的批评家,以及其批评自身也具有一定艺术价值的文字吸引到了《现代》上来。
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而不是从批评家的某些特殊的身份来决定稿件的取舍,使《现代》的批评作者来源较为多样,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如既有鲁迅,茅盾,郁达夫这样的大家,也有刚出道不久的新人,如当时还在清华大学哲学系读书的李长之,在安徽小县城里当小学教师的王淑明,既有周扬,瞿秋白,胡风,冯雪峰等左联批评家,和本属左联后又离开的韩侍桁,杨邨人等,也有来自于创造社的穆木天,还有苏雪林这样的不属于任何文艺社团的人,以及参与编辑《现代》的杜衡和施蛰存本人等,都在《现代》上发表过自己对于文艺的意见。
不过,在这些批评家中,本文所要讨论的对象却并不是很多,这是因为上述的人中,有很多批评家发表的文章较少,有的只是偶一客串,并不足以影响《现代》批评风格的形成,因之也不能代表《现代》的批评立场。此外,他们的个别言论,也有悖于施蛰存对《现代》的批评的要求。在第四卷第一期,施蛰存将原来可以无所不谈的“随笔、感想、漫谈”栏,改为用以公开发表读者或作者对于文艺的意见的“文艺独白”栏,在卷首语里,施蛰存对栏目名称中的“独白”的“独”字做了一番解释。
再,这“独”字颇容易使人联想到“独立”,“独出心裁”那一类意义上去。这表示本栏不甚欢迎应声虫式的附议文章。我们希望在这儿所发的,都是由衷而发的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各种各式的八股文。然而这意思并不是请大家定要标新立“异”,诚意的“同”于人,自然不必归入应声虫之列。
这段文字颇耐人寻味,“独立”或“独出心裁”固然是《现代》所追求,但施蛰存还一再强调在这里发的应是“自己的意见”,是“由衷”的,而不是“应声虫式的”文章,或者干脆就是“八股文”,其中的深意,也就是他更注重批评的独立性,这个独立性,是希望有自己的独立的见解,而不要人云亦云,更不要为“各种各式”的理论所蛊惑,失去自己的判断,成为“附议”的八股文。这是表现在批评的出发点和立场上的独立性,在具体的批评中,施蛰存一样要求批评家保持其独立性,在第二卷第五期,施蛰存在谈到书评栏的纲领时,就指出了这一点。
本刊自从刊载书评以来,对于作者完全抱着极忠诚的态度,一点不敢意气用事。使书评栏等于谩骂捧角之场。但是对于任何一本书的批评,其未必能为作者所首肯,亦等于其未必能为该书读者所首肯。所以有作者来函自剖,我很乐意发表,使读者有所参考。批评家对于一个创作家,本来是决不会有所损益的。(注:《现代》第2卷第5期,第866页。)
显然,在施蛰存看来,哪怕是对一本书的一篇小小的书评,批评的独立性也是不可动摇的,只要这批评是“由衷而发”,是对作者“抱着极忠诚的态度”,那即使是作者不认可,读者不同意,也是没关系的。他这段话,就是说给因不认可《现代》上的一篇对他的小说集《复仇》的批评,而致函《现代》表示不满的巴金听的。
苏雪林在《几个超越派别的文评家》一文中,曾言韩侍桁,王任叔,朱光潜,李健吾,梁宗岱,沈从文,晨风,还有李长之,都是三十年代具有“独立思想”的,“超越派别”的批评家(注:苏雪林,《苏雪林文集》(第三卷),第387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而与《现代》关系密切,并在《现代》上发表了相当批评文字产生较大影响的就有韩侍桁,李长之和她自己,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代》对批评的独立性的追求,从中也可看出施蛰存的所言不虚。
这篇文章所要论述的批评家除了他们三个外,还有杜衡,穆木天,王淑明,以及作为刊物主编的施蛰存的一些思想,希望能从对这几个有代表性的批评家的批评中看出《现代》的批评的态度,及其相关的特点。
《现代》的批评的基本价值取向
若谈到《现代》的批评的基本的价值取向,势不能绕开杜衡,这不仅是《现代》创刊不久,就因杜衡的一篇《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一文而掀起轩然大波,以至于《现代》在外人看来,几成杜衡所言的“第三种人”的基地,也是由于杜衡是在《现代》上发表批评文字最多的人,而且,《现代》也几乎是他一生中发表文艺批评文字最多的杂志,同时,他还从第三卷第一期后与施蛰存联合主编《现代》,负责小说创作和杂文的编辑工作,而在此之前,从第一卷第一期起,他就应施蛰存之邀,在审阅批评和一部分小说创作的稿件。并且,众所周知,在《现代》之前,他就和施蛰存,戴望舒,刘呐欧等人长期身处同一个文学团体,所以,他的批评姿态,从某种意义上,对其他的《现代》的批评的作者,也是具有一定的示范性的。
这其中,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需要考虑,那就是施蛰存尽管在编辑《现代》时,力争使自己保持中立的立场,但其对杜衡的文艺观并不反对,相反,他并不讳言,自己是赞成他对于文艺的观点的。在“第三种人”论争持续一年后,施蛰存在第二卷第五期的社中日记里坦陈,“我实在并不以为苏汶先生的文艺观即是现代杂志选录创作的标准,虽则我对于文艺的见解是完全与苏汶先生没有什么原则上的歧义的。”(注:《现代》第2卷第5期,第769页。)关于这一点,施蛰存并不只是说说而已,在他的一些批评文字里,也确实表现出了他的与杜衡近似的,甚至相同的文艺“见解”。这“见解”也正是他编辑具体稿件,包括批评在内的标准,因此,杜衡的批评相较《现代》的别的批评家而言,也就更具有了代表性。
所谓批评的基本的价值取向,在当时,无外乎文艺与现实的关系,其中又主要涉及到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以及评价文艺的标准等比较“大”的和比较“基本”的问题。这里先谈文艺和现实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杜衡在第二卷第一期《现代》上所发的《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一文中说得很清楚,文学应该作为反映现实,也即反映时代发展矛盾的一面“镜子”和“时代的里程碑”而存在。
……历史的演化是没有终极的。这就是说,任何社会秩序都不会是终极的。每一个时代都有它底矛盾,而这些矛盾便是历史演化的新环节的张本。过去是如此,现在是如此,而且将来也必然地是如此。正因为矛盾没有完全绝灭的一天,我们便时常需要一面可藉以认识这矛盾的镜子。供给时代以一面镜子的任务,固然由社会思想家们用他们的锐利的解剖和批判来担任了,但我们知道,单单有这种根据纯理智的批判和解剖是不够的,我们还得感觉的地来体验这些矛盾。(注:《现代》第2卷第1期,第129页。)
而这面“镜子”的作用,当然是为了使人们能够更加全面和清晰地发现时代的真相和矛盾,并进而为改善这一矛盾提供帮助,杜衡指出,这才是文学的“永久的,绝对的,决不能用旁的东西来替代的任务。”从这个观点出发,必然要求文艺要如实地反映现实,而作品与现实的吻合程度,也就是其“真实”与否也就成了衡量文艺价值高低的重要标准。杜衡由此进一步指出,为维护文学的真实性起见,文艺必不能成为某种政治势力的“留声机”,并把作品的意识是否“正确”来判断文学的价值高低的标准,这样只会使文学成为粉饰与歪曲现实的宣传品,从而丧失其文学性,因为一旦文学沦为政治的“留声机”,就只能按照某种政治势力的要求,把“意识正确”放在第一位,而把真实放在第二位的。从而也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真实地反映时代,做时代的监督,而成了一面“哈哈镜”。
杜衡的这一观点,显然是与左翼所提倡的所谓唯物辩证法的文艺观,也即受制于“意识正确”,即政治正确的比较偏狭的阶级论的反映观是相违背的。所以,受到左翼的攻击也就很自然了。但杜衡并不是要求文艺与政治绝缘,在同一篇文章中,他直言,“我当然不反对文学作品有政治目的,但我反对因这政治目的而牺牲真实。更重要的是,这政治目的要出于作者自身的对生活的认识和体验,而不是出于指导大纲。”(注:《现代》第2卷第1期,第133页。)在第五卷第一期的社中座谈里,他再次明确地表达了这个认识,“文学者不必强自与政治合流,但同时亦不必一定与政治背道而驰;各随心之所安,我以为是真实的态度。”(注:《现代》第5卷第1期,第216页。)应该讲,杜衡的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也是正确的。因此,施蛰存才会在第二卷第一期的社中日记里说杜衡的文章“也很有精到的意见,和爽朗的态度”。(注:《现代》第2卷第1期,第216页。)
其实,施蛰存在这些基本观点上,也和杜衡有相似之处,如在第三卷第四期的社中座谈里,他也将《现代》比作一面使人得以看见“中国社会的种种黑暗,没落,颓废的景象”的镜子,使读者多少能得到些“刺激与兴奋”(注:《现代》第3卷第4期,第579页。),同样,他也认为文艺应反映现实,不过,他更注重是人对现实的感受,或对当下的生活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这一点在他关于《现代》上的诗歌的论述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纯然是现代的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
所谓现代生活,这里面包括着各式各样的独特的形态:汇集着大船舶的港湾,轰响着噪音的工场,深入地下的矿坑,奏着Jazz乐的舞场,摩天楼的百货店,飞机的空中战,广大的竞马场……甚至连自然景物也和前代不同了。这种生活所给予我们的诗人的感情,难道会与上代诗人从他们的生活中所得到的感情相同的吗?(注:《现代》第4卷第1期,第7页。)
透过这段话,可以看出,施蛰存谈自己对于文艺上的见解,和杜衡“没有什么原则上的歧义”,并非虚言,其背后的文学观和杜衡确实相去不远。但其对文艺的期望值并没有杜衡高,他不像杜衡那样,企图通过文学的认识作用来对社会矛盾的解决有所助力,而是只要求其能让一些读者感到“刺激与兴奋”就行了。这也许就是他和杜衡的一个区别。
此外,作为《现代》的重要的诗评家,穆木天所持的观点也几乎与施蛰存和杜衡如出一辙,他在第五卷第二期的文艺独白《诗歌与现实》中,就提出,诗人应该把自己对社会现实的真实感情表现出来,“感情,情绪,是不能从生活的现实分离开的,那是由客观的现实所怀抱出来的,是人间社会的现实生活之反映……诗人,为了对于自己忠实起见,是必须对于客观的现实忠实的。真正地认识客观的现实的人,真正地认识社会动向的人,是才能获得崇高的真实的感情的。”(注:《现代》第5卷第2期,第222页。)显然,这个表述背后,所持的也还是文学应反映现实的观点。
除了要求文艺作品真实地反映现实外,在杜衡看来,在评价文艺时,还有一点就是要求作品自身应具有艺术上的完整性,其实质,就是一种对艺术自律性的追求,即追求艺术的“纯粹性”,反对艺术服务于非艺术的政治和道德等并成为其附庸的作法,这也是现代性在审美上的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表现。如在第四卷第一期的文艺独白《新的公式主义》里,杜衡就不仅批评了中国的批评家的粗暴的公式主义的批评,还反对那种为迎合时代的狭隘的流行标准对作品进行增删的作家和编辑,他以当时常见的小说结尾的雷同现象为例说,一篇东西的价值与意义,不是为作品有无“革命的尾巴”或在结尾是否“指明出路”决定的,而是“全篇发展的自然的结果。”(注:《现代》第4卷第1期,第6页。)在进行具体的批评时,作品是否自洽也是杜衡的一个批评的准绳,在第五卷第六期评介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安得生的发展之三阶段》一文中,杜衡就从艺术上指出了他的小说的缺点。
安得生在写长篇小说的时候,仿佛是跟短篇小说有不同的意向的。写短篇是单纯的表现着人物和个性,写长篇却处处不忘记一有机会就把自己的混乱的人生哲学加到他的人物的嘴上去;这些人物并不是各人说着各人的话,却一致的说着安得生的话。这倾向,是大大的损害了作品的价值的。在《多婚》里,竟有接连好几十页的写着主人公的说理的(并非是心理描写的)独白,而叫人没有终卷的耐性。(注:《现代》第5卷第6期,第977页。)
显然,对作品艺术性的重视与考察,也是杜衡的批评的一个核心的立足点。而这一点,正是当时很多批评家,尤其是左翼的一些批评家所缺失的。
《现代》的批评的具体路径
用施蛰存的话来说,《现代》的绝大多数批评家在文艺观上是和杜衡“没有原则上的歧义”的,但上文已谈到,即使这样,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两人也还是有一定的差异,只不过,这种差异并不足以影响到他们在文艺见解上的一致性罢了。同样,下面即将谈到的那些可以代表《现代》的批评的批评家,如韩侍桁,李长之,苏雪林,穆木天,王淑明等人和他们的批评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批评家与作家的关系问题
因为当时的某些左翼批评以及一些比较公式化的批评对作家作品的狭隘、生硬和粗暴的批评,使作家普遍对批评比较反感,也使其他的批评家对批评的作用产生了疑问,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其实就是如何看待批评与创作的关系的问题,这也是批评家在进行批评时首先必须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也可说成是批评的出发点。
在这个问题上,《现代》的几个批评家观点是统一的。如都强调批评家与作家应相互尊重对方的劳动,而不应高高在上,视对方为低一等的存在等。杜衡也在第四卷第二期的看图有感中,借美国星期六评论(The Saturday Review)上的一幅漫画,针对中国批评的现状提出,希望能把批评“弄成帮助艺术的发展而不是摧残它的工具”。(注:《现代》第4卷第2期,第286页。),身为《现代》重要的翻译家的高明在同期的文艺独白《关于批评》中也说,批评家不应动辄用“意识不正确”,“内容空虚”等政治化的标准来批评艺术作品,甚至对美国电影也一样要求着“正确的意识”,而应起到其应起的作用,“它对读者,则帮助他们去理解作品;对作者,则和他们做取材方面题材处理方面的种种讨论,使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长处在那里,短处在那里。”(注:《现代》第4卷第2期,第280页。)当然,无论杜衡还是高明,也还都只是从作家的角度出发对批评的作用作出解释。韩侍桁和李长之则从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对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作出了说明。
在第四卷第四期的文艺独白中,韩侍桁发表了题为《批评与作家》的文章,在文中,他也谈到批评家和作家双方都要互相尊重的问题,但不能仅仅要求批评家尊重作家,作家也应充分地理解批评家,他认为,批评家的批评也是创作,和作家一样,批评家也不是专门为某个人或某些人写作的,他是为广大的读者写作的,所以,“他的批评正确与否是和被批评的作家的满意与否毫无关联的。”(注:《现代》第4卷第4期,第644页。)因为即使是创作,也很难让所有的人都满意,而一个批评家,只要是诚恳地说他所要说的话,就算是尽到了责任。更重要的是,韩侍桁还指出了批评和创作的一种独特的“竞争”关系。
批评和被批评的作品是处在互相竞争的地位,作品的本身的价值有时可以淘汰了那批评,而坚实的批评有时也可以压倒了一部不良的作品。(注:《现代》第4卷第4期,第645页。)
正因为此,无论是作家,还是批评家都应对对方的工作持一种“超然的”态度,一方面,批评家没必要过多地顾及自己的批评是否为作家所喜而缩手缩脚,不能说出自己真心所想,另一方面,作家对于善意的批评也可有接受的气量,不要因噎废食。这样才会对文学的发展有好处。
李长之在第四卷第六期的《论目前中国批评界之浅妄——我们果真是不需要批评么》一文中,也强调批评家和作家的工作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真正的大批评家不仅敏锐,同时也多有创作的天才,其创作的经验也不见得就比作家贫乏多少。何况,批评家还需要远比作家广博的知识,和深刻的洞察力。所以批评家有资格也有能力成为作家的挚友。
伟大的批评家,是作家的一面镜子,使太重视自己作品的作家来一个清醒,又使太失掉自信的作家重建起自信,同时那些流俗的足以动摇视听的褒贬,以及会影响作家的高兴或扫兴的舆论,批评家也负着扫荡廓清的职责,总之,任务在使作品的真面目真价值大白于天下,不但为读者,也为了作家。(注:《现代》第4卷第6期,第996页。)
镜子这个比喻再次被使用,不过,这次镜子所反映的对象又显示变成了作家的作品,当然,李长之在这里的用意,是与杜衡一样的。在这篇并不算长但却爱憎分明的文章中,年轻气盛的李长之还对“浅薄愚妄”的中国批评界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评。如因学术上的贫困,而又“无知妄作”,批评家们便像军阀一样,只会依靠外人的势力,指生搬硬套外国的理论,来“压迫”本国人等种种缺点。并进而指出,中国并不是需不需要批评的问题,而是需要什么样的批评家的问题。在文末,李长之也毫不讳言地说出了他的想往,那就是期待“真正的大批评家”的出现,能够“从文学批评到文学史,文学史到文学建设”,开拓出“惟一的康庄大道”出来。
显然,他的这一期盼过于理想化了,如果能注意到《现代》上的批评,包括对自己的批评有一定的认识,他也就不会这么失望了。即以当时在《现代》比较活跃的王淑明为例,他的批评就起到了李长之所说的“镜子”的作用,如他在第五卷第一期评论张天翼的《洋泾浜奇侠》时,就既谈其高妙之处,也对其缺点直言不讳。
张天翼的小说,原以他所特有的讽刺味和作品的能采取新形式而为读者所称道。但到了现在,似乎在他的作品里存在着一个危机。那就是由讽刺而流于滑稽的危险。在他的以前作品里,如长篇《一年》已有好些地方,表现着这样的坏倾向,然而那只不过是萌芽而已。到了现在的《洋泾浜奇侠》中,似乎这样的不好倾向,正在积极地成长着,使我们看了他的作品,只觉得令人发松,惊奇,这虽然不是它的主要机能,但已成为它的主要机能了。(注:《现代》第5卷第1期,第212页。)
王淑明的批评不可谓不尖锐,但其用意,还在引起作者的重视,予以反思和改正,也就是说他对作者是尊重的,批评也是善意的。所以,在文章结束,作者满怀希望地说,以张天翼“所独有的天才”,一定会在以后的作品里克服掉这些缺点,并相信其“一定能超过它(指上述缺点)的。”而王淑明的这种态度并非只表现在这一篇作品之中,在第四卷第三期他对老舍的《猫城记》作了同样尖锐的批评后,也同样不吝赞美地给与了这部作品很高的评价,称其为“现在幽默文学中的白眉。”(注:《现代》第4卷第3期,第628页。)
当然,这种态度,在《现代》的批评家中,也并非独有。
2.批评的方法问题
从《现代》的几个批评家对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的看法上就可发现,这些人和大多数作家一样,对当时处处以导师自居的某些左翼批评家的那种政治化批评很反感,所以,他们在进行批评时,也很注意这一点,以免使作家产生误解或反感。如韩侍桁在第四卷第一期的《〈子夜〉的艺术,思想及人物》的文末就不惜画蛇添足,加上了一段话,“最后,我必需声明,我不是从无产阶级文学的立场来观察这书以及这作者,如果那样的话,这书将更无价值,而这作者将要受更多的非难。”(注:《现代》第4卷第1期,第140页。),其实这几句话并无必要,因为只要看了这篇文章的人都知道,作者的批评立场为何一目了然。但韩侍桁还是不放心。由此可见,当时批评家的处境的尴尬。
这种在具体的行文上进行表白的作法其实并无多大意义,问题的根本还在于批评家所采用的批评方法上,如果方法仍是某些左翼批评家的那套生搬硬套的所谓的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即使再声明,也没什么用处。而韩侍桁之所以要声明,固然有其正式的一面,同时也不无嘲讽的味道。也正是因为他的确不是从“无产阶级立场”来观察茅盾的《子夜》,他也才敢这么有恃无恐地说出来。而他所采用的批评方法,就是一种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在批评时,比较注意作家作品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和反映现实的真实性,并以此为基础,来进一步考察作品的艺术性是否完成,以及完成的是否理想等,而且,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韩侍桁,还是别的几位批评家,都非常注重从作品出发,通过对作品的细致的分析来说明自己对作品的意见,这种以作品为中心的批评方法实则就是一种文本批评,其本质也是对一种艺术自律性的追求。如,韩侍桁就在这篇批评《子夜》的文章里谈到,茅盾对人物的塑造多有缺陷,且不说吴荪甫过于理想化,就是对他手下的屠维岳的交待也嫌仓促,因为作者并没有叙述这个乡下小伙的成长过程与环境,就一下子让其在吴荪甫面前“成熟”起来,让人觉得难以置信。同样,韩侍桁认为,茅盾对吴老太爷的死的安排也有丑化的嫌疑,上海无论是怎样一个魔窟,也不会马上让一个大活人死掉。韩侍桁指出,吴老太爷的死是“不自然的,是不庄重的”,这说明作者在作着“观念论的游戏”,他并不反对茅盾把吴老太爷当作“五千年老僵尸的旧中国”的象征,“但他也同样需要真实性,需要艺术的苦心,以他当作一个丑角色,赶快就把他打发开去,这与他的‘企图’都有极大的害处。”(注:《现代》第4卷第1期,第135页。)此外,韩侍桁还对茅盾小说的叙事上的问题作出了批评,觉得他心理分析虽多,但却很零碎,不够精细,在场景的描写上也多有缺陷,并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等。这就是纯粹从文本出发,对其是否符合艺术的真实性,也即作品在艺术上是否自洽所作的细致的探索了。
因此,如果概而言之,可以说,《现代》的这几个批评家所奉行的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历史批评与文本批评相结合的方法,即“社会历史批评——文本批评”法。
这种方法有一定的代表性,从中也可看出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以及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等人的影响。如韩侍桁在第五卷第二期《现代》的文艺独白《时代的束缚》中,就指出伟大的作品“是由强烈的时代的精神和艺术的完整之适当地调和而成。”(注:《现代》第5卷第2期,第224页。)这里的“艺术的完整”,即作品在艺术上的自洽性。这也是他批评《子夜》等作品的重要的标准。但强调作品艺术性的完整并不等于脱离时代和生活,相反,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现实,是否有一定的“时代精神”,也是衡量作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标准。这从韩侍桁在《现代》第四卷第六期《文坛上的新人》中对沙汀的作品的批评就可看出一斑,韩侍桁对沙汀的小说艺术性的评价并不高,但同时他也指出了沙汀的创作的价值所在,那就是他的作品给当下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材料”,这里的所谓“新的材料”,指的是沙汀作品中所出现的那些“新的生活”,即生活在农村的人的惨酷的痛苦的挣扎,这也可看作某种“时代的精神”的一种体现,所以,有鉴于此,韩侍桁依然对沙汀褒扬有加,“一般的读者正在渴望着表现在文学里的材料。而且虽然他的写法是混乱的,含着极大的错误,而仍然使我们对他怀着极大的期待。”(注:《现代》第4卷第6期,第973页。)
正是在批评时,既考虑到了作品与社会历史相联系的这个“面”,又考虑到了作品自身的艺术自洽性的这个“点”,使《现代》的这几位批评家在对作家作品进行批评时,能够以比较全面的眼光考虑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避免了批评中很容易出现的偏狭和浅陋的毛病。如穆木天,他在批评时虽也采用唯物辩证法,喜欢对作家的阶级身份进行区分,也比较注重作家的阶级身份所代表的思想和情绪在作品中的反映,但由于他对作品本身的重视和良好的艺术感受力,使他的批评并未像左翼的一些批评家那样,落入狭隘的阶级分析的窠臼。在第五卷第一期的《王独清及其诗歌》中,他就认为王独清的诗,“始终代表着一个集团的心理意识”,“特别是他的前期作品,是表露着当时普通的没落贵族的悲哀来。”(注:《现代》第5卷第1期,第33页。)但他并未就此止步或对这种“意识”横加贬斥,以示自己的“意识”正确,而是承认这种“意识”的合理性,并通过对王独清的诗歌的细致的分析,从中发现他所表达的情绪的真实性及其艺术感染力。在同期的书评栏,他还对林庚的诗集《夜》进行了批评,在他眼里,林庚同样也是没落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一分子,他的出现,是与当时的农村经济的破产有关,但他诗中的情绪却又与王独清不同。
诗人林庚的闲逸的没落心情,如果我们更把它同故都北平联系起来,也许更可以了解得清晰些。在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各地有各地的特殊性。地方的特殊性,虽是决定诗人意识之次要的要素,然而,为的了解某一诗人的生活与作品的特点,则是成为不可轻视的东西。一方面感到没落,而同时,在故宫颓垣,同沙漠一般的故都北平,还得以营着孤立的小市民样的寄生生活,那么,他不能(进)一步地去把握现实,亦决非偶然。(注:《现代》第5卷第1期,第203页。)
由此也可看出,穆木天在进行批评时对诗人及其作品所作的开阔的然而也是合理的分析。这也是他与那些左翼批评家的区别所在。
王淑明也有这个特点,在批评中,他也试图从作家作品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入手来把握作品,不过,他更重视的是从作品自身的“艺术完整”来评判一部作品的得失。如在第四卷第三期对老舍的《猫城记》的批评,就凸显了这一点。他认为小说的主人公小蠍的性格在书中前后变化太大,开始异常呆笨、贪婪、自私,后来却一变而为爱国青年,思想老到,对事实的批评也非常深刻、准确。从艺术上讲,这显然是不符合人物性格的真实性的。
然而问题到不在于这些性格变动的不应有,而乃是他们的心理和行动,为什么突然转换了?这样说,我并不要求作者只表现书中人物的静态,而忘却其动态的一面。但在《猫城记》我们却看不出小蠍与这个旅行火星上的外国人,心理展开的过程,不:连一些变动的影子,都找不出来,这种作品中间情调统一的破坏不能说不是作者表现手法之失败。(注:《现代》第4卷第3期,第627页。)
他还认为,老舍在小说中由于过多地在自己的作品中发表自己对事物的一些“判断”和“近似判断的一些主观解释”,从一定程度上,就不如只进行客观的描写,而让读者自己去体会,更能收到“艺术上的效果”。在第四卷第六期对黎锦明的小说集《失去的风情》进行介绍时,他也一样批评了黎锦明的喜欢在小说里用人物之口来表露其对于艺术和哲学上的见解的做法。
本来文艺这东西,是藉形象而思索,如果在事件的进行中间,多分的渗入些哲学的艰深术语,和一些不平常的艺术哲学上的见解,这不但使作者的情节容易松懈,而且也破坏全体的统一情调。好像比较进步的创作方法,是把人物的描写融化在整个故事里,多用动作的场面,来暗默的表示书中故事之进行,和人物之行动性,而很少叫书中的主人公来做些主观的自白,或从别人的口中来一次关于这主人公人生观的叙述的。(注:《现代》第4卷第6期,第1062页。)
这还是比较委婉的批评,在同期对靳以的小说集《圣型》的批评,则要直接得多,因靳以的这本集子里的作品基本上都是取材于异域,或以异域的人生活着的殖民地为背景展开自己的故事,王淑明认为,这固然是个鲜明的特色,好和坏一时也很难回答,“不过取材的奇僻险窄似乎让作者在这方面的偏向,更无限止的发展下去,则将来会容易为这样的局限性所拘囚,取材将愈艰难,愈偏狭,而愈走入险窄的路上去,则是可以预言的。”(注:《现代》第4卷第6期,第1073页。)当然,这也是对作者的一个善意的提醒。这一提醒,也还是从艺术上出发的。
3.批评的风格化问题
《现代》的这些批评家,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他们的批评比较个性化,风格化。在批评时,比较注重抒发自己的感受,也不隐瞒自己情感上的好恶,而且文笔生动活泼,各具特点,绝不雷同。不像左翼的一些批评家,在批评时更多地从概念和理论出发,行文生硬干涩,不管是周扬,还是瞿秋白,冯雪峰,其文章尽管有说理的方式之别,但也许是为求“意识正确”之故,大都面目僵硬难辨,给人千篇一律之感。
而之所以如此,也还是与双方所采的批评方式不同有关。在这点上,李长之的理论最足以说明问题。李长之在第三卷第四期《现代》发表《我对于文艺批评的要求和主张》,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批评理念,简言之,就是“感情的批评主义”,主张在对作家的作品进行批评时,要对作家有理解的同情,首先批评家应了解和把握作家的创作的“中心观念或思想观念”,其次,是要感同身受,“批评家在作批评时,他必须跳入作者的世界,他不但把自己的个人的偏见,偏好除去,就是他当时的一般人的偏见,偏好,他也要涤除净尽。他用作者的眼看,用作者的耳听,和作者的悲欢同其悲欢,因为不是如此,我们会即使有了钥匙也无所用之。”(注:《现代》第3卷第4期,第455页。),而且,不仅理解作品时应如此,即使在批评作品的技巧时,也要如此设身处地的去体验作者的甘苦,方能对作品的技巧运用的是否成功了然于胸。这就是李长之取之于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采(今译克罗齐)的理论而敷衍而成的“感情的批评主义”,但其并不偏废于感情体验一途,所以,在此前提下,他更强调批评家在批评中应注意“似乎更重要”的问题,即“必须知道作者的社会,环境”。因此,他特别指出,他并不反对用唯物辩证法或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分析作品。但是不能将其简单化或片面化。
赞成唯物史观的人,无疑地首先要分析作者的阶级基础,检定作者的阶级意识。这是应当的。即使不以为文学的创作和批评是种斗争,是件武器,也可以由此而窥出作者所以有那样表现的必然性,以我用前边那两种了解的方法,作为一件有益的对照。人,无论如何跑不出物质的手掌。不过,话必须说得详细一点,否则会陷入一时易犯的错误。物质的条件,并不限于阶级的关系。这是必须辨明的第一点。说明了物质的条件,并不一定包含了评价的意味,这是必须辨明的第二点。(注:《现代》第3卷第4期,第455页。)
他的阐释可谓合情合理。正是这样,他才不赞成那种仅将“物质的条件”视为单一的“阶级的关系”的经济学观点,而将“天性和教育”,也作为其中的重要的因素。这是对作者而言,对作品的评价,他认为主要应考察其内容和技巧两个方面,尤其对作品的技巧批评,他更是非常重视。
关于技巧,技巧的重要,并不次于内容,在创作一篇文艺品时,技巧的重要,无宁是说有过于内容。其所以为艺术者,不在内容,而在技巧。因为技巧是文艺之别于一般别的非文艺品的唯一的特色之故。文艺品不成了法律,不成了广告,不成了传单,其故在此。现在的人,一般的是轻视技巧的,往往顾惜了内容,对技巧有所宽容,这无疑的是,否认了文艺,——即便对内容的论断不妄。(注:《现代》第3卷第4期,第460页。)
这节对技巧的论断的话,简明,有力,显示了李长之的锐利,这也是他的批评文字的风格,因为是哲学系的学生,理论素养较高,他的文章一般都高屋建瓴,逻辑清晰,行文很有气势,又因年轻,而措词用语无所顾忌,故而锋芒毕露,才气迫人。是当时很少的有自己独立系统的文艺主张的批评家。所以,他敢在文中直呼,“感情就是智慧,在批评一种文艺时,没有感情,是决不能够充实,详尽,捉住要害。我明目张胆的主张感情的批评主义。”(注:《现代》第3卷第4期,第462页。)
正因为批评时愿意放入自己的感情,并且不羞于将自己的感受诉诸笔端,才使《现代》的批评家们的文章皆能各备一格,显示出不同的风貌。苏雪林在批评时就笔端常带感情,如果是自己欣赏的作家,华词丽句毫不吝啬,如果对方不为自己所喜,则也会毫不留情地予以说明。如她在第四卷第三期有《论闻一多的诗》一文,将闻一多比作唐诗人孟郊,而对其第一部诗集《红烛》,则有如下论述:
闻氏第一部诗集《红烛》出版于一九二三年,与他同时诗人比较则气魄雄浑似郭沫若而不似他之直率显露;意趣幽深似俞平伯而不似他的暧昧拖沓;风致秀媚似冰心女士而不似她的腼腆温柔。(注:《现代》第4卷第3期,第481页。)
看完这段评论,几让人疑闻一多为天人,但苏雪林并不仅仅满足于抒发自己的感受,她认为闻一多的诗除有世人罕见的“精炼”之美外,还有以下几个特色:一,完全是本色的;二,字句锻炼的精工;三,无生物的生命化;四,意致的幽窈深细。这样的明晰的分析的确让人不由不信服作者的感受。第五卷第五期的《王鲁彦与许钦文》中,苏雪林也是爱憎分明,他推崇前者,称王鲁彦“善于描写乡村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心理与生活,则使他天然成为鲁迅的高足了。”(注:《现代》第5卷第5期,第765页。)对于后者,她则罗列出一串缺点,如,“一则重复语太多”,“二,措词拖沓”,“三则尚有主观口气。尤其不该对人物行动的原因自加解释……又布局空气不紧张;说话不甚合自然语气;拙于写景,文字缺乏鲜明美丽色彩,均是他不及王鲁彦处。”(注:《现代》第5卷第5期,第771页。)从中也可了解,苏雪林的批评并非无根无据。这也是苏雪林批评的特点,即不繁琐,生动,有女性的敏锐的感受力和强烈的情感,而且善用比喻,行文果断快捷,文风泼辣,论点清晰,语言华美,文白相杂,很善于从作品入手,对其本身进行研究,视野也很开阔。
韩侍桁行文冷静,但却幽默风趣,喜欢就事论事,细细分析,让作品自己露出破绽。如在批评《子夜》的那篇文章中,他指出茅盾为使作品吸引读者,也像当时流行的“低级小说”一样,故意设下了许多不必要的“色情的人物和性欲的场面”。所以,他辛辣地讽刺了这一现象。
再如,冯曼卿,既已经莫名其妙地和大块头的资本家赵伯韬开了旅馆,睡了一夜,也就够了,又何必在清晨使她穿着睡衣走到凉台上来,让风吹起她的衣服,“露出她的雪白的屁股”!(注:《现代》第4卷第1期,第137页。)
韩侍桁还批评茅盾让吴荪甫在苦闷时“演了一场不合理的性欲狂”,没有必要地抓住吴妈发泄了一通。
我们直到读了四百四十八页的书,也不晓得吴公馆里有着这么一个“脸上有着风骚的微笑,身上有着风骚的曲线和肉味”的老妈子。(注:《现代》第4卷第1期,第137页。)
当然,韩侍桁也很注重在批评时将自己放入作品中,去感受作品,如在《文坛上的新人》这篇文章中,他在对徐转蓬的小说进行批评时,就谈到,尽管徐转蓬是一个刚离开学校的大学生,但其作品却让人感到不空虚,原因就在于他的每一篇作品中都有一个“故乡”存在。
这一点或者也就是新文坛上的一个比较独特的例子吧。自从鲁迅的小说以后,在许多无数作家的作品里,我们是很少嗅到作家的故乡的气味了,没有故乡味的作品,是使人觉着干燥,觉着不真实,所见到的人物景色虽然应当亲切而反(感)到生疏,因为其中西洋文学的技术的模仿或影响是太深了的原故。(注:《现代》第4卷第4期,第684页。)
这就纯然是他的感受了。
此外,王淑明的一丝不苟的说理,平白如话的文风,还有穆木天的由表及里层层深入的分析和婉转的行文,也都是很有个性化和风格化的批评。
综上所述,即可看出,《现代》的批评态度,即在评价作品时,一方面不脱离现实生活的基础,另一方面,不忘辅之以艺术的考验,概而言之,可称为在现实中追索艺术的完美,这在当时,甚至在以后的很多年,也都是殊为难得的一种态度。这个标准,即到今天,也并未失去其价值。而他们的一些批评作品,也依然值得今天的人们再次予以批评。
标签:施蛰存论文; 艺术论文; 现代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文化论文; 文艺论文; 子夜论文; 李长之论文; 韩侍桁论文; 王淑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