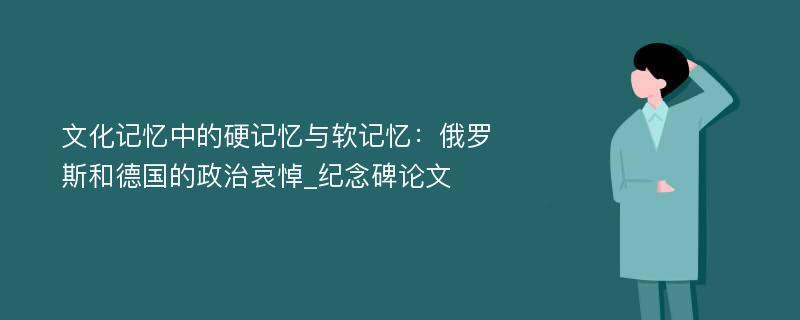
文化记忆中的硬记忆与软记忆:俄罗斯与德国的政治悼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记忆论文,俄罗斯论文,德国论文,政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创伤现实主义 没有哪一种文化象征主义能够表现出大屠杀的极端残暴和它带来的无尽苦难,这一点无需赘言。正如阿多诺的一句名言:在奥斯维辛之后写(关于奥斯维辛的)诗是野蛮的。而其他人则认为,只要是能够描述和铭记这样一场灾难的事情就应该去做。比如作家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他也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他说,如果当年刚从集中营被释放出来时就有人问他该怎么处理这些集中营,他会说:“将它们和纳粹、德国人一起永远地毁掉。”但是,40年后的今天,他更希望在这个地方竖起一座警示性的纪念碑。除了竖立在德国纳粹集中营旧址上的纪念碑,古拉格集中营的幸存者们撰写回忆录的行为也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对极端罪恶的表现和陈述是人类一项基本的、但又不可或缺的活动。从德国的纪念碑到俄罗斯的回忆录,我们可以发现这些都是一连串的——用弗洛伊德的经典表述——“悼念工作”。 在德国,对创伤后遗症的心理学分析表明,创伤经历是代际传递的。创伤事件之后的第二代人、甚至第三代人,在心理健康和社会行为方面都呈现出一种不正常的状态。针对大屠杀的文学想象,迈克尔·罗森格(Michael Rotherg)发明了一个概念:“创伤现实主义”。这样的现实主义不是以被动模仿的方式来反映过去的创伤,而是通过“创造”过去来迫使读者或观者形成对“后创伤文化”的看法。在许多其他的后创伤文化中,文学想象被赋予了社会功能,用以影响人们的政治选择和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时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俄罗斯,斯大林主义政权操控了几代人,比德国纳粹当权的时间还要久。因此,可以预见其后几代俄罗斯人也可能会经受更久的历史创伤,而同时,他们不断掩盖创伤的源头,否认创伤的一系列症状。他们创造出颇具自嘲意味的“苏维埃人”的形象,一种没有道德和经济自主权的生物,这表征着他们向后苏联时代转变的第一步。类比弗洛伊德对神经症的理解,可以想到这种对过去创伤的文化表征事实上具有疗伤的作用。那么,任何这样的表征——包括纪念碑、博物馆、回忆录、历史文本以及小说等——都具有这样的功效吗? 在所有后苏联时代有关古拉格劳改营的纪念物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1990年代末发行的面额为500卢布的纸币(大约价值20美元),现在仍在流通。在2002年发行面额1000卢布的纸币之前,它一直是单张面额最大的流通纸币。它的正面是索洛夫卡修道院,这是位于俄罗斯最北部一个岛上的历史建筑。索洛夫卡当地的历史学家认为,钞票上不常见的圆屋顶确切地表明这张照片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末,而彼时正是古拉格管理下最早和最重要的索罗夫卡集中营发展的鼎盛时期。这种钞票的设计验证了文化记忆的力量,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些不可思议的新问题。我们应该支持那种指责财政部官员有颠覆意图的阴谋论吗?或者,这些文化形式表征的是一种无意识的、但却真实存在的对过去的悼念,将其阐释为一种创伤症候是否更为合理?再或者,这些只是一些平凡的新发现,只是后来才被记忆的狂热者重新解读而已?又或者,我们能将这些连作者或拥有者都无法讲清楚其历史内涵的文化产品作为一种历史的纪念物吗? 无论究竟是以上哪种情况,阐释本身就是一种记忆行为,与立一尊雕像或写一部回忆录一样意义重大。 硬记忆与软记忆 记忆的方式多种多样。公开发布文件或是竖立纪念碑,撰写回忆录或是制作其他纪念物,进行公开讨论或是创建博物馆,都可以获知过去。就像计算机的组成分为硬件与软件一样,文化的记忆形式也有两种。软记忆主要由各种文本组成(包括文学文本、历史文本和其他类型的叙事文本),而硬记忆主要由各种纪念碑组成(有时也包括国家法律和法庭裁决)。当然,软记忆和硬记忆是相互依存的。诸如博物馆、墓园、各种纪念庆典、向导旅游以及历史教科书等,都是硬件(雕刻、方尖塔、纪念馆、历史遗迹)与软件(导游手册、指示牌、碑文、历史研究)在多个层面不停互动的、复杂的文化记忆体系。在记忆领域,没有刻上碑文的纪念碑是沉默的,而不刻在纪念碑上的文字也注定是转瞬即逝的。 历史记忆的硬件——比如纪念碑——是沉默的,而且实际上来说,除非它们被讨论、被质疑、被阐释,或者换句话说,除非它们与文化记忆的软件、也就是当下的精英话语和政治话语之间产生互动,否则形同虚设。而另一方面,那些软件——公共舆论、历史讨论、文学想象——如果不能依托各种纪念碑、纪念馆和博物馆,也会在代际传递中渐渐丢失或被篡改。记忆的“硬件化”是一个有着具体功能、条件和各种限制的文化过程。赋予文化记忆以生命的并非其中硬件和软件的单独存在,而是它们之间的互动、渗透和相互引导。 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动员一批法国作家编纂出版了八卷本的《记忆之场》(1984),这套书专门研究承载着法国历史记忆的各种纪念碑和其他场所,现在已经成为经典之作。通过把文化记忆研究的重点从内容和功能转移至其形式和“场所”,诺拉把分属于法国不同历史阶段的各种纪念碑阐释为不断变化的民族身份认同的一种表征。他认为,国家竖立这些纪念碑的目的是针对某个阶段的自我表征,进而建构一种宏伟的国家形象。这样的记忆就如同一座先哲祠:是专门遴选出来用以表彰过去的伟人和业绩的。对于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而言,使过去的胜利和伟大的领袖成为不朽的记忆不仅是一种必要的手段,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已经成为它们自身结构的一部分。这样的纪念碑彰显的是一种从伟大的开国元勋一直延续至今的政治传统。看看位于华盛顿、伦敦或圣彼得堡的任何一座纪念碑,我们都能感受到一个政府是如何通过这种纪念过去的方式来确证自己与过去一脉相承的。这样的纪念碑成为国家自我展示的实体,它们将国家的身份认同表征为一个联结民族国家、人民和共同历史的理想的统一体。它们生产“真相”,然后将这些“真相”强加给公民和旁观者,它们充当着爱国主义情感的物质表征形式:民族主义总是通过扭曲过去来创造未来,当然,这些承载着历史记忆的场所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成为体现民族主义的物质实体,看得到、摸得着。 帝国主义国家一般不会竖立纪念碑来纪念它们的罪恶。所以,尽管它们曾经在自己的殖民地犯下罪行,如今,对这些罪恶进行记忆的重任是由从前的被殖民国家来承担的。大多数为革命和内部冲突竖立的纪念碑都是为了颂扬胜利者,而有意忽略那些战败者,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比如美国对内战的纪念。与民族荣耀相伴而生的那些苦难则多数以口头传诵或书面文本的形式被保存下来,而不是通过各种纪念碑。在革命年代,这样宏伟的纪念碑往往不可避免地成为最明显的攻击目标。在最近的伊拉克战争中,萨达姆·侯赛因的雕像就成了一出出闹剧的舞台。针对这些纪念性建筑的革命暴力行为,在美国、法国和俄国的革命中同样十分重要。 历史摧毁身份认同,而记忆则建构身份认同。如果说历史遵从主体的多重转变(并且通常紧随其后的就是身份认同的丧失),那么记忆则努力排除各种干扰,保证身份认同的连续性。政治性忏悔可以进一步佐证这个看似矛盾的结论。一个政府为之前的受害者竖立纪念碑,就等于宣告了自己的转变,每一个这样的纪念碑都在诉说着这个政府与之前那个政府的不同。这种纪念碑具有承载历史记忆的功能,这点与一般的纪念碑不同。一个政府为前任领袖竖立纪念碑,是为了确证其政治传统与过去一脉相承的一种连续性;而为之前的敌人(无论是真敌人还是假想敌)和真实存在的受害者竖立纪念碑,则表明了其政治传统与过去传统的决裂。 在我看来,一种关于记忆的政治理论应该以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批判法国大革命时提出的一个著名论断为基础,他说:社会契约“不仅是生者之间存在的一种合作关系,更应该是那些生者、死者以及即将出生者之间存在的一种合作关系”。在这种契约中,不同的世代、死者和生者都是合作伙伴。这份“伟大的原始契约”包含的观点有一定的保守性,但同时又具有创新性和普适性。伯克写道,在这份契约中,一个民族国家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条目而已”。这种对过去和死者的关注在神学语境中比在政治语境中更为常见。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一定程度上将这种关注理论化了,他写道:“过去的一代人与当代人之间存在着一个秘密协议。”各种引证和纪念碑实际上都印证了伯克和本雅明提出的存在于代际之间的秘密协议。引证就是互文性的纪念碑,而反过来,纪念碑则是跨历史的引证。 在缺少大规模公共纪念性建筑的情况下,俄罗斯文化记忆的方式主要集中在文本领域,包括诗歌、想象类文学、通俗历史、传记、回忆录、史学研究著作以及政治辩论等。许多俄罗斯作者在小说(甚至包括一些回忆录)中都尝试着幻想如果没有这段革命,自己会成为什么样。这些幻想的中心主题其实还是历史。这些小说表明,为了把自己重塑为一个更幸福的人,靠想象理想状态下的身份认同根本行不通,需要想象的是整个社会和历史的转变。在研究俄罗斯历史小说——包括从布加柯夫(Mikhail Bulgakov)、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到佩列文(Victor Pelevi)等人的作品——的过程中,我尝试着引入了“神奇的历史主义”这个概念,特指这些作者对历史的一种离奇操控,他们将历史视为一种实验装置,将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其实也暗指他们自己)转换成历史产品的替身。尽管这些文本中充斥着各种疯狂的幻想,但是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一个人的身份必定是历史环境的产物。在这样的文本描述中,人没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改变他们的生活。而能够改变生活的唯一方式就是去想象一条不同的历史轨迹,回溯到历史中,进而用神奇的手段来重塑它。受到质疑和拷问的,不仅仅是这些作者的身份认同,还包括苏联时期的记忆,最终还有整个俄罗斯的历史。 与德国或法国相比,俄罗斯还没有专门针对过去的集体的罪责、记忆和身份认同而展开的严肃的哲学讨论,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尽管历史学家、古拉格集中营的幸存者德米特里·利哈乔夫(Dmitrii Likhachev)在1990年代曾尝试发起一场讨论,可惜在俄罗斯知识界并没有产生能够与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的《德国的罪过问题》(1945)相媲美的成果。在德国或法国,否认大屠杀就是一种犯罪。但是在俄罗斯,政客或教授却可以明目张胆地忽略过去的罪恶,不用承担任何风险。而现在,还没有一种更高的权威,比如说来自职业的压力或国际法庭,能够解决这个难题。“怀旧”已经成为一个很流行的词,成为后苏联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过去的影射已经成为今天政治气候的一个重要特点。俄罗斯各政敌之间最显著的不同不在于他们对经济改革或国际关系的看法,而在于他们对过去的不同阐释。只要是讨论当下的政策问题,都会参照历史经验。像“斯大林主义”、“个人崇拜”以及“政治迫害”这样的概念,在使用频率上与现代法律术语或经济术语的使用频率一样高。20世纪中叶发生的那些事件如今依然历历在目,充满争议性,而且一不小心就有卷土重来的危险。像当代俄罗斯文学一样,今天俄罗斯的政治中也充斥着关于过去的各种知识上或情感上的争论。当代渗透着太多的过去,这份混合的“溶液”不会产生任何沉淀。正如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所说:“如果说西欧的问题是缺少记忆,那么欧洲大陆另一半的问题则刚好相反。这里的问题正是有太多的记忆、太多的过去,人们通常将其当作一种武器,与坚持不同过去的人相对抗。” 这里的历史记忆是一个活跃的综合体,有着不同的历史分期,充斥着各种不同的象征和结论,而社会公众在同一时间体验着这一切。与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概念相比,我们可以把俄罗斯这种历史的过度饱和称为多元历史主义。这种多元历史主义的建构具有去中心化的特征,而且缺乏一个中立的锚点或其他参照点。这导致社会公众无法感知到不同部分之间的不一致或逻辑上的矛盾之处。因此,整个建构很容易因为一点轻微的、随机性的影响而崩塌。当然,俄罗斯的历史记忆很容易成为西方后现代主义嘲讽的对象。比如,圣彼得堡的一家高级饭店叫“俄罗斯刻奇”(Russian Kitsch,意为“俄罗斯式媚俗”):这家饭店的壁画极具俄罗斯转型时期的特色,上面画着苏联集体农庄的农民在与美国的印第安人攀谈,而旁边则是看起来像是美国娱乐界偶像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的勃列日涅夫正对着石器时代的部落发表演讲。这听起来可能相当地后现代主义,不过后现代主义通常对形势秉持着一种讽刺性的自知,但俄罗斯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纪念碑:记忆的结晶 进入一个纪念性的建筑群,游客通常首先看到的是纪念碑,绕过纪念碑就进入了博物馆。在不同的文化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双重结构的纪念性建筑,比如:德国和波兰的纳粹集中营旧址,美国内战的战场和黑奴叛乱的旧址,1812年战争和1941-1945年战争的俄国战场。这种结构模式是一种跨文化的纪念实践模式,它为最不可思议的问题找到了可能的答案,那就是为不可表征的事情找到了表征的方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德战场的战争一结束就开启了纪念过程,虽然整个领土还在盟军的占领之下。同盟国接管了集中营,并且很快对公众开放。这一过程交织着两种作用。首先,对公众开放的集中营成为一个安全、透明的地方,表明这个地方不再有恐怖的事情发生。其次,这种对集中营的保留和修缮,连同过去遗留下来的所有遗迹,都恰恰说明了恐怖的事情的确曾经在这个地方发生过。 在大屠杀旧址上兴建的纪念性建筑通常由两部分组成:一座博物馆和一个纪念碑。博物馆负责讲述故事并展示过去的残留物,它就像演讲或图书一样,提供的是一种连贯的叙事,这使得论证分析和理性批判成为可能。比较而言,历史纪念碑并不符合理性原则。纪念碑通常会使人们产生情绪反应,所以更具有仪式性。归根结底,它们是一种艺术作品,是对神圣的传承。典型的纪念碑通常是一个塔楼,或者是方尖石塔,或者是其他世俗的、抽象的符号,随处可见。与博物馆承载的内容相比,纪念碑通常没有任何比喻性的历史含义。在博物馆中,重建毒气室、营房和监室是为了仿造它们的历史原型,并且这种仿造越逼真越好。与此相反,纳粹统治下的集中营里却没有纪念性的尖塔。关于纳粹集中营的纪念碑并不是要还原历史实物,而是一种情感和判断的表达。纪念碑总是笔直地矗立在最核心的位置,就像一根木棍将神话中的吸血鬼钉在地上,或许这是一种解释纪念碑的方式。 纪念协会的资料库里记载了苏联斯大林时期各地建立的大约500处纪念碑、牌匾以及纪念性题词。同样,这个资料库里还记载着由大约400个广泛分布的集中营组成的古拉格集中营系统。显然,这样的纪念从规模上来说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从质量上也远远达不到应有的水平。在古拉格众多的集中营里,只有位于索洛韦茨基和彼尔姆的集中营旧址上设有一些小型博物馆,用以展示集中营的条件、折磨和谋杀囚犯的方式以及各种文件、画像。这两个集中营分别标志着古拉格集中营系统的开始(索洛韦茨基集中营)和终结(彼尔姆集中营)。有些集中营在1930年代末期囚禁了数十万受害者,然而,针对这些最重要的集中营却没有任何纪念活动。 甚至在游人如织的旅游胜地索洛韦茨基这样一个作为古拉格记忆的代表的地方,也没有任何一处由曾经的营房直接改造成的博物馆。它曾经是第一个集中营,也是示范型集中营,运营了长达20多年时间,有近100万人在这里被监禁。考虑到这些事实,今天这里的情况相当令人震惊。曾经用来监禁受害者的那些修道院的楼宇如今又重新成为东正教的教堂,履行着其最初的职能。500卢布的纸币上纪念的正是这些建筑。在这些见证了曾经的血腥大屠杀的楼宇中,只有一处有一个纪念性的牌匾,上面写着“索洛韦茨基集中营儿童营房”,如此简单,但又如此令人心碎。索洛韦茨基曾经发起了一些更为日常性的纪念活动,包括在之前的一个营房中开设一家私人博物馆。在所有的纪念项目中,不出所料,最成功的是一本书。最近由当地历史学家和摄影家尤里·布罗茨基斯(Jurii Brodski)编辑的这本书,已经成为纪念古拉格受害者的最重要的软记忆。 在诺夫哥罗德市,距离古城墙不远的地方有一座苏联风格的公园,是当时一些共产党老兵为纪念十月革命而建的,其中有一座献给受害者的纪念碑,由花岗岩制成,呈一个蜡烛形状,顶端是金属制的灯芯。纪念碑上镌刻着如下铭文:“不要让我们的命运成为你的命运。”就像很多其他实例所展示的那样,文本总是比纪念碑传达出更强大的力量。 石头和十字架 在索洛韦茨基岛上,全俄东正教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Alexei II)在谢基尔卡山的入口处竖起了一个十字架,这个地方就是臭名昭著的1920年代大屠杀遗址。十字架上刻有长长的详细文本,书写着关于受害者的记忆,虽然以古体文字写成,但语言却清晰有力。在很远处就可以看到这个十字架,然而必须走到最近处才能看清上面的文字。多数游客并没有看到这些文字,而只是将这个纪念碑视为修道院里无数十字架中的一个。在索洛韦茨基的一处万人冢旁,有两个纪念碑看起来像是在互相抗衡:一个是东正教的十字架,一个是纪念协会主持竖立的花岗岩纪念碑。两个都没有包含任何埋葬在这里的受害者的信息。2002年,莫斯科绘画雕塑建筑学校与莫斯科纪念协会在索洛韦茨基联手举办了一次献给“政治压迫的受害者”的纪念馆设计大赛。在50个设计中,有20个设计以东正教教堂作为纪念的主体建筑,有9个设计以十字架、天使和时钟为核心角色,有11个设计以方尖石塔或废弃物等世俗象征为主;只有5个设计主张建造庄严的博物馆空间,2个设计提议重建集中营的部分建筑。 将对古拉格的记忆转向宗教象征主义存在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关乎受害者的宗教信仰(其中一些受害者是无神论者),另一个问题是:受害者的遇难是一种非宗教性质的牺牲。与德国的情况类似,这种遇难带有世俗的、政治的色彩,这就使得一切宗教的、有时甚至是非宗教的阐释受到了高度质疑。将这种记忆的形式从宗教渊源中解放出来并不容易。在俄罗斯,很多纪念性建筑,甚至一些当代的新建筑,都使用了象征着苦难、屈辱和死亡的基督十字架。但是,在东正教教堂里,只有对那些信教者而言,十字架才是适当的纪念物。使用十字架作为纪念物并不能将国家恐怖主义造成的死亡与其他死亡区别开来。因此,这样的象征形式否定了古拉格灾难的历史特殊性。许多死于古拉格集中营的受害者并非基督徒,而是犹太人或穆斯林。除此之外,还有一多半是无神论者。东正教的十字架与天主教和路德教派的十字架在形状上也并不一样,而且,即使老派的东正教十字架,也与权威的东正教十字架不一样。因此,在一些地方,除了巨大的东正教十字架,人们还可以在旁边看到很多少数派宗教竖立的十字架。这种宗教象征主义似乎并不适合反映其政治和历史本质。 白海—波罗的海运河是古拉格集中营劳改犯曾经工作的最大的建筑工地之一,当地纪念协会的热心活动家就在俄罗斯西北部靠近运河的地方发现了其中一个最大的万人坑。1997年,这里建起了桑达尔莫赫(Sandarmokh)公墓。今天,这里已经成为俄罗斯发展最好、也是最重要的记忆之场。这处纪念地的主要元素就是木桩,每一个木桩都代表了一个坟坑。这些木桩的顶部都有尖尖的角,似乎是在暗示观者,这是一个乡下的十字架或是祷告时竖立的手指,这样的特殊造型成为当地表达悼念的一种象征。散落在松林里的几十个木桩在这片可怕的、坑坑洼洼的土地上形成了一幅骇人的图景。这处纪念地还有一尊比拟性的雕塑,象征着坠落的囚犯和用翅膀保护他们的天使。铭文上镌刻着:“人类,请勿彼此残杀。”此处开放之后,不同的宗教派别都在这里竖起它们自己的十字架,这些十字架与木桩之间以及十字架彼此之间相互抗衡。俄罗斯东正教也在附近建起了一座教堂。桑达尔莫赫在视觉结构上相当有效,但却没有任何相关的文本信息。这里没有博物馆或信息展板,甚至连高速路边的指示牌上都只是写着“桑达尔莫赫公墓”,但却未表明这是一处历史纪念之地。像许多其他的案例一样,这种公开信息的缺乏并不是由于政治审查制度。这处纪念地的发起人出版的《卡累利阿记忆之书》(Karelian Book of Memory)非常棒,书中罗列了数千名恐怖时期的受害者,这再次证明了书籍在保存记忆方面比纪念碑更好。 在最为祥和的20世纪之初,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曾经提到过一个很著名的观点:在地球上没有什么比纪念碑更不起眼了。然而,后苏联时代的纪念碑显然比其他纪念碑更不起眼。从圣彼得堡到普斯科夫的高速公路边有一家小餐馆,餐馆的墙上有一面用金属精心制作而成的纪念板,上面写着:斯大林主义的受害者在这里被谋杀。这个纪念板没有提到这些受害者是谁,也没有告诉我们又是谁制作了这个纪念板,小餐馆的现任老板也对此一无所知。在圣彼得堡与莫斯科之间的谢利格尔湖畔的修道院入口处竖立着两块一模一样的纪念版,上面分别用俄语和波兰语写着:成千上万的波兰士兵在这里死去(二战期间,他们从德国逃到俄罗斯,却又死在这高墙之内)。对于同样死在这里的苏联公民,却没有任何相关记载。这两块纪念板是波兰人竖在这里的,他们还将文本翻译成了俄语,这已经很不错了。 世俗的多元文化社会需要并且也制造出了一些共同的象征符号,但是这些符号本身并没有很强大的文化力。为了建造献给受害者的纪念碑,俄罗斯的艺术家们使用了一些人物或动物的形象,比如一个哭泣的女人(阿巴坎市)、一个跪着的男人(特维尔市)、一只受伤的鸟(阿斯特拉罕市)以及狮身人面像(圣彼得堡市)。这些形象传达的效果并不好。几乎在所有的设计中,“受害者”都被表征为被动的受难者,没有反抗的能力,“政治迫害”被呈现得像死亡一样不可避免。这样的意象与当代德国和以色列的情形非常不同,尤其是在以色列,对大屠杀的表征追求的是反抗的英雄而非被动的受难者。当时的政治犯之间的团结,他们与施害者以及当局的斗争,以及发生在集中营的无数反抗和逃跑事件,所有这一切在俄罗斯的纪念碑中没有一点痕迹可寻。除了一些寻常的刺铁网图案,我们无法再从这些纪念碑当中获知有关当时的酷刑、监禁以及处决的更多信息。缺乏相关信息是这些纪念碑典型的通病,包括那些最为精致的纪念碑也是如此。比起高度抽象的纪念碑,那些信息展板和历史说明似乎更容易受到攻击,也因此,那些记忆活动的发起人将他们了解的内容写进了书籍。梅德韦日耶戈尔斯克市一家博物馆的馆长就认为,比起在大屠杀旧址上放一块信息展板,在博物馆里面举办一场“政治迫害”展览更容易些。 社会共识的缺乏和政治连续性的断裂增加了从文化层面进行历史表征的难度。一些艺术家和活动家通常采用巨大的原石来进行表征,这其实是一种美学上的极简主义方式。继十字架之后,巨石成为俄罗斯纪念碑的第二大类型。这种抽象的象征主义使得记忆的需求与政治对抗的风险之间达成了一种妥协。对于这样的纪念碑而言,文字至关重要;没有文字,巨石传达的意思就会模糊不清。 德国的记忆艺术中有很多实验性的尝试,既有成功也有失败。其中一个成功的案例是位于倍倍尔广场上纪念柏林焚书事件的建筑。这座建筑于1996年建成,人们透过人行道上的半透明玻璃,可以看到位于广场地下的一排排空荡荡的书架,这是一座没有图书的图书馆。另外一个引人关注的例子是位于布痕瓦尔德市的“温暖纪念碑”,它于1995年建成。50年前,就是在这个地方,曾经的被囚禁者为那些遇害者竖起了第一座纪念碑。雕塑家在此地竖立了一块方形石头,并让它保持人体的温度,从而使得冬天的游客很愿意去触摸它。还有一个例子是位于汉堡市郊的一座大屠杀纪念碑,它由一个13米高的水泥圆柱构成,因此成为涂鸦的天然场所。这座纪念碑的巧妙之处在于它一直在缓慢地下沉。7年的时间里,它完全沉入地下,一起消失的还有纪念碑上数以千计的签名。 早期的雕塑具有更强的叙事性。俄罗斯19世纪的纪念碑都带有冗长、复杂的自述,今天看来也许只有漫画能与之媲美了。另外,俄罗斯那些纪念二战胜利和受害者的纪念碑也都拥有多幅图画,兼具多重叙事性。今天,在俄罗斯西北部旅行的游客一定不能错过“伟大的卫国战争”纪念性建筑群,其中就有展示牺牲前一刻全副武装的士兵形象的叙事性纪念碑。这些建筑群里刻有英雄的名单以及“没有什么事件被遗忘,没有什么人被遗忘”这句话。虽然这句题词无处不在,但它并不总是正确的。 俄罗斯几乎所有的记忆工程,无论是软记忆还是硬记忆,都是由个人启动的。主动承担这项工作的是来自各种背景的热心活动家。其中,我曾采访过的有物理学家、水管工、前军队军官以及一位博物馆馆长。而另外一方面,如果不与政府合作,独立的个体和志愿者组织也无法竖起纪念碑。政府控制着档案,在最近10年,查阅档案也变得越来越难。而任何纪念性建筑所需的财政资源和土地也由政府控制。如果说撰写回忆录主要是个人活动,那么建造纪念碑就是集体性活动。此外,由于它巨大的规模和公共属性,一般也需要有政府的参与。因此,硬记忆通常由政府负责,而软记忆则属于社会的责任范围。 由于各自特殊的政治环境,德国文化与俄罗斯文化分别产生了对待过去的不同方式。德国的记忆更多地体现在“硬件”型的纪念性建筑(比如博物馆)中,并且随后总是紧跟着一场文化论争,来讨论如何激活记忆,防止其僵化。而俄罗斯的记忆则弥散于“软件”型的文本和各种即时的体验之中,没有在各种稳定的、无可争议的纪念性建筑中得到固化。尽管俄罗斯记忆的发展是缓慢而痛苦的,但是相较于德国而言,它是一个自动的过程,不像后者的发展部分是在外部压力的驱使下完成的。记忆的固化是一个有着特定功能、条件和各种限制的文化过程。它能确保事态不会重蹈旧辙,过去的恶魔会被驱除,而当下会获得胜利。在一个民主国家,这样一个过程需要在公共领域内达成相关共识。而这种共识通常是在“软件”型的社会讨论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达成,因为这种讨论也是达成共识的原因。如果没有达成共识,那么没有纪念碑作为载体的记忆就很容易受到周期性的质疑和否定。新的声音总是能抚慰人内心的罪恶感,所以即使是最有影响力的文本也会受到新文本的挑战。 虽然文化记忆依据不同的原则建构而成,但是它是公共领域(哈贝马斯如此定义)中重要的一部分。针对同一个历史主题,可能会有两种不同的、却又都合理的解释,但是,两种纪念碑在同一地点同时存在是绝不可能的。针对过去的知识性讨论,可以是多种讨论同时存在,但是纪念碑只能是单个存在。一次历史论争无法为一个记忆问题画上句号,然而纪念碑可以做到。但是,没有哪一种记忆是绝对的硬记忆:就像资本可以被转移一样,纪念碑也可以被移除。圣彼得堡在一个世纪里曾四次更名。纪念碑可以移来移去,这对看惯了沙皇铜像移来移去的俄罗斯人来说并非大新闻。即使木乃伊的位置也可以是不固定的。1961年,苏联大众就从电视机上获知了斯大林遗体从列宁墓中迁出的消息。 *本文原载《灰色房间》(Grey Room)2006年夏季号,译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