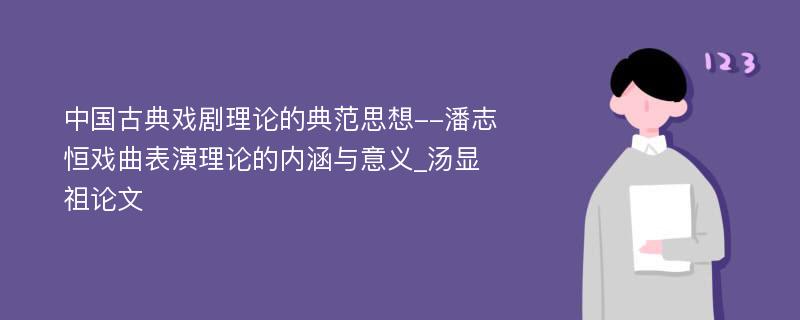
情痴说:中国古典剧论的典范思想——潘之恒戏曲表演论的内涵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戏曲论文,典范论文,中国古典论文,内涵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9)06-0122-04 [收稿日期]2009-08-10
中国的古代戏曲理论历来重视作家和作品的评论,无论是钟嗣成的《录鬼簿》、贾仲明的《续录鬼簿》,还是吕天成的《曲品》、祁彪佳的《远山堂曲品》、《远山堂剧品》等,其着眼点都在作家、作品身上,而真正体现一部戏曲作品的艺术生命力还是要靠舞台表演,但是关于演员表演艺术的评论在中国的古代戏曲理论中一直是较为薄弱的环节。
元杂剧演出兴盛的元贞、大德年间,与关汉卿、马致远等人同时的就有珠帘秀、天然秀等一大批优秀的演员,以这些演员为介绍对象的夏庭芝的《青楼集》应运而生。在《青楼集》中,夏庭芝对这些艺人们的表演作了一些简单的评论,使我们得以了解那个时代的戏曲演出情形。明传奇演出兴盛的万历年间,与汤显祖、沈璟等人同时的有杨美、傅灵修、杨仙度等一大批杰出的演员,潘之恒作为这个时代独具慧眼的戏曲评论家,对她们的表演作了更加细致的评论,使中国古典戏曲理论中关于表演艺术的评论得以充实和发展。
一
潘之恒(1566—16227),字景升,歙县(今属安徽)人。他所著《亘史》、《鸾啸小品》中有大量关于戏曲演员表演的评论,这些评论在中国戏曲理论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潘之恒的戏曲表演论是以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里一批优秀演员的表演为评论对象,对其表演经验作了较为具体的总结,非常具有启发性,而且他的表演理论又有一定的深度,接触过潘之恒戏曲表演论的人大多为他的理论所折服。有论者甚至认为:“潘之恒对搬演问题接触的广度,理论探讨的深度,在古典剧论家中可推第一。”[1](P200)
在戏曲表演方面,潘之恒针对演员的素质、表演的技巧以及演员的情感体验等问题都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尤其是他戏曲表演论中的“情痴说”值得我们予以充分重视。
潘之恒的“情痴说”与汤显祖的名著《牡丹亭》有密切的关系。明代万历剧坛上,汤显祖的《牡丹亭》一出现就引起很大的轰动,他所塑造的杜丽娘——这一为了情而出生入死的人物形象深深地打动了人们的心灵。《牡丹亭》很快被搬上戏曲舞台,但如何演好杜丽娘这个至情至性的女子,是摆在演员面前的一道难题。为此,潘之恒在《情痴》一文中提出:“故能痴者而后能情,能情者而后能写其情。”[2](P72)即演员必须是情痴之人才能理解杜丽娘的至深之情,从而准确地将她再现在舞台之上。潘之恒的“情痴说”虽然是针对如何演好杜丽娘而发,但在戏曲表演中实具有普遍意义。
在潘之恒看来,凡是优秀的戏曲作品都是以情动人的。他说:“推本所自,《琵琶》之为思也,《拜月》之为错也,《荆钗》之为亡也,《西厢》之为梦也,皆生于情,而未致也。”[2](P13)《琵琶记》、《拜月亭》、《荆钗记》、《西厢记》等作品虽然都是以情动人,但尚未达到极至,只有汤显祖的《牡丹亭》塑造了杜丽娘这一具有“至情”的人物形象,才感人至深:“夫情结于梦,犹可回生死、结良缘,而况其构而离,离而合以神乎?自《牡丹亭》传奇出,而无情者隔世可通。此一窦也,义仍开之。而天下始有以无情死者矣。”[2](P70)作品聚集了作家的情感,人们阅读作品时,可以通过剧中人物直接体会到作家的思想感情,而演员的任务不仅要自己体会到作品中所蕴藏的情感,而且还要在舞台上通过身体和语言将这种情感再现出来。因此,演员必须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否则他就不可能体验到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又是作家思想感情的投射,一个思想平庸、情感枯竭的作家不可能创作出感情丰富的人物形象,像汤显祖这样感情充沛的作家,当其塑造了杜丽娘这样的为情而出生入死的人物形象时,如果演员仅仅是个感情丰富的人,也不一定能把握住杜丽娘情感的细微之处。这一差距,演员们该如何解决呢?潘之恒认为,演员必须是个情痴之人,才能演好杜丽娘这样有至情的人物形象,他说:“夫情之至,不知其所始,不知其所终,不知其所离,不知其所合。在若有若无,若远若近,若存若亡之间,其斯为情之所必至,而不知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而后情有所不可尽。而死生生死之无足怪也。故能痴者而后能情,能情者而后能写其情。”[2](P72)
“故能痴者而后能情,能情者而后能写其情。”这句话是潘之恒戏曲表演论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它有三个方面的含义:
首先,他要求演员“能痴”,即演员能痴于情,或者说演员须是个情痴之人。潘之恒所说的情痴,不仅指演员在舞台上能痴情、忘我地表演,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要有执著的感情,这是成为一个优秀演员必备的一种素质。潘之恒赞扬出色的演员时,每每用“情痴”二字,如友人让他品题常州昆曲演员李纫之时,他脱口而出“情痴”二字[2](P133);他认为友人吴越石家班中的演员江孺、昌孺“各具情痴”[2](P73),所以才能饰好杜丽娘与柳梦梅。
其次,要“能情”,即演员要善于解情。潘之恒认为“能痴者而后能情”,也就是说,一个情痴之人才有可能理解他人之情,演员仅有情痴还是不够的,戏曲表演不能抛开理性的因素,出色的演员不仅要熟谙人情,而且要善解人情;不仅能在曲师、教习等人的指导下熟悉作品,了解人物,而且也要凭自己的智慧去理解角色情感背后更深层的东西。演员是情痴之人,剧中人物为至情之辈,演员就很容易对剧中人物所蕴涵的情感产生共鸣,从而深入了解剧中人物的情感,因此,情痴之人还须善解情,否则只能是痴而不化,成不了出色的演员。但情痴者痴于情又不能溺于情。潘之恒说:“虽然,情重者,非谓其溺也。谓其溺,而不能以想超也。”[2](P70)演员培养自己痴绝的情怀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角色的情感,溺于情则限制了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及艺术表现力,也不能很好地解情。潘之恒把演员对角色情感的理解提到很高的位置加以强调,他认为这是演员表演成败的关键。他说:“又见丹阳太乙生家童子演柳生者,宛有痴态,赏其为解。而最难得者,解杜丽娘之情人也。”[2](P72)丹阳太乙生家童子即吴亦史,潘之恒曾多次观看过《牡丹亭》,他觉得只有吴亦史把握住了柳梦梅的性格特征,所以才能将柳梦梅演活[2](P210)。其后只有吴越石家班中的昌孺所演柳梦梅差可与之媲美。解杜丽娘之情的人最为难得,因为杜丽娘的情感世界细微复杂。而江孺成功地把握住了杜丽娘的性格特征,以自己的情痴去体会、理解杜丽娘的至情,终于很好地饰演了这一角色。
再者,是写情,即演员在表演时要把他所理解的人物形象再现在舞台之上,这种再现是演员对剧中人物情感体验的结果,它是建立在解情的基础之上。潘之恒以江孺、昌孺为例对此进行了说明,江孺领会到杜丽娘的“情痴而幻”的情感特征,昌孺领会到柳梦梅的“情痴而荡”的情感特征,因此在表演时,“江孺情隐于幻,登场字字寻幻,而终离幻;昌孺情荡于扬,临局步步思扬,而未能扬”[2](P73),他们的表演成功地刻画了人物形象。
情痴——解情——写情,是潘之恒对戏曲表演的一种概括,情痴是基础,解情是关键,写情是目的。即使是一个平庸的演员,他也有解情、写情的过程,而出色的演员解情解得透彻,写情写得充分,而要做到这样,必须以情痴为前提,潘之恒拈出“情痴”二字构筑了其戏曲表演论的基石,我们可以称之为“情痴说”。
二
潘之恒的“情痴说”不是凭空创造出来,它的产生有一定的理论背景,它是晚明戏曲理论中“主情说”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同时,又与晚明文人的审美情趣息息相关。
晚明的戏曲评论中以李贽为肇端的“主情说”有着一股强劲的势力,戏曲评论是李贽文艺评论的一个部分。李贽文艺思想的核心是“童心说”,因而他的戏曲评论也贯穿着“童心说”。就文艺创作而言,李贽的“童心说”重在标举“真心”。他说:“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3](P92)童心也就是赤子之心和真情实性,只有用童心即真心去创作才能有真文学,否则就是假文学。由此出发,他认为,任何体裁的文学创作,只要融汇了作者的真情实感,而且感人至深,都可称为“天下之至文”。因此,他针对《拜月亭》、《西厢记》、《琵琶记》几部感人至深的作品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拜月》、《西厢》化工也;《琵琶》,画工也。”[3](p90)他还指出:“画工虽巧,已落二义矣。”[3](p90)这是因为《拜月亭》、《西厢记》都是绝假纯真之作,而《琵琶记》却是“似真非真”之作。李贽通过评论具体作品提出作家在创作戏曲作品时,必须要有真实感情,他把真情放在声律、关目、宾白之前加以强调,由是而揭开“主情说”的滥觞。
汤显祖在李贽“童心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把主情的理论带到戏曲作品中。在汤显祖看来,戏曲作品主要通过剧中的人物形象来打动人的心弦,一部戏曲作品要能做到感人至深,剧中的人物必须有至深之情,而剧中人物的至深之情也是作家真情的一种艺术化的再现,他以自己笔下的杜丽娘为例指出:“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漠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必因荐枕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4](p1153)汤显祖在这段话中提出,像杜丽娘梦中之情这类的事,不一定非要真有其事不可,它不过是作家的艺术创造,作家也只有通过艺术构思才能创作出有至情至性的人物形象,其作品才能感人至深。汤显祖的“至情说”从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进一步丰富了“主情说”的内容。
潘之恒的“情痴说”则是直接建立在汤显祖的“至情说”基础上。汤显祖既然塑造了杜丽娘这一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演员就有责任将她演好,但这并非一件易事。潘之恒认为,演员必须是情痴之人才能体察、理解杜丽娘情感世界中细微、深刻之处,从而把握她的精神实质,进而准确地将她再现在舞台之上。潘之恒的“情痴说”重在演员的情感体验,他从吴越石家班中的演员江孺身上看到自己最理想的表演:“本是情深者,冥然会此情。难逢醒若梦,愿向死求生。”[2](p205)潘之恒从表演的角度再一次丰富了“主情说”。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李贽的“童心说”要求作家创作要有真实感情,尤其是以感动人心为目的的戏曲创作更要有真情。在戏曲创作中,李贽的“童心说”也可称之为“真情说”,它侧重于作家的创作素养;汤显祖的“至情说”要求作品中的人物能体现感人至深的情愫,才能打动读者或观众的心弦,它侧重于作品的内涵;潘之恒的“情痴说”要求演员必须做情痴之人,用自己的情痴去体会作品人物的至情,然后将它再现在舞台之上,它侧重于演员的表演。从作家、作品到表演,李贽、汤显祖、潘之恒三人的戏曲理论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三者紧密联系,以“情”字为线贯穿其中而又层层深入,它们构成了晚明曲论中“主情说”的骨干。
三
潘之恒的“情痴说”不仅有理论上的根源,而且也是晚明文人审美情趣的一种表现。潘之恒说:“余有情痴,闻情事则屡夜不寐。”[5](卷31)可见,他的“情痴说”与其审美情趣有很密切的关系。类似的表述在晚明文人中不乏其例。如冯梦龙在《情史》一书的序言中云:“情史,余志也。余少负情痴,遇朋侪必倾赤相与,吉凶同患。”[6](P1)他在《情史》中辑有“情痴类”,称庄子笔下的尾生是“万世情痴之祖”[6](P226),也表现了他和潘之恒相近的艺术趣味。张琦的《衡曲麈谭》里有《情痴寤言》一篇,亦是以情痴自勉:“人,情种也;人而无情,不至于人矣,曷望其至人乎?情之为物也,役耳目,易神理,忘晦明,废饥寒,穷九州,越八荒,穿金石,动天地,率百物;生可以生,死可以死,死可以生,生可以死,死又可以不死,生又可以忘生。远远近近,悠悠漾漾,杳弗知其所之。……斯情者,我辈亦能痴焉,所问一腔热血,所当酬者几人耳?”[7](P273-274)在晚明文人话语中与“痴”意思相同的还有“癖”。袁宏道在《与潘景升》信中说:“弟谓世人但有殊癖,终身不易,便是名士。如和靖之梅,元章之石,使有一物易其所好,便不成家。”[8](P1597)张岱也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9](P92)在他的名篇《湖心亭看雪》中,张岱借舟子之言说:“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9](P73)痴和癖都表现了人的一往情深,晚明文人推崇痴与癖其实就是对真的赞美。后来,张潮在《幽梦影》中所言“情必近于痴而始真,才必兼乎趣而始化”[10](P81),即是此义。所有这些关于“痴”与“癖”的议论都集中出现在晚明这一段时间决非偶然,它表明,在假道学盛行的明代社会,人们对真性情的讴歌与赞美,这也是晚明文人审美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戏曲表演的角度来看,潘之恒的“情痴说”意义还不止于此。他的“情痴说”强调演员的情感体验,即要求演员在日常生活中注意体会各式各样的感情,来培养自己的痴情,再用这种痴情去体验剧中人物的感情,进而将它表现出来。从这个层面上看,潘之恒的“情痴说”近于西方戏剧表演论中体验派一类的理论。
西方演剧理论中的体验派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为代表,他主张演员在创造角色时,必须体验角色的感情,设身处地,假戏真做,要把角色的心灵放到演员的身上,演员要生活于角色,始终与角色保持一致。他引用19世纪意大利著名演员萨尔维尼的话说:“每一个伟大的演员都应当感觉到,而且应当确实地感觉到所表演的一切。我甚至认为,演员不仅要在研究角色的时候一次再次地体验自己的激动心情,并且在他每次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无论是第一次或者是第一千次,他都应该或多或少地去体验这种激动心情。”[11](P29)中国古典戏曲表演中除了程式化的表演体系之外,确实有一些演员注重对角色的体验,表演时和角色融为一体。明代女优商小玲可谓杰出代表,她以擅演《牡丹亭》中的杜丽娘著称,每当演到《寻梦》、《闹殇》等折时,都能做到“真若身其事者,缠绵凄婉,泪痕盈目”[12](P197)。一天,她演《寻梦》,由于感怀身世,悲伤过度,竟至随身倚地,死在台上。商小玲把自己化为了杜丽娘,同剧中主人公一起魂人地府,她以生命为代价,体验了主人公出生入死的情怀。潘之恒的“情痴说”也是要求演员以情为通道进入到角色里面去,从而在表演中达到忘我的境界。他在谈到女演员杨美的表演时说:“杨美之《窃符》,其行若翔,受拷时雨雪冻地,或言可立鞠得辟寒,美蒲伏不起,终曲而肌无栗也。”[2](P32)杨美是潘之恒最为欣赏的女演员之一,她的表演之所以博得潘之恒的赞赏,就是因为她在表演时与角色融为一体。
在中国古典曲论中,像潘之恒这样注重演员内心体验的曲论家并不多见。一些戏曲研究者认为,中国传统的戏曲表演除了重表现之外,也重视体验,那么,潘之恒的“情痴说”就是最好的注脚。通过潘之恒的曲论,我们对中国古代伶工注重内心情感体验的认识又可以往前深入推进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