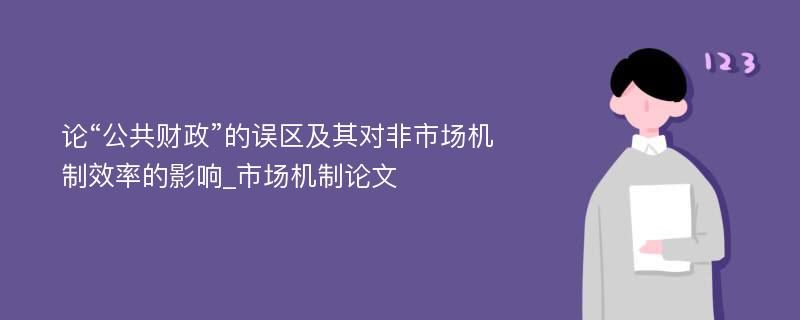
——论“公共财政”的误区——兼论非市场机制的效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机制论文,误区论文,公共财政论文,效率论文,兼论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关于财政学的名称及变迁
亚当·斯密创立古典财政学之后到本世纪50年代之前,财政学的英语名称通常用"Public Finance"来命名。"Public Finance"相对应的学科名是"Business Finance"。后者译为“企业财务”看来是没有多大争议的。据此,"Public Finance"的直译应该是“公共财务”。但是,“公共财务”的译法在中国并无市场,因为一开始就被意译为“财政”,而且被广泛接受和流传至今。
“财政”这一译法是“拿来主义”的产物。“财政”最先是由日本人学习西洋文化,对"Public Finance"意译的结果。这一学科领域涉及的问题和市场机制领域是既有共性又有区别的。相同点都是货币收支,区别点在于"Public Finance"的货币收支都与政治有关。可见“财政”作为意译名称是揭示本质特征的,因而可以说是较好的译法。既然“财政”是"Public Finance"的意译,就不存在“公共财政”的译法,更不存在“公共财政”和“财政”是两种不同财政类型的概括问题。甚至可以认为“公共财政”是一种不伦不类的说法。
上世纪末中国维新派引进西洋文化是从间接“进口”的。中日文字同宗,故沿用财政译法。1898年主管国家财务的“户部”(相当于“财政部”)向皇帝上的奏本(相当于国家职能机构向最高统治者递送的报告)上就用了“财政折”的称谓。“财政”的流行和普及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深入人心有关。孙中山在宣传三民主义的时候,多次强调“财政”改革。满清政府被推翻以后,主管国家财务的职能机构也用“财政部”命名。与此相适应,西方国家的类似职能机构的命称"Treasury"也被译为财政部。这个译法也是“财政”在中国深入人心以后的意译译名的例证。相应的例子有"Public Rrevenue","Government Revenue"被译为“财政收入”,"Public Expenditure","Government Expense"被译为“财政支出”等等。
由于“财政”是个意译名称,因此其中已经隐含了“公共财务”,“国家财务”的背景内容。财政部就有“国家财务部”或“国家资金供应部”的含义;财政收入就有“国家收入”的含义;财政支出就有“国家支出”的含义。“国家”和“公共”之间本来就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因为国家从其诞生起就以代表“公共利益”的面目出现的。至于“国家”是否真正代表公共的利益,或代表到什么程度,那是另外性质的问题。
现代西方财政学已经扬弃了"Public Finance"的用法,而代之以"Public Sector Economics"的规范用法。本世纪50年代,财政大家马斯格雷夫(R.A.Musgrave)在撰写财政学时,仍然用了"Public Finance"这一命称。例如他撰写的"Public Finance in Theory and Pracrice"(中国著名教授邓子基有删节的中译本,译为“美国财政理论和实践”)一书,影响很大。但作者在书中指出,当时学术界已经都更喜欢用"Public Sector Economics"这一称谓了。他只是考虑到"Public Finance"的名称已经沿用很久,因此在书中加入新内容以后更易普及推广,故沿用旧命称。"Public Sector Economics"的直译是“公共部门经济学”。但“公共部门经济学”的术语在中国影响不大,考虑到“财政学”是意译,因此把新名称译为“财政学”也是未尝不可的。
二、财政学名称变化的原因
财政学科用"Public Finance"来概括和用"Public Sector Econo-mics"来概括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同呢?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变化的呢?"Public Sector Economics"(以下简称“现代财政学”)与"Public Finance"(以下简称传统财政学)的区别主要有两点。一是传统财政学只注重于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收入)的经济分析而缺乏对财政支出的经济分析,而现代财政学弥补了这一缺憾。二是传统财政学没有对财政决策进行经济分析,而现代财政学则是重要的分析领域。这一变化是在理论和实践的交互发展中形成的。
由于财政学科与国家相联系,因此长期以来与国家学说,政治学说,社会学说纠缠在一起,没有办法作经济分析。以致于在亚当·斯密之后的近200年间,财政学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发展(萨缪尔森语,见《经济学》),严重滞后于经济学说的其他领域(主要是市场机制领域的学说)。现代财政学开创以来大大推进了整个经济学说的发展。现代财政学已经不单纯是经济学说的部门学科,而在经济学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现代财政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本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20年代以前社会公平问题在古典经济学中已经被提及,在传统财政学中也有支出类别的介绍,但缺乏经济分析。以致于“社会公平”属于伦理范畴还是经济范畴争论不下。为“社会公平”成为经济学中研究范畴作出理论贡献的首推福利经济学家庇古。尽管社会公平的标准至今仍在争论且没有统一的认识,但运用新古典经济分析方法分析社会公平问题的理论却日益完善。社会公平的职能是由国家去履行的,市场机制无能为力。因为在市场机制领域收入分配的法则是要素定价,即土地的价格是地租、资本的价格是利润、劳动的价格是工资,不占有任何要素者是不可能获得收入的。看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非国家莫属。因此,庇古在研究社会公平问题时首次提出了非市场机制(non-market)这一新概念。庇古的研究成果对其后财政学的发展影响巨大。一是对国家的经济行为运用新古典经济分析方法分析。二是对国家的经济行为用非市场机制来概括。虽然庇古主要是针对社会公平而言的,但其后在国家进行资源配置、宏观调控等方面的经济分析,显然也是属于非市场机制的。这为现代财政学成为“非市场机制经济学”和“市场机制经济学”并驾齐驱的学科开了先河。本世纪40年代产生的“混合经济”概念就是指经济社会中这两种机制的“混合”。
财政学获得飞速发展的第二阶段是本世纪30年代以后,到50年代形成现代财政学体系,一直发展至今。需要指出,这主要是指英语国家的情况。在19世纪后期,一些非英语国家(指欧洲大陆国家和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一些国家)的经济学者已经开始对国家的经济行为在支出方面和决策方面作经济分析的尝试,著名的有魏克塞尔、林达尔等人。但与英语国家并无学术交流,直至30年代后才开始传入英语国家。因此当英语国家在30年代至50年代在上述领域掀起研究浪潮和成果迭出的时候,可以说是独立的、自成体系地发展起来的。
第二阶段的发展可以分两个分支,一是以凯恩斯为首的凯恩斯主义;另一分支的发展却是多角度的,代表人物有阿罗、萨缪尔森、布坎南、马斯格雷夫等。新制度经济学派对现代财政学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凯恩斯创立的经济学拓宽了经济学范畴,使宏观经济学登入了西方经济学的大雅之堂。而且凯恩斯又为国家的经济职能拓宽了领域,从而使国家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上了一个新台阶,至40年代,发达国家在实践上成为真正的“混合经济”。虽然凯恩斯本人并未对财政支出和财政决策的非市场机制本身进行新古典分析,但为后人研究拓宽思路显然起了重要的作用。
对财政支出进行经济分析就要相应的分析概念,萨缪尔森等人在40年代率先提出公共商品(Public Goods)概念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公共商品是一个理论分析概念,没有这样的概念,要对财政支出进行经济分析是不可能的。顺便说一句,公共商品的译法至今仍未被普遍接受(吴俊培,《财政研究》1994.5),公共产品、公共品、公共财货的说法却到处可见。“产品”、“财货”等并不是经济分析的规范名称,只有商品才是经济学分析的基本范畴(马克思,《资本论》),但从市场机制的“商品”概念到非市场机制的“公共商品”概念却经过了一百五六十年的努力。这一步跨越的理论意义怎样评价都不会过高。
既然国家要提供公共商品(即非市场机制提供的消费品),那么国家就要为公共商品筹措和供应相应的成本,就要考虑消费者的消费受益,因而同样存在成本—收益的经济分析,同样存在资源配置(包括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的机会成本比较问题。尽管对公共商品进行像市场机制领域的商品(即私人商品,Private Goods)那样的经济分析有许多困难,尽管萨缪尔森的分析是以纯理论假设(仍然难以运用于实践)为前提的,但毕竟开创了非市场机制达到市场机制同样效率的分析途径。这条途径在实践上最终是否能够走通那是另外性质的问题,但至少其后的经济学者在沿着这一道路探索。对非市场机制进行新古典分析几乎是一种浪潮。
公共部门的概念和公共商品概念的建立是密切相关的。既然国家提供的消费品同样是经济学意义的公共商品,那么国家就是生产公共商品的“生产者”。这一经济理论在我国同样未被普遍接受。例如在谈到财政资金安排时,要考虑“社会效益”云云。他们所说的“社会效益”是脱离经济分析轨道的。那是因为不了解对非市场机制(或政治行政机制)进行经济分析的途径。公共商品有各种类型,可以满足各种各样的消费需求。例如国防提供的安全安定劳务,教育提供的教育劳务,法律提供的社会秩序劳务等等。与此相适应,国家要组织各种职能机构去“生产”相应的的公共商品,各种职能机构就是公共部门,就是具体履行生产某种公共商品的“生产单位”。公共部门也就是我们通常称的行政事业单位。既然公共部门是生产单位,那么其经济本质和私人商品的生产单位并无二致,效率要求也并无二致。
公共商品的供给规模是由政治行政程序控制的,那么政治行政方法可以达到公共商品供给的帕累托效率状态吗?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就是以新古典方法回答这个问题的。
帕累托效率首先产生于市场机制领域,为私人商品资源配置效率提出了标准。这是对价值规律另一个角度的把握。斯密的价值规律只是指出采用自由放任就可以达到资源配置优化的途径。帕累托对资源配置优化状态提出了可作定量分析的界定。这有点类似于斯密只提出供求关系是价值规律的实现形式,而马歇尔把供求关系纳入了可作定量分析的轨道一样。当然,没有马歇尔的基础,帕累托效率也是无法分析的。帕累托效率是建立在消费者主权和生产者主权的基础之上的。只要消费者在其收入约束下通过出价竞争的方法自由选择消费品,生产者按照利润极大化原则供给相应的消费品,那么就可以达到帕累托状态。因此效率的本质在于消费品是由消费者决定的。虽然公共商品的性质决定了市场机制供给的无效性,但如果公共商品的供给也是由消费者的偏好选择决定的,那么公共商品的供给也就是有效率的。公共选择理论就是分析公共商品选择的政治行政机制。于是,决策理论被引进了财政学。
其实,在市场机制的私人商品生产领域同样存在非市场机制。例如公司内部,董事会与总经理,总经理与部门经理等之间的关系同样有类似于政治行政方式的科层关系和科层组织,新制度学派就是根据这一现实情况发展起来的。新制度学派的理论大大丰富了财政决策理论和公共部门的生产理论。
总之,从财政理论的发展进程来看,其英语名称由"Public Finan-ce"演变为"Public Sector Economics"是顺理成章的。
三、关于财政效率问题
目前财政界的用语极不一致,“公共财政”、“国家财政”、“政府财政”等等提法都有,有的甚至认为这些提法实际上都是一样的。这部分是因为对现代财政理论把握上的不同,部分是因为翻译上的问题。上面的分析主要指出了现代财政和传统财政在研究范围上运用新古典经济分析方法的主要区别,这里探讨对“非市场机制行为主体”把握的不同对财政学科名称的影响。
我们已经指出过,“财政”这一意译名称隐含了“财政活动”行为主体是“国家”的命题。因此,“国家经济行为”和“财政经济行为”是类似的或者说是相同的概念。那么何以有"Public Revenre"(公共收入),"Public Expenditure"(公共支出)"Government Revenue"(政府收入),"Government Expenditure"(政府支出)等用语呢?在“财政”意译的用法上,上述用语均可理解为“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或者都可理解为“国家收入”,“国家支出”等含义。事实上在英文用语中并没有"National Revenue"或"Country's Revenue"(国家收入)等等用法,因为要把“财政收入”的行为主体揭示出来,只能是“政府”或“公共部门”。这是对“国家”进行经济分析的必然结果。
现代财政理论把国家看作是一个“组织”或一套“制度”,这是与传统财政理论的根本区别所在。传统财政理论却把国家拟人化,即把国家看作一个独立的行为主体,这就不可能对财政决策和财政支出进行经济分析,而“政府收支”或“公共收支”直接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因而可以看作是“国家收支”的同义语。但是,若对国家进行组织分析或制度分析,情况就不一样了。
国家是由政治家、官僚、选民组成的一个系统。政治家是财政收支的决策者,从政治制度来看,政治家由政府首脑、议会成员、党派领袖等组成。官僚是指执行财政决策的政府及其相应的职能机构和工作人员(文官),因而官僚是个中性词而没有任何褒贬的意思。可见官僚是执行决策的职能机构。选民是公共劳务的享用者(接受者或消费者),同时也是政治家的选举者。因此,决策是必须为选民(消费者)服务的。由此可见,在“收入”前面加上“政府”的定语,其含义是明确的,不存在把“国家财政”变为“政府财政”的问题。虽然财政决策有相应的“公共选择”理论,但不存在“公共财政”比“国家财政”概括更准确的问题。这是因为“财政”天然就是“国家的”、“公共的”,对“国家的”、“公共的”经济行为进行结构分析并不会否定财政的“国家”(非市场)性质。
官僚执行财政决策,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现代财政理论和传统财政理论也是有很大区别的。传统财政理论假定官僚是中性的,即不折不扣地执行决策或履行财政职能。现代财政理论同样把官僚看作是一个制度结构(组织系统),其中的工作人员同样是理性人。因此,官僚能否不折不扣地贯彻决策意图取决于官僚系统的激励约束机制。据此分析,官僚不只是决策的被动者,而且对决策有重要影响。
官僚自身的利益包括他的工薪、特权、社会声望、受人尊敬等。这些利益的极大化和公共部门(职能机构)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提供公共劳务的目标是不一致的。因为要实现官僚利益的极大化,官僚机构的扩大,人员的增多,待遇的提高以及办公条件的改善等密切相关。这些因素都要求公共预算的扩大,显然与效率要求相悖。这种自身利益极大化的冲动,在制度安排中是有可能得到实现的。首先,在公共部门和决策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公共部门处在提供公共劳务的第一线,对有关信息了解比较全面,因此决策者要由他们来提供信息。决策者虽然处于信息的终端控制地位,但无法有效地过滤出效率信息。其次,在决策者和公共部门之间类似于公司的“委托—代理关系”,因此,公司的“经理模型”被运用于公共部门分析。为了提高公共部门的效率,在“委托—代理”关系中设置机动权是必要的。机动权的设置不仅属于管理科学的范畴,而且是一门艺术。没有机动权就没有效率,机动权太大就要失控,即代理者就不会全力去完成委托者的目标。事实上,即使在公共部门最基层一线的每个工作人员都有机动权,因此很难保证委托—代理目标不被偏离。最后,委托—代理制自身存在交易费用。要实现委托—代理目标,委托者要不断搜集有关的新信息,要对代理者的行为进行监督,要对代理者的岗职进行调整等等,这都有交易费用问题。显然,交易费用是管理精细化的约束值。当这些交易费用大于代理者由此提高效率的收益时,这种对代理者的强化监控就失去了经济意义。总之,公共部门效率的提高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由上述分析可知,把国家作为组织制度结构来看,那么公共商品的供给的效率有两部分组成。一是公共供给的资源配置效率,这是属于预算决策(在我国还包括预算外决策和其他政府收支决策的问题)的范畴。二是公共商品的生产效率,即公共部门的效率,这通常被称之为X—效率。财政效率就是这两种效率的统一。当我们在研究财政的资源配置效率时,是假定不存在X—无效率的;同样,当我们在研究X—效率时,是假定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现实中这两种假设都不存在,但都是力图按照有效率的方式运作。这是现代财政理论转入可操作性运用提出的难题和新的前景。这种变化,显然不能用“公共财政”来代替“国家财政”得到正确的概括。
标签:市场机制论文; 财政学论文; 公共部门论文; 公共财政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代理理论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公共财政收入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经济学论文; 官僚资本论文; 代理问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