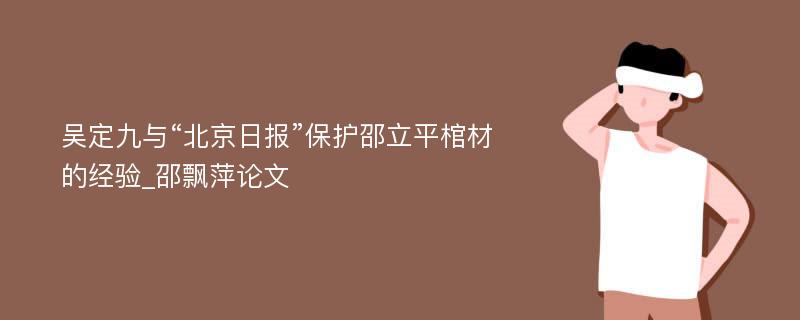
吴定九及《京报》同人对邵飘萍灵柩保护之经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京报论文,灵柩论文,人对论文,吴定九论文,邵飘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1926年4月26日邵飘萍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杀害后,先外公吴定九和《京报》同事们为其殓葬的全过程,笔者在《对一幅邵飘萍殓葬照片的重新解读与思考》(《新闻春秋》,2014年第3期)一文中已作详述。邵遇难半年后,置放于天宁寺内的灵柩又横遭奉系官兵袭扰,吴和同事们旋对其采取了一些有效保护措施,以免再遭破坏,现将此经过补叙如下。 一、潘劭昂和吴定九天宁寺之行 1929年4月24日,《京报》为纪念邵飘萍殉报三周年,专出一期《邵飘萍先生被难纪念特刊》,上面登出时任《京报》总编辑潘劭昂的一篇题为《我负飘萍先生》的文章,其中回忆到: “重履北京,已在先生殁后之半载。翌晨赴天宁寺凭吊先生之灵。……十五年十月二十九日,余偕吴君定九至天宁寺视先生之灵榇,并以祭奠。停灵所为东院三间,两明一暗,灵即在明间。时军阀牙爪,充塞北京,寺亦驻兵,即东院之暗间,亦为盘据。驻兵初未知英魂为何,尚未相扰。因余之往,由脚役处悉姓氏,乃仿其上,谋扩充地盘而肆其糟践兽性。集十余人之力,图移灵室外,不胜,适益其怒,竟出刃猛砍。幸灵经重重布裹,层层漆封,只缺损一二,寺僧闻嘈喧,驰至劝阻,不听,跪地叩首请免,且以十数人不能移动,必有神助慑之,始罢手。盖此辈穷凶,逞残肆虐已惯,久已无天理人情之观念,祗鬼神之说,始足稍戢其凶耳。幸不久此军他调,乃得乘隙移放于寺后旷地,而暂作浮厝,屋身悉用铁筋洋灰,极为坚固,所以防是类兽军之或再践焉。” 潘劭昂与吴定九是上海嘉定同乡,两人早在1918年《京报》始创期间就已相识。当时,其兄潘公弼与吴定九共辅邵飘萍创办《京报》,潘劭昂则在北京求学,常利用课余时间到邵飘萍的新闻编译社服务,后担任京报社编辑,并受到邵资助赴美留学。邵被害不久,潘在美国接到邵夫人汤修慧电报,于半年后回国,又与吴定九共辅汤办报。从时间节点上看,潘劭昂从美国返回北京的第二天即由吴定九陪同到天宁寺祭奠,可见其心情之迫切,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此次天宁寺之行却招来邵灵枢被奉军严重袭扰,他和吴定九也险招不测之祸。 从这次天灵寺祭祀结果来看,潘劭昂和吴定九此行显得准备不足和过于仓促。潘由于受到邵飘萍一手栽培,且因在美深造无缘参加邵的殓葬活动而心感不安,故在对国情不甚了解的情况下急于前去凭吊尚可理解。但作为京报馆负责经营管理和行政事务的总经理,先外公吴定九做事一向计划周密,谨小慎微,有条不紊,从不莽撞行事,前阶段邵飘萍之所以能顺利成殓,其间也曾传来军阀要碎尸万段的一些恐怖流言,但在吴精心组织和安排下并未出任何差错。此次天宁寺之行,他不可能不知道那里驻扎着奉军,那又为何硬要甘冒风险而陪潘前往呢?这个问题曾一度让笔者颇感困惑,好在与《邵飘萍先生被难三周年纪念特刊》同日出版的《京报》正刊第八版上,也刊发了一篇署名“贞白”的题为《飘萍先生之灵》的小文章,其内容与潘文相似,读来从中可觅见端倪,摘录如下: “有一位飘萍至好的朋友,从外国回来,因为飘萍殁时,他尚在外国,所以回到北京,赶快就来吊唁。询明灵枢停在天宁寺,他也不通知邵先生家属,就备一桌祭席,挑夫挑着,直奔天宁寺来。 一到天宁寺,守门的兵士,不放他们进去,他们说是来祭奠的,麻烦了好半天,由里面的和尚恳求了长官,才放进去了。事后,驻军问收检傢伙的挑夫,祭的究竟是哪一位?他们说是邵飘萍先生。那官长听见马上大怒,说道是邵某人吗,他是我们少帅枪毙的,他敢在这里停灵。来祭的一定也是乱党,要早知道,就把他扣下来了。一面连骂带踢,把祭席也抢了一空,一面却奔到后面,找着那里的灵枢,要想扛下来火化。 奇怪的很,不科学的说法,三四十个的奉军,会扛不动一口棺材,然而是实啊!到底没抬得动,事过之后,家属进去观察,棺木上面有刀斫的痕印道。……飘萍的灵魂,是伟大的,是有不可磨减的价值,是永在天地间的。他们什么少帅?什么军人?杀一个无罪的人,还想要把他棺木火化,这种理性以外举动,只是人类中弱虫,如何有扛得起灵枢的力量啊!” 贞白是1928年6月《京报》二次“复活”后的常见撰稿人,真名不详,有可能也是一位《京报》的编辑或记者,且与吴、潘二人熟知,其文对潘劭昂的回忆起到了互为印证和补充作用。“他也不通知邵先生家属”这一句,说明潘当时只通知了吴定九一人,或因他认为亲友中也只有吴最适合陪同他前去凭吊吧。按常理,比潘年长六七岁,且对国情十分了解的吴定九在接到潘劭昂的通知后也许会婉言相劝,力陈利害而择时成行。但最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当潘一旦决定了要去天宁寺祭奠恩师邵飘萍,以吴对待朋友一贯负责到底的行事风格和遇事敢于担当的秉性而言,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选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话说回来,吴、潘二人也真算是幸运的,假如二人再晚走一步以“乱党”罪名落入那支奉军之手,彼等可不是什么“弱虫”,而是如狼似虎的一帮恶魔,后果乃不堪设想。 二、邵灵柩得以保护之因 邵飘萍生前因严厉抨击军阀黑暗统治而惨遭杀身之祸,死后其灵柩又险遇军阀黑手侵扰。所幸,在这一点上吴定九和邵夫人汤修慧早有预见性,他们事先采取了一些有效的防范措施。潘劭昂和贞白的文章里都谈到了奉军官兵挥刀猛砍棺材这一细节,然“幸灵经重重布裹,层层漆封,只缺损一二”,或只留下“有刀斫的痕印道”,而棺材本身基本上没受到多大损失。这一结果可谓不幸中之万幸,但若进一步探问其所以然,则与吴定九早年的身世及经历有关。 外公吴定九少时家境殷实,其父为嘉定外岗镇上以经营棺材为主的木器店主,在当地属于大户人家。吴天资聪颖、多才多艺,他在家读私塾的同时,又跟店内的师傅学得木工绝活,有着一手制作家具和棺材的好技术。邵被害后,吴等亲友花重金为其选购入殓的本就是一口楠木好棺材,后又对其进行了“重重布裹,层层漆封”等加固和密封措施,以防不测,此其一。 驻天宁寺那支奉军调走后,亲友们赶紧在寺外找到一处空旷之地,下挖数尺,用钢筋水泥为材料制成一个“浮厝”(一种半地下陵寝),将邵灵柩抬出移放进去后砌就密封,“极为坚固,所以防是类兽军之或再践焉”,此其二。当然,与为邵备棺相似,这项永久性保护措施同样是在吴定九的专业性指导下完成的,因为毕业于日本名古屋高等工业学校(现为名古屋工业大学)土木系的吴,早在成为职业报人之前就已是一名业有所成的建筑工程师了,1918年3月修建于中山公园内的“公理战胜”牌坊(现为“保卫和平”坊)和建于1925年10月的京报馆(现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即出自其手,而为挚友修一座浮厝,对他来说并非难事。 其三,潘劭昂和贞白的文章中均提到,奉军原本打算将邵灵柩移到寺外焚毁,但因有神灵暗中佑护英魂,以至于他们动用了十几名,甚至几十名年轻力壮的士兵都抬不动棺材,终因“必有神助慑之,始罢手”,“祗鬼神之说,始足稍戢其凶耳”。对这种有神灵相助的“不科学的说法”,作为接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潘、贞二人大概也感到非常奇怪,但他俩均未给读者作出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笔者认为,英魂是否真得到神灵佑护,似不仅是一个闻者信其有和科学与否的简单问题,而视其属精神层面或宗教信仰范畴的一种认知问题似更为合适,此处暂且不论。不过,棺椁本身材质厚重,结实牢固,不易损坏,且无一定技巧则难以搬动,确是保护者主观能动因素所致结果,此为不争事实,更不容忽视。 三、保护邵灵柩的意义及影响 今回首,若无当年吴定九率《京报》同人在保护邵飘萍灵枢和建造厝居方面所起到的特殊作用,很难想像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侵蚀,葬于天宁寺外荒野之中的烈士遗骨最终能保留下来,并于1980年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应该说,如此结局无论对于保护者还是被保护者来说都是功德圆满的一个结果,这些当年以笔为武器反抗军阀暴政的文人志士可瞑目矣,毕竟,历史老人给予他们的是公平和正义的回报。 对今人而言,回眸这段往事仍具镜鉴意义,不仅在继承革命先辈光荣传统方面有其正能量作用,也有助于从细微末节处了解那段沧桑历史。国民革命时期,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是如何看待军阀统治阶层的?潘劭昂和贞白的文章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 不难看出,潘、贞二文有一共同点,即在于对奉系军阀残暴、丑恶本性的无情抨击。二文发表时,虽然北伐业已结束数月,张学良也易帜归顺国民政府,且身居党政军要职。但在二人笔下,奉系军阀这一杀害邵飘萍的主要元凶仍是十恶不赦、令人憎恨的角色。潘劭昂将奉军喻为“兽军”,斥其“盖此辈穷凶,逞残肆虐已惯,久已无天理人情之观念”。贞白则严辞质问:“什么少帅?什么军人?杀一个无罪的人,还想要把他棺木火化”,继而指出:“这种理性以外举动,只是人类中弱虫。”此种看法,不仅仅是《京报》同人,也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阶层对奉系军阀的一种普遍性的蔑视,具有一定代表性。 话再说回来,半年前荷枪实弹的军警包围京报馆时,外公吴定九窬墙而逃幸免于难,这次天宁寺冒险之行算是他第二次摆脱掉反动军阀魔爪之害,不知冥冥之中是否也有神灵暗中保佑他?言及此,笔者不禁联想起某位烈士的两句诗:“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何等英雄气慨,邵飘萍不也是这样笑对死亡的吗?本文主旨,意在驰念先烈的同时去寻觅和追忆先外公吴定九及京报馆同事们,从而使得我们后人能真真切切感受到,北伐得胜利,军阀被推翻,包括《京报》在内的进步舆论力量功不可没。而那一代报人不屈的身躯和正义的呐喊,恰恰是这股反抗专制统治,追求民主法制力量的化身与写照,那些勇于走在时代前列,铁肩辣手的报人们,是真正值得今人景仰和学习的新闻界英雄前辈,历史应该永远记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