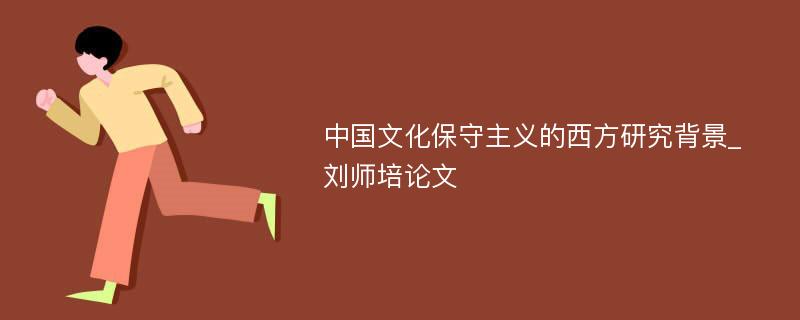
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西学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保守主义论文,西学论文,中国文化论文,背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人们的印象中,文化保守主义者即便不是穿着长袍马褂的食古不化、抱残守缺的古 董先生,也至少是以拒斥西方文化、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为己任的。因此,人们在评述保 守主义者的学术观点时更注重的自然是他们的国学背景。但是,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 都有着深厚的西学背景,甚至可以说他们所接受的西学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并不亚于同时 代的激进主义者。而且,他们的西学背景对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形成又有着相当 密切的关系。我觉得,离开了他们的西学背景来探讨其学术立场,往往会有意无意地遮 蔽或改写他们的真实主张,也就不利于全面完整地总结近代以降中国思想、文化的演进 历史。
一
中国之所以产生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西学的涌入。晚清时期,随 着西学的大举进入,中国士大夫开始痛苦地意识到,在强大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中国 传统文化已面临灭顶之灾。看看王韬当年的表白,我们就能领略到对传统文化一往情深 的士大夫们的切肤之痛:“世变至此极矣,中国三千年以来所守之典章法度,至此而几 将播荡澌灭,可不惧哉!”(注:张岱年主编:“中国启蒙思想文库”《园文录外编》, 字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0页。)张之洞亦发出了“儒术危矣”的慨叹(注:张 之洞:《劝学篇·循序第七》,载《张之洞论著选辑》,台湾巨人出版社1978年版。) 。既然领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就要灭亡的恐惧,那么力图维护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的“ 有志之士”们奋而去“保”去“守”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 西学是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催产婆。
当然,仅像那些顽固不化者那样一味地拒斥西学,是无法在激烈的中西文化碰撞中维 护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的。吸纳西学以达到文化保守之目的,正是以曾国藩、冯桂 芳、王韬、薛福成、张之洞等为代表的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体用派”与顽 固派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张之洞明确说过:“今日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 。”(注:张之洞:《劝学篇·循序第七》,载《张之洞论著选辑》,台湾巨人出版社1 978年版。)曾国藩能集理学家和洋务派代表人物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头衔于一身,就与他 在西学的激活下改造理学的努力密切相关。自冯桂芬在1861年提出著名的“以中国之伦 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注:张岱年主编:“中国启蒙思想文库”《采西 学议——冯桂芬、马建忠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4页。)的主张始,这种 “中体西用”的模式就成了一条中国文化救亡图存的重要路径。“体用派”虽然还坚持 “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但对“西用”的热衷事实上已将以理学为代表的儒学无 力应对世变的缺陷暴露无遗。作为理学家的曾国藩比他的前辈的高明之处,最主要的就 在于,他注重道德内省之外更加讲求经世之学,从而恢复儒学的“外王”功能。曾国藩 之作为理学家的学术底蕴在1990年代的“国学热”中备受学界关注,但我觉得,曾国藩 的西学背景更是成就曾国藩的关键所在。我们不能忘了,像容闳、华蘅芳、李善兰、陈 兰彬、徐寿等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西学人才,都曾集中在曾国藩的幕府中,尤其是 其中的容闳,是“第一位中国留学生”,于1854年毕业于世界一流的美国耶鲁大学(注 :刘大椿、吴向红:《新学苦旅》,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155页。)。其 幕府中著名的有“曾门四弟子”之称的两人——薛福成、黎庶昌都曾远涉重洋,访问过 欧洲,对西学有着更切身的体会。
康有为的儒学宗教化努力也同样有着深厚的西学背景。与曾国潘、张之洞等努力恢复 儒学的“外王”功能从而达到改造儒学之目的不同,作为“孔教派”首领的康有为,其 改造儒学的路径则是试图实现儒学的宗教化。康有为把立孔教为国教作为他一生不变的 。在孔子成了方兴未艾的各种新思潮攻击的目标之时,仅这一点就足以凸现出他的文化 保守本色了。而当他与作为孔教会名誉会长的张勋于1917年共同策划臭名昭著的复辟事 件之后,在崇尚西学的文化激进主义者眼里,就更是被等同于顽固的遗老。但在文化观 上,康有为又显然与顽固派不同,他对儒学的改造和对孔教的痴迷,与他以开放的心态 吸纳西学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因戊戌政变的失败,康有为在1899年至19 11年的十余年时间里一直流亡海外,这么长时间的海外经历对他的文化观不可能没有影 响。康有为将儒学宗教化的最初动因就是为了抵制西方宗教的大举进入,在西方传教士 在华活动日渐频繁的时候,他有了比张之洞“儒术危矣”更为沉痛的危机感:“若国步 稍移,则彼非金元无教者比也,必将以其教易吾教耳。犹吾孔教本起中原,散入新疆、 云南、贵州、高丽、安南也。以国力行其教,必将毁吾学宫而为拜堂,取吾制义而发挥 新约,从者诱以科第,不从者绝以戮辱,此又非秦始坑儒比也。”(注:《戊戌变法前 后·康有为遗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3页。)从中可看出康有为把西方宗 教侵略的危险过于高估了,但也可看出,康有为那立孔教为国教以抵御西方宗教入侵的 努力还是真挚而不无悲壮的。不过,康有为的宗教思想并非纯然是土生土长的,也来源 于他对西方宗教的学习。这一点可以梁启超的话为证:“先生幼受孔学,及屏居西樵, 潜心佛藏,大彻大悟。出游后,又读耶氏之书,故宗教思想特盛,常毅然以绍述先圣, 普度众生为己任。”(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六),中华书 局1989年影印本,第67页。)康有为不仅借鉴西方宗教形式,去建立孔教的教规、教会 、教律和礼拜形式,而且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还处心积虑地以西学中的资产阶级政 治学说以及民主、自由思想来赋予儒学以新的意义,比如他在《孔子改制考》中提出的 著名的“三世说”,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有“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 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代表了君主专制时代、君主立宪时代、民主共和时代。比如他以 博爱、平等来诠释原本等级森严的儒学。他说“博爱之谓仁”(注:康有为:《论语注 》,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5页。),他在诠释《孟子》“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 谓也”时,认为“此孟子特明升平授民权、开议院之制,盖今之立宪体,君民共主法也 ,今英、德、奥、意、葡、比、荷、日皆行之”(注:康有为:《孟子微》,中华书局1 987年版,第20、23页。),并指出“人人独立、人人平等、人人自主、人人不相侵犯、 人人交相亲爱,此为人类之公理”(注:康有为:《孟子微》,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 0、23页。)。从康有为的以西学改造儒学的努力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年保守者的创新意 识并不弱,就如曾以《猛回头》、《警世钟》表现了激进的革命立场的陈天华所说的那 样:“不想守旧则罢,要想守旧,断断不能不求新了”(注:张岱年主编:“中国启蒙 思想文库”《猛回头——陈天华、邹容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二
谈论20世纪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似乎总是绕不开“国粹派”和“学衡派”。在以往 的主流历史叙述中,“国粹派”和“学衡派”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 对立面而以反面教材的身份被迫“参与”历史的建构。以致至今仍有不少人还想当然地 将它们视之为死抱中国传统的守旧派。当然,我并不是说以往的主流历史叙述就是一无 是处的,国粹派和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提倡者在诸多问题上的对立确是不争的事实 ,我要指出的是,他们的对立并不是一种向西方学习的“趋新”与回归中国传统的“守 旧”的对立,其实,在我看来,在向西方学习这一点上,国粹派和学衡派与“五四”新 文化提倡者一样也是“趋新”者,无非两者所“趋”之“新”有着显著不同罢了。
20世纪初的国粹派,以章太炎、刘师培、黄侃、邓实、刘节等为代表,以“研究国学 ,保存国粹”为宗旨,以《国粹学报》为阵地,掀起了一股轰轰烈烈的文化保守思潮。 国粹派之所以倡导国学,当然是为了与勃兴的西学相抗衡,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忽略 了国粹派的西学背景。朱维铮先生曾指出,“《国粹学报》的名实并不相符。岂止‘国 粹’一辞是从日本输入的,就是它存在七年间贯穿八十二期的一个基调,所谓中国文化 西来说,也属于舶来品,从19世纪晚期法国汉学家拉库伯里那里贩来的。”(注:朱维 铮主编:《刘师培辛亥前文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319、106、123—131、134 页。)国粹派的复兴古学,当然不是缘于思古之幽情而复古,他们提倡的“古学”,即 “国学”,除与西学抗衡之外,也是要与“君学”对举。复兴尚未形成君主专制的先秦 时代汉民族的学术的目的,显然是要否定秦汉以降服务于专制政治的成为“君学”的儒 学。从策略上看,这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通过批判中世纪和复兴古代以创造近代精神 的思路确实极为相似。对国粹派深有研究的郑师渠先生就曾指出:“国粹派的所谓古学 复兴,归根结蒂,其在实践上最终是表现为推动传统学术向近代化的转换。”(注:郑 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7页。) 而从相关文献上看,国粹派“古学复兴”的文化策略又确实是对西方文艺复兴传统的借 鉴。刘师培在刊于《国粹学报》创刊号上的文章中就表达了他们要在中国步当年但丁之 后尘的意图:“昔欧洲16世纪,教育家达泰氏(即今译之但丁——引者注),以本国语言 用于文学,而国民教育以兴。”(注:朱维铮主编:《刘师培辛亥前文选》,三联书店1 998年版,第5、319、106、123—131、134页。)作为《国粹学报》总纂的邓实在考察了 欧洲各国的文化复兴之路和日本的“王政复古”之后,更是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安 见欧洲古学复兴于15世纪,而亚洲古学不复兴于20世纪也?”(注:邓实:《古学复兴论 》,《国粹学报》第9期,1905年。)作为国粹派的台柱子(注:虽然国粹派的盟主是章 太炎,《国粹学报》的总纂是邓实,但就理论贡献来看,当推刘师培,据朱维铮先生统 计,总共出了82期的《国粹学报》,其中有80期登载了刘师培的文章,而且好多期上还 不止登载一篇。参见朱维铮主编:《刘师培辛亥前文选·导言》,第5页。),刘师培徘 徊于“国粹”与“无政府”之间的学术经历,对于我们了解国粹派的西学背景不失为一 个典型个案。作为国学大师的刘师培,不仅有“中国无政府主义第一人”之称,还有着 “东亚卢梭”的美誉。通过严复等人翻译的西洋各种译著了解西学,尤其是利用社会进 化论、民约论等西方思想来进行排满宣传,是国粹派的一个论战策略,刘师培对卢梭天 赋人权理论的介绍更是不遗余力。他在《中国民约精义》的长文中详细介绍了卢梭的天 赋人权学说,并从卢梭的“民约”出发,主张回复“天赋”的自由平等之权利,并从中 得出废除君主专制制度的结论(注:《刘师培全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 7年版,第560—597页。)。在《人类均力说》中,称“近世西儒卢梭,又创天赋人权之 论,是人类平等之旨久为先哲所昌言”(注:朱维铮主编:《刘师培辛亥前文选》,三 联书店1998年版,第5、319、106、123—131、134页。)。在《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 一文中,刘师培还从中国历史为无政府主义思想寻找依据,以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平均 ”观念来印证无政府主义的“平等”思想(注:朱维铮主编:《刘师培辛亥前文选》, 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319、106、123—131、134页。)。刘师培的西学背景当然不 限于无政府主义,他还就中国家族与西洋伦理进行比较,认为“西洋家族伦理始于夫妇 一伦,中国家族伦理莫重于父子一伦”,并指出中国三纲为主的伦理关系“最不平等” (注:《刘师培全集》(第二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页。)作为《共 产党宣言》第一部中文全译本的组织者,刘师培在为其所作的序言中还发现了马克思、 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对国学研究的指导意义:“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 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注:朱维铮主编: 《刘师培辛亥前文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319、106、123—131、134页。)
如果说国粹派至少因为其反清立场还能在政治上享受“革命派”的礼遇,学衡派则远 没有这么幸运。学衡派更多的时候都被视为“五四”的对立面。学衡派的主要成员吴宓 、梅光迪、胡先骕等都曾留美深造,仅就所接受的西方文化教育来看,他们是完全可以与“五四”新文化提倡者相比的。实事求是地看,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的抵制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复古。“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作为《学衡》杂志的办刊宗旨是众所周知的,但人们在评价学衡派时已习惯于只见“昌明国粹”,视而不见“融化新知”。暂且不论他们的目的和实绩如何,他们在“融化新知”方面作过切实的努力是不应忽视 的。胡先骕认为倡导新文化和重估我国旧学“必以欧西文化之眼光”,“对中外历史、文化、社会、风俗、政治、宗教,有适当之研究”(注:胡先骕:《论批评家之责任》,《学衡》(南京)第2期,1922年。)。吴宓曾说,“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吾国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皆当研究之,保存之、昌明之、发挥而光大之。而西洋古今之学术德教,文艺典章,皆当研究之、吸取之、了解而受用之”(注:吴宓:《评新文化运动》,《学衡》(南京)第4期,1922年。)。由此可见,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一样深知建设新文化的必要性,也深知新文化的建设必须参照西方文化,必须汲取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只不过他们在如何建设新文化,尤其是在汲取西方文化中哪些成果方面有着重大的分歧罢了。
而且,学衡派对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迷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来自于西学的激活。学衡派主要成员在美国留学期间,受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影响极深。我们甚至可以说白璧德是学衡派的精神领袖。《学衡》创刊不久,就译介了白璧德的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重头文章(注:胡先骕译:《白璧德中西文化教育说》,《学衡》(南京)第3,1922年。)。从作为总编辑的吴宓在编发这篇译文时所写的按语中我们即可读出学 衡派对白璧德的推崇备至:“白璧德先生为哈佛大学教授,而今日美国文学批评家之山斗,与穆尔先生齐名。其学精深博大,成一家之言,西洋古今各国文学而外,兼通政术哲。又娴梵文及巴利文,于佛学深造有得,虽未通汉文,然于吾国古籍之译成西文者靡不。特留心吾国事,凡各国人所著书,涉及吾国者,亦莫不寓目。”(注:胡先骕译:《白璧德中西文化教育说》,《学衡》(南京)第3期,1922年。)吴宓显然已把这个“虽未通汉文”但“特留心吾国事”的“美国文学批评家之山斗”视为中国问题的顶级专家来崇敬了。白璧德作为著名的反现代性的思想家,主张以恢复古希腊文化、儒家文化、佛教文化等古典文化的精神和传统秩序,来匡现代性的弊端。他把西方古典文化的代表人物亚里斯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和东方的释迦牟尼、孔子均尊为世界领袖人物,以图复兴古典文化并从中找到人性复归的精神价值。他推崇渐进式的改良而反对激进的革命,主张一个社会应该有秩序有纪律有规矩,奉行中庸平和的人生哲学,反对自我的膨胀和个性的张扬,倡导典雅的保守的文学观和人生观。这样的思想主张显然与“五四”的时代风尚背道而驰。白璧德在评价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时,直截了当地对这种革命式运动的“崇信机械之功用”和“注重感情(欲望)之扩张”的倾向进行了批判(注:胡先骕译:《白璧德中西文化教育说》,《学衡》(南京)第3期,1922年。) 。学衡派的主将们正是全盘接受了这种不合时宜的思想主张,才成为“五四”新文化运 动的对立派的。从对白璧德这个西方著名思想家的全盘接受来看,有着“复古派”、“ 保守派”之称的学衡派,虽口口声声要“昌明国粹”,倒也称得上是不折不扣的“全盘西化派”。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大爆发”,现代性追求中诸如科学至上、忽视人的精神价值、个人欲望的急剧膨胀等弊端开始显露的时候,处在西方社会的白璧德对现代性的批判应该说是有其针对性的,而对于刚刚在内忧外患中艰难地踏上现代化征程的20世纪初的中国来说,这种对于现代性的批判显然因过于超前而显得“不合时宜”。
这里再简单提一下很难归入哪个具体的派别,但在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有着深远 影响的辜鸿铭和陈寅恪。这两个在西方高校接受过系统教育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中国 传统的坚决守护并非与他们所接受的西学毫无关系,作为辜鸿铭在爱丁堡大学的导师, 英国思想家卡莱尔的激烈抨击资本主义的思想言论对于辜鸿铭的影响不容低估;陈寅恪 师承西方史学的兰克学派在史学界已不是什么秘密,而史学家兰克正是有“保守主义先 知”之称的柏克最有影响的德国两大门徒之一。
三
20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学术成果最为丰硕的 学派,当推“现代新儒学”。现代新儒学从1920年代至今,从以梁漱溟、熊十力、张君 劢为代表的第一代,以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为代表的第二代,到以牟宗三、唐 君毅、徐复观为代表的第三代,以及以杜维明、刘述先、余英时、成中英等为代表的仍 然活跃在当今学术界的新一代,其思想相当庞杂,但是他们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 为己任的文化保守立场还是基本一致的。与这种文化保守立场相映成趣的是,现代新儒 学对西学的吸纳相当明显。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现代新儒学之所以为“新”,乃 在于它用新的现代西方哲学,去系统地改造古老的中国儒学。
现代新儒学中的第一代学者中,张君劢曾先后留学日本和德国,系统地接受过西学教 育。职是之故,学界在谈到这一代新儒学学者的中西融化之功时,似乎更称道张君劢以 康德哲学和冯特的构造心理学来改造宋明理学、构建心性理论的努力。其实,没有系统 地接受西学教育的梁漱溟、熊十力对西学的借鉴亦不容忽视。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生命 哲学对梁漱溟宇宙观和认识论的影响不容忽视。梁漱溟曾明确说过:“我曾有一个时期 致力过佛学,然后转到儒家。……后来再与西洋思想印证,觉得最能发挥尽致,使我深 感兴趣的是生命派哲学,其代表人物是柏格森。”(注:梁漱溟:《朝话·中西学术之 不同》,《梁漱溟全集》(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6页。)为了向人们 展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所包含的真谛,梁漱溟以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来阐 发中国文化的价值,为现代新儒学开创了宇宙生命本体论。梁漱溟认为,生命是宇宙的 本体,宇宙是永恒绵延的生命的“相续”;要认识宇宙,只能凭直觉,而唯科学主义的 理智思维对宇宙生命毫不相关。因此,他把柏格森直觉主义的感觉、理智、直觉套到佛 学的唯识宗的内核上,创造出“三量说”(“现量”、“比量”、“非量”)的认识论, 并认为“三量”的认识过程正好达到了“体识宇宙生命”的境界(注:梁漱溟:《东西 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另外,梁 漱溟还吸收西方现代心理学的成果,用“理性为体,理智为用”改造传统儒学的心性论 ,建立了现代新儒学的心性本体论(注:韩强:《现代新儒学心性理论评述》,辽宁大 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35页。)。熊十力构建的“新唯识学”博大精深,除他的道 友、门生之外,能领会其艰涩奥义的人并不多,但他对柏格森、康德哲学的批判性吸纳 倒是明摆着的。为了回应西学的冲击,熊十力对待西学的态度其实又是相当平静客观的 。他曾说:“今日文化上最大问题,即在中西之辨。能睹异以会其通,庶几内外交养, 而人道亨,治道具矣。吾人于西学,当虚怀容纳,以详其得失。”(注:熊十力:《十 力语要》,明文书局1989年版,第73页。)
现代新儒学的第二代学者中,牟宗三没有在西方的高等院校里接受过系统西学教育, 但他对西学的用力之勤,在现代新儒学的学者群中堪称典范。有学者认为“牟宗三对康 德的理解和研究,就是在整个中国哲学界也是第一流的”(注:单世联:《反抗现代性 ——从德国到中国》,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71页。),他的“道德形而上学” 体系中最重要的四部书中,《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和《现象与物自身》是对治康德的 《纯粹理性批判》而作,《圆善论》是对治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而作,《真善美的 分别说与统一说》是对治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而作。仅此即可见出牟宗三与西学的不 解之缘。
在现代新儒学的第二代及其后的学者中,冯友兰以中西比较哲学论文《人生理想之比 较研究》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贺麟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后,又去德国专 攻德国哲学;方东美以《英美唯实主义的比较研究》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刘述先获得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的宗教哲学博士;余英时获得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博士 学位;成中英、杜维明获得哈佛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一些尊崇儒学的人,往往津津 乐道于这些对西学有着精深研究的学者如何最终摈弃西学改宗儒学,而且还把他们这种 “弃暗投明”的选择作为儒学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例证。其实,对于这些长期浸淫于西学 之中,其中不少人还发表过大量西文论著的学者,西学自然要成为其展开儒学研究不可 或缺的重要学术资源。冯友兰吸取他的导师孟太格新实在论思想,改造宋明理学,建立 了“新理学”的庞大思想体系(注:冯友兰:《新理学》,见《三松堂全集》(第四卷)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贺麟从新黑格尔主义和陆王心学相结合的立场构建他 的“新心学”(注: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方东美以柏格森 、怀特海的生命哲学和《周易》的“生生”哲学为形而上本体的思想资源,构建“生命 精神学”(注:方东美:《生生之德》,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版。);刘述先吸 纳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和西方当代的基督教神学的精髓,采取现象学和解释学的方法 重构中国哲学系统(注:刘述先:《中国哲学与现代化》,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0年版 。);余英时以西方现代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哲学的方法构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自我 超越的价值系统”(注: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见《余英时 新儒学论著辑要·内在超越之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成中英发挥他 的导师——美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奎因的“机体网络”思想,以本体诠释学的方法在中西 哲学比较中构建他的儒学心性思想(注:成中英:《从本体诠释学看中西文化异同》,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这些现代新儒学中深有 影响的成果,都是无法与西学剥离的。尤其是现在还活跃在学术界的新一代新儒学学者 ,从其基本文化价值取向看,虽然仍然以弘扬儒学为己任,但其论著中已不见古色古香 的儒家特色,而是充斥着西方现代乃至后现代哲学的概念、范畴,要读懂这些当代新儒 学论著,对西学素养的要求甚至远远要高于国学素养。
从国际学术背景上看,现代新儒学的产生和发展,可以说是对西方社会现代性批判的 遥相回应。一战结束前夕,施宾格勒那本题为《西方的没落》的冗长晦涩的书却在西方 极为风行,这或许即可视为西方文化危机的表征。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重创之后,西 方的文化危机更是日益加剧。于是,一些西方学者将更加注重生命情调和价值指归的东 方文化视为西方文化走出困境的“救护神”而倍加赞赏。西方学术界在现代性反思中显示出来的这种贬抑西方文化、褒扬东方文化的倾向,作为一种逻辑支撑还是能给信奉儒学千古不衰之生命力的现代新儒家们以百倍的自信,将它拿过来作为儒学之强劲生命力的见证,也就顺乎自然的了。
四
1990年代,国内的学术界又掀起一股文化保守思潮,学界称之为“新保守主义”。学 术界对新保守主义的界定虽不一致,但都认为对文化激进主义的反省批判和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弘扬是其最主要特点(注:关于“中国新保守主义”的讨论详情,请参见以下论 文:李坚、周忠玺:《当代中国新文化保守主义述评》,《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 科学版)1997年第2期;李翔海:《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内涵、意义与困限》,《天 津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周晓明:《一种值得注意的思想文化倾向:新保守主义》 、昌切:《新保守主义泛起的背景》、王又平:《新保守主义:当下的文化反讽》,《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5期。)。在此我无意去界定新保守主义,只是把 以回归民族文化传统为基本价值归属视为其最主要的特征,从而将新保守主义作为一种 社会思潮进行整体把握。
1990年代以来,从主流意识形态到学术界到文化界到民间,真可以说中国的上上下下 都响彻着弘扬传统文化的呼声。体育界的气功报告、卫生界的养生保健、科学界的卫星 预测、文艺界的古装老戏、教育界的国粹讲座、各界人士参与的大规模祭孔活动以及民 间社会的气功热、方术热等等可视为鱼龙混杂的回归传统热潮之表征。学术界掀起的“ 国学热”更是把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推向高潮。在“盛世修典”的口号激励下,《 中华大典》、《孔子文化大全》、《四库全书存目》、《续修四库全书》等浩大工程纷 纷上马,“国学丛书”、“国学大师丛书”争相出笼,影印古籍成为出版社的时尚,趋 之若鹜地资助出版乡贤文集成了地方政府文化振兴计划的重头戏,作为人文社科研究重 镇的北京大学还创办了《国学研究》刊物,并举办声势浩大的“国学月”活动,有“国 宝”之美誉的季羡林老先生满怀豪情地宣称“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文化就将 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时期”(注:季羡林 :《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文汇报》(上海)1992年3月10日。),曾经被视为19 80年代文化激进主义重要代表的刘再复开始温情脉脉地与宣称自己是“新儒家”的李泽 厚一起提出“告别革命论”(注: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 公司1995年版。)……所有这一切,确实与此前的80年代西学热潮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但是,我们不能仅仅被上述表面现象所迷惑。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 我们应该看到,1990年代以来,学界对西方批判理论同样极为热衷,英国文化批判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海德格尔、杰姆逊、汤因比、亨廷顿、萨义德等等的论著与“国学丛 书”、“国学大师丛书”一起成为中国出版界的热点;学界追踪西学新动态的热情丝毫 不逊色于1980年代,对后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后殖民主义等思潮的译介在 1990年代的中国委实可以“不余遗力”来形容(注:关于后殖民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 系,国内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后殖民主义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组成部分, 如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三联书店1997年版;另一 种意见认为后殖民主义是继后现代主义之后出现的一种新思潮,如徐贲:《走向后现代 与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王宁:《后现代主义之后》,中国文学出 版社1998年版。本文认同后一种意见。)。虽然新文化保守主义往往以文化激进主义对 立面的形式出现,并常常指责对方受西方话语所牵制,然而,究其实,新保守主义又何 尝不深陷于西方话语之中呢?
新保守主义的西学背景其实相当耐人寻味。如果从学术资源上看,我们未必就不能说 ,中国新保守主义遵循的依然是西化的逻辑。只不过,西学对中国新保守主义的影响, 最主要的并不是体现在哪些具体观点的横移,而是体现在理论氛围的整体营造上,而氤 氲弥漫着的理论氛围对特定社会文化思潮的形成来说,往往比一些具体的观点更有影响 力和涵盖力。我从以下三个方面说明中国新保守主义的西学背景。
首先,与世界强国相比现代化水平还相当低的中国,1990年代在铺天盖地地引进西方 后现代理论中所掀起的现代性批判热潮,为新保守主义的出场做足了理论准备。中国学 界对复杂的后现代理论的接受有一种明显的偏向,即对“破坏性的后现代”的兴趣要远 远高于“建设性的后现代”,而且巧妙地运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战术,把破坏 性后现代中的解构策略视为颠覆西方中心论的利器,且非常善于寻找后现代与中国传统 文化的契合点(诸如从后现代主义在批判启蒙理性、弃置镜式哲学的同时所表现出的反 对主客二分的理论意向中寻找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境界的契合之处等等),“东方 复兴论”、“中国文化优胜论”也就水到渠成、呼之欲出了。
其次,西方保守主义在冷战后的勃兴,又为那些正咀嚼着因1980年代的激进立场的受 挫所带来的迷惘和无奈的学人适时地提供了新的理论样板。既然看到冷战结束后的西方 社会,倡导渐进式改良的保守主义比主张跃进式革命的激进主义更为新潮,那么,风云 激荡的“五四运动”遭到质疑,曾经让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心潮澎湃的法国大革命受到 批判,从西方保守主义理论元老柏克、西塞尔到西方新保守主义理论巨匠哈耶克、丹尼 尔·贝尔骤然之间成为我们时代的话语英雄……所有这一切,对于善于以西学为理论源 泉,紧追世界最新学术动态,领导国内学术新潮流的学人来说,当然顺乎自然的了。
再次,对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误读(有意或无意)中祭出“民族性”这面大旗。作为 西方激进理论的后殖民主义到了中国,则成了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利器,此中的阴差阳 错,很大程度上只能归之为中国学者的误读。作为一种西方理论,后殖民主义是以德里 达的解构主义和福柯的知识话语理论为基础,旨在揭示隐含于西方知识系统中的权力结 构,虽然其代表人物萨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都是具有东方血统的学者,但它毕 竟定位于西方知识体系的内部(注:参阅刘康、金衡山:《后殖民主义批评:从西方到 中国》,《文学评论》1998年第1期。)。但我们的学者却硬是将《东方主义》读成“金 刚怒目式的著作”,将萨义德读成“替第三世界各民族打不平的文化斗士”(注:张宽 :《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读书》1993年第9期。),并认为后殖民主义“给 长期以来从事反对殖民主义霸权、为实现本国和本民族的非殖民化目标而奋斗的第三世 界人民以有力的精神支持”(注:王宁:《20世纪西方文学比较研究》,人民文学出版 社2000年版,第220页。),而且坚信由本土立场出发去思考自身文化价值的“第三世界 文化”能“在第一世界理论的盲点和不见之处打开新的领域”(注:张颐武:《在边缘 处追索——第三世界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学》,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于是有了对张艺谋电影的批判和“文论失语症”的论争以及“中华性”的构建,甚至还 出现了“警惕殖民主义的苗头”、“文化殖民主义现象不可等闲视之”等相当尖锐的声 音(注:上世纪90年代关于“殖民文化”的论争详情,可参见寒梅撰写的综述:《怎样 认识“殖民文化”》,《文艺理论与批评》1996年第3期。)……所有这一切,显然都在 把后殖民主义导向对抗性和民族性。萨义德在其《东方学》的再版“后记”中对那些任 意曲解的“漫画式的变形”阅读表示了极大的遗憾,并明确指出《东方学》的目的“不 是对一种处于无可救药的对抗状态的自我的确认”,否认自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强调 要超越非此即彼的僵硬二元对立的东西方文化冲突模式,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思 维来取代那种东西方对垒的传统观念(注:参阅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三联书 店1999年版,第424—438页。)。对后殖民主义的误读,使当代中国的新保守主义对民 族性、本土性、中华性的高扬获得了西方新潮理论的强力支撑。
标签:刘师培论文; 儒家论文; 康有为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保守主义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国学论文; 梁漱溟论文; 学衡论文; 国粹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