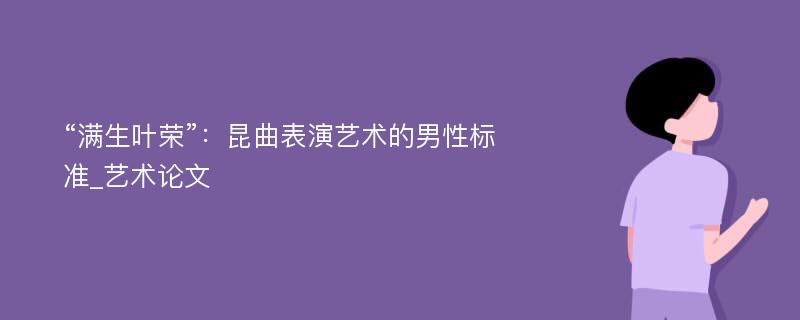
“曼声冶容”:昆曲表演艺术的男性化规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男性化论文,昆曲论文,表演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毋庸置疑,昆曲是美的,然而昆曲之美在于何处却又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有人喜欢读昆曲剧本中华丽典雅的文字,从中领会中国古典文学的诗情画意;有的人喜欢柔曼缠绵的声腔,从中感受的一唱三叹的音乐韵味。事实上,昆曲的剧本、声腔、表演处处都展示着中国古典文化优雅的审美品格。昆曲底本中唱词的华美典雅是无数文人击节赞赏回味过的,《牡丹亭·惊梦》中那典雅优美的文字,“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单单咀嚼这些文字就足以令人口齿生香,但是对于许多无法真正领会昆曲唱词意蕴的欣赏者来说,昆曲的美丽更直接表现在它表演上所具的声色之美上。戏曲是作用于耳目的艺术,演艺者的表演,耳得之而成声,目遇之而成色,许多优美的演出所留给我们绵久的印象,一在于美妙动人的美声,一在于美艳炫目的美色,“百戏之祖”的昆曲更是这种声色之美的集大成。从音乐风格看,昆曲的节奏缓慢低回如潺潺的江水,在抑扬起伏中隐藏着缠绵和绮靡;从表演的角度,昆曲又充分利用并挖掘了江南女性的柔媚多情在伎艺表演方面的巨大潜能,遵循典雅和柔媚的基调,并将其发展到极致,从而使昆曲表演艳丽纤细、美不胜收。昆曲艺术具有如此明确的柔媚特色,其缠绵娇媚恰似一个绝色佳人。
王永健先生在《吴文化与昆曲艺术》一文中,准确地把昆曲表演艺术的特点归纳为“慢、小、细、软、推”五个字,“慢”是指昆曲和昆戏的节奏缓慢,轻柔而婉折。“小”是指昆曲最适合在家宅的厅堂或者花园的亭榭上演唱,是典型的“红氍毹艺术”。所谓的“细”是指昆戏的表演十分细腻,所谓的“软”是指昆腔说的是吴侬软语,唱的是柔婉的“水磨调”,再加上擅演缠绵悱恻的文戏,自然给人以一种软而香的感觉。所谓的“雅”,是指昆曲和昆戏所具有的高雅、文雅、典雅和清雅的风韵。①昆曲从声腔特征、表演风格、演出场地、审美取向几个方面所具有的“慢、小、细、软、雅”这种风格正是女性之美最突出的特点,因此,昆曲表演展示出了浓郁的女性色彩。
昆曲这种具有强烈女性色彩的艺术,最典型的特色是声腔柔媚。昆曲从诞生之初文人就赋予了昆曲演唱声腔求媚求雅的倾向,使其具有其他声腔所无法比拟的柔婉妩媚。昆曲大家魏良辅对昆山腔进行改革时愤南曲之讹陋,对之进行了“尽洗乖声,别开堂奥”的革新,要求“调用水磨,拍捱冷板,声则平上去入之婉协,字则头腹尾音之毕匀”,以达到“功深镕琢,气无烟火,启口轻圆,收音纯细”②的演出效果。昆曲演唱要极其注重咬字行腔的抑扬顿挫与曲折婉转,声分平上去入,字分头腹尾音,以至于达到“气无烟火,启口轻圆,收音纯细”的细腻典雅,典雅成为昆曲演唱中要严格遵循的规范,这种演唱方式被称为“水磨腔”。水磨是糯米粉的一种加工工艺,经过加水磨出来的米粉最细腻滑润,入口香糯甜软,这和昆山新腔对声、字进行精雕细琢的特点十分相似,昆山新腔入耳软得似乎要化,入口则满口余香,所以用“水磨”来称呼其因经过各种处理而变得细腻柔婉的曲调正生动地体现了昆曲在声腔上这种柔媚绵软的特点。在无比婉转细腻的声腔中渗透出的似水柔情,非常细致地转达出中国古代文人许多难以言传的微妙的内心情感,打动了文人内心世界最柔、最嫩之处,是昆曲成为了梦一样诗一样的艺术晶类。女声之柔媚清丽与昆曲声腔的艺术特点颇为一致,而婉转绮靡又恰是吴语的鲜明特色,所谓的“吴侬软语”正是对吴语特点的准确概括所指即此。因此,昆曲的表演充分利用并挖掘了善于歌舞技艺的江南女性尤其是苏州地区女子的巨大潜能,使昆曲表演成为“吴姬”的擅场,以至于“四方歌曲,必宗吴门”。其次,昆曲的乐器伴奏也展示了女性温润缠绵之美。昆曲伴奏以曲笛为主,辅以笙、萧、唢呐、三弦、琵琶等,曲笛音色柔美缠绵,哀怨婉转,和曲唱的轻柔细腻融为一体,有一种幽深艳异、缠绵深情之感。昆曲声腔和旋律的细腻深情与歌妓们柔婉甜美的声音结合在一起,使得昆曲越发地具有了古典美人的特质。
昆曲之所以具有明显的女性化特征完全是文人士大夫的审美取向使然。昆曲最初产生并长时期繁盛于文人士子的厅堂或园林,是典型的“红氍毹”艺术,而中国古代的封建文化又属于典型的男权文化,昆曲就是在男权文化的氛围中被赋予了可鉴可赏的女性色彩。在中国传统的男权观念中,“女人”是一个生来就被塑造的“第二性”③,女性被社会赋予了谦柔、卑下的品性,成为男人王国的“臣子”,满足着男人的统治欲、权利欲以及性欲。在男权社会中,男性心目中女性的价值就是贤淑的德行和艳丽的容貌,前者给男人安全感,后者让男人赏心悦目。男性对良家妇女的德行进行强调和标榜导致了普通女子对才艺的疏离,而以取悦男性为职业的妓女则着力发展了才艺,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妓女几乎成了才女的代名词,虽然男性在欣赏着享受着这种才和色的同时又在诋毁着她们。昆曲的演出除了极少数文人的自娱自乐外更多地交由了能歌善舞的歌妓们。昆曲表演所面对的是观众是由文人士大夫和官吏组成的比较稳定的男性观众群体,男性对女性妩媚多情的声音、艳丽光彩的容貌需要导致了昆曲的欣赏者、评论者不约而同极大地发挥、挖掘了作为女性在声容艺术上的巨大潜力,昆曲声腔和旋律所固有的深情缅邈与歌妓们细腻柔婉的声音、如花的美貌相得益彰,使昆曲表演成为一种专为满足男性需要而具有强烈女性色彩的声色艺术,因此明清时期,出现了歌妓争演昆剧的时尚。
昆剧曲调柔媚缠绵之美契合了歌妓取悦于人的内心欲求,以悦人之姿唱“荡人④”之曲,使得“妓尤妙于此”⑤。当时苏州的很多歌妓都擅演昆剧,并以串戏为雅趣乐事。如陈圆圆能唱弋阳腔,更擅昆山腔。“演《西厢记》扮贴旦红娘角色,体态倾靡,说白便巧,曲尽萧寺当年情绪。常在余家演剧”⑥。邹枢还曾描写陈圆圆的演技:“浓点啼眉,低梳倭髻,声骤平康。苔翠氍毹,花红锦毯,趁拍舞霓裳。双文遗谱,风流谁解?卿能巧递温凉。香犀挽,生绡淡束,几疑不是当场”。风流才子冒辟疆在《影梅庵忆语》中也记载了观看陈圆圆演出的情景。他感慨道,“是日演弋阳红梅、以燕俗之剧,咿呀啁折之调,乃出陈姬身口,如云出岫,如珠在盘,令人欲死欲仙。⑦”李香君更是师从吴人周如松学习昆腔,成为旦行的翘楚,尤其擅长演《琵琶记》。歌妓们以如花美貌传唱精美绝伦的昆曲,使得美人与美声相互生发,美人唱美声成为江南地区一道美丽的风景,成为风流才子心中不可多得的风流雅事,不自觉地满足了文人对“小红低唱我吹箫”这一理想境界的追寻,因而江南地区形成了歌妓擅演昆剧的风潮。在传承昆曲的过程中,歌妓们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昆曲和歌妓的结缘实在是昆曲女性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男权文化的必然产物。文人追求声色之美的心理强化了昆曲表演对声色之美的挖掘,导致了昆曲作为文人艺术的逐渐女性化,而昆曲在男权文化的土壤上,最终根据男性的审美需要逐渐发展为一种宜阴宜柔的高雅艺术,这其实恰巧正是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词曲的艺术特质,因此昆曲从声腔到表演所渗透出来的意味和神韵都是宋词的余音,《顾误录》作者用“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宛转之度”⑧来形容昆曲,正恰切地展示了男性对女人风情万种的香艳描绘。
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冶游猎艳之风由来已久。从历代野史艳史以及诗词曲赋中所透露的信息我们明显地看到文人狎妓之普遍,且不说谢安携妓东山,也不必谈杜牧、柳永留恋青楼、苏轼为朝云不弃而泣涕,仅以明清时期而言,举国上下妓风炽然。清严思慎,《艳囮》云:“明万历之末,上倦于勤,不坐朝,不阅章奏。辇下诸公亦泄泄沓沓。然间有陶情花柳者,一时教坊妇女,京尚容色,投时好以博赀财”⑨。钱牧斋《金陵社夕诗序》云“秦淮一曲,烟水竞其风华;桃叶诸姬,梅花漾其妍翠”⑩,秦淮河内胭脂粉黛清歌妙舞,苏杭欢场翡翠鸳鸯爱煞文人豪客。然而文人狎妓不只在求皮肉之欲,更注重耳目声色之愉悦,因此有品藻花案之举。文人以才情色艺为妓女分列品目,这种妙选姿容的举动在无形中强化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妓之技艺,促使妓之技艺更精湛化。当时名列花榜之首的名妓均为色艺俱佳者,这和文人士大夫的审美品味是分不开的。明清时期,昆曲盛行于坊间,娼妓均以昆腔为娱客之上品。《吴门画舫续录》说:“未开宴时,先唱昆曲一二句,合以丝竹鼓板,五音和协。豪迈者令人吐气扬眉,凄婉者亦足消魂荡魄。……客有善歌者或亦善继其声,不失未雅会。(11)”《续板桥杂记》说:“河庭设宴,向只小童歌唱,佐以弦索笙箫。年来教习,凡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声容至美者,派以生旦。各擅所长,妆束登场,神移四座。缠头之费,十倍梨园。至名姬仙娃,亦各娴法曲。非知音密席,不得轻啭歌喉。若《寄生草》《剪靛花》淫靡之音,乃依门卖笑者歌之,名姬不屑也。”(12)名姬以昆曲高自标置,文人士子锦心绣肠以昆曲演出水平目妓,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昆曲的女性化特征就越发地鲜明起来,其情调也呈现了一种如歌妓的悦人之姿。
明中后期,一般文人学士鄙视胡元文学,而大倡复古运动。明代著名文人徐渭《南词叙录》提及当时北方音乐影响及于全国,颇有不以为然之意,他认为“今之北曲,盖辽、金北鄙杀伐之音,壮伟狠戾,武夫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之日用。宋词既不可被弦管,南人亦遂向此,上下风靡,浅俗可嗤”、“有人醅信北曲,至以妓女南歌为犯禁,愚哉是子!北曲岂诚唐宋名家之遗?不过出于边鄙裔夷之伪造耳。夷狄之音可唱,中国村坊之音独不可唱?原其意,欲强与知音之列,而不探其本,欲大言以欺人也”(13)。在徐渭看来,北方的音乐与艺术固然有其特点,但那毕竟带有太重的杀伐之气,因此,只有这样一种风格,而没有注意到江南地区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艺术传统、甚至对南方的音乐与艺术心存歧视,那就不仅不公平,而且,这种重“夷狄之音”远远超过对“中国村坊之音”之尊重的风气,决不是文人雅士应取的美学态度。徐渭的态度代表了明代文人的审美趣味,文人们求雅的审美取向使得他们对昆曲审美品格的追求就如同他们对名妓的追求一样带上了优雅、典雅、清雅的格调。这从袁枚当年到广州对粤地妓女颇为鄙薄一事即可看出,《随园诗话》云:“久闻广东珠娘俏丽。余至广州,诸戚友招饮花船,所见绝无佳者。故有‘青唇吹火拖鞋出,难近都如鬼手馨’之句,相传潮州绿篷船人物殊胜,犹未信也……”(14)。陈大声《嘲北地娼妓曲》以北地胭脂和南国金粉相对比时所作的调侃和揶揄也完全是江南文人求雅心理的表露,他说:“门前一阵骡车过,灰扬。哪里有踏花归去马蹄香?棉裤棉裙子,膀胀。哪里有春风初试罗裳?生葱生蒜生韭菜,腌脏。哪里有夜深私语口脂香?开口便唱冤家的,不正腔。哪里有春风一曲杜韦娘?举杯定吃烧刀子,难当。哪里有兰陵美酒郁金香?头上松髻高尺二,蛮娘。哪里有高髻云鬓宫样妆?行云行雨在何方,土炕。哪里有鸳鸯夜宿销金帐?五钱一两等头昂,便忘。哪里有嫁得刘郎胜阮郎。(15)”江南的文人欣赏江南女子娇小玲珑之美,含蓄细腻之韵,尤其赞赏婉约柔媚之态。江南文人以对女人婉约之味柔媚之态的追求塑造了昆曲流丽悠远柔曼妩媚的风格。男权社会的影响深深地烙印在昆曲的审美追求中,使得昆曲最终成为愉悦文人士大夫的声色之资。
注释:
①见程德祺、郑亚楠主编《吴文化研究论丛》(第一辑),143页,苏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②沈宠绥:《度曲须知》,《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
③西蒙·波伏娃《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
④徐渭《南词叙录》,《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中国戏曲研究院编,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
⑤同上。
⑥邹枢《十美词纪》,周光培主编《历代笔记小说集成》三十三册,《清代笔记小说集成》,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⑦据《香艳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册二,页23引。
⑧清 焦循《剧说》引《汇苑详注》,参《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册八,页88。
⑨清 严思慎《艳囮》,见《香艳丛书》册一,页293。
⑩钱牧斋《列朝诗集小传》丁集“金陵社夕诗序”。
(11)见台湾版《笔记小说大观》(台湾新兴书局有限公司1981年)第五编第十册。
(12)《续板桥杂记》,参《香艳丛书》册五,页4921。
(13)参《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册三,页245。
(14)袁枚《随园诗话》,5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15)陈大声《嘲北地娼妓曲》,转引自王书奴《中国娼妓史》,259页,团结出版社,200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