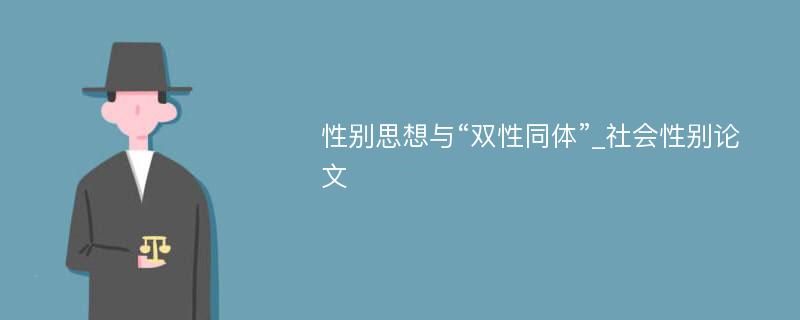
性别思想与“双性同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同体论文,性别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性别”思想的提出
“社会性别”思想是启蒙思想的副产品。18世纪启蒙思想者霍布斯、洛克、卢梭曾运用契约思想来论述男女性别平等的问题,从而成为“性别”思想/“社会性别论”[1]的最初建构者。
传统社会的观念认为,社会秩序是自然法则所决定的,它源自上帝的意志、宇宙的规律以及血缘、性别的天赋。而启蒙思想者则将包括性别关系的所有社会秩序解释成为经由人之理性的审视、并由个体间自由意志达成的“契约”。他们虽然承认“性别”是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关系,但却认为,这些因素也只有在社会和文化的调节与诠释下才能发生作用。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西方早期女性主义者开始了对性别问题的思考。为摆脱“性生物决定论”的束缚,使女性也获得与男性同等的理性和人权,他们将父权制解释成为两性的“社会性别”差异的结果。他们认为,男女生理性别有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性别特征在行为上的表现并非天生和人所固有的;欲望的产生及其构造、表现及其满足都是受社会的支配和影响的,是传统和文化对个体影响的具体反映。
基于这样的理念,她们对“性别”和“社会性别”进行了区分和定义:“性别”(sex),作为自然的构成,指的是生来就有的,由男女生理差异所决定的生物属性;“社会性别”(gender),作为社会的构成,指的是两性在特定文化环境中后天习得的一套规范的社会期望和行为,特指男性气质(masculinity)和女性气质(femininity)的观念与理想。
通过女性主义者对“性别”和“社会性别”的描述,我们不难看出,由社会建构的性别身份,并不需要与拥有一个男人或女人的躯体直接联系,即:作为社会性别的男性气质/女性气质并不必然与作为生物本体的男性/女性一一对应。这在理论上便为西方女性主义者颠覆父权制文化提供了有利武器,因为既然作为权力象征的“男性气质”是社会建构的,那么男性和女性就都可以平等地获取它,从而通过一场彻底的性别革命来实现女权主义者重构社会和文化体系的梦想。但是“社会性别”范畴本身却存在着诸多矛盾和漏洞,并日益受到质疑和挑战。这是我们重新思考“社会性别”、对西方女性主义思想走向做出前瞻性展望的根本动机。
二、“性别”理论的内在矛盾
对“社会性别”理论的质疑,须从男女两性缔结性别契约的具体情景和条件的考察出发。
契约论者在讨论契约有效的条件时曾指出,契约的最终达成有赖于签约主体对它的普遍满意,而要使它以签约主体的赞同为基础,就必须保证每个主体意志的自由。因此,由契约达成的社会秩序中必然蕴含了个体自由、主体平等的前提本质。“无论一个男人拥有对一个女人的什么权利,在她是他的平等对象的意义上,都必须得到她的同意的保证”[2]。既然父权制性别关系是通过人谈判而非自然制定的,它必须得到男女双方的同意,那么我们不禁疑问:女性为何默认在社会生活、私人生活以及文化实践中普遍存在的不公正事实?为何屈从于这份形式上平等,实质上并不平等的性别契约?“社会性别”理论尽管强调,父权制是以一种纯粹的、以自由平等为前提的男女间性别契约为基础的,而并非依凭性别的自然秩序,但是最终还是不得不受制于两性生理差异的现实。
那么,我们就看一看到底是怎样的生理现实导致了女性在两性关系上的劣势。按恩格斯的说法,在以社会化大分工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兴起之前,两性之间就存在着广泛的“生物性劳动分工”。就生理特性而言,“生育”是女性生命中最突出的经验特征。在原始早期社会,人种的繁衍、人类自身的再生产对人类社会的延续无疑有着重大意义。“生育”使得妇女被迫固定在与家务劳动有关的事务上。在社会生产力低下、生活条件恶劣的情形下,育婴的重任往往使女人遭遇生存的空前困境,她必须在严酷的社会生活中被迫做出妥协、让度一部分权利,才能寻求一个男人的保护。就女性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言,她拥有支配自己的自由,并能够成为契约的一方;但作为一个女性,在她达成契约之前,必因生理和心理的劣势而受到不可避免的限制:她需要有所依赖,得到保护,以面对母子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生存挑战。
因而,与其说是男女双方自由的意愿达成的父权制的契约内容,不如说正是男女两性在契约中的相对地位、相对条件决定了他们签订契约的方式。“社会性别”范畴的提出恰恰在两性“机会平等”的表面下,掩盖着两性“条件不平等”的现实;两性关系的文化构成要素中不可回避初始的男女自然差异对它得以形成的重大影响。
再者,在传统文化形态中,男性一般总是比女性拥有更大的权力、更高的社会地位,如果这种结果单纯是文化所为,那就难以解释为何只限于生物学意义上的男人拥有,以必然成为男性气质的男性来统治女性。这是“社会性别”本身所无法回答的问题。
基于“社会性别”本身存在矛盾的事实,我们就需要进一步解释“社会性别”是如何生成以及如何与“生理性别”相联系的问题,即考察基于两性生理差异的现实是何以影响观念层次上的“社会性别”构造的。最终,我们才能揭开“社会性别”的起源及其内在本质的真正面纱。
三、“性别”的起源
作为某种文化的建制,“社会性别”始终难以摆脱男女生物性存在对它的重大影响。
“生育”,是两性差异的最大事实。女性因为经历了怀胎、分娩、哺育这一系列过程,而与婴儿建立了独特的人际关系:“他”曾经作为“她”生命的一部分而内在于“她”,经过分娩之后,“他”从她肉体中分离出来并作为异己的个体而存在着,但是这依然无法改变“他”过去曾作为“她”肉体的一部分而存在过的事实。“母亲”的特殊经历,使得女性容易认识到人与人之间彼此相连的事实,更多地认为,“自我”之外的他者并不完全是异己的存在——“他”或许曾与“自我”骨肉相连、血脉相通。与之相对,男性由于这一心理经验的缺失,则容易倾向于缺乏人与人彼此相连的观念,而去崇尚“自我”的完全孤立、“自我”与他者利益的冲突和彼此间绝对的差异。
从生理的角度来看,女性拥有独特的经验,这使得她的精力不时被肉体以及与肉体密切相关的情感所牵引。对于无法摆脱的沉重肉身的深刻体悟,使得女性更加关注物质的、现实的、与生存相关的生活内容。而除了饮食、排泄、偶或的疾病,男性与女性相比获得了更大的肉体上的自由。
正是两性内在的上述差异,导致了他们建构自我的不同方式。南希·乔德罗(Nancy Chodorow)曾说:“自我基本的女性意识表现为与世界的联系,而自我基本的男性意识则是分离。”[3]
自从割断与母亲肉体相连的脐带,男性便更为彻底地割断了与种系相连的历史。这为其试图超越肉体的束缚、进行精神性自由的思考,寻求抽象自我价值的实现,建构公共领域和形而上学的思维体系提供了条件。其实,不唯男性,所有个体在“自我意识”凸显之时都将一切外在于“我”的存在视为异己的存在;正是为了在情感依恋中赢得坚强独立的自我意志,人类才踏上了仇视情感、拒绝情感、逃避情感的不归之路。文明的进程就是孤独的自我主体性建构的过程;正是在“自我”不断凸显的巨树之巅才盛开了绚烂夺目的文明之花。人类文明所包括的“社会性别制度”,很大程度上是由男性来创造的,它是男性摆脱情感依恋、建构超我的表现。
既然男性更容易意识到自我的孤独是绝对的,自我与他者泾渭分明,那么男性的自我想象进入他人内部的能力就易受到限制。“与其他拥有大致相等权力的人共存是本质上不稳定的……对人们自身来说,自由与安全似乎需要统治他人”[4]。享有“孤独”体验的男性由于绝对孤立的处境而焦灼不安,这种不安全感和焦虑不断向外投射,从而形成了其侵略、竞争和征服的行为,以及对等级、权力、财富、女性的欲望。这诚如理安·艾斯勒(Riane Eisler)所言:“所谓需要控制和统治别人,从心理学上讲,并不是一种权力感的功能,而是无权力感的功能。”[5]正是这种自我与他人绝然二元对立的思维作怪,才导致崇尚等级、支配和征服的“男性气质”。
四、“言说性别”——父权制维系的话语机制
这种崇尚个人、崇尚等级的价值观必然表现为对人类共生现象和融合关系的忽视,导致对“自然”“肉体”“情感”和“女性”的否定。古希腊戏剧中,俄狄浦斯王因弑父娶母的罪过而刺瞎双目,用苦行来为自己赎罪,这恰是厌恶感性生命的极致之表现。因为他发现,肉体会突然变成亵渎和玷污灵魂的累赘,因而他不惜戕害自己的肉体,来脱离肉体的束缚,超越这肮脏、污浊的感性生命。于是,“女性”逐渐成为一种象征符号,成为肉体、物质、自然、情感的象征;凡是追求超越于生活的人都必须摆脱女人,似乎唯此才能上升到尘世之上的神圣天堂,到达澄明的灵魂彼岸。
在传统社会里,人们往往习惯于将思想、精神或灵魂这些崇高的概念与父亲或男性因素相联系,而只有在文学艺术中表达最初与母亲共生以及人与人之间存在融合关系的事实。这种对“母亲”/“女性”/“肉体”的潜在的社会性仇视情感成为了“集体无意识”,在历史的变迁中、文化的实践中以性别歧视和性别压抑的方式表现出来,反映了人类心灵支离分裂的历史。
当我们再次审视“社会性别”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它恰是在男女两性建构自我的不同遭遇中、在人类二元对立思维结构中凸显出来的。它在两性生理差异的基础上进一步于文化的、观念的层次上宣扬了两性差异,是对“男优女劣”观念的强化与升华。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关“社会性别”(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话语绝非个人性别的本质属性;而是通过对自然差异的扬弃,转化了它的存在方式,并继续着男女两性曾经对立,并且永远对立存在的传说。难怪盖尔·卢宾(Gayle Rubin)说:“狭义的社会性别身份远不是自然差异的表达,而是对自然相似性的压抑。”[6]“社会性别”以对性别差异的承认为前提,是对差异的性别身份的进一步弘扬,它是从父权制逻辑中产生的“性别差异崇拜”的现代形式。
这样一来,现代意义上的“父权制”已经摆脱了前现代社会暴力血腥统治的不光彩面目,而是具备了“后极权主义”的表现艺术和统治策略。它不再是保证女性服从于男性的家族或社会性暴力机构,也不再是以法规面目出现的惩治女性的手段;它所真正关心的目标更多体现为对于女性的言说方式、支配、利用与臣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意义的“父权制”需要一套全新的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保证了女性时刻成为谈论的兴奋焦点和话语载体,并总是处在被谈论、被承载的状态之中。
“社会性别”作为有关“性别差异崇拜”的意识形态,一方面是父权制权力系统承递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又在传播启蒙的“个人主义”的精神指向中鼓动女性争取和追求个体的“独立”和“自由”。这一方面解放和发掘了优秀女性的生命潜力,一方面也因轻视女性天然和历史性形成的生理和情感结构在现实生活中的限制,而让现代女性在家庭和事业的“双重付出”中承受了更多不公平的待遇。但是,“社会性别”正是在不断言说过程中,帮助父权制成功地达成了目标——对于女性的支配与观照、鞭策与盘剥。因为“权力的主要效应之一,就在于某些身体、某些姿态、某些话语、某些欲望被确认和构成为个体”[7]。
既然作为西方女性主义核心范畴和理论基础的“社会性别”对瓦解父权制事实起不到任何助益,反倒成为其得以维系的话语机制,那么他们这番思想探索和理论建构的意义何在呢?笔者认为,无论视“女性主义”为理论学派还是政治派别,它的存在都首先应是“消灭自我”,即破除“唯女性而女性”的话语方式,打破性别的壁垒,“从性的机器内部运作的话语中分离出来”[8]。其次,便是“启迪男性”,将男性同样视作需要理解、渴求觉悟的人类另一半,从而弥补传统社会中久已颓靡的“女性质素”。
五、“女性质素”的文化内涵
对女性质素的尊视早在人类发展的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了。在新石器时代广泛存在着对于女神的崇拜。后来,人们将她的身体比作“容纳生命的奇迹并通过自然的神秘循环而且有起死回生的力量的圣杯”[9]。在卡塔尔·惠雅克的神龛中,女神的存在总是由强有力的动物,诸如豹、虎、公牛相伴随,因为她是自然中一切生命的象征。“甚至在她那神秘的外表里,在学者们所谓的神秘的或世俗的东西中,她始终被描绘为自然秩序的要素,正如所有的生灵都产生于她,在死亡时又回归于她而再次获得新生那样”[10]。
原始人形成的这种对于女性的最初认识源自自我意识觉醒的最初体验。在与自然界万物打交道的过程中,人类形成了最初的自我,也正是伴随着理性光明的最初闪耀,“自我”必然会发现他感到神秘的生命来自女性身体的事实。不仅万物的生命来自丰产的女性形态,自然界也如女性一样经历着神秘的周期轮回。这些事实进一步使我们的祖先认识到,生命和维系人类生生不息发展的原初动力来自女性的形态。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无数的宗教、神话、传说中,女性化身为英雄的孕育者、保护者、引领者。中国神话中的天帝、地帝、黄帝都是其母神奇感应受孕而生,他们成了倍受景仰的千古贤君;英雄忒修斯正是在阿里阿德涅的线团帮助下,才安全通过了迷宫,杀死了怪物弥诺陶洛斯;《神曲》中的贝雅特丽采、《浮士德》中的格蕾卿、海伦,她们成为一种理想和追求,指引着英雄通过重重迷雾无限接近至真、至纯、至美的境界。
不但在异教信仰的创世神话中,女性被描绘成孕育整个世界的大地,而且即使作为父亲的创世神灵也要通过女性的变形媒介以改为其形状,才能进入人间的各种经验,这个女性的媒介通常就是宇宙女神。在《创世记》的开篇描绘创生万物乃至人类的上帝时,曾说道:“上帝的灵运行于水面上。”而与“水”相关的恰恰是女性的原则——克里特岛的阿里阿德涅、性爱女神阿芙洛狄忒就是诞生于大海的。在印度教神话中,宇宙女神就是“自我”通过她而创造出世界万物的那个女人;她就是那种诱使处于自我沉思中的神从事创造的动力。这一切都证实:早在男性神灵出现在神坛之前,女神早已经占据了绝对的崇拜优势,对于女神的崇拜恰恰折射出史前社会的精神实质——对于生命和维系生命之原初动力的高度珍视、由衷敬仰。
女神象征的女性占中心地位的价值,并不能证明妇女必然统治男人的推论的合理性。“妇女在史前宗教和生活中发挥了重要而有力的作用的事实,并不意味着男人是处在从属地位上的。因为,在这里不仅男人而且女人都是女神的孩子,正如他们是支配家庭和部落的妇女的孩子一样。而且虽然这的确赋予妇女以一种很大的权力,但是从我们现在关于母亲和孩子的关系来进行类比推理,这种权力似乎是这样一种权力,它更是一种责任和爱的权力,而不是压迫、特权和恐吓的权力”[11]。因此,我们可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于女神的崇拜恰又象征着这样一种宇宙观:万物彼此统一而相互联系,而并非像在男性统治的神学和科学理论中那样追求差异、对立和冲突。
在阐述“社会性别”起源时,我曾经指出,在建构自我的过程中,由于不同的生存经历形成了两性对生命层次的不同关注,才导致建构自我的不同方式。女性由于生育的经历和生理的现实,更易形成关注肉体、注重联系的宇宙观。而男性则更易走向反面,趋于崇尚对立、分离、仇视肉体的宇宙观,因此,两性建构自我的不同方式易导致生成的“自我”不同的意义,那么人之自我的真正内涵是什么呢?我们看中国古代哲人如何阐释:
《老子》的开篇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老子所谓的“道”乃指宇宙、万物的本源和规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揭示的就是“道”所蕴含的存在的原初意义。而理解《老子》全篇这一点睛之笔的关键则在于对后一句的阐释:“所谓‘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是说‘道’作为不可名状的天地之源,就像尚未成熟的少女一样,还没有孕育出任何成果;‘道’作为可以命名的天地之源,则像已经怀孕的妇女一样,成为生育万物的母亲了。”[12]在这里,“母”作为“道”的象征,成了“宇宙万物最大的根本”[13]。这一点在《老子·六章》中又得到进一步的证实:“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玄牝之门”指女性生殖器官;作为“道”的原始意象,女性还是作为“繁衍整个宇宙和天地的根本”[14]来定性的。“在神话的图像语言中,女人代表着所能知道的事物的全部……女人是达到感官冒险之极至的引导者”[15]。女性果真如老子所言具有创生的原初意义并包蕴着宇宙万物存在的规律吗?
女性的原则不仅仅是肉体、生命的原则、强调创造而非毁灭的原则。从某种意义上,“女性”的原则更是一种象征——因母亲对婴儿抚养与爱护而获得——一种“爱”的象征。“爱”,揭示着人与人之间能够存在着关系,更揭示着这种能够存在的关系的性质。“爱”意味着“联系”,孤独的自我只有在万物的簇拥中才能成其为“我”;其他万物存在的事实,证明了“自我”存在的事实。“我中的‘我是’只有深刻地在‘你是’之中体现自己,它才能超越自己的局限……这个在本质上具有‘唯一’感的人格,在一个个的事物、思想和事实中实现它自己”[16]。“爱”又意味着“关怀的联系”,它在证明“我”之外顽强地存在着某个生命的同时,刺激着“我”自身生命存在的感受。正是在关怀对方、施爱于对方生命的联系中,“我”发现了一个在种种虚荣假面的掩饰下潦草生存的“孤独自我”,一个渴望被感受、渴望被理解、渴望被爱的“自我”。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说:“我们仅仅是在与他人的联系中把自己看作是分离的,我们只是在他人与自我的区分中来体验关系。”[17]这种关系就是“关怀”的关系、“爱”的关系,正是在关爱他人生命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建构、实现了“自我”。
然而,基于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认识的“关怀”,“爱”的概念并不是要消弭自我的理性,转而将自我价值的追求寄托于外在于自我理性的东西,而是试图彻底打破、超越自我与他者的界限,在自我与他者的统一中建构完善的独立人格。这种伦理理想的实现依然是建立在自我理性自明的基础之上的。
虽然在施动者关爱时使“被关怀的人们失去了自主,但当这一个人去关怀别人时就又恢复了自主,人生是一个在关怀与依赖之间不断变换的过程。但关怀的本意并不是使依赖永久化,而是要结束依赖”[18]。只有被爱者,被关怀者切实感受到了爱与关怀,并对其做出回应,“关怀”本身才能够实现。因此,“爱”的实现在“关怀”的意义上说,依赖双方的理性觉悟,它正是禀有清醒、独立的自我意识的人超越自我、寻求自我真正意义和价值的表现。“无论何时,只要自我真正认识了自我之外的东西,那么,在我之内的‘我是’就实现了它的扩展,实现了它的无限”[19]。这恰恰证实了自我的真正内涵:“自我”并非孤立的、绝对的存在,它与外在于形体自我的存在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自我存在的意义也绝非仅属形而上的范畴,因为自我本身就是兼有肉体和灵魂、时间和永恒的双重属性。
六、“双性同体”的学理意义
这种对于生与死、善与恶、美与丑、苦与乐、男与女、自我与非自我两重性和统一性的理解,在女神的早期雌雄同体形象上就得到了深刻的阐释。
希伯来的《光辉之书》曾经记载道,每一个灵魂和心灵在进入这个世界之前,都是由一个男性部分和一个女性部分结合在一起而成为一体的。在它一下降到人间,这两个部分才分离开来;在获得生命的同时,成为两个不同的躯体。这种对个体的诞生和性别由来的解释在创世的神话那里得到印证。
在宇宙由来的创世神话中,往往预设一个先于时空存在的原始整体。它或者表现为混沌,或者就是一个球形的宇宙卵——通过它的爆裂露出了具有生殖力的众生之父,然后他再一分为二而成男女,进而分门别类地生育出自然界的万物。个人之不朽的基本要素与宇宙万物的祖先同出一辙;创世神话同时也揭示出个人和性别的起源。这一过程包含着丰富的象征意义。这个从“一”到“二”的过程恰恰象征着从完美的境界堕落到二元状态的开始,从此人类走上了残缺的、分裂的命运之途;而通过男女之爱使“二”合为“一”、产生新生命的过程,又象征了从残缺、分裂到完美、永恒的回归,它是新的宇宙演化周期的开始。由此可见,二合为一、双性同体的状态是完美、永恒状态的象征。
双性同体的神灵在早期更多地表现为女神的形态。这大概基于对于女性原则的认识。“爱的实质,就是寻找被分离的部分,并要求恢复整体”[20]。爱的原则是女性的原则,正是“爱”的存在使双性同体、合而为一成为可能,因为“爱的最终经验是理解到‘二’的错觉之中含有同一性,即‘此中有彼,彼中有此’”[21]。
“柯勒律治曾说,伟大的心灵总是雌雄同体两性因素并存在……只有当两性因素融为一体之时,心灵才会才气横溢,充分发挥其所有功能”[22]。当我们再度谈论双性同体神的现实意义时,“双性同体”在很大程度上或许并不是意指经验意义上的、生理层面上的雌雄两性人——它的存在或许基于上帝的特别眷顾,或许不过是造物主不经意的错误。但是从它推衍开来而形成的无数奇思妙想却是人类独特的创造。正是借着这种双重形象的想象翅膀,人类的心灵仿佛才能够聆听到异域彼岸的绝世之响。因此,“双性同体”在更多时候借指人的某种完美的心灵状态和生命状态;在人类超越本质的意义上,它寄托了人类渴望实现沟通、爱、美德与“自我”之完整人格的梦想。“双性同体”概念的真正内涵恰正在于:消除自我中心主义,在尊视生命的基础之上实现自我和他者的沟通、理解与终极融合。
基于上述认识,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每个人的心灵都是既具男性因素,又具女性因素的。“双性的心灵是易于共鸣而有渗透性的……充分发展的心灵之特征,乃是它不会特别地或孤立地考虑到性别”[23]。荣格也认为,所有人都是先天的男女同体,两性通过了解自身异性的因素而达到与异性沟通的目的。心理学同样证实,男女双性气质者兼有单一气质者的种种优点,并能够表现出良好的性别自认和环境适应能力。由此可见,性别差异并非不可逾越,相比之下倒是人与人之间的个体差异更为关键一些。
于是,当我们带着“双性同体”大胆的设想再一次反观“社会性别”的时候,我们会蓦然发现:在界限分明的社会性别身份背后,恰恰是内在的双性态人格现实。男性气质/女性气质是社会的建构,并不必然与男性/女性发生一一对应的关系,因而从人格层面上,男性和女性都可同时具备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事实上,真正的单一气质表面下隐藏的正是男女双性气质的特点。然而,在女权主义者对于“社会性别”的运用过程中我们发现,在历史条件业已改变的今天,向往自由、追求平等的女性依然无法找到“自我”之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故而,假如女权主义“社会性别”思想探索果真具有意义的话,我们就应当站在超越差异和尊重差异的立场上,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追求一种真正理性的、双性同体的理想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