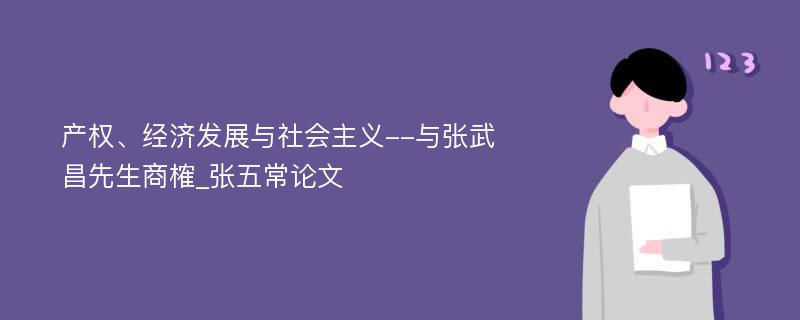
产权、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与张五常先生商榷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发展论文,产权论文,张五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在经济运行中,财产的终极所有权并非无足轻重和可有可无,而是与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互相作用的;经济发展是产权制度的函数,而完整的经济发展函数应为:F发展=f(c产权、t土地、L劳动、Z资本、j技术、g管理……n);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公有主体型产权结构+劳动主体型分配结构+国家主导型市场结构,“三主制度”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当代解决公有与私有、公平与效率、计划与市场三大世界性基本经济矛盾的最佳模式,操作得法,可以优于西方的经济及其制度;在国家调节主导作用发挥得较好的社会里,公有产权可以比私有产权更适合现代市场经济,产生更高的整体效益。
1994年,笔者在香港看到久闻大名的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院长张五常教授四本论著。拜读后感到:无论是《卖桔者言》、《中国的前途》,还是《再论中国》、《中国的经济革命》(以下引言均出自这些书),都是以产权为基点来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充满着作者的民族激情、敏捷思维和辛辣笔调,不愧为产权经济学派的“高手”,实在令人佩服。敬仰之余,又觉得不少观点使人费解,不敢苟同,有必要请教,交流思想。好在张五常先生说过:“希望能够引起有建设性的辩论”,“我对辩论视作家常便饭——就算是再激烈十倍,也从不介于怀。”这与本人的学术个性倒完全一致。本文先就产权同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作一求教。
产权与国有制
张五常先生写道:(一)“私有产权必须包括三个权利:1.私有的使用权(有“权”私用,但不一定私用);2.私有的收入享受权;3.自由的转让权。这看来是个浅显的定义,但我要用三年时间才敢肯定。主要的思想障碍,是我想来想去也不明白为什么私有产权要有私人的‘所有权’。当时我遍读西方有关产权的法律书籍,它们都一致认为‘所有权’重要,不可忽略,然而我总是认为‘所有权’在经济上无足轻重,可有可无。”(二)“承包制可以节省交易费用而增加生产活力。所有权并非私有——但这是不重要的”,“彻底的承包制是私产制”,“所有权可归国有”,“私产不需要私人的所有权”。“虽然政府可以不放弃资产的所有权而维护社会主义的形象,在政治上大为可取,不过,总是要付出点缚手缚脚的代价。东欧的捷克,开门见山,摆明要放弃共产,不管社会主义为何物,以大手笔出售‘国产’的办法来推行私产制,只三年功夫就欣欣向荣。要顾全‘社会主义’的面子而不放弃所有权,在理论上可行,但在意识上这会给特权分子诸多藉口,左推右搪地维护或增加自己的权益。”(三)“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为了要保持‘社会主义’的形象而坚持这些资产的所有权为国有,代价实在太大了……中国若不放弃这些资产的国家所有权,工商业的承包困难解决不了。即使国营机构不采用招标的办法,把资产出售,而把它送给职工——取之于民为国有,还之于民为私有——在道义上没有谁会反对的吧?”
为了不曲解原意,摘引了这么多原话。其中,在理论与实践上至少存有如下几个疑问:
第一,在经济运行中,财产的所有权果真“无足轻重,可有可无”?
以较难解释的上市股份公司为例。作为财产终极所有权的股东,既可以“用脚投票”来影响公司的经营行为,更可以通过股东大会各项决议来制约公司的重大经营活动,包括财产使用、收益和转让方面的高层次战略决策。显然,这些影响和制约作用对于公司经营活动的效率和效益,决不是无足轻重和可有可无的。不分青红皂白,完全抛弃财产的最终所有权,过份抬高其他权利的功效,是古今中外任何经济法律条文所不宜采纳的。这就难怪在所有的西方法律书籍中找不到根据——可能永远也找不到。如果说所有权明确界定和拥有后就是无关紧要的,那么,人们也同样可以说,其他权利明确界定和拥有后也是无关紧要的。可见,财产的终极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处置权)这几项经济权利各有各的作用,都是重要的、互相牵制的。
再以非国有化运动为例。假定财产的终极所有权归属问题无足轻重,为何美国里根和英国撒切尔夫人要联手在全世界掀起一个非国有化浪潮?众所周知,西方的国有企业是基本拥有张五常先生所说的“三权”的。倘若断言只要拥有“完整的私有产权”,经济效率问题立即可以彻底解决的话,那么,又为什么要搞非国有化呢?事情恐怕并非如此简单。现有的私产权理论要真正使人信服,也许首先还得听听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不同政见。
第二,依据同一产权学说,怎么既推断“中国不放弃这些资产的国家所有权,工商业的承包困难解决不了”,又推断“彻底的承包制是私产制,所有权可归国有,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对于在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模式上既否定国家所有权,又肯定国家所有权这两个截然相反的说法,任何人绞尽脑汁也是难以理解的。可见,在保持国有制的条件下实行彻底的承包制到底可行不可行的问题上,似乎出现了推断逻辑的混乱。就算人的思想会否定之否定地发展,第二个断言是新近定下的,这里仍有含糊不清之处。张五常先生曾提出中国的产权改革至少有三个重点:“(一)在重要的非人力资源的资产上,不放弃国家的所有权;(二)在国有的资源上,推行彻底的承包制,以之作为大举私产化的重要基础(不要忘记,私产不需要私人的所有权);(三)在难以独占的企业上,推行明确的股份制。”这段话好像要表明下述一层意思:中国应当在重要的资产上实行彻底的国有承包制及股份制,这在经济理论和实际中都是可行的方案。若此种理解没有违反作者本意的话,那么,再建议中国模仿捷克搞的非国有化的完全私有化,则又进一步露出破绽。依据同一产权理论,最佳的政策建议不可能是大相径庭的两种方案。
人们不难察觉到,私产权学派内含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遵循所有权归属不重要,只要拥有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构成的完整的私产权,经济制度就完善了,经济效率就会因交易成本最低而达到极大化这一思路,在重要资产上存有大量的国有企业也是可行的,即“社会主义顺理成章”,进而推导出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结论。但这个结论,显然又不是该学派所愿意看到的。因为他们十分赞赏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蜕变成财产所有权私有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国家,并希望中国也能立即模仿它们。面对这一矛盾怎么办呢?看来解铃还需系铃人。
第三,说以首钢为代表的彻底的承包制是私产制,而非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这种理论抽象是否十分科学?
为便于读者独立分析,先介绍一下张五常先生曾去调研过的首钢情况。首都钢铁总公司以1981年上交利润2.7亿元为基数,以后每年的上交额比上年递增7.2%,承包期为15年;超过上交额的利润全部留给企业支配,国家不再给投资,完不成上缴额由企业自有资金补足。1992年企业增加值达到48.63亿元,改革以来年均增长17.68%;实现利润达到32.02亿元,改革以来年均增长18.43%。同时,经济效益水平也不断提高。14年完成生产性建设投资49.99亿元,同期按国际可比口径计算的企业净利润56.75亿元,年均投资收益率为16.3%。反映企业实际投资收益率的所有者权益利润率,按国际可比口径计算,1992年为17.3%。承包后14年上交国家各种利、税、费137.16%亿元,平均每年9.8亿元。1994年实现销售收入312亿元,比上年增长41.18%,实现利税66.1亿元,比上年增长22.2%,创汇8.1亿美元。承包前的1978年,占用固定资产11.04亿元,定额流动资金3.9亿元,共计14.94亿元。到1992年,在国家不再追加投资的情况下,首钢国有资产帐面值(所有者权益)已增长到79.41亿元,14年的总积累率达到432%,年均增长11%。按现价计算,固定资产已达300亿元,相当于11.04亿元的27.17倍。1994年产钢一跃上升到823.7万吨,成为以钢铁为主跨18种行业的企业集团。首钢逐步通过组成国家独资有限公司来实行全权委托式的全员资产承包制,做到国家终极所有权与企业法人所有权的分离已有的实践证明:以这种改制后的承包方式,也可以建立产权明晰、职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这种国有独资公司的实质,是国有民营(不是国有私营)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假如有人把这种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体制称作私有制,似乎有张冠李戴之嫌:假如再把私产制视作“资本主义的骨干”和核心,那就等于说:国有民营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私产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难道这种产权论本身没有必要重新反省和严格界定一下吗?!
应当认识到,我国过去使用“两权分离”的术语,即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现在改用新的“两权分离”,即国有资产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的分离,实际上都是要表达国有资产的终极所有权与企业法人所有权应科学分离的含义,只不过目前采用的概念更具进步性,但无论如何,把国有资产的企业法人所有权说成是“私产权”或“私产制”,总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中外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恐怕难以接受这样一种笼统的概括:把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个人业主制、合伙制、合作制、无限责任公司、两合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公司等不同财产权利形式的制度,一律称为“私产制”,而抹煞其中私有产权、共有产权与国有产权以及自然人与法人等等的内在差别。其实,若没有误解的话,私产制倡导者要表达的一层意思非常简单,即包括国有制(非国营制)在内的任何企业,都必须拥有独立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对此,并无非议,只是觉得用“私产制”来说明,反而言不达意,造成逻辑不清。
产权与经济发展
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影响较大,其合理性在于继承和发挥了人类经济学说史上的科学视角,把制度视为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内生变量,探讨经济制度变迁的规律及对经济发展和运行效率的影响,同时又注重物与物交换背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这弥补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纯数量分析的不足,也与中国主流经济思想有某些相通之处。但正如该学派的不少论点已受到国际学术界批评一样,笔者对“私产制是经济发展的独步单方”之类的命题存有疑问。
张先生提出:(一)“从历史的经验看,没有其他成功的制度,而经济理论也没有其他可取的办法。私有产权是独步单方。”“我一向认为若要发展经济,私产制度是我所知的唯一可靠途径。”“私有产权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因素。”“私产制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稍事推行,就有起死回生之效矣!”“要选择一个能够促长生产的制度,不管分配是否合理,而又尽可能援助一些贫困交迫的人,私有制度是唯一的选择。”(二)“中国的秦始皇统一了度量衡,协助了产权的界定及市场的交易:秦朝的富裕是不难理解的。……美国的宪法将保障私产作为大前提,效果怎样毋庸细述了。……战后英国回复了旧观,就开始尝试搞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国营企业,不十年间就给日本爬过了头。瑞典挂‘社会主义’之名,却实行私产制,人民的生活也就大有改观。”
从大量类似的言论中,人们很容易产生这样几个疑点:
第一,单纯运用私产制度去阐述多姿多彩的各国经济发展史,是否染上了“简单化”和“呆板性”的嫌疑?例如,中国自夏商周以来各王朝的经济发展及兴衰变更,若一律只用所谓私有产权进行阐释,恐怕没有一位史学家会赞同。其道理十分清楚:如果说秦始皇统一了度量衡,协助了产权的界定及市场的交易,秦朝就富裕了,那么,秦王朝统治不久便被灭亡,就只好归因于统一度量衡的取消和市场交易的混乱了。而这一点并无充足的历史资料来支撑。
又如,美国的宪法保障私产,对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可不要忘记自1787年制定美国宪法以来,其经济发展曾周期性地大起大落,这并非宪法拥有保障私产这个“大前提”就能圆满解释的;况且,除个别国家例外,自奴隶社会以来,古今中外的国家在不成文或成文的法律上都是“将保障私产作为大前提的”(甚至连奴隶本身也界定为奴隶主的私产),若说一句“效果怎样毋庸细述了”,势必难以揭示世界各国及不同时期经济起伏的变动规律。
再如,二次大战后东亚经济发展模式之所以比较成功,主要是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等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发挥了比其他私产制国家更多的作用。日本的经济奇迹离不开著名的“行政指导”、产业政策和政府计划;韩国全部工商业资本中,国家资本最高曾占60%,“政府主导”威力极大;台湾国营工业在资本形成的毛额结构中,50年代占34.9%,60年代占28.7%,70年代占32.9%,80年代占26.6%(不包括迅速膨胀的国民党党营企业),1987年占20.8%(而同年英国只占6.5%)。若进一步放宽视野,我们还可以看到:巴西60年代末开始的高速增长,就是在国家资本占社会总资本54%的状态下实现的;被称之为实行私产制较好的瑞典,1976年起连续6年掀起的国有化运动,使1982年国有企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如此这般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这些例子都是真实而可以考证的。”举例的目的并非要得出,国家干预或国有企业的作用越大经济发展就越好。因为国家干预有合理与否之区别,任何性质的企业也有经营管理体制和水平之差异,不能一概而论。这里只是想说明,在自由经营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两大国际性经济思潮的论战中,偏激一方,未必有充分的事实依据。
第二,产权只是经济及其发展系统的重要因素之一,科学地阐明经济发展系统的规律,要不要确立辩证的系统思维方法?
从现代系统科学来观察,社会经济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劳动、资本、技术、土地和信息,个人、企业和政府,经济制度、经济心理和经济行为,经济时间和经济空间,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构成经济大系统的子系统或要素。它们之间密切关联和依存,有时甚至互为因果。此外,经济系统并不孤立,它又与政治、文化等系统组成社会更大的系统,进而互相产生信息交流与行为制约。当人们去阐明某国某时期经济发展何为头等重要的因素时,完全要因时而异,并没有一成不变的“独步单方”和“唯一可靠的途径”。否则,除了新制度经济学,其他任何经济学派和学者均无要事可做了,各国首脑也无必要发表内容各异的施政纲领了。
为了进一步说明上述论点,我们随便举一例。根据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索洛等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或罗宾逊等剑桥经济增长模型,都可以从劳动力、资本量、生产技术等要素的分析中,得出某国某时期经济增长的重要促进因素及排列次序,但迄今尚未看到,新制度经济学派倡导者是如何在剖析一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中将私产制排到首位的。倘若对经济发展中各种增长因素都不能进行有说服力的实证分析和逻辑论证,人们就必定怀疑该学派理论的正确性。不过,假如仅仅说私产制是大前提,而必须放在促成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首位,那么,继续推论下去,也就有理由否定杨怀康在为张五常论著作序讲的一句话,“教育并不见得就是解决中国积弱问题的独步单方。”理由在于,私产制的理论发明和实际操作,均以受过教育的人存在为大前提,因而教育恰好成为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独步单方”和“最重要的因素”。
正确的思维是:经济发展是产权制度的函数,但完整的经济发展函数为:F发展=f(c产权、t土地、L劳动、Z资本、j技术、g管理……n)。换句话说,产权对于一国经济发展,不是唯一重要的。其他重要的因素还有:土地(威廉·配第强调)、劳动(大卫·李嘉图强调)、资本(亚当·斯密强调)、技术(熊彼特强调)、管理(弗雷德里克·泰罗强调)、信息(托夫勒强调)、环境(罗马俱乐部强调)、文化(马克斯·韦伯强调)等,它们互为前提,互相促进,共同推动经济发展。当某一因素发展相对滞后,阻碍其他因素正常发挥效应时,解决该因素的发展问题便是最重要的。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说,此因素是经济大发展的“独步单方”和“灵丹妙药”。
产权与市场社会主义
综观人类近现代经济思想演化的历史,可以看到有两种思潮曾长期主宰世界经济运动:一种思潮认为,市场经济只能与资产私有制相容;另一种思潮则认为,资产公有制只能与计划经济相容。以中国为典型的经济体制改革经验,已同时突破了支配东西方传统主流经济学的两种教条,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可以兼容”的崭新命题。可是,国内外仍有许多经济学家停留在传统思想领域,并不断抨击该命题,张五常先生是其中一位较有影响的学者。这就有必要进行探析:公有制与市场社会主义或市场经济肯定无法兼容吗?
张教授说:(一)“中国大陆的共产经验一败涂地,而又不愿意行私产制度,那怎么办呢?这是经济学上一个极为湛深的问题。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形象,但又要有私产与自由市场的经济活力,而这二者并驾齐驱,又要搞得像样,不至于挂羊头卖狗肉。说实话,我想不到哪一位曾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能有可行的答案。”“一方面坚持共产的优越,另一方面支持自由市场,这其中不是有很大的矛盾吗?”(二)“私有产权是真正的市场的先决条件。”“私产的界定是市场成交的先决条件。”“唯一没有经济浪费的竞争准则是市场价值。这种准则只有在私有产权下才可以有效运用。私有产权制度就是资本主义的骨干。”“中国改革的要点当然是要把资产转为明确的私产,……就是政府要尽量让资金落在私人或私营机构的手上。”(三)“资产的转让权若不被大量放宽,中国的经济增长就只可翻一两番,再多就不可能了。但若要让多种重要的资产自由转让,共产的形象就保不了。”
还有很多重复的相似分析和结论。对此,可以提出三点质疑:
第一,从经济学上说,社会主义初级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没有根本的冲突?
在本世纪30年代前后爆发的一场关于社会主义资源配置问题的国际大论战中,米塞斯就曾断言:“因此,抉择仍然是: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市场经济。”这一观点遭到奥斯卡·兰格和巴伦的严厉批判。后来,哈耶克又反驳声称,只有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才能保障个人自由和高效率地发展经济。通读张五常的四本书,其基本思路没有超出前人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窠臼,添加的倒是一些互相矛盾的事例和结论。为了证明这一点,仅列举一段同第(一)部分引言截然相反的话语:“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与自由市场在基本上是没有冲突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个见解是可以说得通的。”当一位声誉极高的学者从同一角度论述同一重大命题时,在一处写上“说得通”,又在另一些地方写上“有很大的矛盾”,“想不到哪一位曾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能有可行的方案”,读者由此会产生何种感觉呢?人所共认,经济学也是一门严肃的科学,它毕竟不是在市场上卖桔子,可随着行情的涨落自由开价,理论应当严谨而鲜明。
与此不同,中国的改革成功经验及部分经济学家已大大推进了兰格“模拟市场机制”的思想,也推进了前南斯拉夫“半市场社会主义”的模式,与英国亚历克·诺夫1983年提出的“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说比较接近。笔者前几年曾倡导一个同诺夫和于光远教授有些差异的社会主义经济新公式: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公有主体型产权结构+劳动主体型分配结构+国家主导型市场结构。也就是说,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由公有制主体型产权制度、按劳取酬主体型分配制度、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制度这三项基本内容构成的,即两个主体和一个主导的“三主制度”。它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当代解决公有与私有、公平与效率、计划与市场三大世界性基本经济矛盾的最佳模式。操作得法,可以优于西方的经济及其制度。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私有主体型产权结构(制度)+资本主体型分配结构(制度)+国家指导型市场结构(制度)。
中国传统的国有企业由国家经济管理部门直接来经营,与要求自由经营的市场经济天性必然存在冲突,这也是西方某些国有企业效率较低的缘由。不过,国内外已有经济学家认识到,只要依法实行国有民营,使企业真正按照市场竞争原则和效益极大化目标而自主决策、自由经营,那么,它就不会同市场经济的本质发生根本的冲突,进而得以实现高效率。
由此看来,在一个国家调节主导作用发挥得较好的社会里,公有产权不仅可以与市场经济相融合,而且可以比私有产权更适合现代市场经济,产生更高的整体效益。
第二,私有产权与市场经济(交易)究竟是何种关系?
假如说,资产私有制或私有权是市场交易和市场经济产生的先决条件,这毫无新意,自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以来的多派经济学早已揭示过:假如说,撇开资产终极所有权,由资产的使用权、收入享受权和自由转让权组成的私有产权,是市场交易和市场经济存在的先决条件,这显得不够全面。原因在于,由资产的使用权、收入享受权和自由转让权耦合的产权,不一定只可采取“私人或私营机构”的“私有产权”的形式。它也可采取合作组织、集体组织或国有民营组织的“共有产权”和“公有产权”的形式,甚至可采取“国有产权”的形式,自然还可采取多种“混合产权”的形式。换句话讲,产权的类型会呈现多样化,决非“私有产权”一种。
从数百年市场经济的变迁史来看,各种产权形式在不同层次上均能同社会生产力和市场制度互相依存、互相适应,那种主张只有私有产权才是“市场成交的先决条件”的论点难以成立。张五常自己也察觉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因而曾含糊地承认:“在‘私产’与‘公产’这两个极端之间,可以有各种不同的产权结构(制度)。但不论什么经济制度下,只要这些制度的运作费用是完全免费的,资源的运用都会达到最高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制度的选择将是一件随机、偶然和不可确定的事。”这段话又出现两个理论漏洞:其一,一方面断言“只有在私有产权下才可以有效运用”,另一方面断言“各种不同的产权结构(制度)……的选择将是一件随机、偶然和不可确定的事”,让人们相信哪个论断好呢?其二,不管在什么产权制度下,“运作费用是完全免费的”状况并不存在,只有高低多少之区别。至于“唯一没有经济浪费的竞争准则是市场价值”之类的话,恐怕很难有第二位世人会首肯。因为完全没有经济浪费的市场竞争,人类尚未发明出来,且不要提“30年代大危机”所造成的巨大经济倒退和浪费了。
第三,多种重要的资产自由转让,就不是社会主义了?
张五常高度重视包括土地和生产资料在内的资产自由转让权,认为“若不被大量放宽,中国的经济增长就只可翻一两番,再多就不可能了。”稍微浏览一下迄今为止的新中国经济史,这类缺乏经验常识的预言便不攻自破了。因为即使处于旧体制中,国民经济总量也不可能翻两番之后就永不增长。至于说到改革逐步允许资产自由转让保不了社会主义的形象,这又混淆了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事实上,在全民和集体资产占社会主体的前提下,各种资产自由转让与社会经济性质及形态无关。
末了,我觉得还是毕业于香港大学的英国曾澍基先生评论得好,他在《香港政治经济学》中写道:“‘私有产权’及‘自由经济’论者企图再把市场机能翻新推销,是注定要失败的。刚巧是因为自私,人们才不愿意遵守市场的游戏规律。从这个角度看来,真正能够充分地、全面地利用市场机能的,应该是一个个别成员之间的利益矛盾已经大部分消失的经济制度,一个尖锐的阶级对立已经被超越的社会境界,你称不称这种制度和境界为社会主义,那是你的自由。”
标签:张五常论文; 产权理论论文; 经济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产权论文; 国有经济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