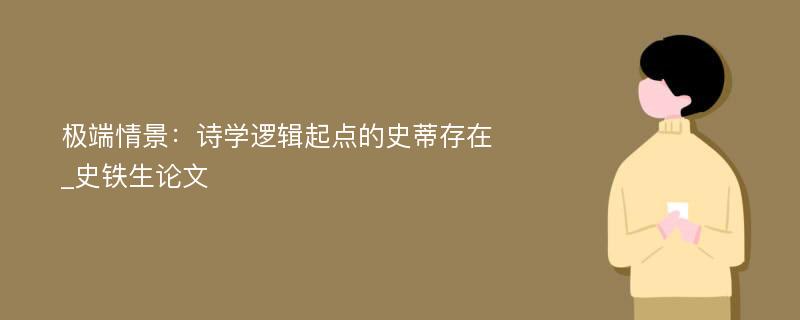
极限情景:史铁生存在诗学的逻辑起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逻辑论文,情景论文,极限论文,起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史铁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文学家之一。他的写作进入现代汉语文学和诗学未曾到达过的领域。那里隔着一条河,河的那边是一片人迹罕至的思想飞地,史铁生从写作之夜出发,摇着轮椅,借助冥思和无与伦比的意志到达那里。史铁生记录这个过程写下的那些小说、随笔,是这个时代汉语思想界足以与帕斯卡尔、克尔凯郭尔、薇依等人媲美的思想录。
一位学者在谈到史铁生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时指出,“如果放长时间尺度——例如半个世纪,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来估量中国文化的发展,这部被人忽略的长篇小说,就会以其卓绝独特的品格,立在世纪之交的地平线上,成为一柱标尺:这个有着悠久文明的民族,可能已经开始新的艰苦寻求。”(注:赵毅衡:《神性的证明:面对史铁生》,《开放时代》2001年7月号。) 另一位学者对史铁生曾经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们面前终于出现了一位作家,一位真正的创造者,一位颠覆者,他不再从眼前的现实中、从传说中、从过去中寻求某种现成的语言或理想,而是从自己的灵魂中本原地创造出一种语言、一种理想,并用它来衡量或“说”我们这个千古一贯的现实。在他那里,语言是神圣的、纯净的,我们还从未见过像史铁生的那么纯净的语言。只有这种语言,才配成为神圣的语言,才真正有力量完成世界的颠倒、名与实的颠倒、可能世界与现实世界的颠倒;因为,它已不是人间的语言,而是真正的“逻各斯”,是彼岸的语言,是衡量此岸世界的尺度。……它理智清明而洞察秋毫,它表达出最深沉、最激烈的情感而不陷入情感,它总是把情感引向高处、引向未来、引向纯粹精神和理想的可能世界!……使逻各斯的真理自由地展示在他心里,展示在读者面前。(注:邓晓芒:《灵魂之旅——九十年代文学的生存境界》,第151—152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史铁生从自身的残疾,看到了人的残缺和人的有限性;从人的有限性思入了人的存在;又从对人的存在的追寻,抵达了对神在的仰望。他完成了从审美向伦理、向哲学,最后向宗教的跳跃。他为人的“不可能”的现实,敞开了一个无限的可能性世界。而这些非凡之“思”则是以“诗”的方式完成的。这为当下以至未来已经或将会被消费欲望引诱或刺激得失魂落魄的汉语文学与诗学,找到一条超越之路。
我以为史铁生的诗学是一种存在诗学。一方面,他确曾受到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深刻影响(注:参林舟:《生命的摆渡——中国当代作家访谈录》,第175页,海天出版社,1998年。);另一方面,我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存在”的:“存在”是“语言活动中发生的意义之在”。对存在的思考即对意义之在的思考。只有把握了意义之在,才有可能理解人的存在,即此在,因为人的存在,本质上即意义之在的历史性发生(注:参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七章,第14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当然,史铁生的存在诗学在思路和言路上可能与哲学不一样,它是倒过来的,他首先面临历史性的此在,并由此在出发去追问和追寻那个意义之在,再反过来让此在的意义得到澄明。
史铁生的存在诗学是以生命体验为逻辑起点的。他是从常人难以遭遇的困境中感受到的体验出发,开始诗学之思,这决定了他诗学的走向、样态、品质、高度和深度。
二
史铁生诗学的逻辑起点,或者说那个生命体验为何?简而言之:极限情景。极限情景是存在主义的关键性概念之一。始作俑者雅斯贝尔斯用以指称人类生存中这么一些情景:
我们从未选择过它们,而它们却使我们面对“在此世存在”之彻底开放性和疏远性。……这些情景中最重要的有偶然、过失以及死亡。它们是人生不可逃避的,但又无法改善的状况。它们向我们的生活注入一种使人不舒服的对危险和不安全的感觉,使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脆弱和无家可归。(注:詹姆斯·C.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下卷),第694、686、638、690、634、619、61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显然,极限情景是一些威胁生存,又无法逃避,把人直接抛入无家可归的深渊性事件。
史铁生在21岁上遭遇了这样的事件:高位截瘫。他在《我与地坛》中说:“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然地残废了双腿”,突然成了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什么也找不到了”(注:史铁生:《我与地坛》,见《中华散文珍藏本·史铁生卷》,第8—9、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请注意这个时间:21岁,这是人生最美好的一切正在和就要展开的时候。如果是先天性残疾,或者是没有记忆之前已经这样了,也许史铁生不会如此剧烈地体会到命运的巨大偶然性和不公。不期而遇的苦难,从此把他残酷地锁定在轮椅上,将一个活蹦乱跳的生命囚禁于见方之地,绝望的高墙陡然间隔断了他的前程。灾难并未就此结束,五十岁左右他又患上尿毒症,双肾坏死,每三天去医院做一次透析。死神须臾不离地觊觎着他的生命。接踵而至的苦难,注定了史铁生——如果他要活下去——终生必须无休无止地撞墙。这是加谬《西绪福斯神话》里那堵“荒诞的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面对的那堵“监狱的高墙”,是安德列夫象征世界中“我和另外一个麻风病人”以胸膛撞击,用鲜血染红的那堵墙,也是史铁生笔下那堵神明般启示的墙、“伟大的墙”:墙永远地在他心里,构筑恐惧,也牵动思念(注:史铁生:《墙下短记》,见《中华散文珍藏本·史铁生卷》,第104—10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就这样,史铁生实际上成了萨特境遇剧的主人公,他面临一个致命的问题,即当年丹麦王子哈姆莱特曾经面临过的:是死还是活?也是存在主义哲学家认为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判断人值得生存与否”的问题(注:加缪:《西绪福斯神话》,《加缪文集》,第624页,译林出版社,1999年。)。这意味着,史铁生必须在命运设定的极限境遇中做出“自由选择”——生与死的抉择。
许多年以后,当他在回忆当年残疾的情景时这样写道:“心里荒荒凉凉地祈祷:上帝如果你不收我回去,就把能走路的腿给我留下。”但是上帝没有应答,也没有给他留下能走路的腿,只是把无路可走的绝望,以及还要不要继续走路和走怎样的路的问题留给了他。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史铁生一思索就是好几年。
从一般的意义而言,史铁生陷入了这样的悖论:对于他,生存下去就是受苦,而这种受苦如果没有意义,也就失去了生存下去的正当性,不如及早解脱;而要解脱,又必须找到去死的理由,寻求死亡的意义,否则就此放弃生命这一行为本身也就失去了根据。换言之,不解决死的意义,这样的死与无意义的活没有什么两样。可是,死的意义不是容易解决的,它关涉到人生的根本问题。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来说,人就是向死而生的存有。死是存在与非存在的边界。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死是毁灭性的虚无,是人面临的一种无可逃避的、非存在的威胁。死的意义是如此重大:“对于死亡时虚无的预想,赋予了人的生存以其生存的特性。”当然,人受到非存在威胁的还不仅仅是死,另一位存在主义的大师萨特认为还有无意义之威胁(注:蒂利希:《存在与上帝》,刘小枫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中卷),第850、854-862、865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即是说,虽不死,但无意义地活着,依然是非生存。这样,史铁生事实上陷入了更大的悖论:选择死,就是选择非存在,选择活,倘若无意义,也是非存在。那么,剩下的就只有一条路了:活,而且必须活出意义。不过,这只是存在主义的理论推论,而史铁生面对的是更为残酷的生命事实。
据史铁生回忆,在那些思索的日子里,他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他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注:史铁生:《我与地坛》,见《中华散文珍藏本·史铁生卷》,第8—9、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后来,他在另一处也表达了与此相似的意思:“剧本早都写好了,演员的责任就很明确:把戏演好,别的没你什么事。”(注:史铁生《病隙碎笔》,第189、72、69、168、95、10、168、172、166-167、147、96、95、63、96、95、109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史铁生是怎样弄明白的,使他得出了这一达观得有些宿命色彩的结论,而将他从极限情景中拯救出来,决定活下去的?这要看逼迫史铁生思考生死问题的究竟是什么?说穿了,就是残疾。当他选择活下去的时候,实际上他确认了这样一个事实:残疾地活下去是值得的、有意义的。换言之,他为人的残疾找到了正当性根据。
人的残疾是正当的、有价值的、有意义的?是的。因为史铁生从一己肉体的残疾,看出了人、人类的残缺,即根本性局限——人的有限性。
史铁生认为:“残疾,并非残疾人所独有。残疾即残缺、限制、阻障。名为人者,已经是一种限制”(注:史铁生《病隙碎笔》,第189、72、69、168、95、10、168、172、166-167、147、96、95、63、96、95、109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人的残疾即是人的局限”。残疾人的残疾是肉体上的,整个人类的残疾却是与生俱来的残缺,“对某一铁生而言是这样,对所有的人来说也是这样,人所不能者,即是限制,即是残疾,它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注:史铁生《病隙碎笔》,第189、72、69、168、95、10、168、172、166-167、147、96、95、63、96、95、109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人都是残疾人。何以这样说?或者说史铁生的根据是什么?
在史铁生看来,人的出生是不可选择的、不可辩论的偶然性事件,人“只是一具偶然的肉身。所有的肉身都是偶然的肉身,……是那亘古不灭的消息使生命成为可能”(注:史铁生《病隙碎笔》,第189、72、69、168、95、10、168、172、166-167、147、96、95、63、96、95、109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从生存论的角度看,“我们生存的空间有限,我们经历的时间有限”。而残疾的蓦然而至,更使人感受到命运的荒诞。史铁生对人之存在的这种完全的偶然性和尖锐的荒诞性体验,帕斯卡尔曾有过这样的描述:
当我思索我的生命历时之短暂,这生命被以前以后的永恒所吞没,又思索我所占据的空间之渺小……,我被抛进了无限浩翰的空间之中,我对之一无所知,它对我也十分陌生,这时候我会感到恐怖,我为自己生存于此地而不是彼地感到惊骇,因为没有任何理由是在此地而不是在彼地,是在此时而不是在彼时。是谁把我放在此地的?这个地方和这段时间,是根据谁的命令和指示而分配给我的?(注:詹姆斯·C.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下卷),第694、686、638、690、634、619、61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从认识论的层面说,我们的知识永远不可能穷尽外部世界的奥秘,“我们其实永远在主观世界中徘徊。而一切知识都只是在不断地证明着自身的残缺,它们越是广博高妙越是证明这残缺的永恒与深重,它们一再地超越便是一再地证明着自身的无效”(注:史铁生《病隙碎笔》,第189、72、69、168、95、10、168、172、166-167、147、96、95、63、96、95、109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这是人的“智力的绝境——你不可能把矛盾认识完”(注:史铁生:《答自己问》,《写作之夜》,第24、24、30、17、17、18、29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
从行为能力着眼,就像高位截瘫的人不能行走一样,健全的人也不能飞翔。概而言之,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生而为人,终难免苦弱无助,即便是多么英勇无敌,多么厚学博闻,多么风流倜傥,世界还是要以其巨大的神秘置你于无知无能的地位(注:史铁生《病隙碎笔》,第189、72、69、168、95、10、168、172、166-167、147、96、95、63、96、95、109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这样,史铁生实际上就从审视生理上的残疾,上升到了对人的有限性的形而上学的思考:人是有限性的存在。何谓有限性?当代著名的存在主义神学家蒂利希解释说:“受到非存在所限制的存在,是有限性。”非存在又显现为存在之尚未,以及存在之不再。史铁生对人的有限性的上述思考,是颇富洞见的,暗合了蒂利希的理论。蒂利希认为,时间、空间、因果性和实体性都具有存在与非存在这双重性,其中的非存在性是人成为有限性存在的重要因素。时间是本体性质的,它吞噬着它的所造物,使其由盛而衰,归于消亡,人由此产生了“对于不得不死的焦虑”,正是在这种焦虑中,非存在被人从内部体验到了。人“占有空间,也就意味着受制于非存在”,意味着“不拥有任何确定的地位”,意味着“不得不最终丧失每一个地位,并随之而丧失存在本身”。因为人终有一死。因果性的非存在性,对人而言则表现为不拥有“自存性”,即人的存在不是自明的,人存在的原因不在自身,而在之外。“自存性只是上帝才有的特点”,作为有限的人,如海德格尔所言是被抛入存在的。因而“人的存在是偶然的;他自身没有任何必然性”,他是非存在的猎物,“把人抛入生存的那同一种偶然性,也可以把人推出生存”。这也决定了人是从属于偶然事件的实体,也可以说,“它在偶然事件中表现自己”(注:蒂利希:《存在与上帝》,刘小枫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中卷),第850、854-862、865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
三
人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的根本困境。史铁生认为,人有三种根本困境:
第一,人生来注定只能是自己,人生来注定是活在无数他人中间并且无法与他人彻底沟通。这意味着孤独。第二,人生来有欲望,人实现欲望的能力永远赶不上他欲望的能力,这是一个永恒的距离。这意味着痛苦。第三,人生来不想死,可是人生来就是在走向死。这意味着恐惧。(注:史铁生:《自言自语》,《写作之夜》,第51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
孤独、痛苦、恐惧是人生无法根除的苦难。这些苦难是在体性,它们塑造了人,成为人的存在本身,也构成了人的命运。这里的命运,不是一种无意义的宿命,“它是与意义结合在一起的必然性”(注:蒂利希:《存在与上帝》,刘小枫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中卷),第850、854-862、865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在史铁生看来,自觉到人的有限性和苦难的在体性,是人寻找生命的意义的开端,也是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艺术的动力和源泉。换言之,人的残缺和苦难,对于人不仅不是无意义的,而且是意义之源。
生命的意义只能在生命的过程中产生和建构。意识到这一点,就可能从当初重视生命的目的转向重视生命的过程:“惟有过程才是实在”,何不在这必死的路上纵舞欢歌呢?坦然地“把上帝赐予的高山和深渊都接过来,‘乘物以游心’,玩它一路,玩得醉心神迷不绊不羁创造不止灵感纷呈”(注:史铁生:《答自己问》,《写作之夜》,第24、24、30、17、17、18、29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在欢乐中承担苦难,在承担苦难中享受欢乐,在苦难和欢乐的过程中创造生命的意义。只有过程才是对付绝境的办法:
过程!对,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与悲壮。但是,除非你看到了目的的虚无你才能进入这审美的境地,除非你看到了目的的绝望你才能够找到这审美的救助。但这虚无与绝望难道不会使你痛苦吗?是的,除非你为此痛苦,除非这痛苦足够大,大得不可消灭大得不可动摇,除非这样你才能甘心从目的转向过程,从对目的的焦虑转向对过程的关注,除非这样的痛苦与你同在,永远与你同在,你才能够永远欣赏到人类的步伐与舞姿,赞美着生命的呼喊与歌唱,从不屈获得骄傲,从苦难提取幸福,从虚无中创造意义,直到死神和天使一起来接你回去,你依然没有玩够,但你却不惊慌,你知道过程怎么能有个完呢?过程在到处继续,在人间、在天堂、在地狱,过程都是上帝的巧妙设计。(注:史铁生:《好运设计》,见《中华散文珍藏本·史铁生卷》,第5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其次,迫近心魂的自由。外在肉体的残疾,存在时空的有限,好比是一场安排好的戏剧,人是这出剧中的演员。而“一个好演员,必是因其无比丰富的心魂被困于此一肉身,被困于此一境遇,被困于一个时代所有的束缚,所以他/她有着要走出这种种实际的强烈欲望,要在千变万化的角色与境遇中,实现其心魂的自由”(注:史铁生《病隙碎笔》,第189、72、69、168、95、10、168、172、166-167、147、96、95、63、96、95、109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如果说残疾是肉身折磨着精神,孤独、痛苦和恐惧是精神折磨着心魂,那么,受多重磨挫的心魂,必产生冲破肉身与精神囚禁的巨大驱动力,奔赴其自由的境界。
再次,探入艺术的根基。艺术的根基是什么?史铁生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困境”。已有的文化是否成为艺术的根基,取决于它是否为人类造出困境,“惟其造出困境,这才长出文学”,长出艺术(注:史铁生:《随想与反省》,《写作之夜》,第78—79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因为困境是这样一种东西,它让艺术家一来就“掉进了一个有限的皮囊”,他的周围“是隔膜,是限制,是数不尽的墙壁和牢笼,灵魂不堪此重负,于是呼喊,于是求助于艺术,开辟出一处自由的时空以趋向那无限之在和终极意义”,从而使艺术禀有了“美的恒久品质”(注:史铁生《病隙碎笔》,第189、72、69、168、95、10、168、172、166-167、147、96、95、63、96、95、109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就纯文学而论,它所面对的就是“人本的困境”,“譬如对死亡的默想、对生命的沉思,譬如人的欲望和人实现欲望的能力之间的永恒差距,譬如宇宙终归要毁灭,那么人的挣扎奋斗的意义何在等等,这些都是与生俱来的问题,不依社会制度的异同而有无。因此它是超越着制度和阶级,在探索一条属于全人类的路”(注:史铁生:《答自己问》,《写作之夜》,第24、24、30、17、17、18、29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
最后,人的有限性和苦难在体性的澄明,使人不断寻求超越之路。史铁生说:“无缘无故的受苦,才是人的根本处境”,也正是上帝的启示。但“这处境不是依靠革命、科学以及任何方法可以改变的,而是必然逼迫着你向神秘去寻求解释,向墙壁寻求回答,向无穷的过程寻求救助”(注:史铁生:《宿命的写作》,《写作之夜》,第11、8、12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说,世俗生活世界的一切无力解救人的困境,人必须探询一条世俗意义以上的路:超越之路。个人永远都是有限,都是局部,“局部之困苦,无不源于局部之有限,因而局部的欢愉必是朝向那无限之整体的皈依”。所以史铁生说:“只要你注意到了人性的种种丑恶,肉身的种种限制,你就是在谛听或仰望那更为高贵的消息了。”(注:史铁生《病隙碎笔》,第189、72、69、168、95、10、168、172、166-167、147、96、95、63、96、95、109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所以史铁生又说:“人既看见了自身的残缺,也就看见了神的完美,有了对神的敬畏、感恩与赞叹。”(注:史铁生《病隙碎笔》,第189、72、69、168、95、10、168、172、166-167、147、96、95、63、96、95、109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从探询生命意义的方向来看,认识到人的有限性和苦难的在体性,使人向个体自身和生命的内部要意义。史铁生引用刘小枫的话说,人的有限性以及受苦是私人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不是现世社会意义上的,所以根本不干正义的事。为私人的受苦寻求社会或人类的正义,不仅荒唐,而且会制造出更多的恶。个体的不幸及生命的意义只能靠个体自身来解决。正如俄罗斯思想家弗兰克在其《生命的意义》中所说,生命的意义不是给予的,而是被提出来的:
生命的意义不在向外的寻取,而在向内的建立。那意义本非与生俱来,生理的人无缘与之相遇。那意义由精神所提出,也由精神去实现,那便是神性对人性的要求。这要求之下,曾消散于宇宙之无边的生命意义重又聚拢起来,迷失于命运无常的生命意义重又聪慧起来,受困于人之残缺的生命意义终于看见了路。(注:史铁生《病隙碎笔》,第189、72、69、168、95、10、168、172、166-167、147、96、95、63、96、95、109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所以,对探寻生命意义的个体心性而言,史铁生认为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客观真理,而是克尔凯郭尔的主观性真理。
作为存在主义者的克尔凯郭尔不相信所谓的客观反映之说,对理性的客观性大加挞伐,指责其把主体变成了偶然随机的东西,把主体的生存改造成了某种非人格的东西,排除了人的切身体验,否定了人的自由选择与自我决定,从而也就否定了人自己造就自己的能力和事实。纯客观的真理不能认识人类生存的真理,“真理恰恰在于内在性”,“因为,每个人都是一个精神性的存在,对他来说,真理不存在于任何别的东西之中,而存在于亲自运用的自我活动之中”(注:詹姆斯·C.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下卷),第694、686、638、690、634、619、61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真理的这种切己性是说,“我们只有从生存上去体验另一种生存方式,才能理解那种方式”,这就好比马丁·路德所说:“一个人成为神学家,靠的是生活、死亡、受罚,而不是靠理解、阅读、冥想。”(注:詹姆斯·C.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下卷),第694、686、638、690、634、619、61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人的有限性和苦难的在体性,催迫人向生命的内部要意义,寻找主观性真理,其实质是“要找到一个对我来说是真实的真理,要找到我可以为之生为之死的观念”(注:詹姆斯·C.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下卷),第694、686、638、690、634、619、61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这样的主观性真理,虽然“不存在供人们建立其合法性以及使其合法的任何客观准则”,但却“是发扬生命的难以捉摸、微妙莫测和不肯定性的依据”(注:史铁生《病隙碎笔》,第189、72、69、168、95、10、168、172、166-167、147、96、95、63、96、95、109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在长篇小说《务虚笔记》中,“我”对主观性真理有过一段生存现象学式的还原与阐释。有一天我知道了“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一个试图知道全体的部分,不可能逃出自我指称的限制。由此,我获得了更多想象的自由,我的冥思也开始澄明。当我要“回答世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样的问题,我发现:“一个不可逃脱的限制就是,我只能是我。事实上我只能回答,世界对我来说开始于何时。”比如,“我”生于1951年,但它对于“我”只是一个传说。因为它对“我”来说是一片空白,是零,是完全的虚无。只有到了1955年的某个周末之后,世界对“我”才开始存在,才渐渐有了意义。据说生“我”那天下着大雪,从未有过的大雪,可是,“我”总是用1956年的雪去想像1951年的雪,或者说1956年的雪,才使1951年的雪有了形象,有了印象,雪对于“我”也才开始存在。“因为我找不到非我的世界,永远都不可能找到。所以世界不可能不是对我来说的世界”(注:史铁生:《务虚笔记》,第84—8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
自觉到人的存在的有限性和苦难的在体性,对于史铁生,不仅形成了关切生命过程、迫近心灵自由、深入艺术根基和寻求超越道路这样的生命意义结构,确立了在生命内部探询主观性真理的意义叩问方向,而且使史铁生具有了谦卑的伦理心态,站出人自身反观人的能力和处身位置,在主体内部产生了“我”与“史铁生”这一主客体交互的对话结构,从而对个体心性和人的存在的勘探,抵达了理性不能照亮的“黑夜”。
四
有必要再一次提到克尔凯郭尔,不只因为他是存在主义哲学家,而是因为他关于绝望与拯救的论述太过切合史铁生的心路历程。克氏认为绝望可以导致一种精神上的僵硬和死亡,也可以有助于唤醒一个人,使他明白自己永恒的正当性。他甚至断言,除了经历绝望之外,是不存在任何拯救的:
我劝告你要绝望……不是作为一种安慰,不是作为一种你要继续留在其中的状态,而是作为一种需要灵魂之全部力量、严肃和专注的行为……。一个人倘若没有尝过绝望的痛苦,他也就错失了生命的意义。(注:詹姆斯·C.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下卷),第694、686、638、690、634、619、61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绝对地绝望,就是挣脱有限的观察角度对自己的束缚,因为,“当一个决意要(绝对地)绝望的时候,他也就选择了绝望所选择的东西,即处于永恒正当性之中的自身”(注:詹姆斯·C.利文斯顿:《现代基督教思想》(下卷),第694、686、638、690、634、619、61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史铁生所处的极限境遇,曾经使他深陷绝望的深渊,思想情感无数次行走在自杀的边缘。但他终于从个体肉身的残疾,看到了人类的残缺和有限性,产生了寻求生命意义的内在动力,明确了意义寻求的方向、伦理态度,以及在个体内部展开主客体交互对话的意义询问方式。绝望的痛苦,催他上路,去求索生命的永恒的正当性。
到此这样说一点也不为过:史铁生是从个体的生存体验,走向形上的存在之思,还从存在之思叩问超越之路。简言之,他是从经验的生存,走向先验的存在,并朝着超验的神在跳跃。
自觉到生命意义的重要固然关键,但意义不会自动呈现。从存在的此岸世界,到达神在的彼岸世界,需要过渡的桥梁,或者说中介。这个桥梁或中介,对于史铁生而言就是写作。
写作,是对史铁生的救赎。在《我与地坛》中,史铁生思考了三个要命的问题:要不要去死?为什么活?干嘛要写作?在这里,写作问题是与生死问题并列的同等重要的问题。当死的问题被悬置(解决)以后,写作与活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了。那么,写作与活的关系又如何呢?史铁生否定了为了写作而活着的说法,认为“只是因为我活着,我才不得不写作”。抑或是因为还想活着,所以才写作。写作是活下去的一条路:“写,真是个办法,是条条绝路之后的一条路。”(注:史铁生:《宿命的写作》,《写作之夜》,第11、8、12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 在另一处,史铁生在回答“人为什么写作”时,更是直白地说:“为了不至于自杀。”(注:史铁生:《答自己问》,《写作之夜》,第24、24、30、17、17、18、29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
换个提问的角度:为何写作拯救了史铁生?为何写作使他不至于自杀?一个直接的理由是,写作“油然地通向着安静”,通向灵魂的安宁(注:史铁生:《宿命的写作》,《写作之夜》,第11、8、12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在史铁生残疾不久的日子里,他被命运击昏了头,脾气坏到极点,经常像发了疯一样,这时,写作使他浮躁凌厉之心,趋于平静。后来史铁生回忆说:“我其实未必合适当作家,只不过命运把我弄到这一条(近似的)路上来了。左右苍茫时,总也得有条路走,这路又不能再用腿去趟,便用笔去找。而这样的找,后来发现利于此一铁生,利于世间一颗最为躁动的心走向宁静”。“写作救了史铁生和我”。在这个意义上说,“写作为生是一件被逼无奈的事”(注:史铁生《病隙碎笔》,第189、72、69、168、95、10、168、172、166-167、147、96、95、63、96、95、109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当然,有一个推论也是可以成立的:我们知道,史铁生是因着生命的意义而活下去的,既然写作可以让他活下去,那说明写作于他而言,是可以产生意义的。对此,史铁生如此说:“写作便是要为活着找到可靠的理由,终于找不到就难免自杀或还不如自杀”(注:史铁生:《答自己问》,《写作之夜》,第24、24、30、17、17、18、29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写作就是要为生存找一个至一万个精神上的理由,以便生活不只是一个生物过程,更是一个充实、旺盛、快乐和镇静的精神过程”(注:史铁生:《答自己问》,《写作之夜》,第24、24、30、17、17、18、29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写作在这里成了寻找,成了一个在寻找中精神不断攀升,生命的意义不断涌现的过程。
问题是,史铁生处身于一个绝对价值缺席的时代,他借以救赎、借以寻找生命意义的写作所面对的是“世界黑夜”,这构成史铁生无法逃避的又一极限困境。它的困难程度远远超过了肉身的残疾:他是人在自觉到人的有限性之后,却无法突围,难以超越,趋向无限的一种深渊困境。史铁生把这一困境命名为“写作之夜”。
史铁生曾经这样描述这个时代:“神约”已然放弃,人性解放成魔性,而“魔性一经有了人性作招牌,摩菲斯特宏图大展正是一路势如破竹了”;人虽然放逐了诸神,“可人造为神的现代迷信并不绝迹”;新的神祗——“一切以商品、利润为号召的主义”——正在各处显身(注:史铁生《病隙碎笔》,第189、72、69、168、95、10、168、172、166-167、147、96、95、63、96、95、109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人们追求的只是对物质与权力的渴慕,“从不问灵魂在暗夜里怎样号啕,从不知精神在太阳底下如何陷入迷途,从不见人类是同一支大军,他们在广袤的大地上悲壮地行进被围困重重,从不想这颗人类居住的星球在荒凉的宇宙中应该闪耀怎样的光彩”(注:史铁生:《答自己问》,《写作之夜》,第24、24、30、17、17、18、29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史铁生描述的这个时代的特征,正是海德格尔笔下的“世界黑夜的时代”的写照。在海德格尔那里,随着赫拉克斯(Herakles)、狄奥尼索斯(Dionysos)和耶稣基督(Christus)这个“三位一体”弃世而去,世界时代的夜晚便趋于黑夜,世界黑夜便弥漫着它的黑暗。上帝的离去意味着:“神性之光辉也已经在世界历史中黯然熄灭。世界黑夜的时代是贫困的时代,因为它一味地变得更加贫困。它已经变得如此贫困,以致于它不再能察觉到上帝之缺席本身了。”(注:海德格尔:《诗人何为?》,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第407—408、408-410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
史铁生的特殊困难还在于,他要在这个失去了意义根基的世界,通过写作找回意义。这如何可能?这样,史铁生在写作之夜对生命意义的寻求,只能是“吟唱着去摸索远逝诸神之踪迹”,“从而为其终有一死的同类追寻那通达转向的道路”;只能是在黑夜的时代里“道说神圣”(注:海德格尔:《诗人何为?》,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第407—408、408-410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只能是对上帝的重临和诸神的返回发出泣泪的呼告。
因此,史铁生写作所面对的黑夜,“不是外部世界的黑夜,而是内在心流的黑夜”(注:史铁生《病隙碎笔》,第189、72、69、168、95、10、168、172、166-167、147、96、95、63、96、95、109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心灵的黑夜不只在黑夜,也在白昼的狂欢之中,而“写作不过是为心魂寻一条活路”。因为,在史铁生看来,“唯心神的黑夜,才开出生命的广阔,才通向精神的家园”(注:史铁生《病隙碎笔》,第189、72、69、168、95、10、168、172、166-167、147、96、95、63、96、95、109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才通达“诗意地栖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