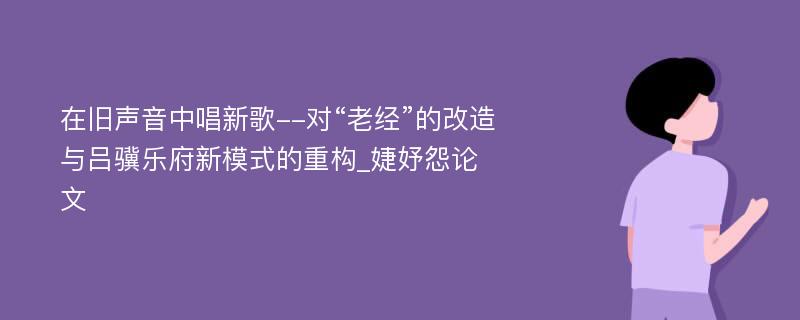
咏新曲于故声——改造旧经典、再造新范型的陆机乐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乐府论文,经典论文,咏新曲论文,新范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8)03-0078-08
明清以降,许学夷、王夫之、陈祚明、黄子云、沈德潜等学者对陆机诗歌作出了相似的贬抑:以模拟为主,“性情不出”。例如,陈祚明曰:“士衡束身奉古,亦步亦趋,在法必安,选言亦雅,思无越畔,语无溢幅。造情既浅,抒响不高。拟古乐府稍见萧森,追步《十九首》便伤平浅,至于述志赠答皆不及情。夫破家之余,辞家远宦,若以流离为悲,则悲有千条,倘怀甄录之信,亦幸逢一旦,哀乐两柄易得淋漓,乃敷旨浅庸,性情不出。”① 在20世纪以来的陆机诗歌研究中,特别是在陆机乐府研究中,这种负面看法一直占据着上风。问题在于既然陆机诗歌以模拟为主、“性情不出”,为何会被钟嵘誉为“太康之英”、被唐太宗推为“百代文宗”?
通常我们把乐府分为民间乐府和文人乐府。陆机乐府属于文人乐府中的一个特殊的类型——士族文人乐府。所谓士族文人乐府乃是指在两晋南朝时期出现的由士族文人所创作的乐府诗,此类作品在承继了前代乐府诗中的贵族色彩的基础上,表现出鲜明的士族意识。“太康之英”陆机是士族文人乐府的开创者和集大成者,陆机乐府的出现标志着士族文人乐府的诞生与成熟。陆机乐府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旧经典在形式上加以绮靡化的改造;二是对贵族物质享乐生活的展现与反思;三是带有士族印记的功业追求。这三点也成为陆机之后土族文人乐府的重要特征。
一
陆机《遂志赋》云:“拟遗迹于成规,咏新曲于故声。”他的乐府中既有模拟之作,也有新曲创作。并不是题目中标有“拟”字就一定是模拟乐府,简单地说,模拟乐府乃是指文人用乐府旧题完成的敷衍古辞之义的作品。应当承认,陆机现存乐府中既有“亦步亦趋”者,也有“性情不出”者。所谓“亦步亦趋”之作,不仅指主题与原作相同,字句也与原作基本对应。按照这个标准来看,陆机“亦步亦趋”的作品主要集中在《拟古十二首》中,乐府中“亦步亦趋”之作数量有限,其中最典型的当推《驾言出北阙行》,此诗虽然与阮瑀的《驾出北郭门行》题目相近,内容却是对《古诗十九首》中《驱车上东门行》一诗的模拟。钟嵘《诗品》说:“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钟嵘明明说拟诗十四首,不知何故《文选》中却只选了十二首。有学者认为“《驾言出北阙行》必为十四首拟诗之一甚明”②。陆机乐府中更多的是题旨与原作相同但字句并不对应的模拟之作。例如:《班婕妤》,拟班婕妤的《婕妤怨》;《苦寒行》,拟曹操的《苦寒行》;《燕歌行》,拟曹丕的《燕歌行》二首;《塘上行》,拟曹丕甄夫人的《塘上行》;《门有车马客行》,拟曹植的《门有万里客行》;《从军行》,拟王粲《从军行》;《饮马长城窟行》,拟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这些作品就是后人眼里的“性情不出”之作。
既然陆机之诗具有“亦步亦趋”、“性情不出”之弊,为何钟嵘《诗品》要誉其模拟诗为“五言之警策者”?王瑶先生在分析古代诗人为何写作模拟之作时指出:“他们为什么喜欢拟作别人的作品呢?因为这本来是一种主要的学习属文的方法,正如我们现在的临帖学书一样。前人的诗文是标准的范本,要用心地从里面揣摩,模仿,以求得其神似。”他还说:“这种风气既盛,作者也想在同一类的题材上,尝试着与前人一较短长,所以拟作的风气便越盛了。”③ 具体到陆机诗歌来看,这些所谓的“亦步亦趋”、“性情不出”之作似乎并不是“临帖学书”阶段的产物,倒是与“与前人一较短长”的说法比较接近。只是,这样的说法还不够具体。我们认为:陆机热衷于模拟前人之作的动机乃在于有意用士族的审美意识去改造那些被视为标准的范本。
陆机对旧经典的改造主要表现为对士族艺术趣味的张扬。我们知道,乐府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民间乐府到文人乐府的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乐府歌词从质朴走向华丽,描写从简单走向繁复,风格从天然走向缛绣。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人物值得特别关注,一个是曹丕,一个是陆机。从理论上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诗赋欲丽”的主张,从创作上看,正如沈德潜所说:“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古诗源》卷五)曹丕诗歌中不仅出现了“殊美赡可玩,始见其工”(钟嵘《诗品》)的诗篇,更重要的是他以抒情性代替了写实性,从对社会现实的临摹进入到对文人心灵世界的展示,以深邃的哲思、哀婉忧伤的情调使建安诗歌的内涵更为丰富。到了太康时代,陆机在《文赋》中进一步明确提出“诗缘情而绮靡”的观点。在陆机的理论体系中,“诗缘情而绮靡”不仅是诗歌创作的纲领,也是士族诗歌的重要标准。陆机不仅按照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也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前人。在他看来,前代乐府和古诗中的典范之作缘情固缘情矣,而绮靡则未必。所以他要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去改造昔日的范本,使之符合自己心目中的范型。可以说,是曹丕曹植兄弟和邺下诸子把民间乐府引向文人乐府之路,而陆机等太康诗人则进一步把文人乐府导入了士族文人乐府之途。
何为“绮靡”?陆机《文赋》说:“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藻思绮合,清丽芊眠。炳若缛绣,凄若繁弦。”以上语句当是对“绮靡”的具体解析。结合陆机的诗歌创作来看,所谓的“绮靡”无非包括:文辞华丽、语句对偶、词语雕饰、描写繁复、结构严整等特征。《汉书·艺文志》说“(汉乐府)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建安时代,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等和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诗篇都保持了汉乐府的叙事性和质朴本色。而陆机拟乐府则放弃了汉乐府的叙事性,加强了诗歌的“绮靡”程度。例如,郭茂倩《乐府诗集》卷38《饮马长城窟行》引《乐府解题》曰:“古词,伤良人游荡不归,或云蔡邕之辞。若魏陈琳辞云:‘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则言秦人苦长城之役也。”④ 陈琳《饮马长城窟行》以“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开始,先写长城吏与太原卒之间的对话,继而用“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表现在长城边太原卒只是其中的缩影。最后用边城健少劝内舍妻子嫁人的悲惨遭遇,揭露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的现状。全诗着眼于小人物的命运,古朴自然。陆机《饮马长城窟行》云:“驱马陟阴山,山高马不前。……将遵甘陈迹,收功单于旃。振旅劳归士,受爵藁街传。”陆诗改变了陈诗所采用的叙事方式,也改变了陈诗所采用的平民视角,陆机站在将帅的角度写边塞军旅生活,充满了对建功立业的渴望,词语比旧作明显华美绮丽。其实,曹丕诗歌中已经出现了一些“殊美赡可玩”之作,曹植诗歌更是达到了“骨气奇高,辞彩华茂”的高度。陆机模拟之作从曹丕、曹植乐府中吸取了华丽的成分,文辞愈加委婉曲折,描写日益繁复,对偶更加工稳,人工痕迹更加明显。较之曹丕曹植,陆机在华丽精致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应该说明,陆机诗歌中的“绮靡”化,不是仅仅体现在模拟之作中,也体现在非模拟诗歌中;不是仅仅体现在仕宦洛阳之前的诗歌创作中,也体现在仕宦洛阳之后的诗歌创作中。《文选·文赋》李善注引臧荣绪曰:“天才绮练,当时独绝。新声妙句,系踪张蔡。”许学夷《诗源辨体》卷五曰:“五言自士衡至灵运,体尽俳偶,语尽雕刻,不能尽举。”显然,陆机诗歌具有“绮靡”化倾向得到了后人一致的认同。“自士衡至灵运”正是士族文人乐府的兴盛期,俳偶与雕刻也是士族文人乐府的共同特点。
后人说这些作品“性情不出”,是指它们没有直接传达出诗人自己的身世感慨,但作者在前人广泛的题材中选择自己所要模拟的对象之时,并不是一种完全无意识的行为,诗人的选择和模拟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曲折地透露出自己的性情。在陆机的拟作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诗人的失落感和孤独感。他能够悉心模拟《古诗十九首》中的大部分作品,它们“文温以丽,意悲而远”的风格无疑是感染陆机的重要原因。读陆机拟乐府,我们会看到他非常关注失意的女性。其《班婕妤》云:“婕妤去辞宠,淹留终不见。寄情在玉阶,托意惟团扇。春苔暗阶除,秋草芜高殿。黄昏履綦绝,愁来空雨面。”郭茂倩《乐府诗集》卷43《婕妤怨》引《乐府解题》曰:“《婕妤怨》者,为汉成帝班婕妤作也。婕妤,徐令彪之姑,况之女。美而能文,初为帝所宠爱。后幸赵飞燕姊弟,冠于后宫。婕妤自知见薄,乃退居东宫,作赋及纨扇诗以自伤悼。后人伤之而为《婕妤怨》也。”⑤ 陆机《塘上行》云:“……男欢智倾愚,女爱衰避妍。不惜微躯退,但惧苍蝇前。愿君广末光,照妾薄暮年。”郭茂倩《乐府诗集》卷35《塘上行》引《乐府解题》曰:“前志云:晋乐奏魏武帝《蒲生篇》,而诸集录皆言其词文帝甄后所作,叹以谗诉见弃,犹幸得新好,不遗故恶焉。若晋陆机‘江蓠生幽渚’,言妇人衰老失宠,行于塘上而为此歌,与古辞同意。”⑥ 《燕歌行》二首是曹丕诗歌的压卷之作,郭茂倩《乐府诗集》卷32曹丕《燕歌行七解》云:“《乐府解题》曰:‘晋乐奏魏文帝秋风别日二曲,言时序迁换,行役不归,妇人怨旷无所诉也。’”⑦ 以上诗歌中涉及的女性皆美丽而善良,但她们命运多乖,处境维艰。出身高贵、才华横溢而又经历了亡国之痛、仕途坎坷的陆机对她们的不幸命运自然会产生同病相怜式的同情。
同时,陆机还时常借助征人的苦辛来传达自己的命运。其《从军行》云:“苦哉远征人,飘飘穷四遐。南陟五岭巅,北戍长城阿。……苦哉远征人,拊心悲如何!”《苦寒行》云:“北游幽朔城,凉野多险艰。……剧哉行役人,慊慊恒苦寒。”陆机纵然没有诗中所写的军旅生活和行役之苦,但他有丧国亡家的经历,他完全能够体味到远征人和行役人内心的苦楚。至于陆机《门有车马客行》中所写的:“拊膺携客泣,掩泪叙温凉。借问邦族间,恻怆论存亡。亲友多零落,旧齿皆凋丧。市朝互迁易,城阙或丘荒。坟垄日月多,松柏郁茫茫。”很容易会让读者联想到陆氏家族在时代大潮中的起落变迁,也能够联想到陆机对家乡对亲人的深切思念。
大量写作模拟之作,这是士族诗人的嗜好,也是士族文人乐府的重要特征。对前人作品如此大规模的模拟在陆机之前还没有出现过,陆机是大力模拟乐府的第一人。因为陆机的写作和倡导,模拟诗也成为诗歌中的一种重要类型。在六朝时代,这个类型曾经非常流行。这些在明清学者和今人眼里的“亦步亦趋、性情不出”之作,在陆机自己看来并不是纯粹的模拟,而是对旧范本的改造,其中蕴含着士族的思想意识与审美情趣。《晋书·陆机传》云:“至太康末,与弟云俱入洛,造太常张华。华素重其名,如旧相识,曰‘伐吴之役,利获二俊。’”《文选》注引臧荣绪《晋书》云:“机流誉京华,声溢四表。”据此判断,吴平之后,在华亭闭门读书时期的陆机,模拟了许多乐府和古诗,他自己虽然尚未入仕洛阳,但他对旧范本的改造获得了成功,得到京华和北方诗坛的承认,成为引领当时时代潮流的新声。《南史·刘烁传》载:“(刘烁)有文才,未弱冠,拟古三十余首,时人以为亚迹陆机。”看来,陆机的模拟之作在两晋南朝成为贵族文人们遵奉的典范。当时的批评家大都肯定了“绮靡”在诗史发展史上的必要性。除了钟嵘把陆机的模拟之作看作“五言之警策者”之外,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也说:“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萧统《文选序》说:“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刘勰既指出陆机诗文有繁琐之弊,但也对其才华给予了肯定,《文心雕龙·熔裁》曰:“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文心雕龙·乐府》曰:“子建士衡,咸有佳篇。”从这个角度看,陆机改造旧范本的目的达到了,他的作品成为后人特别是士族诗人所仿效的样板。
二
陆机在改造旧范本的同时,也在积极创作直接表现士族意识的新典范。除了继续保持诗歌形式上的“绮靡”之外,新典范在内容方面主要表现为对贵族物质生活方式的描绘、反思和对光大父祖勋业的执著追求。
陆机热衷于描写贵族生活既与时代因素相关,也与他自己的贵族家庭出身密不可分。从《晋书》和《世说新语》等记载魏晋故事的典籍中,可以窥探到奢靡享乐风气在西晋社会肆行程度。陆机出生于东吴最大的士族家庭,早年生活豪奢的程度可想而知。平吴之初,陆机的家族受到了重创。但西晋统治者对南方大族并未采取压制措施,没有没收他们的财产。据《晋书·陆喜传》记载,太康中武帝下诏征召吴尚书陆喜等人“随才授用”。陆机家族固然已经今非昔比,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陆机兄弟依然过着衣食无忧的贵公子生活。据《晋书·戴若思传》记载陆机入洛时“船装甚盛”引来了强盗的青睐。进入北方后,陆机有条件时常出入于达官贵人的府第,有机会接触声色犬马的生活。
陆机乐府中时常会流露出这样的情感:因为体悟到时光易逝,人生短促,从而决定放纵自己,享受人生。这种情感在先秦诗歌中还很少见,一直到了汉乐府和汉魏古诗中才日渐成为最常见的诗歌题材之一。《诗经》中有部分公卿列士们的献诗,其中既有对贵族糜烂生活的讥刺,也有对符合礼制的宴享生活的赞美。《小雅》中的《鹿鸣》、《鱼丽》等诗写到了贵族们的饮宴聚会,《车攻》、《吉日》等诗描绘了王室的田猎活动。《诗经·唐风·蟋蟀》在及时行乐与勤勉奋斗之间展开了思考,诗中既有“今我不乐,日月其除”的放纵之想;也有“好乐无荒,良士瞿瞿”的自我节制。《毛诗序》评曰:“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欲其及时以礼自娱乐也。”此诗是否为晋僖公而发,今天已经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地说本诗是对“中礼”与“娱乐”之关系的理性思考。实际上,《诗经》中贵族文人的美刺之作皆以是否符合“礼”作为评价的标准。屈原出身于楚国高级贵族家庭,《楚辞》中包含一定的贵族色彩,但屈原作品中并没有宣扬及时行乐的思想。两汉时代,散体大赋、乐府和古诗中都有再现宫廷生活和贵族生活的作品。汉乐府《怨诗行》云:“天道悠且长,人命一何促。百年未几时,奄若风吹烛。……当须荡中情,游心恣所欲。”此诗和《古诗十九首》中的《驱车上东门》、《生年不满百》一样,旨在宣扬享乐主义的人生态度。汉乐府中的《鸡鸣》、《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三首诗中,作者皆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描述贵族家庭生活的。建安后期,曹丕兄弟和邺下诸子一起创作了一些游宴聚会、酬唱应答的作品。曹丕在《芙蓉池作诗》、《孟津诗》等作品中透露出纵情任性的习气。曹植的《名都篇》、《闺情》等诗写他早期的享乐生活,单纯读这类诗,给人以“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八首》)的印象。
在现实生活中,陆机是一个喜欢、欣赏奢华生活的人。其《吴王郎中时从梁陈作诗》云:“玄冕无丑士,冶服使我妍。轻剑拂鞶厉,长缨丽且鲜。”玄冕冶服让他津津乐道,久久难忘。太康老诗人张华身居高位,忧心世俗,写有《轻薄篇》一诗讽刺贵族的骄奢淫逸的生活。与张华不同,面对贵族们纸醉金迷的享乐生活中,陆机不仅不是一个批判者,反而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陆机的《短歌行》云:“置酒高堂,悲歌临觞。人生几何,逝如朝霜。时无重至,华不再扬。苹以春晖,兰以秋芳。来日苦短,去日苦长。今我不乐,蟋蟀在房。乐以会兴,悲以别章。岂曰无感,忧为子忘。我酒既旨,我肴既臧。短歌可咏,长夜无荒。”郭茂倩《乐府诗集》卷30《短歌行》引《乐府解题》曰:“《短歌行》,魏武帝‘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晋陆机‘置酒高堂,悲歌临觞’,皆言当及时为乐也。”⑧ 显然,作者对曹操的《短歌行》的评价是一种误读。曹诗虽然写到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可以解忧,唯有杜康”,但曹操的忧伤不在于为了个人的享乐,而是忧惧时光易逝一统天下的壮志难以实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明完成统一大业乃是曹操终生的追求。陆机的诗中缺乏曹操那样的天下意识,他只是沉醉在“长夜无荒”的享乐生活当中。这样的享乐思想和行为反复出现在陆机的乐府诗中。其《饮酒乐》云:“蒲萄四时芳醇,琉璃千钟旧宾。夜饮舞迟销烛,朝醒弦促催人。”其《顺东西门行》云:“桑枢戒,蟋蟀鸣,我今不乐岁聿征。迨未暮,及时平,置酒高堂宴友生。激朗笛,弹哀筝,取乐今日尽欢情。”其《董桃行》云:“聊乐永日自怡,赍此遗情何之。人生居世为安,岂若及时为欢。”这时看不出陆机和那些沉溺于享乐者有多少区别。
早在建安时代,作为有抱负的士人,曹丕曹植兄弟没有在轻歌妙舞、美酒佳肴中迷失自我,他们能够透过享乐生活体会到深刻的悲凉。曹丕的长篇乐府《大墙上蒿行》细致地表现出他不安于物质享乐、执著探求人生真谛的思绪。曹植早期诗歌多有对生命悲剧的体认,深重的悲叹发自于一个春风得意的少年王子之口,不能不令人惊讶。和曹丕曹植一样,陆机也有自己的政治追求,在他的乐府中同样有对荣华不久的警觉,有对享乐生活的理性反思。陆机《君子有所思行》云:“命驾登北山,延伫望城郭。廛里一何盛,街巷纷漠漠。甲第崇高闼,洞房结阿阁。曲池何湛湛,清川带华薄。邃宇列绮窗,兰室接罗幕。淑貌色斯升,哀音承颜作。人生盛行迈,容华随年落。善哉膏粱士,营生奥且博。宴安消灵根,酰毒不可恪。无以肉食资,取笑藜与藿。”郭茂倩《乐府诗集》卷61《君子有所思行》引《乐府解题》曰:“《君子有所思行》,晋陆机云:‘命驾登北山。’宋鲍照云:‘西上登雀台。’梁沈约云:‘晨策终南首。’其旨言雕室丽色,不足为久欢,宴安酰毒,满盈所宜敬忌,与《君子行》异也。”⑨ 这些诗句让我们看到,即使是在享乐生活中陆机的心中还有另一个痛苦的世界。酒色生活可以暂时麻醉诗人的神经,却不能让志士彻底消解忧愁、忘怀现实世界。
与那些纯粹的酒色之徒不同,陆机乐府中还渗透着文人雅士的审美情趣。其《日出东南隅行》是一首值得特别关注的作品。郭茂倩《乐府诗集》卷28《日出东南隅行》引《乐府解题》曰:“古辞言罗敷采桑,为使君所邀,盛夸其夫为侍中郎以拒之。”郭茂倩认为:“若陆机‘扶桑升朝晖’,但歌美人好合,与古词始同而末异。”⑩ 这是一篇美人赋,以前的诗歌中的美女都是个体形象,陆机此诗第一次描写了美女的群体形象。诗人首先写美女出现于高台上浚房中,通过美目、娥眉、鲜肤、巧笑描绘了她们的秀色,继而描绘了她们华美的装束。接着写美女们来到洛水之滨游春,同时进行了盛大的歌舞表演,“赴曲迅惊鸿,蹈节如集鸾”等句写美女集体舞蹈动作生动传神,如在目前。全诗既有静态的美,也有动态的美。诗中没有写到士人与美女之间的情感交流,只有士人对美景美色的保持一定情感距离的观赏。
陆机另外一些诗歌着意展现大自然的美,诗人体会到了天人合一般的乐趣。其《棹歌行》云:“迟迟暮春日,天气柔且嘉。元吉隆初已,濯秽游黄河。龙舟浮鹢首,羽旗垂藻葩。乘风宣飞景,逍遥戏中波。名讴激清唱,榜人纵棹歌。投纶沉洪川,飞缴入紫霞。”在暮春时节,诗人和朋友们在黄河中游玩。郭茂倩《乐府诗集》卷40《棹歌行》引《乐府解题》曰:“晋乐,奏魏明帝辞云‘王者布大化’,备言平吴之勋。若晋陆机‘迟迟春欲暮’,梁简文帝‘妾住在湘川’,但言乘舟鼓棹而已。”(11) 其《董桃行》也写道:“和风习习薄林,柔条布叶垂阴。鸣鸠拂羽相寻,仓鹒喈喈弄音。”其《悲哉行》云:“和风飞清响,鲜云垂薄阴。蕙草饶淑气,时鸟多好音。翩翩鸣鸠羽,喈喈仓庚吟。”……人与自然融合为一体,大自然给诗人带来了精神上的愉悦,这样的诗篇直接启迪了晋宋之际的山水诗。然而,大自然带给诗人的并不总是欢快的体验,有时候诗人从中感受到沉重的悲伤。其《豫章行》云:“泛舟清川渚,遥望高山阴。……寄世将几何,日昃无停阴。前路既已多,后途随年侵。促促薄暮景,亹亹鲜克禁。曷为复以兹,曾是怀苦心。远节婴物浅,近情能不深。行矣保嘉福,景绝继以音。”郭茂倩《乐府诗集》卷34《豫章行》引《乐府解题》曰:“陆机‘泛舟清川渚’,谢灵运‘出宿告密亲’,皆伤离别,言寿短景驰,容华不久。”(12) 其《悲哉行》云:“游客芳春林,春芳伤客心。……伤哉客游士,忧思一何深。目感随气草,耳悲咏时禽。寤寐多远念,缅然若飞沉。愿托归风响,寄言遗所钦。”郭茂倩《乐府诗集》卷62《悲哉行》引《乐府解题》曰:“陆机云:‘游客芳春林。’谢惠连云:‘羁人感淑节。’皆言客游感物忧思而作也。”(13) 《上留田行》云:“嗟行人之蔼蔼,骏马陟原风驰。轻舟泛川雷迈,寒往暑来相寻。零雪霏霏集宇,悲风徘徊入襟。岁华冉冉方除,我思缠绵未纾,感时悼逝凄如。”当此之时,诗人陷入深切的忧愁中难以解脱。
概之,陆机乐府中,有一部分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贵族文人的物质生活状态,其中有对贵族及时行乐生活的再现,也有区别于世俗声色享乐的高雅情趣,还有诗人对享乐生活的深切反思。
三
陆机《君子行》云:“天道夷且简,人道险而难。休咎相乘蹑,翻覆若波澜。去疾苦不远,疑似实生患。……近情苦自信,君子防未然。”显然,他对人心的奸险、仕途的险恶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出处进退的问题上,他始终存在着矛盾心理。其《折杨柳行》云:“人生固已短,出处鲜为谐。慷慨惟昔人,兴此千载怀。”如上所述,有时他也有“岂若及时为欢”的享乐主义思绪,但是,享乐生活并不是陆机生活的全部,甚至不是陆机生活的主体。努力进取、建功立业、耀祖光宗才是他生命中的主旋律。面对险而难的人世,面对进退出处的矛盾,陆机坚定地选择了积极入世的人生之路。正如徐公持先生所说:“陆机的家世出身,予他一生以绝大影响。……而陆机一生的行止,也显示出他是西晋文士中政治追求最为执着、功名欲念最为强烈的人物之一。”(14) 刘熙载说:“士衡乐府,金石之音,风云之气,能令读者惊心动魄。虽子建乐府,且不得专美于前,他何论焉?”(15) 可以肯定,并不是陆机所有的作品都具有“金石之音,风云之气”。在陆机乐府中最具有“金石之音,风云之气”的作品无疑是那些与建功立业之追求相关的诗篇。
陆机《月重轮行》云:“功名不勖之,善哉古人,扬声敷闻九服,身名流何穆。既自才难,既嘉运,亦易愆。倪仰行老,存没将何观?志士慷慨独长叹,独长叹。”《日重光行》云:“日重光,但惆怅才志。日重光,身没之后无遗名。”据姜亮夫先生考证,以上两篇作品创作于入洛前。他说:“(《月重轮行》)文中言志士慷慨,独自长叹,盖寄意之作也。”“(《日重光行》)文中旨意,与上首差近,而情调益迫切……全诗皆叹逝之不可回,没身无遗名,然命生有分,但怅己之才志如何,其意象情形,皆唱盛年不得遇也。”(16) 陆机的《秋胡行》直接说:“生亦何惜,功名所勤。”这些作品也许不见得具有“金石之音,风云之气”,但强烈的功业意识非常明显。功业意识贯穿于陆机一生的诗篇中,其《长歌行》云:“逝矣经天日,悲哉带地川。寸阴无停晷,尺波徒自旋。年往迅劲矢,时来亮急弦。远期鲜克及,盈数固希全。容华夙夜零,体泽坐自捐。兹物苟难停,吾寿安得延。倪仰逝将过,倏忽几何间。慷慨亦焉诉,天道良自然。但恨功名薄,竹帛无所宣。迨及岁未暮,长歌乘我闲。”可以看出,陆机在抒发其建功立业之志时,时常伴随着感时悼逝的悲凉。其《上留田行》中云:“我思缠绵未纾,感时悼逝凄如。”其《董桃行》中亦云:“感时悼逝伤心,日月相追周旋。”因为人生短促,从而试图及时行乐;但诗人深知荣华不久、满盈自损,何况诗人还身负光宗耀祖重任,因此他不会沉溺于享乐生活中;诗人积极投身建功立业的大业当中,但人生苦短,功业难建,又让诗人陷入更深的痛苦之中。感时悼逝、及时行乐、建功立业三者互相交织纠缠,组合成一张无形的网,将诗人困于网中。这样的痛苦,这样的矛盾,这样的困境,反映在诗歌中就使陆机诗歌增加了一份悲凉和深沉。
在陆机之前,三曹等建安诗人采用乐府形式表述了他们治平天下、建功立业的抱负。特别是曹植,无论是早期深受曹操宠爱、踌躇满志的时候,还是后期名为藩王、实为囚徒的时候,他都以建功立业为人生的第一追求。表面看来,陆机和曹氏父子一样都具有强烈的功业追求,但实际上,曹氏父子的功业追求中所蕴含的主要是天下意识,而陆机的功业追求中掺杂着太多的士族意识、家族意识。诗人所倡扬的到底是天下意识还是士族意识、家族意识,这是判断是否是士族文人乐府的重要标志。陆机的士族意识在《吴趋行》等诗中表现得甚为明显,《吴趋行》在描写了吴国的风物和历史之后,诗人热情地歌颂了吴地的门阀士族:“楚妃且勿叹,齐娥且莫讴。四坐并清听,听我歌吴趋。……属城咸有士,吴邑最为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实名家。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礼让何济济,流化自滂沱。淑美难穷纪,商榷为此歌。”《世说新语·赏誉》云:“吴四姓,旧目云:张文朱武陆忠顾厚。”刘孝标注引《吴录士林》曰:“吴郡有顾陆朱张为四姓,三国之间,四姓盛焉。”从士族诗歌史的角度看,陆机的《吴趋行》未尝不是一篇“诗史”式的作品。在陆机眼里,包括陆氏在内的吴地高门士族无不文德武功,礼让济济,流化滂沱。到了太康时代,吴国已经成为了历史,四姓八族受到了重创。作为陆氏家族的栋梁,重振家族雄风,再创门庭辉煌,便成为陆机人生的主要目的。
《晋书·陆机传》中既说他:“伏膺儒术,非礼不动。”又说他:“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以进趣获讥。”据此看来,也许在早年他只是在表面上接受了儒学思想,而他的内心深处本来就缺乏儒家文化中的德行意识和天下意识;也许是为了达到克振家身的目的,进入洛阳政权后的现实迫使陆机放弃了早年接受的儒家文化精神。陆机《长安有狭斜行》云:“伊洛有歧路,歧路交朱轮。轻盖承华景,腾步蹑飞尘。鸣玉岂朴儒,凭轼皆俊民。烈心厉劲秋,丽服鲜芳春。余本倦游客,豪彦多旧亲。倾盖承芳讯,欲鸣当及晨。守一不足矜,歧路良可遵。规行无旷迹,矩步岂逮人。投足绪已尔,四时不必循。将遂殊涂轨,要子同归津。”此诗表明在故国灭亡之后,投靠北方政权的东南士族子弟,为了出人头地、占据要路津,意欲放弃“守一”原则,不再奉行规行矩步的儒家道德戒律。其《猛虎行》云:“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恶木岂无枝,志士多苦心。整驾肃时命,杖策将远寻。饥食猛虎窟,寒栖野雀林。日归功未建,时往岁载阴。……眷我耿介怀,俯仰愧古今。”首两句表明诗人一开始还在坚持政治操守,有所不为,但到了“日归功未建”之时,便只好屈节随俗。“饥食猛虎窟,寒栖野雀林”两句是对《猛虎行》古辞的改造,原辞是:“饥不从猛虎食,暮不从野雀栖。野雀安无巢,游子为谁骄。”在情急之中,诗人不得不改变初衷,放弃耿介之怀,趋利求进。《晋书·贾谧传》曰:“(贾谧)开阁延宾,海内辐辏,贵游豪戚及浮竞之徒,莫不尽礼事之。”陆机也在“降节事谧”(《刘琨传》)者之列,看来不是偶然的。其实,不仅是“降节事谧”一件事,进入北方的陆机,不断地投靠、依附于一个又一个权门。为了出人头地,为了家族的兴盛,这固然也是出于无奈,但也和他缺失了儒家文化真精神不无关系。胡应麟《诗薮》云:“余尝谓富贵溺人,贤者不免,文士尤易著脚,而六朝为甚。潘、陆、颜、谢诸君,往往蹈此。”(17) 陆机兄弟、谢灵运等六朝士族诗人的不幸遭遇,固然不是导源于他们的富贵生活,但他们的遇难与其士族家庭出身相关,也与他们个人强烈的士族意识相关,这是毋庸置疑的。
魏晋文人乐府中大致有三种类型:曹操乐府;(曹)丕(曹)植乐府;陆(机)谢(灵运)乐府。曹操乐府乃英雄之乐府,其诗中的忧患意识,天下襟怀,千古一人;曹丕曹植乐府乃文士之乐府,子桓乐府多叙人生之忧,子建乐府多写失志之痛,在后世文人中最容易引起共鸣;陆机谢灵运乐府乃是士族文人之乐府,其声名隆盛于中古之时,沉寂于明清之后。曹操继承了汉乐府关注现实的精神,用乐府旧题描写动乱的时事,并抒发自己一统天下的理想抱负,其作品具有英雄主义气概。曹丕曹植兄弟把民间乐府引向了文士乐府的不归之路。到了太康时代,陆机进一步把文士乐府引入了士族文人乐府的苑囿。陆机不仅用绮靡的风格去改造旧经典,同时,用乐府记录和再现了贵族们的物质生活,表现了具有士族特色的功业追求。在六朝这样一个门阀士族异常兴盛的时代,陆机乐府比三曹乐府更具有典范性。所以,我们看到在六朝时代不仅没有人批评陆机乐府“性情不出”,而且那时的贵族文人对陆机乐府非常推崇赏识。陆机之后,“元嘉之雄”谢灵运把陆机乐府看作乐府诗的经典去全力模拟。日本学者藤井守先生说:“将谢灵运作品与陆机作品相比较,句数、押韵等形式方面自不必言,内容上也非常类似。虽说乐府诗以模拟为原则是理所当然的,即使如此,谢灵运的作品也与陆机过于靠近,最终只能流于平板。他放弃了自身应有的主张,因陆机之作而作,所以终于成了单纯的模拟诗。”(18) 颜延之、谢惠连等人也多有模仿陆机乐府之作。《文选》中共选乐府40首,古乐府只选有3首,曹操曹丕乐府各选有2首,曹植乐府选有4首,而陆机的乐府选有17首之多。到了明清以降,学术界才开始流行起陆机乐府“性情不出”的观点。看来对古代诗人的褒贬和接受的程度,既与一定的时代相关,也与读者自己的家庭出身相关。这是接受美学所研究的问题了,在此暂且搁置。
收稿日期:2008-01-28
注释:
①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十,清康熙刻本。
② 傅刚:《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页。
③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00—203页。
④ 郭茂倩:《乐府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卷38,第558页。
⑤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43,第626页。
⑥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35,第523页。
⑦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32,第470页。
⑧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30,第449页。
⑨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61,第899页。
⑩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28,第419页。
(11)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40,第593页。
(12)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34,第502页。
(13)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62,第899页。
(14) 徐公持:《魏晋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5页。
(15) 刘熙载:《艺概·诗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16) 姜亮夫:《陆平原年谱》,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1页。
(17) 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18) 宋红编译:《日韩谢灵运研究译文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7页。
标签:婕妤怨论文; 饮马长城窟行论文; 古诗十九首论文; 曹植论文; 君子有所思行论文; 贵族精神论文; 读书论文; 乐府诗集论文; 郭茂倩论文; 短歌行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