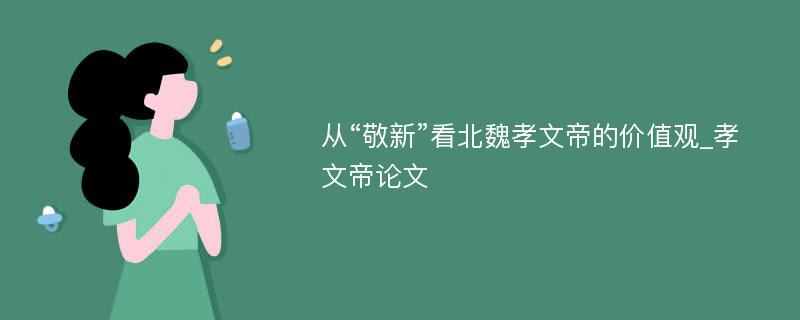
从“去故崇新”看北魏孝文帝的价值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魏论文,价值观论文,文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所处的时代,是社会急剧变革的历史转折时期。自其在位的太和八年(公元484年)至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北魏政权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持续改制,广泛涉及经济、政治、文化、习俗等各个方面,堪称一次全方位的社会改革。对于这场一千五百年前的重大改革,学术界已有诸多论述,但大多仅限于拓跋鲜卑和北魏政权封建化的范围,而对孝文帝的价值观念以及这场改革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及其作用,则阐述较少。本文拟结合孝文帝亲掌大权以后的实践,对其提倡和追求的价值观作一分析和探讨。
(一)
拓跋鲜卑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同入主中原的其他少数民族一样,拓跋鲜卑是作为一个远远落后于中原发展水平的民族而成为北方统治者的。刚刚迈入奴隶社会的拓跋鲜卑族,一到中原就处于封建生产方式和封建文化的包围之中。随着与中原汉族战争与和平等诸种方式交往的日趋频繁,以及统治区域的日渐扩大,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日益深刻地浸润和影响着拓跋鲜卑,推动着北魏政权开始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急剧转变。
大凡社会制度新旧更替、急剧变革的历史转折时期,新旧两种社会势力的斗争便表现得特别激烈。而新旧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则是这种斗争在思想观念上的集中体现。北魏政权自然也不例外。由于北魏封建化的过程,是在中原封建生产方式和封建文化的影响和推动下进行的,因而北魏政权的变革措施,实质上就是借鉴和吸取中原汉族的封建统治经验和思想文化,用以改变拓跋鲜卑原有的统治方式和文化习俗,也就是所谓“用夏变夷”①。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新旧两种价值观念的冲突,便突出地表现为鲜卑贵族的价值观与中原封建地主阶级的价值观之间的冲撞与交锋。而其冲突的焦点,则可以归结为“崇武”与“尚文”的较量。
拓跋鲜卑进入中原以前,是塞外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徙的游牧生活方式,使他们习惯于马背上的生活,养成了精于骑射、骠悍善战的习性和崇尚武力的传统民族心理。拓跋鲜卑的崛起,相当程度上得力于这种武勇之风。但是在入主中原以后,环境与形势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相当一部分鲜卑贵族却依旧恪守“崇武”的传统不变,顽固地坚持其固有的统治模式。其主要表现有三:
一是孜孜于抢掠、班赏。历史上的游牧民族,居无定所,加之骠悍骁勇,常常通过战争掠夺财富、人畜。拓跋鲜卑贵族也是如此。他们以劫掠财富的方式来满足其生活需要,依据功劳大小和品爵高低来瓜分战利品,史称“班赏各有差”②。虽然这种以班赏形式分配财富、人口的做法,在封建式的农业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但毕竟是基于暴力抢掠的一种野蛮分配方式。不仅因其手段的残虐而激起各族人民的普遍不满,而且在战火渐熄的情况下也难以为继,必然引发官吏的巧取豪夺和贪污成风,导致吏治的败坏。这种抢掠、班赏不适宜于统治中原是显而易见的。然而鲜卑贵族却不愿放弃和改变,甚至在冯太后以班禄制取代班赏制以后,他们还固执己见,上表“奏求依旧断禄”③,要求继续保持抢掠旧风。
二是拒绝学习和接受中原文化。史载:“北人每言北人何用知书”④。此处所谓“书”者,当指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相对于进入奴隶制阶段时间还不长的拓跋鲜卑来说,中原封建文化无疑是一种先进文化,尤其是其中相当丰富的汉族地主阶级的统治经验和相当精致的典章礼仪,对于急欲巩固其统治的北魏政权显然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从拓跋珪开始,鲜卑的有识之士就很注意学习和提倡中原的封建文化,视儒家经典为“益人神智”⑤之书。但是,拓跋珪等人的提倡和身体力行,并不能改变鲜卑旧贵族拒绝学习和接受中原文化的态度。他们以“北俗质鲁,何由知书”⑥为借口,其实却认为“何用知书”,甚至担心“知书”会使鲜卑人失去其勇武的性格和习性。这种自尊与自卑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理,导致了他们自甘封闭、拒绝先进文化的保守趋向。
三是排斥和反对重用汉族士大夫。“从来北族之强盛,虽由其种人之悍鸷,亦必接近汉族,渐染其文化,乃能致之。过于朴塞,虽悍鸷,亦不能振起也。”⑦其所以如此,乃是由于汉族士大夫受到儒学的长期熏陶,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而且深谙治国之道,具有丰富的统治经验。故招纳汉族士大夫,不失为学习中原先进文化的一条捷径。从拓跋珪、拓跋焘到其他北魏帝王,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这一点,因而对汉族士大夫能“留心慰纳”,“苟有微能,咸蒙叙用”⑧,直至委以重任,视如腹心。可是,相当一批鲜卑旧贵族对此却愤愤不平。史载:“及帝迁洛阳,所亲任者多中州儒士,宗室及代人往往不乐”⑨。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尚且如此,则其反对重用汉族士大夫的顽固立场不难想见。究其原因,固有权力分配上的利害冲突,惟恐亲彼而疏己。但更深层的原因仍在于借排斥汉族士大夫以抵制中原文化的影响。
拓跋鲜卑贵族上述种种表现,是其坚持“崇武”传统不变的心态的外在反映,表明他们是把鲜卑族历史上既成的规范、习性、传统等视作不随时空条件推移而改变的永恒之物。这正是保守的价值取向的典型特征。
与此截然相反,中原士大夫却力主“尚文”。早在西汉初年,陆贾就明确地向刘邦指出:虽然天下是“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王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⑩陆贾的这番议论,可看成是封建统治者治国方略的代表作。这一不能以马上治天下的思想,不仅为汉代统治者所接受,而且成为此后历代君主治理国家的一条基本原则。
“文治”的核心内容,是儒家学说的“仁”与“礼”。而这也是儒家伦理价值体系的两大主题。因此,所谓“文治”的原则,实质上就是儒家伦理价值观在政治领域里的体现和运用。虽然就其本质而言,中原士大夫所遵奉的儒家伦理价值观同样注重传统,因而也同样具有因循、保守的特性(关于此点,将在下文作具体分析),在这一点上,与鲜卑旧贵族所坚持的价值观念并无根本区别。但在拓跋鲜卑封建化的社会背景下,由“崇武”转向“尚文”,即摈弃鲜卑旧贵族的价值观念,转而接受中原士大夫的价值观念,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因而是值得肯定的进步;同时,中原士大夫所持的伦理价值观,既有其因循、保守的一面,也有灵活运用原则、托古而革新的另一面。孔子就说过:“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11)在他看来,君子处理天下之事,并没有具体规定应该怎样干,只要符合“义”的原则就行。可见,在一定条件下灵活运用原则,通权达变,是儒家伦理价值观所允许的。
在拓跋鲜卑由奴隶制迅速转向封建制的历史变革时期,上述两种相冲突的价值观念同时并存,且看孝文帝如何抉择。
(二)
几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同时并存,乃是历史上常见的现象。社会变革时期尤其如此。关键在于如何依据正确的判断,对现存的种种价值观念作出取舍和抉择。历史人物的识见和作用,也由此而分出高下。
从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至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这十年中,孝文帝拓跋宏亲掌国政,主持改革,他的思想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一系列诏令和言论中,拓跋宏表现出了强烈的改革愿望和决心,同时也反映了他对现存价值观念的选择。
太和十四年十月,冯太后安葬完毕,在君臣为是否守制三年进行的辩论中,孝文帝表示:“朕仰惟太祖龙飞九五,初定中原,及太宗承基,世祖纂历,皆以四方未一,群雄竞起,故锐意武功,未修文德。高宗、显祖亦心存武烈,因循无改。朕承累世之资,仰圣善之训,抚和内外,上下辑谐。稽参古式,宪章旧典,四海移风,要荒革俗。仰遵明轨,庶无愆违。”(12)
太和十六年正月,为修缮太极殿颁诏称:“朕以寡德,猥承洪绪,运属休期,事钟昌运,宜遵远度,式兹宫宇。……其去故崇新之宜,修复太极之制,朕当别加指授。”(13)。
太和十七年五月,孝文帝谋迁都洛阳,召见任城王拓跋澄,屏人谓澄曰:“今日之举,诚为不易。但国家兴自朔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今将移风易俗,其道诚难,朕欲因此迁宅中原,卿以为何如?”(14)
太和十九年五月,孝文帝欲变旧俗,禁鲜卑语,在引见朝臣时,明确表态说:“朕尝与李冲论此,冲言:‘四方之语,竟知谁是?帝者言之,即为正矣,何必改旧从新。’冲之此言,应合死罪。”(15)
从上引诏令及言论中,我们不难看出:其一,孝文帝清醒地看到了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与治国政策的关系。他认为其祖辈之所以“锐意武功,未修文德”,是由于当时“四方未一,群雄竞起”。而他所处之时,则“抚和内外,上下辑谐”。条件不同了,所以必须“移风易俗”,实行“文治”。这种“教随时设,治因事改”(16)的改革意识,是孝文帝提出“去故崇新”方针的思想出发点。其二,孝文帝改革的根本内容,是要改以往的“锐意武功”为“修文德”、行“文治”,仿周、汉之兴隆,达到“迈迹前王”的目标。其三,在价值取向上,孝文帝也接受了儒家伦理价值观的传统,以殷周、汉晋为理想社会的楷模,一再宣称要“稽参古式,宪章旧典”,表示要“仰遵明轨,庶无愆违”。这就表明,在“崇武”与“尚文”的冲突中,在鲜卑旧贵族的价值观念与中原士大夫价值观念的交锋中,孝文帝明确地选择了后者,并以之作为指导改革实践的理论原则。因此可以说,孝文帝拓跋宏基本上是全盘接受了中原封建地主阶级的传统价值观。
孝文帝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价值目标的选择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是随心所欲的,而必须要受到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拓跋宏所处的时代,我国北方的各少数民族空前活跃,民族战争接连不断,与中原汉族的交往也日益频繁。特别是拓跋鲜卑迅速崛起并入主中原,在近百年的时间里,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已在封建化的进程中取得了初步成果。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条件,不但与拓跋鲜卑入主中原前截然不同,而且比起拓跋珪、拓跋焘时期也有了新的发展。与此相联系,北魏政权面临的主要任务,随着统一北方的实现,也转变到如何完成封建化以巩固统治。历史一再证明,“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7)拓跋宏在社会历史条件和主要任务都已改变的形势下,在其阶级的需要和利益的驱动下,顺应历史潮流而作出这样的抉择,乃是势所必然。
其次,孝文帝的选择亦有其家世渊源。在拓跋鲜卑封建化的进程中,拓跋宏是后来者。在他之前,北魏前期的拓跋珪、拓跋焘等已在不同程度上着手实施封建化。他们的活动,虽然距拓跋宏较远,难以对他发生直接影响,但他们毕竟已在变革旧俗方面树立了楷模,开创了新风。尤其是在拓跋宏幼年即位后临朝称制的冯太后,更给予拓跋宏以深刻影响。冯太后是汉族人,其姑母是北魏太武帝的昭仪,颇有一些文化修养。生于长安的冯太后在父亲死后即进宫由姑母“抚养教训”。这一优越条件使她从小就有机会接受汉族的传统文化教育;加之冯太后长期生活在北魏皇宫,得以熟知鲜卑旧贵族的弊端。这样两个有利因素,把冯太后造就成一个颇有作为的女政治家。在操纵北魏大权的时期里,她先后主持了班禄制、均田制、三长制等重大改革,为鲜卑封建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冯太后虽然私生活放荡,却颇能重用贤才,对李冲、高闾、高允、游明根等有才干的汉族士大夫,均委以重任,给予很高的礼遇。拓跋宏长期生活在冯太后身边,成人后又与冯太后共掌朝政,耳濡目染,冯太后力主改革的言行,对他影响至深。且祖辈的榜样使拓跋宏有先例可援,大大减少了“去故崇新”的阻力和风险。
再次,孝文帝的个人素质也不容忽视。价值目标的选择,除了要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以外,还要受到人们自身主观条件的制约。在北魏时期,要比较自觉地接受中原士大夫的价值观,必须对中原文化特别是儒学有较深的了解。拓跋宏是具备了这个条件的。冯太后以汉人而成为北魏女主,十分重视用汉族封建文化教育皇族子弟。她曾下令:“自非生知,皆由学诲,皇子皇孙,训教不立,温故知新,盖有阙矣。可于闲静之所,别置学馆,选忠信博闻之士为之师傅,以匠成之。”(18)拓跋宏出生以后,其生母即依北魏旧例被赐死,由冯太后“躬亲抚养”,深受其熏陶,养成了对中原文化的浓厚兴趣和刻苦读书的习惯。而自幼父母俱亡及冯太后的专横,又促使拓跋宏在刻苦读书中寻求自己的乐趣。特殊的环境和没有欢乐的家庭生活,反而使拓跋宏在读书中加深了对中原文化的了解,提高了自身的素质。史载:拓跋宏“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援,采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老庄,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19)拓跋宏能做到儒、道、佛俱通,诗、赋、文并茂,正是他“雅好读书,手不释卷”(20)的结果。如果没有学习中原文化的浓厚兴趣,没有对儒学经典的广博知识和深刻理解,纵然具备了社会历史条件和家世渊源,拓跋宏也未必能作出这样的选择。关于这一点,太子拓跋恂的表现恰是极好的反证。拓跋恂生而母死,也由冯太后亲自抚养。拓跋宏更是对太子寄予厚望,在为他行冠礼时,告诫说:“字汝元道,所寄不轻。汝当寻名求义,以顺吾旨。”(21)在命太子赴平城参加外戚冯熙葬礼时,也告诫他一路上“当温读经籍”(22)。还选择了汉族士大夫李冲等人为太子师傅。拓跋宏对太子的教育可谓用心良苦。可是拓跋恂却“不好书学”(23),拒绝学习中原文化,结果不仅不能承继父业,反而背道而驰,处处作梗,直至密谋叛乱。由此观之,拓跋宏父子对中原文化及儒家传统价值观的不同态度,显然是与他们个人素养的高下直接相关的。
(三)
孝文帝拓跋宏亲掌大权以后,继续推行改革,尤致力于文化、习俗等思想意识方面,推动了改革的深化。纵观拓跋宏所采取的各项改革措施,无不体现了他对中原文化的仰慕,亦无不贯穿着“去故崇新”的基本原则。拓跋宏推行这一系列“去故崇新”措施的目的,固在于“移风易俗”;而“移风易俗”的深层目标,则在于提倡和追求儒家的传统价值观。
在社会制度新旧更替的变革时期,拓跋宏明确提出了“去故崇新”、“改旧从新”的思想,无疑反映了他企图变革现状、改变不适应时代要求的旧观念、旧制度、旧习俗的革新精神。若与当时鲜卑旧贵族抱残守缺、守旧不变的精神状态相比,孝文帝的革新精神显然是一种积极的、锐意进取的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实行的各项去鲜卑陋习之故、崇封建化之新的措施,对于完成北魏封建化、促进北魏社会发展,无疑是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的。
但是,我们在对孝文帝“去故崇新”思想所体现的革新精神加以肯定的同时,必须对其内涵进行具体分析。任何时候的“新”,都是相对于当时的“旧”而言的。孝文帝所要革去的“旧”,是不适应时代要求的鲜卑旧习,包括落后的旧习俗、野蛮的旧制度、保守的旧观念,等等。为了实现拓跋鲜卑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这一类旧东西是必须扫除的。而孝文帝崇尚、遵从的“新”,则是上文已经指出的中原的封建统治模式和封建文化,其深层结构则是儒家传统的价值观。这一传统的价值观,自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以后,至两汉已日臻完备并基本定型。经历魏晋而到北朝,虽然对于拓跋鲜卑统治者来说依然不 失为“新”的观念,但从其自身来说早已不再新鲜了。孝文帝把这一传统价值观当作“新”观念加以推崇和提倡,自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因为他在完成封建化的过程中不可能提出比之更新的观念,除了把它当作“新”观念接受之外,别无选择。但是,当孝文帝全盘接受了这一传统的价值观念之后,就不得不把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都置于这一价值观念的束缚和制约之中。
在价值取向上,传统的价值观不是面对现实,面向未来,而是面向过去,主张“法先王”、“宪章文武”。对于传统的特别注重,使得“大家都以为黄金时代在上古”(24),祖宗奠定的原则成为衡量人们行为顺逆善恶的天然尺度。于是一举一动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言必称上古三代。孝文帝也在价值取向上鲜明地表现出这种面向过去的特色。他多次明确表示,他之所以要移风易俗,实行改革,目的就是效法先王,建立殷周、汉晋那样的理想社会。如迁都洛阳,孝文帝借拓跋澄之口说明是要“卜宅中土以经略四海,此周、汉所以兴隆也”(25);禁绝鲜卑语,孝文帝则宣称目的在“欲令魏朝齐美于殷周。”(26)。
诚然,在面向过去的传统价值取向中,也有着托古以改制的一面。历代的改革者在变革现状、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中,常常利用托古改制,给改革披上一件传统的外衣。近代的康有为在描述这种心理时指出:“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27)。拓跋宏贵为天子,执掌国政,改制时未必会有杀身之祸,但“事大骇人”、阻力重重则大抵相同,打出“先王”的旗号以减少阻力的考虑也是一致的。故孝文帝每每以“先王”、“圣人”为旗帜,从祖宗那里去寻找改制的依据。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孝文帝以南伐为名谋迁都,命太常卿占卜,其兆遇“革”,孝文帝即引《革卦》之《彖辞》曰:“‘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吉孰大焉!”①一些大臣以“众情不乐”反对迁都,孝文帝又从祖宗那里寻找依据:“王者以四海为家,或南或北,何常之有!朕之远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始都东木根山。昭成皇帝更营盛乐,道武皇帝迁于平城。朕幸属胜残之运,而独不得迁乎!”②尽管在把传统视为天经地义的特殊的社会心理氛围中,改革者为减少风险而时常采取托古改制的方式,但这种方式的因循、保守性是十分明显的。这不仅是因为托古改制在价值取向上并没有摆脱面向过去、“法先王”的束缚,依然是以“先王”、祖宗的是非为是非;而且是因为改制既然必须托古,一旦无“古”可托,在“先王”和祖宗那里找不到合适的依据,连改革者自己都会产生理不直气不壮的负罪感,更不用说实行了。拓跋宏虽有“教因时设,治因事改”的变革意识,但由于他在价值取向上的面向过去,使得他的改制仅仅限于变革鲜卑旧俗,而对于中原士大夫恪守的传统却不能作丝毫改变,而且几乎是原封不动地接受下来。拓跋宏的一切改革措施都在传统价值观的支配下实施,这就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改革的深化,使改革染上了妥协、因循的色彩。仿中原模式定族姓、建门阀制度便是最突出的一例。
在价值评判的尺度上,孝文帝也一成不变地接受了传统价值观的规范。孔子所倡导的“礼”,向被视为人们的行为规范,是维系社会秩序、国家稳定的支柱。“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也。”(28)孝文帝熟读儒家经典,深知崇“礼”的意义和作用。他多次阐发对“礼”的认识,诸如“夫先王制礼,内缘人子之情,外协尊卑之序”(29);“礼乐之道,自古所先,故圣王作乐以和中,制礼以防外”(30),等等。显然,孝文帝是完全赞同以“礼”作为衡量人们行为的价值尺度的。
对于不合封建礼仪的言行,孝文帝严加斥责。其弟拓跋禧不遵守与“八族及清修之门”通婚的规定,“取任城王隶户为之,深为高祖所责”。对于“族非百两,拟匹卑滥,舅氏轻微”的婚姻,孝文帝认为是“违典滞俗”而“深用为叹”。他对婚姻极为重视,认为:“然则婚者,合二姓之好,结他族之亲,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必敬慎重正而后亲之。夫妇既亲,然后父子君臣、礼义忠孝,于斯备矣。”(31)这是企图通过对婚姻的重视来达到以“三纲五常”规范人们行为的目的。
为了贯彻以“礼”为价值尺度的观念,孝文帝极看重对社会各阶层的教化。对于皇族,孝文帝认为:“教风密微,礼政严严,若不深心日劝,何以敬诸。每欲立一宗师,肃我元族。”并特命彭城王拓跋勰为宗师,“委以宗仪,责成汝躬,有不遵教典,随事以闻,吾别肃治之。”(32)。对于朝臣,除亲撰《职员令》二十一卷以“厘整时务”外,又多次亲自为群臣讲“礼”,以致李彪称颂道:“自古及今,未有天子讲礼。陛下圣睿渊明,事超百代,臣得亲承音旨,千载一时”。(33)。虽不免阿谀,也可见孝文帝对“礼”的重视。对于百姓,孝文帝也颁诏规定:“乡饮礼废,则长幼之叙乱。孟冬十月,民闲风隙,宜于此时导以德义。可下诸州,党里之内,推贤而长者,教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顺、夫和、妻柔。不率长教者,具以名闻。”(34)向社会各阶层进行“礼”的教育,是孝文帝以“礼”作为衡量价值的最高尺度的充分体现。
对于孝文帝全盘接受中原传统的价值观,并以之作为自己价值观的做法,要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必须充分注意到孝文帝拓跋宏身份的两重性。
首先,拓跋宏作为拓跋鲜卑族的最高统治者,摆在他面前的最紧迫任务,就是完成封建化以巩固统治。因此,他决策的出发点首先要考虑必须有利于拓跋鲜卑的社会发展。由此出发,拓跋宏接受中原传统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尺度,并以此为指导,采取“去故崇新”的各项措施,对于革除落后旧习,建设封建新秩序,无疑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从根本上说,这样做有利于拓跋鲜卑的社会发展,有利于北魏封建化的完成。在拓跋鲜卑的发展史上,拓跋宏在祖辈奠定的基础上大大前进,提供了比其祖辈更多的新东西。这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
其次,拓跋宏又是中原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因此,还应该把他的思想和活动放到整个封建社会发展的大过程中加以考察,以便判断他是否提供了前人所没有的新东西。
如前所述,中原传统的价值观早在两汉即以基本定型。汉武帝“独尊儒术”的结果,使儒学及其价值观成为封建地主阶级遵奉的信条。但是,东汉末年社会的动荡,动摇了人们对儒学及其价值观的信仰。不少士大夫由对儒家传统价值观的失望而产生怀疑,又由怀疑而趋于否定,转而探寻新的价值观念。魏晋玄学的兴起,便是一部分士大夫力图摆脱传统束缚的一种尝试。然而,孝文帝拓跋宏却在永嘉之乱以后“礼乐文章,扫地将尽”(35)、儒学及其价值观遭到极大冲击的情况下,崇儒兴学、制礼作乐,提倡和追求传统的价值观。如此举措,尽管对中原封建文化的中兴有所贡献,但是与魏晋士大夫的思索与探寻相比,却不能不说是一种倒退。
不仅如此,孝文帝接受和提倡的传统价值观,几乎是两汉传统的全盘吸收。从上文分析可见,无论是价值取向还是价值尺度,孝文帝所主张的,实质上与汉代传统如出一辙。在儒学及其价值观业已遭到很大冲击的情况下,拓跋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君主,竟能近乎原封不动地加以接受和继承,其“汉化”真可谓是到家了。
(四)
一千五百年前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实践,使他成为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改革家。同时,他接受和提倡传统价值观的结果,则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孝文帝“汲汲于用夏变夷”(36),完全接受了中原封建文化及其价值观,而全未虑及其不良成分之腐蚀性,亦置本民族特点于不顾。在儒家传统价值观的支配下,孝文帝照搬中原封建统治方式和礼仪制度,甚至从语言、服饰、习俗等各方面全面地实行“汉化”,为之而付出了将本民族消失于与汉族融合过程之中的代价。但是,这一改制却并没有达到他“欲传之子孙”、使北魏政权长治久安的目的。尽管我们不能把数十年后的北魏乱亡完全归咎于孝文帝的改制,但他在实行改革时没有充分地认识和考虑本民族的特点,没有对中原封建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加以区分,结果引起鲜卑贵族的强烈不满和对立,也造成了鲜卑贵族的迅速腐化。北魏后期的乱亡,与此两条是密切相联的。
导致孝文帝改制失误的思想根源,在于他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尺度都打上了深深的传统的烙印。他虽然勇敢地摆脱了鲜卑旧传统的束缚,却又陷于中原封建传统的束缚之中。自然,改革本非易事,更何况一千五百年前的孝文帝,不可避免地带有其无法摆脱的局限。本文对孝文帝价值观的探讨,无意苛求于古人,这是无须多说的。
(作者附记:本文的摘要,曾发表于《探索与争鸣》1994年第8期)
注释:
①(36)《资治通鉴》卷142“齐永元元年”条。
②《魏书》卷4下,《世祖纪下》。
③《魏书》卷54,《高闾传》。
④《魏书》卷21上,《广陵王羽传》。
⑤《魏书》卷33,《李先传》。
⑥《资治通鉴》卷139,“齐建武元年”条。
⑦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73页。
⑧《魏书》卷21,《太祖纪》。
⑨《资治通鉴》卷140,“齐建武三年”条。
⑩《史记》卷97,《郦生陆贾列传》。
(11)《论语·里仁》。
(12)《魏书》卷108之三,《礼志三》。
(13)《魏书》卷53,《李冲传》。
(14)(25)《资治通鉴》卷138,“齐永明十一年”条。
(15)(18)(26)(31)《魏书》卷21上,《咸阳王禧传》。
(16)《魏书》卷7上,《高祖纪上》。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2页。
(19)(20)(34)《魏书》卷7下,《高祖纪下》。
(21)(22)(23)《魏书》卷22,《废太子恂传》。
(24)赵纪彬:《困知录》。
(27)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卷11。
(28)《左传·僖公十一年》。
(29)《魏书》卷108之一,《礼志一》
(30)《魏书》卷109,《乐志》。
(32)(33)《魏书》卷21下,《彭城王勰传》。
(35)《魏书》卷84,《儒林列传》。
标签:孝文帝论文; 魏书论文; 冯太后论文; 孝文帝改革论文; 中原文化论文; 北魏论文; 价值观论文; 文化价值观论文; 贵族精神论文; 士大夫精神论文; 汉族文化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中原论文; 儒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