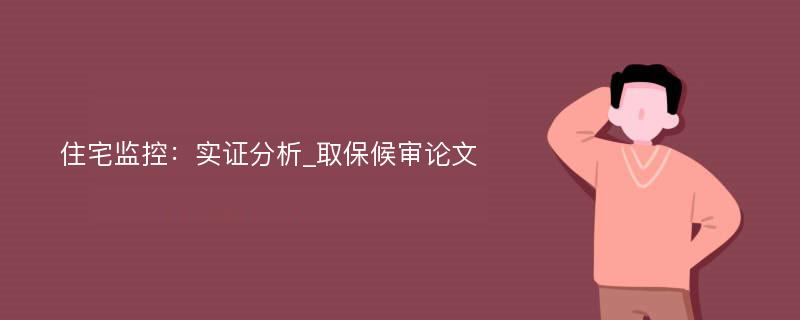
监视居住:一个实证角度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角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论:论题与方法
一般认为,监视居住与取保候审都具有替代羁押的功能。①在规范层面,监视居住通常适用于符合羁押条件,但犯罪情节轻微或者社会危害不大、有患病或怀孕或哺乳情形的犯罪嫌疑人,个别情况下也可以在证据不足时作为侦查羁押的一种变更适用方式。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不得离开其住所,不得干扰证人作证、毁灭伪造证据或串供,在传讯时应及时到案;对侦查机关而言,在监视居住期间不得中止对案件的侦查。②总之,监视居住是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逃避诉讼而适用的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其人身自由的诉讼手段,但在强制性上又远未达到羁押程度,从而具备了替代羁押的功能。本文将从功能主义视角出发,③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对监视居住的适用状况进行一个简要考察。最后,笔者将在考察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监视居住制度的改革作出思考。研究资料来源于2005年11月至2006年1月课题组对S省N市N县、Y市Y区和C市J区公安局进行的统计、访谈和档案检索。调研中,课题组发现,绝大多数受访对象仅能解释不采用这一措施的理由,而无法描述这一措施的运行程序及实际存在的问题。有鉴于此,笔者将以数据、档案资料为基础,结合有限的访谈情况与以下两个典型个案④展开分析:
【个案1】湛×(男,贵州人)涉嫌与张×于2003年7月的一天利用虚假银行卡共同诈骗钱财。经被害人指认,派出所将湛×抓获,而张×在逃。湛×到案后辩称用卡取钱一事系张×指使,自己并不知道卡上存款系他人所有。由于张×在逃,湛×的口供无法得到印证。检察院作出不批捕决定后,派出所拟报劳教。为留出审批时间,遂于7月30日报分局批准对其监视居住。由于湛×无固定住处,派出所指定某宾馆一个房间为其临时居住地,安排民警与其同吃同住。派出所在监视居住期间报请劳教,因未获批准,在8月1日解除了对湛×的监视居住。
【个案2】2004年4-5月,犯罪嫌疑人暨××(女,广东人)涉嫌多起手机诈骗案件。5月16日,派出所对暨××实施留置,在留置期间暨××未供认罪行。由于其已怀孕不宜刑拘,为进一步展开讯问,5月18日,派出所报分局批准对其实施监视居住,指定监视地点为J区妇产科医院。监视期间办案人员讯问了3次,暨××供述了2起犯罪事实。5月20日,暨××趁上厕所之际脱逃。
二、功能分析:替代羁押与限制权利
替代羁押是监视居住的预期功能。对三个地区公安机关的调研结果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监视居住确能发挥这一功能,但容易转化为变相羁押,使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受到不当限制。
从统计分析的角度,可以发现实际的监视居住期间、监视居住后的处理结果与替代羁押功能/案件消化功能相联系,监视居住的主要功能是替代羁押。以监视居住数据与档案最齐全的J区公安局为例,2003年以来11例监视居住的批准期限都是6个月,但实际执行期间则呈现两个极端:4例的期间是5-6月,另7例的期间最长15天、最短1天、平均4.6天。就处理结果而言,解除监视居住的5例,转为取保侯审的4例,1例转捕,另有1例因嫌疑人脱逃而未予处理。将监视居住期间与处理结果对应起来分析,笔者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4例监视居住期间为5-6月的,其处理结果均为解除监视;另有1例处理结果为解除监视的案件实际监视期间为3天,系未批准劳教而不得不解除的情形;此外,所有监视居住期间较短的案件分别对应于取保候审、转捕与逃跑三种结果。由于解除监视实际上就是撤销案件、排除犯罪嫌疑,因此,笔者推测凡实际监视居住期间较长而最终解除,期间较短而作出进一步处理的案件,其监视居住功能分别对应于消化案件与替代羁押。相关访谈证实了这一推测。J区法制科办理监视居住最多的一名审批官员称,监视居住期间接近或用尽6个月的通常未采用任何监视措施,决定监视居住其实就是“放人”。⑤针对监视居住期限较短且采用其他处理方式的情形,上述审批官员未能作出解释,但课题组在对上述两起个案的侦查人员的访谈中了解到,监视居住期间较短的个案都得到实际的执行,执行结束后根据案件情况作出相应处理。可见,实际执行期间较短的监视居住反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替代羁押的功能,但其作用可能较为有限,因为最终的处理结果很少是转捕,转为取保候审的则不明确其最终的处理结果。
从个案角度,上述两起个案的监视居住均得到实际执行,侦查人员也希望通过监视居住为惩治创造条件。因此,这两起个案的监视居住具备了替代羁押功能。从它们反映的信息情况分析,其实际监视居住期间短(均为2天),其中1例为报送劳教未获批准而解除,另1例系因犯罪嫌疑人脱逃而未能处理。这一信息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统计分析的结论。不仅如此,两起个案还反映出其替代羁押功能适用的两个条件:适用对象条件方面,犯罪嫌疑人都是外地人;执行条件方面,侦查机关指定了监视居住场所。在犯罪嫌疑人是外地人的情形下,如果不采用监视居住而选择取保候审,很难达到预期目的。湛×与暨××都是外省人,在J区也没有亲属和其他较密切的社会关系。其中,湛×平时容身于录像厅,无暂住地,被派出所怀疑其长期从事小偷小摸活动;暨××虽有暂住地,但同伙被捕之后无其他人居住,也无其他正常的社会关系。上述二人均无法提供取保候审的担保。对此,办案人员明确指出,如果这两名犯罪嫌疑人是本地人就不会考虑监视居住,因为如果是本地人的话可以很容易找到担保人,落实保证责任。这一适用条件也通过Y区公安局的监视居住档案资料得到进一步印证,在6名被监视居住人员中就有5人是外地人。
确保监视居住的替代羁押功能最为重要的条件也许是为犯罪嫌疑人指定居住场所,以此为基础实施全天候监控。在犯罪嫌疑人是外地人的前提下,如果不为其指定居所并实施有效监控,监视居住很难产生任何效果。而在指定居所时,如上述两起个案,侦查机关通过一定的强制方式限制了犯罪嫌疑人的活动范围。犯罪嫌疑人被明确告知不得离开指定的活动区域,但可以在极为狭小的空间内(如宾馆房间、医院边界)“自由活动”,同时受到侦查人员目光监视,如有离开的举动就会被侦查人员采用人身约束手段。对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而言,身边无时不在的侦查人员其实就是一堵流动的“监狱之墙”。如果不采用指定居所、全天候监控的方式,犯罪嫌疑人的活动情况就很难真正被侦查机关随时掌握,其脱逃、重新犯罪、威胁证人都十分容易。监视居住与刑事拘留、逮捕的作用相似,区别主要在于被监视居住人员生活环境相对较好,在指定场所内可以自由活动并与外界保持一定的信息联系。由于监视效果较好,笔者认为,指定居所式的监视居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需指出的是,指定居所后的监视在实践中基本被侦查人员转化为一种物理强制,从而模糊了与羁押的界线。上述两起个案中的监视行为也反映出这一特点。换言之,监视居住的确存在羁押化倾向的问题。已有的文献资料也已证明,监视居住的羁押化绝非个别现象。⑥
基于上述分析,侦查实践中监视居住确能发挥替代羁押功能,但这种功能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不当限制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基础之上的。从外地犯罪嫌疑人占有一定比例的情况来看,⑦监视居住应有较大的适用空间。如果仅考虑这一因素,监视居住适用率应能达到较高比例。然而,进一步的分析将表明,受制于各种条件,监视居住的确很难得到充分利用。
三、适用率分析:问题与原因
1996年刑诉法修改前,侦查实践中滥用监视居住的现象相当普遍。⑧新刑诉法实施后不久,相关报道或调研成果表明,在不少地区监视居住适用率仍相当高。然而,这并非是监视居住制度的正当化改革带来的结果,而主要与监视居住地点通常被设置在公安机关的羁押场所(如拘留所、留置室、看守所),从而演变为一种变相拘禁手段有关。⑨在这种机制下,侦查机关对于证据不足的案件可以“监视居住”为借口实施实质性的羁押。无疑,这种高适用率的背后并不是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张扬,而恰恰是侦查权力的无所节制。在此情形下,监视居住的功能实际上等同于羁押。
近年来,监视居住的适用有明显弱化趋势。⑩在三个调研地区公安局,监视居住的适用率可以用“稀有”一词概括。1996年刑诉法修改以来,N县公安局没有使用一例监视居住。Y区公安局的情况略好,但也只有6人,其中1997年4人,2002、2005年各1人。J区公安局监视居住档案中最早只有2003年的数据,2003年至今共适用于11人,其中2003年1人,2004年7人,2005年3人。与同年度刑事拘留甚至取保候审总量相比,Y区、J区公安局监视居住的适用都相当有限。上述考察导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监视居住适用率如此低下?课题组对监视居住适用最多的J区公安局相关审批官员、侦查人员的访谈情况表明,在羁押场所以外适用监视居住警力耗费较大、经费支出较高,这构成最重要的限制性因素。个案分析亦将进一步证实这一结论,同时还揭示出实际执行时存在的困难。
上述两起个案均采用指定居住方式,并派专人监视,由此产生三个问题:其一,指定居住的费用较高。在湛×案中,租用宾馆房间花费300元,用餐花费约150元,两项总计450元,平均一天花费150元。暨××案中,虽然因指定场所在医院而节省了宾馆费用,但却属于非常特殊的情形。如果按湛×一案中每天150元的标准计算指定居住的费用成本,6个月的监视居住费用将高达2.7万元。这对办案单位来说是难以承受的。以J区公安局经费状况最好的一个办案单位C派出所为例,2005年总计收99万元,总支出96万余元,其中大部分经费用于人员支出及日常办公支出,真正用于办案支出的不足20万元。(11)在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将过多的经费用于监视居住,则不利于全局性侦查效益的实现。其二,监视力量投入较多。湛×案中,执行监视居住的有3名正式警察,另有2名群防队员;其中,1名警察带领2名群防队员,一天换班一次。暨××案的警力投入情况与此相似。在基层派出所和刑警队,办案的组织形式是“探组制”,一个探组由两名侦查人员组成。如果对犯罪嫌疑人执行监视居住,该探组的警力基本不可能再从事其他侦查活动。在目标考核导向下,这不是一种经济的选择。(12)其三,实际执行存在一定难度。如暨××一案中,侦查人员百密一疏,导致犯罪嫌疑人脱逃。湛×一案中,犯罪嫌疑人也未戴手铐,可以在房间内自由行动,但负责监视的警察高度紧张,晚间也很难入眠。这两起案件均属指定监视场所的情形,办案人员相对主动,尽管执行中存在一定困难,但也基本可行。如果监视地点是犯罪嫌疑人的住宅,监视人员住宿、饮食等都将成为问题,因为私人生活的隐私性问题,也不便展开监视。
部分受访人员认为,这些问题的产生与监视居住地点被设置在羁押场所或公安机关之外直接有关。如果监视居住被置于羁押场所或公安机关,无论费用支出或警力投入均不存在问题,“监视”效果更是勿庸置疑。进一步的调查显示,近年来,Y区、J区公安局监视居住的适用均在公安机关以外的其他场所,因此个案反映的问题具有地区普遍性。Y区公安局的6例监视居住档案资料中,有3例注明了监视居住地点,其中2例(1997年)在市看守所,另1例(2005年)在犯罪嫌疑人住宅。J区公安局的监视居住档案资料均未注明监视地点,但该局法制科审批官员称对监视居住地点有严格要求,不可能在羁押场所实施;上述两起个案的侦查办案人员承认,“在90年代初,监视居住还可以关在所上,规范以后就不能了。”上述人员反映的“要求”或“规范”即《程序规定》第98条之规定,(13)也包括J区公安局执行的C市公安局强制措施文件的相关规定。(14)可见,在监视居住地点限于公安机关以外的其他场所,并且由于种种原因不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住所时,侦查人员回避这一措施的适用有其客观必然性。
四、一个可能的改革进路
在监视居住制度的改革方向问题上,一直有废存之争。废弃说的根据主要有:监视居住与取保候审的适用对象、范围、条件相当,可以被取保候审所替代;实践中,监视居住容易沦为变相羁押,侵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监视居住执行方式成本高、可操作性差,已基本上不为侦查机关所采用。(15)完善说并不否认监视居住存在重大缺陷,但认为,监视居住在强制措施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有利于保障诉讼顺利进行和减少羁押、兼顾被适用人的合法权益,监视居住在适用中出现的问题主要由立法缺陷所造成,为此,应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而不是予以取消。(16)其实,无论名称如何,监视居住均是各法治发达国家侦查程序中较常用的限制人身自由的替代羁押措施。如意大利的住地逮捕,(17)德国延期执行逮捕令中的限制外出(18)及实践中发展起来的电子监视,(19)法国司法管制中的部分情形,(20)英、美附条件保释中的专人看管与限制外出,(21)等等。与保释/取保候审相比,监视居住是一种更为积极、主动的诉讼监控机制,如果设计与使用得当,更有利于发挥替代羁押、保障犯罪嫌疑人参与诉讼的作用。因此,笔者并不主张取消监视居住,而是持制度完善立场。笔者认为,监视居住制度的改革必须紧紧围绕其实践中的主要问题展开。上文的实证分析表明,监视居住实践的主要问题一个是监视居住的羁押化倾向,另一个是适用率低下。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充分发挥监视居住的诉讼保障作用,笔者建议有针对性地进行制度改革。
(一)解决监视居住羁押化问题的制度改革
解决监视居住羁押化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将监视居住的决定权与执行权分离,将执行权交付司法行政机关。在具体执行中,如果犯罪嫌疑人有违反监视居住适用条件的意图或行为,司法行政机关应及时报告公安机关,由后者决定是否中止监视居住,变更为羁押措施或采用其他惩罚机制。理由如下:
监视居住实践中变相羁押问题曾经较为普遍,其原因在于侦查机关将监视居住场所确定在羁押场所或公安机关的办公场所。为解决这一问题,1998年修改后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98条禁止公安机关建立专门的监视居住场所,禁止在羁押场所或公安机关办公场所执行监视居住。该措施仅仅解决了“将监视居住作为羁押措施使用”的问题,却未能杜绝“监视居住的羁押化倾向”。笔者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监视居住决定权与执行权集中一体。在现行制度中,侦查机关既是监视居住的决定主体,也是执行主体。由于监视居住的效果与侦查利益直接相关,侦查机关会设法使监视居住满足侦查目的需要。同时,侦查机关本身是具有武装性质的权力机关,具有多样化的强制措施,这客观上也为其在监视居住中使用强制手段提供了条件。因此,侦查机关执行监视居住时很难避免强制权的滥用。
进一步的问题是,监视居住可否由基层群众组织或单位负责执行?在1979年刑诉法框架下,监视居住可以由公安机关委托人民公社、被告人的所在单位执行。但实际执行中,受委托执行的单位不愿履行或不能履行职责的情况较突出,使这一措施很难执行或起不到应有的作用。(22)在人员流动增强、外来人员犯罪剧增而社区的社会控制能力有所减弱的情形下,由基层群众组织和相关单位执行监视居住确实不具有普遍的可行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执行监视居住则既能形成对决定权的制约、避免其不当使用,又有专门的人员与机构,具有较强的组织、执行能力。由其负责监视居住的执行,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在执行权的配置上,应赋予司法行政机关监视、跟踪、报告的权力与责任,但禁止其运用物理强制,否则,将不能彻底杜绝监视居住的羁押化问题。
(二)解决监视居住适用率问题的制度改革
以提高监视居住适用率为目的,笔者认为可以同时采用两种方式:
1.将监视居住纳入取保候审
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可以提出取保候审申请,甚至应当获得取保候审的权利,这使较高的取保候审适用率成为可能。相对于取保候审,犯罪嫌疑人不能提出监视居住申请,由此限制了其适用率。从权力—权利关系的角度,监视居住是侦查机关根据案件特点和侦查需要的一种权宜之计,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无关。如果监视居住的适用不能满足侦查利益,或者虽能满足侦查利益但成本过高,侦查机关就很难适用这一措施。将监视居住纳入取保候审体系解决了监视居住权利化的问题,从而使监视居住的适用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启动,而不仅仅是侦查机关单方决定,这就为监视居住适用率的提高创造了条件。(23)同时,在制度层面上,监视居住与取保候审在适用目的、理由和对象方面并无根本不同。根据现行法规定,对于同一名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既可以选择适用取保候审也可适用监视居住,有学者甚至将监视居住理解为取保不能时的弥补措施。(24)这一特点表明,取保候审与监视居住具有较强的兼容性,从而使监视居住被纳入取保候审成为可能。
2.将分散式监视改为集中式监视
现行刑诉法第51条规定,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执行;第57条规定,被监视居住人未经批准不得离开住所,无固定住所的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指定居所。《程序规定》第96条规定,执行监视居住的部门为派出所;第97条规定,公安机关不得建立专门的监视居住场所。上述规定确立了监视居住的分散式监视方式。上文的考察也表明,公安机关确实较严格地执行了这一监视方式。这种监视方式最大的问题是耗费的警力、经费较多,成本较高,很难被频繁使用。有学者主张借鉴德国警方采用的电子监视方式以解决警力不足问题。(25)但是,这种手段需要相应设备、技术的投入,一次性经费投入较多,作为制度性改革措施尚不具有普遍适用的可能。
就当下来说,较具可行性的是以集中式监视替代分散式监视,即由执行主体(司法行政机关)设立专门的监视场所。但这种监视场所不同于羁押场所,无限制自由的外在条件。执行机关可以通过专门人员和设备来实施监视。集中式监视的优点是可以聚合有限的资源,使其发挥最大效用。当然,如果监视居住数量稀少,分散式监视的平均成本可能会低于集中式监视;但如果监视居住适用率提高,集中式监视则更为经济。不仅如此,集中式监视还具有统一管理的优点,可以有效避免分散监视中的随意性问题。对此进行外部监督也较为方便,有助于减少直至杜绝监视居住的羁押化问题。
注释:
①参见陈瑞华:“未决羁押制度的理论反思”,载陈瑞华主编:《未决羁押制度的理论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姚春艳:“论强制替代羁押性措施确立的理论基础”,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12期。
②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7、58条,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程序规定》)第103条。
③迪尔凯姆曾指出:“为了说明某一社会现象,仅仅指出它产生的原因是不够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至少还必须说明在确立社会秩序中的功能。”参见[美]乔纳森·H·特纳著:《社会学理论的结构》,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3页。迪尔凯姆的话揭示了功能主义的一个基本主张,即系统组成部分的存在只能用维持系统整体或社会秩序中的功能来解释。据此,一特定制度的运行状态不能脱离最初确定该制度时所设定的功能及其人们在操作它时为其实际附加的功能,不同制度运行的差异也可以从其功能差异中得到解释。
④课题组通过对Y区、J区公安局监视居住档案进行研究发现,仅有一名侦查人员先后办理过两起监视居住案件,其余办案人员均只办理过一起。课题组认为,从个案角度,该名侦查人员办理监视居住的案件相对较多,无论从适用程序角度还是从执行技术角度均有较多的体验,故可以此两案作为访谈、分析对象。同时,这两起监视居住都得到实际执行,从而与一些以消化案件为目的的监视居住案件有所不同,从功能分析的角度较具价值。
⑤课题组对取保候审的调查与分析表明,与监视居住不同,它的主要功能不是替代羁押而是消化案件,因此,消化案件/案件处理功能成为取保候审制度实证分析的一个重点。比较而言,监视居住尽管在实践中也有消化案件功能,但与替代羁押功能相比,还是要弱得多。并且,其案件消化功能的产生原因与取保候审的情形如出一辙。为了避免重复考察并使问题集中,笔者仅就监视居住的替代羁押功能进行细致分析。
⑥参见周伟:“关于监视居住的几个问题”,载《当代法学》2000年第4期;陈建新:“对监视居住措施实施现状的调查与思考”,载《人大研究》2003年第1期;姚玉林、张伟:“监视居住合理性分析”,载《检察实践》2004年第2期;等等。
⑦访谈情况表明,在三个调研地区中,J区外地人犯罪比例最高,这可能与J区处于S省省会、城市流动人员较多有关。关于外地人犯罪比例情况仅有J区公安局的统计资料能够提供部分线索。在J区公安局,由于资料不全,课题组无法就历年刑事拘留人员中外地人员的比例情况进行统计,但可以根据留置人员中外地人的比例情况及留置转刑拘比例、刑拘人员中被先行留置这三组数据作出推断。在2004年度,1608名留置人员中外地人员有1540人,占95.8%;留置转刑拘人数为682人,当年刑拘总数为1141人。据此可以认为被刑拘的犯罪嫌疑人中,外地人应当占有较大比例。参见《C市公安局J区分局被继续盘问人员情况统计表(2004)》,《J区公安局总体数据统计表》。
⑧参见崔敏著:《中国刑事诉讼法的新发展:刑事诉讼法修改研讨的全面回顾》,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页。
⑨根据陈建新对某地公安分局在1999、2000两年内监视居住情况进行的调查,在603名被监视居住人员中,在治安拘留所执行的就达588人,而在居住地执行的仅有15人。参见陈建新:“对监视居住措施实施现状的调查与思考”,载《人大研究》2003年第1期。
⑩根据李忠诚的介绍,2002年度,我国进入诉讼程序和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适用率约占逮捕的3.8%,参见李忠诚:“如何建立预防和纠正超期羁押的长效机制?主要措施是什么?”,载正义网http://www.jcrb.com/zyw/n180/ca101599,htm,2006年8月10日下载;国内部分地区监视居住适用率较低的情况,可参见徐俊:“浅淡监视居住的适用价值及其完善”,载《政法学刊》2000年第2期;李卫平:“监视居住制度废弃论”,载《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张东红、叶阳:“监视居住的存废尴尬及解决思路”,载《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11)参见J区公安局C派出所《2005年经费支出明细帐》。
(12)J区公安局各办案单位对侦查办案人员均有明确的目标考核要求。以C派出所为例,2005年度每名办案人员的目标要求是破案1件、打击1人。在目标考核导向下,对普通办案人员而言,最重要的是如何在较短时间内尽可能提高破案、打击的数量。耗时费力的监视居住显然并不符合这种“办案经济学原则”。
(13)《程序规定》第98条规定了如下内容:公安机关不得建立专门的监视居住场所,对犯罪嫌疑人变相羁押;不得在看守所、行政拘留所、留置室或者公安机关其他工作场所执行监视居住。
(14)《C市公安局刑事强制措施工作规范(试行)》(2003)第50条规定重申了《程序规定》第98条的要求,扩展了对监视居住场所的限制。它规定“不得在看守所、行政拘留所、收教所、戒毒所、留置室或者公安机关其他工作场所执行监视居住。”
(15)参见李忠诚:“强制措施”,载陈光中、严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方正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201页;姚玉林、张伟:“监视居住强制措施存在的合理性分析”,载《检察实践》2004年第2期;李卫平:“监视居住制度存废论”,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16)参见陈光中:“中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载陈光中、[德]汉斯-约格阿尔布莱希特主编:《中德强制措施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页;杨旺年:“关于监视居住几个问题的探讨”,载《法律科学》2001年第6期;徐俊:“浅谈监视居住的适用价值及其完善”,载《政法学刊》2000年第2期。
(17)参见黄风译:《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84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6页。
(18)见李昌珂译:《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216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1-52页。
(19)参见[德]沃尔夫厄姆·谢德勒:“德国刑事诉讼法的保释与其他非尖锐性措施条款”,载陈光中、[德]汉斯-约格阿尔布莱希特主编:《中德强制措施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161页。
(20)参见余叔通、谢朝华译:《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3-65页。
(21)参见孙长永著:《侦查程序与人权》,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245页。
(22)参见崔敏著:《中国刑事诉讼法的新发展: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全面回顾》,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5页。
(23)当然,监视居住权利化的改革仅仅是提高了它的适用机会。如果取保候审的决定主体仍是侦查机关,决定过程仍然遵循行政化的内部审批程序,犯罪嫌疑人即使有权利提出申请亦很难获得批准。在此意义上,监视居住制度改革应与取保候审同步进行,即采用外部/司法化的审查机制。
(24)参见徐俊:“浅谈监视居住的适用价值及其完善”,载《政法学刊》2000年第2期。
(25)电子监视方式是借助传感器等电子仪器的方式监控犯罪嫌疑人在住所内或外出,以方便监视机关及时采取相关行动。在2003年中德刑事强制措施的交流研讨会中,德国马普研究所的阿尔布莱希特教授提及电子监视在德国的运用,沃尔夫厄姆、谢德勒检察官详细地介绍了这种措施的实施过程与效果,他评价称“迄今为止,电子监控是避免审前羁押的执行的非尖锐措施中最为精确、最为可靠的手段。”参见[德]汉斯-约格阿尔布莱希特:“审关羁押——实证的情况”,载陈光中、[德]汉斯-约格阿尔布莱希特主编:《中德强制措施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7页;[德]沃尔夫厄姆·谢德勒:“德国刑事诉讼法的保释与其他非尖锐性措施条款”,载上引书第159-1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