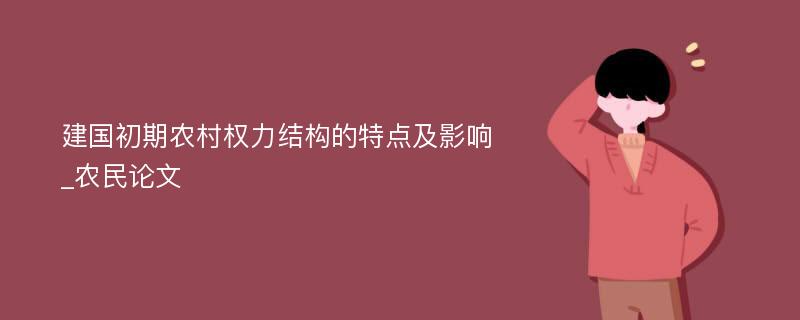
建国初期农村权力结构的特征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权力论文,特征论文,农村论文,结构论文,建国初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4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01)05-0051-03
农村权力结构是指农村决策权力在各个阶层的分配状态,具体表现为决策人士的阶层构成及组织形式。20世纪初叶,国家权力开始在农村渗透,但都因未能达到充分整合而失败。一个发达的、非正式的潜在权力系统——民间宗法系统一直在农村占据主导地位。建国初期,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乡村改造运动(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农村权力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民间宗法系统趋于瓦解,呈现出相对集中的走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地位的划分是权力阶层分野的基础,贫下中农成为农村的主权阶层。
我国是农业大国,土地改革是我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自20世纪20年代起,为了实现“耕者有其田”,“两党的争论,就其社会性质来说,实质是在农村关系的问题上”。(注:《毛泽东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7页。)新中国成立后,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新的解放区继续根据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总路线进行土地革命。在土改中,阶级划分是中心环节。贫困成为贫雇农身份的骄傲和获得地位的条件,他们因此分得了大致相等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社会地位由过去的最底层而一跃居于首位。许多积极分子还成了地方领导。据湖南省统计,到土改结束时新建的13274个乡中,9443个乡的乡长、乡农协主席、团支书、民兵队长、妇女会主任等主要干部47215人,95%以上是翻了身的农民。但是,与富农相比,贫雇农的经济实力显得单薄,加上他们文化知识和管理经验有限,这些因素影响着他们掌握政权。此时,国家派遣了大量的工作队到基层帮助贫雇农开展工作。在划分阶级成分、组织农民队伍和选拔积极分子进入政权组织等方面,工作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相应地,在权力结构中,绅士或地主阶级成为底层一极。土改时,他们的土地被没收,财产被分割,虽然手中还有一部分土地和财产,但是政治权力再分配没有按经济均值方向设计,“他们失去的还有按M·韦伯观点同样代表一个阶级社会地位高低的声望”。(注: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8页。)他们不仅以往养尊处优的地位丧失殆尽,而且成了批斗、控诉的对象和管制、镇压的对象。
夹在上述两阶层之间的是中农阶级。党的政策是保护中农、联合中农的。因而,中农的经济地位没有受到冲击,并有继续上升的趋势。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旦阶级成分被划定,便脱离了政治主流。也有一些人在贫雇农尚未发动和未能充当主要政治角色的时期和地方,往往取而代之充当着领导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农业合作化期间,贫雇农人口由土改前的70%下降到30%,中农人口比例从土改前的20%上升到60%。尽管农村中农化趋势明显,但党中央和毛泽东仍未放弃由贫苦农民管理合作社的思想。在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序时,毛泽东专门强调“树立贫农的优势”。为巩固合作社,1955年7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对我国中农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作了进一步分析,把新老中农中的下中农从中农里区分了出来。他认为:“合作社的领导机关必须建立现有贫农和新下中农在领导机关中的优势。”(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38页。)根据这一意见,已建立的合作社如果未能保证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则必须解散或改组。“调整后合作社的领导干部,贫下中农居于领导地位,即优势地位。”(注:高化民:《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页。)
第二,农民协会、互助组、合作社等政治经济组织各自发挥作用,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土地改革带来了农村权力结构的变化,也调动了广大农民参与政治的热情。在工作队的领导下,各地纷纷成立了新的权力机构——农民协会。农民协会既是村民自治组织,又是土地改革中的合法执行机关。其主要领导人在贫雇农中挑选。为了联合中农,当时还提出要保证中农占农民协会领导成分1/3的数目。(注: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新华月报》,1950年第7号。)农民协会在没收地主土地和财产分配给农民、组织农民生产、中障农民享有政治权力等方面起了重大作用,树立了较高的威信。贫雇农也正是通过农民协会,掌握了农村政权,成了农村的主人。
土地改革完成后,农村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党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采纳了毛泽东的立即否定私有制逐步向集体化过渡的建议。(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94页。)这样,我国农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它一改我国传统农村一直依靠家庭组织生产的格局,创建了农村新的政治经济组织。
我国农业合作化采取的是由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的形式稳步前进的。最初创立的是互助组,它没有触及到生产资料私有制,在组织上具有松散性、简单性和多样性的特征,往往出现“春组织,夏散伙”的现象。从1953年开始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初级社),组织化程度大为提高。初级社下设生产队,它的领导机构是管理委员会,委员会主任又是合作社主任,生产队长和直属生产组长由管理委员会委派。合作社的主任有权检查、监督生产队、生产组的种植计划,达到统一计划、统一调配、统一生产经营和统一收益分配。
如果说初级社的创建是出于推进农村经济发展的话,那么,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的高级社则更多地出于政治需要,渗入了更多的政治动机。高级社在生产、劳动、分配和生活方面都高度组织化。从内部组织设置上看,它分为三个部分:社员大会、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社主任和副主任。高级社的行政属性明显,它不仅要管理和组织农村经济活动,还要负起对社员进行政治教育、维护农村社会秩序、执行上级行政部门的命令、发展农村文化等任务和责任。可以说,它是农村权力结构走向高度集中形态的前奏。
第三,党组织开始在乡村蓬勃发展,党员分子是农村各组织的领导者。
在推进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乡村开始建立党组织。1954年11月,中央组织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工作会议。“会议前,全国22万个乡中,已有17万个乡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农村党员近400万人,占农村人口的0.8%。”(注:李炼忠等:《基层党组织建设新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针对党的发展不平衡,这次会议确定在1955-1957年的三年内,农村发展党员200万到300万,并提出在农业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中建立党小组,党员多的还可以建立分支部。此后,党员和党组织蓬勃发展,党员分子成为农村各组织的领导者。到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全部国家生活中居于领导地位。
第四,社会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家族势力逐渐削弱。
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不仅重构了农村的权力结构,还沉重地打击了旧有的家族组织。在土地改革中,家族活动的寺庙、祠堂、族田等财产被没收,家谱被焚,家族活动被禁止。由于家族组织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仪式基础被毁,它也失去了控制其同族亲属的基础。在合作化运动中,生产的统一经营,按土地入股和劳动比例分配的原则的贯彻,统购统销体制的推行,使家族的生产功能进一步削弱。经过合作化,分散的小农经济被改造成了集体经济,农民加入了超家族共同体的集体组织,家族组织失去了其凝聚力。在此基础上,行政力量还对一些地方的社区格局作了有力的干预、调整和组合,形成了混合的、杂居的新的行政格局。
综上所述,建国初期我国农村权力结构呈现出相对集中特征。那么,这种权力结构对我国社会的现代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布莱克教授曾把现代化分为内生型现代化和外生刺激型现代化两种模式,并认为在外生刺激型现代化国家,建造一个强大的能有计划地推动现代化建设的政府系统是必不可少的。(注: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我国是一个外生刺激型现代化国家。建国初期农村权力结构的相对集中形态有利于政府直接介入现代化进程,从而实行国家的现代化计划。从一定意义上说,它符合了后现代化国家的发展之路。
首先,相对集中型的权力结构有利于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土地改革和合作化,农村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的农村政权代表了三亿农民的利益,农民从中体会到翻身的喜悦,生产热情高涨。此外,新的权力结构实行权力相对集中,政治、经济组织各自发挥作用,也符合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原则,因此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从1949年到1955年合作化前的6年时间里,农业总产值由326亿元增加到550亿元,增长70%,每年递增9.3%;粮食总产量由2162亿斤增加到3496亿斤,增长61%,每年递增8.3%;农民生活有很显著的改善,农业人口每年平均纯收入由48元增加到72元,增长50%,每年递增7%。
其次,相对集中型的权力结构有利于当时的社会动员。所谓社会动员,就是“现代化领导集团引导、组织和推动传统社会成员向现代人转化的变迁过程;引导、组织和推动全体社会成员(反现代化社会成员除外)将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的过程”。(注:张静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现代化》,湖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历史的国家,农民是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的群体。建国后,以贫雇农为核心的权力结构的建立,调动了广大农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长期以来他们由于受压迫而难以分享权力资源所形成的政治冷漠性格。通过政治动员,国家把农民吸引到国家目标之上,使他们认同了自己在现代化中的地位,也承担起现代化建设的重任。
再次,相对集中型的权力结构也有利于社会整合。在1949年以前,中国农村社会缺乏有利于现代化发展的组织,社会整合层次较低。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曾痛心疾首地把广大农村比作“一盘散沙”,形象地说明了农村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大难题。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粉碎了长期统治中国农村的封建势力。农村权力结构为与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相一致得以重建,并形成相对集中形态。它使农村社会与政府紧密地连在一起,“增加了国家(和共产党)的直接影响,扫除基于财产和地方积累起来的权力之上的权威,把对血亲的忠诚转向对新发展起来的法人团体即集体的忠诚”。(注: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8页。)国家藉此达到了对农村高度整合的目的。它清除了半个世纪以来农村的大动荡,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了良好的环境。尽管建国后的20多年里曾反复出现政治运动,但是在稳定的农村的烘托与支撑下,中国由农业社会转为工业社会的进程却基本上没有中断过。
[收稿日期]2001-0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