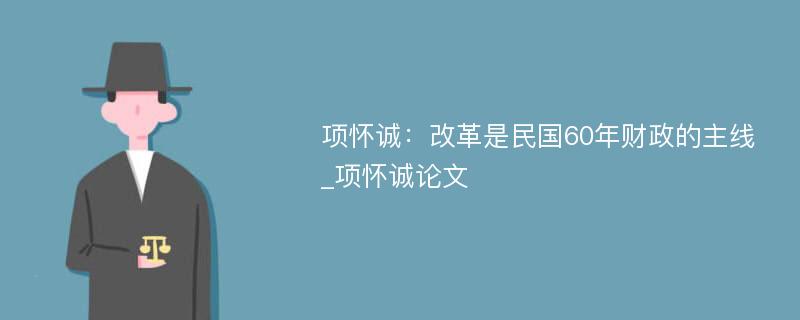
项怀诚:改革是共和国财政60年的主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和国论文,主线论文,财政论文,项怀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是共和国财政60年的主线
《经济观察报》:从你的个人经验出发,你如何认识从1949年到1978年的财政改革与调整?
项怀诚:解放初期,财政部缺钱,财政收入主要是公粮,一切为了前线。1953年之后,国家的工作重点首次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财政处在建设阶段,就是毛泽东说的两句话“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1978年之前,这一直是财政工作的目标。我们经常要计算每年的财政支出里面有多少钱、多少比例是用于建设的。但是那时体制不好,工业产值增加很多,但效益不好,GDP虽然有很大增长,但产品存量不多,人民生活没有多大改善。中国经济走上了一条消耗大、成本高、效益差的道路。
建国后财政体制的变化偏多,财政体制本身缺乏稳定。偏多到什么程度呢?平均每三年就要变一次财政体制,最短的一次只存在了一年,最长的也只不过五六年。在这个体制之下,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制度安排不稳定,变化无常,原因其实不是人的问题,而是体制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那么前三十年财政体制改革的主线就是寻找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合理权力界限?
项怀诚:对,就是财政权集中到什么程度,用什么制度保证的问题。我们摸索了三十年,做了很多有益的尝试。所以,不能说财政改革只是后三十年的事。
大略地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事实上是无可奈何地学习苏联。苏联派来了很多顾问,当时各部委都有苏联的顾问,财政部也有。苏联专家帮助中国建立苏联模式。其实,中国内部也在探索,陈云就对苏联的东西做了很多修改,不是完全照搬苏联的那一套。财政改革前三十年有过很多探索,包括“分灶吃饭”、“包干制”、“总额分成”以及我们现在进行的“分税制”等。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当初搞这些东西没有成功?
项怀诚:主要原因是条件不具备。但是不能否认,改革是六十年财政政策一个主线,六十年里财政始终是处在改革中。前三十年已经做了很多探索、很多实践,当时的改革绝不能抹杀,不能说中国财政改革就是后三十年的事。事实上,前三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财政体制改革,为后三十年的改革进行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探索,为后三十年的改革打下了基础。从大脉络上讲,60年的改革实际上是财政由高度集中向分级分权转变的过程,是财政管理逐渐科学化、规范化的过程。
财政包干
《经济观察报》:改革开放之初,财政形势如何?
项怀诚:当时国民经济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财政非常脆弱了,赤字率很高,很危险。1980年发生了“吴赵大战”,就是吴波和赵紫阳之间的争论。赵紫阳主张“包干制”,吴波主张“分灶制”。当时赵紫阳还没有到北京工作,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省委第一书记。当然,吴波从来不承认“吴赵大战”,他说他只不过是作为一个下级讲了应该讲的意见,并没有“战争”。后来中央会议决定采取包干制。
《经济观察报》:那么在分税制实行之前,主要实行的财政体制就是包干制?
项怀诚:尽管在一段时间里面有变化,但是就其性质来讲,主要是实行包干的体制。实际上包干体制是改革开放以后,为了解决激励机制不足,在没有完善的法制条件下出现的一种过渡办法。最早是从安徽的凤阳小岗村开始的农村大包干,后来这种包干制度就被引入企业,最后也被引入了财政制度里。当时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也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怎样使地方政府尽可能地放心,实行包干制度是可以部分解决这个问题的。在体制多变的情况下,包干体制能够起到调动积极性的作用,但是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当时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不是太快,中央财政增长的速度相对而言更慢一些。那个时候一年财政收入能够增加一二百亿就不错了。
《经济观察报》:实现包干制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什么样的状况?
项怀诚: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实行减税让利,在减税让利政策的前提下,把一部分财政收入有意识地让给企业,增加企业的活力。1980年到1990年,GDP的平均增长率为9.5%,可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却逐年下降,1979年为28.4%,1980年就下降到25.7%,到1993年则降到12.6%,总降幅为15.8个百分点,大体上每年的降幅超过一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在整个的财政分配之中,中央财政的收入分配不占主导地位,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不断下降,从1984年的41.5%降到1993年的22%。所以中央财政的发言权就相对比较小。当时国门已经打开,我接触了很多人,包括台湾的前“财政部长”陆润康。他说台湾的财政是“弱干强枝”,中央比较弱,地方比较强,这在台湾是不行的,在内地更是不行的。
《经济观察报》:这番话对你有何影响?
项怀诚:我认识到,中央集中一定的财力是有必要的。1987年我到南斯拉夫去考察,南斯拉夫当时有个副部长叫奥格奥夫斯基,是个经济学家,他跟我说,南斯拉夫的中央财政占国民收入比例太低了,仅有11%,他担心国家要出事。果然,我回国后不久,南斯拉夫就出事了。
《经济观察报》:当时中国的中央财政状况与南斯拉夫相似?
项怀诚:中国的情况与南斯拉夫不同。我们除了预算内收入以外,还有一部分预算外收入和政府性收费。所以比较不同的国家时要慎重。但无论如何,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在逐年下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太低,财政部很窘迫,当时有“悬崖边上的中央财政”的说法。由于中央财政收入严重不足,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初,甚至发生过两次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借钱”而且不还的事。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在急呼缺钱,如粮食收购财政亏损补贴资金不到位,铁路、民航、港口等重点建设资金不到位等。当时连某些中央机关都已经到了不借钱工资就发不出去的境地。我的前任刘仲藜部长三次找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希望他批条子向银行借钱,朱镕基不允许。可见,包干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1993年7月23日,全国财政、税务工作会议召开。朱镕基副总理来到会场,对所有与会者说:“在现行体制下,中央财政十分困难。现在不改革,中央财政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如果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到不了2000年(中央财政)就会垮台!”
分税制改革
《经济观察报》:分税制改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确立起来的?
项怀诚:分税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很早就有的,世界各国普遍实行。到1993年我们搞分税制的时候,世界上大体有三种不同的分税制类型,即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的联邦式分税制,以英国、法国为代表的集权式分税制,以及以日本、意大利为代表的混合式分税制。当时我们推行的分税制,比较接近集权式分税制。
《经济观察报》:分税制改革是怎么推行的呢?
项怀诚:1993年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率走高。当时中央派了13个部长到了26个省市调查研究,最后形成了13条建议。朱镕基当时是主管经济工作的常务副总理,他开玩笑说13条建议不吉利,应该加几条,后来加了3条,形成了16条,这就是1993年的《中共中央6号文件》。这个文件非常重要,为经济体制改革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对于分税制的展开起了非常大的作用。1993年下半年,我们几乎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分税制改革上,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其中许多是非常紧急的,因为上上下下并不熟悉分税制。财政部部长刘仲藜在北京龙泉宾馆主持召开了一次体制改革座谈会,我当时是常务副部长,在会上做了个发言,第一次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分税制。差不多同时,时任国家税务总局党组书记的金鑫再次向中央汇报了工商税制改革的方案,并经中央同意。在分税制改革方面,龙泉宾馆会议对统一思想非常有益,随后工商税制改革和分税制改革就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了。1993年下半年,财政部和税务总局的两个办公楼经常在夜晚灯火通明。当时计算机已得到普遍使用,效率大大提高。那年我还开了很多座谈会,就工商税制改革和分税制改革听取各方面意见,这次可能是历史上历次改革中听取意见最充分的一次了。
《经济观察报》:在你的回忆文章里,你实事求是地记载了你们与朱镕基在分税制问题上出现的争论。
项怀诚:我们主要是对以1993年为基数有异议。朱镕基就分税制改革调研去的第一站是海南,第二站是广东,财政部部长刘仲藜同志随行。以1993年的财政收入为税收返还基数,就是广东省汇报工作时提出的。后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决定以1993年为税收返还基期年,这在当时是个非常大的政策。当时我和刘仲藜都不大同意以当年为基数。但当然,财政部绝对会执行中央的政策。我们当时主要担心地方的数字弄虚作假,担心今年中央财政收入上去了,明年又无以为继。实际上,在宣布以1993年为基数后的几个月里,确实出现了一些异常情况,比如一些企业向银行贷款交税,甚至倒闭的企业都把以前的税补齐了,凡此种种,造成了1993年后4个月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
《经济观察报》:这对1994年的财政收入有没有影响?
项怀诚:这是我最担心的,因为我是分管预算的副部长。在1994年1月,我是忧心忡忡,寝不安席。到了1994年2月8日,1月份的财政收支报表出来了,收入为27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6亿元,增幅为62%,这是从来没有过的速度。我高兴得不得了,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财政收入数据显示,1994年每个月的财政收入都比上年同期增加,全年财政收入增长了869亿元,比上年增加20%,是以前历史上少有的。自1994年实施财政改革以来,到2007年已经14年了,财政工作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财政收入由1993年的4349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51300亿元,14年平均年增3354亿元,平均年增长19.3%。这一切充分说明了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功不可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次广泛而深刻的改革,它奠定了中国特色改革的基础。
《经济观察报》:这时回顾你与朱镕基的争论,你怎么想?
项怀诚:现在我对于以1993年为基数的政策已经心悦诚服。这个政策说明,在推进重大的财税改革时,必须要取得地方政府的强有力支持。这是必要的妥协,这个代价必须付出,这一让步争取了民心,统一了思想,保证了分税制改革的顺利推行。朱镕基说过一句话:“对财税体制取得的成功,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经济观察报》:1998年你上任的时候,恰逢亚洲金融危机,当时的感受如何?
项怀诚:1998年3月我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根据党的十五大精神,财政政策是适度从紧的,力图缩小财政赤字。但那时经济形势不好,朱镕基有一个比喻说:“我使劲踩油门,但是经济就是上不去”。我记得马路上到处都是“大减价”、“跳楼价”,商品卖不出去,生产过热,银行贷款也没人贷。1998年6月,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对财政政策转型的想法。我认为财政政策见效比较快,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长一些、慢一些。当时我国的基础设施比较差,可以加大投入。很快高层就做出了决策。当时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投资方向,包括水利、机场、农村电网、高速公路等。当时财政部手里没多少钱,要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压力很大,最后国家决定发1000亿元国债。
改革的体会
《经济观察报》:你参与多项改革,有哪些体会和心得?
项怀诚:体会很多,笼统地说有这么几点。
第一,财政体制改革要正确地把握财政和财权的集中程度。在集权和分权之间找寻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这是我们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几十年来的财政体制改革始终围绕的核心。
《经济观察报》:到底什么是合理的?
项怀诚:每一个时期是不完全一样的,有的时候要相对集中一点,有的时候可以相对分散一点,都是为时代服务的。比如说解放初期,朝鲜战争正在进行,中央提出来“边抗、边建、边稳”的“三边政策”。在这个时候,政府就要集中了。到改革开放初期,政府的权力是过于集中了,企业没有活力了,地方没有活力了,所以就要分散一点,来激发、调动积极性,所以20世纪50年代的“统收统支”是对的,20世纪80年代的适当分散、调动积极性也是对的,因为历史背景不一样。我认为,财政收入中,中央政府至少要保持55%—60%。这是我们中央政府实施宏观调控必要的基础。
第二个体会,财政体系要相对地稳定。多变不是办法,会造成上下互相猜忌,地方上没有稳定的预期。所以,在一个时期里财政体制要相对稳定,这是一种制度保证。
第三个体会,财政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侧面,是配套改革的一个方面,所以既不能滞后,也不宜孤军深入,就跟打仗一样,一定要照顾大局。这是个突破口,但是决定胜负的不是这个突破口。
第四个体会,财政体制的调整实际上就是利益的调整,是利益分配关系的调整。任何调整都涉及方方面面利益的增减,所以一定要非常地慎重。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主张财政体制要实行渐进的改革,缓缓而行,稳步前进,可谨慎一些,不要冒进。我们做财政工作的干部经常被描写成为保守分子,我觉得很正常,我从来不讳言、也不害怕人家说我保守。
第五个体会,财政改革要有长期打算,不要期望毕其功于一役。我们搞成功的这一次财政改革,是由前三十年的历届老同志为我们打下了基础,我们现在的任务是为后人打基础。
第六个体会,重在制度建设,要有制度创新。我做分管预算的财政部副部长时,中央财政的压力很大。我当时想,有没有一种制度本身就对减免税有限制作用?经济学家跟我说,世界上就有现成制度,就是增值税。我就到欧洲去考察增值税,觉得增值税确实是有道理的,在增值环节收税,前面已经交了税了可以抵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这样我们就引入了增值税,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一个好的财政体制应该具备哪些要素?
项怀诚:一个好的财政体制有以下几个衡量的标准:第一,要能够调动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第二,要体现合理的分配或调节,要体现国家发展过程基本的分配关系;第三,要保证财政收入在经济发展、流通扩大的基础上稳定地增长;第四,分配要日益合理化,财政的分配要能够逐步地体现公共财政的理念;第五,财政体制的改革结果有利于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最后,财政改革要支持、促进其他经济体制的改革,包括税收、金融、物价、能源等体制改革。
《经济观察报》:总体上你对中国60年的财政有何评价?
项怀诚:如果以一个财政干部的角度来讲中国60年的财政,我并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共和国60年,我到财政部工作将近50年,其中有一半的时间是做财政部最基层的干部,后来的20多年走到财政部领导岗位上。但不管是当一般干部也好,还是做部长、副部长也好,从中国财政60年历史来说,我都不是决策者。只能说见证了一部分历史。
《经济观察报》:而且也参与创造了历史?
项怀诚:这不敢说。因为有各种局限,对历史的偏见都是避免不了的。如果说这一代人在思想上完全是市场经济的思想,实际上是说假话。我们这些人身上永远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痕迹,这种痕迹是少一点还是多一点,在于我们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对中央的精神理解是深一点还是浅一点,跟中央的步伐是快一点还是慢一点,对自己的要求是高一点还是低一点,如此而已。
《经济观察报》:也有一个学习能力问题。
项怀诚:也有一个悟性问题。今天要我来讲中国财政的60年,不可避免地带有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过程中间,在思想上最崇拜、影响最深刻的是谁呢?是陈云、张劲夫、吴波、王丙乾等人指点我们工作,影响我们的为人,这是近距离的。陈云和我们没有近距离接触,但是我们从参加工作以后,就不断地听到陈云指导经济工作的事情。比如,在解放初期,他在上海指挥统购统销的战役,成就辉煌。现在来看,统购统销似乎有问题,但是当时非常实用。陈云同志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任财经委员会主任,他提出了很多观点,尤其是他提出的“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对我们的思想影响深远。再如,他提出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要“比较、交换、反复”,多少年来我们就是这么实践过来的。在吴波、王丙乾同志家里都有陈云写的条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都对陈云心存感激。
《经济观察报》:共和国60年的财政历史给你什么样的思考?
项怀诚:我们走过的60年是一个摸索的过程,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人在当时就清清楚楚地知道,10年以后怎么样,20年以后怎么样。我们不可能在20世纪50年代时期就想到这些,我们也不可能在20世纪60年代就想到今天怎么样,我们是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摸索、不断地完善。在60年中,我们应对了很多挑战,包括美国对我们的封锁、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苏联撤毁协议、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也包括改革开放出现的新问题和思想的混乱。我们的60年,不是高歌猛进的60年,不是莺歌燕舞的60年,而是充满了挑战、充满了艰难探索的60年,是既有丰富的经验、又有很多深刻教训的60年。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是摇摇摆摆走过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特别谨慎:第一,不要感觉太好;第二,碰到问题以后也不用灰心丧气。老实说,我们历史上碰到的困难比现在碰到的困难深刻得多,严重得多,今天我们碰到什么困难?无非一个就是世界性的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我们现在有6万多亿财政收入,有2万多亿外汇储备,和当年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既不要感觉太好,以为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一了,也不要妄自菲薄。财政改革在发展中,方向是公共财政。改革任重道远,需要继续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