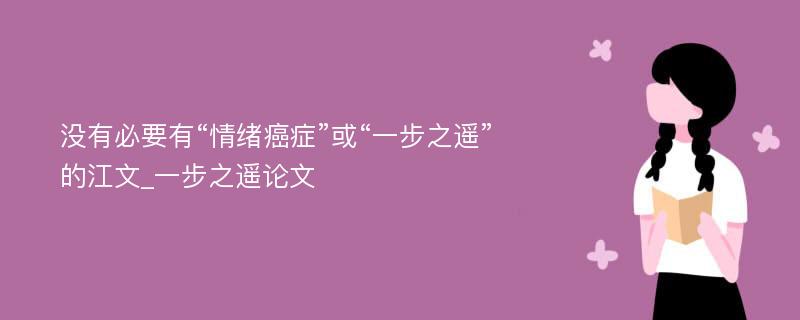
莫须有的“情怀癌”或与姜文的“一步之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莫须有论文,或与论文,之遥论文,情怀论文,姜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年来电影票房的火爆已经成为一个新常态。年轻人成双成对涌向电影院,随便一部什么国产片就是上亿的票房,这使我们已经不用怀疑就可认定影视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主导文化。如果考虑到互联网、移动终端,再想想苹果的辉煌业绩,我们不用论证就可以感受一个视听文明的时代正在到来。虽然这个时代已经被定义为第三次产业革命时代,或者电子科技产业主导的后工业化时代,但更准确地从文明变革角度来看,相对于此前的口传文明和书写文明,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个视听文明到来的时代。 中国在视听科技与视听艺术领域,还只是扮演消费者的角色,在视听科技方面没有任何的技术主导能力,最成功的是做出微信这种应用和小米手机这种二流的模仿科技。在视听艺术方面更是无所作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为“中国故事”还有市场,《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站台》之类还有国际关注度。到了新世纪,中国电影除了小制作打点“地下”、“独立”牌,很难吸引欧美电影人或国外普通观众眼球。现在,各方面都在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这张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是大有作为的。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也要对文明变更有深刻认识,如果还是老一套思维,历史演绎,现实悲情或假大空的欺瞒占据主导地位,也不可能讲好“中国故事”。中国的影视创作和传播,目前还是延续旧有的观念的手法,几乎很难看出多少创新性的作品,个人的才情已经被对消费市场和娱乐观众的适应全部抹煞。我们甚至想当然认为,电影就是娱乐化的产品,观众就是上帝。我们甚至不相信艺术产品也能培养接受它的公众(除了在非艺术的层面强行灌输)。公众虽然在每一个当下就能决定艺术产品的价值和意义;但公众说到底是艺术产品培养和制造出来的。就此而言,永远适应公众、不能挑战和冒犯公众的艺术家是没有出息的艺术家。 公众说到底是艺术产品培养和制造出来的 2014年有两部电影同时上映,这就是姜文的《一步之遥》(以下简称《一步》)和徐克的《智取威虎山》(以下简称《智取》),前者比后者早上市五天,却抵挡不住后者强大的群众基础。后者几乎可以说是好评如潮,点赞一片。上映第一天,有网友统计,该片已收获一千二百六十三条好评,差评只有三十二条。这与《一步之遥》几乎是骂声一片,形成鲜明对比。曾经神气活现的姜文哪曾想到,重拍一下《智取威虎山》就使《一步之遥》相形见绌,岂止是相形见绌,简直就是让姜文无地自容。姜文之所以没有一头撞死,不是因为他有多么坚强大度,而是他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一步之遥》是一部预言性电影,它有一只脚跨进了另一个时代——就此而言,姜文(以及我们)很长时间都不会理解这一点。 去读读那些恶评,足以让英雄气短。仅仅几天之内就有两千多篇,几乎是一边倒的骂声。题目就极为刺激:《几乎一无是处的电影和“死”于情怀癌的姜文》,或者干脆称它为《一部极其自恋的个人主义精神病作品》。本文不想去比较两部电影的优劣,只有一点是十分清晰的,《智取》只是一个现成的改编样板戏的并无个人创新举措的作品,加入的新的戏份和线索,情理不通,故事不顺。片中的智取威虎山的特技场景是其渲染的看点之一,片尾座山雕驾机逃跑的场景直至挂在悬崖峭壁上的生死瞬间,也不过是对好莱坞的全面模仿。这些已经算是中国电影中超级震撼大场面,放在好莱坞也不过是二三流的场面而已。稍加推敲,影片的大逻辑和小逻辑在今天的语境中都难以成立。所谓大逻辑,即东北剿匪,歼灭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然而,有历史资料表明,东北被剿的这些“土匪”乃是当年抗日颇为顽强的队伍。另一边的电影电视正是国军与共军合作的“抗日神剧”上演正酣,且如今台湾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也是大势所趋。那一段历史如果讲究历史真实性的话,今天的现实语境很难让其自圆其说。当然,现在的《智取威虎山》也深知这一点,土匪就是土匪,他们的罪恶在于残害老百姓,与国民党无关。就故事性的内在自恰逻辑而言,新加进去的栓子和青莲的故事,原是《林海雪原》少剑波和少女护士白茹的朦胧爱情,现在则变成栓子找母亲青莲,母亲青莲想儿子的故事。隐约萌动的爱情在小说中描写楚楚动人,放在一个大运作的电影里就没有效果;于是就改为母子情感,但是,在电影里,这条线索却要在数个关键时刻起作用,因而变得经不住一点推敲。例如,杨子荣和战士要冒着暴露的危险去追回跑掉的栓子,栓子要拖子弹箱等等。尤其是杨子荣面对青莲的勾引,在不明白青莲的任何底细和真实动机的情形下,会说出栓子想念母亲青莲的事,这等于立即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其他姑且不论,就这条加入的线索,也可谓漏洞百出,不合当时当地情理逻辑。所有这些小逻辑小情理,对动作片大师徐克来说,均不足挂齿。或许他是参透了“视听”艺术这本经的人,他需要的是那些能表现视听的场面和情节,一切都以视听的场景为中心来展开电影叙事,不再是依凭故事性的内在关节或真实的情感关联。事实上,这部电影少剑波和白茹的形象几乎没有给人印象,就剩下杨子荣和座山雕。但是杨子荣内含的性格,关于历史正义、勇敢、冒险、心细、随机应变等等,已经让位于各个场面的戏剧性刻画,也让位给诸多的战争打斗场面,枪炮、火药和山体倒是占据着一个又一个镜头。至于座山雕,他主要是用于猎奇和谐谑,他既不具有历史真实性,也不表明人类命运之类的暗喻,他几乎就是一个符号化的角色,真正是一个电影中的丑角,如此而已。 我们再看看姜文的《一步》。在恶评如潮的阻击下,这部电影节节败退,原来气壮如牛扬言要二十亿的票房,结果就在12月23日上映第五天又遭遇《智取》阻击,立即溃不成军,从黄金时间档退下。随着《智取》声望与日俱增,《一步》票房急剧下降,止步于四五亿之间。很多人是为了验证是不是真的如影评所言那么差才走进影院去看《一步》,比如我就是出于这种心理。我进电影院时,《一步》已经是强弩之末,颓局已定。我前后左右都是年轻人,都愤愤然表示看不懂。电影终场,偌大的电影院只有我一人站起来鼓掌,前排某个观众犹豫不决地应和了几下声。我在想,偌大的中国,总算还有五六个亿的票房,到底有多少人看了电影不表示很不爽呢?又有几个人看明白姜文的电影呢?那么多号称职业影评人,有那么精深的电影修养,如果《一步之遥》都不能接受,我觉得这不是姜文的失败,也不是酷评挟中国电影观众的胜利,它是一次恶作剧的成功罢了。 如果《一步之遥》都不能接受,我觉得这不是姜文的失败,它是一次恶作剧的成功罢了 《一步之遥》确实是姜文以个人的思考介入电影,甚至强行介入现实,这部说着历史的电影有着强烈的现实感,在历史、个人与现实之间建立起强大的反讽语境,这就是这部电影的不同凡响之处。这样的独门绝技,如何让大多数人接受呢?但中国有句老话,过去走江湖的开场白就得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观众懂不懂不要紧,看热闹就行——这部电影热闹得还不可以吗?影片的主导故事很清楚,“花国总统”完颜英意外死亡,作为最大嫌疑人的马走日只有四处潜逃,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虚假故事在舞台上被王天王一场又一场拙劣地表演,最后武六借拍电影之名,帮助马走日越狱,结果二人被追捕,马走日被击毙身亡。这个故事的情节结构很清晰,且还有原型民国时期的阎瑞生案做底,不存在什么情节不连贯,看不明白。至于其中插入的无厘头、插科打诨的细节或台词,正是对这段历史故事的拆解和反讽。就普通观众的观赏性而言,也是够热闹的:那么大的选美场面,那么多的大腿,还抖碎了五个暖瓶,飞向月球,还有王天王的大砍刀表演……这对得起观众了,还不够爽吗? 门道呢?那些号称电影行家里手的,总可以耐着性子看看门道吧?姜文确实有点恃才傲物,那不是什么“情怀癌”,是勇气,是才华!这部影片的主题其实是很明了的,只是因为我们已经麻木,习惯于装作不知道,故这样的主题看上去就陌生了。不和陌生人说话,这已经是我们生活的自觉守则。这部电影说到底,借着一个历史故事,说的是如此盛大的繁华,不就是虚假、空洞、屎么?从电影的开场武七说一个意大利女子要吃什么豆腐,气锅到底有气没有气之类,这是明摆着瞎白活。观众看到这里可能就已经无法忍受了,这么胡扯还没完没了,这是干什么呢?难道姜文真的脑残了吗?随后的选美也是一派胡扯,矫揉造作,盛大的繁华累赘拖沓,反复炫耀的大腿舞,让人疑心姜文是彻底完蛋了。影片到了这里,冒出了I do,那是作死,那是拉屎,这才看出,这属于恶搞嘛。有这么大胆恶搞的吗?前面不是说老莎翁的那句严肃得顶天立地的经典台词“生还是死(to be not to be)?现在突然间一个“I do”要拉屎,这不是把生与死给刷格了吗?这是要屎里觅道啊!这么搞的电影还真是没有见过,也是从这里,如果这部电影不是乱搞,那就一定有非凡之处啊!无论如何,姜文,九个人精一样的编剧,总是多少可以信任一点吧?我也是看到这里,才耐下心来思索一下姜文这样搞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一方面,他是有勇气要揭示点什么;另一方面,他被逼无奈,想想在中国,有话能好好说么? 整部电影的表层故事是关于爱、友情、信义与背叛,内里却是对历史与现实的空洞化(虚无化)的彻底拆穿。中国的电影何尝表现过这样的主题呢?中国哪一个导演有能力去面对这样的问题呢?这其实是百年中国历史、今日中国现实遗留或隐藏在最后的根本问题。其要点就在于,没有真实的爱,没有真实的友情,没有真正的信义!对虚假化和虚无化的表现,影片两次煞有介事地说到“I do”——那就是屎啊!多么大的悲哀!这部电影内里的灵动竟然是靠着悲愤的情绪,愤怒出诗人,这部电影难道不是诗吗?难道不是有一种诗的情怀吗?怎么就是“情怀癌”呢?其实姜文就是个孩子,他装逼,因为他就是赤裸的,他要指认其他的赤裸,他天真率直、自以为是,不信邪,他就这样了,还能怎样?孩子般的天真啊,确实有点“童心未泯”呢!姜文也半老不小了,说他孩子可不是糟践他么?并非如此。看看鲁迅写《孔乙己》、《阿Q正传》,那么多孩子式的趣味;看看帕慕克说过他如何以孩子般的眼睛来看世界;再看看莫言的数部精彩之作,何尝不是孩子般的玩闹呢? 整部电影的表层故事是关于爱、友情、信义与背叛,内里却是对历史与现实的空洞化(虚无化)的彻底拆穿 怎么样叙述这个电影故事已经不重要了,它其实已经出神入化了!他走火入魔也就是如入无人之境,如入无物之阵,随物赋形,随心所欲,行于所行,止于所止。就像那一段戏,马走日到武大帅家里,教他们一家人弯腰练身,武大帅竟然也信以为真,听马走日喊口令做着操;另一场戏武大帅他们在典礼上,竟然放声高歌起意大利美声唱法,这些虽属搞笑的噱头,却使整部影片变幻自如,无拘无束。前者是在险境中化险为夷,后者是在庄重中诙谐戏谑,故而整部影片洋溢着反讽幽默的效果。尤其是王天王在舞台拿着砍刀表演马走日谋杀完颜英的戏,实在精彩之极。后来王天王逼马走日演戏,竟然是他要马走日念:“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演戏。”马走日不肯屈服,偏要念成:“认认真真做人,老老实实演戏。”从字面上来说,其实没有差别,人老实才能认真,认真才能老实。姜文故弄玄虚一下,主要是起到强调的修辞的作用。这两句“一步之遥”,但从王天王嘴里念出和马走日说出,就有天壤之别。说到底,这就是对今日中国影视戏剧乃至于文化、乃至于社会现状的批判。不老实、不认真,就是今日中国最根本的问题。虚假、谎言四处横行,唯利是图、急功近利,除了对权钱顶礼膜拜,其他都可以弃之不顾。影片开头的“to be or not to be”的严峻的名言被戏谑,到“I do”就是拉屎,是要把历史与现实的浮华表象全部空洞化(虚无化),这就是要在屎里觅道。直到提出要“认认真真做人,老老实实演戏”,这一切就十分明朗了,所有历史的浮华的故事——历史总归是死去的,总归是由人讲述和表演的,像王天王一样胡搞,都会博得满堂喝彩。 这部电影的叙事特征,或者是说它在艺术手法上显示出的才气和力道之处,正在于它能乱中取胜 现实呢?历史与现实也只有“一步之遥”,如何对现实负责呢?马走日是一个较真的人,他不肯屈服。爱在他心中复活、升腾,他和武六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末路之爱。马走日就是一个被社会抛弃和愚弄的末路英雄。他原来以为自己是个英雄,可以摆平一切,结果被别人摆平。整个故事是关于男人的友情(马走日与项飞田、武七)如何走向背信弃义;也是关于男人爱情(马走日与完颜英、与武六)如何意外,如何走向末路。这两条线索都曲折多变,意味无穷。从故事性来说,变数多了些,但都变得自然巧妙。但是,这个故事承载的却是世道人心。影片一步步推向高潮,王天王在剧场里表演就是次高潮,就是对影片前此内容的总结和概括。所有的繁华盛世最终就落到了这么一出戏剧上(顺便说一句,王志文在这出戏里的表演可以说是出神入化,那副嘴脸,那副德性),写尽了世事之空洞、虚假,写尽了人生的荒凉虚无。当然,电影峰回路转,要让爱来完成救赎,只有爱能救赎,虽然有点无力,无力本身其实能透出更彻底的虚无。最终马走日身亡,就说明了其最终不得不完成的主题。 电影最后落在拍摄以马走日作为杀人犯为故事主角的电影上,这部电影其实提出了电影要如何讲述历史,如何讲述现实。马走日本来是个厉害之人,替武七洗钱,策划了盛大的选美比赛,要把“new money”洗成“old money”,不想把自己洗进去了,自己变成了“历史”中的人,变成了电影中的主角。民国的阎瑞生案拍成的电影,成了中国电影史上最早的长电影,某种意义上具有中国现代电影起源性的意义。姜文戏仿这部影片,显然包含着他对中国电影的尖刻的反思与反讽。这部电影甚至试图成为当代电影的里程碑,它有能力通过讲述历史来击穿现实!中国当代电影何尝有过这样的野心——这算是“情怀癌”么? 当然,有人会有疑问,即使我的阐释可以成立,这部电影包含了这么多的想法,有这么多的要颠覆、要改写的东西,也就是说,它毕竟是杂乱不堪吧?如此它也犯了电影之大忌,犯了艺术上不明晰和不单纯的条律吧?但是,我以为,这部电影的可贵之处可以在这一点上继续探讨。这部电影的叙事特征,或者是说它在艺术手法上显示出的才气和力道之处,正在于它能乱中取胜。看上去杂乱无章,内里却有一根筋拎着走。老子说,玄而又玄,众妙之门;这部电影是乱而又乱,但他能乱中有道,乱中取胜。它的灵动式思维、碎片式的连接,极多的跳跃、滑动、旁逸,随时又能收回来,回到主干叙事,乱中握住他要握住的东西,那也是众妙之门。每一次跳开、滑动、转折,都是别开生面,如同变魔术般有着意想不到的奇妙。看看2014年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电影《鸟人》,要多乱有多乱,要多杂有多杂,怎么在欧美就没有成为一个问题呢?在中国也没有受到类似的指责?当然,这部电影在中国的反响也寥寥,它也只能说明中国公众离接受这样的电影也有“一步之遥”。《鸟人》这部电影的成功和获得欧美电影界的承认,表明电影作为这个时代最具有表现力的艺术形式,它理所当然成为当代思想文化与审美感知最具有表现力的文化形式。《鸟人》这部影片几乎有这个时代最混杂的艺术样式,它有文学——改编自卡佛的极简主义小说;它有哲学,关于选择、颓废、生与死的思索;它有情绪,戏谑、嘲讽、感伤、虚无等等;它有电影语言,拼贴、长镜头、戏中戏、夸张与荒诞化……所有这些,这部电影在杂乱中有一种自由的流畅。它的思想随时流露一点,只是一些意味,让人思索和体味无穷。 从表现形式来看,《智取威虎山》与《一步之遥》这两部电影可谓都参透了视听艺术这本经,无疑也领会透了视听时代到来的真谛。前者所有的故事、人物、场面,都是为了视听的艺术/技术手段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不用思考,它不用人物思考,也不用整体电影语言去思考,视听艺术效果与娱乐效果二方面就是其全部,故而今日中国所有的人接受它。后者则想用导演的思想来推动影片的展开,它还想用思考去粘合历史与现实的反讽关系。它想要有对抗性,想要有现实实在性,它甚至还想让电影有其现实实在性,它竟然还带有现实主义的梦想。在中国电影导演中,姜文是一个鲜明的浪漫主义者,但是,他又是认真的现实主义者。浪漫主义只是它的外衣,而骨子里,它不能忘怀现实主义。这一点,他与王朔如出一辙,他们真正是一丘之貉!就这一点而言,姜文还带着书写文明时代的抱负,带着要替书写文明抵抗的英雄情结,它不相信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就完结了,他还是要顽强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立联系。他相信写出来的东西,这是他与徐克的深刻区别。徐克从来不知道书写之物为何物,他甚至从来都不用写作剧本,《智取》的剧本早就在那里,只需要加上一点内容就可以,作为一个鬼才,他只相信鬼画符——这正好是视听时代的伎俩,有这样的伎俩,在视听时代不愁没有市场。但姜文却相信写作,他的这部电影竟然要请九个编剧,他要故事性,要人物,要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要台词,还要隐喻和寓言意义。满篇都是台词,而新编《智取》除了沿袭原来的台词,几乎没有一句台词是需要或可以记住的。《一步》确实也是一部烧脑的电影,它之烧脑不是因为有多么高深的专业术语概念,而是需要人们去想想今天中国人身处于其中的现实,去看看历史,看看中国电影的历史,看看今天中国人及影视人的德性。不用说姜文装逼格,也不要疑问他有什么资格责问世人?他有什么理由摆出道德优越感?但是,问题在于,今天中国的知识群体、影视群体,能提出这样的问题的人越发少见了,姜文提出来了,他就有资格。 今天确实是一个由媒体舆论主导的时代,是死是活,“to be or not to be”,确实是由媒体说了算(当然是指在现实性意义上),但媒体也因此肩负更重要的义务和责任。网上醅评已经习以为常,所有的评判都要推到极端,但“情怀癌”之类的评判还是让人觉得过火粗暴,摆出的架势就是要打倒姜文。当今时代有些网评与“文革”期间的大字报批判几无二致,造反有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小鬼闹天下,唯恐天下太平,已经不能好好说话,甚至正常一点、理智一点说话都不会了。当然,如今时代是否就是任何正常、理智的话都没有听了?如果是这样,那就真的没有办法了。 这么多的否定批评,一边倒,其实也不过是人云亦云。一些浅薄的道理却能应者云集。比如,批判姜文搞了一部观众看不懂的电影,罪莫大焉。这是什么道理?这显然不成理由。电影固然是大众化的艺术,但观众看得懂看不懂并不能成为电影好坏的绝对标准。人民不满意,只有在一个特定的政治语境中才是一件严重的事情。如今的评论一方面在另一些场合,抨击现在的观众只要娱乐至死,只要浅薄无聊的东西:在另一些场合又以观众(人民)之名,作为标准尺度。可见这都是一些机会主义的观点。回到电影艺术或者说关注电影叙事的批评,主要针对姜文的这部影片太多个人的思想和视点,按照姜文个人的情怀来展开叙事,故事情节和场景、人物关系和结构,不是按惯常的逻辑和规则来展开,而是多有别出心裁。比如,批评姜文“死于情怀癌”的文章主要是持这种观点。这种观点明显在强词夺理,影评界一向批判某某这个导演,那个导演没有一点个人的追求,没有一点个性风格,总是高喊反对墨守成规,厌恶落入俗套,何以有一点个人情怀就“得癌”了?一点反常规就受不了?就要拿常规常理去硬套? 与张艺谋和陈凯歌以及贾樟柯都做在面子上相反,姜文都做在骨子里,面子上反倒是西方的东西 即使如此,还是要去思考(因为你不得不面对,甚至很快就要面对)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视听文明即将到来的时期,中国的影视在代表视听艺术创新性的表现方面没有任何作为。例如,在代表最前沿先导的科幻电影方面,毫无准备,也无积累。无论是关于地球的生态论的现实思考,还是关于地球文明的前景,或者是地球与宇宙的时空论哲学方面,电视界和知识界都没有这方面的深刻关注,更谈不上初步成果。这种非现实化的、未来学的、末世论和救赎论的思想,与我们文化传统和文化现实都不协调,故而无法有主动性的作为。另一方面,中国的历史却又并未终结,关于要清理的历史记忆,关于要面对的现实难题,所有这些,对于中国的文学艺术,尤其对于影视来说,都是未竞的事业。 确实,中国的影视还需要很长的时期寻求书写文明向视听文明的过渡转型的连接方式,而如何给予书写文明的历史记忆以更有力的视听艺术的形式——也就是更为自由、更有内在张力、更为出神入化的那种视听形式,可能是中国影视转型时期的重要战略。中国影视也可能在这一意义上,有自己的创造的可能性。姜文的《一步》虽然可以看出众多的欧美经典的电影语言,看到他向好莱坞大师致敬的表现手法,但通篇贯穿的依然是他的思想性,他要把历史和现实连接起来的勃勃野心。那种把现实隐喻化和寓言化的历史叙事,在华丽杂乱的游戏般的视听场景中,用自我解构式的非自我中心化式的游戏,去抓住历史的空洞与现实的要害,从而完成了对现实的严肃质询。就此而言,《一步》是一部不可能让西方世界完全理解的电影,其内涵与艺术性都不可能被西方理解。与张艺谋和陈凯歌以及贾樟柯都做在面子上相反,姜文都做在骨子里,面子上反倒是西方的东西,那里可以看到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斯坦利·库布里克、看到昆汀·塔诺,但是,这部电影骨子里和他的问题是真正中国的,吃进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的深处(痛处)。 在这一意义上,《一步》不过是以怀旧般的眷恋,困守住书写文明的写作方式,顽强地要在书写与视听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这是对中国国情及现实可能性的认真而老实的认识,它知道这是它越不过去的坎,它知道这又是它可以利用的机遇,它那跳跃式的表演,本来表演的就是三级跳,它完成了。《智取》是一个无历史无现实也无自我的视听表现,它有着盛大的视听现场,它只是视听的在场,它也是提前闯入视听的现场,或者说提前让视听闯入现场。对即将到来的视听时代来说,《智取》以无本质的方式完成了视听拼接,它汇入游戏、动漫等巨大的视听表现世界。但是《一步》是有关怀的电影,是有情怀的电影,它关怀历史、现实和生活的真相,关怀人性的真相,它痛恨虚假,它把那些无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人看。它无疑还是有不少不尽人意处,进入得太慢,结尾的追击打闹还在玩粗俗……但这些缺点绝不是什么“情怀癌”,也掩饰不住影片的机智与才华。而且它的信念很明确,在那些变幻不定、自由流转的电影图像的内里,它还是要有东西确定下来,要有东西能被写下来,它既超前又恋旧,它给当代电影留下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正视它,重视它,而不是诋毁和恶搞。固然,与姜文的这“一步之遥”在当今中国,有无数的理由和必然性,但这不应该成为攻讦姜文的理由。正视这一点,中国电影的水准,或许能因此上一个台阶,不管是“走日”还是“飞田”,那一步之遥都应该跨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