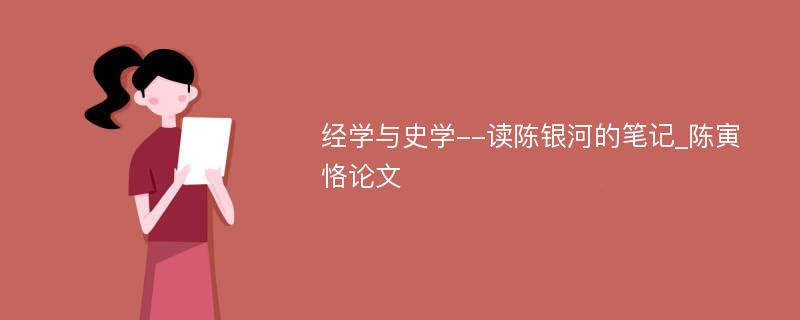
经学与史学——读陈寅恪札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学论文,史学论文,札记论文,陈寅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画鬼与画人
陈寅恪先生尝自谓:“不能读先秦之书”,“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三复斯言,当有深意,似不宜仅仅看作谦辞。鄙意陈先生每次这样说,都是在明确地表示一种学术态度和见解,并且都有针对性。
在《刘叔雅庄子补正序》中,陈先生称赞刘先生之书为“天下之至慎”,[①a]同时批评“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者”[②a],“颇有改订旧文,多任已意,而与先生之所为大异者。”[③a]陈先生把他们比作金圣叹之批《水浒传》;金圣叹批书当然有其不可掩的文学价值,但是“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谈商周邃古之朴学”,[④a]这样一种“当世之学风”,[⑤a]却是陈寅恪必定要与之划清界限的,故曰:“寅恪平生不能读先秦之书”。[⑥a]
又,在《武曌与佛教》一文中,陈先生引据并补充王国维对敦煌残卷的考释,证明了武则天大周革命以为合法性根据的《大云经》,乃“原本出自天竺”之“大乘急进派经典”,[⑦a]经过于阗传译至中土,非若后来新旧唐书及小说家言,为薛怀义等所伪造。武曌的母系乃笃信佛教的杨隋皇室之宗亲,从小习染天竺之风的武曌,将“其中有以女身受记为转轮圣王成佛之教义”[⑧a]的《大云经》现成拿来,作为反对不许妇人与闻国政的儒家旧说、实现其政治革命的理论根据,自然要比操纵一帮御用文人无中生有地去伪造一部经典有力得多,她本人在心理上也会觉得踏实得多。人的心理作用,常有跨越时空的普遍性,只要所处的具体情境相似,心理意向也往往相同。正因此,陈寅恪从“武曌之颁行《大云经》”,一下子跳跃言及“王莽之班符命四十二篇”,认为“其事正复相类,自可取与并论。”[⑨a]“并论”的结果,当然是不同意康有为的“新学伪经”之说,故曰:以“古文诸经及太史公书等悉为刘歆所伪造或窜改者,其说殆不尽然。”[⑩a]揆度人之常情以测史实,当然比标新立异、刻意为非常异议可怪之论,要近真得多。但心理内省的推测,毕竟不能代替客观史料的证实。好作非常异议可怪之论者,就喜欢在文献不足史料缺乏的地方,逞其口辩,施其伎俩;今文家康有为属之。陈寅恪固然反对其说,而也更要在立论标准上表明态度,区以别之,所以说:“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固不足以判决其是非。”[11a]语气谦抑而语意实很坚决。
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陈寅恪又一次说:“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12a]这次是针对着经学与史学的关系而言的。该文开头就说:“有清一代经学虽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13a]其原因陈先生认为不能单单归之于清室的忌讳,即一般所说“文字狱”之类,而是经学与史学之间反比的关系有以致之,一言以蔽之:“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致史学之不振也。”[①b]
陈寅恪不笼统地讲“宋学”、“清学”,但要具体地分辨经学与史学。史学要求“实事求是”,困难就在这里。历史上的“实事”,不象多数科学实验中的实事那样可以复制。史实是唯一的,一过性的;一旦过去,不可再历。要把已归于无的过去实事考索出来,重建起来,惟有依靠遗传的史料。书籍、档案、钟鼎、甲骨、金石、竹简,这些是史学者据以重建的资具,同时也对史学者构成不容其以意为之、随便穿凿的限制。
经学则不同。经学所求的是“意义”。所谓“意义”,不象事实那样有客观的硬标准,常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②b]经学训诂与史学考异虽然都是用比较对勘的方法,但两者所欲侦察的材料,在经学是保守的、有限的(黄侃说:“八部书外皆狗屁”);在史学则为开放的、无限的(章太炎却硬说甲骨文是刘铁云伪造)。原始材料之残阙不足,正好供给经学者主观想像或穿凿的园地,却往往令严肃认真的史学者无所措手足。
陈寅恪将经学“譬诸图画鬼物,苟形态略具,则能事已毕,其真状之果肖似与否,画者与观者两皆不知也。”[③b]经学譬诸画鬼,则史学自当譬诸画人。画鬼容易,画人难,画人有一个象不象的问题。陈寅恪屡言不读先秦之书,其意殆谓要象画人一样形态略具甚至毫毛毕肖地画出先秦史概貌,如其本人在魏晋隋唐史和明清史的某些题目上所做到的那样,那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我揣想陈先生的意思甚至更进一步:要按照他治中古以降历史的标准治上古史,不仅是主观上困难,实乃客观上不可能也。
史学衰疲因为经学过盛,经学盛则以实际利益解释之:“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④b]功利的作用,在清朝只是使史学不振,延至后世,则更将史学也经学化了,“今日吾国治学之士,竞言古史,察其持论,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⑤b]陈寅恪心目中理想的经学,则应反过来,应是将经学史学化。这在《杨树达论语疏证序》中讲得十分明白。文中陈先生又一次说“不敢”:“寅恪平生颇读中华乙部之作,间亦披览天竺释典,然不敢治经。”[⑥b]《论语疏证》显然是一个经学的题目,而陈寅恪独加揄扬:“先生治经之法,殆与宋贤治史之法冥会,而与天竺诂经之法,形似而实不同也。”[⑦b]又说:“今先生汇集古籍中事实语言之与论语有关者,并间下己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此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乃自来诂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楷模也。”[⑧b]
从“史”的观点视“经”,早就有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说法,钱钟书且又在《谈艺录》中举出七条章氏之前已说过同样或类似话头的例子,[⑨b]牟润孙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也找到一条。[⑩b]但学问之事,重要的不在于坐而论道,而在于起而实行。陈寅恪很推崇杨树达以史学方法治经的实践,却不很看得起“史论”(章氏《文史通义》盖亦属“史论”或“史学哲学”一类),认为其“无关史学”,[11b]甚至谓其作用只在“废物利用”。[12b]颇有点象大科学家对所谓“科学哲学”的态度。例如爱因斯坦就调侃数学哲学上的争论为“青蛙和老鼠之间的战斗”。S·霍金更刻薄,他说科学哲学家“是失败的物理学家,他们知道自己无能力发现新理论,所以转业写作物理哲学。”[13b]总而言之,陈寅恪先生盖无往而不对史之为学坚持其客观而严格的要求和标准。
二、“经学”一例
经学的任务是注经和传经。既然“六经皆史”,既然古史的材料在经中,按理说该是经学越发展,古史越明朗,怎么反而会经学发达过甚转致史学不振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历来的经学缺乏客观的史的眼光。经学在长时期里的踵事增华,模糊了原始经传的本来面目,反而给史的研究造成了困难。
且举《论语》为例。
《论语》传到汉朝,有三个不同的本子。《鲁论》二十篇,《齐论》二十二篇,《古论》二十一篇,情况已是纷繁复杂。到了东汉大经学家郑玄手里,他对三种本子作了一个综合处理,情况就更加混乱。敦煌千佛洞所出《论语郑注》残卷,其所存篇下皆题“孔氏本郑氏注”。“孔氏本”即《古论》。但按皇侃:“古论篇次乡党第二”,而此残卷的篇次却为“泰伯第八子罕第九乡党第十”,悉同于《鲁论》,既如此,怎么能说它是“孔氏本”呢?这个矛盾该怎么解释呢?
幸而,后来有些记载可以让我们知道郑氏当时搞综合作用的方法。何晏《论语集解序》云:“古论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说,而世不传。汉末郑大司农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以为之注。”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云:“郑元就鲁论张包周之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又云:“郑校周之本,以齐古正读凡五十事。”《隋书·经籍志》亦有类似说法。王国维总结郑注本的特点为“篇章虽仍鲁旧,而字句全从古文。”[①c]这样,《论语郑注》的敦煌残卷叫做“孔氏本”也就说得通了。
如果上引何、陆、王诸人所说不错,那么大经学家郑玄缺乏史之眼光也就明矣。诚然,郑玄拿不同的本子对勘互校以求定于一是,确是在作考据之事;但他不是在考史,他作这事遵循的原则与“考史”的精神有违。史的精神最讲究“实事求是”,若是对人与事作具体的观察、了解、分析,那就应该鲁论是者依鲁论,齐古是者依齐古,怎么可以事先作一个形式的划分:“篇章根据鲁论,字句根据古文”呢?如果鲁论与古论字句歧异处,确实都是鲁论错了,古文正确,那也应该是一一作具体考释以后的结论,而不是从事之前就立定的规矩。
事实上,郑氏这样的校注法,真的酿成了困难和问题。例如,“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一语。陆德明《释文》:“鲁读易为亦,今从古。”按《鲁论》,此句应为:“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与《易经》无关,意思完全两样了。郑玄当初据古改鲁,如果有史的意识,应作起码的考释,讲明理由。但是并不,他只是在句下按己意解释一番:“加我数年,年至五十以学此易,其义理可无大过。孔子时年卅五六,好易,玩读不敢懈倦,汲汲然,自恐不能究竟其意,故云然也。”两种截然不同的意思,弃取之际,竟未尝有一言及其理由,不亦惑乎?
郑玄当时,去古未远,想要弄清楚一些事实,比千载以下,总要容易得多。等到清儒重新提出这一问题,则任凭他们训诂的本事多大,已难以理据充分地判明是非了。各人自信颇坚的解释(如俞樾、惠栋、毛奇龄等都论及此事)均不免武断的成份,令没有成见的读者无所适从。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孔子五十学易辩”条认定“鲁论为是”,[②c]其理由是:“孔子实未尝传《易》,今《十传》皆不出孔子,《世家》亦但言孔子四十七不仕而修诗书礼乐,并不及易。而《正义》谓其学易之年,明为误矣。《世家》又谓‘孔子晚而喜易,序易传’,盖皆不足信。”[③c]这些理由似乎仍不够坚强。信世家之“前言”,又不信其“后语”,未免主观。且未尝传易,并不等于未尝学易。人于自己特别喜学,甚至特别精通的科目,往往不下一字,亦不出情理之常。《先秦诸子系年》全书功夫精深,发明多多,但此条实不足以餍人心。取“鲁论为是”,固可说通;但只要主观上愿意,取《古论》与郑注,也不难说通。孔子五十以前说“五十而学易”,此为将来之打算,但因忙于修诗书礼乐,实际至晚岁七十始得学易,这样说也并无什么滞碍。总而言之,莫衷一是。
如果“孔子学易”成立为古史的一个问题,则按照陈寅恪所悬的解决史学问题的标准,这问题就是无法解决的。这仅仅是一个例子,古史中类似此例的情况所在皆是。古史因年代久远,材料本就不足,再加经过两千年“经学”的缺乏史识的加工,造成真与假、现实与理想、客观与主观的一团乱麻,分理为难,简直超过了人工的范围。
陈寅恪向来视“读书”与“治学”为一事。《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①d]读书治学决不象其他的人类活动那样,可轻易纳入竞争比赛的规则系统(竞争比赛的规则系统即是一种“俗谛之桎梏”。)知识分子、士,本质上不应是运动员。如果知识分子本质上是运动员,那么陈寅恪就不该说“不能读”、“不敢读”之类的话。吴宓早就推尊陈寅恪“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②d];汪荣祖断言陈寅恪的高度“可以超越,又不可能超越”;[③d]陈寅恪己身也有自许如“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④d]之诗句。事实上有那么多人在读先秦之书,怎么陈寅恪反而不能读呢?所以,从运动员比赛的角度所作的这些评价,说到底都是可以忽略的。
不仅先秦之书“不敢读”,即使对其所喜读之中古以降文化史,陈寅恪亦每每叹“读书之难”。如关于钱牧斋有美诗“苏堤浑倒踏,黟水欲平填”句,便自云:“寅恪少日读此诗,颇不能解。……及垂死之年,……始恍然大悟”。[⑤d]又如,九岁时已习诵吴梅村《圆圆曲》,“历六十余载之久,犹未敢自信能通解其旨趣。可知读书之难若此。”[⑥d]这些,都是在以他个人主观的感受,表达一种超越于个人主观以及俗谛桎梏之外的真实、客观、绝对的境界,这才是读书治学的本质意义所在。
三、史学应讨论问题
陈寅恪批评经学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成立问题。”[⑦d]从应然的要求来说,任何学术研究,都以讨论问题为主,经学自亦不能例外。所以陈寅恪对“经学”、“史学”的划分,实质上是对两种不同的治学态度、精神、方法、途径的划分,而不是对研究对象、领域的划分;所注重的是“怎样”(how),而不是“什么”(what about)。以经学的态度治史,仍不脱经学之藩篱;取史学之途辙研经,自臻于史学之轸域。岂有他哉!
陈寅恪自己的文章,短至千字文,如《蓟丘之植植于汶篁之最简易解释》,长至数十万言之巨篇,全都是对高质量问题的讨论。要象读一般传记那样读《柳如是别传》,那是难以进行的。即使是为别人的著作写序或审查报告,这类似乎最容易说概括性话语的地方,也充满了具体问题的抉发和提示。例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就提出中国思想演变历程之“一大事因缘,即(北宋)新儒学之产生”,[⑧d]对此大问题,复有进一步具体深入的提示:“凡新儒家之学说,几无不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之佛教为之先导,如天台宗,佛教宗派中道教意义最富之一宗也。其宗徒梁敬之与李习之之关系,实启新儒家开创之动机。北宋智圆提倡中庸,甚至以僧徒而号中庸子,并自为传以述其义,……似亦于宋代新儒家为先觉”,“足见新儒家产生之问题,犹有未发之覆也。”[⑨d]时至今日,“国学”、“儒学”重新成为关注热点。陈先生提示的这些问题,正当有人去认真从事研究。与所有的科学一样,史学的任务是研究问题。“问题史学”一目,不当为年鉴学派所专有。
所谓“讨论问题”,按陈寅恪的意思,就是要“发未发之覆”。问题不是现成在那里的,更不是任何一个带问号的句子,都可以成为问题。问题有待发现。发现问题是研究过程的一部分。常言道:“开头开得好,一半完成了。”发现并成立一个好的问题,等于完成了一半的研究工作。
比较是发现问题的有效途径。但是须知,比较亦有法度,不可乱来一气。用陈寅恪的话来说:“比较研究的真谛……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①e]今日比较之风特盛,大有超出“荷马比屈原,孔子比歌德”之怪诞者在。多数的做法,凭空悬一题目,远望略取形似,就可以洋洋洒洒写比较研究的大文了。作文而己,研究云乎哉。所谓“以西方为坐标批评中国,以中国为坐标批评西方”,离开了“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的引导,亦仍旧不脱穿凿附会之窠臼。
正确的史学比较方法,必须深入到具体的史料中去,从史料的对勘中发现和提炼出真正值得进行比较研究的问题。问题不能从外边强加给研究,用以比较的材料亦不能拉郎配式地强行捆绑在一起。
陈寅恪本人的实践树立了最好的典范。兹举一例。《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可说是对中国印度传统思想作的一个比较研究,其问题之成立,则据于敦煌写本《诸经杂缘喻因由记》中的一个“脱漏”。此写本述莲花色尼出家的因缘,乃是受到“七种咒誓恶报”,[②e]但实际却只载六种。陈寅恪初读时以为“七”乃“六”字之讹。后反复寻绎原文,发现文中“七之为数乃规定不移之公式”,不可能是讹。陈寅恪进一步又排除传写者无心脱漏之可能。于是,此“脱漏”乃成立为一个问题,值得研究其所以然了。
研究的办法是从巴利文佛典中寻检出它的原本来对照,结果发现“法护撰涕利伽陀此篇注解所载此尼出家因缘,与敦煌写本大抵相同,惟其中有一事绝异而为敦煌写本所无者,即莲花色尼屡嫁,而所生之子女皆离夫,不复相识,复与其所生之女共嫁于所生之子。迨既发觉,乃羞恶而出家焉。”[③e]至此已不难断定敦煌写本之脱漏,其实是有意的删削。此有意的删削集中反映了中印之间伦理观念之绝大差异。
佛法初入中国,其教义中与此土社会组织及传统观念相冲突者,不止一端。如“沙门不应拜俗”、“沙门不敬王者”,与君臣父子之义显相杆格,但并不妨佛门中人宣传和实行此类教义,甚至有“高僧大德,不顾一切忌讳,公然出而辩护其教义中无父无君之说者。”[④e]独独讲到男女性交聚麀之事,“则此土自来佛教著述,大抵噤默不置一语。如小乘部僧尼戒律中,颇有涉及者,因以‘在家人勿看’标识之。”[⑤e]可见伦理观念的系统中,亦有层次和方面之分,有些较具弹性,允许一定程度的伸缩和变形;核心处则绝坚固,丝毫不容妥协。中国字里,“耻”之一字,份量特重。耻闻之事,当然也不可看,不可说,即使用批判的贬斥的态度,也难以启齿。可以想见,当时那位敦煌写本的写手,正是怀着这种心情把第七种恶报删掉的。
伦理观念的长期熏习,9形成顽固的下意识心理禁忌,转使坦率直言的“贝多真实语”,成了不可轻宣的教派“秘密语”。久而久之,秘密起源于伦理禁忌的事实被遗忘了,“秘密”反成了有正面意义的存在,这些戒文咒语,仿佛真有了不可思议的神力。陈寅恪引《高僧传·康僧会传》:“[孙皓]因求看沙门戒,会以戒文禁秘,不可轻宣”后,下语曰:“疑与此同”[①f](即与“在家人勿看”之标识同),即提示了上述这样一个过程。陈寅恪的研究,每每有这种“小处看手,大处看眼”的风格。
能不能准确精炼的表述问题,也是发现和成立问题的重要一环。陈寅恪在《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一文中,论到赵翼《廿二史札记》“江左世族无功臣”条,谓“赵书此条暗示南朝政治史及社会史中一大问题,惜赵氏未能阐明其义”,此问题即“江左历朝皇室及武装统治阶级转移演变之倾向是也。”[②f]陈寅恪概言此一倾向云:“宋齐梁陈四朝创业之君主,皆当时之功臣。……以功高不赏之故,遂取其旧来所拥护之皇室而代之耳。”[③f]原来,只因为有功的世族相继取皇室而代之,自己做了皇帝,所以才显出世族中无功臣的现象。赵瓯北正确地看到了“江左世族无功臣”的现象,却不知其与“南朝帝室止出于善战之社会阶级”的现象,实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事情,真可谓一间未达。也因此,赵瓯北遂失落了一个重要问题:“此善战之阶级,在江左数百年之变迁,与南朝境内他种民族之关系,治史之人,固应致意研求者也。”[④f]
并非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与其他科学一样,史学上也有长期得不到解决,甚至看不到解决希望的问题。对此要承认,不能含混过去。一门科学,越是存在凸出显眼的硬问题,其科学性越强。厚厚三大本《柳如是别传》,就是一部围绕着钱柳因缘主线展开的问题集。陈寅恪自己说,写作此书的目的之一,是“欲自验所学之深浅”。[⑤f]自验的结果,陈寅恪解决了大部分问题,(提问题也是学力深浅的一种表现,书中有些问题,老实说也只有陈寅恪能提得出)同时也留下了若干“俟考”题(“尚待考证”,“尚待考实”,“有望于当世之博雅君子”等等),其中特别有两大困难问题:一为惠香公案,一为黄毓祺之狱。[⑥f]
且说“惠香公案”。牧斋诗文中多次出现“惠香”之名,以“惠香”之名作诗题的也有好几首。问题是:惠香究竟是何许人呢?首先排除掉何梦华、黄丕烈二氏认惠香与河东君为一人的“殊为谬妄”[⑦f]的看法,至少还有三种可能的假设。关于惠香与河东君之妹绛子是否实为一人,陈寅恪谨慎地说:“尚待考实,今难断定”,[⑧f]实际倾向于不取。对另一个“或说”,即认为惠香即卞玉京,虽也倾向于不取,故谨慎地说:“似颇有理,但尚少确据,未敢断定”[⑨f];但同时仍为它提供一佐证:牧斋有“赠旧校书”诗二首,此旧校书净华“殊有为卞玉京之可能”,而寻绎诗意,也隐约可见“净华乃牧斋心目中之惠香也。”[⑩f]
陈寅恪自己的推断,则是用了类似于逻辑学中摹状词的办法,即在不知道主词是什么的情况下,尽量把主词所具有的谓词性质收集拢来,然后据以推断主词是什么。这也有点象福尔摩斯探案,以案主留下的蛛丝马迹以及可能与案主有关的一切细节为素材,先行在脑中整合构拟出一个主体来,然后就多少可以用对号入座的办法把现实中的案主识别出来。陈寅恪以崇祯九年牧斋为所校录元刻《阳春白雪》题跋时即提到“惠香阁”,却迟至崇祯十三年才在诗文中出现惠香一女性名字,故推测惠香乃是“人因建筑物(惠香阁)而得名”,“盖牧斋心中早已悬拟一金屋之名,而此金屋乃留待将来理想之阿娇居之者。”[11f]从牧斋诗文中有关惠香之内容,进一步推得此女性为一能歌之人,居处必与嘉兴及苏州有关,崇祯十五年春曾伴送在苏州卧病的河东君返常熟牧斋家,牧斋苦留之不得,因为筑“留仙馆”,实寓欲留惠香之意,却故作狡狯,托名“慈溪冯氏尔康号留仙者”[12f],“深情奢望,可怜可笑”,[①g]等等,等等。根据这些事实,陈寅恪猜测惠香即是张宛仙,但仍声明只是“姑备一说于此,殊未敢自信也。”[②g]总之,陈寅恪认为这个问题尚未解决,“殊难参决”,自赋诗云“尚托惠香成狡狯,至今疑滞未能消”,并瞩望“当世通人傥能补此遗憾,则幸甚矣。”[③g]
法国作家法郎士的著名小说《企鹅岛》里那位虚构的历史学家慨叹写史的困难:“撰写历史是极其困难的。我们永远没法准确地知道过去的事是怎样发生的。资料越丰富,历史学家的困难也越大。当某一事件只有一个出处证明时,我们会不太犹豫地加以接受。如果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出处时,困惑就会跟随产生,因为这些出处总是互相矛盾,无法调和。”[④g]“惠香公案”的困难有类于此:“或说”太多,互相矛盾。当正确运思于现有材料已达其极限,再无能为时,问题的解决也就只能留待于发现更新的材料以为“参决”。这一类的问题,正是有能力的史学家最感兴趣、也最能发挥其才力的用武之地。一般说来,上古史材料苦其少,中古以降特别是近代史材料苦其多。材料少,是人为不能解决的困难,是“天难”,不是“人难”;材料多,错综庞杂,互相矛盾,则是向人力挑战的困难。《企鹅岛》作者视“天难”为不难,认为孤证的历史反而好写,从治史的角度看,其言未免谬妄,但对作家不必苛责。陈寅恪的态度则是,在“天难”面前,知难而退,有所不为,绝不涉妄,是为狷,所以三复斯言说不敢读先秦之书;在“人难”面前,知难而进,越难越进,是为狂,一定要把所面对的问题,方方面面,角角落落,纤发无遗,都剔抉出来,疏理清楚,弄不清楚的,也一定要把它局域地定位好,以待后来。可以说这是最正宗的科学的历史学态度。狂狷庶几乎中庸,进德修业上固如此,科学认知上又谁不云然?!科学所追求的,就是在人能解决的问题范围内,解决困难的问题。科学家的高低,即以他所提出和解决的问题的困难程度相区别。史学岂例外哉!
注释:
①a②a③a④a⑤a⑥a《金明馆丛稿二编》229页。
⑦a⑧a同上,148页。
⑨a⑩a(11)a《金明馆丛稿二编》150页。
(12)a(13)a《金明馆丛稿二编》238、239页。
①b《金明馆丛稿二编》238、239页。
②b③b④b《金明馆丛稿二编》238页。
⑤b《金明馆丛稿二编》239页。
⑥b⑦b⑧b 同上,232页。
⑨b 《谈艺录》263-265页。
⑩b 《注史斋丛稿》542页。
(11)b(12)b 《金明馆丛稿二编》248页。
(13)b 《霍金讲演录》30页。
①c 《观堂集林》卷4。
②c③c 《先秦诸子系年》15、16页。
①d 《金明馆丛稿二编》218页。
②d 《吴宓与陈寅恪》4页。
③d 《陈寅恪评传》251页。
④d 《寒柳堂集·寅恪先生诗存》18页。
⑤d 《柳如是别传》中册,384页。
⑥d 《柳如是别传》中册,751页。
⑦d 《金明馆丛稿二编》239页。
⑧d⑨d 《金明馆丛稿二编》251、252页。
①e 《金明馆丛稿二编》224页。
②e 《寒柳堂集》151页。
③e 同上,153页。
④e⑤e 同上,155页。
①f 同上,155页。
②f③f④f 《金明馆丛稿初编》94页。
⑤f 《柳如是别传》上册,3页。
⑥f 《柳如是别传》下册,882页。
⑦f 同上,中册466页。
⑧f 同上,472页。
⑨f 同上,497页。
⑩f 同上,499页。
(11)f(12)f 同上,466页,577页。
①g 《柳如是别传》下册,578页。
②g 同上,472页。
③g 同上,487页。
④g 《企鹅岛》,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2页。
标签:陈寅恪论文; 经学论文; 读书论文; 柳如是别传论文; 先秦诸子系年论文; 国学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儒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