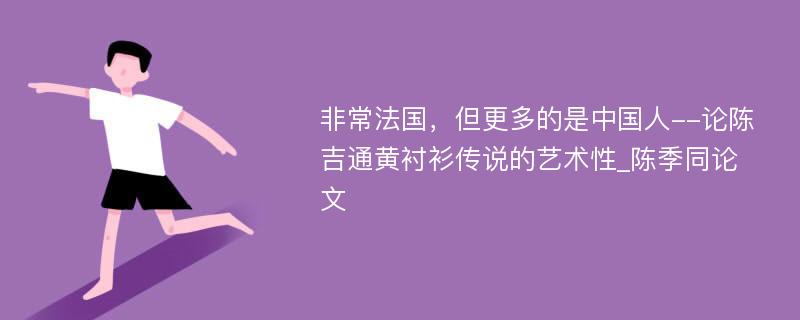
非常之法国化,却更具中国味——论陈季同《黄衫客传奇》的艺术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国论文,艺术性论文,更具论文,中国论文,黄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5-0060-05 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在索邦大学的阶梯教室里亲自听过陈季同的讲演。他听后的评价是:“他的演讲妙趣横生,非常之法国化,却更具中国味。”①我们觉得用这一评语来总括《黄衫客传奇》的艺术特色也非常贴切。陈季同的身份虽然是驻法大使馆的武官,可是他博览法国乃至欧洲的文学典籍。这在他对曾朴的娓娓不倦的指导中就可以得到证明。《黄衫客传奇》可说是“法国化”与“中国味”的相当完美的结合。 与中国当时的小说对比,一开始就觉得他突破了中国小说的习惯套路。中国小说常以梦起以梦结,以诗起以诗结……但《黄衫客传奇》开头就是欧式的一段风景描写,而且还不断地变换角度:“让我们休息一下眼睛,改换一个视角”,“我们先不去管它们,再回到江面上”,等等。他的笔就好像是一部移动的摄像机。而且他笔下的风景也并非完全写实,它如真似幻,甚至将镇江的小金山也搬到了南京。而一只只花船本应在秦淮河里轻飏,他却将它们搬到了浩瀚的长江江面上游弋。反正法国读者不会计较他的虚构,而只注重小说风景多层次的美感。但小说所反映的生活却是中国味的。小说的第一节就是主人公李益与他的表兄崔允明在发榜前夕到妓女莲花家去冶游的情节。他们在花船上因下棋的输赢而开始对话。崔允明虽然输棋了,但他说:“在生活中我赢了你。”他说李益非常聪明,因此大家赠他“无双”的雅号,可是非常了解他的表兄却指出李益有“双重性格”:“你总是想要又放弃。你有想压倒天朝男儿的雄心壮志,但你又会为了一个穷人而两手空空。当你想当一个恶棍的时候,你又忍不住去行善。……”但李益的回答是:“人只能服从命运的安排。”这一段“说教”也预示着李益以后的人生道路是在犹豫不决和莫衷一是中经受挫折。这段话将李益的性格弱点和盘托出。为塑造人物,在小说一开始就用如此的“说教”,我们认为未免失之过早,这是作者对读者的一种“灌输”。但是其中有一句话是很实在的,那就是“在生活中我赢了你”。他们上岸,到莲花家就使这句话得到了证实。 在进莲花家门之前,崔允明还在门外弹着“四弦吉他”吟唱了一曲《莲花吟》,这当然是非常法国化的行为。外国的小伙子为追求心爱的姑娘,不是总喜欢在那女子的窗下弹琴唱歌吗?可是他们一进门,小说却充满了中国味。其实那是一种最高级的妓女的家,古代称为“书寓”。这种书寓的女子是多才多艺的,琴棋书画都能拿得起,专门接待富有的雅客,并且标榜是“卖艺不卖身”的。当然对她看中的“恩客”,是可以作为例外的。在他们享受了一个愉悦的夜晚之后,崔允明留下来进入了温柔乡。在返回途中,李益自言自语地说:“我不懂生活!”回到狭小的学生宿舍,“孤单又笼罩了他。这一晚,他比以往更感到凄凉和无助”,他决定要去求助于“姻缘代理”鲍夫人。 在中国的小说中媒婆往往是反面人物,中国古代的男女婚前是不能见面的,因此,就凭媒婆从中撮合。而在媒婆的嘴里,能将嫫母说成西施。可是陈季同却为中国的媒婆翻了案。鲍夫人,曾是王府郡主的贴身侍女,但她有空就学习女红、音律和识字,后来她竟成了郡主的女塾师,直升至王府的女主管。当郡主出嫁后,她也赎了身,嫁给了一个珠宝商。但她不局限于在东方式的珠宝丛林般的商店里做老板娘。她善做月下老人,“她只是把撮合姻缘当成一种快乐”,而且将它作为一门艺术。她只给第一流的人物配亲。李益过去曾经托过她,请为他找一个相爱的人,但被她婉言推辞了。她要他等18个月之后再来。等考试发榜后,她能为“最有名的进士配最富有、最美貌的小姐”。当时,这位有才华的李益不过是个“潜力股”罢了。 成为状元的李益头上有了耀眼的光环,加之风流潇洒,一表人才,鲍夫人为他介绍了“一颗真正的明珠,一个美貌的仙子”,家里不仅富有,而且“教养也是第一流的”。郎才女貌,当然一见倾心。李益立即被她们母女留住在她家,作为未来的乘龙快婿。在蒋防的《霍小玉传》中,霍小玉是妓女式的女子,她当天晚上就主动到李益的房中,脱衣解带,同卧鸳被。而在《黄衫客传奇》中,乃是两人因当天的奇遇而激动得无法入睡,就在各人的房外相遇,是男女的“自然本性法则的召唤”,他们一起进了小玉的卧室。他们知道这是“出轨”,因此向她母亲隐瞒着。可是不久被小玉的母亲发现,当母亲回到自己卧室后“双手抱头,痛哭流涕”。第二天清晨,她严肃地责问了李益。善后的办法是他们得邀请至亲好友,加上李益的好友崔允明和韦夏卿,举行一次“非正式的、还未获得允准的婚礼,举行一个正式的庆贺仪式”。从此,他们二人就作为“特例”面对亲友,俨然成为夫妻,幸福地过了两年多的“蜜年”般的生活。他们相爱的许多镜头,往往令人联想起十八、十九世纪法国爱情小说的情景。虽然李益的母亲一再来信,对这段“婚姻”表示坚决抵制:因为霍小玉虽有王族血统,但她母亲只是霍王的一个得宠的侍妾,地位卑贱;当霍王逝世之后,嫉妒的兄弟们就给了他们一笔财产,而将她们母女逐出了王府,改姓了郑。但李益除了山盟海誓之外,他始终认为:“我母亲不能强迫我娶别人。”他的决心是小玉与她母亲的一剂“定心丸”。当他两年后再经吏部的考试发表为郑县主簿时,他要顺道去探望久别的母亲,那是小说的第15章节,他还向他夫人保证,要“像一个男人一样站在她(母亲)面前”,“他要投入战斗,他会胜利,一定会胜利”。他相信他母亲“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接受”。这就是从小说开始到第15章节开端的“法国化”和“中国味”相融合的描绘。可是以第15章节为界,情况急转直下,直到第18章,那也是小说最带有浓厚的“中国味”的、使人意想不到的转折。一个早已精心策划好的阴谋在等待着他,李益“溃不成军”。 蒋防的《霍小玉传》原是唐传奇中的著名篇章,而经过明代大戏曲家汤显祖改编成《紫钗记》,就更加深入人心。与二者相比,《黄衫客传奇》有4大关键性的“转轨”,显示出陈季同的独创。一是改变了主人公的性格:他将《霍小玉传》中的负心郎的李益改成有爱心而真诚的李益;他将《紫钗记》中坚决抵制恶势力的李益,改成了软弱与举棋不定的李益。二是由于主人公的性格的改变,结局也就大大的不同。《霍小玉传》的结局是彻底的背叛;《紫钗记》的结局是大团圆;而《黄衫客传奇》的结局是一个惨绝人寰的大悲剧。三是增加了前二者中所没有的一位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人物,那就是李益的母亲。她代表着“家族制度与礼教的弊害”,她执拗而冷酷。《霍小玉传》中的李益的品质本来就有严重的问题;《紫钗记》里的李益受到的是高官卢太尉的迫害。只有《黄衫客传奇》中的母亲,她使小说更具有对全社会制度的控诉性。四是陈季同将前二者中实有的黄衫客这么一位活生生的英豪,变成了一个虚拟的人物,成了一个时时会在关键时刻出现的幽灵。有了这4大变化,陈季同的小说就成了他自己的独特的创造,一部不是依傍、不是改编,而是焕然一新的独立的作品了。 李益的母亲是小说中彻底毁灭爱情的罪魁祸首,是用母爱去屠杀爱子的刽子手。小说中最可怕也是最精彩的场面就是李家家祠的那一场“戏”。那场面那背景是令人不寒而栗的。母亲面若严霜,将李益带进了家祠,立即将门关上。“房间里烛火高照,香烟缭绕。四壁挂满牌位,依照谱系等级排列,还有完整的列代宗谱”,这是一个神人或者说人鬼交通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场合。他母亲用严厉的声音训斥他,这是一场母亲代表列祖列宗对李益的审判: 而你呢?当你有能力继承他们的传统而且可以光宗耀祖的时候,你做了什么?你要把未来寄托在一个没有父亲的女子身上吗?正是她,在某一个晚上,像花船上跑出来的歌女一样,投入你的怀抱;你竟想让这样一个女子跻身于我们高贵清华的门第吗! 我为你感到脸红,我也为我自己、为所有的祖宗感到羞耻。……如果我们用这样的可耻行径侮辱神圣的祖先,触犯神明,我怎么敢站在他们面前?不,我不会同意你们的露水姻缘。决不!在倾听我们祖先和惩戒我们的罪孽的神明面前,我向你发誓。 这是李益的母亲在他措手不及的情况下的一次偷袭,一次狂轰滥炸。母亲可怕的狂怒、神秘的场所、对亡灵和家中守护神的召唤,让李益的“大脑停止转动”、“他像醉汉一样脚步踉跄”、“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当家祠的门一打开,“她已将新郎的红色绶带递过来,又飞速给他戴上婚礼时才用的金花冠”,然后高声宣布:“承蒙总督大人光临寒舍,着实令蓬荜生辉。今以亡夫的名义宣布,同意爱子李益与卢小姐喜结连理!”如果说,在家祠中是列祖列宗成为他母亲的后盾,将李益打得晕头转向,那么在这个突然袭击的婚礼上,有总督大人为母亲压阵,神志不清的李益成了由母亲牵线的木偶。最后连木偶也不是了,在他的幻觉中看到小玉家的复仇之神黄衫客的弓箭瞄向自己,“猛然间,一道闪电划过眼前,他头痛欲裂,之后,一切都消失了……他昏了过去”。 在三个星期之中,李益命悬一线。幻觉中的母亲成了一个怪物般的吸血鬼。但是还有一个女人经常出现在他身边,他听到柔和的声音……他以为这是他的小玉,又觉得是一个可爱的护士。他稍有知觉时问母亲,和你一起的那个人是谁?具有讽刺性的是,在第17章节里,他一连问了5次:“她是谁?”在那次强迫的婚礼中,他并没有挑起过新娘脸上的红盖头,他当然会问出这样大惑不解的问题来。他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婚礼,他失忆到问他母亲:“我几岁了?”但当他渐渐清醒时,他母亲告诉他:“这是你的夫人。”李益狂怒了:“哦!你的手段太高明了。但先别庆贺。现在我清醒了!你会看到我到底是一个落入圈套的孩子,还是冲破你的同谋布下的罗网的男人!”那时,这个“同谋”冲了进来,跪在夫君的面前,向他呼冤:“我不知……一点儿也不知道!我向你发誓,你妈妈隐瞒了我们,我的父亲和我……如果他知道,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绝不会同意这样的骗你。”她在李益说胡话中知道他有一位挚爱的对象——小玉,有时他狂吻她的手,以为她就是小玉。“自从你让我知道这残酷的真相之后,我和你一样苦恼。李益,晚上,我坐在你的床边,总是以泪洗脸”。那女子纯洁、真诚,他们只能一起哭泣,“他们两人都是牺牲品”。 我们不知道法国读者品尝这道苦涩的大餐时是怎么咽下肚子里去的。而我们当然会想到鲁迅所说的“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难道我们不为之“忧愤深广”吗?可惜的是那个要像“男人”一样,要去冲破母亲设下的罗网的李益也只是瞬间的“灵光一闪”。他的对策是赶快离开这个家,却带着那个和他只能同床异梦的夫人。他曾想把她留在妈妈身边,但他知道这样“他将会面临着新的斗争”,他终于不像个男人,而且在斗争的意志方面他永远并不是一个“男人”。他可以不带小玉同行,这是为了爱,他要安排好一切,在三个月之后,再去接那挚爱的人;可是他为什么一定要带上那个只能“同床异梦”、他并不爱的女人呢?他身上就没有那根为爱而斗争的“脊梁骨”!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悲剧的下场。 黄衫客这位霍家的保护神在文中出现了5次,这个幽灵式的人物代表着公正与正义,却并不令人恐怖!这种虚拟的手法,也带有法国味:“这就像传说中,在杜伊勒里宫,一个红衣小人总在关键的时刻现身一样,两者之间只是颜色不同而已。”②我们觉得黄衫客在小说中的作用并不像小说的书名那么重要。他有何“传奇”呢?他并不存在任何“传奇”:“此书的法文标题Le Roman the I’Homme Jaune,法国读者一眼看去,似乎是‘黄种人的小说’,读过全书,才知道里面有一位幽灵般的黄衫客。”③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位“黄种人”是双关的,你可以实指有一个幽灵“黄衫客”,你也可以理解为李益就是这位“黄种人”,这部小说就是黄种人李益的传奇。使那些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法国读者,知道在陈季同的那个时代,黄种的中国人的婚姻是如此的不自由;陈季同给法国读者讲述了一个婚姻的悲剧“传奇”,无可理喻的“传奇”。 从第20章节至第28章节,实在也有些无可理喻的事情,令我们费解。我们认为这是小说从精彩的高潮稍有滑向下坡的可能。使我们捉摸不定的是软弱、犹豫的李益就没有作出任何决策。正如他自己曾经说过的:“人只能服从命运的安排。”他对小玉的挚爱没有成为他的动力。这只能有一个解释,陈季同要快速地让这个悲剧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他要早一点将这对恋人推向死亡的深渊,以便完成他的事前对小说情节的设计和主题的确定。 当李益与卢姓夫人去上任后,他的一切行为,都无可理喻,他并没有设法写信告诉小玉被迫成亲的窘境,对他这样一个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的状元来说,这是轻而易举的事。当小玉私下卖掉紫玉钗,命亲信之人送给他一封非常知心而可怜的信件时,他不回信也罢,可是他却扣留了送信人,也就是希望他结婚的消息不让小玉知道。原说三个月后要去接小玉,可当他拖了一年多之后,得到了升任新职的机会,他到京城谢恩,于是他与小玉就近在咫尺,可是他处处躲避与小玉相熟的人。当他第二天要回到新的任所去的时候,他甚至觉得非常轻松,好像他逃过了一劫似的:“现在,他自由了!他能离开南京了,不必担心被发现、担心不期而遇的会面,那只会带给他可怕的痛苦。”那么,小玉的痛苦呢?他能贴心地感知吗?在小玉的那封信中,她不是将自己的痛苦表达得清清楚楚了吗?但这位善于作心理描写的陈季同并没有告诉我们足够的、可以说服我们的有关李益当时的心理逻辑。陈季同为了让他们二人“速死”,甚至将李益写得与负心郎相比也相差无几了。李益只有两个没有行动的想法:“开始,他还想回到小玉身旁,跟她一起私奔,但一想到这么做的后果:名誉扫地、背井离乡、隐姓埋名、居无定处、违背法律和道义,不容于人群,最后会更加不幸。”另外,他就是幻想“奇迹”的出现。奇迹能从天而降吗?如果没有自天而降的奇迹,他似乎要向小玉隐瞒一世?他只自认自己是清白的,他只是入了他母亲精心策划的圈套而已。难道作这样的自我安慰就够了吗?这就是一位状元的智商?实际上陈季同在创作上是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如果误会不深,小玉就不会死,他事先设计的主题就无法表现,那么他的小说的结局,就会向《紫钗记》靠拢。而要让小说直奔主题,他就必定要将李益无可理喻地延宕和隐瞒。但又不去强调过去李益曾暴露的“人只能服从命运的安排”的人生观。这是小说中出现的不成熟和不够圆满的笔触。李益既然是如此,那小玉在得知他已结婚的消息之后,她就有权作她的“浮想联翩”,于是误解就产生了: 她的李郎,她疯狂爱着的李郎,就是这样对他的。 这个男人的行为多么背信弃义!可以肯定抛弃她是他预先谋划好的,在离别的前夜,他将她抱在胸口,情话喁喁地让她陶醉,这是他鄙卑戏剧的最后一幕。哦!必须承认,他真有表演的天赋!……他表演得太完美了……令人厌恶吗?简直不可思议!正是背叛才能演得那么温柔;正是谎言才使他在她身旁颤抖、爱抚、祈求、哭泣,而她真是个傻子,相信一切,一点儿看不出,也不能理解他在骗取她的信任,玩弄她的纯真!哦!可耻!可耻! 陈季同笔下的小玉的心理描写是真实可信的;相反,我们无法理清李益的思路。他可以成为状元,他可以善处政务。可是在他所爱的小玉面前,我们只能说无可理喻。正因为无可理喻,小玉才会在愤怒中死亡。 当李益以为明天可以离开南京而感到“自由了”时,他甚至在崇敬寺里还饮了几杯酒。这时他遇到了好友崔允明与韦夏卿。他们向他开火,并将他带到了小玉的家中。在汤显祖的《紫钗记》里也有类似的一幕。小玉在李益的面前责问他,但李益一再真诚地解释,使晕过去的小玉又醒过来,相信了李益的真情还是属于她的,李益并没有向卢太尉屈服。但是陈季同笔下的李益在小玉面前却像一尊“冰雕”。他认为只有当小玉母亲和崔允明、韦夏卿不在面前时,他才可以跪在小玉面前痛哭流涕地向她诉说一切。那真是“男儿膝下有黄金”啊;他也没有一滴眼泪,在这样冰冷的场面中,“冰雕”是不会融化的,“冰雕”当然不会“流泪”,这也真是“男儿有泪不轻弹”了!于是,愤怒的小玉站起身来,走近她的情人: 那么,你要给我的就是沉默、冷淡和蔑视吗?她喊道。我还以为会好一些呢。我觉得男人利用一个女子的软弱欺骗了她,即使没有真诚的忏悔,至少也会表示一句歉意。连这样的要求,你都拒绝我!可是你却毁了我的一生,让我因你而死。……她满含泪水地看着他,焦急地期待他告诉她些什么。她的表情突然改变了,双手捧心,站立起来,双目直视,好像看到什么可怕的景象;她发出一声惊叫,颓然倒下……姑娘的心脏已停止跳动,小玉终于从痛苦中获得解脱。 自认“清白”的李益看到小玉如此愤怒地将他说成一个骗子,觉得简直是“南辕北辙”。他实在将小玉这一年多的揪心的痛苦,太置若罔闻。直到姑娘逝去,他才扑在尸身上千呼万唤,但小玉是永远听不到了。其实,只要他将自己平时对小玉具有的“负罪感”的百分之一流露出来,也许小玉在这种“精神治疗”中可以不死;即使已病入膏肓,她死后的灵魂也可以在这种“负罪感”中得到安顿,用不着时刻跟着李益,让他永远不得安宁。 就在小玉心脏停止跳动时,另一个人却得到了无限的欣慰。那就是“婚姻代理”鲍夫人,她听到李益回到小玉的身边了,觉得作为介绍人,小玉这一年多的痛不欲生,她也是负有责任的,因为她缺乏预见,她作为“月下老人”,没有看准李益是这样一个无情的人。现在李公子回来了,她在她的珠宝商丈夫面前感到多么愉悦。可是正在她充满喜悦与庆幸时,小玉家的仆人来报凶讯,要她去安慰正沉浸在悲痛中的失去女儿的妇人。这时珠宝商正在琢磨一块美玉:“砰地一声,传来玉石摔碎在地板上的声音,可怜的珠宝商手中的杰作掉在地上,化成无数碎片……”即使是在这喜悦向惊愕的“突变”中,作家还不忘欧化的象征手法的自如运用。接下来当然是中国的丧葬的繁文缛节的描写。陈季同将多种中国民俗风情在小说中充分地展现了,家祠、结婚、丧葬等等细节都不是生硬地插入,而是很自然地镶嵌在小说的情节中。正如严家炎先生所说的:“如果说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风俗画反映的是近代法国的社会风尚史,那么陈季同《黄衫客传奇》中的风俗画却主要是描绘中国传统的民俗场景与画面。……陈季同自觉地向欧洲读者介绍中国的民俗,目的是希望能够增进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④而法国《图书年鉴》1890年号也说:“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会以为自己来到了中国。作者以一种清晰而富于想象力的方式描绘了他们同胞的生活习惯。” 在本书的情节链中,小玉的惨死也预示着李益的必死无疑。如果他的确不爱小玉,那么小玉的死倒使他在两个女性的“矛盾”中得到了解脱。可是这尊“冰雕”的内心却又是火热地爱着小玉的。那就必然会增加他的负罪感,而且最终会被这种负罪感所压垮。当他回到新的任所后,他喜怒无常,有几次几乎危及卢氏的生命,好像小玉是卢氏害死似的。但有时他会跪在卢氏的脚前向她忏悔,他大概也知道,卢氏也是受害者、牺牲品。在暴怒与柔情的交替反复中,最后他疯了: 一天早晨,可怜的疯子被抬到庭院中,在夫人和岳母的看护下,躺在长椅上休息。 突然,他半坐起来,长久地凝视着身旁。 他的双眼一时间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好像能看到、懂得和认识身旁的人了。 然后,他注视着天空中的一个亮点,正面的太阳将一大块白云变成平缓的银色山峰。黄衫客从天上飘然而落,小玉跟他在一起。她拉着李益的双手,温情款款地微笑着说: ——来吧,李郎!你受的苦够多了。疾病的折磨能够抵消你的过错了。我现在原谅你了,我还是爱你的,我来带你同去那无尽的乐土。来吧,我的爱人! ——小玉,我来了!他大声喊着。 他用尽气力站起来,僵在那里;不幸的面孔,被狂喜所照亮,一时间变得英俊非凡。随后,他全身剧烈地痉挛,发出一声深深的叹息,又倒在椅子上。通过幸运地与死亡亲吻,李益最终从身体的折磨和精神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也只有死亡,可以永久治愈人世间所有的苦难。 小说以这样的双双死亡落下了悲剧的帷幕。陈季同突破了传统的章回体的束缚,以法国读者非常习惯的手法,震撼着他们的心灵。同时,好让我们再次去深味,在这部小说问世35年之后,有一位伟大的中国作家将自己的国家比喻成“人肉的筵宴”,而且连“子女玉帛”也能作为“办酒的材料”,他呼唤道:“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而在鲁迅发表这样深刻的杂文的35年前,陈季同就用小说的形式,写了在当时的家族制度与礼教统治之下,一个“中国味”的用“母爱杀子”的故事。 注释: ①引自罗曼·罗兰1889年2月18日日记,转引自《中国人的自画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 ②转引自《黄衫客传奇》封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③李华川:《黄衫客传奇·译后记》,《黄衫客传奇》,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8页。 ④严家炎:《〈黄衫客传奇〉·中译本序》,《黄衫客传奇》,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