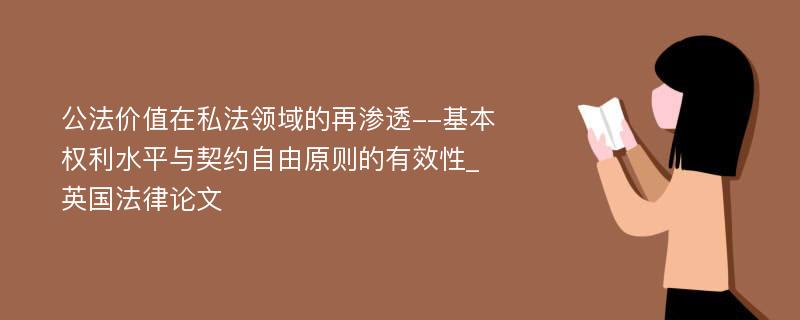
公法价值向私法领域的再渗透——基本权利水平效力与契约自由原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法论文,私法论文,基本权利论文,契约论文,效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基本权利效力并非是一个单纯的宪法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宪法与民法的关系问题。如果坚持宪法只规范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契约自由实行严格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则基本权利只有垂直而无水平效力。且它还是一个同时涉及法学与政治文化关系的问题。对人的本质属性的假定、国家定位、公法与私法、宪法与民法的关系构成该问题的核心,故而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成为理解基本权利水平效力与契约自由原则关系的一个深刻的政治哲学背景。
一、垂直还是水平?
基本权利水平效力(horizontal effect)① 与垂直效力(vertical effect)对称,在不同国家的称谓不同。德国称其为第三者效力(third-party effect)或者间接第三者效力(indirect third-party effect);美国称其为“州政府行为理论”(state action doctrine);加拿大称其为“政府行为”(governmental action);英国称其为“水平效力”(horizontal effect)。在宪法学理论和实务上,基本权利效力经过了一个发展变迁的过程。传统基本权利效力仅及于国家,这是将基本权利限定于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结果,表现为基本权利仅有垂直效力。但是,新的理论和实践却突破了这一认识和做法,基本权利不仅用于抵制国家专断侵害个人权利,其效力也扩及私法关系,产生了水平效力。而基本权利在何种情况下构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水平效力依然是一个值得认真解说的话题,英美与欧陆在此问题上不仅是称谓不同,而是有立国哲学的深刻差异。
基本权利水平效力有三重含义,它们分别是伦理或宗教意义上的水平效力、宪法或制定法上的水平效力、司法上的水平效力,也被称为作为哲学的水平、作为诉讼前的水平、作为司法创制的水平(Horizontality as philosophical;Horizontality as pre-litigation;Horizontality as judicial creation)。② 狭义的基本权利水平效力是指后者,③ 指法院在裁决私法关系即两个私人之间争议过程中就当事人主张的宪法权利进行权衡和裁判的过程。伦理或者宗教上的水平效力是指个人基于宗教或者道德确信要求在一切领域中贯彻基本权利,这是一种既缺乏实际纠纷又没有规范基础的哲学或者神学主张;④ 宪法或者制定法上的水平效力是指要么宪法直接规定基本权利效力及于私人,⑤ 要么制定法在规范私人关系的普通立法中将基本权利具体化。⑥ 这既是基本权利水平效力一个很重要的维度,也是挑战传统认为基本权利效力不及于私法关系的一个有力基础。传统观点认为,基本权利不适用于私法关系,只有垂直效力。该观点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有些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宪法基本权利可以在私人之间实施,从而使基本权利水平效力具备了规范基础。这一观点同样忽视的另外一个基本事实是,通过制定法,基本权利同样可以产生水平效力。普通立法机关负有规范私人关系的立法义务,立法者可以在制定普通立法时将宪法价值具体化,其具体化的过程就是基本权利在私法领域中展开的过程,也是基本权利的水平效力。这一点,特别体现在针对宪法平等原则的普通立法中,如美国的反歧视立法,我国的劳动法等社会法。司法上的水平效力不同于前两者,它要求必须有实际的民事纠纷。在该民事纠纷中,一方当事人主张宪法权利,法院支持当事人的主张;它是法院在既缺乏宪法明示规范又没有普通立法可以援引的情况下对基本权利适用于私人及为何适用于私人的一种正当化过程。本文所阐明的基本权利水平效力正是在这一较为狭隘的意义和脉络上的分析与展开。
基本权利水平效力是对传统宪法理论的一个发展。虽然德国的第三者效力或者间接效力与美国的“州政府行为理论”客观上产生了同样结果,即基本权利适用于私法关系,但细究起来,两者的性质却有很大不同。“州政府行为理论”依然是基本权利垂直效力的另一种表现,因为该理论适用于私法的前提是必须在一个私人关系中寻找“州行为”或者“国家行为”要素。这是一种坚持国家与社会二分的哲学思考模式,也是消极国家观的法律理论表达,以及经济自由主义或放任主义在公私法关系领域中的体现。基本权利第三者效力或者间接效力与之不同,其干预私法关系所依据的是另一种哲学立场与法理,它将国家置于能动地位主动保护个人自由,从而染指私法自治领域。因之,对比美国的“州政府行为理论”,第三者效力或者间接效力在基本权利适用于私法关系时远较美国来得率直。
二、警察权力、契约自由与垂直效力
从前述分析可以看出,水平效力不单纯是一个宪法问题,甚至不单纯是一个法学家族内部宪法和民法的关系问题,而是与政治哲学密切相关。这一政治哲学就是如何看待人?如何定位国家权力?如何界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契约自由(liberty of contract或者freedom of contract)可称为经济自由,与社会主义或者干预主义对称,是指个人在经济生活中的自由不受国家干预,也是经济放任理论在私法关系中的体现。作为一项私法原则,契约自由在持不同信念国家的表现有很大差异,涉及国家与社会、公法与私法的关系之思考。这一原则产生于17、18世纪,是启蒙思想家对当时欧洲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理论总结。它强调私人领域自治,主张国家不得干预个人经济自由,国家只是一个被动的管理者,私人领域由当事人根据意思自治自我主张,订立契约。这是一种坚持国家与社会分离的观点。支持这一观点的更进一步的理论基础是政治哲学予以解答的问题。英国很早就形成了一种认识这些问题的深厚传统,其经典阐述体现在弗格森《论市民社会的历史》(1759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这一传统将人视为一个追求自身经济利益和幸福的个体,他们共同组成市民社会,国家只不过是为了个体利益的实现而设立的管理者,是从市民社会“长”出来的一个政治组织。个人先于国家,高于国家。对于市民社会和个人而言,国家是手段而非目的。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国家观。受此观念支配,此时的国家被称为“夜警国家”,国家只享有“警察权力”(state's police powers),其职能限于维持治安。国家的角色是消极和被动的,市民社会即私人领域获得了自治属性,任何时候国家不得染指,除非为了公共利益。因而在英国思想家那里,国家角色不仅是被动和消极的,还在道德上被赋予“恶”的属性,成为一个令人生厌和恐惧的想象物,即“怪兽”。国家之手或者“利维坦”只履行公共职能,超出这一领域之外便是国家的“禁地”。受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支配的契约自由原则对国家存有的“防禁”之心跃然纸上,禁绝国家干预和插手个人事务。契约自由原则是该认识前提下的一个逻辑推论。
这一政治哲学同样支配了英美法律体系。英美等国没有欧陆那样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英国人拒绝对法律体系作出这样的划分。在他们看来,将法律体系划分为公法与私法,国家机关和私人适用不同的法律,由不同的法院审理纠纷,既是区别对待,也是对平等原则的违反。英国法律坚持“政府和公民同受法律之治”。此处的法律是一个同一体系,无所谓公私法之分。因而,拒绝对法律体系作出公私法之分,是坚持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平等地位,拒绝将国家视为在道德上优越的伦理存在,体现了个人先于国家,以及国家是手段而非目的的自由主义政治理念。
这一自由主义理念充分体现在法院的判决中。美国最高法院1905年判决的“洛克纳诉纽约州”一案被认为是坚持这一政治立场的产物。该案的判决受到了持异议的法官霍姆斯的激烈批评,他说:“该案是依据一种大部分国家所不支持的经济理论所做出的判决。假如它是一个问题,我是否同意这一理论,在做出我自己的决定之前我都想进一步和长期研究它。但是,我不认为那是我的责任。因为我强烈地认为我同意与否与多数人法律意见所支持的权利是无关的。”⑦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坚持自由主义和经济放任理论,裁决规制诸如最高工时、最低工资等方面的州制定法侵犯了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中的“自由”。在当时,第14条修正案规定的“任何一州,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人的生命、自由、财产”中的“自由”被解释为经济自由,即契约自由。并且,由于最高法院对这一立场的顽固坚持致使罗斯福新政受挫,从而导致总统联合国会改组最高法院的计划引发宪法危机。在强大的政治压力及最高法院内部法官结构改变的双重影响下,最高法院才于其后的判决中改变了立场。
基于这一立国哲学,基本权利效力的发展在美国遵循了相同逻辑。鉴于南部各州广泛存在的制度性歧视,在缺乏国会立法可以直接将宪法基本权利适用于私人关系的情况下,美国法官有强烈意愿矫正这一现象,从而以“州政府行为理论”来正当化其作为。由于该理论需要在一个本属于私法关系中寻找州行为,虽然表面看似基本权利适用于私人关系,但其理论本质依然属垂直而非水平。类似地,英国《人权法案1998》(The Human rights Act 1998)规定将《欧洲人权公约》并入英国的法律体系,规定“公共机构”有义务实施《欧洲人权公约》规定的基本权利条款。“公共机构”⑧ 包括法院、地方政府、履行公共职能的私人公司,要求私人公司行为必须与《欧洲人权公约》基本权利条款相适应,这既构成了公司社会责任,也是道德和伦理意义上的基本权利水平效力在公司这一私法领域中的体现。英国《人权法案1998》对私人公司实施《欧洲人权公约》基本权利条款是强调私人公司履行“公共职能”,而不是泛泛谈及公司基本权利保护责任。持相同政治理念的加拿大,其“政府行为理论”也是强调私法关系中必须有“政府行为”,而不是理直气壮和不加掩饰地将基本权利直接深入至私法关系中。虽然英国公司社会责任是道德上的基本权利水平效力在公司这一私法领域中的展开,但与美国和加拿大强调私法关系中渗入“州”或“政府”职能实有异曲同工之妙,是同一种逻辑思考下的产物,反映了英美深受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文化浸染这一事实。故尔这些理论在实质上都属于基本权利垂直效力的变体,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水平效力。
三、伦理国家、契约自由与水平效力
对比英美等国,同样是契约自由,其所包含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解读在欧陆却大相径庭。隐含在其后的政治理念构成德国第三者效力或者间接第三者效力的理论基础,从而使基本权利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水平效力,而不仅仅是垂直效力的变体。
在欧陆,对契约自由的解读所依赖的对人的本质属性的假定及国家角色远不同于英美。欧陆素有这样的认识传统,认为共同体先于个人存在;人的本质属性是政治的。⑨ 共同体中的个人渴望政治自由与实现美德,而非自由主义哲学假定个人追求经济利益和获取幸福。⑩ 其与英美自由主义哲学认为个人先于国家、国家是从社会中“长”出的那种认识相去甚远。在欧陆哲学这里,共同体先于国家与人具有政治属性决定了个人自由只能依赖国家获得,而不是相反。欧陆政治学与国家学认为国家具有伦理属性,国家是最大的善,是目的,(11) 而非仅仅是手段;个人只有仰赖国家才能获得自由。这一思想的经典表述是黑格尔,其最早的哲学阐释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亚氏将人假设为政治的,(12) 黑格尔则认为“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13) 个人只有成为国家的一员,才能实现他自己,才能在政治生活中获得身份资格和权利。他说“由于国家是客观精神,所以个人本身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也就是说,个人如果脱离国家,不接受国家的统治和管理,他就丧失了自由和作为市民的种种权利。(14) 因此,虽然在欧陆哲学家那里也存在着国家与社会分离的理论,但其理论内核和实质却从未获得过英美那样的理解。国家与社会固然分离,但国家并非从社会中长出,而是相反,国家保障着市民社会和私人利益。社会领域的经济自由和自治端赖国家保护,离开了国家,社会自治和个人自由是不能存在的。这一思想的法律阐释则首推孟德斯鸠,其经典表述见于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关于何谓自由的概念中。他说,“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15) 所以,在欧陆这里,“人的自由”中的“人”并非是单个存在的个体,而是“公民”。(16) “个人”是不依赖共同体的一种独立存在,“公民”则是依赖政治组织获取的一种身份资格。“自由”则指拥有共同体成员资格的政治自由,(17) 而非英美国家个人的经济自由。(18) 与之对应的国家也不似英美那样令人生厌和充满恐惧,近不得,又离不开,而是一个可以依靠的对象和保护者,是父亲。这是典型的国家主义观。欧陆契约自由的含义就存活于这一观念之下。因之,受国家主义观的支配,契约自由从未获得在英国那样绝对自治免于国家干预的内涵。
国家主义观念同样支配了欧洲大陆公私法的划分。虽然公私法的划分在表面看来是国家与社会、公域与私域二分的结果。但是,罗马法关于公私法的划分所坚持的正是国家与社会分属不同职能,赋予公法在道德上较私法优越地位的结果。国家的伦理属性决定公法必须不能与私法共处一体。虽然罗马法的公法与私法体系同样高度发达,但公私法区分本身即为不平等视之的结果。不仅二者的道德地位有异,表现为公法优越,私法从属,即公法是保护公共利益的法律,私法是保护个人利益的法律;且公法法律关系还被认为是不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私法关系的当事人双方是以法律上对等的意思力而对立的,公法的公定力乃国家意思有优越效力。(19) 而在英美那里,虽然于理论上缺乏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但人们还是在心里预设了一个公域与私域的对峙。这一对峙无疑是一种平等形象与图式。欧陆虽然有公私法的划分,但二者实为不平等,有等级之别。
在德国基本权利水平效力的发展脉络中,可以清晰地辨识出基本权利深入至私人领域过程中国家主义的痕迹。这可以从尼伯代最早论证第三者效力的案件中识别(1954年12月)。法院指出:基本权都是社会生活的秩序原则。这些社会生活的秩序原则,对于国民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直接意义。因此,所有私法的协议,法律行为及作为,都不能与之抵触。(20) 认为国家及法律秩序具体的结构及公秩序,都是由之形成的。德国宪法法院1958年于“路特”案中第一次发展出作为“客观价值秩序”的基本权概念正当化了基本权利的水平效力。(21) 在基本权作为“客观价值秩序”(objective order of values)的法理之下,一国法律秩序无不受宪法价值(规范)的统领。在此,公域与私域、公法与私法的界限再度模糊,国家权力和公法价值表现出优越感。作为“客观价值秩序”的基本权深入至私法领域,侵害契约自由原则是由宪法的最高法地位决定的,因为宪法规范既是客观价值,也是最高价值。这既是一种将一国法律秩序视为一个等级结构,也是坚持公法价值(具体表现为宪法价值)优越于私法的认识结果。既作为上位价值又作为公法价值的宪法规范指引和规范着包括私法在内的下位规范和私法价值,下位规范和私法规范有义务遵守上位价值和公法价值,将其贯彻在私法关系中。这便是真正意义上的基本权利水平效力,其背后隐含的是能动积极的国家观念,及公法优于私法的认识。在同属于欧洲大陆的希腊和西班牙,基本权利水平效力秉承同样的逻辑和法理,不需要立法创制,一些基本权利可以覆盖私人诉讼。(22) 这说明,欧陆在看待宪法与私法关系时受相同或者相似的政治哲学及受此哲学影响的法理支配。
对于契约自由原则而言,受国家主义观浸染的德国普通法院法官与宪法法院法官从未将体现私人自治的契约自由视为神圣“禁地”。与之相联系的是,欧陆不仅是福利制度的发源地,其宪法也是最早规定国家干预政策的宪法类型之一。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还是历史上第一部规定基本权利可以适用于私法关系的宪法,从而开创了宪法规范上的基本权利水平效力先河,说明在欧洲大陆,无论在政治哲学那里,还是在公私法的关系上,从来没有或者缺乏英美等国那样将私人领域视为神圣禁地,除为了“公共利益”之外,任何时候国家不得进入的区域这样一种认识。因而,透过公私法的划分,宪法直接规定基本权利水平效力,以及其后劳工法院法官和宪法法院法官在基本权利作为“客观价值秩序”的法理之下正当化基本权利水平效力过程,都可以感受到公法之于私法的优越地位。而这些做法的背后,是国家主义之下国家作为伦理和目的的政治哲学的支持。
四、道德水平效力对契约自由的再渗透:公司社会责任
基本权利水平效力极大地影响了契约自由原则,致使公法价值进一步向原来仅单纯服从公共利益限制的契约自由原则渗透。这一渗透最为集中的体现就是公司社会责任,并于客观上导致了公私法的深度融合。(23)
作为私法人,一直以来,公司贯彻契约自由原则,除为了公共利益目的得限制公司行为之外,公司行为不受其他限制。但是,基本权利水平效力却促进公司接受更多的宪法价值。具体而言,公司社会责任就是工商业企业在盈利之外,无论在何处经营都负有尊重和促进普遍的义务和责任。虽然“普遍的义务和责任”的含义模糊而不确定,但是,从目前世界各国和一些国际组织的典章和做法中可以看出,除了遵守法律、法令和公共道德之外,“普遍的义务和责任”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人权责任。(24) 这是公法价值,亦即宪法人权价值向私法自治组织渗透的体现,也是道义或者道德意义上的基本权利水平效力在公司法领域中的体现。更为具体而言,它要求公司与利益关系人,包括雇员、合同签订机关、供货商、服务提供人、消费者、监管机构、商业伙伴、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部门培养牢固的互惠互利关系,促进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除了市场全球化、竞争加剧、私有化、消费主义、非政府组织作用的增强,通信发展和因污染和资源枯竭带来的环境挑战等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之外,人权价值的普遍化和日益增强的影响力构成公司社会责任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英国《人权法案1998》规定,公共机关与《欧洲人权公约》相抵触的行为无效或者非法。《法案》规定公共机关的定义是广泛的,包括法院和法庭,以及职能带有公共性质的任何个人。其外延不仅扩展政府部门和地方权力机关,还包括某些行为具有公共性质的私人机构,如从事公用事业的煤气、电力、排污和供水的私人公司。这些公司履行公共职能,尽管它们在本质上依然属于盈利的私人公司。目前,这一状况已体现在英格兰的判例法中。一名家庭物业业主向当地的供水和排污公司提出诉讼。由于自1992年以来公司未能修理好他家附近的排污设施,导致他家被水淹。公司拿出证据表明,要解决每一个可能遭受相同问题的家庭的淹水问题,平均每户至少耗资3万英镑,因此公司的总支出将超过10亿英镑。一审法庭认为,根据法案,作为一个公共机关,该公司未修理排污系统是对业主的《欧洲人权公约》第八条规定的家庭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和“第一议定书”第一条平安享受财产的权利的侵害,尽管公司列出证据,但它不能解释对该业主权利的干涉“对国家的经济利益是必需的。”在该案中,供水和排污公司是一家私营企业,但是法院却按照《欧洲人权公约》规定的权利标准要求它。这是基本权利水平效力的体现。这一过程得益于两个因素:一是根据《法案》的规定,法院作为公共机关有义务在诉讼中贯彻基本权利,英国法院是审理普通诉讼包括处理私法纠纷的机关,法院负有贯彻基本权利的义务就意味着它有义务在审理普通的民事法律纠纷中适用基本权利;二是根据《法案》的规定,履行公共职能的私营企业是公共机关,负有在与客户的关系中贯彻基本权利的义务。两方面因素的结合,是基本权利水平效力在公司行为领域中的具体体现,也是公司社会责任的表现。(25)
目前,公司社会责任已不是偶尔的姿态或出于市场或公关目的的举动,而是渗透到公司的综合政策和行为规范中,纳入到整个商业运营和决策程序中,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增进公司的经济利益,包括减少风险、增加品牌价值、增进良好信誉和加强员工士气,提高生产效率。英国政府和金融公司在此方面已有行动。英国政府已任命了一位部长负责公司社会责任。贸易与工业部已对公司法实施了检查,目的是将英国兴办工商业的框架现代化。英国的金融领域也考虑了公司社会责任概念的兴起。专门从事股票指数的设计与计算的FTSE公司(即“伦敦金融时报股票交易指数”公司)于2001年7月推出了一种被称为FTSE4GOOD(伦敦金融时报优良指数)的新的道德交易指数。欧盟也认可在公司社会责任领域有更大的发展,并发布了一份公司社会责任讨论文件。其目的是指引欧盟如何在欧洲和国际上促进公司社会责任的广泛辩论。2000年7月,联合国发布了《全球条约》。该条约不是一个规范性文件或行为准则,而是将自己视为一个平台,用来促进在人权、劳工和环境领域的对话和学习,目的是促进学习和对话来传播基于九项普遍原则的良好行为惯例。这些原则来自《世界人权宣言》、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权的基本原则》和《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原则》。另外,联合国促进和保护人权分会制定了关于公司行为的指导原则。这些指导原则寻求全面了解工商业根据《世界人权宣言》负有的责任,还强调公司的原属国政府和驻在国政府有责任监管第三方的行为(第三方包括公司),以在其司法管辖区保护个人的人权,指导原则草案于2001年11月公布。(26)
在这些发展的共同作用下,公司日益加入到开展公司社会责任的行动和行列中来,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包括制定标准和培训计划,用以衡量公司社会责任。并且,公众对公司在国内和国外的行为的期望值增加,要求它们不仅实施对社会负责的行为规范,还要向他们的主要利益关系人就此作出汇报。南非工人对英国一家公司Cape Plc提起诉讼,表示他们因为Cape公司在南非的开矿活动染上石棉沉着病和相关疾病。Cape公司试图辩解英国不是适当的审讯地,此案应由南非法院审理。上议院驳回了这一论点,裁决确认,英国公司可能因其在国外的行为在英国法院被起诉。2000年年初,Cape公司发表声明,同意向工人和他们的家庭支付2100万英镑的赔偿。顺应全球领域公司社会责任的兴起,我国2006年1月1日起实施的《公司法》也规定了公司的社会责任。(27) 《公司法》第五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该条作为《公司法》的一个原则,明确了公司的社会责任,因而也是道义意义上的基本权利水平效力在公司这一私法人领域中的体现。(28)
综观全球领域兴起的公司社会责任这一现象,它既是人权这一公法和宪法价值向传统私人领域渗透的体现,也是道德意义上的基本权利水平效力的开展,且其已不仅局限于司法领域,而是体现在日常行为规范及评估过程中。因为司法只是事后的,日常行为规范更有意义,它可以有效阻止公司一切可能的侵害人权行为的发生。因而,当今契约自由原则已不同于已往。以盈利为目的的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不单纯是个人意志的集合,而须更多地考虑公法价值,即人权或者基本权利。这也是一个公私法的再度融合过程。亦即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表现为公法的人权价值向私法领域渗透,私法须受公法人权价值的约束。
五、宪法崛起、公私法融合、人权保护水平提升
从对基本权利的消极解释到积极解释开放了正当基本权利向私法领域扩张的法理,既提高了宪法的地位,也有助于提升人权保护水平。这一过程是通过公私法融合而达至的,因而也是公私法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此处尚有一问题不容忽视,即欧陆能动积极国家的角色究竟限定在何处?美国消极被动国家的角色在尊重契约自由原则的前提下究竟还可以走多远?该问题也可以这样发问,即欧陆第三者效力和美国“州政府行为理论”在各自遵循不同法理的前提下究竟有多大空间?
首先,宪法地位的提高表现在德国宪法法院在将基本权利效力扩及至私人过程中的推理和正当化过程中,这就是将宪法及宪法列举的基本权利解释为“客观价值秩序”,而不仅仅是个人的主观权利。(29) 主观权利和客观价值秩序所依据的既是不同法理,客观上也会产生不同的司法和立法效果。如果一项宪法明示的基本权利是个人权利,则这一权利受到侵害之时,个人可以向法院起诉,这是“无权利无救济”的显现;而如果一项宪法明示的基本权利不仅仅是个人主观权利,还是“客观价值秩序”之时,则不仅普通立法者负有立法作为义务,通过制定法律将这一价值体现在立法秩序中,而且行政和司法机关也负有在执法过程中贯彻这一价值秩序的义务,否则,两机关的行为就构成违宪。德国宪法法院是在“路特案”中首次提出基本权利作为“客观价值秩序”这一概念的。(30) 在该案中,宪法法院要求管辖民事诉讼的法官使用系争基本权利作为裁判过程中的法源。这一裁决意味着,如果可以适用,则民事法官有义务去调停不仅是基于民法典所产生而且也是基于基本权利的两个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这里发生了一个魔力般的转换,即基本权利并未直接适用,而是进入民事程序。这是一个根据民事法官有义务依据宪法条款去解释民法典的特定条款即所谓“一般条款”而产生的结果。宪法基本权利透过民法典“一般条款”(general clause)这个过滤器,渗透至民事裁判程序中,从而使公法价值融进了私法关系。在其后著名的“堕胎合法化”案件中,宪法法院对基本权的价值秩序性质又进行了深入阐发,指出:“依基本法第二条第二项第一款的规定,可导出国家有义务保障人的生命。……根据联邦宪法法院历来的裁判,基本权条款不仅是个人对抗国家主权的防御权,同时也是客观秩序……国家这一保障义务当然不仅禁止国家直接侵害形成中的生命,也要求国家在出生之前予以保护。换言之,防护来自他人非法的侵害。……在基本法价值秩序中,位阶越高的法益,国家所负有的保障义务也就越大。无庸赘言,人的生命在基本法秩序中,具有最高的价值,它是人性尊严的生命基础,也是一切其他基本权的前提条件。”(31) 通过将宪法解释为“客观价值秩序”,宪法的地位也实实在在地得以提升。
其次,基本权利以不同法理适用于私法反映了全球范围内公私法进一步融合的趋势。虽然大部分美国学者同意在此问题上抵制德国做法,赞成将基本权利限制在垂直效力上,即坚持基本权利的“政府行为理论”,但是,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是,就连奉行自由主义理念的老牌国家英国,也因循情势变化承认并发展了基本权利水平效力,虽然其背后的法理依然是垂直。美国法官的坚持在很大程度上值得钦敬和理解,它既是法官恪守权力分工原则的体现,即法院尊重国会在依据宪法,将宪法价值具体化过程中的优先权,也反映了美国法官对契约自由原则和个人自治的充分尊重。因为必须看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法官发展“州政府行为理论”,将基本权利效力适用于私法关系时是出于被迫不得已的选择。当时,尽管宪法第13、14、15条修正案已明确禁止制度性的种族歧视,即州政府和公共机关的种族歧视,但在南部各州,私人关系中的种族歧视依然大量和严重存在,此时国会尚没有制定禁止私人歧视的法律在个人之间实施,亦即在宪法基本权利水平效力缺乏制定法基础的情况下,法官才不得不挺身而出,通过将特定案件中的私人歧视解释为法官实施不平等有违宪法,从而使宪法平等原则及于私法关系,纠正私人关系中的种族歧视,因而其在本质上依然是垂直而非水平效力。其后,国会通过立法在私人之间贯彻平等原则之后,法院减轻了这方面的负担,“州政府行为理论”在司法实务中的效用便不再那么重要。如果发现在私法关系中存有歧视,法官不再需要曲意婉转,非要在其中发现和确认一个“州行为”或者“政府行为”而适用宪法基本权利,只要直接适用国会立法就可以纠正私人之间的歧视。这说明,在美国,法官既恪守权力分立原则,又严格坚持宪法关系的垂直属性,对私法自治原则给予高度尊重。自然,这一理论还有发挥作用的余地和空间,法官可以之为基础继续在其他个案中通过解释特定基本权利条款适用于私人关系,扩大和提升人权在私法关系中的保护水平。
可以看出,无论是美国的“州政府行为理论”还是德国的“间接第三者效力理论”,其实质并非是法院跨越契约自由原则的界限,将所有基本权利贯彻于私法关系中,主要是在个案中集中于宪法平等原则和其他特定基本权利条款。(32) 鉴于基本权利水平效力自始就存在着通过制定法的方式及于私法关系,严格意义上的水平效力只是司法实施基本权利的结果,因而立法机关或者立法者如果以普通立法实施宪法平等原则,矫正私法关系中的不平等可以有更多作为,其姿态更为积极,效果也更为普遍,且可以有效矫正立法和执行机关事前侵害人权的行为。因为,法院固然可以通过水平效力将平等原则及于私人关系,但毕竟司法权的本质决定了这一矫正是有限的;司法权的被动属性决定了它只能在事后提供救济,而不能防患于未然,并且,它不能纠正大面积存在于私法关系中的歧视,只能于个案中通过解释宪法贯彻基本权利水平效力,因而其效果是极为有限的。立法机关在此方面却有着更多的余地和空间,可通过制定法的普遍效力来解决这类问题,从而不假司法机关之手,将私法关系中违反基本权利的行为通过设定法律秩序禁止在事前,因而也是一种更为积极的事前保护人权的方式。自然,法院在此方面的作用也并未完全消失,而是在相当程度上起着补充作用。在此,除了立法的滞后是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之外,法院还可以能动地在私法关系中继续实施其他特定宪法基本权利条款,扩大私法领域中的基本权利保护,且法院于事后的补救作用依然是不可替代的。这也是基本权利水平效力之所以可以继续发挥作用的原因。
该思考同样可以帮助回答本节前面的设问,即欧陆国家水平效力限定在何处和美国州政府行为理论究竟能走多远?这里可以对此作出回答:欧陆国家水平效力限定在立法所不及之处,美国州政府行为理论保持在国会无立法之地。亦即欧陆水平效力理论只适用于立法所没有规范的地方,美国“州政府行为理论”只限定在国会不予立法之处,其共同之处就在于两者都只是在缺乏制定法上水平效力的前提下,才于私法关系中实施基本权利。因而,尽管两者所采取的立场不同,一个在实质意义上属水平,一个在实质意义上属垂直,但实际情形是趋于中平,并且两者都不会在此方面走得太远。(33) 如果立法机关在普通立法中充分考虑人权价值,则法院不必在私法关系中假手“客观价值秩序”或者“州政府行为理论”,普通法院和民事法官只消实施议会立法即可。该问题同时说明,在贯彻宪法价值这一问题上,普通立法者负有更为重要的立法作为义务。
再次,基本权利水平效力从原来单纯课以司法者的义务开始向着立法者和行政机关方向发展,预示着人权保护水平的提升,及促进人权政治文化。这既表现在德国宪法法院的判决上,也体现在英国政府的有关行动上。德国宪法法院在“路特案”中提出基本权利作为“客观价值秩序”之时,它正当化基本权利水平效力是通过强调民事法院法官的义务而进行的,但在其后的法理中,宪法法院开始集中于强调立法者的义务。如果德国宪法法院课以立法者义务属于法院向立法者发布指令,立法机关采取措施是基于宪法法院的指令而带有被动性,英国在此方面的发展则已远远超出了这一点。在英国,受《人权法案1998》的影响,在立法和行政层面贯彻《欧洲人权公约》规定的基本权利已成为两者的共识,且这种认识已开始向着行动方面转换。英国的这一做法具体表现为英国创立了一个“人权联合委员会”(the joint Committee on Human Rights,JCHR)作为议会的一个委员会。有学者将之称为人权保护的“议会模式”。这一模式的宗旨在于纠正现代议会和政府在保护人权方面的低能,从而对传统司法仅限于事后对侵害人权的补救提升至议会和政府事前的保护上来。(34) 英国的这一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人权保护水平的提高,并有助于创新一种新的人权保护模式,促进人权文化。虽然英国早于1951年就批准了《欧洲人权公约》,并于1953年生效,但是,由于担心《欧洲人权公约》与英国议会“绝对主权”相冲突,历届英国政府都拒绝将《欧洲人权公约》纳入英国的法律体系。布莱尔上台后,议会于1998年制定《人权法案》,2000年生效,从而使《公约》的基本权利条款真正并入了英国的司法体系,特别是法院在解释法律时须考虑《公约》,使公民可以借助《公约》的基本权利条款获得在英国国内司法体系中救济的权利,而不必动辄到位于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人权法院提起诉讼,后者既费钱,又耗时。但是,英国官方认识到,如果要将《公约》真正并入英国的法律体系,仅有司法事后实施基本权利是不够的,要促进一种新的人权文化,必须在议会和政府的立法和执法过程中贯彻基本权利条款,从而将基本权利保护提升至事前,以有效减少立法和政府侵害人权行为的发生。为此,在吸取其他国家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英国创立了“政治权利审查”(political rights review)这一概念,由议会设立“人权联合委员会”,增加议会监督和保护人权的功能。
英国议会设立的“人权联合委员会”是在吸取加拿大和新西兰两国议会监督模式概念的基础上加以改进的结果。(35) “人权联合委员会”的功能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它提醒议会立法要考虑人权含义;其次,促进与《人权法案》目标密切相关的人权政治文化,督促部长、部门官员和法案起草者考虑法案在人权方面的后果;再次;评估政府对司法宣布立法抵触的回应;第四,对于被质疑不符合人权的法案提出法律意见。目前,英国议会“人权联合委员会”对一系列法律进行了审查。尽管到目前为止,评价英国议会“人权联合委员会”在促进人权文化方面的效果的功绩还为时尚早。但是,在长远意义上,该机构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人权保护“议会模式”的产生,在传统司法审查之外引入了一个“政治权利审查”概念,它有别于司法的事后审查,也是试图分散传统权利保护责任,由所有公共机构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共同承担权利审查职责的一种新模式。同时,在宪法学理论上,这也是制定法意义上的基本权利水平效力在立法和行政两个领域中的体现,它改变了法官实施基本权利水平效力的被动性和单纯事后救济的局限性,从而将人权保护提至立法和执法层面,基本权利由单纯的事后救济改变为事先保护和事后救济并举,减少发生基本权利受国家机关和个人侵害的可能性,不啻为人权保护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促进人权政治文化。
最后,基本权利效力的变迁与契约自由原则的发展,提供了在我国认识公法与私法、宪法与民法关系的新契机。一直以来,“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是我国公法与私法、宪法与民法两大法律和学科关系的真实写照。除了滥觞于罗马法的公私法二分为我们在理论上设立认识经验世界复杂情形的一个直观和方便模式之外,更为直接的原因是宪法在我国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实施,包括缺乏宪法的立法解释和司法实施。但是,真实生活场景却一再提醒我们,二者从来没有、也难以在真正意义上分离。不用说一国法律体系体现为以宪法为根本法的法律秩序,一国法律秩序实为宪法秩序,就是在观看和探知基本权利效力变迁和契约自由原则发展的过程中也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在一国法律体系和法律秩序内部,公法与私法、宪法与民法之间是一种如何微妙和内在的有机联系关系。透过这一狭小视野,一个基本真实再次向人们展现:即国家与社会、公域与私域、公法与私法的对立和分离只是一种理论假定,是为了研究方便于理论上设立的一种认识模型,实际情形是二者从来没有、也难以在真正意义上截然分离。
纵横俯仰,公法与私法、宪法与民法的关系,观基本权利效力与契约自由原则关系之演变,无疑是经历了理论上的分离之后于现实舞台上的再聚首。这是一个充满戏剧和魔力性的嬗变历程。在此,基本权利水平效力之于契约自由,除了作为哲学的水平是一种永恒的理想诉求,宪法和制定法上的水平一直是一个事实之外,司法创制的水平则既是情势所迫,也得益于法官的亲力而为。
注释:
①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基本权利都可以产生水平效力。如果将基本权利分为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那些程序基本权就没有所谓水平效力问题,因为程序基本权是纯粹对抗或者抵御国家的权利。如果将基本权利分为私人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则政治权利中有的权利产生水平效力问题,如选举和被选举权、言论自由权等(有的国家不将言论自由权作为政治权利,而作为自由权),创制、复决、罢免则没有水平效力问题,它们是纯粹对国家的要求;由于社会权利是要求国家积极作为的权利,其实现需要立法者制定法律,故而其只产生制定法上的水平效力,一般不认为产生司法上的水平效力。但近来,这一状况有所发展,这就是有些国家和地区的法院通过对自由权作扩大解释,将社会权纳入自由权,从而使它们远看像社会权,近看像自由权,雌雄同体,一些社会权利也具有了私法效力。如果按照传统理论解说,只有宪法上的私人权利才产生基本权利水平效力,因为私人权利是纯粹个人权利,它们存在于私人关系中,在宪法语境下,它们对抗国家。当私法关系中的个人主张作为上位价值的基本权利时,便产生了基本权利水平效力。
②③ Georg Sommeregger,The Liberal Root of Third-party Effect Doctrines,http://www.iue.it/Personal/Researchs/Sommeregger/Horizontality%20—%20web.htm.
④ 目前,伦理或者宗教意义上的基本权利水平效力已经体现在立法中,表现为作为某一普通立法的法律原则。例如,公司社会责任就是伦理和道德意义上的基本权利水平效力在公司领域中的体现。我国《公司法》也将公司社会责任规定为该法的一项原则。亦即伦理或者宗教意义上的基本权利水平效力在某种程度上已向前发展了一步,被法典化,成为法律的一项原则,具备了规范基础。但由于这一规范仅体现为原则,尚不具体,其司法上的效力如何,即违反这一原则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司法上的责任和后果,或者制裁形式如何尚不确定,因而对比制定法和司法上的水平效力而言,作为原则的规范基础的公司社会责任尚欠薄弱,其法律责任和后果需要在立法中规定或者司法解释。关于《公司法》中规定的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法律后果问题,可参见王利明《谈谈公司的社会责任》(载“中国民商法律网”),作者也认为这一问题比较复杂,需要进一步探讨。
⑤ 宪法直接规定基本权利水平效力有三种立法例。第一种情况是宪法规定基本权利约束所有国家机关,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其中约束司法即有这一含义,即审理普通民事诉讼的法院在处理民事和私法关系中有义务适用基本权利。这一情况可见于德国基本法、南非1996年最终宪法和英国《人权法案1998》。德国基本法第一条(三)规定,下列基本权利直接有法律效力,并约束立法、行政及司法。南非最终宪法section8(1)规定:The Bill of Rights applies to all law,and bind the legislature,the executive,the judiciary and all organs of state。(See Ziyad Motala,Cyril Ramaphosa,Constitutional Law :Analys is and Cas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318,319.)英国《人权法案1998》也作出了类似规定。第二种情况是宪法以一般原则的方式规定其条款适用于私人,例如,我国宪法第5条第4款“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被认为宪法在一般意义上具有约束私法关系的意义,因该章规定在“总纲”中,被认为是基本权利水平效力在一般原则意义上的宪法规范基础。第三种情况是宪法规定特定基本权利条款适用于私人,例如,我国宪法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第36条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可视为特定基本权利条款具有水平效力的规范基础。该条规定:“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又如1919年的《魏玛宪法》第118条规定言论自由之时,规定“如其人使用此权利时,无论何人,亦不得妨害之”,159条规定劳工的结社自由之时,规定“为保护及增进劳工条件及经济条件之结社自由,无论何人及何种职业,均应予以保障”。这些都可视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水平效力。
⑥ 例如,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13、14、15条之后都附有这一规定:“国会有制定适当法律,施行本条规定的权限”。这三条宪法修正案是纠正种族歧视,贯彻平等保护原则的条款。宪法修正案的这一规定,是宪法对国会的立法授权,也是宪法赋予国会的立法义务,因而是一项宪法委托,是宪法要求或者委托国会以普通立法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规范私人关系,贯彻平等保护这一宪法原则。因此,随后国会制定的一系列所谓“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正是国会实施这一宪法义务的结果,也是制定法上的基本权利水平效力的体现。依据这些“民权法案”,私人关系中的种族歧视被国会立法所禁止,宪法平等原则进入私人关系中,成为约束私人在签订契约之时的法律禁止性原则和条款。
⑦ Jacob G.Hornberger,“Economic Liberty and the Consitution”,Part 7,December,2002,http://www.fff.org/freedom/fd0212a.asp。
⑧ “公共机构”和“国家机构”的含义不同。“国家机构”包括按照宪法和组织法设立的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种国家权力的机关;“公共机构”的含义更为广泛,既包括履行各种国家权力和职能的机关和组织,也包括履行一些非国家宪法和法律上的权力,但却属于公共职能的机构和组织。
⑨ 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本性上,城邦先于个人,全体先于部分。“城邦虽然在发生程序上后于个人和家庭,在本性上则先于个人和家庭。就本性而言,全体必然先于部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8、9页。“城邦”就是国家。“国家”的拉丁文就是“城邦”。
⑩ 这里可以再次识别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关于个人生活目的认识上的差异。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先导,认为个人生活的目的是经济自由和一己的幸福;国家主义则认为政治自由和美德才是个人幸福,西塞罗也认为国家的职能是使“公民得到快乐而有道德的生活”。因而,同为“幸福”,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提供了不同的理解。自由主义认为“幸福”纯粹是个人的事情,是私人领域的自治与满足;国家主义认为“幸福”必须在共同体中才能获得,“幸福”是个人美德的实现。对个人品行的假定和要求因此构成了自由政体与共和政体不同的基础。自由政体看重个人私利的满足;共和政体则须建立于公民美德之上并着重于公民美德的实现。作者注。
(11) 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的目的是“最高的善”。国家是社会团体之一,它囊括一切社团;既然每一个社团都以一种善为目的,则国家便是以最高的善为目的。他把国家与社会分开,突出国家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国家是必要的、中立的、为人民谋福利的。参见吴恩裕:《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政治学》,北京城市: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7页。
(12)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生来就具有合群的性情”。“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7页。
(13)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53、254页。
(14) 贺麟:《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一书评述》,《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6页。
(15)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54页。
(16)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和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所论述的个人都是以“公民”身份出现,所有的自由也是指“公民”的自由,也就是政治自由。这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欧陆哲学传统中个人是国家和政治中的存在这一假定,而非英美原子式的个人概念。
(17) 孟德斯鸠认为“自由”就是指“政治自由”。他在《论法的精神》一书界定“自由”的定义时大量列举的“自由”的各种概念几乎都是团体中的自由,涉及个人与团体的关系。他明确指出,在民主国家里,个人自由就是政治自由,并说:“在民主国家里,人民仿佛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真的,然而,政治自由并不是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接下来就是他对于何谓“自由”的经典阐述。[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第154页。
(18) 与欧陆对应,“自由”在英国哲学家那里,则更多是一种经济自由,表现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和财产的获取,其在法律上的表现就是所有权和契约自由。前者通过占有和保护占有物确保这一自由,后者通过财产流转进一步获取财产来确保自由。关于这一点,洛克有明确论述,他的经典命题是“政府的主要目的是保护财产”。他说:“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在于保护他们的财产。”参见[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77页。因而,受自由主义理念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法院在解释宪法修正案“自由”一词时,都把“自由”解释为经济自由,或者契约自由,即占有和获得财产的自由。
(19) [日]美浓部达吉:《公法与私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前言第4页。
(20) 陈新民:《宪法基本权利及第三者效力理论》,《德国公法基础理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01页。
(21) 在该案中,宪法法院承认基本权是个人针对国家的防卫权,但也承认基本法并非一个价值中立的秩序。宪法法院屡屡提及基本权利是要产生客观的价值秩序。而客观的价值秩序,应该在各个法领域内实践。认为基本权利的规定,就是要建立一个客观的价值秩序,以强化基本权利的适用力,对立法、行政及司法都有拘束力,成为他们的行为方针与动因。参见陈新民:《宪法基本权利及第三者效力理论》,《德国公法基础理论》,第314、315页。
(22) See Ziyad Motala,Cyril Ramaphosa,Constitutional Law:Analysis and Cas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318.
(23) 公法与私法融合是很早就开始了的事情。美浓部达吉在撰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公法与私法》一书中不仅坚持公法与私法的分离是相对的,指出私法公法化,而且还标明这一现象在具体法律关系中的存在,将之分为四项予以阐释,即所有权公法上的限制;企业的公共化;契约自由之公法上的限制;公法与私法的结合。并且,针对国家权力对经济生活调整这一维度的私法公法化,他还预示了其发展趋势,说道:“这种意义上的私法公法化,今日尚不十分显著。盖犹有萌蘖之秋,势将徐徐伸长于今后。”参见[日]美浓部达吉:《公法与私法》,第234—251页。
(24) 目前,我国学界对公司社会责任中的“社会责任”还停留在遵守法律、法令、道德和公共秩序这一狭隘认识上,特别体现为作为“公司社会责任”规范基础的《公司法》第5条规定的内容上。自然,按照法律理论,作为《公司法》原则的这一规定属于“一般条款”,其内涵延展有待解释,特别是司法解释。就是在国际层面,何谓“公司社会责任”向来也是莫衷一是。美国学者认为公司社会责任包含三层含义:即遵守法令的责任;实践公司之伦理的责任;自行裁量的责任。参见刘连煜:《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4页。但从国际组织目前的做法和实践来看,美国学者的这一认识也有过于狭窄之嫌,它没有注意到人权文化的兴起及其对“社会责任”中“社会”一词内涵的扩充,因而“公司社会责任”是一个发展的法律概念。
(25)(26)(28) 参见艾伦·米勒:《英国1998年人权法案》,载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法制与管理》2002年第2期。
(27) 关于我国《公司法》规定公司社会责任的意义,可参见王利明:《谈谈公司的社会责任》,载“中国民商法律网”。
(29) 关于基本权利作为“客观价值秩序”的脉络、法理依据及相应的宪法理论后果,可参见郑贤君:《作为客观价值秩序的基本权:从德国法看基本权的保障义务》,《法律科学》2006年第2期。
(30) 通过分析德国法上将基本权利视为“客观价值秩序”的法理可以看出,这一概念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将一国法律体系和法律秩序视为宪法统领下的秩序亦即宪法秩序来看待的。这无疑是宪法作为“母法”,普通法律作为“子法”的认识视角。普通法律作为子法必须贯彻和遵循“母法”确立的价值秩序。在此,依然有必要重新思考传统宪法学理论中关于宪法与普通法律之“母法”与“子法”关系的认定,而不能轻易或者断然否定二者关系的这一形象比喻。该认识提供了对宪法和普通法律关系另外一种角度的思考,虽带有较强的国家主义特征,但某种程度上依然不失为一种较为确当的关系。近年来,学界对这一关系的定位给予较大程度的否定,多是出于从宪法制约普通法律的角度来思考的。但矫枉过正,且两大法系对宪法与普通法律关系的不同定位、理解和解释本有更为复杂的文化背景和政治哲学作为支撑,断然否定两者的这一关系恐忽略了不同法律文化和传统之下对一国不同法律之间关系的复杂认识,无助于增进对法律现象的立体与全面认识。至于我国,因深受欧陆制定法传统的影响,国家主义实际已成为法律文化不可否定的背景要素,故宪法与普通法律的母法与子法关系的认识有其理论基础和现实合理性,也是可以予以解读我国法律现实的一个恰当法律命题。
(31) 参见吴庚:《宪法的解释与适用》,台北:三民书局,2004年,第113页。
(32) 除了宪法平等原则在私法关系中的贯彻要求比较多,客观上开发了司法上的基本权利水平效力和州政府行为理论之外,常见的宪法价值及于私法关系中的争议还有人的尊严包括人格权、名誉权、生命权、言论自由等。从法院的判例来看,利用水平效力和州政府行为理论,基本权正通过法院的努力逐案适用于私法关系中,其前提是缺乏普通立法基础。这也说明,在缺乏普通立法时,不同地区的法官通过适用这两个理论,在扩大私法领域中的人权保护方面还有很多作为。并且,由于各国早期私人关系中的歧视现象,包括种族歧视和男女平等问题比较严重和普遍,法院在此方面深觉责任重大,不得已利用水平效力理论实施基本权利,其后的发展是在个案中逐步扩大其他基本权利条款于私法关系中的适用。
(33) 从德国水平效力和美国州政府行为理论的实践发展来看,两者都只局限在一定空间里,而没有走太远。德国宪法法院在1958年的“路特”案中首次正当了基本权利水平效力的法理之后,在其后的一系列涉及私法关系中的言论自由与财产权保障冲突的案件中,对水平效力都只字未提。例如,其后的“张贴选举海报案”,“史密特案”、“旧物品收集者案”和“杂志案”、“索拉雅”都涉及这类问题,宪法法院却并未用基本权利水平效力理论支持裁决,而是刑法等法律的直接适用。美国也如此,从法院适用州政府行为理论的实践来看,总的趋势是缩小适用范围的。这说明,两种理论在两种不同的违宪审查体制中都没有走得太远,并且也不会走得太远。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宪法固然可以作为一个“客观价值秩序”,但其本质属性和主要功能依然是防禁国家;另一方面,不能忽视立法机关的普通立法,如果有普通立法可以依循,法院不必或者无须求助于解释宪法基本权利条款,只要在私人纠纷中直接适用普通法律即可。这也暴露出一个问题,即在很大程度上,基本权司法上的水平效力是由立法者的立法不足而引起的。如果基本权作为“客观价值秩序”须体现在法律秩序中,则这一价值秩序完全可以交由立法者来完成,不必假手法院。这也意味着在实现宪法价值这一问题上,立法者的立法作为义务因此加重。
(34) Janet L.hiebert,Parliament and the Human Rights Act:Can the JCHR Help Facilitate a Culture of Right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Vol.1,2006,pp.19,20.
(35) See Janet L.hiebert,Parliament and the Human Rights Act:Can the JCHR Help Facilitate a Culture of Right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titutional Law,Vol.1,2006,pp.19,20.
标签:英国法律论文; 宪法的基本原则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英国政治论文; 宪法监督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法律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