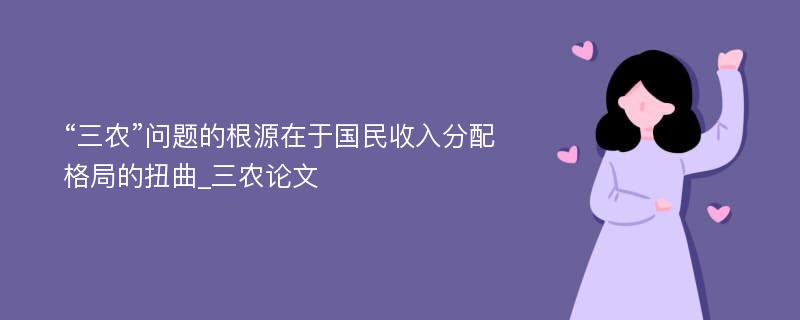
“三农”问题根在扭曲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农论文,收入分配论文,格局论文,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至今,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几乎没有太大变化。城乡资源配置存在着诸多弊端,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重视往往还停留在口头上和文件中。“三农”问题的要害,是政策的城市倾向和国有工业倾向,而这种倾向在农村财政政策和农村金融政策上都得到了反映:
财政支农政策仍存在问题
农业的弱质性和它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客观上要求国家财政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力度,支持那些风险大、投资效益低、对农业生产起着保护、开发作用或有示范效益的项目(如大中型农业基础设施、农业科研和推广、农业环境保护等),以弥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缺陷。而财政支农支出和农业基本建设投资的变动趋向,则表明我国的财政支农政策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90年代以来财政支农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1991-1997年分别为10.3%、10.0%、9.5%、9.2%、8.4%、8.8%和8.3%。1998年提高到10.4%,但这源于国家发行债券的因素。当年,国家发行1000亿元债券,用于与农业有关的资金350亿元,主要用于长江中下游、松花江、嫩江、黄河的堤防工程,蓄洪区建设,移民建镇和水利枢纽工程等,直接用于农业的只有20亿元。1999年国家增发了600亿元国债,但直接用于农业的为零。
农业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远低于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前者仅仅是后者的1/2至1/3,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相称。1993年发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规定,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但是,实际执行情况出入很大。1993年以来,除了1994年和1996年,其他年份国家财政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均低于其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
同时,分析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应与农业税收政策联系起来。我们看到,在财政支农份额逐年降低的情况下,国家财政来自农业的税收收入却大幅度增长。特别是实施分税制改革后,由于农业税、农林特产税被划归地方税种,激发了地方政府在这些方面加强税收征管工作的积极性,从而造成农业各税收入的快速增长。在分税制改革后最初的3年间,国家财政支农支出仅增加了68%,而农牧业税收增加了近2倍,比农业产出增长幅度高出近1倍。1993年全国农业各种税为125.74亿元,1998年增加到398.8亿元,平均每年净增54.6亿元。如果加上地方税农业附加等因素,广义农业税的实际征收税率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低,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支持要打不少折扣。
财政支农资金中,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份额90年代明显低于80年代,在20.2%~23.8%间变动。财政支持的农业研究项目资金占财政农业支出的比重持续下降,80年代前期,在4.5%以上,最高达5.2%,80年代后期在3.9%以上,最高为4.3%;进入90年代后,最高为3.4%,低于80年代的最低水平。
分税制对乡镇财政影响最大
分税制后,困难的是县和乡(镇)这两级财政。由于有限的财力被中央相对集中,省级也采取了诸如通过与地方其他各级分税来集中部分既得财力、调整“两税”增量的返还比例或部分截留中央的两税返还收入(有的省不返还给地市和县)等措施,使得中央分税改革的部分意图不能得到有效的贯彻,从而加剧了省以下地方财政的困难。同理,地市级也可以采用同样的办法,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层层挤压的现象只能愈演愈烈,使得乡镇成为最终的利益损失者。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之间的收支范围和权限,是靠相互交涉而决定的,而且不断改变。乡镇政府是最基层的政权组织,所以在各级地方政府的交易中必然处于最为不利的谈判地位。这样,各级政府如有条件则尽可能地上收财权,下放事权,即尽可能多地从下级财政抽取资金,将那些收入多、增长潜力大的税种收入,全部或高比例地上收;将那些需要投入多、难度大的事,向基层下放。现行的国家行政体制和干部考核机制也加剧和固化了乡镇一级财政困难的状况。基层干部为免受批评、甚至降职处理,或为提高政绩得到提拔,通常采取借贷、摊派等手段尽量并超额完成税收任务。几年过后,烂摊子交给了下一任。如此循环往复,最终承担恶果的是国家和普通老百姓。
在权、责、利不明确,“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基本态势下,乡镇领导的理性选择,一是膨胀机构、扩充人员,以便与上级的“条条”部门相对应;二是把负担摊到各村或是转嫁到乡镇企业头上;三是举债度过难关。村一级则同样如法炮制,最终负担落到最基层的农民老百姓头上。而乡村两级则负债累累、机构庞杂。固然,确有一些乡村干部用各种方式剥夺农民,肥了自己,苦了老百姓,但农民负担沉重的主要根源还在于财权和事权不对称的体制。乡(镇)财政要负担乡(镇)干部、中小学教员、卫生院医务人员及大量不在编人员的工资、医疗、差旅、福利和日常经费的刚性开支,但较稳定和较好的税源都由地(市)级以上逐个上收,县以下几乎所剩无几,到乡(镇)一级几乎没有什么税源和稳定的收入,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都出现了困难。
资料显示,现在约有50%~60%的乡(镇)入不敷出,经济拮据。据农业部1998年对中西部10个省区的调查,乡村两级负债是普遍的,乡级平均负债400万元,村级平均负债20万元。现在全国1080个县发不出工资来,其中60%是教师的工资。
财权和事权不对称引发基层公共产品供给危机
公共财政困难、负债累累,在连基本工资都不能保障的情况下,许多乡镇政府几乎完全丧失了为本地区农民提供社会公共产品的能力。就拿农村义务教育来说,经费基本上由县、乡、村三级自筹。一般县财政拨款、乡镇的教育费附加、农村教育集资,是农村义务教育的主要资金来源。现在.国家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在税费改革的“试点方案”中,已规定取消向农民征收教育费附加,原由乡统筹费开支的乡村两级九年制义务教育支出,由各级政府通过财政预算安排。取消在村一级进行教育集资,中小学危房改造资金亦由财政预算安排。在这种情况下,维持农村学校的日常支出将主要靠财政预算内拨款。而预算内教育支出的大头是教育事业费的个人部分,主要包括教职工工资、民办教师补助、离退休人员费用等,教育事业费的公用部分支出和改善教育条件的基建支出所占比例很低。结果,许多农村中小学校危房得不到改造,教学设备得不到更新。
农村义务教育的事例说明,如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而强调“量入为出”,只能是在现有扭曲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下的一种治标的权宜之计,有可能会加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危机,最终结果只能是,距我们所追求的使不同地区和从事不同职业的公民和法人单位能够享受水平相近的基础性公共服务的目标越来越远。
信贷政策不利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近年来,在国家资金供应非常充裕的情况下,国家银行对农村信贷总规模和资金投入却呈逐年减少的趋势。在各项贷款总额中,农业和乡镇企业所占的比重偏低,并且9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下降。结果造成农村贷存比例下降,农村信贷资金外流。1994年以来,平均每年金融资源从农村的净流出量高达568.2亿元。由于农民从正规金融机构(国家银行和信用社)很难得到贷款,就不得不依靠民间借贷,承受更高的利息,最终影响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从《中国金融年鉴》各年的数据可看出,农业和乡镇企业从国家银行系统获得贷款额度,最高的年份也没有达到17%,而且从1995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这种状况与农业的基础地位不相称,也与农村各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份额不相适应。在90年代的大多数年份中,农村地区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基本上一直保持半壁江山的地位,但其获取的国家银行系统的金融资源却不到1/7。
在取缔了农村合作基金会之后,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领域可谓“一枝独秀”,但近年来农村信用社的贷存比逐渐降低,存贷差逐渐增大,大量资金流入城市,农民很难从信用社得到贷款,一般只占其总借款额的不足20%。一些农民和企业有很好的项目,产品更新换代也有市场,但就是缺乏资金。这样,越是需要资金者越得不到贷款,越得不到贷款就越阻碍经济发展,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此外,农村信用社的利率远高于国家正现银行的利率,阻碍了农民收入的提高。例如,河南省某村农民1996年8月买了一辆中巴搞客运,通过各种“关系”在5个信用社共贷款3.5万元,全部是月息2.4%,是国家正规银行利率的3.5倍;按季度封息,否则扣违约金。结果,至1999年8月买车的3年间,利息、各种罚款及预先扣除共计2万多元,仅利息就有19568元。
农民和乡村企业从正规金融系统得不到贷款的状况,促进了民间借贷的发展。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金的供需矛盾,但借贷者却不得不付出更高的利息。根据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研究人员2001年的调查,中原某省一个3000人口的村,以放贷为主业的就有10户,平均放贷规模为12~15万元,大约70~80笔贷款,多是1000元~2000元的小额贷款。月息3分,年息36%。此外,村里还有50户小规模的放贷户。
在80年代,大部分非正式贷款没有利息,极少数需要支付利息的借款中,利率通常接近机构贷款者的利率。但在90年代,城乡有别的金融市场严重阻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提高。由于农民收入增长困难,外出打工机会少,农民对资金的需求大而又从正规银行得不到贷款,从而刺激了民间借贷的发展。而农民也很少借高利贷投资于生产,用于购买化肥、农药、机械等生产资料,只是到了生活难以为继时,才不得不向高利贷者借钱以度过难关。
多年来,农民负担问题屡禁不止,“按下葫芦起了瓢”,减轻之后又反弹,像这样反复出现的问题必然有其深层次的、体制上的根源。我们认为,农民负担的问题出在下面,根子在上面,根源即是分税制所反映出的扭曲的国民收入分配体制。税费改革的深刻内涵不是减轻农民负担,而是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