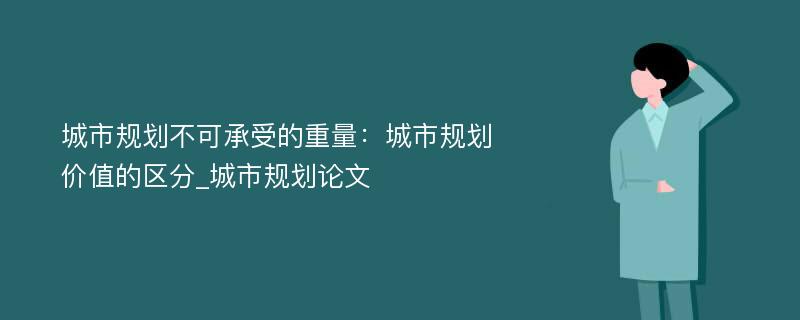
城市规划不能承受之重——城市规划的价值观之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市规划论文,之重论文,不能承受论文,观之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363(2006)01—0011—07
在我国进入到城市快速发展的阶段,发展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第一要务。但对于如何实现发展以及如何面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却产生了不同的认识。在众多的论述中,城市规划被认为应当以效率优先,以发展为要务,以各类建设项目的快速开展为目标。同样,城市规划制度的改革也应当保障发展的效率,促进建设的快速进行,甚至提出,如果不考虑我国城市快速发展的条件,不从效率优先出发,那么城市规划就是失败的,甚至还出现了“城市规划阻碍城市发展”之类的论调①。这不仅是社会各部门(包括政府行政首长)对城市规划的要求,而且也已经成为城市规划部门、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规划师以及城市规划学术研究者自觉的共识,甚至在规划人员的意识中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并自觉地去这样做或以此来要求自己。在对城市规划现状及其未来发展进行研究的时候,有许多相应的问题也困扰着人们。比如,在讨论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问题时,就会提出公众参与会妨碍城市发展的效率,因此不宜提倡等等的说法。总之,无论是城市规划工作者还是政府官员或社会的其他人士,都以是否或能否推进或促进城市的快速发展作为评判城市规划的基本准则。
从这些判断中,可以读解出对城市规划作用的认识,如果与国外相关认识进行对比, 就可以看到这种认识带有非常鲜明的“中国特色”。当然,这并不是要否认在其他国家或者在西方社会就没有对城市规划作用的否定②,事实上,在知识界或实践领域内始终存在着支持或反对城市规划的传统,这两种传统都源远流长,而且在影响力方面在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都几乎旗鼓相当,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意识形态下占据着不同的地位,并在特定的情况下,对城市规划作用的否定甚至占据着社会的主流,如1980年代在英美等国就是如此。但仔细考察同一时期的相关文献或者城市规划的实践(无论是规划方案的编制成果,还是政府文件、规划政策以及规划管理的实际运作),尽管许多文献都提到了比如规划过程和管理的工作效率等方面的内容,但并没有看到强调城市规划要以效率作为评价准则的论述,也很少看到把提高建设和发展的效率作为城市规划终极性的目标。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城市规划学者或规划人员和政府官员对此问题的漠视,还是对城市规划作用的另一种定位?相反,人们却看到了一系列新的控制方式在这一时期的出现,如“增长管理”(growth management)、环境评估等等控制手段的出现和推广。 而在我国广泛运用到房地产市场中的、被翻译成“新城市主义”的“New Urbanism”③ 运动在美国广泛推行,其实质更多是对过去郊区建设方式的一种社会性的抵制和重塑,至少,这种新的规划/设计方式对郊区建设带来了更多的控制,其所倡导的建设方式使得过去那种以Levittown式④ 的快速开发方式更加难以实现。
当把这两种现象放在一起进行对比之后,人们不能不产生出这样的疑问, 中国的城市规划为什么会想方设法地将提高城市建设效率作为城市规划的目标,为什么西方的城市规划并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与此同时,人们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困惑:当将发展效率作为规划所追求的目标之后,人们却发现城市规划的处境越来越困难,城市规划想要顺应发展的潮流、赶上建设的步伐,其结果却是“变化比规划快”,编制完成的法定规划的寿命越来越短。这其中出现的问题究竟源自何处?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1 效率是评判城市规划的准则吗
要认识这样的问题,有必要对现代城市规划本身的特点及其作用做一简略的分析, 也即只有认识了城市规划是干什么的,才有可能来判断什么是衡量城市规划的准则。
城市规划是有关公共事务管理的一个方面,因此,就城市规划与市场运作的关系来说, 规划为市场的运作建立最基本的行为框架,提供有组织的信息作为市场中经济行为者决策的背景和基础,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不受到市场运作消极面的冲击,通过社会资源的配置并提供公共物品以保障社会的有序发展⑤。因此,从根本上说,城市规划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从现代城市规划的发展来看,城市规划的作用并不是要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而是针对于“市场失效”而建立起来的,是为了保障市场能够克服其自发运作过程中所可能带来的、对其自身机制产生破坏性的不利方面,因此,规划是保障市场运行长期有效的一种机制。作为在同一社会中运行的两种社会机制,城市规划与市场运作的出发点肯定不同,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的研究也揭示了这一点。他通过对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规划(planning)进行了全面和整体的分析,认为公共领域的规划与市场理性观念无关,而主要对应于社会理性的概念⑥。也就是说,市场的运行依赖于“市场理性”,而城市规划的原则则更多来自于“社会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两者的完全分离,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生计依赖于私人部门,因此私人部门的固有功能是这种社会所必需的,城市规划作为社会的基本建制之一就理应对此进行支持。但是私人部门在市场理性的鼓动下,对利润生产的无限制追求却有可能会造成对作为社会生活基础的人际互惠联系的严重损害。因此,在弗里德曼看来,公共领域的规划(包括城市规划)就应当“刺激和支持资本的利益,但必须阻止那些利益损害到公共生活的基础”。这不仅仅是城市规划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基本职责,而且也是所有政府公共行为的基本准则。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资本对利益的追求实质是对效率的追求,而且有无数的经济学家都曾经论证过,通过市场竞争和市场行为可以比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获得更高的效率。但城市规划作为政府性行为,其本身的目的显然并不是为了效率。现代城市规划从诞生之日起几乎就是在弥补市场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是在限制市场的作用范围,几乎是在对市场的过度膨胀和对效率的盲目追求进行制约。也正是由此,城市规划在许多拥护者和反对者看来是市场体制的对立者,但这只是表面现象,许多学者已经充分论证了城市规划对国家体制、市场经济体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发展所具有的作用⑦,而现代城市规划之所以能够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产生和不断发展的原因即在此。从某种角度讲,在这些国家中如果没有城市规划这样的社会机制,其资本主义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是否能这样持续有效地长久运行,就很值得怀疑。从这一简短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市场体制的目的是为了效率,而城市规划并不是;城市规划并不反对对效率的追逐,但城市规划本身并不以对发展效率的追求为目的,并且把克服和解决市场追逐效率所带来的问题作为己任。由此出发,福利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已经充分论证了,要发挥这样的作用就需要从社会的公正、正义、公平等方面出发,而这也是弗里德曼所说的“社会理性”的核心内容,只有以这些内容为准则才有可能更好地来解决市场追求效率所带来的问题。
在1980年代初,英国保守主义政府所推进的社会制度改革改变了城市规划的作用, 竭力推进以市场和开发为导向的规划方法来替代之前以规划(plan)为导向的方法,其结果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市场的发展,但随着这种制度进一步的全面运作和长期积累,很明显地强化了市场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并带来了更为深刻的结构性问题,由此而迫使大量的市场机构(如房地产商协会等)要求政府实施战略性的市场管理(strategic market management)⑧。 由此也可以看到,城市规划如果仅仅以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效率为指针,或者追随市场的需要以促进城市的快速建设为目的,就必然会遭致其本身职能的缺失,而这种缺失一旦发生作用,市场的有效运行就会遭到损害,市场运行的主体就会作出反应,也就是要么否定这种形式的规划的存在,要么建立更有效的并不以效率为准则的规划控制机制。仔细想想其中的道理也是非常的简单,既然市场已经有了很好的追求效率的准则与机制,并不需要城市规划也去做同样的事,别人的事情让别人去做,如果不能做好自己的事却还要去做别人的事,而且肯定还是做不好别人的事或者做得不如别人,那么,还会有你存在的空间吗?正所谓,如果城市规划能做任何事,那么就什么事也做不成了( If planning is everything,maybe it's nothing)⑨。
从现代城市规划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形成并不断得到发展的历史事实可以知道, 城市规划作用的发挥绝不是某些人(规划师或政府官员)的一厢情愿,而是市场机制本身运作过程中的自愿选择,是市场本身发展的需要⑩。而市场对城市规划的需要也并不是要其以效率为准则,而是在市场追求效率的同时通过城市规划来实现对社会利益的调配,避免出现如弗里德曼所说的由于市场对效率的过度追求而导致对社会发展的公共基础的冲击。这里以两个例子来说明城市规划是如何发挥其在市场经济运作中的作用的(11)。这两个例子均发生在1980年代,当时英、美两国的主导性意识形态是强化市场的作用、放松管制,以达到全面促进国家和城市经济发展的目的。但即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城市规划对市场运作的影响力仍然非常强大,而且确实通过对社会公正、公平准则的运用而对市场经济的运行发生作用。第一个例子发生在伦敦,在Spaital Fields Market再开发区地内,根据规划部门与开发商进行的规划协商, 作为开发商的国际财团同意捐出约5hm[2]土地给当地社区,以获得邻里团体在开发过程中的合作。社区还进一步提出要求提供4千万英镑作为社区发展使用,127套住房和就业培训计划(jobtraining scheme), 最后得到了国际财团的同意并付诸实施。在英国的社会建制下,通过规划过程进行协商和获得规划收益(planning gain)是城市规划过程中进行利益调配的重要手段。之所以要采取这样的手段是由于在再开发项目中,社会利益会发生极大的转变,一方面,这些改建后的项目实现的是以办公楼为基础的就业,其所带来的可能结果是导致该地区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大幅度下降,使原来在该地区就业的广大非熟练工人发生就业困难。另一方面,在进行了这样的改造后,该地区的房地产价格会迅猛上涨,迫使该地区的居民向外迁移,或增加了他们的生活成本,破坏了社区结构,该地区的小型商业等也会承受经济上的压力等等。总之,在此改造后,作为开发者的国际财团将获得非常巨大的利益,而居住在此地的居民及其社区将要承受增长了的成本,以及集体福利条件的大幅度下降。因此,为了维护社会公平,使获得利益者资助遭受损失者,这就需要在规划实施的过程中通过一系列手段的运用,对开发活动及其可能产生的利益不均进行必要的调配(这种调配的思想基础和基本手段均源自于福利经济学的相关准则),并且将此作为这些再开发项目开展的必要条件,城市规划在此过程中充当的是社会利益调节的作用。第二个例子发生在美国西部城市旧金山,该城市在1980年代初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每年将办公楼的开发面积限制在10万m[2],这项措施尽管在最初遭到了政府官员和商业团体的强烈反对,但经过广泛的讨论,最后由城市议会批准后执行。在此期间,旧金山地区正处于城市结构调整、经济快速发展和大规模建设时期,之所以要采取这样的措施是考虑到办公楼的大量建设会引起办公楼的过度供应,导致办公楼市场的租金大幅度下降,这种下降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极为不利的破坏作用,甚至导致市场的停滞。同时,如果不对大规模的办公楼建设进行抑制,就会导致现有办公楼租金的大幅度下降,这对先前已经建成或正在建设办公楼的投资者和业主来说也是不公平的,是剥夺了他们赢利的权利。而作为这项对新建设进行控制的结果,这个城市办公楼的空置率从1986年的18%降至1991年的12%,而1980年代末正是英美等国房地产业普遍出现明显衰退的时期,纽约、伦敦等城市的房地产价格暴跌,进入到又一个不景气时期,而在旧金山不仅办公楼的空置率降低而且其价格还略有提升。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规划的控制具有巨大的潜力来繁荣房地产业,并避免城市整体经济受到冲击。应该看到,在撒切尔夫人主政英国和里根总统主政美国的1980年代,政府最重要的发展战略就是刺激商业性房地产的发展,希望通过放松管制和提供补助等方式来刺激开发商提供高质量的、便宜的使用空间,并且以此来获得更多的税收以挽救许多城市在1970年代出现的财政危机。因此,在相当程度上,城市政府以企业家管理的方式,以商业利益为主导,并将城市房地产的发展作为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但即使在全面放松管制的情况下,这两个城市的案例却非常清楚地告诉人们,城市规划仍然是政府宏观调控社会经济发展和利益分配的重要手段,这也是弗里德曼所说的“社会理性”的含义,并且正是通过这种手段使整个国家以及各个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保持稳定和持续。
2 城市规划要解决什么问题
由以上的简短讨论和实例可以看到, 城市规划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并不在于加快发展的速度或者对发展速度的鼓动,更不是以是否有利于具体建设项目的开展作为评价的准则,而是在于发展的公平和公正方面。从这样的角度对现代城市规划发展的解读可以看到,城市规划从来就不是实现城市发展效率的工具。城市规划可以促使城市发展得更好,但并不一定就是要使城市建设项目开发得更快。当然,从长远来说,发展得更好就意味着效率,但这种效率并不是短时期内可以看到的,尤其不是对单个项目建设开展的快慢来评判的。从根本上说,城市规划所涉及的是社会资源的配置问题,而对于资源配置来说,在社会整体的层面上,其终极准则是公平和公正,而不是效率,或者说效率只是第二层面上的准则。也就是在配置资源时首先应当考虑的是公正和公平问题,然后才是效率问题,而不应该仅仅只根据谁能更有效率地使用资源来进行配置。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为了更有效地使用好资源,就有必要高效率地使用资源,因此也就会让能够高效率使用资源的人更多地使用资源,但在作出这样的配置时就需要对其他未能使用的人作出补偿。作出这种补偿的考虑显然不是从效率本身出发的,这从上面所举的伦敦的例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安排不仅需要有较长时间的讨价还价,而且还要从开发者手中拨出大量的资源,从而使得开发者本身的效率有可能大大降低。如果以效率来进行评价的话,整个地区或整个项目的发展效率也就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现在,国内有许多学者经常引用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F.A.Hayek)的观点来论述市场机制对发展的作用,其言下之意就是城市规划的制度安排对于谋求发展来说是并不必要的,或者是无效的。确实,哈耶克严密地论证了市场经济要比计划经济更有效率,而且计划经济有走向极权的危险,但在他的文献和论述中也并不绝对地反对城市规划,也并没有把城市规划等同于计划经济来看待,他所反对的是不顾市场机制的运作或完全取消了市场机制的城市规划。在他思想体系的集大成者《自由秩序原理》(12) 一书中,哈耶克专门列出了一章来讨论“住房与城镇规划”问题。他认识到,“从许多方面来看,城市生活的紧密纷繁,使得原有的种种构成简单划分地产权之基础的假说归于无效了。在城市生活的情况下,那种认为地产所有者不管如何处理他的地产都只会影响他自己而不会影响其他人的观点,只能在极为有限的程度上被认为是正确的。经济学家所谓的‘相邻效应’,即一人因对自己地产的处理或使用而对他人的地产所造成的种种影响,在此具有了重要意义。城市中几乎任何一块地产的用途,事实上都将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此块地产所有者的近邻的所作所为,而且也将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公共的服务——如果没有此种公共的服务,则分立的土地所有者就几乎不可能有效地使用这块土地”(下册p.115~116)。在这种以外部性效应占据主导和公共物品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经济现象中,“私有财产权或契约自由的一般原则,并不能够为城市生活所导致的种种复杂问题提供直截了当的答案”(下册,p.116)。因此,也就需要有其他的手段来作出回答,而城市规划就是这样的手段之一。在直接针对城市规划是否需要的问题上,哈耶克直截了当地说:“……这里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人们是否应当赞成城镇规划,而在于所采纳的措施是补充和有助于市场还是废止了市场机制并以中央指令来替代它”。由此可见哈耶克的基本认识,他认为核心问题原来就不在于是否需要城市规划,对是否需要城市规划的问题并不是需要争论的问题,因此可以判断他认为针对城市中普遍存在的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的状况,城市规划肯定是需要的,之所以需要城市规划则是由于可以使市场经济运行得更为有效。但这种城市规划应当是有一定限度的,这是哈耶克所认为的关键性问题,也就是城市规划应当是补充市场,并且是有助于市场的运行的,而不是用城市规划来替代市场的作用。这就必然要求城市规划要从市场的盲点中去寻找到自己的立足点,而不是依循市场经济的准则。与此相关联的是,哈维(David Harvey)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城市规划的目的与作用也进行了论证,尽管他的理论出发点和基本价值观与哈耶克是完全相反的,但其所得出的结论也可以说与哈耶克的思想如出一脉。他认为,城市规划的任务“……不仅是维护这些系统,而且提供这些使用价值在空间上的协调,并创造新的综合使用价值”,从而保证了资本主义制度长久而有效的运作。因此,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通过社会机制对土地使用进行全面控制,其目的在于:“①处理将土地作为商品而产生的外部性问题;②创造住房和其他适宜的环境,满足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③提供由资本作为生产方式而使用的桥梁、港口、街道和公共交通系统的建设和维护;④保证这些基础设施有效运行的空间协调”(13)。
正如弗里德曼所指出的那样,城市规划确实能够促进市场经济本身的发展, 但这种促进的作用并不是通过对效率的追求而达到的,恰恰相反,城市规划是在对“社会理性”的运用过程中才能起到这样的作用。由此出发,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运行和城市规划应当各司其职,发挥各自的作用,而它们都是共同地维护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因此,市场的事情应当让市场去做,城市规划应当做自己应当做的事情,而不应当去抢市场能做的事情尤其不应当去做市场能做好的事情。市场和城市规划在社会的发展中各有各的事情要做,缺少任何一方面都不利于社会整体的发展。
3 为什么人们要城市规划解决发展的效率问题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无论是从理论研究还是从西方国家的社会实践的角度来看, 城市规划从来都没有以解决发展的效率问题作为其核心。讨论城市规划究竟应该是效率还
是公正(公平)优先,其实是一个伪问题,如果以效率为先,那么还要政府、还要作为政府行为的城市规划干什么?一切都可以交给市场去解决,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市场在这方面要比政府、城市规划做得更好。那么,为什么在中国的城市规划会被赋予这样的要求,并且成为社会对城市规划的基本要求?甚至成为城市规划从业者的自觉追求呢?笔者以为,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首先,城市规划作为政府行为,必然会延续政府的主导意识形态,而政府在相当长时期内都以发展的效率为其核心工作,城市规划也就必然地会以此作为自己的任务;其次,我国城市规划在核心价值观上所存在的误区也是重要原因。当然,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但这两方面显然是最重要的,而且也是城市规划近年来步履维艰的原因所在。
从政府行为来看,我国近20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追求的是效率优先,并以效率优先作为评判一切制度、 政策等等方面的准则。这种选择也同样是由于多种原因造成的,比如,经济后发国家往往都会把关注点集中在对经济发展速度上,并把对发展的谋求集中到一些单一性的指标上,为自己设定赶超的目标,从而确立起其政府动员社会资源的合法性。这也不是我国所特有的现象,而是所有后发国家的共同特征。而一旦确定了这样的目标,所有的评判都建立在能否保证这些指标的尽快实现,在这样的思想下,以效率为准则的资源配置就成为了关键,这也是“GDP 崇拜”形成的思想基础。
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具体行为来看,改革开放后,政府事务之所以出现以效率优先,也可以说是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意识形态思想下计划经济体制的延续,其中也有对过去不重视效率的一种反弹。政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全能之手通过计划机制替代市场运作,而在所谓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发现了市场的高效率性,意图用市场体制改造管理体制,以市场原则主导行政过程。在许多人看来,对效率的追求就是走上了市场化,就可以实现市场机制,当政府掌控着几乎所有的资源或绝大部分资源的时候,为了寻求发展或者更快的发展,对效率的追求就成为其行为绩效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由于在一定的时期内,缺乏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所有的市场运作都需要或必须纳入到政府的系列中才能得到最终的成果,因此,实现效率就被看成为是政府理应承担的职责。在此背景下,至今为止所有的快速发展都可以说是由政府部门计划出来的(如GDP)。而地方政府则从本地的需要出发来促进快速发展,这是导致20年来多次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建设过热的根源所在。在没有任何监督机制的情况下,政府自我假定是代表了社会公众,代表了城市市民的意愿,因此也就可以假定社会效率的提高是城市社会的唯一需要,并以此作为所有政府行为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这样,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政府心安理得地做了市场的事,大量的法律法规、行政规章都是建立在政府追求市场效率的基础上,并美其名曰与市场、与国际接轨,政府把自己看成是市场的主体,约束和规范的是真正的市场主体及其行为。而大量的行政法规则走向了更为极端的状况,现代行政法规的很重要方面是对行政权力的约束,但在我国却是为了保障行政部门更好地推行其权力,消除社会的阻力从而保证行政权力实施的效率。就城市建设而言,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土地管理法,在此过程中,政府行为的最大效率就是可以通过行政权力征收而无需动用市场过程,如农地(集体所有)向国有土地的转变,动拆迁(14) 等等。而对于城市政府来说,一方面期望自身的力量不断扩张(无论是城市的还是政治领导人的),在这样的状况下对城市进行投机式的扩张,尤其是在前景尚不明朗的情况下(也即并不清楚这样的扩张之后究竟由谁来进行填充),抱着筑了好巢就会引来好凤凰的信念;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扩张涉及到众多的不同因素,竭力表现出“强”政府四面出击、全面掌控的态势,不断强化、扩充系统化的组织管理,致使行政力量与市场资本共谋,以行政资源操纵市场运作,掩饰市场供需信号,或者为资本充当打手,创造垄断资本的前提条件。
由此,从政府行为的分析可以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为了鼓动快速的发展,出现了严重的“政府缺位”现象,尽管政府还是存在着的,但它没有做作为政府应该做的事情,做得更多的是别的事情,这些事情也许由其他的机构来做可以做得更好。有些城市发展得快,被人称为“强势政府”,但其所强的并不一定是政府行为,而恰恰是政府做了其他方面的事情。当今社会矛盾在局部领域和局部地区的加剧和外化,其原因就在此。城乡问题,城市中的大量社会问题就是由于将效率放在首位并且不考虑其他的社会要求而导致的,是政府在过去20多年中严重缺位的集中反映,这同样说明,对于公共事务的管理,仅仅依靠效率准则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根据经济学、政治学以及社会学等等的研究成果,在现代社会中,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鼓励社会去追求市场效率,而自己促进公正,并在公正原则下管理市场的运行,避免对效率的追求导致社会的失衡。
在政府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城市规划也做了或者说主要做了并不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并成为了政府追求效率的工具,还美其名曰与市场、与国际接轨。在这期间所有的城市规划(plan)都是为了城市建设而编制的,其核心内容是为建设服务的,并可以为建设而违反或修改已有的法定规划。因此,当规划一旦不能与发展的要求相符时,没有人认真地反思一下,这样的发展是否是城市所需要的,而是首先将矛头转移到城市规划上来,认为是城市规划有问题,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正是由于将城市规划定位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而且城市规划就将城市的快速发展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因此,一旦出现城市建设过热、经济发展过热或耕地被占用过快等问题时,城市规划就再次成为导致这些现象出现的原因(15)。尽管这里有许多社会的因素,但也可以说是城市规划丧失立场之后的自取其辱。就此而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到今天的实际状况可以说是一个明证。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在借鉴了美国区划(zoning)技术方法基础上,意图强化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城市规划作用,从其名称就可以看到规划界的愿望,并经1989年《城市规划法》确立了其地位。但从那时以来的实际发展状况,却已走向了另一方向:首先,地方政府已经把控制性详细规划作为加快土地批租速度和加快建设步伐的有力工具;对于原初想要控制的对象开发商来说,控制性详细规划基本上已经成为谋取超越常规控制、实现自己开发意图的手段;对于城市规划界而言,控制性详细规划要么成为规划编制单位的利润工具,要么成为规划管理部门的摆设。只要对比一下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划之间的关系就可以看到控制性详细规划究竟实现了什么。而为规划界人士所诟病的“开发区热”、“房地产对城市规划的冲击”以及城市中的高强度、高密度的无序开发,无处不透露出控制性详细规划在其中的作为,这些现象本身的产生虽然不能说是控制性详细规划所导致的,但人们几乎无处不能看到其中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影子,这就给了人们一个警醒:为什么控制性详细规划走向了其预设作用的反面了呢?其中就是由于城市规划把对发展效率的谋求作为了首要准则,控制性详细规划成为了追求市场效率的吹鼓手、推进器,在相当长时期内,对容积率提高和改变用地性质的追求被看成是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主要目的,而现在说“城市规划阻碍城市发展”所针对的主要对象也恰恰就是控制性详细规划。
这样的事例当然并不限于控制性详细规划这样一种规划类型,比如,修建性详细规划现在几乎是房地产商的利润工具[16],而且可以想象,最近几年兴起的战略规划也将面临着同样的命运。战略规划的蓬勃兴起正处于各城市城市规划越来越短寿的同时,而地方政府推动城市建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建设行为高热时期。仔细考察这些战略规划,几乎没有一份不是以地域扩张为基调,以满足城市政府所谓的经营城市的愿望的,从某种角度讲,都是以疯狂掠夺土地资源为主要内容。城市总体规划确实存在着诸多问题,但并不能用来说明战略规划兴起的根本原因。由于城市总体规划受到一系列规程、规范的制约,无法实现地方政府超常规发展和谋求地域大规模扩张的需求,因此,尽管战略规划并没有法律效力,但各大城市都愿意花费大量资金和精力去开展这一工作;在不具有法定地位的前提下,战略规划却成为地方政府实现自己意愿的操作工具。在许多规划人员和政府首长的心目中,战略规划的前提就是可以不顾当前(包括当前法定的规范),从长远来看问题(至少是可以超越总体规划的时限),进而使得战略规划所提出的方案在规模上可以远远超越于总体规划所可能提出的,进而达到了尽快做大城市的目的。因此,在城市规划整体遭受全面指责的同时,战略规划却受到了各方的追捧,被认为是指导城市发展的最佳手段。如果从对控制性详细规划发展历程的反思中进行思考的话,这就不能不由人担心起战略规划的未来命运。
4 结语
城市规划的核心问题是城市建设和城市开发的外部性问题,是不同主体间的相互关系,效率不足以来评判这种关系。效率更适合的是对具体行为的评判,也就是在单一因素内部的评判,即当一件事的目标已经确定,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也就是在目标实现的过程中,效率可以作为对此过程中的行为进行评价的依据和准则(对于城市规划而言,所谓提高效率应该集中在提高工作过程的效率,加快规划管理中的审批速度等方面)。而城市规划主要是处理城市发展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果以效率为准则则有可能带来根本性的问题,甚至可能出现效率越高失误越大的结果。以追求效率的方式去解决外部性问题,其结果只会使外部性更加加剧而不能缓解,而且以这种方式来解决外部性的效率越高,那么外部性累积得越快,爆发得也将越猛烈。我国当今诸多社会经济矛盾突出的很重要原因,就在于过去只强调了效率的准则而忽视了其他内容,这是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指导思想提出的重要背景。
城市规划从来都难以承受效率准则的考评。系统方法论企图用技术的手段来解决其中的问题,强化了效率准则, 但最终的失败是由于其“技术决定论”的思维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与其以效率为准则的取向有关。1980年代以后以美国城市为代表的以企业家方式管理城市以促进城市的发展,但可以看到,其基本的手段并不是城市规划,与此同时,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质量,在城市郊区以“发展控制”为代表的发展控制机制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在城市中心则在区划控制的基本通则基础上,更加强化城市设计等的作用,并且把城市设计的内容作为开发控制的重要因素,使建设项目的开展不仅要符合区划法规所设定的基本指标,同时必须为城市空间尤其是公共空间的营造作出贡献。从当今西方城市的发展实践中可以看到,尽管政府通过“公私合作”的方式来促进城市的开发与再开发,但相对于以前的规划控制来说,在许多方面更加强调对社会公正的考虑,并采用多种手段来强化这一准则。1970年代以后的公正规划的兴起以及对普遍范围的公众参与的支持也同样是明证,英国2004年的规划法将公众参与的前置和强调更突出反映了这一点。如果人们不从这样的角度进行认识的话,那么也就有根本无法理解西方城市规划体系及其具体做法的可能,而且也将最终影响到我国城市规划的生存和发展。
注释:
① 通常的情况是这样的:当城市通过各种手段想要引入某个项目,结果发现该项目所需要的土地或者其所要求的开发强度等等与已有的经过法定程序批准的规划不相符时;或者在建设项目的城市规划管理过程中,根据已有的经过法定程序批准的规划不能符合开发者所提出的要求时,对这些项目关注的人,包括政府首长、开发商,甚至规划人员就会对城市规划做出这样的评价。
② 相反,在国内几乎看不到有关于否定城市规划作用的严肃讨论,但是在大家有口无心的对城市规划作用进行全面肯定的情况下,实际上却是对城市规划概念及其作用的彻底的偷梁换柱。这正是下文的讨论所要揭示的内容。
③ 将“New Urbanism”一词翻译成“新城市主义”在词义上有许多是无法贯通的。其实,在1980年代的美国之所以广泛地使用“New Urbanism”这个词,主要是所针对勒·柯布西埃于1922年出版的一本法文书《L' Urbanisme》(该书在1929年翻译成英文书名改为《明日城市及其规划》(The City of Tomorrow and Its Planning),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明日城市”的设想)。从词义上讲,“Urbanism”源自于法文“Urbanisme”, 在一般的法汉词典中都翻译为城市规划。在英语中,根据《Longman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Urbanism”的含义包括两部分:一是城市居民独特的生活方式,二是对城市社会的特征和物质需求进行的研究。与此相关的“Urbanist”《Longman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直接以城市规划师(town planner)来释义。因此,“Urbanism”不应从“主义”的含义去理解。“New Urbanism”的倡导者之所以将自己称为“新的”,主要的原因在于将以勒·柯布西埃为代表的“Urbanism”看成是现代城市规划,为了将自己基于传统或后现代的规划理念与之区别而称为“New Urbanism”。从1980年代以后在英语文献中广泛使用该词的用法来看,所有的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都被包括在这样的名称下,可参见Nan Ellin于1996年出版的《Postmodern Urbanism》和Han Meyer于1999年出版的《City and Port:Urban Planning as a Cultural Venture in London,Barcelona,New York,and Rotterdam:Changing Relations Between Public Urban Space and Large-Scale Infrastructure》等文献中的有关“urbanism”的用法。Han Meyer在书中还给出了后现代理论家之所以更喜欢使用“urbanism”而不是“urban planning”或“urban design”的理由,是希望将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将它们分离,甚至提出应当以城市设计的思想和方法来进行城市规划,以城市规划的思想和方法来进行城市设计。因此,笔者以为,将“New Urbanism”一词翻译成“新城市规划/设计”可能更为适宜。
④ Levittowns最早是Levitt and Sons公司于1947~1951年间在纽约附近的新泽西建造的郊区居住区。在该居住区的建设中,采用预制装配式和流水线式的建造方式,结果就能以低廉的价格、在短时间内造起了大批几乎相同的房屋,从而创立了新的郊区居住区的建设模式。这一模式在美国郊迁化快速发展时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⑤ 有关城市规划作用的详细论证请参阅笔者即将出版的《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中的相关论述。
⑥ J.Friedmann,1987,Planning in the Public Domain:From Knowledge to Act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⑦ 如D.Harvey的《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1985,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M.Dear & A.Scott的《Urbanization and Planning in Capitalist Society》(1981,Methuen)。而Leonie Sandercock等则从更为多元文化的角度揭示了同样结论,见L.Sandercock编辑出版的《Making the Invisible Visible:Insurgent Planning Histories》(1998,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⑧ 见Patsy Healey,1993,The Reorganisation of State and Market in Planning,in R.Paddison,B.Lever & J.Money (eds.),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in Urban Studies I,London:Jessica Kingsley Publishers
⑨ A.Wildavsky,1973,If Planning is Everything,Maybe It's Nothing,Policy Sciences
⑩ 有关城市规划为什么以及如何从市场机制本身的运行要求中发展起来的论证,参见笔者即将出版的《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中的相关论述。也可参阅Mike E.Miles,Gayle Berens和Marc A.Weiss所著的《房地产开发:原理与程序》(第三版,刘洪玉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和Denise Dipasquale和William Wheaton所著的《城市经济学与房地产市场》(龙奋杰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等。
(11) 此两个例子均见S.S.Fainstein,1994,The City Builders:Property,Politics,and Planning in London and New York,Blackwell
(12) Friedrich A.von Hayek,1960,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13) D.Harvey,1985,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4) 1990年代以来在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实现的动拆迁,大多数都是由政府来组织实行的,即使是完全的商业性的开发。而在此过程以及对社会的宣传中,几乎都强调了城市的公共利益,从而保证了动拆迁的效率。对这一过程的深入研究完全可以看到在我国绝大多数城市中现代政府职能的缺失。
(15) 这里的悖论是非常值得深思的,一方面城市规划被认为阻碍城市及其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被认为是城市建设过热的原因。这两种完全相悖的说法几乎在同一时期的出现,并且始终贯穿于近2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深刻地说明了对城市规划认识上的偏差。
(16) 从现代城市规划诞生初期就可以看到,城市规划一直得到房地产商的支持,甚至有些规划是他们所倡导的,如1909年的芝加哥规划,而纽约的1916年的区划法规的形成与通过,房地产商在其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但房地产商对城市规划的需要主要是出于维护市场的运作,避免个别的房地产商的投机性行为。当然,这种现象不仅在城市规划形成之初是这样,在后来的发展也同样如此,如,1989年,针对撒切尔政府放松规划管制的政策,英国房地产协会的报告就提出,没有或缺少适宜的规划控制,只能使少数投机者获益,而对整个市场带来不确定性,从而破坏了房地产市场的健康、有序的运行,因此而呼吁政府要加强战略性的宏观管理(详见见Patsy Healey,1993,The Reorganisation of State and Market in Planning)。但在国内,城市规划与房地产商的关系好像已经走向了反面,是为了个别房地产商借用所谓的规划来钻政府控制的空子,而城市规划师在某种程度上是在为虎作伥地来突破上一层次或上一版规划(即使上一层次或上一版规划是其自己编制的)。
收稿日期:200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