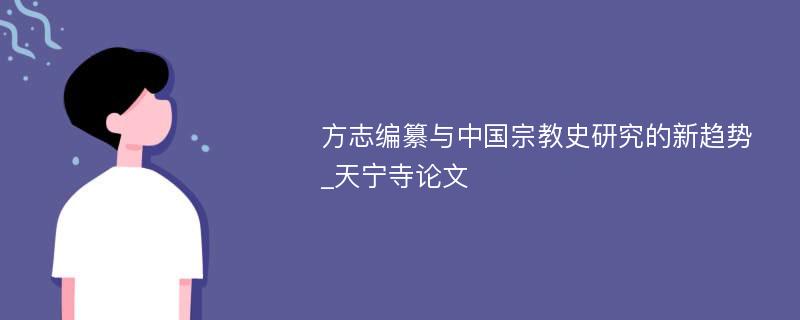
地方志文献汇纂与中国宗教史研究的新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方志论文,中国论文,文献论文,史研究论文,宗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半个多世纪前,美籍华裔学者杨庆堃指出:“对中国宗教及其功能和结构的研究,存在着资料缺乏的问题,这种困难始终是一个障碍,令中国学者对研究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功能角色望而生畏。一个相对尚未被发掘的资料,是大量存在的地方志。”[1](P36)他还特别提到了美国著名学者休中诚(E.R.Hughes)的观点:“做任何研究,从县志……都能发掘出足够多的资料,来写一本有关民间宗祠、民间神坛、道教和佛教的庙宇,以及纪念孔子的孔庙等大部头的书。到目前为止,这些地方志几乎完全被西方学者忽视了。”[2](P9)其后,虽然有少数国内外研究中国宗教史的学者尽力发掘地方志文献中的佛道教史料,但是,总体而言,真正自觉地充分利用地方志佛道教文献的还是很少见,即使是一些地方性的宗教史(包括佛教史和道教史)写作,学者们使用当地的地方志佛道教文献仍存在着明显的不足①,更不用说全国性的宗教史研究了。2013年,经过多年的努力,收录了全国各地(包括港澳台地区)6813种方志佛教和道教文献的《中国地方志佛道教文献汇纂》终于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学界称之为“开辟佛道教研究新天地”,将“会极大地改变我们三十年来处理的宗教资料的构成,当然也会极大地改变我们花费了三十年建构的宗教史的描述”,因而将“会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①。在这里,我想结合个人在主持编纂这套巨制过程中的体会,谈谈地方志文献的开发利用将可能推动国际性的中国佛道教史研究呈现出三大发展趋势,愿就正于方家。 一、以道场为中心的人物、教派和社会相关联的立体史研究走向 过去的中国佛教和道教研究,多着重于人物、思想、教派和重大历史事件的探讨,而很少开展以佛教、道教道场(寺观)为中心的佛教史或道教史的研究。②[3][4][5]事实上,任何人物都只可能活动于某个或某几个道场当中,任何思想都只可能产生和传播于具体的道场之中,任何教派也只可能以某个或某几个道场为中心而扩散到其他道场,任何重大历史事件都只可能发生在某个或某些道场当中,或与相关的道场有关联,而这些道场的兴衰又与同时代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势力之兴衰有着直接的关系。《康熙新会县志》卷之九载:“僧道之有寺观,犹士之有学,工之有肆也。寺以山传,人以寺著,不如是山林寂寞矣。”然而,就已有的佛教各种《大藏经》和“正史”文献来看,除了数量有限的若干重要道场的寺观志和山志之外,绝大多数历史人物、思想、教派和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的道场都没有具体的记载。然而,在全国各地历代所编纂的地方志文献当中,这样的历史记载比比皆是。 地方志中寺观资料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不只是针对一个个孤立的寺院佛教史或宫观道教史的研究,还是针对同一个地区或同一个寺观相关联的不同地区之佛教史或道教史的研究。这一点最集中地体现在历史上一些重要的教派或道派的兴衰、传承和影响的演变当中。以美国著名学者韩明士(Robert Hymes)对宋代道教天心派的兴起及其传播的研究为例,韩氏虽然是以江西华盖山为中心探讨天心派的兴起与传播,但他所涉及的华盖山道教的传播已“跨郡越县”,扩散到华盖山以外的许多地区。如他所说:“(《道藏》中的)天心派文献将所有地点当做可以互换的抽象物”,“它从来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地方教派,也不和某地方维持特殊关系”。源于华盖山的天心派终究从江西的抚州传向南北各地,“从它的老家传向了远方。这是一个扩散性的教派”。而天心派的法师道元妙宗、邓有功、赵子举等也都分别在邓州、洪州、江州、扬州、严州、舒州、开封(东京)等地的道观中呆过并行法。[6](P46-47)因此,如果要了解天心派,仅仅就华盖山的道教史进行研究显然是不够的,不仅要考察抚州的道教史,还要考察相关联的以上诸州的道教史。可是,这也不是单纯地考察各地的道教史所能完成的工作,最重要的是对以上天心派的法师们所到过和所住持过的道观进行考察。这里的许多道观是不可能有专门的史书的,而只可能寻求历史上其所在地方的方志文献。也正因为如此,作者引用了雍正《抚州府志》、民国《南丰县志》、同治《崇仁县志》、光绪《吉安县志》、同治《临川县志》、《太平寰宇记》和《舆地胜纪》等许多地方志文献。 当然,研究天心派的兴起与传播,仅有以上这些志书显然是不够的。事实上,上述提到的抚州、邓州、洪州、江州、扬州、严州、舒州、开封(东京)等地的历史方志已经大量存在,而且也不仅仅局限于清代的一些方志。好在韩明士大作的重心并不在于探讨天心派的传播史问题,而是研究宋以后道教与民间信仰和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关系。即使如此,如果能够更充分地利用地方志文献,那么他在书中的论述肯定会充实和合理得多。只要翻阅一下《中国地方志佛道教文献汇纂》中以上地区所涉及的方志,就不难发现这一点。在这里,我们无须对韩著提出具体的批评,但仍然不可轻视地方志中的寺观文献对于研究地方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如清代乾隆时期安徽《寿州志》卷之十一《寺观》云:“寿州僧舍大小当以百数,不胜志,亦不足志也。然琳宫梵刹,远者数千年,近者亦数百年,盛衰兴废,亦地方消长之一端也。故择其名胜者,著于篇。志寺观。”[7](P216-217) 在中国历史上,仅佛教而言,就有著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之乱。中国的佛寺和道观虽然始于汉代,但是,能够保存超过百年的寺观是非常少见的,更不用说超过千年的了,而历史上的寺观总是屡兴屡废。这当然与中国历代的王朝更替、政权轮换和社会变更有着直接的关系。以寺观为中心的佛教和道教是中国历史上与儒教(家)并列为三教的社会教化和文明表征,在广大的民间社会和士大夫阶层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江苏乾隆年间的《溧水县志》有《永寿寺饭僧田》文,详载永寿寺之建,得益于五十多年前豫章徐公莅政之时,“壮立崇观,雄镇一邑,斋寮香积,无之不备”。然而五十年之后,徐氏离去多年,社会几经沧桑,永寿寺也因此而废。“寺旧有田若干亩,盖众信置以饭僧者,历年既多,为坏教者所鬻,田既没,而寺因之圮矣。”溧邑士绅和民众深感名胜之地,非浮屠法不足以护国佑民,非名僧尊宿不足以兴寺弘法,于是到吴中聘请高僧永泰模禅师卓锡兴教。禅师“比至止于右庑,败屋数楹,风雨不蔽,庭有奥草,厨无宿舂,空规残状,良用喟然。因与弟子,剃除葺塈,不惮辛劳,道力坚宏,有感斯应。于是一方善信,咸识皈依,不待慕求,旧观用复,缁衲高流,闻风云集。师开堂广纳,无向求露处之叹矣”。也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士绅官商和学子为永泰模禅师“阐宗风于此地,道高而行苦,丛林既开,樵苏不给,而邑有义田,徒为奸劣阴据而坐饱焉,甚无谓也”的为法忘躯的精神所感动,特发起捐赠义田以养僧的活动,既可以资助“寺之偏西”的文昌祠“香火之需”,又可以“给衲子焚修之供”。因此,作者感叹:“邑之有浮屠,非第释氏之庄严,实溧邑之望也。寺之盛衰,即邑之盛衰矣。”[8](P304-308) 其实,寺观之兴衰与地方消长相并行的情况在不同时代的许多地方都不难看到。晚清时期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对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的佛寺道观文庙等都造成了历史性的破坏,僧道被杀或被驱赶,寺庙被毁,神像佛像被砸,佛藏道典和儒经被焚,是历史上的空前之举。然而当曾国藩发表《讨粤匪檄》并以保护儒释道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作为旗帜最终打败太平军之后,各地很快就相继恢复和重建传统的儒释道及民间信仰的道场,于是我们今天在方志中不难看到以上各省区的绝大多数寺观,都是在清光绪之后逐渐兴建起来的。因此,寺观的兴建虽然并不必然能够带来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兴盛,但是,从历史上看,一个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带来佛寺道观的复兴。就此而言,佛寺道观的兴衰几乎可以看做是地方社会兴衰的一个晴雨表。因此,以寺观为中心的佛教史和道教史研究,将会使原来以人物、思想为中心的时间史、线性史的研究,扩展为以道场为中心的宗教与社会相关联的立体史研究。 二、以诗文碑刻、图像和舆地(环境)为主体的多维视角的动态史研究走向 真实的宗教史研究需要以多维视角来全方位地展示历史现场,通过各种图像并以生动的文字解说形式将读者带入历史的现场,使读者仿佛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从而将历史从被人为推演的静态研究过渡到历史自身得以呈现的动态研究。这就要求有远超出以往佛教史和道教史研究以文字表达形式为主的历史资料,使文字资料不是孤立的表达,而是与表达历史现场的空间道场(寺观)及其空间方位(环境)(堪舆图或绘图)、表达历史主体(人物)形象的绘图或影像图及其现场解说文字(诗文碑刻)的集合。而这正是地方志文献所展现出来的佛、道教历史的一个显著特点。也正因为如此,地方志的佛道教文献能够使得佛教和道教的历史研究可以趋向于一种多维的动态史和参与史的研究。 江苏省境内有两个著名的天宁禅寺,一个是常州天宁禅寺,一个是扬州天宁禅寺。两者都创始于唐代,历经千余年。前者与扬州的高旻寺、镇江的金山寺和宁波的天童寺并称为近代中国江南四大名刹;后者虽然在近代并不显赫,但在清代前期的影响和地位较之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常州天宁寺只是乾隆皇帝下江南时三次临幸,而后者却早就得到康熙皇帝的三次临幸并题诗题额,乾隆皇帝五次临幸并题诗题额题字。因此,康熙至乾隆年间,也正是扬州天宁寺地位最为显赫、发展最为鼎盛的时期。可是,扬州天宁寺在咸丰时期遭遇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的摧毁之后,虽然也逐渐得到了恢复,但是与得到迅速恢复起来的常州天宁寺相比,命运却大不相同。后者成为近代中国的名刹,民国时期的佛教大居士濮一乘先生甚至专为常州天宁寺编撰了著名的《武进天宁寺志》一书。相比较而言,曾经辉煌的扬州天宁寺却既无寺志,也绝少被人提及,几近泯灭于历史之中。 值得庆幸的是,在明清两朝和民国时期,先后有近十种《扬州府志》、《江都县志》等地方志书都对扬州天宁寺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最为重要的是,这些方志有关扬州天宁寺的记载,不仅有文字材料,还有大量生动的舆地图和寺院绘图材料,从而将可能泯灭于历史之中的扬州天宁寺几近复活起来。 据清代学者考证,史载扬州天宁寺于“唐则天证圣元年建,名证圣寺,世传柳毅舍宅为寺,寺有柳长者像,僖宗广明二年改正胜寺,宋大中祥符五年改兴教院,政和三年从蔡卞之请,以院为天宁禅寺。绍兴十三年诏令天下州军,并立报恩光孝寺以奉徽宗皇帝香火,而寺额得并改,云岁久倾圮,郑兴裔、赵师睪、贾似道先后修葺之。又传寺在东晋时为谢太傅安别墅,义熙十四年有梵僧佛驮跋陀罗尊者译华严经于此,时右卫将军褚叔度特往建业请于谢司空琰求太傅别墅建寺焉,号广陵福地,亦名谢司空寺。《华严经序》云,尊者于寺别造履净华严堂译经,改寺为兴严寺”。[9](P277-279)但是,扬州天宁寺真正进入全盛时期是康熙朝之后。康熙皇帝于康熙四十二年、四十四年、四十六年三次巡游天宁寺,都留下了诗作。[10](P146-151)康熙四十二年有诗云:“空蒙为洗竹,风过惜残梅,鸟语当阶树,云行动早雷,晨钟接豹尾,僧舍踏芒埃,更觉清心赏,尘襟笑口开。”康熙四十四年有诗云:“十里清溪曲,丛篁入望深,暖催梅信早,水落草痕侵,俗有鱼为业,园饶笋作林,民风爱淳朴,不厌一登临。”从这些诗中我们不难想象当时天宁寺的清幽怡人和扬州的社会繁盛之风貌。[11](P147-148) 康熙四十六年,康熙皇帝有《述怀近体诗并序》,《序》云:“朕每至南方览景物雅趣,川泽秀丽者,靡不赏玩移时也。虽身居九五,乐佳山水之情,与众何异?但不至旷日持久,有累居民耳。所以一日即过者,亦恐后人错借口实而不知其所以然也。”并有《天宁寺》诗云:“天宁门外天宁寺,最古花宫冠广陵,指月禅杖阅百代,庋经阿阁耸三层,亲民乍为思苏轼,传法何须问慧能。我自多忧非独乐,岂能香界镇吟凭。”他另有《驻跸天宁寺行宫叠旧作韵》:“曲径相通向右边,了知行馆最清便。旌又驻仲春月,香扆何殊壬午年。嘉荫仍看乔柏峙,幽芳已有早梅妍。大观堂里披书坐,无逸当前意悚然。”[12](P162-177)当时有儒生蒋易作《天宁寺树下作同景州东湖》诗云:“招提何代树,古月见初生,独向霜钟老,从教陆海更,烟开才露影,风定亦闻声,莫问隋堤柳,繁华昔系情。”[13](P147)这些都反映出从皇帝到儒生莅临扬州天宁寺的亲身感受。 到了雍正时期,扬州的天宁寺在地理上并没有变化,但我们从时人彭桂所写的《再游天宁寺诗》中不难感受到此时的天宁寺与康熙时期的景象已经大不一样了:“乍逢尘市路,更得到精庐。危殿前嚣甚,回廊后杳如。钟声迂自绕,竹径暗犹疏。回日看楼敞,闲僧觉院虚。经床人尽闭,斋食鸟还余。凋敝随民俗,仁慈急豕鱼。刹竿高易竖,朝寝废多墟。胜地心偏恋,良辰步且徐。曾传柳毅宅,犹说谢安居。翻为探幽尽,前游怅未□。”雍正执政时期没有一次南巡,江南的寺院有些已经衰落,如常州大刹天宁寺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时,祥符寺主纪荫应邀执拂,在檀越曹廷俊等人的帮助下大有缔造,可惜后来“无何,纪荫退席,寺又不振”,直到“乾隆九年甲子(1744),住持际圆接席”,才又有所恢复。[14](P10-13)当然,与常州天宁寺不同,扬州的天宁寺似乎没有那么不幸,但毕竟江南百姓的生活似乎不如康熙时期那么好,民众的生活状况与寺院的兴衰相伴随。 乾隆时期是清代社会发展的又一个盛世,江都县志所载天宁寺的图景又有了一番繁盛景象[15](P149),此时距康熙最后一次巡游江南(1707年)已经过去了三十六年,距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1751年)还有八年。乾隆南巡,对扬州天宁寺倍加热爱,“圣祖仁皇帝屡赐书墨宝,乾隆十六年、二十二年、二十七年、三十年、四十五年,皇上五次临幸,御制联额诗章书籍法帖图画经文,颁赐稠叠。其右为皇上行宫二十七年三月,御题大观堂额并书对联诗章。三十年御题省方设教额“商鼎周彝自典重,槛葩苑树相芬芳”一联,又五言古诗一首,五言律诗二首,七言绝句四首。四十五年御题静吟轩额“成阴乔木天然爽,过雨闲花自在香”和“窗虚会爽籁,座静接朝岚”二联,又御制五七言诗七首。四十四年恭见御书楼,内供皇上颁到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全部,御题文汇阁及东壁流辉额。四十五年御题五七言律诗各一首。四十七年颁到端石兰亭全卷。”[16](P33-34)“天宁寺行宫”五个字说明扬州天宁寺已经成为名正言顺的圣祖仁皇帝的皇家寺院,建筑规整,内有皇帝的御书楼,藏有皇上钦定的《古今图书集成》全套,并多有御题诗、额、联、字和御颁(赐)法帖图画经文等。天宁寺不再是一般的佛教信众可以自由出入的道场,而是乾隆皇帝先后五次南巡时专享的游玩、办工和休憩之所。 上述只是利用了清代康熙至乾隆年间的几种扬州和江都的方志,就将扬州天宁寺百年的变迁史作了一个简略的展示,我们仿佛在看一部扬州天宁寺的3D历史影片,欣赏着百年扬州佛教的变化,也体味着百年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变迁。《中国地方志佛道教文献汇纂》正是展现历史上各地方佛道教与地方社会生活变迁的魅力:从汉代至1949年,多种甚至十多种(有的多达二十余种)同一个行政区域的不同时代的全国一统志、省通志、州府志、县志和乡镇志中有关佛教和道教的寺观、人物、诗文碑刻文字及各种图式在同一个文献读本中同时展现出来。作为佛教和道教之主体的道场和人物不再是一个个孤立地、静止地、单向度地呈现给历史的解读者。同一道场、人物和不同时代之间、同一时代的不同道场和人物之间,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动态的和多向度的有机整体。因此,立足于地方志文献的佛教和道教的历史文化研究,必将会突破以往主要依赖于教内《大藏经》、《道藏》及“正史”文献基础之上的分散的、静态和单向度的研究模式,而趋向于多维的动态史、参与史的研究模式。 三、以民众现实需要及其生活方式为中心的社会史解释模式走向 中国的历史文化通常被看做是儒、释、道三教交织的形态。因此,无论是儒教史、佛教史或道教史的研究,都避免不了对三教交涉与交融史的探究。不过,过去国内外的中国三教关系史研究,多着重于从思想史(如三教论争)和政治史(如“三武一宗”之乱)的角度去发掘,结果三教的历史关系给人们的一个印象似乎要么只是思想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与融合,要么只是充当了政治斗争和争夺现实利益的工具。事实上,我们如果稍微翻阅一下地方志当中的佛教和道教文献,就会完全改变以上长期以来对待儒、释、道三教关系的认识模式。历史上的儒、释、道三教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意识形态上的冲突,也非一定充当政治斗争或各种现实利益之争夺的文化工具。 在历史上,全国各地有许多三教堂或三教寺,这些三教堂或三教寺或以其他寺名或观名而实崇奉着三教圣人,这些道场多为佛教僧人或道教的道士所住持,虽然他们从事的主要是佛教或道教的活动,但是,他们对三教的圣人孔子、佛陀和老子都一致的崇拜。如明代万历年间,山东济宁的荷河地区重修三教堂,是由道士于清明暨弟子李一香在当地八十余位三教信众的帮助之下结社以重建起来的。当地的贡生范谦亭在《重修菏河三教堂记》中特别提到:“三教之不谋久矣,卫道者争排二家,至不相容。今跻之一堂,礼欤?有父老进曰,窃闻至道之极,无方无倪,万流亿派,通复为一,执枢应环,何辞老释,仰其愽史,仰其慧照,欲跻之诚明之室,固兹堂之所由建也,而奚计其末流之异岐?余曰,言然,且世传夫子适陈时,尝憇吾邑境,故治有夫子堂云,此岂其迹近欤?方今圣祀典崇,固无借此附以二氏,亦不知其孰始,但谚云,三教原来是一家,亦本其同一心焉耳。故何足泥登斯堂而肃此心,合三为一。又释道之苛别云乃记而勒诸石,以俾后世知乡人崇奉之意。”[17](P150) 清代康熙年间,山东高唐地区有道士马士奇在原观音堂废墟之上建起了一座崇奉儒、释、道三教的善感寺,并请当地州官撰写建寺碑记:“三教之立名由来不同,而其为功于天下则一,曷为乎一也?儒以经济治天下,道以法力安天下,而释以慈悲渡天下,以故人闻梵音则怡然悦,听法鼓则肃然敬,阿弥陀佛一语,虽村童愚妇,皆熟悉口耳,盖因佛有西方极乐之说,人故其惕于轮回六道之关,恶念潜消,善心增益,此释之为功,并于儒而超于道,实默助圣王之为治者也。”“今道人以稚龄竟为远迩绅士所心折,建此百年不朽之大功,不于此征道人修行虔而福禄厚也哉,今予仲秋之杪巡郊来此,亲见其人其事深为嘉叹,盖叹疲乏人之能以善感佛,以善感人,而佛与人俱为所感,无非为善所感也,因名其庵曰善感寺,道人于三教中究未知何所适从,尚始终于此善可乎?”[18](P284-287) 这篇碑记有两点值得关注:其一,作者作为地方官员,亦是儒家士大夫,虽然对于道人马士奇赞美有加,并赞成马道人三教合一之旨,但是他更倾向于崇奉儒、佛,而对道教有所贬抑。其二,作者虽然对道教有所贬抑,并对马道人“于三教中究未知何所适从”而有所不快,但是并不能改变马道人对三教的共同尊崇,而马道人之所以能在原观音寺基址上建起善感寺,而不只是恢复原有的佛教色彩浓厚的观音寺,固然与他的道士身份有关,但更与大力支持他兴建善感寺的广大当地信众本来就是崇奉三教合一之宗旨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有佛教信仰倾向的儒生来说,或许会对三教之中的道教有所贬抑,但这并不能代表当时广大民众的真实信仰特征。 事实上,像马道人这样的异教人士恢复或住持佛教道场,或是其他佛教僧侣恢复或住持道教道场,这类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祀祭碧霞元君的泰山行宫,本是道教的道场,可是咸丰时期的山东德州的泰山行宫为尼众所住持:“泰山行宫,祀碧霞元君,在西关外,比丘尼居之。岁孟夏孟冬两月,香火甚盛,游人杂沓,亦名西山,即八景之一。”[19](P150)清末山东济宁北关真武庙也由佛僧住持:“踏冰和尚,不知何许人,顺治五年,携一徒来济宁北关真武庙,赤脚露项,破衲褴褛,托钵市中,夜坐于琉璃灯下,口喃喃不知其何诵,亦不见其卧,每于严冬,取巨冰履竟日,如是数载,谓其徒曰,我明午当归,可为具沐浴。浴毕,登神几,坐曰,三日众火化,葬诸水可也,遂逝。其徒依遗命,烟起聚空为僧形向西,久之乃殁,因投灰于洸水,随流而去。”[20](P157-158)当然,也不乏道士住持佛教寺院的,如乾隆时期山东临淄县观音院,就为某道士住持:“□道士,言谈朴诚,冬夏惟衣一衲,乾隆三十年后,栖于杜山巅之观音院,山田自耕,所收谷露出于庭,养长生鼠百余头,依恋其旁,无少惊。夜忽有齿其衲衣者,一呼而群鼠至,指其一,群鼠皆去,唯一鼠留伏作罪状,道士呵之曰,吾不忍杀汝,可去我于百里之外。”[21](P247)而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儒、释、道三教混合的宗教信仰形式,如民国时期云南的中甸县,就有所谓的三教合一的新教,但实际上只是混合着三教信仰,并非一种新的宗教形态。正如该县志所说:“凡县城及第三区江边汉族人民均崇信之,非其先有佛道混合教之见解与目标而后立教,实本中国人见像必拜、见庙必礼、见经必读之相沿习惯。而中甸又僻居边隅,素无规模完备之佛教或道教,故遂演成佛道混合之一种新教。如其洞经会中所绘神像,系于三清左右,绘释迦、孔子。而所谓之经卷,亦杂大洞、金刚及明圣经普门品而并陈之。习此教者,均系汉族中之优秀士绅,故有时亦自称为儒教焉。”[22](P92) 以上说明,虽然儒家士大夫比较偏向于儒教信仰,但是在广大的地方社会里,人们对于儒、释、道三教并不作严格的宗教形态上的区分,儒家的士大夫虽然有排斥佛教或道教而高扬儒教的倾向,但并不坚决地摒弃佛教或道教,而是程度不同地接纳乃至信仰佛教或道教。对于广大的民众来说,无论是儒教,还是佛教或道教,都不过是圣人神道设教以教化天下“诸恶莫做,众善奉行”,没有必要作截然的区分,信仰儒教或佛教、道教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同时信仰儒、释、道三教也并不存在矛盾或冲突。佛教的寺院是由僧尼还是由道士住持,道教道场由僧尼还是道士住持,在地方社会里并不是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无论是僧尼还是道士住持的佛教道场或道教道场,都是他们表达儒、释、道三教信仰的场所。因此,大量的地方志文献资料完全颠覆了已有的各种三教关系的研究模式,将中国传统的三教关系真正拉回到历史的现实社会当中,还原其本来的面貌。这也就是说,是民众的现实需要及其生活方式真正决定了其所信仰的佛教或道教的特征。 地方志文献对于中国宗教史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是多方面的,这里只是列举三例来加以说明。总体说来,地方志毕竟是历代各地方社会最接近广大民众和士大夫之真实生活的直接记录和反映,较之佛教和道教的教内文献和国家“正史”文献,它对宗教道场(寺观)、宗教人物(释道)和宗教文字(诗文碑刻)的记录要更加具体、详尽,也更加贴近现实社会生活,形式更加多样化,从而更加全面和真实地反映了历史状况。它将使中国宗教历史文化研究走向更加全面、真实和生动的多维度的立体动态史的研究之路,突破过去以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为中心的思想史和政治史解释模式的局限,走向以社会信众的现实需要及其生活方式为中心的社会史解释模式,让研究者更能够体味历史、参与历史和重现历史,从而在发掘历史、与历史展开深入对话的过程当中,更加科学地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佛教和道教文化的优秀历史传统,更加自觉地为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发展开创美好的未来。 注释: ①以阮仁泽、高振农主编的《上海宗教史》为例,该书74万字,论述从古代至1949年间的上海地区宗教史,分《上海佛教史》、《上海道教史》、《上海伊斯兰教史》、《上海天主教史》、《上海基督教史》五个部分,佛教史、道教史占了近一半的篇幅,其中利用了《宋绍熙云间志》、《元至元嘉禾志》、《万历嘉定县志》、《乾隆奉贤县志》、《同治上海县志》、《乾隆金山县志》、《嘉庆松江府志》、《光绪南汇县志》等22种方志中的佛道教资料,但是,从现有的《上海方志提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来看,上海地区1949年以前的方志有140种以上,而我们编纂的《中国地方志佛道教文献汇纂》就收录了上海地区的各种方志达110多种。 ②《发掘地方志文献的新价值——访〈中国地方志佛道教文献汇纂〉主编何建明》,载《光明日报》,2013-05-12;《发掘地方志文献新价值,开辟佛道教研究新天地——〈中国地方志佛道教文献汇纂〉出版座谈会举行》,载《中国民族报》,2013-05-28;《中国地方志佛道教文献汇纂——开辟佛道教研究新领域》,《光明日报》,2013-06-20;尹志华、郝光明:《〈中国地方志佛道教文献汇纂〉:开启中国宗教研究新局面》,载《中国道教》,2013(2)。 ③我国台湾学者卓克华先生著有《从寺庙发现历史》一书,是一部很有代表性的以寺庙为中心的佛教史之研究成果,而晏安宁的《道教全真派宫观、造像与祖师》一书也对大量的全真宫观进行了专门性的探讨,吴亚魁的《江南全真道教》以苏南浙北六府一州历史上的全真道教为研究对象,使用了比较多的地方志文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可惜这类作品目前实在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