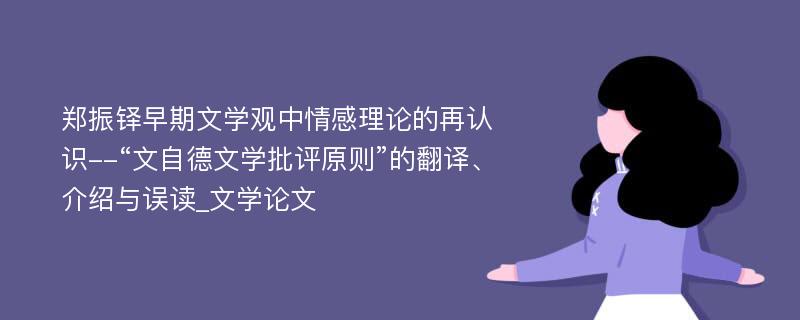
重识郑振铎早期文学观中的情感论——对文齐斯德《文学批评原理》的译介与误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批评论文,误读论文,原理论文,斯德论文,情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0)05-0106-06
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郑振铎的文学思想通常被研究者概括为“为人生的现实主义”,而其“血与泪的文学”主张,更被认为是在理论上极大地促进了新文学现实主义主潮的生成。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的导言中,郑振铎将转向“革命文学”后的创造社纳入“‘血与泪的文学’的同群”,而主张“为艺术而艺术”的前期创造社,以及主张文学复古的“学衡派”,则被他视作异党。这种由郑振铎对文学团体之间观点论争的历史总结,无疑为后人解读他的文学观时提供了一个有效参照,但也导致论者容易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的简单辨析中,形成对郑振铎文学活动的刻板印象,疏于挖掘其早期文学思想中异质性的一面。
1921年8月,郑振铎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开始连载《文齐斯德〈文学批评原理〉》一文,虽然他只是夹叙夹议地介绍了该书自序及前五章的主要内容,但文齐斯德的诸多观点已频繁出现在郑振铎这一阶段的文学论述中。他特别认同文齐斯德关于“文学诉诸情感之力”这一基本命题,并由此展开对新文学之审美内涵与社会功用的相关论述。有意思的是,在郑振铎之前,正是作为创造社成员的田汉,在写于1920年的《诗人与劳动问题》中首次翻译了《文学批评原理》一书的“诗论”部分,并将其观点诠释为浪漫主义的表现论;而在郑振铎之后,这本书的正式译介出版,又是由郑振铎的另一个论敌——“学衡派”学人完成的,由景昌极、钱堃新、缪凤林译,梅光迪校,于1923年在商务印书馆正式发行。因此,如果以新文学阵营内、外的文学论争为背景,这个特殊的译介事件,恰恰能反映出郑振铎早期文学观的复杂内涵——与创造社和学衡派在文学主张上意见分歧的郑振铎,为何也把眼光投到了这本小册子上?当郑振铎处处从情感因素出发谈文学时,“现实主义”一词能否涵括其早期文学思想中的表现论色彩?对文学“为人生”这一社会功利性价值的一贯强调,又使他在译介和阐发文齐斯德的文学情感论时作出了怎样的改写与误读?
《文学批评原理》(some principle of literature criticism)初版于1899年,是美国Wesleyan大学英国文学教授C.T.Winchester(1847-1920)编著的一本带有概论性质的文学教材。或许因为这本小书偏于常识介绍,作者又名不见经传,后来的研究者几乎遗忘了它在郑振铎众多译著中的位置。《郑振铎全集》没有收入《文齐斯德的〈文学批评原理〉》一文。郑振伟在《郑振铎前期的文学观》中虽已注意到文齐斯德一书对郑振铎的影响,却因未能查阅到《学灯》上的译介原文,没有对其译介中与原著观点的抵牾展开更为深入的论述[1]。陈福康虽指出郑振铎早期对文学作为作者主观情感的重视并不亚于当时的创造社作家,但也未对其文学情感论述作出专门研究[2]。本文认为,把“情感”作为郑振铎早期文学思想中的一个核心范畴,分析他对文齐斯德文学情感论的理解与阐发,可以凸显其早期文学观中的理论个性和向后延伸的思考脉络,从而更好地理解其“为人生的文学”及“血与泪”的文学主张。
一、译介初衷:文学情感论的现代内涵与革命潜能
《文学批评原理》全书共九章,从内容提要中可以看出,文学情感论是该书的核心命题:一方面,文齐斯德继承浪漫主义的文论传统,把情感置于文学四要素(情感、想象、理智、形式)之首,强调“诉诸情感之力”是文学区别于科学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身处美国特定的历史语境与文学教育发展的特殊阶段,文齐斯德又自觉发扬阿诺德的人文主义理想,将情感要素的重心,从浪漫主义的作者表现说转移到了文学感化读者的效果上来,以合乎普遍人性的道德规定来约束个人的主观抒情,试图以情感为中介去沟通文学在审美快感与道德教谕上的双重功能。《文学批评原理》一书实际上是一种“打了折扣的浪漫主义,19世纪早期原本反叛的、精力旺盛的浪漫主义在维多利亚时代被阿诺德式追求‘光明与美好’的道德理想主义所调和”[3](P56),而这种混杂性的存在,也使得文学主张上意见分歧的接受者难免在译介文著时“六经注我”,对文齐斯德的文学情感论作出不同的筛选与改造。
郑振铎译介该书的初衷是要以“文学原理”这种特殊知识形态的输入为新文学正名。他曾撰写《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目录几乎涵盖了所有20世纪一二十年代曾对新文学建设产生重要影响的外国文论,而《文学批评原理》就名列其中。郑振铎大致抄写了该书目录,称它“是一部研究文学原理的很重要的著作”,“他以情绪为文学的最重要的特质,受他此论的影响的人极多”[4]。
郑振铎无疑是被影响者中的一员。在其《文学的定义》中,他就遵照文齐斯德的文学四要素说,指出:“文学是人们的情绪与最高思想联合的‘想象’的表现,而它的本身又是具有永久的艺术的价值与兴趣的”[5](P394)。但不同于文齐斯德针对科学的为诗辩护,郑振铎尽管也花大半篇幅模仿文齐斯德论述文学与科学之别,可真正论及自己的写作缘由时,却说是因为近来许多作同题论文的人,把“严中外之防的皇皇奏疏”、“梁启超的呜呼式的论文”等都算作了文学,“真是完全不明白文学是一个什么东西”[5](P394)。因此,郑振铎之所以特别认同文学“诉诸情感之力”一说,首先是为了把传统“文章”观念排除到新文学之外。在《新文学观的建设》中,郑振铎开篇便把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即文以载道论与文学只是供人娱乐的雕虫小技论定为“谬误”,并进而指出:“文学是人类感情之倾泄于文字上的。……文学就是文学;不是为娱乐的目的而作之而读之,也不是为宣传、为教训的目的而作之,而读之。作者不过是把自己的观察、的感觉、的情绪自然的写了出来。读者自然的会受他的同化,受他的感动。”[5](P435)强调文学是作家情感的自然流露,以此确立新文学无功利审美的现代特征,这不仅排除了以道德教训为目的的旧式文章,也拆穿了当时流行的黑幕小说、《礼拜六》派、鸳鸯蝴蝶派以博取读者快感为目的、“为文造情”的旧式文人面孔。
从这一点上看,郑振铎对新文学之现代内涵的基本认识,其实与明确推崇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想的创造社成员并无二致——1920年,田汉在《诗人与劳动问题》中翻译了文齐斯德著“诗论”一章“讲定义的一段”,称其“解释文学绝佳”,他认同文齐斯德的原因,就是因为文齐斯德明确把诉诸情感之力当作了纯文学的根本特质——可以说,他们都将情感表现说当作了文学革命以新辩旧的利器。
然而不同于创造社成员独尊个人情感的浪漫主义倾向,郑振铎在对文齐斯德文学情感论的译介中,显然注意到了文齐斯德对浪漫主义文学思想的反省。如果承认诗歌是情感与想象混合的虚构之物,那么远离现实的诗人独白又有什么用呢?文齐斯德明确反对仅重文学内在价值的“为艺术而艺术”,因而其“以情养德”的主张,在郑振铎看来,恰恰在以情感论为前提解决“何谓文学”的同时,为阐发“文学何为”的问题也预留了一条有效途径。因此,当郑振铎将文学比作“通人类的感情之邮”时,是与文齐斯德一样强调文学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必然生发的情感交流现象,并以此为前提,说明文学只有以情感为中介,才能更大限度地发挥其社会功能。
这一思路在《文学的使命》中体现的尤其明显。郑振铎先引用韩德的话来概括文学应当承担的伟大使命,但他又随即指出,韩德“未免有些太偏重于理性方面了。他看思想太重,而于情绪却一个字也没有提起。我以为文学中最重要的元素是情绪、不是思想。……文齐斯德以为文学的职务,在轻而易读,而不使人费思索之力;而纯以作者的情感来引起读者的情绪。我极以为然”[5](P402)。于是,文学的首要任务不再是“伟大的思想或原理的承认、含孕、并解释”,而是“个人的思想与情绪的表现”,文学创作不该是作家全从冷静的理智出发传达对“时代精神的正确解释”,而应当是作家主观世界中“对于时代的环境的情绪的流露”。
暂且不论郑振铎对文学使命的意见是否与温彻斯特一致,他如此强调文学情感的中介作用还有其特殊的时代焦虑。在郑振铎和费觉天、瞿世英(菊农)讨论文学与革命的往来通信中①,透露了三人对“五四”之后如何继续文学革命事业的忧虑与反思。他们认为20世纪20年代初五四运动退潮后青年们革命意志普遍消沉,是“因为他们的憎恨旧秽的感情不大盛的原故”,这种判断基于一个共识,“理性是难能使革命之火复燃的。因为革命天然是感情的事”[5](P420)。从“五四”到“五卅渗案”前几年间,尽管知识分子始终坚信社会变革的首要任务是转变心灵,但即使在“五四”之后,民众对于启蒙的呼声依然是隔阂的,新文化运动亦或文学革命的领导者逐渐意识到,“促成新思潮从北大冲向校外街道和乡村的,不是思想说服力,而是‘五四’爱国运动”[6](P160)。费觉天在给郑振铎的信中给出了同样的结论,“好比文学革命,其成功所以这么快,难道真是批评的结果么?不然,大谬不然!实在是‘五四’的鼓动”[7]。如何使思想革命真正在实践上与社会革命相结合,如何继续在民众中传播启蒙思想,当理性批评被证明常常止于知识阶层的文士之论时,类似于“五四”爱国热情爆发的巨大能量,情感的激动无疑是更好的选择。“革命就是需要这种感情,就是需要这种憎恶与涕泣不禁的感情的。所以文学与革命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5](P421)郑振铎在得出这一结论之前引用文齐斯德的观点,正是为了提醒作家在注意文学的思想性之外,更加关注创作中的情感因素。
将作者的主观情感表现视为文学的首要特征,将情感交流视为实现文学功利性价值的必需中介,郑振铎早期文学思想中的这一基本思路,使他能在文学的审美自律与社会功能之间保持平衡,也使他相比其他趋向现实主义的“人生派”作家,在思考写实的内涵与方法时表现得更为灵活。
二、洞见与误读:为人生的同情说
那么,如何以情感为中介释放文学的革命潜能呢?仅仅依靠人类社会的共通感或情感的可交流性还不够,还必须解决“文学应当抒发怎样的情感”的问题。如果说在看重文学的情感要素方面,郑振铎与创造社成员并无区别,那么他们真正的分歧就在于此。在《文齐斯德的〈文学批评原理〉》中,郑振铎指出,有人认为把情感分成等级是没有必要的事,“但文齐斯德却坚执着‘人生的艺术’的意见,以能表现出最高道德的情绪为最高的情绪。‘彼道德的成分,或被实物的道德暗示(moral suggestions of material things)所激起的情绪,比之被纯然的物质的或感觉的事物所激起的情绪,其等级是高些的。更明白的说,就是,道德的情绪的文学上的价值是比纯然的或美学的情绪高些。’这种见解,自然有很多人反对他,但我以为在现在的黑漆漆的世界上——尤其在黑漆漆的中国里,提倡‘人生的艺术’是必要的,并且也是必然的趋势,反对他也是无用的。”[8]
与郑振铎不同,田汉在译介文齐斯德书中的“诗论”内容时,完全回避了文齐斯德对情感作出的道德规定。文齐斯德在书中明确指出,文学不应当表现“自私与痛苦之情(the self-regarding and painful emotions)”,而田汉却说,诗是用韵文写的自叙传,诗歌既是以感情为主,只要它是诗人个性的真诚表达,是他对自己人生经验的直接感悟,那么无论是嗟叹、欢呼或是恐惧的感情都可以入诗[9](P122)。概言之,对于创造社成员来说,文学情感必须遵守的道德约束只是——“忠于你自己”。
虽然郑振铎也常用“真诚”、“真挚”等概念来描述作家情感表现的理想状态,如“文艺是人的自由的心胸里的产物,是人的真挚恳切的情感的产物”[5](P512),只要情感真挚,无论作家诉说什么,都不需要接受任何外在道德规范的训示,但是当他著文批评当时大量沉湎于个人爱情或唯艺术倾向的新文学创作时,他显然在认同田汉等人用“诚”从创作态度方面对抒情主体提出主观要求之外,对抒情内容也提出了新的道德规定,希望作家们能走出个人的情感圈子,以对他人的爱与美的情绪、对社会黑暗的憎恶之情去感染读者。
事实上,把“诚”作为个人情感表现的要求是许多“五四”一代新文学作家的共同主张[10]。既然“诚”是仅就作者非常个人的自然情感而言的,那么“立诚”的前提就是要保证抒情主体能够正视自己的一切生命本能,而不是归顺于后天的道德训诫,这根本上改写了儒家人文教化思想中关于如何立人、如何修善的基本表述,确立了一个全新的“个人”观念,从而促进了具有“自我意识”的现代主体的生成。当郑振铎像田汉等创造社成员一样强调文学中的情感因素时,他其实也在肯定这种主情主义文学思想背后所蕴涵的反传统力量,认为倘若以“诚”的情感伦理学替代“旧文章”观念背后的一整套传统价值规范,就能实现五四文学革命个人启蒙与个性解放的根本意图。分歧在于,在郑振铎看来,这个觉醒的个人或许能够凭借由“我”而发的情感放歌从旧的道德束缚中一跃而出,但他并不能真正摆脱这个“黑漆漆的世界”。早在《人的文学》一文中,周作人就将新文学的要求表述为“人道主义”,是“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意味着五四“新人”必须首先是从封建礼教关系中解放出来的、拥有自我意识的个体,然后还应当被放回到一种新的普遍性认同中去,以便制衡这个不加限制的个人。在《文学的使命》中,郑振铎在以文齐斯德的观点修正韩德重“理性”、轻“情感”的偏颇之后,将文学的使命概括为:
扩大或深邃人们的同情与慰藉,并提高人们的精神。……现在的世界是如何残酷卑鄙的世界呀!同情心压伏在残忍冷酷的国旗与阶级制度底下,竟至不能转侧。而人们的高洁的精神,廓大的心境也被卑鄙的实利主义、生活问题泯灭消减而至于无有。救现代人们的堕落,惟有文学能之[5](P402)。
这与文齐斯德对文学之用的论述已有所不同。如何用利他主义的同情心制衡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如何将现代社会中的个人重新放回一个超越阶级、国家、种族的“人类主义的乌托邦梦想”中去?对于秉承“人生派”传统的郑振铎来说,这必然成为他理解文齐斯德情感论时先行带入的问题意识。因此,相比田汉对文齐斯德的译介,郑振铎的洞见之处在于他发现了文齐斯德旨在“以情养德”的文学思想,但是当他从以情感激动人们投身社会改造的角度对文齐斯德的道德情感做出阐发时,又误读了文齐斯德的初衷。
一些有趣的例子充分暴露出这种译介中的错位:文齐斯德在书中多处批评拜伦对情感表达的不加节制,而郑振铎却赞颂他对于个人自由的坚持、对于传统礼教的批判;文齐斯德反感易卜生、左拉、托尔斯泰,而郑振铎却认为他们揭示了社会悲剧,是文学革命的先驱。文齐斯德所谓的“以情养德”是首先针对个人内在修养而言的,他在书中借用阿诺德的人文主义思想来诠解道德情感,是因为他所身处的世纪之交的美国社会同样面临着阿诺德时代人们对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的盲目崇拜与功利主义倾向,所以高级的文学情感应当激发起现代人完善自我的冲动,真正的美德应当源于对自己内心各种冲动的节制与平衡。文齐斯德曾批评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认为它之所以大受欢迎,只不过是迎合了当时“人道主义之念正炽”的社会改造运动,他使用了“humanitarian”一词,让人联想起比他稍晚的美国新人文主义理论家欧文·白璧德对“人文主义”(humanism)与“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的区分。白璧德指出:“一个人如果对全人类富有同情心,对全世界未来的进步充满信心,也亟欲为未来的进步这一伟大事业贡献力量,那么他就不应被称作人文主义者,而应被称作人道主义者,同时他所信奉即是人道主义。”[11](P7)如果按照白璧德的观点来看,文齐斯德就是一个典型的人文主义者,而郑振铎则显然是一个人道主义者。
由此可以理解,为何这同一本书经过学衡派文人的译介阐发后,反而成了批评新文学的话语资源。由于借鉴白璧德,虽然当时的中国明显滞后于同期西方社会的现代化程度,学衡派仍然在新文化运动中看到了文齐斯德所批判的“现代”症候,在学衡派看来,中国最严重的民族危机不是被殖民的落后现实,而是新文化运动急功近利的社会改革对儒家道德礼制的破坏。于是,当田汉与郑振铎都在文齐斯德的情感论中发掘出以文学革命逗发思想革命、再汇入社会革命的动力时,学衡派恰恰瞅准了新文学作家们推崇情感扩张的浪漫主义倾向,将文齐斯德的“道德情感”说诠释成了以理制欲的情感中和。
回过头来看,郑振铎对文齐斯德误读的发生也并非无迹可寻。在他开始专门译介《文学批评原理》的同年,曾为耿济之译托尔斯泰《艺术论》写过序言,托尔斯泰反对把文学情感局限于自我表现,认为艺术的目的在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郑振铎把托尔斯泰的主张同样概之以“人生的艺术”,显然是把他视作了文齐斯德的同道。但托尔斯泰用来判断文学情感价值的依据,其实与文齐斯德有着本质区别。托尔斯泰认为高尚的情感应当体现一种兄弟般团结友爱的宗教意识,这种普遍情感本来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但随着工业化进程中的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越来越使艺术堕落为上层阶级的特权,艺术的使命就是代替宗教宣扬对全人类的爱,特别是对劳动阶层的怜悯。同样主张文学代宗教,文齐斯德的理解是阿诺德式的,“宗教的主旨是克服人身上种种显而易见的动物性的缺陷,使人性达到道德的完善”[12](P16)。文齐斯德所说的“同情”(sympathy)并非指对弱者或悲惨之事的怜悯,而是更接近康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共通感”概念。
郑振铎实际上是用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理想置换了文齐斯德的“人文主义”,用托尔斯泰的“同情说”改写了文齐斯德的“怡情养性”,将文齐斯德的情感论整合到了旨在变革社会现实的文学思想中。
三、“血与泪”的文学:从真诚的情感到真实的体验
从郑振铎对文齐斯德文学情感论的接受和误读来看,“为人生的同情说”或许比“为人生的现实主义”能更准确地概括郑振铎早期文学思想的根本出发点。郑振铎对欧洲特别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最初关注是从现实革命的需要出发的,赞同它重视文学的社会功利性价值的一面,而对于它受西方现代科学思潮影响强调客观反映社会现实这一本质特征与创作方法,其实并没有完全接受。早在编辑《新社会》宣传社会改造思潮时,郑振铎就在《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第一集·序二》中指出:“我们中国的文学,最乏于‘真’的精神,它们据于形式,精于雕饰,只知道向文字方面用工夫,却忘了文学是思想,情感的表现,所以它们没有什么价值。俄罗斯的文学则不然。它是专以‘真’字为骨的;它是感情的直觉的表现;它是国民性格、社会情况的写真。”[13](P4)在这段论述里,“真实性”就同时包含了主观情感的真诚表现与社会现实的客观描写两个方面。
郑振铎本身就从事文学创作,他必然清楚,仅仅在主观创作态度上明确作家应当表现的文学情感是不够的,真诚的、能引起读者共感的同情心不能依托于主观的向壁虚造,还必须以特定的题材与内容来充实。从某种程度上说,郑振铎后来向现实主义创作原则靠拢,其实是为了更好地落实文学情感论的革命潜能,为新文学作家自觉表现“为人生的同情”提供一套具备可操作性的实践方案。
革命的文学家,“现在有吗?”我敢回答一句:“没有!”现在所有的不是鸳鸯蝴蝶派变相的小说家、诗家,就是空谈爱自然的填塞风云月露,山水花木等字的作者。最高等的不过是家庭黑暗,婚姻痛苦,学校生活,与纯粹的母爱的描写者。至于叙述旧的黑暗,如兵士之残杀,牢狱之惨状,工人农人之痛苦,乡绅之横暴等等情形的作品可称得是“绝无仅有”。就是偶然有一二篇,也是表面的肤浅的描写,从没有能使人感到极深刻真切的影像而哭泣、而痛恨的。……凡是一种痛苦的情形,非身入其中的人决不能极真切极感动的把它写出。……我想:我们理想的革命文学家决不是现在的一般作家,而是崛起于险难中的诗人或小说家[5](P422)。
在这段话中,郑振铎实际上给“为人生的同情说”附加了两个新的规定:第一,高级的情感应当通过描写“旧的黑暗”的诸种现实题材表现出来;第二,真诚的情感只有通过“身入”社会现实的真实体验才能获得。由此可见,当郑振铎最终将自己的文学主张归纳为“血与泪的文学”[5](P490)时,他并没有放弃其早期文学思想中注重情感因素的出发点,而这一带有文学性隐喻的概念,恰恰还更好地兼容了浪漫主义的主观情感表现说与现实主义的客观反映论:
一方面,“血与泪”的原意是作家身体的自然流溢物,这意味着郑振铎在号召作家重视文学反映时代或宣传革命的功能时,仍保留了创作者的主体位置,“文学是情绪的作品。我们不能强欢乐的人哭泣,正如不能叫那些哭泣的人强为欢笑”[3](P499),“血与泪的文学”并非对某种思想观念的灌输工具,它首先仍应是作家主观情感和个性的表现;另一方面,“血与泪”又必须是在外力作用下才能发生的生理现象,郑振铎用它来规定作家应当表现的情感内容,意味着作家必须走出沉溺于自我的感情圈子,去亲身经历更为广阔的现实的苦难。正如安敏成所说:“表现所指涉的‘流溢’只有当身体受损(血)或心中注满怜悯之情(泪)时才发生。这一隐喻似乎暗示自我表现,只有在创伤和痛楚的情况下才成为可能。”[14](P48)
“血与泪的文学”主张显然比“为人生的同情说”包含了更多创作实践层面上的思考,通过“观察生活”才能获取真实的体验,借助“客观描写”才能再现触动主观情弦的社会语境,由此引申开来,现实主义的艺术法则也就自然被嫁接到了郑振铎始于情感论的文学思考中。
1922年,以茅盾为首的文学研究会作家开始在《小说月报》上积极展开关于自然主义的讨论。他们之所以提倡自然主义手法,是因为当时的“问题小说热”热衷于理性层面的思想探求,在创作上陷入了脱离生活、主观想象的概念化倾向。这场讨论可能加速了郑振铎此时对其文学思想中有关情感问题的调整,但恰恰也衬托出他不同于其他新文学现实主义者的独特性。温儒敏指出,这场讨论使现实主义者们将注意力从理论探讨转向了创作方法的问题,但又使他们陷入了在“提出问题”与“客观描写”、在“艺术追求”与“现实追求”之间来回滑动的困境,如果一味强调自然主义的客观真实性,必然使作品丧失作家独特的思想感情气质[15](P44-46)。而郑振铎几乎在讨论达到高潮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困境。在1921年9月3日《致周作人信》中,他提出了“修改的自然主义”一说,专门指出,作家不拘于平凡视域的思想情绪比具体的写作技巧更为重要。这种在发挥创作主体性与客观写实之间的折中观点,不排除是受到了文齐斯德的影响,因为早在《文齐斯德的〈文学批评原理〉》一文中,郑振铎就特别注意到了文齐斯德关于“极端的写实是不可能的”的论述。正是郑振铎早期文学思想中对情感的特别重视,使他相比茅盾等现实主义作家对“真实性”有更为圆融的理解,使他易于在提倡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时,注意平衡艺术的主观倾向性与客观真实性。
以郑振铎对文齐斯德的译介为镜像,可以简单归纳出郑振铎早期文学思想的一个发展趋向:最初是在文学发生论的层面上强调作家个人的主观情感表现说;接着是在文学接受层面上要求表现论从情感的个人性转向情感的普遍性,形成“为人生的同情说”;最后则是在具体的创作实践经验中主张“血与泪的文学”,以现实主义的写作原则来落实情感动力学。这三个阶段或许并非界限分明,但的确显现了郑振铎早期文学思想中不能简单以“拥护现实主义”全然概括的复杂性。
然而,无论是创造社的浪漫主义追求,还是文学研究会的现实主义文学观,随着1927年“革命文学论争”的兴起,他们都成为过去式,无论是情感的个人性还是普遍性都被阶级性的讨论所取代,人生派作家的现实主义也被新一代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者批评为对被压迫者的空洞同情。在笔者看来,如果以上述思路来理解郑振铎的“血与泪的文学”主张,就会发现,这种危机其实早已潜伏在他的早期文学思想中。郑振铎在译介文齐斯德的过程中对自己的文学思想进行的几次调整,就是希望能在无损于作家个性与情感自然流露的前提下,以普遍的情感交流方式将个体联合成一个彼此互助互爱的“情感共同体”,最终使他们都投身于民族救亡与社会变革的事业中去。但悖论在于,共感效应发生的前提,是作为抒情主体的作者或被情感打动的读者都是自然状态下拥有普遍人性的个体。可以想象,如果个人被看作是社会环境后天养成的,如果国家、阶级等存在着利益冲突的群体范畴先于个人,那么超脱于社会关系之上的普遍情感就会成为一个面目可疑的理论假说,郑振铎所向往的情感共同体也必然暴露其乌托邦的色彩。
但对于新文学现实主义日趋政治化的发展来说,郑振铎早期文学思想中强调以情感为中介实现文学社会功利性价值的观点以及他对现实主义的独特思考,毕竟为如何理解后来围绕现实主义创作的真实性、倾向性、主观性、艺术性展开的数次讨论,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先例。
[收稿日期]2010-02-22
注释:
①这三篇文章包括郑振铎《文学与革命》(载《文学旬刊》1921年8月10日第10期)、菊农《与西谛、觉天二兄论〈文学与革命〉书》(载1921年8月15日《时事新报·学灯》)、费觉天《答吾友郑西谛先生》(载1921年8月16日《时事新报·学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