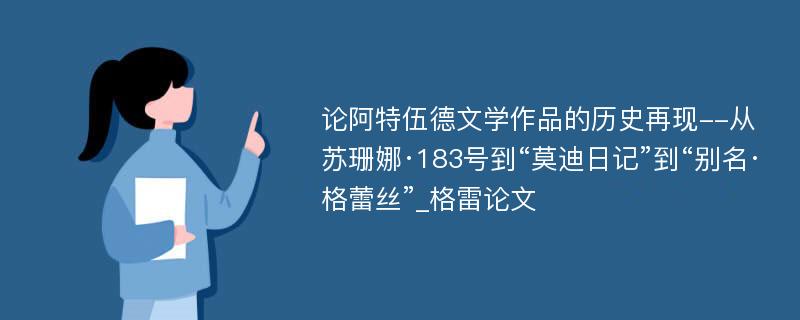
论阿特伍德文学作品中的历史再现——从《苏珊娜#183;莫迪的日记》到《别名格雷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别名论文,文学作品论文,格雷论文,伍德论文,阿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7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29(2008)06-0047-06
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因父亲的昆虫研究工作的需要,刚满六个月时,就随家人开始了年复一年的丛林旅行:春天进入林区,冬季来临前返回都市。幼年和童年大都这样度过:每年数月远离文明、栖居荒野丛林,玛格丽特和哥哥有许多时间玩耍和阅读;母亲充当老师,每天上午上课,下午放假,很像加拿大早期的移民女作家苏珊娜·莫迪在其自传体小说《丛林中的艰苦岁月》和《拓荒生活》①中所描述的当时移民妇女的生活方式。多年以后阿特伍德读到莫迪这些作品中自己十分熟悉的生活方式时深受触动,激发了她的创作灵感。在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历史人物莫迪以及她所描绘的19世纪的加拿大先后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出现在阿特伍德的作品之中。她至少有三部作品是受莫迪及其作品的启发而作,它们是组诗《苏珊娜·莫迪的日记》(The Journals of Susanna Moodie,1970)、受莫迪书中所述的历史事件“格雷斯·马克斯案件”启发而作的剧本《女仆》(The Servant Girl,1974)和长篇小说《别名格雷斯》(Alias Grace,1996)。
1832年,莫迪随丈夫移居加拿大,在一个农场定居。她写了好几本关于加拿大早期移民拓荒生活的书,生动描述了刚到加拿大时的经历和见闻:荒芜的丛林、突发的疾病、肆虐的霍乱、当地居民的冷漠、移民面临的种种艰辛等等,这些都与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及欧洲文明形成鲜明的对比,使她心里产生一种恐惧。但她同时又在作品中流露出对加拿大原始、壮丽的湖光山色的迷恋。阿特伍德早年阅读莫迪作品时就发现了这种矛盾的心态。
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她真正着手以莫迪为原型进行文学创作的?
是诺斯洛普·弗莱在《加拿大文学史》第一卷中对莫迪的评论——她被形容为“一个被冷漠的荒野丛林四面环绕的孤独的人”——促使刚获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奖的诗坛新秀阿特伍德创作了组诗《苏珊娜·莫迪的日记》,并在其中重点刻画和揭示了莫迪对新家园加拿大爱恨交加的矛盾心态,并“将莫迪上升为超越历史的加拿大人的集体无意识”。(New:754)
全书分为三组“日记”,莫迪为第一人称叙述者。第一组日记从1832年延续到1840年,自她与家人渡过重洋抵达魁北克起,写一家人如何沿圣劳伦斯河而上,经霍乱流行的魁北克城和蒙特利尔市,后定居在丛林中一个偏僻的农场;写她既无条件保持自小培养的英国习惯,又不愿完全放弃它的两难,写她与家人经历的七年艰辛使自己的外貌与内心都发生了变化:
皮肤像树皮一样粗糙
(头皮上)长出了白色的根须
双手变得僵硬,手指
脆如树枝
……嘴唇干裂
如被火焰劈开的岩石(Atwood,1970:24)
她刚开始适应丛林拓荒生活,却不得不离开农场,去丈夫升任法官的小城贝尔维尔。第二组日记从1840年延续到1871年,写莫迪对城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对早期丛林拓荒生活的回顾,包括三个梦—三个丛林生活场景:自然中的暴力、企图自杀的早期移民、惊吓牲口又威胁人类的夜熊;还有她对自己淹死的幼子的感怀:
我把他种在这个乡村
像一面旗帜。(Atwood,1970:31)
其余的孩子也一个个地死去。但在她眼里,他们都变作了路边蔓生的植物:
沿着浓荫的小路
不论我走到哪儿
我的裙裾都被这些爬伸的蔓枝钩住
细细的小手想捉住我的双脚(Atwood,1970:41)
第三组日记将莫迪从1871年一直带到该诗集发表的前一年1969年。叙述者莫迪经历了与社会格格不入、有点疯狂的老年期,直到死亡。然而,阿特伍德让莫迪的叙事生命超越了死亡,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被埋葬的莫迪在诗中化成大地桀骜不驯的精灵,以一位老妇人的形象出现在当代多伦多的公共汽车上,谴责加拿大人把自己封锁在水泥和玻璃的世界里。
《日记》隐含了多方面的双重性。
第一种双重性是叙述者的双重声音。作品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是英国移民莫迪夫人。然而,还有另一隐藏在女主人公叙述之后的声音,即作者阿特伍德的声音:她以20世纪的观念和视角,对19世纪莫迪书中的所述进行反思或加以评判,突出了莫迪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的内心分裂这种双重心态。在全书的末尾,作者让莫迪的叙述声音超越了“传统的空间与地域”,(Davey:24)也超越了死亡,在20世纪多伦多的公共汽车上响起。这显然已不是叙述者莫迪的声音,而是作者阿特伍德借莫迪鬼魂之口发出的声音了。
第二种双重性是莫迪对加拿大这片新国土又爱又恨的矛盾心态。这种心态的形成,与莫迪移民前的英国淑女身份、欧洲悠久文明在她所受教育中的积淀等密切相关。初到这个陌生世界,她已带着欧洲旧大陆的先入之见和行为准则,并想把它们强加于加拿大的丛林荒野。然而这片土地非但不接受她所带来的文明,反而要毁灭“文明的”她。文明与蛮荒之间的矛盾使她内心分裂:
一个声音温文尔雅,
以水粉作画,
幽幽地谈论着
尼亚加拉瀑布,
另一个声音
却自有一套理论:
男人散发着汗臭
还免不了酗酒……(Atwood,1970:62)
她与这陌生的环境之间形成了一种既依赖又排斥的紧张关系:她要生存,就不得不依靠这片富饶的土地,然而这片土地同时又是荒芜的、残酷无情,时时威胁着她和家人的生存。因此,她对这片新国土的态度是矛盾的,她在其中既看到壮美又感到恐惧。这种又爱又恨的双重心态又与其他拓荒者和这片荒野(大自然)相互依存又相互毁灭的矛盾关系紧密相连。昔日的莽莽丛林已变成开垦过的沃土,现代化大都市已取代了往日的荒芜。成片的原始森林在隆隆的推土机声中被玻璃和水泥的“荒野”所取代。像莫迪一样,许多早期拓荒者成了荒野丛林组成的大自然的受害者;而今天,大自然又成了人类文明进程的牺牲品。在组诗的末尾,莫迪化作的精灵以老妪形象在多伦多的公共汽车上告诫人们:
转过来,往下瞧:
那儿没有城市;
这是一个森林的中心
你们的城市是空的。(Atwood,1970:61)
《日记》中最突出的双重性意象是一个代表了全体加拿大人的、患了“妄想性精神分裂症”的女主人公。②不同的文化背景、环境、语言的冲突造成了女主人公的异化感,(Relke:51)以及确认自我身份的困难和混乱。她失去了旧的自我,又找不到新的自我。阿特伍德笔下的莫迪登陆魁北克后对眼前的“新世界”发出的是哀叹(Moss:66):
这不能倾听的空间
流动的水将不会映现
我的倒影。
岩石不理睬我。
我成了外语中的
一个词③。(Atwood,1970:11)
莫迪的这种自我身份的错乱感深深地植根于加拿大人的集体无意识之中。他们不管是否出生在这片土地上,都无时不感到自己的根在别处,好像永远处于漂泊不定的状态,像莫迪一样无休无止地寻找,寻找失去的自我。寻找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意识、自己的国家,寻找属于自己的土地。阿特伍德在后记中总结说:“假如说美国的民族精神病症是夸大妄想狂(megalomania),那么加拿大的民族精神病症则是妄想性精神分裂(paranoid schizophrenia)。”(Atwood,1970:62)
阿特伍德在创作《日记》的过程中被莫迪作品中提到的“格雷斯·马克斯案件”所吸引。该案发生于1843年7月23日,又称“金尼尔-蒙哥马利双重谋杀案”。南希·蒙哥马利死前是同案被害者金尼尔的管家兼情妇,验尸时发觉她已有身孕。几天后,结伴逃往美国的女仆格雷斯·马克斯和男仆詹姆斯·麦克德莫特以双重谋杀罪在美加边境被捕,报界认为他们是情人。格雷斯异常美貌、年轻。詹姆斯被判绞刑,临刑前咬定是格雷斯唆使他杀人,因为她嫉妒南希,并答应以身相许;而格雷斯却声称对谋杀案失去记忆。因格雷斯刚满十六岁,加之出现精神错乱症状,后改判为终身监禁。该案因牵涉到性、暴力及阶级矛盾等敏感问题而被加拿大报纸大量报导,美、英报界也连篇谈论。
莫迪在《拓荒生活》等书中描述了1851年自己在金斯顿监狱和多伦多疯人院两次见到格雷斯的情况。阿特伍德初读莫迪作品时(上世纪60年代),对莫迪的描述和评判深信不疑。然而数十年以后,她有了不同的认识。她回忆并反省说:
……莫迪将格雷斯描绘成整个凶杀案的原动力——一个勾引男人的十几岁的阴沉妖妇;而她的同案犯男仆詹姆斯·麦克德莫特在莫迪的笔下只不过是一个被引诱者,受他自己对格雷斯的色欲及格雷斯软硬兼施的伎俩所驱动。……那是我所见到的该故事的第一个版本,由于当时自己年轻,还相信这样的说法:即“非虚构性作品”就意味着“真实”,对莫迪的观点,我没有产生任何疑问。
(Atwood,2004:211)
1974年,加拿大广播公司邀请阿特伍德根据这一历史事件写一部电视剧,她便按照莫迪的观点创作了以格雷斯·马克斯为女主人公的剧本《女仆》(The Servant Girl,1974)。
1996年,阿特伍德又一次以该案为素材创作了长篇小说《别名格雷斯》。这时距她撰写《日记》的1969年已有近三十年的时间跨度,她的历史观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库米·维瓦娜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与历史》一文中指出:
阿特伍德一直关注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关于历史的后现代主义争论。历史学家、文化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们都对“历史代表了过去的客观真实”这种传统观念争论不休,因为他们生活在历史、宗教及民族的“叙述大师们”纷纷失去权威、怀疑主义普遍存在的语境中,因而,这些重要的知识体系正面临着被贬低为“一堆瓦砾”的危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否认有真实的过去存在,只是想指出,任何历史记述(account)都只不过是我们所能得到的关于过去的许多碎片的重构,任何历史叙说(narrative)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某位特定的历史学家所采取的观点来决定的;讲述历史一直就是一个如何解读(历史)的问题。(Howells,2006:86)
可见在撰写《别名格雷斯》时,阿特伍德已受到当代的多元历史观的熏陶,对“记忆”、“历史”、“解读”等重要概念有了更深的理解。在小说撰写过程中,她发现,作为一种历史记忆,这个凶杀案因涉案人员“证词”相互矛盾,美、加、英媒体“报道”众说纷纭,历史文件与个人记录阐释各不相同,显示出个人和集体“记忆”与“解读”的多元性。德国记忆研究专家阿斯曼(Aleida Assmann)的观点也许能更好地解释阿特伍德重写此案时的感受:
在时间层面出现了记忆对象与记忆活动的不同步,记忆研究所面对的,一方面是对记忆对象的重构,另一方面是记忆活动的历史流传、传统,等等。简言之,记忆从而也就需要双重反思。在记忆活动层面存在着选择的问题,也就是激活记忆的视角问题,因为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的再现方式。(王炳钧,102)
《别名格雷斯》是阿特伍德对该历史事件出色的当代重构。她巧妙糅合了心理分析、女性主义、后现代等种种批评理论和创作手法,让小说以各不相同、有时相互矛盾的多种“记忆”汇合成一个“多声部”大合唱,讲述了以下故事:
女仆格雷斯·马克斯因涉嫌参与谋杀雇主托马斯·金尼尔和他的管家兼情妇南希·蒙哥马利而被判终身监禁,已在金斯顿监狱服刑十多年。公众对格雷斯的看法很不一致。有些人认为她是无辜的,因为1843年谋杀发生时她才刚满十六岁;另一些人则认为她要么有罪,而且很邪恶,要么就是精神不正常。而格雷斯的确曾在多伦多精神病院住过一段,现在坚持说她对谋杀毫无记忆。
西蒙·乔丹是当时新发展的精神病治疗领域一名有理想的年轻美国医生。他受金斯顿一批“改革人士”和招魂术信徒的聘请,对格雷斯进行精神上的调查和鉴定,旨在写出一份专家鉴定报告,附在他们的请愿书里,从而使格雷斯获得赦免。乔丹医生引导格雷斯回顾和叙述自己的身世:全家历尽艰险从爱尔兰远渡重洋移民到加拿大、她从十二岁起就在不同雇主家做女仆的辛酸;他一步步把格雷斯带到她丧失记忆的那一天,并了解到金尼尔与南希间的情人关系,以及谋杀案主犯男仆麦克德莫特早有凶兆的种种言行。格雷斯的回忆越来越接近问题的核心。然而就在这时,乔丹却陷入了困境:作为心理医生,他的职业宗旨是唤醒她沉睡的那部分记忆,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她的叙述使他感到困惑,他不知最后会发现什么样的真相:格雷斯究竟是个嗜血的女魔鬼、拉男人下水的女妖精呢,还是在当时特定情况下一个被胁迫的柔弱无助的受害者?在几个月的调查过程中,格雷斯表现出“就连公爵夫人也要羡慕三分”的镇定和自制力,竟使乔丹医生渐渐对她产生了倾慕之心,影响了他的判断;同时,他因与女房东有染而遇到了麻烦……最终仓皇出逃,放弃了对案件真相的探索。……故事的结局似乎还不错,1872年格雷斯终于获得大赦,并有了一个家,她为此感到满足。
选择真实的历史事件作题材,对阿特伍德而言,无疑是为自己挖下许多陷阱。
一方面,为了写这部反映19世纪中叶加拿大安大略地区生活的历史小说,阿特伍德做了极为广泛的调查研究,查阅了大量相关的史料。正如她在“作者的跋”中所写,不仅有关监狱和精神病院的生活“是根据可查找到的历史性材料写成的”,而且对小说中涉及的招魂术和催眠术在北美兴衰的描写也基于史料。她不仅把小说安置在爱尔兰移民远渡重洋来加拿大、加拿大的1837年“大造反”、美国南北战争等历史框架内,而且对许多细节,诸如当时多伦多的街道、商店、时装、风尚等,都逐一做过调查。然而她仍常感到无奈,“不是为了那些过去的记录者写下了什么,而是为了他们遗漏了什么。历史……往往不愿讲述原来就隐蔽暧昧的日常生活细节。”(At-wood,2004:213)因而在撰写过程中,她“不仅得为‘谁讲了格雷斯什么’而费心费力,还得为人们当时如何清理便盆、冬天穿什么样的鞋袜、拼花被各种花样名称的来源,以及如何储存某种腌菜这样的日常生活细节”而头疼,因为它们在所收集的历史记录中几乎无迹可寻。(Howells,2006:32-33)
更棘手的问题是:应该如何取舍所收集到的大量史料。1996年11月阿特伍德在渥太华大学做了题为“探寻《别名格雷斯》:论加拿大历史故事的写作”的讲座,她说:
纸上记录的是什么?和现在纸上记录的一样:罪案、公文、报纸新闻、目击者证词、街谈巷议、传闻、见解、争议,等等。我越来越清楚地发现,现在和过去一样,都没有理由对当时记录在纸上的东西完全相信。毕竟,把这些东西写下来的是人,而只要是人,就都有可能犯错——有意之错或无意之错,也有可能因人性中的欲望或偏见而对所谈的案件夸大其词。(Atwood,2004:212—13)
何况,个人的记忆常常是靠不住的。她在讲座中解释说:
个人的记忆、历史,还有小说,都经过了选择:没有人记得住一切,每一个历史学家都选取那些他或她发现有意义的史实,而每一部小说,不论是历史性小说或不是历史性小说,也都必须限制自己的范畴。(Atwood,2004:216)
多年来,阿特伍德对自己早年读过的莫迪故事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她发现,格雷斯案件的“真相”并不是她间接从莫迪书中读到的仅一个人的一种记忆和解读;何况,莫迪故事的许多细节也难以令人信服。于是,她开始纠正自己以前的认知偏差:指出莫迪故事中的不可靠之处,同时还分析莫迪的阐述出现这些讹误的缘由:
莫迪书中对谋杀案的叙述是对流传的故事的第三手的转述。她把格雷斯看作主犯。出于对托马斯·金尼尔的爱和对南希的嫉妒,格雷斯用性爱上的小恩小惠怂恿麦克德莫特。麦克德莫特则被描写成一个对她极为迷恋、容易被利用的人。莫迪没能够抗拒把这个事件写成情节剧的诱惑:她书中写道南希被分尸四段——这不仅纯属虚构,而且是彻头彻尾的哈里森·安斯沃思。④狄更斯的《雾都孤儿》是莫迪喜爱的小说;它的影响在莫迪对南希充满血丝的眼睛如何缠着格雷斯·马克斯的描写中是显而易见的。
在教养所见到格雷斯后不久,苏珊娜·莫迪又在多伦多精神病院遇见她,当时她被关在狂暴患者病房里。……但是,莫迪的书发表后不久,……格雷斯便被认为精神正常送回教养所了。(阿特伍德,1998:472)
对于莫迪故事中的其他问题,阿特伍德通过小说中的虚构人物——西蒙·乔丹医生与维林格牧师之间的对话来揭示:
“我想去拜访莫迪夫人,”西蒙说,“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不知道如何在不对她所写的内容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的情况下向她提问题。”
“真实性?”维林格不以为然地说,听起来一点也不感到吃惊。
“她书中有些地方毫无疑问与事实有出入,”西蒙说。“譬如,莫迪夫人不知道里奇蒙山在哪儿,她用的人名和日期都不准确,她把这出悲剧里的好几个演员的名字都叫错了。她还给金尼尔先生加了个军衔,可他根本就没有军衔。”……“还有,她的书里写着两个罪犯把南希·蒙哥马利的尸体砍成四块,藏在澡盆下面,事实肯定不是如此。如真是这样,报纸上是绝不会漏掉这样耸人听闻的细节的。……简言之,由于这些漏洞,使人也怀疑其他细节。”⑤(阿特伍德,1998:194—95)
那么,对于所收集到的大量观点不一、甚至相互矛盾的史料,阿特伍德究竟是如何取舍的呢?首先她指出,虽然《别名格雷斯》源于真实(事件),但它是一本小说。而人们所了解的“真实事件”却少得可怜:
1872年,格雷斯·马克斯终于获得赦免。……她是否参与了南希·蒙哥马利的谋杀,并且是不是麦克德莫特的情妇不得而知。同时,也无法判断她是真疯,还是……装疯。历史上的格雷斯·马克斯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仍然是个谜。⑥(阿特伍德,1998:473)
那么,阿特伍德是如何处理这些史料的取舍、“史实”与虚构的比例及关系的呢?她解释说:
我把历史事件小说化了。我没改变任何已知事实。不过,现存的材料相互矛盾很大,很少有事实是明确地“已知”的。……如有不确定之处,我尽量做最合乎情理的选择,同时只要可能就注意兼顾现存的其他几种说法。凡是现存材料中模糊不清,出现空白时,我便自由创作了。(阿特伍德:1998,475)
阿特伍德并不是简单地重炒历史冷饭。她没有把作品写成单纯的侦探小说,她在接受加拿大《环球邮报》的记者采访时解释说:《别名格雷斯》“是非常像侦探小说,只是结局悬而未决。这就是历史与谋杀疑案之间的区别”。(Global Post.Sept.7,1996,p.A6)她也没有过度地渲染性和暴力,甚至没有改变任何已知“事实”,但她确确实实是把历史事件小说化了。
阿特伍德将第一人称自叙与第三人称评述和谐结合,让女主人公的声音与其他人的声音穿插交替。小说一开始便以第一人称的意识流形式表述了格雷斯对谋杀事件所做的明显记忆缺损的不可靠回忆,把关键的情节描写得虚虚实实,悬念迭出,使读者欲罢不能;接着,作者用报纸摘要和民谣形式不置可否地重述了当时社会上对该谋杀案形形色色的流行说法;然后又回到格雷斯的第一人称自述,使读者得以对她的生存境况和内心世界有进一步的了解;再后来,读者听到的却是不同的第一人称叙述声音——乔丹医生与母亲及朋友的通信——穿插回响;时而还有一位持“中立”态度的第三人称叙述者的声音;其间又穿插着格雷斯的自述……。这种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声音给听众“讲故事”的手法使作者便于调整读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格雷斯的自述使读者易于与她认同并受她的情感所感染,但第三人称叙述和其他人的第一人称叙述又及时把读者带出格雷斯的“小天地”,与她拉开客观评判所需的适当距离。同时,这种通过多角度、多人称的“多声部”记忆来重构“历史”的叙事手法,又与小说作者所持的不确定的、多元的历史观相辅相成、遥相呼应。
作家通过巧妙的叙述把读者的心紧紧地扣住了,十六岁的格雷斯究竟杀没杀人?她是男仆的帮凶还是主谋?到底什么是真相?小说一环扣着一环,故事到了最紧要的关头,作者居然巧妙地突然将故事中的许多线索收拢起来,结束了全书。我们这才发现,这一重大事实似乎被作者悬置了,格雷斯有没有杀人并不重要,格雷斯仅仅成了小说的载体,成为女作家反思历史、探索人性的工具。阿特伍德用她独特的小说技巧轻而易举地把读者的注意力转向了引起堕落犯罪的社会。19世纪的加拿大是男权主宰的社会,女性受着压制和歧视,贫穷的女性面临的是更加悲惨的命运。阿特伍德用她一贯的女性主义意识和细腻生动的白描手法再现了那个时代多位女性的生存状态:格雷斯的母亲,操劳一生,为养活孩子不得不随酒鬼丈夫躲债移民加拿大,最后死在了漂洋过海的船舱之中;玛丽·惠特尼,因主人家儿子的始乱终弃,自行堕胎惨死花季;女管家南希也没有逃脱被男主人玩弄的悲剧,而女主人公格雷斯则因为贫穷,十二岁便当女佣,十六岁就被判终身监禁……女作家无疑在告诉人们,底层妇女的犯罪及失误行为的背后,都有着极为深刻的社会原因,留给了读者更多的思考。
《别名格雷斯》发表后,被提名并杀入了布克奖决赛圈;还被提名总督文学奖,终获吉勒奖,赢得评论界一片赞扬,并很快成了国际畅销书。(Cooke:321)
《别名格雷斯》是阿特伍德的第九部小说,但却是她的第一部历史小说。是什么使她转向19世纪,转向思考历史事件与人物?与其说《别名格雷斯》是她小说写作的新起点,不如说这是她写作兴趣的合理延伸。她本科和研究生期间都攻读过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此外还有她对哥特式文学和谋杀故事的着迷,以及在创作《日记》期间对妄想型精神分裂症进行的研究。可以说,《别名格雷斯》是一位成熟的作者在创作的巅峰时期,对很早之前就一直思考的一个故事深思熟虑之后,尤其是对“什么是‘历史真相’”、“怎样在文学作品中再现历史”等问题进行了多年探索后所创作出来的一部精品。
注释:
①《丛林中的艰苦岁月》(Roughing It in the Bush,1852)和《拓荒生活》(Life in the Clearings,1853;译林出版社中译本《别名格雷斯》中该作品译为《森林开发地的生活》)被公认是莫迪的代表作。
②第三组日记是阿特伍德受莫迪夫人晚年的一张照片启发而写,照片上的莫迪看起来很老,似乎有些疯狂。
③黑体为论文作者所加,突出莫迪刚到加拿大时与环境的格格不入。
④安斯沃思(William Harrison Ainsworth,1805-1882),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畅销小说家之一,作品大多是浪漫爱情历史小说,但带有强烈的哥特式小说的神秘色彩和恐怖气氛。
⑤引语中的黑体是论文作者所加,以突显阿特伍德通过虚构人物的对话所表达的对莫迪叙述的质疑和批判。
⑥引语中的黑体是论文作者所加,目的是引起读者的特别注意;此注释也适用于下一段引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