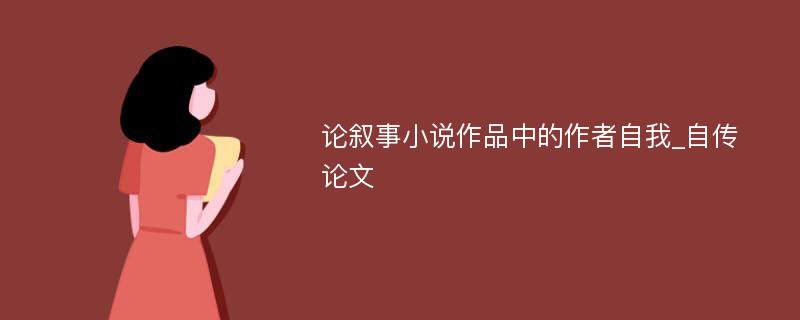
论叙事虚构作品中的作者自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我论文,作者论文,作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7X(2008)05-0130-05
就创作而言,任何作品都是由真实意义上的作者所创造的,在小说这类叙事虚构作品中,展现出一个或多个何种类型的叙述者也是由作者所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任何作品都是作者的产儿。在作品中不可避免地要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而作者作为生活在一定社会中的一分子,他在作品中所表现的生活同样可以包含他自己的生活,就如鲁迅所说:“现在的文艺,就在写我们自己的社会,连我们自己也写进去;在小说里可以发见社会,也可以发见我们自己。”[1](P118)这样一来,也就难以避免在作品中出现作者的自我。美国学者布斯在谈到真实作者对隐含作者的创造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时说:“无论在生活的哪一方面,只要我们说话或写东西,我们就会隐含我们的某种自我形象,而在其他场合我们则会以不尽相同的其他各种面貌出现。有时,这种隐含的形象会优于我们通常自然放松的面貌,但有时隐含的形象又令人遗憾,比不上我们在其他场合的面目。”[2](P31)布斯饶有兴趣地谈到了数十年前与美国知名作家索尔·贝娄交谈时的情景:“我问他:‘你近来在干什么?’他回答说:‘哦,我每天花四小时修改一部小说,它将被命名为‘赫尔索格’。”“为何要这么做,每天花四个小时修改一部小说?‘哦,我只是在抹去我不喜欢的我的自我中的那些部分。’”布斯说他“最欣赏的是知道如何抹去自己不喜欢的自我的作者。”[2](P32)可以肯定的是,不论在什么样的作品中,作者自我的呈现会以不同的方式显现出来。而在叙事虚构作品中,不论在作品中表现出单一的声音,还是以复调的方式呈现出多种声音,也不论人们如何倡导作者在作品中隐退,实际上,作者的声音都不可能在作品中消失或隐匿不见,而会以种种不同的方式,通过其所创作的虚构的叙述者或是作品中的人物表现出来。
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类虚构作品的基本要义,在于它的虚构性。我们知道,在任何小说中,都至少存在着一个讲述故事的叙述者,不论这一个或多个叙述者以何种方式呈现出来。叙述者出现的方式以及在作品中显现的程度可以有种种差异,对此有研究的叙事学家已经做出了细致的区分。[3](P66-67)但是,小说这类虚构作品中的叙述者,与抒发自身情感的散文中的叙述者,或力图描述真实历史的记实叙事中的叙述者明显不同。在记实叙事中,“作者承担其叙事中论断语句的全部责任、因此而不让任何叙述者有任何独立表现的叙事形式。”[4](P139)在司马迁《史记》的诸多篇章中,我们可以不时看到以“太史公曰”为先导而出现的论赞之辞,这样的论赞之辞属于作者——太史公司马迁。在这里,不存在除太史公司马迁以外的虚构的叙述者的论说。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曾提出叙事中“自然叙事”与“人工叙事”的区分,自然叙事叙述的是真的发生过的事情。自然叙事的例子包括一个人昨天的日记,报纸报道甚或是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而“人工叙事却应该是虚构文本所呈现的,那些只是假装在说真实世界里的事的,或那些声明说的是虚构世界里的真事的。”[5](P125-126)以虚构文本所呈现的人工叙事,在这里实际上对应着在小说这类叙事虚构作品中所进行的叙事。既然它属于“假装在说真实世界里的事”,或是“说的是虚构世界里的真事”,人们怎么能把在其中的叙述者的叙说就看作是真实作者的真实自我表白呢?因而,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不管是将小说看作为作者自己的自述传,或将它看作为自己的大忏悔录的一部分,都不能将真实意义上的作者与作品的叙述者相等同,将作者的声音与叙述者的声音相等同,这样,也就不应该从小说中去追寻或印证一个纯粹真实的作者自我。早在一个世纪以前,王国维在其《〈红楼梦〉评论》一文中,针对《红楼梦》是所谓作者自道其生平这样的说法,曾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至谓《红楼梦》一书,为作者自道其生平者。其说本于此书第一回“竟不如我亲见亲闻的几个女子”一语。……然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如谓书中种种境界、种种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则是《水浒传》之作者必为大盗,《三国演义》之作者必为兵家,此又大不然之说也。[6](P151)
这里,王国维实际上已经通过《红楼梦》对小说中的作者与叙述者作出了区分。所谓“自旁观者之口言之”,也就是叙述者以故事事件见证人的身份出现,讲述其眼见耳闻,包括其“亲见亲闻”的诸般事件与人物,而作者自己完全可以置身于所叙故事之外。
对于小说中作者与叙述者之间的区分,萨特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同样说出了很有道理的话:“小说中作者不同于叙述者。……为什么作者不是叙述者呢?因为作者要创作,而叙述者只是叙述所发生的事件……作者创作出叙述者以及叙事风格亦即叙述者的风格。”[4](P142)这就是说,一个是作品的创作主体,这一创作主体确定了小说的面貌;另一个则是作品的叙述主体,这一叙述主体在特定的言语构造中,在一个包含着真实意味的虚构世界中叙说着故事,这二者是不应该混淆的。如果混淆了这二者,将会造成诸多问题,也会有意无意地妨碍作者的创作。当代作家严歌苓曾经叙说过将二者混淆而给她造成的苦恼。在她看来,能写好性爱的作家是最懂人性、最坦诚、最哲思的。她自己早就希望以最不保守、最无偏见的态度去写一部爱情小说,这也是她在写自己的长篇小说《人寰》时的态度。但是,出于对读者将作品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和自己联系起来的担心,她在写作的过程中不得不作了某些调整。她说:“《人寰》这个作品在开始写作时是不保守的,可我感到读者可能会把小说中的‘我’和我联系起来,所以作了些割舍。不然,它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一个女人对一个心理医生讲自己的感情史和心灵史,应该更坦诚些。”[7](P120)对于那些经历过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极左时期,那些经历过文学中的所谓大批判运动的人们来说,应该对批评者那种任意将小说中几句出自叙述者或作品人物的话语抽出来,直接与作者相等同,从而任意将种种可笑的罪名加在作者身上的事例不会感到陌生。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将小说中的叙述者与真实作者等同起来的危害性。
不将叙事虚构作品中的作者与叙述者相混淆,当然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不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只是强调了二者不同的机能、构造、地位以及在作品中所起到的不同作用。任何作品都是作者心血的结晶,都有可能蕴涵着作者自身各种各样的生活体验,有可能包含着作者自身种种复杂而丰富的情感,这种情感有时甚至浓烈到作者自己在作品创作数十年之后都铭刻在心、难以忘怀。歌德在多年之后谈到自己所创作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时,情不自禁地说:“我像鹈鹕一样,是用自己的心血把那部作品哺育出来的。其中有大量的出自我自己心胸中的东西、大量的情感和思想,足够写一部比此书长十倍的长篇小说。”[8](P17)他毫不隐瞒地表明:“这本书是虚构和实事交织起来的。”[9](P159)而这一“实事”是与作者自己的经历与情感密切相关的。在茨威格看来,世界上有创造性的作家,总是把他的“自我”融解在他所描述的客观事物中,直到隐蔽不见,而主观的感觉者,内向的、面向自我的作家,则是让人世的一切终止在他的“自我”当中:“他首先是他个人生活的塑造者。无论他选择哪种体裁,戏剧也好,叙事诗也好,抒情诗也好,自传也罢,他总要不自觉地把他的‘自我’作为媒介和中心写进任何一部作品里去,在任何一种叙述中他首先描述的都是他自己。”[10](P1-2)对于许多作家来说,塑造自我、表达自我的冲动几乎贯穿于整个创作中,而在小说中,作者与叙述者之间这种既相关联而又必须加以区分的关系,使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作者在小说这类虚构作品中自我虚构的问题。
叙事虚构作品中所出现的作者自我虚构,可以贯穿于作品的情节、事件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其中也往往有可能出现一个或隐或显的作者的形象。这一形象,自然不能看作为作者自身的真实形象,而只能作为一个虚构的形象来对待,这一虚构形象与作品中其他的人物形象本质上并无不同,尽管这一虚构形象或多或少在经历、思想与情感上与作者有某些关联与类似之处。从作者的角度来说,人们也意识到,在艺术中,实际上正是这种最贴近作家自身的东西是最难的东西,这种貌似容易的事情是最艰巨的任务。自我描述的成功率往往是很低的,用书面语言描绘出个人的活灵活现的画像的作家是屈指可数的。“艺术家最难于真实塑造的不是他同时代和任何时代的人,而是他的‘自我’”。[10](P4)因而,将作者自我虚构的形象作为与作品中其他的虚构形象一样来理解,不仅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也有助于对作品与人物形象、包括作者自我虚构形象的合理阐释与理解。
叙事虚构作品中作者的自我虚构,既可借助于叙述者、也可以通过作品中的人物来进行。就叙述者而言,其中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区分,即不参与故事而只承担故事讲述的异故事叙述者,与既承担故事讲述、同时又是所讲述的故事或情境中一个人物的同故事叙述者。在这两种不同的叙述中,通过叙述者所进行的作者自我形象的虚构,其表现是有所不同的。
在同故事叙述中,叙述者通常以作品中一个特定人物的身份出现。这一人物既承担叙述的任务,同时又以符合作为所讲述的故事中的特定人物的身份而行动。这样的叙述中,许多是以第一人称“我”作为人物叙述者而出现的。最容易使人将叙述者与作者相等同的正是这种以人物叙述者“我”所讲述的作品。同时,在作品中最容易将人物叙述者“我”与作者自我融合起来的也是这类作品。“我”作为人物所展现的行动和流露的思想情感与作者具有程度不一的关联的情况,在古今中外的叙事作品中都可以找到。作者作为特定社会与文化环境中的个人,都有其独特的经历,都免不了产生种种情感或激情。而这样的情感作家会寻找适当的机会将它表达出来,这种表达不仅与个人与社会文化氛围休戚相关,也与作者个人认识自我的要求、为了了解自我而说明自我的要求密切相关:“为了更清楚更全面地认识自己,他就会像展开一张地图一样把他一生的道路展示在自己眼前。他阐释自己不再为了别人,而是首先为了他自己。”[10](P5-6)这种与自身的经历密切相关的情感表达,通过人物叙述者“我”进行叙说自然是一条十分直接、无碍无障的理想途径。
人物叙述者“我”与作者自我虚构的关系之间,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从经典的自传性文学作品中的自我形象到人物叙述者与作者自我的些许关联,人们可以在中外古今大量的叙事虚构作品中开列出一系列长长的清单。与之相应的是,出现在不同作品中的作者自我虚构的形象可以是完整而鲜明的,也可以是模糊不定的。作者在作品中的自我虚构往往通过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层面来进行。茨威格对在作品中描述自我的三位作家:意大利的卡萨诺瓦(1725-1798),法国的司汤达和俄国的托尔斯泰进行了研究,并注意到三位作家是从不同的层面来进行自我描述的。在他看来,这三个名字象征着三个一级比一级高的不同阶段,他们所代表的不是三种同一价值的形态,而是同一种创造性功能即描写自我的三个不断提高的阶段。卡萨诺瓦代表第一个最低级的原始阶段,即简单地描写自我的阶段。在这种描写中,只报道自己生活的自然的过程和事件,而不作任何评价,对自己也不进行深入的研究。到司汤达,描述自我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即心理描写的阶段。这种描述不再满足于单纯的报道,而是“自我”变得急于想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他观察他个人原动力的必然过程,寻找灵魂里动人心魄的戏剧性的东西。而到托尔斯泰这个阶段,灵魂的自我观察则达到了观察的最高阶段,因为这种观察同时变成了伦理的和宗教上的自我描写。于是,这种自我描述就超出充满好奇心的自我检验,变成了一种自我审判。[10](P2-3)在虚构作品中对自我描述的这种不同情况,我们可以在中外许多作家的作品中看到。
在鲁迅许多以第一人称人物叙述者讲述的小说中,人们可以看到作者自我虚构的不同表现,出现了与作者思想、情感、经历有着不同关系的艺术形象。卢梭《忏悔录》中的人物叙述者“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为卢梭自我的形象,尽管这一形象同样包含着文学虚构。热奈特将诸如此类的自传性作品概括为“经典自传以作者=叙述者=人物为特点”[4](P138-139)。在我看来,除非这种所谓“经典自传”等于描述真实历史的记实叙事,否则,直接以等号将具有自传性质的作品中的作者、叙述者与人物三者加以等同显得过于绝对。因为即便像卢梭《忏悔录》中的人物叙述者“我”仍然是由作者所创作的一个人物,只不过这一人物与许多自传性作品中的人物存在很大的不同,这就是作者遵循“没有可憎的缺点的人是没有的”[11](P13)这样的信条,力图创作出一个真实的自我的形象:“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12](P1)这样的创作态度使卢梭的《忏悔录》与文学史上诸多隐恶扬善的自传性作品不同,塑造出了一个活生生的、与真实作者更为近似的人物形象。但它仍然不能与作者本身划等号,因为这里仍然不能排除作者的自我虚构。歌德的自传性作品《诗与真》的题名很能体现出这类自传文学的实质:它有真实的成分,同时又有虚构的成分。对于在其作品中所出现的作者自我的形象,只应该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才是科学的、有意义的。
至于在许多自称为自传性的作品中,人们往往看得更多的是通过人物叙述者所讲述的、经作者竭力选择之后所展现出的自我美好的一面。这样的人物叙述者,一如隐含作者可以在智力和道德标准上常常高于真实作者本人一样,人们显然更无法将它与真实作者相等同。这种情况,在当今西方一些带政治性的自传中人们依然见得很多。在西方,那些由捉笔人所撰写的仍然健在的政治家的诸如此类的自传中,人所熟知的内容大体上是这样的:“他出身贫寒,通过刻苦工作而成长起来,知道每一个美元的价值,他富于同情心,尽力照顾好自己的母亲,等等——就是那种你希望在政府里所出现的类型。”[13](P131-132)
作者自我形象的塑造,并不以作者自身名字的出现为必然标志。热奈特曾说,不论在同故事叙述或异故事叙述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与作者在姓氏或生平上完全相同或某些相同的叙述者叙述一段明显的虚构故事。[4](P143-144)这一论述是合理的。在《红楼梦》第一回的开头,叙述者叙说了创作这部作品的缘起:“作者自云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说此‘石头记’一书也”。此后,将“石头记”改为“情僧录”,再题为“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撰成目录,分出章回,又题曰‘金陵十二钗’;并题一绝。——即此便是‘石头记’的缘起。”[14](P1,4)这里,以作者曹雪芹名义出现的叙述者,对作品的创作过程做了阐释。即便这里可以或多或少地将这一叙说与作者曹雪芹相关联,却不能将此后出现在作品中的叙述者与作者曹雪芹相等同,将《红楼梦》看作描述作者曹雪芹真实历史的记实叙事。诸如此类的情况在其他的叙事虚构作品中也可以找到,让我们看看下述作品片段:
母亲和宏儿下楼来了,他们大约也听到了声音。
“老太太。信是早收到了。我实在喜欢的了不得,知道老爷回来……”闰土说。
“阿,你怎的这样客气起来。你们先前不是哥弟称呼么?还是照旧:迅哥儿。”母亲高兴地说。(鲁迅:《故乡》)[15](p65)
谁也见不到我们;我一时感情进发,走近照片对她说:
“贝雅特丽齐,贝雅特丽齐·埃莱娜,贝雅特丽齐·埃莱娜·维特波,亲爱的贝雅特丽齐,永远失去了的贝雅特丽齐,是我呀,是博尔赫斯。”……
我感到无限崇敬、无限悲哀。
“你这样呆头呆脑地看下去要走火入魔了,”一个厌烦的声音取笑说。“我让你大开眼界,你绞尽脑汁一百年都报答不清。多么了不起的观察站,博尔赫斯老兄!”([阿根廷]博尔赫斯:《阿莱夫》)[16](P121-123)
丈夫马上说:“尼娜,你可以去倾诉热线工作,你却想着自杀。醒醒吧!你在报纸上登个广告吧:‘女作家戈尔兰诺娃愿意安慰任何一位携带一定价值的食品来找她的人……’”
顺便说说,因为我,他们把刀子藏起来了。但是我还有足够数量的安眠药……([俄罗斯]尼·戈尔兰诺娃:《一个活得很累的当代人与其心灵的交谈》)[17](P144)
从上述三篇小说的片段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故事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明确地提到真实意义上的作者自身。这里所出现的“迅哥儿”、“博尔赫斯”、“尼娜”、“戈尔兰诺娃”等,人们显然不能将它们与作者鲁迅、博尔赫斯或尼娜·戈尔兰诺娃相等同,将他们所叙述的故事看作作者自身真实的经历与情感的表现,尽管作为人物叙述者,他们都有可能或多或少地与真实作者的经历或思想情感有关。在这里,作为署名作者的鲁迅及其他作者从功能上与其作品的叙述者兼主人公的鲁迅、博尔赫斯等人并不相同,即使他们的许多生平特征相似。[4](P144)我们只能将直接采用作者自己的名字作为作者自我虚构的一种特殊修辞方式来看待。这种修辞方式所表明的是,小说有可能与作者自身的生活存在些许关联,或者带有一定程度上的自传色彩,但它从本质上说来,依然是展现虚构世界的叙事虚构作品。上述俄罗斯当代作家尼娜·戈尔兰诺娃的作品带有浓厚的自传色彩,她的小说以俄罗斯当地的日常生活为主要题材,描写女性的生存困境、多子女家庭的艰辛以及女性对多重角色的困惑等。[17](P138)她的《一个活得很累的当代人与其心灵的交谈》很好地展现了当代俄罗斯一个处于多重困境下的女性的生活与内心世界。小说一开头,处于无奈中的人物叙述者就说:“我想割断血管”:她想到了自杀。在叙说了种种无法排解的困窘之后,到小说临近结尾时,人物叙述者又一次想到了自杀:
我的安眠药在哪里?
我服下了一小把药片,我的四肢开始变得僵硬。原谅我这个有罪的人吧,上帝!突然儿子大声喊了起来:
“妈妈,妈妈,来热水了!”
已经三个月都没有热水了。我们这里即便凉水也来得很少,更不用说热水了!……我拖着僵硬的四肢跑到厨房,满心欢喜地洗起碗来……[17](P145)
小说就这样结束了故事,其中包括在前叙引文中出现的作者的真实姓名。在作品的结尾,读者可以明显地看到人物叙述者服安眠药的自杀行为。我们可以把通过人物叙述者“我”所讲述的故事的小说看作带有包含真实作者某些个人思想情感、甚至经历的作品,至于包含着多大程度上的个人自传色彩,像所有诸如此类的作品一样,是一个需要进行细致研究之后才可回答的问题。不言而喻,这里出现了明显的作者自我虚构。叙事虚构作品中所出现的诸如此类的自我虚构,究其原因,可以因为作者对出自自身材料的熟悉,可以因为更为易于宣泄自身的情绪与情感,可以因为能更成功地塑造出自己满意的形象,也可以如茨威格所说的出自使自我不朽的天然要求:“这种不自觉的、模糊的追求自我永存的意志,便是一切自我描述的动机和开端。”[10](P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