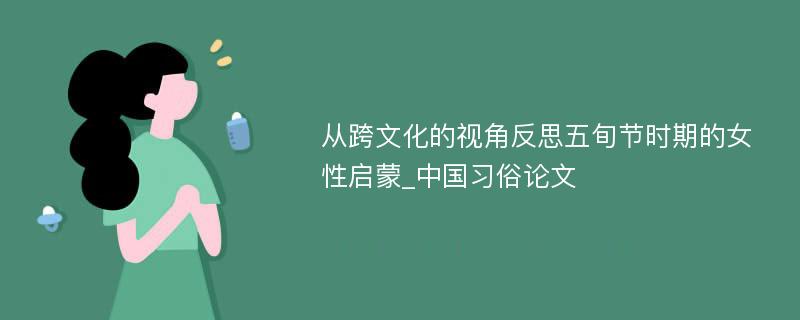
从跨文化视角反思戊戌时期的妇女启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跨文化论文,妇女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反思戊戌时期的妇女启蒙是近年来性别研究领域里的一个热门话题。① 戊戌时期妇女启蒙的中心是“废缠足”和“兴女学”。这“一废一兴”并非无根无蒂,深究其历史渊源及时代背景,我们不难发现,它源自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又在晚清自强维新的语境中发生了变化:从清初复兴女学古义、恪守妇道,到维新派大力宣传“新女性”、塑造“国民之母”,妇女从家庭的“私”领域被推入担负“强国保种”的“公”领域。关于戊戌时期的妇女启蒙,学术界已有一些论著涉及,而从跨文化视角研究妇女启蒙思想的源流及其变奏的专论仍然阙如。本文就此进行探讨,以期深化有关戊戌思想的研究,并对其妇女启蒙思想有所反思。
族群、宗教、时尚:各种反缠足话语
满清入关以前,缠足在汉族妇女中流行了数百年之久。文人骚客笔录纸载称赞三寸金莲为女性美的标志。1644年满族入主中原,清廷在迫使汉族男性接受满族发式的同时,试图废除汉族妇女缠足的习俗。其结果是,汉族男子在“留发不留头”的威胁下在脑后蓄起象征臣服的辫子,而汉族妇女的小脚却躲过此“劫”,于是,有所谓“男降女不降”之说。这是缠足首次成为政治风潮的焦点。
顺治元年(1644),孝庄太后谕:有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次年又下诏,以后人民所生女子禁缠足。② 康熙三年(1664)又令九卿科道官员会议,康熙元年以后所生之女禁止裹足。礼部议定,康熙元年以后所生之女若有违法裹足者,其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议处,兵民则交付刑部责四十板,流徙十年。③ 然而,这一禁令在历史上昙花一现,并无实效。1667年,积极接受汉族文化的康熙皇帝亲政,次年,应汉人左御史王熙上疏,弛禁裹足。
清末学者缪荃荪(1844~1919)在《妇女裹足考》一文中肯定了满族女主严禁缠足之功,指责“汉臣持之不力”导致了民间缠足之风不止。那么,“汉臣”为何“持之不力”呢?在“汉臣”心目中,悠久的中原汉族文化远远优越于关外的满族文化。当满汉冲突时,象征着汉文化和汉族认同的缠足习俗,相对于满族妇女的天足,也就畸形地变成“教化”或“文明”的女性美标志。④ 史料表明,盛清时期一些倾慕汉文化的少数民族家庭开始模仿汉人给女孩子裹脚。一些满人也因喜爱小脚而娶汉族妇女为妻。⑤ 然而,并非所有的汉人都一味地维护缠足。在1840年以前,一些汉族士大夫出于人性的考虑表达了对妇女缠足的同情。他们明确指出,缠足伤害女性身体。俞正燮(1775~1840)和李汝珍(1763~1830)都抨击缠足是“屣贱服”、“造淫具”,不关教化。⑥
至此,我们听到两种反缠足的声音:一是在满汉冲突下,满清贵族出于族群征服的需要禁止缠足;一是明清启蒙思想家发自肺腑地对妇女的同情。这些思想潜滋暗长,成为清季反缠足运动的本土根源。⑦ 在19世纪下半叶的中西文化交汇中,缠足再次成为社会的焦点。此次不同的是,西方人借用报刊舆论把中国妇女缠足诠释为屈从和被奴役的标志。缠足不仅象征了中国妇女的屈从地位,也成为西方人攻击中华文明“愚昧落后”的把柄。一时间,西方的传教士及习俗改良派(abolitionists)和中国维新派都关注着“三寸金莲”,掀起了全国性的乃至跨国界的反缠足运动。
1.宗教话语:欧美传教士
19世纪中叶,来华女传教士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女性。她们制定了一项帮助妇女的社会计划:废除缠足习俗。美国的一些教会出版物极力渲染缠足的血腥和野蛮。由于担心华人会因教会干涉其风俗习惯而排斥“洋教”,罗马的天主教廷和美国的圣公会认为,明智的做法是接受包括缠足在内的华人习俗。⑧ 以汉口的一所女子教会学校为例,这所学校不仅特许女学生缠足假期,还派修女去观察。她们所能想到的改善妇女状况的办法只是在缠足过程中提供医疗监护以免影响女性健康。⑨
传教士的反缠足可谓宣传造势胜过身体力行。他们在海内外期刊上撰文,把缠足描绘为女性受压迫的标志,而反对缠足的理由主要是基督教教义,认为男女的手足都该平等地不受束缚,中国妇女缠足是天底下的一个特例,它违背了上帝的旨意,故应予禁止。⑩ 在中国的教会刊物上,女传教士现身说法来说服华人放弃缠足的习俗,指出:“我泰西妇女,全身皆自由自在,无殊于男子。比来作客中华,目睹浇风,意良不忍……以劝华女之父母”帮助女儿放足。(11) 传教士试图纠正有悖教义的陋俗,自命为“中国姐妹的救世主”或中国妇女的榜样,其理论依据是她们确信基督教文明优越于中华文明。
传教士崇拜西方文明,贬低东方各民族的文明。他们在讨论“印度归主”时,明确指出:“夫人之有学问智慧,即权力之所从出也。”英国人以文明教化传播至印度人的头脑中,印度之所失不过金银财货而已。“核其所得,厥有文明之治法教道及其学问智慧,则谓英国之所得不偿所失,亦奚不可。”(12) 在传教士看来,英国是文明教化之邦,他们的殖民掠夺就是向落后民族传播高级文明,自然是合理合法了,甚至认为印度人为此所付的学费还远远不够。在这种思维支配下,女传教士把自己树为中国妇女的榜样就不足为奇了。来华西人的文化优越感将基督教的权威性合法化了。然而,回顾西方妇女的身体历史,那些由鱼骨兽皮制成的束腰内衣(corset)勒得其内脏畸形甚至肋骨断裂,她们的身体又如何能“自由自在”呢?(13) 传教士盲目夸大基督教文明的优越性,正是为了利用文化霸权建构基督教的权威性。
传教士虽先于中国维新派抨击了缠足陋俗,但考虑到传教的需要,他们迟迟未能将其言论付诸实施。西方人反缠足的舆论激起了维新派的民族耻辱感。直至维新派揭起反缠足运动大旗,传教士才投身其中。(14) 笔者认为,传教士对反缠足的贡献在于他们发动了强大的舆论攻势。他们以文化优越论为支点,策略性地将缠足诠释为屈从、愚昧落后的象征,从而摧毁了大汉族傲视满人的自豪感。缠足从汉族妇女的教化标志转变为中国妇女遭受压迫的野蛮象征。然而,在实践层面,传教士的努力仅限于中国基督教团体的小范围。
2.时尚话语:英国的习俗改良派
在废奴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习俗改良派对各民族的陋习非常敏感。1887年,41岁的英国商妇立德夫人(Mrs.Archibald Little,1845~1925)抵达中国。此前,她遍访欧洲各国,以写作著称。1895年立德夫人创办天足会。这是中国首批不缠足团体之一。立德夫人担任会长,并亲理会务达十年之久,直到1906年离开中国。后人称誉“她在华期间热衷于公益活动,是世纪之交向海外介绍中国的最著名的作家之一”(15)。立德夫人是立足教会之外,西方妇女批评缠足的典型。以往的研究把立德夫人倡导的不缠足和西方传教士的宣传相提并论。(16) 其实,二者并不完全一样,立德夫人反缠足言论有其特殊性。
在华期间,立德夫人从一个维多利亚妇女(作者注:特指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治下的妇女。这一时期的英国妇女,一方面在国内积极争取自身权益,另一方面在海外极力推动当地习俗改良)的兴趣出发关注中国的社会生活。立德夫人批评传教士对华人的影响力太弱,她指出,那些“旅华二十多年却不懂一句华文的人”写出的报告是不足为信的。在她看来,传教士并不想“干涉”华人的习俗,甚至为了传播福音的计划而迎合缠足陋俗。Elisabeth Croll评价立德夫人的作品时指出,立德夫人兼顾中国与欧洲的异同,“她对那些一味指责华人低素质的欧洲中心主义态度深感不满,并向它发起挑战”(17)。尽管如此,立德夫人还是难以理解缠足的习俗。
立德夫人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国际组织来协调各方面的工作以终止缠足。她认为缠足与宗教关系不大,只不过是风俗和时尚之属。(18) 她注意到中国士大夫已经身体力行地反对缠足,而他们大多与基督教无缘。(19) 她认为中国的反洋教势力会殃及反缠足的努力,所以期望反缠足与传教士在行动上保持一定距离。立德夫人倡导的这项“造福工程”在某种意义上给热心公益的旅华欧洲妇女开拓了社交空间。她们积极著文并发表演讲来抨击缠足。像女传教士一样,她们也把欧洲妇女树为榜样。事实上,立德夫人及其追随者视反缠足之举为领导华人社会的新时尚。她们要改变华人社会中以小脚为美的婚姻习俗,倡导天足之美。
立德夫人利用丈夫的商业网络拜见一些朝中显贵,说服他们支持废除缠足。她清楚地意识到由于其英国商妇的特殊身份,那些显贵才会跟她谈及中国女人的脚,而中国妇女则显然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在这里,立德夫人和旅华欧洲妇女自觉地充当了中国妇女的代言人。她们公开致书中国士大夫,呼吁他们帮助妻女放足,“此事本应由男子决定,缘自古至今,女固听命于男。诸君子如告尔妻女曰:余甚欲尔等妇女之足,任其自然,不加缠裹,俾稳立健行,一无苦楚,尔妻女自必乐从”(20)。在海外,立德夫人造访英国各地并广为宣传反缠足工作,她和其他作家把中国的缠足描绘为“野蛮”、“半开化”,还把中国妇女介绍给英国民众,让殖民地妇女看起来像他们“受迫害的姐妹”。立德夫人的一些文章发表在著名的女权主义刊物上,如《英国妇女评论》(The Englishwoman's Review)。许多英国女作家曾利用这本杂志塑造受苦受难、待人解救的印度妇女形象。立德夫人及其英国姐妹营造着一个观念,即在英国背景下,英国妇女在海外成功地解救殖民地妇女。(21)
立德夫人不仅充当了中国妇女代言人的角色,还把自己想像成中国受迫害孩子们的母亲。她“将留给自己孩子的全部爱心普施予中国受苦受难的孩子们”(22)。她竭尽全力募集更多的基金,为她的“中国孩子”修建避难所。因此,她甚至被一些中国官员誉为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二世。立德夫人所表现出的“英国母亲”意识与Antoinette Burton研究旅居印度的英国妇女的表现如出一辙。Burton认为,在日不落帝国大家庭里,印度妇女像女儿一样隶属于她们的“英国母亲”。英国妇女所感受的“对印度妇女的帝国使命感要求如此的权力关系”,她们从“野蛮”的印度男子手中解救“受迫害的女儿”。(23) 值得指出的是,立德夫人的英国母亲身份并未得到中国士大夫的认可,在他们眼里,旅华欧洲妇女不过是“来自异邦的精明的女儿”。关于妇女启蒙的代理人之争已在这里初见端倪。
立德夫人意识到,一旦中国妇女解除了缠足之累,她们将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但她从未将反缠足与任何妇女解放运动相结合。她只是热衷于废除“野蛮的”社会习俗。这并非因其兴趣不在争取妇女权利上。据载,立德夫人年轻时在英国已显露出对女权的兴趣。她由华返英后又曾致力于争取妇女婚后财产权。在她看来,缠足仅涉及习俗和时尚,而无关乎宗教或意识形态。故她并不试图通过废缠足来帮助中国妇女争取权利。事实上,以立德夫人为代表的习俗改良派利用其在拯救华人妇女行动中建立起来的权威性和道义形象,有助于促成她们在祖国争取妇女的财产权和选举权。显然,在她的运思中,宗主国与半殖民地国家的社会状况不同,妇女启蒙的主题因之而异。
3.民族国家话语:晚清的维新派
海外舆论对华人缠足习俗的批评震动了清朝的官员、留学生及外交使节。女人的小脚不只是妇女依附男性的标志,也象征着中华文明的“野蛮落后”。清代一些学者已经触及这一陋俗,加之晚清西方舆论的刺激,戊戌维新派就此发动了一场以妇女为对象,以民族自强为目标的废缠足运动。他们的主张更明确地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现实处境和需要。于是,他们一方面猛烈地抨击缠足习俗,一方面积极塑造中国妇女的“国民之母”形象。
维新派建构反缠足话语的思想底蕴是富国强种。他们认为强种的首要任务是放足,放足才能使妇女成为强健的“国民之母”。留学英国的严复(1854~1921)认为,西方人批评华人裹足为“蛮猓不如”,其言虽逆,却值得有心人平心深思。他依据社会达尔文主义指出:“盖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较之欧洲及日本为强种而提倡妇女锻炼身体,严复慨叹“此真非以裹脚为美之智之所与也”(24)。维新派领袖康有为(1858~1927)指出,妇女裹足一事“最骇笑取辱”于万国。“试观欧、美之人,体直气壮,为其母不裹足,传种易强也;迥观吾国之民,尪弱纤偻,为其母裹足,故传种易弱也。今当举国征兵之世,与万国竞,而留此弱种,尤可忧危矣。”他主张严禁妇女裹足,已裹者一律宽解;若有裹足者,重罚其父母。这样,“举国弱女,皆能全体,中国传种,渐可致强,外人野蛮之讥,可以销释”。(25) 此类主张反映出维新派的妇女启蒙的实用性。妇女首先是作为强种、强国的工具而得到维新派的重视,而非因其天赋人权和男女享有平等权利。
此外,维新派还认为缠足使妇女丧失劳动能力,让男子不得不承担起全家的生活重负。从而导致了家贫,并殃及国家。(26) 依此逻辑,缠足妇女不仅要承担种弱的责任,还要检讨家贫的过失。但这种看法显然言过其实。据目击者记载,缠足妇女仍然坚持田间劳动,她们不是站着而是跪在田里。(27) 中国妇女世代在家里辛勤纺织,远非维新派所描绘的那种不劳而食的寄生虫。(28) 从维新派的偏颇言论中可见,其禁缠足的意图首先不是为妇女谋权益,而是出于挽救民族和国家。
强调妇女作为民族母亲的地位并非维新派的独创。Antoinette Burton曾指出,英国妇女也非常重视自身作为民族母亲的身份,并强调她们在保存种族和延续文明上的作用。但两者的区别很明显:维多利亚女权主义者自觉地宣称自己是民族母亲,而中国妇女则是被动地由男性“赋予”民族母亲的身份。“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权主义文献贯穿着妇女是民族母亲的主题。她们肩负着不亚于男子的民族责任,因而理应平等地在议会里享有权力。”(29) 在中国,维新派承认中国妇女的民族母亲身份,是为了诠释中华民族和文明的衰弱之源。其目的并不在于唤醒妇女的平权意识,而是让妇女分担起民族兴亡的责任。他们认为中国妇女应该放足,像民族母亲那样与他们并肩投入民族救亡图存运动中。
4.主体话语:缠足妇女
以上种种反缠足主张都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讨论妇女缠足问题。在戊戌时期,此类强势话语似乎使这一事件的主体——缠足妇女在历史上处于失语状态。然而,在我们所能接触到的有限史料中,包括物质史、口述史及政治史等,主体话语依然存在,而且其多样性和复杂性清晰可见。
世纪之交最具影响力的女权主义者秋瑾(1875~1907)曾积极投身于反缠足运动。她创办妇女刊物,呼吁兴女学、废缠足。她揭示了中国妇女陷于缠足、包办婚姻和附庸的恶劣处境,认为只有放足、兴女学和自立才是妇女解放的真正途径。有学者指出,在秋瑾看来,废缠足、兴女权和反满革命是不可分割的事业。(30) 由此可见,有些妇女是以争取自身利益为目的而自觉投入到民族救亡的洪流中去。世纪之交,广大中国男子尚未享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权利,妇女又从何直接争取之呢?中国妇女面临着选择:要么与西方姐妹合作,要么与民族主义兄弟合作。正如Burton所指出,在殖民地妇女的代表权问题上,西方女权主义者和本土的民族主义者处于竞争状态。(31)
值得指出的是,一些缠足妇女出于各种目的并不赞成放足。曾任《女学报》主编的薛绍徽(1866~1911)认为女学才是妇女自强之本;缠足乃私事,缠与放无关乎女子对国家的贡献。比较西人的细腰和东洋日本的黑齿,缠足并非不可容忍的习俗。薛绍徽觉得不同文化应有自己的习俗,在外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习俗对本地人则再自然不过了。(32) 也有一些缠足妇女是有感于放足过程中的疼痛及放足后“四不像”的尴尬而发泄不满。辛亥以后,当放足被纳入激进的国民革命,一些极端的缠足妇女甚至以死相抗争。如果说从客体的角度来看,旁观者的反缠足话语往往把放足描绘为一蹴而就的解放;那么,从主体的角度,缠足妇女的声音则让我们感受到习俗改良的复杂性。
综上可见,戊戌时期的反缠足话语可谓众声喧哗,各种声音高低不同,而其思想底蕴亦显然有别。这些声音此呼彼应,互相感染或制约。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戊戌时期妇女启蒙思想的复杂性。事实上,人们熟知的维新派思想仍可再加考量,其妇女启蒙在民族主义思潮中发生的变异颇值得注意和探析。
跨文化视角:妇女启蒙在民族主义思潮中的变奏
1903年,梁启超在游历美国的归途中写道:“西人有恒言曰:欲验一国文野程度,当以其妇人之地位为尺量。”(33) 他以此尺度观察美国,认为:“美国妇人之地位,在万国中比较的最高尚。”“道中男子相遇,点头而已;惟遇妇人,必脱帽为礼。在高层升降机室中,一妇人进,则众皆脱帽。街中电车座位既满,一妇人进,诸男必起让座。”梁氏将这些归纳为“平等主义实行之表征”。而其实际内容,则包括男女职业平权,女子婚后财产权及选举权等。他认为美国妇人权利优于他国,“妇人之加入政界,非徒不可抑亦不能矣”。(34) 梁氏在中西交汇之际对妇女地位与国家文明关系的反思颇值得注意。这是我们考察妇女启蒙如何被纳入到国家民族启蒙的重要线索。
与梁启超的认识相似,早在1860年日本使团首次访美时,日本人也为美国妇女的地位所震动。他们描绘到:该国妇人颇受尊重。男子入室,首先向室内妇人致意,然后才是男子。男子向妇人脱帽致意,对其他男子则不然。男子路遇妇人要站立一旁让妇人先行。妇人在这里所受的礼遇就像吾国之对待家长。(35) 中日两国维新派的记载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妇女地位已经成为西方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价值尺度。故明治维新不仅注重仿效西方讲求声光电化之学,开展修铁路、建电报局等建设,还积极地取缔如男女共浴之类的“陋俗”。正如Sharon Sievers所描述,明治政府所倡导的习俗改良让日本脱颖而出,他们对待西方人的敏感的态度就像个虚心的学生。(36) 日本维新派依照西方的外交礼节,让上流妇女参与外交场合。他们模仿西人尊重妇女的礼节,但并没有男女平权的实际内容。他们没有、也无意实行男女平权的真谛,只是在东西文明的对照中,试图从外表上缩小日本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差距。
反观戊戌维新派,他们对中国陋俗的认识与先行的近邻日本颇相类似。他们虽然也讲男女平权,但更直接地是在西方文明的价值尺度下和西方人的耻笑中发起了对传统陋俗的改良。于是,正如整个戊戌启蒙思想被民族主义主题淡化,自由、独立让位于“合群”、社会一样,清末的妇女启蒙也在民族自觉、国家意识的指挥下发生了变奏。其独特之处是,梁启超创造性地把改良习俗的思想纳入春秋大义之中,较之日本维新派带有更浓厚的儒学色彩。他指出,“以力陵人者,据乱世之政也。若升平世、太平世,乃无是矣。地球今日之运,已入升平世,故陵人之恶风渐销,而天然之公理渐出。非洲、印度之压首,欧洲之细腰,今其地好义之士,各合变力,思所以豁去之,殆将变矣。”(37) 这种全球的变通趋势具体到了中国就该痛改缠足等等陋习。梁氏也注意到,满蒙习俗与汉俗的不同,“幸未染此,后妃崇贵,同屦依然”(38)。他引用“强男之头不如弱女之足”的说法,斥责明清之际汉人抵制满清政府禁缠足之举为“群盲”,“内违圣明之制,外遗异族之笑;显罹楚毒之苦,阴贻种族之伤”(39)。在梁氏的笔下,缠足积习既有别于满蒙习俗,又受外国异族耻笑,故需变通之、痛改之。这里,梁启超淡化了对妇女的同情,或出于男女平权的救赎,也没有对汉族习俗的些许辩护或族群认同感。国家主义压倒了一切,包括性别和族群。
维新派代表人物对妇女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同情,言辞激缓有差,但都彰显出民族主义的思想主题。于是,维新派的妇女启蒙明显地出现了理论缺位:一方面,他们在中西差距和西方舆论中不得不放弃研习、遵循多年的儒学理念,将近代世界大势纳入春秋三世之中,导致中西思想牵强附会;另一方面,他们面对民族危机和救亡图存的使命,不得不放弃西方启蒙思想中许多基本的、核心的价值观念。在其改良陋俗的言论中,男女平权、妇女的独立人格、自由的权利等等已经淡化得模糊不清,流露出来的只是其强烈的羞耻感和国家意识。
进而言之,“废缠足”是解放妇女的身体束缚,可谓妇女启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戊戌维新的语境下,妇女启蒙在民族主义思潮中发生了变奏。梁启超们的民族主义倾向与影响近代中国的殖民主义话语存在深刻关联。妇女的地位是西方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尺度。当这把尺子在其殖民计划中发生作用时,妇女就成了颠覆殖民地男性统治的工具。通过改良当地陋俗,殖民者在英法殖民地将棕色妇女从棕色男性手中解救出来。(40) 当西方殖民话语中的这把尺子变成一把利剑悬在晚清维新派的头上时,他们的妇女启蒙显现出在外界挤压下的急躁和羞赧。维新派要甩掉“品莲者”这一饱受抨击的帽子一跃而成为反缠足的倡导者。
这种以改良陋俗、提升文明为目标的妇女启蒙是应对西方殖民话语的选择之一。以伊斯兰世界妇女的面纱为例,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妇女启蒙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1899年,Qassim Amin出版了《妇女解放》(TAHRIR AL-MAR'A)一书。他鼓动妇女解放,倡导废除穆斯林妇女的面纱。1882年英殖民者占领埃及后,很快就认定穆斯林妇女佩戴面纱是陋俗,它象征着穆斯林文化的愚昧落后。Amin在他宣言式的著作中因袭了殖民者的论调,不加反省地批评穆斯林妇女的面纱阻碍了妇女地位的提升以及国家文明的进步。(41) 由此,在伊斯兰世界中引发了一场广泛而持久的面纱之争。一些改革派坚决主张废除妇女的面纱,以提高她们的地位;一些保守派或民族抵抗力量主张维护妇女佩戴面纱的习俗,并逐渐将面纱发展为抵抗殖民者的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殖民者在国内是女权主义运动的反对派,但在殖民地却积极参与陋俗改良和解救妇女运动。这些殖民者所进行的妇女启蒙带有明显的目的性,即颠覆殖民地的既有统治,树立自身的话语权威。故他们的妇女启蒙在某些殖民地遭到抵制。如在阿尔及利亚,穆斯林妇女的面纱变成民族主义者的标志和抵抗的象征。他们一方面以佩戴面纱作为民族抵抗标志;另一方面,民族主义者巧用面纱这一象征性标志,让妇女取下面纱,以麻痹殖民者并潜入殖民统治中心活动。(42) 可见,对待悬在头上的西方殖民话语的这把利剑,不同政见者的应对方式有所不同。妇女启蒙也在多种力量的交织或角逐中,服从于某种需要而变得工具化。
近来海内外学者纷纷在著述中对于戊戌维新派的反缠足话语进行反思。如高彦颐(Dorothy Ko)从后殖民主义的立场出发,对西方权势话语反戈相击。她从物质史的角度,系统地爬梳了中国妇女缠足的历史,并展示了清末民初废缠足运动中的复杂心态。(43) 在国内,随着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和姚灵犀《采菲录》的重印,一些学者重新审视戊戌时期的反缠足运动,努力发掘妇女的声音。而笔者以为,反思的关键在于突破妇女启蒙工具化的框架,还原妇女的主体性。
戊戌妇女启蒙思想的传统渊源
“一废一兴”是戊戌妇女启蒙的主旋律。梁启超在《论女学》中明确指出:“缠足一日不变,则女学一日不立。”(44) 废缠足是为兴女学做准备,而兴女学又紧密地与国家昌盛相关。在兴女学方面,维新派的妇女启蒙同样受到民族主义话语的支配,“欲强国必由女学”,“吾推极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45)。这种情形深刻地反映了清代女学思想的转变。梁氏强调维新派的女学与古代女学的区别:“古之号称才女者,则批风抹月,拈花弄草,能为伤春惜别之语,成诗词集数卷。斯为至矣。若此等事,本不能目之为学。……吾之所谓学者,内之以拓其心胸,外之以助其生计,一举而获数善。”(46) 一言以蔽之,维新之女学与母教、母仪之类的实学相关,并不指望妇女“晨夕伏案,对卷伊吾”。
虽然梁启超明确指出“古之才女之学”不能目之为学,但他不能否定“女学”古已有之。盛清时期,章学诚(1738~1801)与袁枚(1716~1798)曾就“何为妇学”展开争论。章氏在其著名的《妇学》篇中系统地梳理了女学的渊源。女学自上古三代有之,女学者始作俑于班昭之续《后汉书·艺文志》。(47) 章氏与袁枚的分歧在于,袁枚认为《诗》三百篇大半皆妇人女子之作,故而诗学为女学的正道;章氏则认为“古之妇学,必由礼以通诗。今之妇学,转而因诗而败礼”。章氏主张才女回归“妇才之古义”,即精通家礼推极至“四德”。由此可见,梁氏之否定才女之诗学与章氏的回归“妇才之古义”有相通之处。但二者又不尽相同,特别在妇学的目的上。
章氏明确斥责男子为学的功利性,认为妇女不必为名利所困扰,应该“为学而学”,以学问成其仁。换言之,章学诚凸显了女学的求道主题,强调妇女应熟悉、遵循礼学,养成圆满的“四德”。曼素恩(Susan Mann)教授在讨论章氏的《妇学》篇时,特别指出章氏之妇学与明清女教书所倡导的“女子实学”迥然不同。章氏并不着眼于母教,他更强调妇道之完备。相比之下,梁启超之女学显得颇为急功近利。他虽然也重视女学的道义蕴含,而其实际内容则不是章学诚强调的女德。梁启超讲求的女学之道更偏重于社会实用性,同样落实于民族国家的需要。这一点倒是颇近于明清以来的女教书传统。明代吕坤之《闺范》、清代蓝鼎元之《女学》以及陈宏谋之《教女遗规》等确立了“母仪”在女学中的重要地位。“王化始于闺门,家人利在女贞。女教之所系,盖綦重矣。……即至村姑里妇,未尽识字,而一门之内,父兄子弟,为之陈述故事,讲说遗文,亦必有心领神会,随事感发之处。一家如此,推而一乡而一邑,孰非教之所可及乎?”(48) 女学之对于乡里乃至国家“王化”的意义在陈宏谋的论述中已显而易见了。这种着眼于国家“王化”而推动女学的做法与梁启超的女学论如出一辙。
当然,在新的历史环境中,梁启超的女学论又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与明清女教书作者意在维系社会人心不同,梁启超强调:“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49) 维新派的女学是在万国竞争的环境下倡导的,因而着重强兵强种,“令国中妇人一律习体操。以为必如是,然后所生之子,肤革充盈,筋力强壮也”。显然,维新派的女学与其废缠足主张是一脉相通的,即利用妇女作为工具达到国家民族强盛。这与章学诚所倡导的“为学而学”,复兴“妇才之古义”,以及袁枚所提倡的陶冶情操的妇女诗学大相径庭。梁氏贬抑“古之才女之学”,而对古代女学的教化、经世内涵加以继承和改造。基于现实社会的需要而对古代女学传统进行了辨别和选择,直接影响到才女传统的断层。
故梁启超一方面贬低古之才女,一方面积极树立新女性形象。他认为“中国女学之废久矣”,号召二万万之女子向留美归国的康爱德女士学习,以中国之积弱为耻,请命救国。(50) 事实上,梁启超对女学的取向不仅代表了维新派的偏颇,而且影响后世。当梁氏着眼于女教书传统而论女学,形成“中国女学之废”的思维定式之后,清代丰富的女学内涵就被启蒙学者忽略不见了。五四学者陈东原指出:“清代学术文化,集了有古以来的精英,这时的妇女生活,也把二千多年来的生活加重地重演一番。到维新变政的时候,才渐有萌动的希望。”他还断言,“中国向来没有什么女子教育”。(51) 基于这种估价,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妇女启蒙一时间成了断根绝源的呐喊,而一些新文化人对传统学术文化的偏激态度也曾风行一时。
直到20年代,民谣运动开始,人们再次从《诗经》中发现了妇女的声音和女学之源。蔡元培、胡适、鲁迅及周作人等在传播西方思想的同时,也注意到本土的明清启蒙思想,积极介绍李汝珍、俞正燮等人的男女平权思想。(52) 尽管如此,五四时期的妇女启蒙像戊戌思想一样受民族国家话语的渗透。在救亡的启蒙主旋律下,女学传统,随着传统与现代的断裂而被宣布为废物。一句“批风抹月,拈花弄草”就抹杀了自古以来千百年的才女文化。那些“淋漓悲壮,若五更鼓角”的才女诗词便荡然无存了似的。(53) 这种倾向同样深深地影响到现代女学、妇女文艺,乃至关于妇女的价值尺度。戊戌妇女启蒙是将妇女纳入民族国家话语的重要起步阶段,对中国现代的妇女思想意识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注释:
① Joan Judge,“Reforming the Feminine:Female Literacy and the Legacy of 1898;” Hu Ying,“Naming the First ‘New Woman’,” Rebecca E.Karl and Peter Zarrow,eds.,Rethinking the 1898 Reform Period: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ange in Late Qing China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158~211.
② 贾伸:《中华妇女缠足考》,鲍家麟编:《中国妇女史论集》,台北稻香出版社1992年版,第189页。
③ 缪荃荪:《妇女裹足考》,《艺风堂文续集》卷四,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5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26页。
④ Dorothy Ko,“The Body as Attire:the Shifting Meanings of Footbinding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1997) winter:pp.8-24; Patricia B.Ebrey,“Gender and Sinology:Shifting Western Interpretations of Footbinding,pp.1300~1890”,Late Imperial China,20.2 (Dec.,1999):pp.1~34.
⑤(18)(19) Women's Conference on the Home Life of Chinese Women(Shanghai,1900),p.50,p.46,p.51.
⑥ Chia-lin Pao,“The Anti-footbinding Movement in Late Ch'ing China:Indigenous Development and Western Influence.” Research on Wome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1994)2:pp.145~148.
⑦(52) 李国彤:《明清之际的妇女解放思想综述》,台湾“中研院”近史所,《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1995年第3期,第143~161页。
⑧⑨(15)(17)(22)(27) Elisabeth Croll,Wise Daughters from Foreign Lands (London:Pandora Press,1989),p.46,pp.46~47,p.23,p.43,pp.58~59,p.44.
⑩ 《厦门戒缠足》,《万国公报》第5卷(1879),“清末民初报刊丛编之四”,台北华文书局影印本,第10册,第407~408页。
(11) 《缠足两说·正俗》,《万国公报》第7卷,第15a~16a页,“清末民初报刊丛编之四”,台北华文书局影印本,第24册。
(12) 《续论整顿印度国俗》,《万国公报》第13卷(1901),第2页,“清末民初报刊丛编之四”,台北华文书局影印本,第32册。
(13) 参见Valeria Steele,The Corset:A Cultural History(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1)。
(14)(51)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319、19页。
(16) 郑永福、吕美颐:《近代中国妇女生活》,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
(20) 《天足会会长担文夫人、总办古柏夫人致中国士大夫书》,《中外日报》1899年12月21日。
(21)(23)(29)(31) Antoinette Burton,Burdens of History:British Feminists,Indian Women,and Imperial Culture,1865~1915 (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4),p.109,p.121,p.48,pp.210~211.
(24) 严复:《原强修订稿》,王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页。
(25) 康有为:《请禁妇女裹足折》,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5~336页。
(26)(30) 参见林维红《清季的妇女不缠足运动》,鲍家麟编《中国妇女史论文集》,台北稻香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页。
(27) Croll,p.44.
(28) Francesca Bray,Technology and Gender:Fabrics of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 Susan Mann,Precious Records: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32) Dorothy Ko,Cinderella's Sisters: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pp.38~39.
(33)(34)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二十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45、146页。
(35) Yanagawa Masakiyo,The First Japanese Mission to America,tr.Junichi Fukuyama and Roderick H.Jackson (New York,1938),p.56.
(36) Sharon Sievers,Flowers in Salt:The Beginnings of Feminist Consciousness in Modern Japan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8.
(37)(38) 梁启超:《戒缠足会叙》,《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1页。
(39)(44)(45)(46)(49)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女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44、44、38、39、41页。
(40) 参见Frantz Fanon,A Dying Colonialism,New York:Grove Press,1965; Malek Alloula,The Colonial Harem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6)。
(41) Leila Ahmed,Women and Gender in Islam:Historical Roots of a Modem Debate (New Haven &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2):p.160.
(42) Diana Fuss,Interior Colonies:Fanon and Politics of Identification,Diacritics,(1994)24.2/3:pp.20~42.
(43) Dorothy Ko,Every Step a Lotus:Shoes for Bound Feet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 Dorothy Ko,Cinderella's Sisters: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
(47) Susan Mann,“Fuxue” (Women's Learning) by Zhang Xuecheng:China's First History of Women's Culture,Late Imperial China,13.1 (June 1992):pp.40~62.
(48) 陈宏谋:《教女遗规序》,《五种遗规·教女遗规》,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四部备要》本。
(50) 梁启超:《记江西康女士》,《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19~120页。
(53) 参见Li Guotong,Imagining History and the State:Fujian Guixiu (Genteel ladies) on the Road,Grace Fong and Ellen Widmer,eds.,The Inner Quarters and Beyond:Women Writers from Ming through Qing (Forthcom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