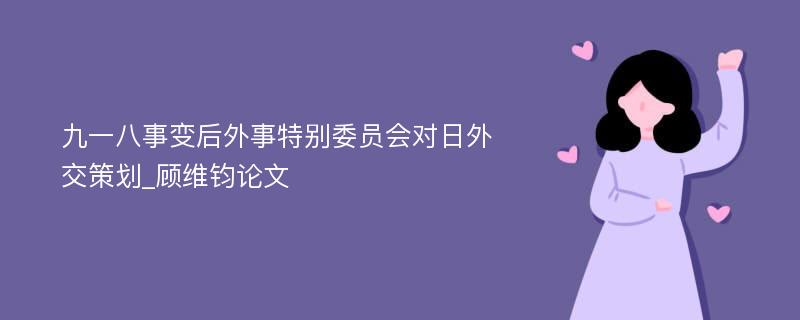
九一八事变后特种外交委员会的对日外交谋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交论文,事变论文,对日论文,特种论文,九一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特种外交委员会全称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它是九一八事变后,由蒋介石提议成立的对日决策研议机关,其成员由国民政府的一些军政要员和外交耆宿组成。外委会活动始于1931年9月30日,迄于1932年1月2日。可以说,在此期间国民党的对日政策皆出于此委员会。本文就其荦荦大者,作初步述论。
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9月21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从南昌返回南京后,立即召集会议,讨论对日方略。蒋介石主张以日本侵占东省事实,先行提交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以自卫最后之行动。会议讨论了军事、政治和外交问题。关于外交,决定成立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相关。(注:《蒋主席召集会议决定对日方略纪事》,1931年9月21日。见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台北1981年版,第281页。)九一八事变后,人民不满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纷纷举行各种集会和游行活动,要求国民政府对日绝交、宣战,并要求撤换外交部长王正廷。9月28日,愤怒的游行学生打伤王正廷。王正廷因而辞职。30日,蒋介石在中央政治会议上再次提议,以原政治会议外交组加入数人,组织特种外交委员会,每日开会,讨论外交问题。(注:原外交组成员有胡汉民、王宠惠、王正廷、孔祥熙、宋子文、吴稚晖、李石曾、王树翰、张群、朱培德、刘尚清、贺耀祖等12人。召集人为王正廷、宋子文。其中胡汉民避居上海,不愿出席,王宠惠在海牙国际法庭任法官,王正廷辞职休养,王树翰、刘尚清时在北平协助张学良,张群为上海市长,难以分身,能经常出席会议者只有孔祥熙、宋子文、吴稚晖、李石曾、朱培德等人。因此,蒋介石提出加入新人。新加入的有戴季陶、于右任、丁惟汾、邵力子、邵元冲、陈布雷。后来陆续加入的有颜惠庆、陈绍宽、刘哲、罗文干、顾维钧、杨树庄、程天放、熊式辉、朱兆莘、何应钦等。以戴季陶为委员长,宋子文为副委员长。)他说:“现在外交部长已辞职,政治会议对于外交更应注意,所以要组织委员会,以谋应付。”(注:中央政治会议第二九一次会议速记录,1931年9月3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印:《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以下简称《文献》),近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187页。)外委会遂于当日正式产生,并举行第一次会议。
外委会开会之时,中国参加国联会议代表、驻英公使施肇基根据国内训示,已于9月21日,正式向国联申述,提出请根据国联盟约第11条(保障和平义务)所赋予的权力,立采步骤,防止情势扩大,而危害各国间和平,并恢复事前原状,决定中国应得赔偿之性质与数额。日本代表芳泽表示日本政府采取不扩大事变政策,关东军已开始撤兵至南满路区域,并反对国联介入,希望中日直接交涉。在连续会议之后,国联于30日作出日本撤兵的决议。因此,特种外交委员会初期的工作主要是谋划如何依靠国联,达成日本撤兵。关于依靠国联,外委会在开会之初认为:“盖国联虽不可尽恃,亦非尽不可恃,此案发生后,中央所以尽力于使国联负解决此案之责任者,因维持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减少日本直接压迫中国之力量,途径惟在于此。日本一面声明不接受第三者干涉,而一面仍不敢不接受国联之决定,则知日本对于国联,亦甚顾忌也。”(注:《蒋介石致张学良副司令告以对日交涉方针案》,1931年10月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291页。此电是在10月6日由外委会讨论提出,以蒋介石名义发出,见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纪录,1931年10月6日。《文献》,第25页。)可见,外委会依靠国联的原因,一方面是判断国联有可能制止日本侵略,另一方面,中国当时内部分裂,军事力量远逊日本,无力抵抗,为减少日本的压迫,也只好把依靠国联作为解决问题之唯一途径。当时,国际上还有一支与中国东北和日本都有密切关系的重要国际力量——苏联。九一八事变后,国内许多方面提出与苏复交。为此,外委会第一次会议就讨论了对苏复交问题,外委会委员普遍认为:“应积极作与欧美联络之工作……并以对俄复交之空气促其与我接近”,“运用此次自然之空气为策略(与俄复交),而仍以联络英美为目的。”甚至有的委员担心“对俄接近是否失去英美之同情”,会“引起日本之恐怖”等,提出“因日本之压迫而遽然变更既定外交方针实有从长讨论之必要”,对苏外交,“可进行但不必立即实行”。(注: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1931年9月30日,《文献》,第5-8页。)宋子文在其后对美外交官的接触中就以中国有可能倒向苏联一边的暗示,催促美国对中日冲突立即采取明确的立场。宋子文说,中国人现在普遍表现出对苏联的友好感情,他本人和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担忧;当然,为了抵抗日本,中国或者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国联及九国公约签字国,特别是美国的介入,或者依靠苏联政府。(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1931年第3卷,华盛顿1964年版,第104,105页。转引自吴景平《论宋子文的对日强硬态度(1931-1933年)》,《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2期,第58页。)
外委会不主张立即恢复中苏邦交,固然有中苏刚刚断交,难以迅速转变政策的客观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过多的考虑了意识形态问题。(注:外委会委员邵元冲在日记中明确地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写道:“因据驻俄莫代表来电谓,苏俄极盼与我从速复交。众意复交固未始不可,然必附相当条件,如不能为共产党宣传等。”见1931年9月30日《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但无论如何,中苏关系未能在九一八事变民族危机严重之际得到迅速调整,影响了在外交上对苏联这一重要国际力量的运用,则不能不说是一个损失。国民政府只是在依靠国联的方针失败后,对苏外交政策才有所改变。
基于此种认识,外委会副委员长宋子文在第四次会议上,提出分电驻华英、法、德、意、西、波、挪等国公使请其派员调查东省事件真相,并视察日本撤兵情形报告国联以供参考。此前,施肇基曾在国联提议,请按希保成例,派遣调查员,因遭日本反对而作罢。宋氏之用意,与施肇基所提相同,即用国际力量督促日本撤兵。此后,外委会主要成员与西方驻华外交人员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第四次会议上,李石曾等人还提议在海牙国际法庭担任法官的王宠惠立即请假前往英美等国,以私人名义与当局说明东省事件与各国关系之重要,对美国尤须多做功夫。(注: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记录,1931年10月3日,《文献》,第19页。)对日本,外委会根据既定之诉诸国联方针,决定不采用直接交涉的办法。10月2日,外委会第二次会议议决由外交部电告施肇基:“在日本未撤兵以前,中国不能与日本作任何交涉,即在日本完全撤兵后,中国对日本之侵略与压迫,亦惟有信任国联始终主持公道,以维持世界之和平。”(注: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记录,1931年10月1日,《文献》,第10页。)不直接交涉方针的采用,一方面反映了外委会对国联的信赖,另一方面也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众普遍反对直接交涉,主张对日绝交甚至与日宣战之呼声强烈,以致国民党在决策时,不得不对此加以考虑。如外委会在电施肇基不与日本直接交涉的同时,还将上海朱庆澜等的全国民意反对直接交涉的通电转电施肇基,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日本政府虽在国联承诺撤兵,但日本军队却在辽吉继续扩大侵略。10月8日,日军飞机轰炸锦州。日军此举,扩大侵略之意昭然若揭。蒋介石训令施肇基向国联提出再行开会的要求。国联行政院遂于13日提前一天召开大会。施肇基提出请国联引用非战公约与美国合作,要求日本撤兵。日本则加以狡辩,指责中国排斥日货,要求与中国直接谈判,先订大纲协定,然后撤兵。所谓订立大纲,始自日本外相币原10月9日答复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要求日本撤兵的照会。该照会称:“两国间应速协定可为确立通常关系之基础大纲数点。此项大纲协定后,国民感情见缓和时,日军始能全行撤退于满铁附近属地内。”(注:日外相币原复驻日公使蒋作宾照会,1931年10月9日。国民党党史会编印:《革命文献》,第34辑,第904页。)但大纲内容,日方并未提出。日本所谓单独交涉,实为欺骗国际舆论,躲避国际干预,以武力压迫中国让步,获得利益的手段。外委会在接到日方照会后,多数反对直接交涉。但此时日本又在国联声言与中国讨论大纲问题,如断然拒绝,则容易失去国际同情,贻日本以拒绝撤兵之口实。对此,顾维钧认为:日本一面提出先订立大纲,一面扩大侵略,在外交、军事双方并进,着着逼我,我方若不速定全盘方针,拟就具体办法,从容逐步应付,转瞬之间失却国际同情,而形势转趋严重,单独应付更感不易,进退维谷,危险更不堪设想。(注:见顾维钧致张学良电稿,1931年10月14日。《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民国档案》1985年第1、2期,以下所引顾维钧等电文皆出此,恕不一一注出。)邵元冲也认为:“如果此案不日在国际联盟提出,我方应付之道,与其专在彼提案中求补救修正,不如自己准备提出一维持东亚和平之大纲。”(注:《邵元冲日记》,1931年10月16日。)10月15日,国联主席白里安召施肇基谈话,询问中国是否愿俟日军撤退时开始与日交涉,施肇基回答,兵未撤尽及责任问题未讨论以前不能谈判,如撤尽后开谈判,以理事会之参加为条件。白里安谓,撤兵并非以交涉成功为条件,中国将来对日提案允否,尽可自由。不能排除白里安的主张有运用灵活的外交方式解决问题的设想,但白里安却忽视了日本军事侵略威胁下,中国难以与日本进行平等谈判的现实。施肇基将此情况电告外委会,外委会讨论后,多数仍主张以先撤兵为最低限度条件。电施坚持。(注:见顾维钧致张学良电稿,1931年10月16日。)同一日,日本向白里安秘密提出5点谈判大纲。(注:5点谈判大钢是:(一)彼此不事侵略。(二)彼此制止国内敌视行动。(三)日本尊重中国领土之完整。(四)中国确实保护在满州各处居住或经营事业之日侨。(五)在满之中日铁路避免竞争与根据条约之各项路权问题之提议,投票反对(此处似不通顺,原整理稿如此,引者注)。见顾维钧致张学良电稿,1931年10月16日。)可见,无论是争取国际社会同情,还是与日本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国都必须认真对待日本大纲问题。
10月17日,外委会经过反复讨论后,作出对日本大纲问题的决议:“我方所取手段除顾全自身利权外,并须(1)不失国际同情。(2)不使日本军阀走向极端。暂时决定六项原则:(一)日本必须在国联监视之下撤兵;(二)中日将来交涉必须在国联照拂之下进行;(三)地点在日内瓦或其他国联所认为适当之地;(四)以后交涉必须在国联公约所定原则之下进行,不得违反下列三要点:(1)尊重中国独立、主权领土完全、行政完整;(2)实行门户开放机会均等;(3)促进远东和平,不得以武力为实行国策之手段;(五)日本需负此次出兵之责任;(六)日本所有任何提案我方保留修正及另行提案之权。”(注: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记录,1931年10月17日,《文献》,第62,63页。关于与日本交涉的问题,外委会委员长戴季陶在21日的中央政治会议上对交涉原则又作了详尽说明:“第一条是保持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及行政的统一;第二条是主张东三省门户开放,机会均等,日本不能破坏这个原则;第三条是以后两国间无论有何事故发生,不能以武力为解决手段,要遵从国联盟约、非战公约及其他国际公约办理;第四条是中日间一切问题都要根据上述三项原则,由两国政府将过去条约,酌量修改;第五条是在国联协赞之下,中日两国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时,要用其他国际方法解决,就是说要有中立国参加解决,将来解决地点,不在中国也不在日本,大概所谈的其他国际方法,是指用国际会议评判的形式。”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二九四次会议速记录,1931年10月21日,《文献》,第197页。)
中国对日本谈判大纲提出的具体对案,既坚持了日军不撤退不与之直接谈判的原则立场,也不失国际同情,在这个问题上赢得了外交主动。
10月16日,白里安提议邀请非战公约缔约国召开国联会议,未参加国联的美国列席。该提议以13比1的票数,不顾日本反对,得以通过。形势对中国有利。19日,外委会通知施肇基向国联提出:日军限10日内撤尽,日军撤退、商计接收办法及实行接收三事,均由中立国人员监视,接收办法以有关交接手续者为限。并告施肇基我方对日方大纲对案五条,及对日本拟提之案的意见。(注:见顾维钧致张学良电稿,1931年10月19日。)10月22日,国联理事会开会,提出议决草案。23日,外委会通过日内瓦通讯社获悉国联决议草案内容。大致是依9月30日决议案,援用国联公约11条及非战公约第2条之条文,请日本撤退铁道以外之军队,于下次理事会开会前完成之,请中国政府对于在满日侨,拟定保护生命财产之办法切实施行。行政院希望中日两国即行商议接收办法。并请中国政府邀中立国人员随同接收军队视察实行接收事宜,一俟撤兵告竣,中日即开始直接谈判一切悬案(其自9月18日以来发生之问题,及铁路问题,均包括在内)。行政院设立调解委员会或类似调解会性质之会。这一决议坚持了9月30日决议要求日军撤兵的立场,并规定了撤兵日期,由中立国人员监督撤兵等内容。中国方面的要求得到国联的支持。对此,外委会立即训令施肇基,准其接受。但对调解委员会问题,外委会也指出灵活方针,日方如坚持反对,我可主张改为国联翼赞之下。(注:顾维钧、刘哲致张学良电稿,1931年10月23日。)
24日,国联通过决议,限令日军于11月16日前撤兵至铁路区域内,中国重申保侨、中日谈判撤兵及其他事宜。13国赞成,只日本反对。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先撤兵而后谈判之目的得达,虽劳心,亦不无有得也。”(注: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134页。)
二
然而,中国之所得,只是道义上的。如特委会委员顾维钧所言,“国联结果,道德上固属胜利,实际成为僵局,未免令吾进退维谷,夜长梦多,殊堪忧虑”。(注:顾维钧、刘哲致张学良电稿,1931年10月25日。)因为,日本在国联表决中以一票反对,依照国联盟约11条,须一致通过。这表明日本决不会撤兵。
在日本拒绝撤兵的情况下,外委会仍积极工作,希望通过各方面努力,促使日本改变态度,达到撤兵的目的。国联决议的第二天,外委会就开会讨论如何促使日本撤兵的问题。颜惠庆委员认为,国联行政院决议案除一、二、三条规定抽象原则,第四条之甲项关于撤兵为日方应做之事外,其余第四条之乙项关于接收日兵撤退地面及保证在该地日侨生命财产安全为中国应做之事,第五条关于协商撤兵及接收办法之细目,第六条关于撤兵完成后之交涉为中日两方合做之事,似应即请政府令知各机关及早准备。(注: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记录,1931年10月25日。《文献》,第79页。)他试图由我方自动完成我方责任,争取外交主动。此外,外委会一面令施肇基随时与白里安接洽,设法促使日方变更态度(注:顾维钧致张学良电稿,1931年10月25日。),另一方面也请各列强分头劝告东京开始自动撤兵。(注:顾维钧致张学良电稿,1931年10月25日。)27日,外委会开会,决定电蒋作宾公使根据议案第五项催日本商订撤兵接收事宜。(注: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记录1931年10月27日。《文献》,第82,83页。)
10月26日,日本发表《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二次政府声明》,拒绝撤兵,继续欺骗国际社会,提出“为了确保在满洲的帝国臣民的安全,首先只有采取措施,消除两国国民的反感和疑惑,并准备与中国政府协商这方面所必要的基本大纲”(注:《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2页。),再次祭起直接交涉的“法宝”。但与10月16日日方密告国联主席白里安者不同,其大纲第五条改为“尊重条约上所规定的帝国在满洲的权益”。顾维钧认为该声明书“末端措词,日方似已稍让步,将其基本大纲与撤兵接收事宜并为一谈,准备与吾国开议。如果日本诚意转圜,不难就其提议谋一无损双方体面而有利吾国主张途径,以避僵局”。(注:顾维钧致张学良电稿,1931年10月28日。)10月29日,外委会讨论日本是否有转圜之意。蒋介石参加,他认为:“日本对于此国联决议坚不接受已甚明显,以后情势实较未决议前更为严重。自国联决议案经行政院会员国除日本外全体一致通过,日本态度非退即进。自日本对华传统政策上看,退步必所不甘,自非更进一步不可。以后情形如何变化,正难预料。本庄宣言所谓头可断,兵不可撤,非故作悲壮,其居心确实如此。”对此,蒋介石提出应对方针:“吾人处此情状之下,单独对付既有许多顾虑,而一方在国际上已得到一致同情以后,自应信任国联,始终与之合作,而为国联本身设想,倘此事无法解决,以后世界和平一无保证,国联即可不必存在。”蒋介石此时对国联仍抱有信心,会议推选宋子文等8人修正中国政府对外宣言,加入下列意思:1.尊重本月24日国联行政院决议;2.决议如失败,即是国际信义破产,国际和平破裂;3.引用华府会议以来各种国际公约尊重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及保障和平维持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之约言;4.日人在东省扰乱事实;5.关于条约问题已由施代表建议仲裁办法;6.引用总理对中日关系之遗训表示我国固有方针。(注: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记录,1931年10月29日。《文献》,第89页。)前4条表示强硬不屈,5、6条表示仍有转圜余地。
但实际上,中日间已无转圜之可能。因为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膨胀,欲壑难填。姑不论日本在东北始终不停的侵略铁蹄,即其直接交涉的大纲也如同软刀,直接危及中国的主权完整和国家独立,如戴季陶所言,“前三条说得冠冕堂皇,没有什么,而第四、第五两条便如毒药一般”。(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二九四次会议速记录,1931年9月21日。
《文献》,第196页。)驻日公使蒋作宾也认为:“吾国承认一条,即将国家独立之资格取消。”(注:《蒋作宾日记》,1931年10月20日,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可以说,是日本之所为,彻底关闭了直接交涉的大门。11月2日,蒋介石召见外委会成员戴季陶、李石曾,于右任、吴稚晖,谈政府对日方针:日军未撤尽以前,不与日方作任何接洽,即将来撤兵后如何开议,手续问题亦不拟先表示,另用间接方法催促撤兵。宋子文亦谓对日以镇静态度为宜。(注:顾维钧致张学良电稿,1931年11月2日。)间接促使日本撤兵的方法和保持镇静就是仍然依靠国联而不与日本进行直接交涉。
11月初,日军开始侵略黑龙江。宋子文提议速电施肇基请白里安迅速设法处理日军进攻黑龙江事件,并探寻白氏是否将依盟约15条办理。(注: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记录,1931年11月6日。《文献》,第110页。)国联秘书处转达白里安来电,表示行政院及一般舆论对黑龙江事件之忧虑,希望中日政府注意双方代表在国联所作之保证,从速训令各本国军队设法避免冲突。外委会决议,电施肇基声明中国始终遵守约言。(注: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记录,1931年11月7日。《文献》,第112页。)此时,中国仍坚信国联可能对日采取强硬措施,如宋子文即根据美国已通知国联绝对赞成国联9月30日决议案,愿与国联用任何方式合作以达目的,及美国已派代表赴东省参观日军撤退,并允将该代表之报告,随时电告国联的情况,判断“国联当可采取强硬态度,必不致如从前之畏首畏尾”。(注:宋子文致张学良电稿,1931年11月8日,《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等致张学良密电选》,《民国档案》,1985年第1、2期。)
与此同时,外委会还采取其他途径努力促使国联对日强硬。11月5日,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电外委会,谓白里安答复芳泽宣言发出后,日本朝野颇滋忧虑,现内阁恐难支持,有由斋藤实改组超然内阁以图转圜之说。(注: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记录,1931年11月5日。《文献》,
第104页。)白里安答复芳泽,即白里安对日本10月26日《宣言》的答复,其中,对日方观点,多有驳斥。外委会将此消息转电施肇基及重要各国驻使,说明日本军阀专横,政府无法制止。如国际对日空气继续强硬,可望和平,否则事变即有扩大之虞。(注: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记录,1931年11月6日。《文献》,第106页。)
不过,在依靠国联的同时,外委会也电请张学良转令黑龙江省主席马占山坚守防地,尽力自卫。(注: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记录,1931年11月9日。《文献》,第114页。)蒋介石于11月12、19日连电马占山,认为马占山的自卫行为,“甚属正当”、“为国争光,威声远播,中外钦仰”,并表示催张学良派兵援助。(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第300,301页。)这是对不抵抗政策的修正。由此可见,在继续依靠国联的同时,国民党对日政策开始出现变化。
三
在日本拒绝国联撤兵决议,继续扩大侵略的情况下,11月16日,国联行政院第三次开会。但会议召开仅20分钟,就宣布休会,没有对日本侵略进行任何讨论,然后,会议进入非正式交涉。这一行为表明,国联此时无力也不愿采取强制手段制止日本侵略。对此,外委会有准确判断,邵元冲认为国联“观察形势似有被日本软化之意”。(注:《邵元冲日记》,1931年11月17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版。)顾维钧则更明确指出:“各国不能以实力制止日本,是极显明之事。”(注:顾维钧、刘哲致张学良电稿,1931年11月18日。)18日,英国外长西门与施肇基谈话,提出四点:(一)向日本庄重声明,中国尊重满洲之条约义务。(二)照会列强及美国,重述第一点。(三)中日间同意指派一铁路专门委员会,主席由国联指派,由中日委员人数相等组织之。其目的在欲达到一满洲铁路营业之协定,防止不良竞争,以力求得一如同一系统之营业协定。(四)在保证第一、第二点并签订第三点后,即实行撤兵。(注:顾维钧、刘哲致张学良电稿,1931年11月18日。)其虽为私人谈话,但偏袒日方的态度,明白可见,似乎在九一八事变中,中国是过错一方。19日,外委会开会,研究西门四点。蒋介石亦出席会议。经讨论,一致通过六点对案:“(一)中日互向行政院及美国声明尊重国际条约原则。(二)关于条约之任何问题或争执,应提交行政院或中日合组之和解委员会。(三)对于西门所提出之第三点,关于行政院派代表及国联协助之建议,主张接受,惟末段修改为‘以谋共同利益’。(四)对于撤兵问题,应规定完成日期及一定期间内之各种步骤。(五)中立代表协助各地之撤兵接受。(六)中日间一切商议,最好在中立地点。”(注:顾维钧致张学良电稿,1931年11月19日。)此六点与西门四点针锋相对,可见,外委会显然对英代表的主张不满。
11月21日,日本向国联建议由国联派遣调查委员会至东省调查,并声明俟安全有保障再撤兵。至调查范围,不可限于东三省,但对于军事行动,不得有所主张,对于中国、日本直接交涉不能干预。11月21日,国联主席白里安告知施肇基,国联决议不能限制日本撤兵期限,惟责成停止军事行动,任何问题可提请委员团处理,并谓此为最优方案,如中国再有要求,势必破坏理事会一致之态度,故劝中国同意。施肇基向外委会汇报后,戴季陶、宋子文、顾维钧当即商议,均认为不能承认。(注:顾维钧致张学良电稿,1931年11月21日。)第二日,外委会开会,蒋介石参加。经长时间讨论,决定不能赞成日方和白里安的提议,指出日方破坏盟约第十条、十二条、十三条,而得引用第十六条诉请国联制裁。(注: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第四十七次会议纪录,1931年11月22日。《文献》,第149,150页。)会议还通过对国联提案七条:(一)国联即日制止日本军事行动。(二)日本于两星期内完成撤兵。(三)日本撤兵后,中国保障东三省日侨生命及财产之安全。(四)国联与美国共同组织中立国代表团,监视撤兵与接收办法,并调查情形,报告于第七项所规定之国际会议,以供参考。(五)中日两国,双方重申尊重国际条约之原则,尤以《国联盟约》、《非战公约》、《九国公约》为要。(六)中日两国在中立国代表参加视察之下,即日开始商订接收详细办法及保障东三省日侨安全办法。(七)中日间关于东三省一切问题,本保障东亚和平及以国际合作方法,促进东三省经济上的发展,由美国与国联共同召集有关系各国之国际会议,根据《国联盟约》、《非战公约》、《九国条约》之原则讨论解决之。(注:顾维钧、罗文干、刘哲致张学良电稿,1931年11月19日。)外委会并训令施肇基,向国联切实声明,以中国此时之坚持尊重盟约,实不啻为国联而奋斗,若国联自堕其责任,则国联地位将丧失无余。(注:《邵元冲日记》,1931年11月22日。)
11月24日,施肇基探得国联预备议决草案,大致为:行政院指派三人之委员团负责就地研究情形报告行政院,中日各派一辅佐人员为代表,如当事国谈判,委员团不得干预,对于各方军事行动之监视,不在委员团范围之内。外委会获悉后,即刻电施肇基坚决主张下列三原则:一、严厉制止日军侵略行为。二、在一定期间内撤兵。三、在中立人员监视之下撤兵。并声明上次所提七条办法须以此三原则为基本,如国联不能接受,其他一切都谈不到。(注: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第四十九次会议记录,1931年11月24日。《文献》,第157页。另见顾维钩、刘哲致张学良电稿,1931年11月24日。)中国对国联态度转趋强硬。
11月初,日军进犯锦州迹象日显。锦州为东北通关内之重要交通要点,沈阳失陷后,辽宁省政府及其他军政机关俱迁至此,是中国政府在东北最后一个重要据点。日军为策应攻锦,在北宁路上的天津也不断制造骚乱。25日,新民陷落,锦州形势危急。当日,外委会讨论锦州问题,顾维钧致电张学良,“锦州一隅如可保全,则日人尚有所顾忌,否则东省全归掌握,彼于独立运动及建设新政权等阴谋必又猛进,关系东省存亡甚巨……是以锦州一带地方如能获各国援助,以和平方法保存,固属万幸,万一无效,只能运用自国实力以保守”。顾氏之电,即外委会讨论之结果。(注:顾维钧、刘哲致张学良电稿,1931年11月25日。)29日,顾维钧、宋子文再电张学良“如日方无理可喻,率队来攻,仍请吾兄当机立断,即以实力防御”。(注:宋子文、顾维钧致张学良电稿,1931年11月29日。)对于天津,外委会认为“天津于政治上,军事上关系至巨,倘日人相逼太甚,我方为争持国家人格计,至万不得已时,自应实施正当防卫”。(注:顾维钧、刘哲致张学良电稿,1931年11月28日。)
11月底,日本欲完全占领东三省之野心完全暴露,而国联无力制止日本侵略之软弱也完全暴露。11月30日,外委会对形势作出如下判断:
判断日本之军事政策,必定达到完全占领东北之目的而后已。其外交当局最初与军事当局意见不同,但在第二次行政院决议之后,外交当局,便已逐渐追随军部行动,现在外交完全为军略所支配,故一切观察,应以军事为前提。
判断日本以完全占领东三省,驱除中国固有之政治军事势力为主要目的……
判断国联之目的,始终在尽力削除日本上项计划之实施与成功,英法皆同……但各国重要政策,因计划皆未完成,故此次决不对日作战。因此国联不能采取任何有力制裁,现在国联努力已将用尽,但即使因日本武力政策之猛进,而国联陷于困境,亦决不致因此而倒。
判断美国态度,至今虽极力避免表示意见,但将来必要时,有运用九国公约出而对日本作有力抵制之可能……据此,外委会提出处理时局的方针:
此时一切政策,以团结民心保持政府人民之信任为根本要图。对外策略,第一,中国无论如何,决不先对日本宣战;第二,须尽力维持各国对我之好感;第三,须尽力顾虑实际利害,至万不得已时,虽在军事上为民意而牺牲,亦所不惜,惟必须筹画取得真实之牺牲代价。故对于锦州方面,如日军来攻,只有尽力抵抗,以树立今后政府在人民间之信仰维系全国人心,俾中国不致因全国瓦解而亡,且必须如此,方能取得国际上较好之地位。对于天津之事件,必须以力保省政府完全之地位,一以巩固人民对政府之信任,一以使各国知中国政府保持国权之决心。(注: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第五十四次会议记录,1931年11月30日。《文献》,第169页,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戴传贤上中央政治会议报告,《戴季陶先生文存》,第373,374页。)
外委会对日本之侵略目的、国联及美国对日本之态度的判断是完全准确的,所提之当前外交策略亦为得当。不过,从外交上看,外委会依靠国联以迫使日本撤兵的一系列外交谋划,至此已走到尽头。
但是,中国当时军事上的困难并不比外交上的困难少。当时的军事情况,如外委会12月8日讨论如何应付目前紧急情势时,朱培德发言所谈到的那样:“锦州军队不应撤退,固属不成问题。惟据军事专家推测,前方一经接触,至多恐不过维持一星期左右。而关内队伍无论从何方面计划,皆无出关援助之可能。”(注:中央政治会议特种外交委员会第五十九次会议记录,1931年12月8日。《文献》,第173页。)即张学良难以锦州一隅抵抗暴日蓄意之侵略,而国民党中央也没有下定最后抵抗之决心。这样,虽然外委会反复劝告、国民政府也发出命令,请张学良守卫锦州,但在锦州前线却没有形成对日本侵略的有力抵抗。锦州于1932年1月2日迅速失陷。至此,东三省全部沦亡。外委会谋划之军事抵抗也最终落空。
弱国无外交,但弱国却比强国更需要外交,因为国弱,更需外交上的纵横捭阉,联合与国,利用敌方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弥补己方实力上的不足。九一八事变后,特种外交委员会依靠国联,采取不与日本直接交涉的方针,群策群力,殚精竭虑,在形势瞬间多变、关系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中与日本打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外交战。通过外交这一无形的斗争,中国赢得了国际的支持和同情,使日本在国际社会日益孤立。但,外交的成功既取决于外交工作本身的艺术、经验和努力,更需要实力为运用外交手段的基础。20年代末,30年代初,西方国家普遍处于经济恐慌之中,又对日本侵略的严重后果缺乏深刻认识,不愿采取有力手段制止日本侵略,而中国更是因种种原因,采取了不抵抗政策。这样,外委会从一开始就不具备获得成功的条件,种种外交谋划亦终归落空。
标签:顾维钧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历史论文; 文献论文; 张学良论文; 宋子文论文; 蒋介石论文; 施肇基论文; 九·一八事变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 西安事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