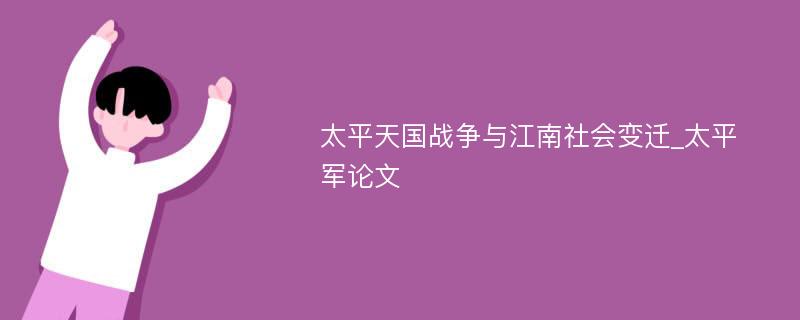
太平军战事与江南社会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军论文,江南论文,战事论文,社会变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4.9;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3)01-0093-10
1853年2月,太平军由武昌东下江南,帆幔蔽江,炮声遥震,沿江州邑,莫不望风披靡(注:张德坚:《贼情汇纂》卷5,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太平天国》(三),第141-142页。)。3月20日,太平军挟千里席卷之势,长歌涌入金陵,开始建造“人间小天堂”。在此后的10多年时间里,太平军继续西征、北讨和东进,战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狂飙所及,庐舍为墟,遍地瓦砾。江南地处风暴的中心,“被难情形较他省尤甚,凡不忍见不忍闻之事,怵心刿目,罄笔难书,所谓铁人见之,亦当堕泪也!”(注:寄云山人:《江南铁泪图》,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版,第3页。)天国的将士们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人间天堂”,但它掀动的大海波潮退去后,留下来的却是一种难以复原的历史变动。
生灵涂炭:人口曲线上的罕见低谷
唐德刚教授在《晚清七十年·太平天国》的“卷首语”中写道:时至晚清,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政府的统治大机器彻底锈烂,社会也百病丛生。广东洪秀全,一个典型“三家村”的土塾师,科场失意,转以“拜上帝会”之名于广西聚众起义,企图建立一个梦想中的“小天堂”。一群狂热信徒被逼上梁山,化宗教信仰为政治力量,终至酿成死人无数的“太平天国”大悲剧。唐教授用“死人无数”四字来形容这场大悲剧,至于在大悲剧中究竟死了多少人,唐教授没有说。
在这场规模空前的内战中,安徽全省、江苏南部、浙江西部和江西北部是受蹂躏最惨的地区。其中,安徽省是太平军和清军的必争之地,战场几经易手,争夺极为惨烈,受创最为深重。譬如,皖南的广德县,就几乎损失了所有的人口。光绪六年(1880)编纂的《广德州志》以沉重的笔触记录了这场惨绝人寰的“奇祸”:
自庚申二月(1860年3月)贼(太平军)窜入州境,出没无时,居民遭荼,或被杀,或自殉,或被掳,以及饿殍疾病,死亡过半。存者至于无可托足,皆迁避于南乡篁村堡。堡民负险拥众,其地倚山,四面环抱,廓其中而隘于路口,故易守。贼屡攻不克,益壮其声势。最后为贼酋洪容海率党攻破,大肆屠戮,居民无得脱者。庚申至甲子五年中,民不得耕种,粮绝,山中藜藿薇蕨都尽,人相食,而瘟疫起矣。其时尸骸枕藉,道路荆榛,几数十里无人烟。州民户口旧有三十余万,贼去时,遗黎六千有奇,此生民以来未有之奇祸也。(注:光绪六年《广德州志》卷60,第25页。)
短短5年间,广德县人口从30余万锐减至6千多,说是“奇祸”一点也不为过。当然,人口的锐减并非都直接死于战争,可能更严重的还是间接地死于战争。所谓“间接”,是指因战争而导致的灾荒使大量的人口饥饿而死,或者因大灾之后瘟疫流行而导致的人口大规模死亡。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许多战区都发生过严重的疫情,而且死于疫情的人口往往超过直接死于战争的人口。还有一个因素也不能忽视,那就是大量居民出于避乱而背井离乡,使人口锐减。
广德县的“奇祸”只是一个缩影,那样的悲剧同样发生在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其他地区。据中国人口史学者何炳棣教授介绍,与广德同处皖南地区的徽州首县歙县在太平天国期间人口至少减少了一半,即从战前的近62万人降至战后的30万人。胡适的父亲胡传的自传证实:在整个徽州府,人口急剧减少并非个别的现象。他曾于1865年(即太平天国失败后1年)被族人推选负责统计幸存的族人,经过数月的彻底调查,他吃惊地发现战前的6000多族人仅剩下1200人。换句话说,幸存者只有原来的1/5。在歙县以北200里的南陵县,受曾国藩委派负责当地善后事宜的一位士绅提供的报告称,他的族人幸存者仅1/4。1851年,浙江人口约为3000万,乱后10年,即1874年,已不足1100万。
对于太平天国战争所导致的人口损失,著名的地理学家、旅行家李希霍芬男爵对太平天国战后的浙江和安徽南部所作的调查报告,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目击者触目惊心的记录:
尽管土壤肥沃,河谷地带已完全荒芜。当你走近一组隐蔽在树丛后的粉刷得洁白的房屋时,会明白它们已成了废墟。这是当年富饶的河谷地带变成荒芜的有力见证。不时可见到临时搭凑的小屋,暂为一些可怜的穷人的栖身之处,他们的赤贫与周遭肥沃的田地适成鲜明的对比。我提到过的城市,如桐庐、昌化、于潜、宁国等地到处都是废墟,每城仅数十所房屋有人居住。这些都是十三年前的太平天国叛乱所造成的。联接各城的大路已成狭窄小道,很多地方已长满高达十五英尺的荒草,或者已长满难于穿越的灌木丛。以往河谷中人烟稠密,这从村庄的数量之多和规模之大可以得到证明;所有原来的房屋都以条石或青砖建造,有两层,其式样之好说明以往这里原是非同寻常的富裕和舒适。无论河谷中的田地,还是山坡上的梯田,都已为荒草覆盖,显然没有什么作物能在这枯竭的土地上繁衍。旧日的桑田因缺少照管,一半已经荒废,说明了蚕桑是以往居民们的主要产业之一。其他地方长满了老龄板栗组成的森林。……
很难想象对生命财产的破坏有比这个地方更可怕的,可是这些地方只不过是遭遇同样命运的广大地区中很小的一部分。看过像这样的地方,人们才能了解东亚的种族在感情极度冲动的时候,是能够摧残破坏到什么地步。毫无疑问,历史上曾多次沦为屠场的浙江省所遭受的生命损失必然与最近这一次(指太平天国战争)同样可怕。我在不同的地方总是打听在太平天国叛乱中幸存的人口的百分比,一般说每百人中仅有三人幸存。西天目山庙中以前有四百和尚,乱后仅三十名幸存,但乡村和城市中幸存的比例更低。大多数人是在逃往深山后死于饥饿的,但死于太平军之手的男女及儿童数量也极大。(注:冯·李希霍芬男爵:《浙江、安徽省书信》,转引自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40-241页。)
李希霍芬男爵的描述是依据自己的访问调查得来的,而不是凭空虚构出来的,它的真实性是用不着怀疑的。因为它是真实的,所以他的描述就更显示出这场悲剧的沉重份量。
其实,不仅安徽、浙江如此,苏南地区的人口损失同样惊人。
江苏省的很多方志依旧例仅载丁数,这使太平天国时期江苏人口损失的统计增添了难度,但从丁数的变化中也可以大致估算出实际的人口损失数量。一向以地少人多著称的苏州府和常州府金匮县的人丁数1830年时分别是341万和26万,到1865年已分别减至129万和14万。江苏西南高淳县的人丁数1837年时为188930,到1869年已降至55159。南京附近的金坛县战前人口超过70万,战后城中仅剩3000人,四乡仅有3万人。浏河县1781年时已有32万人,到战后的1882年犹不足12万;溧水县1775年时已有23万人,到1874年已不足4万。据统计,1851年,江苏人口约为4430万,至乱后十年,即1874年,竟减至2000万不足。曾经人满为患的苏南如今成了人烟寥落之区,那令人羡慕的富庶繁华随之化作了昨日的故事,取而代之的是一派“愁惨气氛”。《中国之友报》的副主笔在苏州陷落后曾由上海前往苏州考察,他所写的《苏州旅行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位亲眼目睹者的真确记述。在这篇游记中,他写道:“我们离开上海后,沿途经过了低洼的平原,其间河道纵横。这片中国最富饶的土地,一直伸展到天边,我们的视线除了时或为不可胜数的坟墓、牌坊和成堆的废墟所阻外,可以一直望到天边的尽头。荒芜的乡间,天气虽然优美,但显得沉郁幽闷。举目四望,不见人影。这片无垠的田野,原为中国的美丽花园,今已荒废不堪,这种景象更加重了周围的愁惨气氛,好像冬天要永远留在这里似的。”(注:呤唎著,王维周、王元化译:《太平天国亲历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01页。)这段近乎白描的写实文字比数据更具象地外化了内战的狂飙过后苏南地区的死寂景象!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大悲剧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一个谜。1883年,美国传教士哈巴安德称,太平天国战争造成的人口损失为5000万,而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则估计太平天国战争导致的人口死亡数为2000万。这是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所作的估算,并没有多少事实依据。中国现当代人口史学者在确凿的史料基础上对此重新进行估算,有的根据太平天国前后《户部清册》所载的户口数,认为从1851年到1864年中国人口锐减40%,绝对损失数量达1.6亿;有的学者则将战前的人口数据与1911年宣统人口普查资料进行对比研究,认为太平天国战争给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五省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至少达5400万,如果再考虑到太平天国战争的其他战场湖南、广西、福建、四川等省的人口损失,那么太平天国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人口损失至少在1亿以上,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达7000万。如果上述结论成立,单就人口损失而言,太平天国战争就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而且也是“世界上最具灾难性的内战”(注:魏斐德著,王小荷译:《大门口的陌生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必须指出的是,太平天国期间中国人口的过量死亡并非都是太平军所致,许多史料显示太平军在一定程度上同情穷人,有时甚至宽容富人,而曾国藩和他的同僚们则坚决主张将太平军斩尽杀绝,即使对叛变投降者和俘虏也不例外。李秀成在被俘后写的自述中回忆:如果曾国藩及其部将对说广西(太平天国的发源地)话的太平军采取纳降、而不是坚持一概杀戮的话,太平军早已自行解体了。湘军和淮军除了一再上演这样的兽行,还在安庆、苏州、天京等地陷落后进行过惨无人道的大屠城。在这场空前的浩劫中,死于清军之手的人口绝不亚于死于太平军之手。
大移民:废墟上的新主人
与人口锐减相伴偕来的是土地的大量抛荒。据苏南地区各厅州县册报,“抛荒者居三分之二”;浙江一省,荒芜田、地、山、荡多至112366顷;各省之中又“以皖南北荒田为最多,其它地方亦以皖南为最盛,如宁国、广德一府一州,不下数百万亩”。换句话说,江南地区战后已化作一片废墟。
然而,这些地方一向是朝廷赋税的命脉所在,田地的大量抛荒势必影响到朝廷的财政收入。因此,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已成为当政者的首要急务。而要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就必须有相应的劳动力作保证。由于战争造成了巨量的人口损失,而巨量的人口损失又必然导致劳动力的奇缺。重建家园、恢复生产与劳动力奇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在这种背景下,“招垦”成了唯一的选择。朝廷一而再、再而三地下令招垦,地方上的父母官更迫不及待地设立招垦局或招垦分局,制订各种优惠的招垦政策,鼓励和吸引各地移民前来垦荒。如安徽凤阳、定远两地的招垦分局就规定:“如有外来客民,情愿领田耕种,取具得保,由总局察验实系安分农民,一体借与牛力种子,准其开垦。”尽管朝廷和地方当局都以招垦为要务,但最初并不顺利,所谓“求之汲汲,而应者寥寥”。战后长江下游许多地方的人口移入的确是一个逐渐进行的、非常缓慢的过程。其中的原因很复杂。有移民耕种稻田能力的制约,每人一般很难超过二三英亩(一二十亩);也有垦荒资金的限制,长期抛荒的土地需要垦复,对幸存的一贫如洗的田主和初来乍到的移民来说,垦荒所必需的资金是他们面临的共同的难题。当然,还有新移民对地权的疑虑:前来垦种荒地的人都是一些穷苦农民,他们希望自己垦种的荒地成为自己的财产,但荒地中绝大多数都有“原主”,如果这些原主还在,新移民们知道这些荒地将来不可能成为他们自己所有,自然不肯“赔贴心力,代人垦荒”了。为了打消垦荒者的疑虑,从1869年起,主持江苏垦务的官员特别订立了一项章程,规定:“必以无主之田招人认垦,由政府发给印照,永远归垦荒者所有。自垦熟之年起,三年之后再交粮纳税。”浙江严州当局则规定,政府招募棚民垦种之地,如果三年内无业主指认,则准许垦户“作为己业,过户完粮”。如果遇到投机取巧的业主,等移民们将荒地垦熟以后,再向政府呈报,当局将他进行处罚,即把他所耕种的田亩的一半罚归垦户所有。这一类规定从法律上保证了垦荒者的合法权益,使响应政府的招垦令而前来垦荒的人有机会成为荒地上的新主人。对于新移民来说,这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于是,受这些保护性优惠政策的吸引,一批又一批移民开始从湖北、湖南、河南和苏北等地,从四面八方翻山越岭涌到苏南、浙江、安徽和江西,在荒芜而陌生的土地上刀耕火种,建立新的家园,由此出现了江南历史上罕见的大移民。湖北一些县整村整村的农民蜂拥而来,希望能耕种无主良田,占有无主的好屋。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争垦”的现象,譬如湖州就曾闹出了“客民入境,争垦无主废田数千亩,讼呶呶不休”的事情,比之最初的“应者寥寥”,自是另一番气象了。据估计,战后苏南地区接纳了大约160-260万移民人口,主要来自安徽、湖北和苏北,外省移民约占100万;浙江省大约接纳了132万移民;安徽接纳的移民最多,约有264万人,其中皖南地区接受的移民人口约为136万,皖北地区接受的移民约为128万。
皖、苏、浙、赣四省一向是人烟稠密的地区,特别是江浙地区地少人多,长期以来只有向外移民,极少向内移民。但太平天国战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大逆转,在一派废墟上一下子冒出了大量的新移民。新移民的大量涌入,对于饱经战乱之苦的长江下游地区社会生产的恢复和战后的重建注入了新的生力军,他们对江南城市和乡村的复兴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新移民的到来也给这些地区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移民们明白他们讨价还价的能力,常常强加条件,有时甚至采取威吓手段;解甲的士兵和移民中的雇农对农村的太平安宁是更大的威胁。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以地权为焦点而日趋激化的土客矛盾。这种矛盾可以说是无时无之,无地无之。从四面八方涌入的新移民往往成群结队,他们反客为主,有恃无恐地“择其屋之完好者距而宅之,田之腴美者播而获之”,由此造成了“有主之业,百不获一;侵占之产,十居其九”的既成局面。移民与土著之间的矛盾由此激化,为争地权而发生的械斗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一火延及数十家,一斗毙及十余命”已不是什么个别的现象。移民的强悍蛮横导致了土著异常的不满,他们往往团结起来,与移民展开肉搏。1883年,浙江北部就曾发生过土著屠杀成百外来移民的悲惨事件。还有一些是因为土著对移民的成见而导致的冲突。苏南地区的土著对来自两湖地区的移民就存有深深的敌意,因为太平军战士中的大部分是来自两湖地区的农民。但自两湖地区及河南一带来的移民是政府出面组织的,土著有怨气,却也没有办法。矛盾因此而越积越多,越积越深。当时有人曾作《田亩记》,其中提到招垦一事时说:“小民生计,上(指政府)安能尽为代谋?招之自下,顺民情者,主爱客;招之自上,倚官势者,客压主。或占种而不顾,或负租而不还,垦辟以后,擅予他人,取其天赀,田主不能过问。……若初垦之时,斗狠强夺,受害之状,官弗见也;既垦之后,起征潜逃,代偿之,官弗闻也。至于显而争讼,隐而诱窃,强而劫略,弱而逃逋,遭累更不胜言。”(注:光绪八年《宜兴荆溪新志》卷3,《田亩记》。)这是政府招垦所带来的弊端。移民的“斗狠强夺”当然不是政府所能容忍的,说政府不闻不问,有点言过其实,但移民也成为该地区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和国赋的实际承担者,因此,政府有意无意地规避土客之争,也是事实。总之,随着大量移民的涌入,如何调停土客纷争,是地方当局痛感棘手的社会难题。曾任两江总督的沈葆桢1877年以后多次上奏朝廷,说即使以推迟经济恢复为代价,停止移民也是持重的措施。可见,当时大移民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严峻性。
太平天国失败后,从各地迁入江浙皖赣的移民人数已经不少,但远没有达到饱和的地步。与这些地方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巨大需求相比,相距依然非常遥远。为了缓和劳动力的严重不足,苏南一位开明的绅士赞同购买西方农机和拖拉机,用改进生产工具来提高劳动效率,解决人少地多的矛盾。两江总督刘坤一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一份奏折中指出:在苏州新阳县仍有约10万亩以前课税的田地抛荒。与此相对应,原来寸土寸金的江南如今却出现了“垦种乏人”的尴尬局面。这个残酷的现实,一方面说明了太平天国战争曾经给全国最富庶、最发达的江南地区造成多么巨大的破坏;另一方面又势必导致土地的严重贬值,李希霍芬男爵所说的原来值4万铜钱一亩的良田如今只值1千文(80分),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在这种背景下,土地贱卖乃成为必然。同治后期,江南因“荒田垦种乏人”,土地贱卖就十分普遍。当时买得土地的人被称为“自种”者。土地的贱卖,无疑又给新移民们提供了一个拥有“恒产”的难得机会。于是,在太平天国的硝烟散去的时候,出现在江南废墟上辛勤垦拓的新移民们开始东挪西借置业购产,为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产业而奋斗。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们在江南“田亩经界,改变旧形”的间隙中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了一小块土地,成为“江南小地主”。
与所谓的“江南小地主”相比,由移民引发的另一种经济变动则更具有时代性。曾经因战乱被逼入条约口岸的官绅、地主和商人,他们在条约口岸立足、发展之后,又会从鼓鼓囊囊的钱袋里掏出一部分闲置的钱款重返乡下,购置便宜得不能再便宜的田产,并以在条约口岸学到手的经营理念进行面向市场的开发,为市场提供源源不断的需求品。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己也摇身一变而为“工商地主”。譬如,江苏、皖南本不出产蚕丝,战后受对外贸易发展的推动,蚕丝的市场需求迅速放大,这些地方“往往辟良畴接湖桑”,大力发展蚕桑种植业,获利丰厚。另一个方面,随着条约口岸的快速兴起,那些生成于特定时势之中新的小土地所有者,即“江南小地主”,面对的是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经济环境,他们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越来越受到来自市场经济的直接或间接的刺激。这种刺激对他们来说包含着冲击和诱导双重意义,拥有地权的小地主因为更多的经济自主,会比寻常租佃关系下的农民更自觉地对这种刺激做出积极的回应。刺激和回应,把他们同近在咫尺的市场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了。他们在开始进行面向市场的经营和开发,这种市场导向使商品性农业在战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商品性农业的长足发展又势必导致小地主们的生产和生活不得不更多地仰赖市场。于是,战后的市场经济日益趋向活跃,由此又形成了另一种类型的“工商地主”。许多小地主由农产品贸易致富,19世纪后期的南浔镇以买卖蚕丝起家而“家财垒聚,自数万至数百十万者,指不胜屈”。可见,因发展商业性农业而发财的小地主,在战后的江南已不是少数。
太平天国战后的大移民,以及从他们中涌现出来的小地主和工商地主,随着岁月的推移,不断壮大,逐渐填补了由旧有人口在战争中的过量死亡所留下的巨大生存空间。他们在废墟上重建江南,并在这种重建的过程中成为江南的新主人。
苏杭的衰落:两个城市与一个时代
太平军战事对江南的浩劫性破坏,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江南传统的中心城市——苏州和杭州的衰落了。
苏州,位于太湖流域下游,处江、湖、海之间,枕江倚湖,兼有江湖之利,陆海之饶,隋唐时就已是东南巨郡都会,至宋、明、清时期,苏州经济繁荣,民殷物阜,科甲鼎盛,人文荟萃,被誉为“科甲之乡”、“东南财赋之区”,不仅成为中国最美丽、富庶、繁华的地方,而且是主导天下雅俗的地方,所谓“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苏州经济上的富庶与繁华,文化上的精致与优雅,使它成为江南地区当之无愧的中心城市。因此,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又常常成为全国视线聚焦的地方,即使是乾隆皇帝也无法抗拒它的富庶与繁华、精致与优雅组合而成的奇特魔力,面对江南的这种魔力,他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酸酸的。他既为江南所吸引,数度南巡,又觉得江南有一些他无法认同的东西,不失时机地刻意予以贬抑。乾隆皇帝的这种心理,哈佛大学的孔飞力教授在《叫魂》一书中有一段极精彩的刻画:
既恐惧又不信任,既赞叹不已又满怀妒忌,这便是满人对于江南的看法。在这个“鱼米之乡”,繁荣兴旺的农业与勃勃发展的商业造就了优雅的气质和学术成就。北京大部分的粮食供应,是经过大运河从江南运来的。因此,几百年来,帝国的统治者们便发现,他们需要不断地同江南上层人士争夺那里多余的粮食。同样令北京统治者感到头疼的,是如何才能建立起对于踞傲不逊的上层学界的政治控制。江南的学界精英所期期以求的并不仅仅是在科举考试中占有一席之地或获得高官厚禄。如果有什么人能让一个满族人感到自己像粗鲁的外乡人,那就是江南文人。面对这个久已存在的江南问题,在处理这种爱恨交织的关系时,弘历(即乾隆皇帝)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凡是满族人眼里最具汉人特征的东西均以江南文化为中心:这里的文化最奢侈,最学究气,也最讲究艺术品味,但从满人古板严谨的观点来看,这里的文化也最腐败。正因为江南文化有着种种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它才对满人的价值观念——那种弘历喜欢想象的价值观念——构成了威胁。如果满人在中国文化面前失去自我的话,那么,正是江南文化对他们造成了最大的损害。(注:孔飞力著,陈兼、刘昶译:《叫魂》,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94页。)
在北京统治者对江南的矛盾心理和暧昧态度背后,是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在社会经济和人文传统方面所具有的超强的辐射能力,这种辐射能力是任何一个其他区域所无法比拟和匹敌的。明清时期的苏州,以及以苏州为中心城市的江南代表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的极致。
作为“天下四聚”之一,苏州的富庶与繁华,对于农民造反者来说,当然也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诱惑力。当他们以席卷之势攻克武昌后做出沿江东下的战略决策的时候,内心里想的最多的大概就是江南的财富了,所谓“三江财富尤贼(指太平军)所觊觎”。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江南便成了攻防易守的战区。1860年5月,太平军决定东征苏州、上海,由李秀成统帅数万大军。于是,江南最富庶的地区亦沦为战区,到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兵锋所至,官绅、商人和地主纷纷携着逃跑。苏州是当时江苏省的省城,由巡抚徐有壬负责城防,对抗李秀成军。徐有壬和总兵马德昭出于城防的需要,颁布三道命令:“首令民装裹,次令迁徙,三令纵火”。三令一出,苏州向来万商云集市肆繁盛的金门、阊门一带,顷刻之间烟焰蔽天,日夜不息,城内外秩序大乱,号哭之声震天。时人曾作《姑苏哀》,讽刺当道:“清军十万仓皇来,三日城门闭不开。抚军下令烧民屋,城外万户成寒灰。健儿应募尽反颜,弃甲堆积如丘山。”(注:转引自李寿龄《匏斋遗稿》卷3,第6-7页。)城外是延烧不息的大火,城内则鸡飞狗跳、惊惶失措,守城兵勇见大势不好,四处焚掠,一派末日景象。
6月2日,李秀成军攻克了苏州,并以苏州为首府建立了太平天国苏福省。作为李秀成的“分地”,苏福省建立后,采取了一些稳定社会秩序的有效措施,苏州的商业重新出现了兴旺景象,所谓“百货云屯,流民雨集,盛于未乱时倍蓰”。但,苏州亦遭受严重破坏。太平军不仅摧毁了城市里的行会组织,也破坏了手工业工场和作坊,许多行业陷于停顿。据太平天国史专家茅家琦主编的《太平天国通史》称:一向十分活跃的行会组织完全被摧毁,行会董事大多逃散或死于战乱,丝经行、丝行商人的行会丝业公所的董事“遭兵四散”;水木作行会“自遭兵燹,前董均多物故”;刺绣业的锦文公所、剃头业的整容公所以及明瓦业公所、圆金业公所等行会,“公所房屋被毁无存”;小木公所“房屋被毁,所有各项帐目及行规等件,一并失去”(注: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下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5页。)。此后,苏州一直“是太平天国整个东南战场的指挥中心,又是太平军南下浙江、东进上海的基地,并以其强大的财力、物力,支援了太平天国后期的革命斗争。皖北沦丧后,苏州更成为天京赖以依托的后方和物资供应基地”(注: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下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0页。)。
但是,只要是战区,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恢复和繁荣。随着整个战局的大逆转,湘军由战略守势转入战略攻势,李秀成苦心经营的苏福省也就成了湘军、淮军的必争之地。在曾国藩的整个战略中,重点是天京会战,苏南和浙江是牵制战场,意在牵制李秀成的后方力量,减少围攻天京的阻力。但李鸿章、左宗棠抓住天京会战吸引李秀成主力之机,在苏南和浙江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使李秀成顿时陷入困境。1863年初,李鸿章统帅的淮军向苏福省挺进,李秀成军与之展开惨烈的大搏杀。
大搏杀开始以后,李秀成治下的苏福省的情况变得恶劣起来。到处是触目惊心的荒凉惨象,到处呈现出混乱、荒寂、悲惨的光景。
在这场大搏杀中,繁华的江南“尽成废墟”,田园荒芜,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和城市手工业被摧毁殆尽,人口锐减。据统计,1831年时,苏州府九县一厅,“实在人丁”340余万,到1865年只剩下128万左右。1863年12月苏州陷落后,李鸿章对苏州城进行“大清洗”,至少有3万太平军将士被押至刑场处死。据说,屠杀发生20天以后,抛满尸体的河道仍旧水带红色,地下3英尺深都浸染了鲜血。1865年1月13日《上海之友》报发表了一位外国商人从苏州到南京的沿途见闻:
在白齐文到南京去的时候(案:白齐文于1863年7月去苏州,8月到南京),南京和苏州之间一带乡间是可爱的花园,运河两岸十八里内全都排列着房舍,居民像蜂群似的忙碌着,处处显示出这些人民有理由可以预期到的繁荣景象。自苏州复归于清军之手后,这些房舍以及无数桥梁全都消失了。整个十八里之内没有一幢房子,四周乡间,举目荒凉。人民畏清兵如豺虎,一见就惶惶逃命。看不见男人,看不见妇女,看不见儿童,也看不见任何一头牲畜。……在通往无锡的路上,遍地荒芜,荆草漫生。……可是沿途布满了数不清的白骨骷髅和半腐的尸体,使人望而生畏。这里没有做买卖的船只,商业绝迹,无锡已成为一片废墟。……到常州府,沿途九十五里,仍旧是一片荒芜凄惨的景象,不见一个做工的人。遍地荒蒿,杂草没胫。……从常州府到丹阳遍地布满了白骨,不幸的太平军,更可能是无辜的村民,一定遭到了极其可怕的屠戮。我从丹阳前进四十五里,前进得越远,地方上的情况就越坏,一言以蔽之,整个情况是“一团糟”(注:呤唎著,王维周、王元化译:《太平天国亲历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66-568页。)。
浩劫之后,江南“几于百里无人烟,其中大半人民死亡,室庐焚毁,田亩无主,荒弃不耕”,苏州更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大破坏,经济上的富庶与繁华随风而逝,文化上的极致与优雅亦如梦幻般消失了。
和苏州的命运相似,受太平军战事的强力冲击,杭州从19世纪中叶开始加速地走向衰落,并最终促成了江南地区城市中心等级的重新调整。首先,杭州丧失了在以京杭大运河为南北命脉的古老商业网络中的战略地位。1853年,太平军占领江南地区时,封锁了大运河上的交通运输,切断了贯通南北的经济大动脉,清廷和商人只好发展途径上海的海上运输,这种变化导致了运河城市带的急遽衰落;其次,太平军和清军的战斗,加速了杭州城市衰落的命运。19世纪60年代初,太平军摧毁了杭州城,号称天堂的杭州,城市人口从80余万骤减至20万,一度仅剩下数万人。重要的是,杭州衰落之日,正是上海崛起之时。得益于破坏杭州繁荣的上述两个因素,以及在对外通商的刺激下,上海从过去普通的滨海县城,迅速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大都市(注:参见Liping Wang,Tourism and Spacial Change in Hangzhou,1911-1927,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1900-1950,Edited by Joseph W.Eserick,University of Hawai' I Press,Honolulu,1999.)。
上海的崛起:从江南的上海到上海的江南
苏州、杭州在太平天国战后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地处长江入海口的滨海县城——上海却因缘时会快速崛起,大踏步地向近代化国际性大都市迈进。从1860年代开始,上海迅速走向繁荣,并取代苏州和杭州,成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龙头。这种取代,是现代城市对传统城市的取代。因此,苏州、杭州的衰落和上海的崛起又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在长达10余年的内战烽火洗礼下,大量难民纷纷避入江南地区唯一的安全区域——上海租界,所谓“江浙两省绅商士庶丛集沪城”。这个“丛集”的过程,同时也是人才和资金向上海汇聚的过程,1860年上海租界人口激增至30万,1862年又增至50万,一度还曾达到70余万。另据最保守的估计,从1860年到1862年短短的两年时间里,至少有650万银元的华人资本流入租界。难民的大规模涌入,给上海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它为近代上海的崛起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资金、劳动力和需求市场。上海租界以一隅之地接纳来自四面八方的难民,成为难民的福地;而源源不断的难民则以他们的智慧、资金和技艺等给上海的都市化和社会经济的转型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他们与界内的外侨一起共同缔造了近代上海的初次繁荣。王韬说:“上海城北,连甍接栋。昔日桑田,今成廛市,皆从乱后所成者。”“当租界成为城市的主体的时候,上海的意义完全改变了,它不再是过去那个传统的棉花和棉布的生产基地,不再是普通的滨海小县城,而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中心,远东的国际商港。上海正在从‘江南鱼米乡’的那个社会模式中国游离出来,成为镶嵌在东西方之间的一块中性地带,一个新开发的商业王国。”(注: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此后,上海便步入了超乎常规的大发展时期。以外贸为例,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上海就取代了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1860-1900年,上海进出口总值平均占全国的一半以上,1864年占57%,1900年占55%,其中进口通常占六成以上。在转口贸易、国内埠际贸易方面,上海起了枢纽作用。从上海进口的洋货,有70%以上要运到内地其他口岸;从内地运到上海来的土货,有80%以上要出口到国外或运到国内其他口岸。转口贸易地区,以长江流域为主,占60-70%;其次是华北地区,再次为华南地区。至20世纪20至30年代,上海在全国的对外贸易和对内埠际贸易中的地位都处于特大中心地位,其外贸在全国贸易总额中占40%左右,1936年达55%。1936年上海的埠际贸易值包括转口贸易值为8、9亿元,占全国各通商口岸埠际贸易总值的75%(注: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外贸优势地位的确立又带动了相关产业包括航运、金融、工商业、信息乃至文化产业的飞速发展。19世纪中后期上海已成为中国的航运中心、外贸中心、金融重镇和西学传播中心,到20世纪30年代,更进一步发展成为集航运、外贸、金融、工商业、信息中心为一体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和集教育、出版、电影、广播、娱乐等为一体的多功能文化中心,并跻身国际性大都市的行列,成为仅次于伦敦、纽约、东京、柏林的世界第五大城市,有所谓“东方的巴黎,西方的纽约”之誉。
作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龙头,上海的崛起对整个江南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而言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江南地区固有的城市格局,而且加速了上海与江南腹地的互动,并以一种新的经济力量重构了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秩序和人文秩序。20世纪初期,就已有人把这种互动中的重构不无夸张地称之为“普遍的‘上海化’”。“普遍”两字用之于全国显然是言之过甚了,但有一点却是可以确认的,上海对江南地区的辐射力,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明显增强。以前是上海“城中慕苏、扬余风”,现在轮到苏、杭来沐浴“海上洋气”了;以前富庶莫过江浙,苏杭称雄天下,而苏州更执江南全局之牛耳,松江市面就曾以“小苏州”为荣,现在是“申江鬼国正通商,繁华富丽压苏杭”,以上海为枢纽,从南北两线展开的“扇形地带”,又伴着上海的节奏“起舞”,嘉兴、无锡、宁波等地,欲夸耀其市容商业繁盛,每每改以“小上海”称之。这种变化,从表面上看,是江南地区城市格局在近代前后的“主从倒置”,其实,在这种“主从倒置”的背后包含着极为复杂而深广的社会历史底蕴,它构成了中国区域现代化史上最亮眼的历史事件之一。
上海的崛起给江南地区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从市场网络到产业布局,从城镇格局到社会生活,受上海强有力的牵引,都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以上海为龙头的一体化趋势。此前的上海是江南的上海,此后的江南则成了上海的江南。且以江南地区城镇体系的演化为例,略加论列。江南地区的城镇布局向以苏州为中心,上海崛起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呈现出归向上海的重新组合,逐渐形成唯上海马首是瞻,以上海港内外贸易为主要联结纽带的新的城镇体系”(注:戴鞍钢:《港口·城市·腹地》,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140页。)。譬如,无锡、常州素以从属于苏州的米、布转运码头著称,上海开埠以后,它们与苏州的经济联系逐渐削弱,与上海的联系不断加强,进口商品及南北货,经由上海采购的常占无锡转口内销总额的70%-80%。1908年沪宁铁路贯通后,沿线城镇与上海的联系更加便捷,更加紧密。其他城镇如杭州及杭嘉湖地区城镇的进出口商品也大多直接纳入上海的货物集散渠道,“浙江的丝,不管政治区域上的疆界,总是采取方便的水路运往上海这个丝的天然市场”(注: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405页。)。至于上海周边地区的城镇,受上海的影响就更为显著了。与上海联系的疏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江南地区城镇的盛衰。“一部分以个体小生产者之间交换日用必需品或家庭手工业所需原料为基本特征的农村集镇的商业活动趋于衰败,代之而起的则是一批适应进出口贸易增长及城市发展需要的新兴市镇。”(注:戴鞍钢:《港口·城市·腹地》,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5页。)而且,这一类新兴市镇发展迅猛,1870年代以后,松江府属各市镇比“太平战乱”之前增加3倍,据统计,单苏州、杭州、嘉兴和松江4府所属市镇在同光年间就增加了110个(注:据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第109-117页所附《十九世纪中叶后江南新兴市镇表》统计。)。这样一批市镇的兴起,以及城镇空间的重新布局,是近代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变迁的一个显著的标志,有位外国学者形象地将这一区域称为“镶饰在老式长袍四周的新式花边”(注:R.H.Tawney,Land and Labor in China (London,1932),P.13.转引自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第108页。)。它表明江南地区城镇格局已由内向型向外向型逐步转化,这种转化又使江南地区卷入到世界市场的循环之中,并使它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先行区域。
收稿日期:2002-08-31
标签:太平军论文; 太平天国论文; 李秀成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江南论文; 历史论文; 清朝论文; 移民论文; 社会变迁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