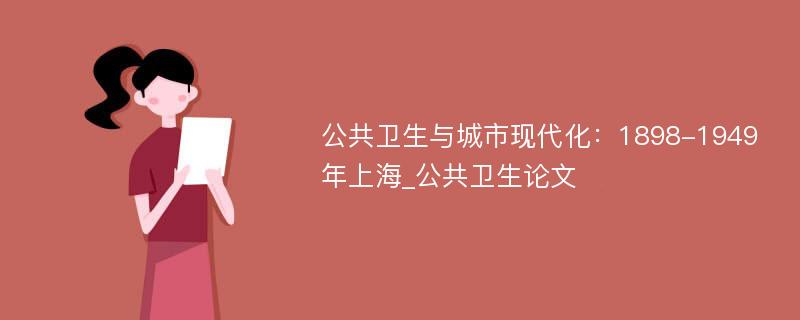
公共卫生与城市现代性:1898—1949年的上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公共卫生论文,上海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03—0097—05
卫生通常与健康联系在一块,同时公共卫生的社会意义还在于其与城市现代性紧密相连。本文试以近代上海为例,从卫生制度的形成、卫生的社会动员与整合、卫生与个体的文明习性养成等方面进行初步探讨。
一、“西力”冲击与城市认同:卫生制度的形成
公共卫生制度是都市文明的产物,近代上海公共卫生制度的形成,是在都市化发展的基础上,租界正向示范和反向刺激、政府和民众的民族意识觉醒、华洋冲突与合作等多方作用的结果。
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远东国际性港口城市,上海都市发展进程加快。都市化带来的人口积聚,使都市公共卫生面临严重挑战。由于上海与外界联系紧密,港口防疫体制常面临很大压力。随着卫生领域的西学东渐,政府与民众的卫生意识觉醒。如何应对日益凸显的公共卫生问题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风险,成为都市自身发展题中的应有之义。
租界行政当局基于自身安全与健康的需要,于1898年首先成立了正式的公共卫生管理机构,制订了一系列的卫生制度与规范,建造了公厕、垃圾箱等各项公共卫生设施,并逐步在卫生防疫、食品卫生、环境卫生、卫生统计等方面实施常规化、制度化管理,由此启动了近代上海的公共卫生事业,初步缓解了都市化进程中的卫生与安全压力。
在卫生管理模式上,租界强调疾病预防。如1927年3月,上海政治、军事形势稍形紧张,公共租界工部局随即召开特别会议,总董召集各董事、警务处、工务处、卫生处等共同商讨若是界内发生严重骚乱,如何处理,“倘遇有必要宣布紧急状态,已经做好哪些准备”,特别强调了如何在动荡中正常维持生活垃圾、粪秽及污水“三大事”的正常处理。[1](P683) 垃圾、粪秽、污水处理不当,是造成疾病流行、危害公共健康的重要因素,租界为此召开特别会议,并大加强调,可见其对界内公共卫生预防重视之一斑。
面临租界在卫生领域的挑战,华界政府与民众做出了积极的回应。租界的卫生规范与制度化管理,给华界政府以良好的正向示范,激发了华界政府的民族意识与竞争意识,在卫生领域采取了相应的建设和管理措施,如内地自来水厂的开设、突发疫病的应急处理等。上海有识之士为维护民族尊严,也视公共卫生建设为城市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上海人要在上海谋生活,要在上海与外国人争面子,必定要办公共卫生”[2](P106),“我们很想重整内部清洁卫生,不失我们大国的风度”[3]。各路精英为此纷纷倡导仿效,并身体力行。1929年7月1日华界沪市建设讨论会上,市长张群总结自治时期的包括卫生事项在内的市政建设时,指出其无较大成绩,“外人常藉口批评我国之口实,是诚属痛心耻辱之事”。[4] 华界防疫体系的建构也是多基于疫病事件的触动,更多的是一种应急行为。即便抗战后的上海市政府,也是倾向于强调公共卫生对都市形象和秩序的维护功能。1946年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不时向担负公共卫生建设与管理之责的机构强调:“上海为东方第一大埠,国际观瞻所系,负责市政者必须注意市内之整洁,以保市民之安全,而免贻笑于外邦”。[5] 政府与民众对租界卫生示范的逐渐理性认同,客观上推动了华界公共卫生的起步与发展。
租界当局的公共卫生管理,又是以维护自身安全为核心的,部分卫生政策的制订带有明显的歧视性,从而给华界官方和民众以反向刺激。如规定对租界外侨食用肉类实行严格检验,而对运往华界的肉类一律免检;更为严重的,租界有时打着卫生的幌子进行界域的扩张,在上海这一条约口岸环境中,“公共健康为外国市政当局在中国土地上的扩张提供了重要途径”。1874年和1898年爆发的两次四明公所血案,成为法租界面积大幅度扩张的重要契机,其中一个重要的借口便是“在发布卫生条例上大做文章”,这些条例为剔除不卫生的会馆棺柩存放处提供了具有科学说服力的必要借口。[6](P118) 这侵害到中国的主权,给华界民众以极大刺激,激发了华界民众的民族意识和自强意识。华界官民多方筹措资金共建内地和闸北自来水厂,反对水厂出卖租界,即是典型案例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近代上海一度是“一市三治”、各自为政的政治格局,给统一的卫生管理带来了很大挑战,造成部分卫生设施不必要的浪费。如自来水管的重复铺设、水质、饮食卫生标准的差异,阻碍了公共卫生的全面发展和都市文明的提升。租界收归之后,上海卫生行政事权统一,本是公共卫生发展的大好时机,然而,由于抗战时期公共卫生设施遭到很大破坏甚至被摧毁,加之资金和人员的紧张,上海公共卫生的战后恢复与重建面临相当的困难。
二、卫生的民间动员与社会整合
公共卫生引发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民间社会力量在近代上海公共卫生的发展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是近代上海公共卫生社会化的重要表征。
面对租界卫生示范的刺激、都市疫病的流行、环境卫生的恶化和城市自身发展的需要,各种社团组织为维护民族大义、或基于共同利益,不仅纷纷参与政府组织的卫生建设和卫生运动之中,而且独立开展了公共卫生宣传工作。他们采取口头演讲、文字宣传和卫生运动等各种各样的方式,引起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市民踊跃参加社团举行的清洁运动、劝止吐痰运动、健康比赛等,加强了市民的疾病预防意识、健康意识、卫生意识与公共意识,促进了都市社会的凝聚和整合。
与此同时,都市社团大力进行了时疫救治工作。每逢时疫易发季节,他们便开设时疫医院,并逐步将其从临时设置改为部分常设机构,在疫病流行控制之后不再拆散,继续为贫民患者免费诊治。时疫医院的兴办及开设的常规化,是时疫患者的福音,为时疫的控制做出了巨大贡献。[7]
社会力量的多元参与,还表现在水、厕及垃圾处置的市场化运营的试行上。例如民营自来水厂的设立、私有公厕的出现、垃圾和粪秽的承包清运等,均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近代上海社会力量的活力。
社团组织开展的公共卫生宣传与时疫救治工作,各种社会力量在水、厕及垃圾等领域的多元参与,不失为公共卫生治理的一种标本兼治之策。社会力量多元参与体现了近代上海公共卫生治理中的社会化倾向。在给予群众以实在好处的同时,对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完善亦是一个相当的促进,与政府形成了一定的互补与互动。
社团卫生宣传中,有相当部分的是医学、卫生等专业性社团,提供了良好的公共卫生治理建议和措施,如在1930年行政当局的成药规则制定上,上海市新药业同业公会由于熟悉药业情况,提出了22条中肯的修缮建议[8](P4),推动政府卫生政策制定的科学化。社团对政府措施不力的批评,造成了一定的社会舆论,迫使政府进行部分卫生改良,有利于加强政府公共卫生政策的执行力度。
社会时疫救治一定程度地缓解了政府资金、人力的不足及卫生资源分配上的不公。在许多政府力所不及之处,社会组织开设临时时疫医院,对贫病者施行免费诊治。而且各种慈善救治,多因出于自愿,故在服务的态度上较为友善,往往让患者和预防注射接种者深怀感激,利于公共卫生的宣传和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
当然,社会的卫生宣传和时疫救治亦存在资金来源欠稳和不足的缺陷,影响到公共卫生事业的推进,同时需要政府的支持。对此行政当局也乐于一定的支持,如市政府颁布专门的《捐资兴办卫生事业褒奖条例》,其中规定凡私人(包括外国人)或团体在沪捐资兴办公共卫生或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医疗事业均受政府嘉奖。具体褒奖办法分为四等。① 以政策性鼓励来拉动社会各界积极赞助公共卫生事业的建设。政府与社会基本上能维持一种较好的合作关系。
社会力量在公共卫生设施市场化运营的实践中,也表现出一定的弊端。如民营的闸北自来水厂水质出现问题;厕所、粪秽承包常为个别大户所掌控,以致产生垄断、卫生恶化,部分私有公厕难保洁净[9];垃圾承包商在载运过程中偷往江河倾倒垃圾等等,给公共卫生造成了消极影响,危及到公众的健康和利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缺乏政府合理规范和社会有力监督的条件下单纯的市场运作出现失灵的可能。市场的正常运作、政府与社会的互动须以制度为基础。因此,政府管理手段的制度化、管理职能的具体化对公共卫生的良性运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应是一种走向管理的市场化。
三、公共卫生与都市文明
公共卫生的近代化又是城市文明化的重要过程,近代上海的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推动了上海都市文明的进程。
公共卫生机构的设立和卫生规章制度的颁布及传播,社团不遗余力的公共卫生宣传,推动了都市社会习俗的改良,有力地规范了市民的日常生活行为,培养了市民的公共卫生意识,激发了市民的参与意识和文明意。市民卫生意识的觉醒又促进了他们自觉地参照卫生规则,广泛参与公共卫生领域的各项实践,鼓舞了上海居民向卫生当局控告城市环境问题使他们的健康遭受到的威胁,为政府的合理化决策提供了宝贵信息。
政府和社会力量对公共卫生设施的共同投入,推动了上海市政的建设,建造了供应净水的供水系统、综合化的近代医疗设备、控制社会疾病发生的公共当局和管理机构。诚如公共卫生史家程恺礼所言:“19—20世纪在中国城市中设置的医疗与卫生基础建设,这些发展很大一部分是由像霍乱这种‘一般和特别的流行病’所促成。”[10](P783) 自来水的推广,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更是增进了民众的健康。“随着上海供水网的形成,并随着它对租界和华界迅速发挥着作用,对上海民众健康的最大威胁清除了”,“上海人平均寿命的提高直接与清洁卫生的自来水普及有关”[11](P353)。道路的扩充和清扫、里弄卫生的整顿、公厕修建、排污管道的安置等,方便了民众的生活,直接促进了都市形象的改观和都市物质文明的发达。在社会各界的参与和支持下,政府制定颁布了系列卫生法规,推动了都市管理法制化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言,公共卫生本身就是一套科学的制度,是都市制度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与社会在公共卫生领域中较为良性的互动,加快了上海市民社会的发育生长,促进了上海都市文明精神层次上的提升。劝止随地吐痰运动的开展,使民众卫生习惯、文明意识及疾病预防意识明显提高。如1932年全国性霍乱大流行,波及18个省,死亡惨烈,“即概略计算,今夏全国死于虎疫(霍乱)之人民,已将以数十万计”[12],就其影响区域和死亡人数而言,堪称民国时期最大的瘟疫。[13](P285) 上海虽然传播最早,同时遭受洪水泛滥和日军入侵两大灾难,但死亡率在全国最低,为7.4%[14]。这与上海采取广泛的预防注射密不可分。据记载,上海有100万以上,即三分之一的人口接种了霍乱疫苗,加上清洁的供水和有效的住院措施,才取得了全国最低的死亡率[15](P462)。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上海在民众的防疫注射上,与全国其他大小城市普遍的强制注射相比,“似乎没有采取强制措施”[13](P291)。在疫病面前,上海社会维持了特有的一种稳定[16](P160)。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租界,“天花之预防似已为界内全体居民深切了解”[17]。大可反映出民众公共卫生意识的提高。
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对城市生活某些习俗的改革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例如火葬方式相对土葬通常要卫生,利于防止传染病的传播,现在一般都把它当作一种卫生习俗来提倡,但是传统的丧葬习俗使得卫生的火葬推行困难重重。不过伴随着公共卫生的宣传与发展,近代上海火葬有了相应的推广。如前所述,还在19世纪末法租界与宁波旅沪同乡们因棺木堆积的停葬而发生流血冲突,尽管其中有复杂的原因,但至少有一点可表明当时华界民众对火葬方式是难以接受的一件事情。不过到了1927年静安寺公墓购进新式大功率煤气火化机炉时,除外侨外也有不少华人光顾[18](P17)。1934年市政府以传统的丙舍浮厝占地多且不卫生而颁布《取缔丙舍规则》,要求迅速火葬处理,受到广大社会团体和舆论的支持[19](P6)。“值兹酷暑,丧家惨遭不幸之余,于料理善后,每感手足无措,连日若运动家孙硕人、方镜湖等各丧家,委托办理殡仪,均认为非常满意,既节光阴,又经济便利,为各界称道”[20]。公墓的兴起亦可反映火葬市场的兴盛,根据《上海市年鉴》统计,至1935年仅在市卫生局注册登记的公墓就达18家之多[21](P37)。公墓、火葬场、殡仪馆之多,近代上海在全国处于领先位置,既是公共卫生发展的要求,又是都市文明的有力体现。
公共卫生的发展推动了都市民众公共意识、健康意识和安全意识的增长。根据史料反映,20世纪30、40年代出现了大量市民举报控告垃圾乱倒、随地便溺、住宅区私设影响环境卫生和住户健康的作坊等现象。有曹新发等30余人联名控告浦东张家浜大华烧胶厂,“设备欠周,污水臭气四溢”;有控告杨金发等人在徐家汇三角地后的潘家宅,私建制造硫酸的厂房,“终日恶气四溢,并私积大量硫酸公共危险物品”;有反映长宁路芦薛宅的张远明等人合设牛皮厂,将牛皮垢物倾入河浜等。诸如此类的事例不胜枚举,基本上反映出市民对社区环境卫生的关注,同时也体现了卫生机构成立、卫生法规的出台为社会公共卫生的参与提供了可能。卫生机关对来自市民的反映基本上能做出相应的回应,派出卫生稽查人员调查,情况属实者按照相应法规进行惩处。如上述张远明等人就各被罚处一千元[22]。市民这种广泛的卫生信息提供及上述都市社团的积极参与,与政府当局形成了一定的互动,不仅推动了都市公共卫生的进步,而且表明都市公共性的增长。
总之,公共卫生与人群的健康直接相关,是人类一个基础性问题。早在20世纪30年代,身处上海的医界名士陈邦贤就发出这样的感慨:“没有电灯、没有电话、没有交通、甚至没有警察,都可以支持两三天,可是一天不排除污秽,马上便发生很大的危险了。”[23](P10—11) 随着都市化发展,公共卫生愈显重要。它将越来越多的人们牵扯在一起。在近代上海都市化的进程中,众人纷纷组织社团,参与到政府的卫生治理之中,使公共卫生逐渐走向多元共治的格局,遂成社会化趋势。公共卫生是都市文明的一大载体,反映了近代上海的新变化。在高度分化的近代上海,公共卫生把众人的利益又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维系都市人群的纽带之一。因此,租界与华界、国家与社会的合作也非常明显,他们的共同参与,推进了近代上海都市文明的进程。
此外,公共卫生“与国家之兴衰,有莫大之关系,盖国家兴衰,以人民之强弱为衡,而人民能否强健,则以公共卫生为准”。“一个国家的文明与野蛮,就是清洁和污秽的区别”,“卫生是养成健全民族的基础”。“我国今日民穷财尽,由于外国经济之侵略,而经济侵略,何以施之于我,而我竟无术自强,探本穷源,亦因未能注重公共卫生所致。”[24](P1—2) 因此,公共卫生问题绝非一个简单的健康问题,还与国家、民族、政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由于近代上海租界的存在,使得公共卫生问题更加复杂化,产生了租界与华界在卫生管理上的冲突甚或利益之争。国家亦则力图借用公共卫生来整顿社会秩序,实施社会整合。
近代上海公共卫生,已是世界公共卫生体系链条上的重要一环。近代上海公共卫生的变迁与都市的发展息息相关。既是都市发展的必然要求,又是都市文明的象征和体现。
注释:
① 奖状分为四等,由省政府或直辖市政府给予;奖章分金质、银质两种,由卫生部给予;匾额由国民政府给予。捐资给奖标准:30—50万元发四等奖状,50—100万元发三等奖状,100—200万元发二等奖状,200—500万元发一等奖状;500—1000万元发银质奖章,1000—5000万元发金质奖章;5000万元以上发给匾额。见《捐资兴办卫生事业褒奖条例》,上海档案馆藏,Q1—16—64。
标签:公共卫生论文;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预防医学论文;
